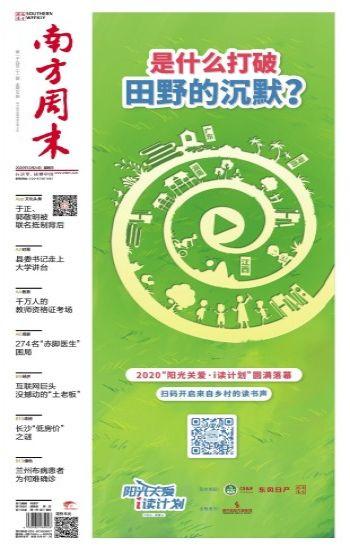特朗普“毁约退群”,拜登“返群”在即?
南方周末记者 施璇

2020年11月7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的支持者们在纽约街头游行庆祝胜选。新华社 ❘图
★“特朗普总统在房地产行业拥有较长的从业经验,只有双边关系才会让他感到舒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斯科特·米勒(Scott Miller)进一步解释说,“多数房地产谈判都是在买方和卖方之间进行……他(执政后)将美国看作是一种资产,不愿这种资产在多边场景下遭到稀释。”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近日表示,要在上任百天内尽可能多地修复损失,尤其要撤销特朗普签署的一系列“退群毁约”的行政命令。
“特朗普入主白宫三年多,还未提出他的外交政策。”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近日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批评说,“现在是时候给它命名了,就叫‘退出主义。”
从2016年美国大选至今,特朗普政府都在奉行“美国优先”为主旨的外交政策,带领美国从至少13个国际组织或条约等国际机制中退出,他威胁过要退出的“群”则更多。
外界预测,随着当选总统拜登的上台,这种“退群”局面或将会发生逆转。2020年11月24日,拜登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介绍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团队时表示,“美国回来了”,并准备再度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他还承诺,就任后将摒弃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政策。
“美国回来了,多边主义回来了,外交回来了。”由拜登任命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Linda Thomas- Green-field)也公开表示。
“处处留下残骸”
在2016年竞选期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就曾多次对国际组织和相关条约进行公开抨击。
“所有过时的、不必要的、对美国工人不好的或和美国国家利益相悖的规定都将被完全废除。”特朗普认为,北约组织是“落伍的”“若解体,就解体”,《巴黎气候协定》是“对美国企业不利的”“将美国的能源使用权交给外国官僚控制”;联合国更是“一场政治游戏”“没有解决过任何问题”。
在2017年1月的就职演说上,特朗普再一次痛诉多边合作让美国走上错误的道路,“几十年来,我们以牺牲美国工业为代价,让外国工业富裕了起来……我们让别的国家富裕起来,却让自己的财富、力量和自信都逐渐消失。从此刻开始,美国优先。”
上台后,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论”的第一步就是“退群”。2017年1月23日,他正式进入白宫办公的第一天,就签署行政令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该协定的签署国包括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它们的经济体量大约占全球GDP 的40%。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被视为美国巩固其跟亚太地区盟友关系的重要黏合剂。特朗普则将其视为“糟糕的协定”,不仅伤害美国制造业,还会带来“潜在灾难”。
三年多来,特朗普以“使他国受益,对美国不公”为由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并威胁退出万国邮政联盟、《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等;他还以“存在反以色列偏见”为由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停止资助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特朗普还以伊朗不履约和以色列反对为由退出《伊核协议》、以俄罗斯不履约为由退出美俄《中导条约》和《开放天空条约》。
特朗普看似果断利索的“退群”举动之后,却没有出台任何替代的解决方案,以至于反“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前特使布雷特·麦古尔克(Brett McGurk)讽刺说,“如果说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有什么一致性的话,那就是处处留下残骸。”
“从原则上来说,因为协议有缺陷或以缔约方违反协议为由合理地退出某项协议的解释是可以被接受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表示,“但所有协议都难免不完美……至少到目前为止,鲜有证据表明退出这些协议会迎来更好的选项。相反,作为一种外交政策,这种做法正在危害美国的繁荣、安全和影响力。”
特朗普认为,“退群”使盟友不得不重新评估美国的可靠性,进而使其获得更大的自主权。
“美国当然有权从各种宏大的战略承诺中退出,但这是以降低全球影响力为代价的,”美国《大西洋月刊》文章分析认为,“特朗普无休止地展现单边主义,只会加速削弱美国的实力。”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前(2020年4月20日),一项针对12个州的民调显示,大约56%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让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更加不被尊重。
“退群”思想溯源
特朗普的思维方式和执政理念不同于美国传统的政治精英,他的“退群”成瘾被认为与他出身商人的经历有关。
“特朗普总统在房地产行业拥有较长的从业经验,只有双边关系才会让他感到舒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斯科特·米勒(Scott Miller)进一步解释说,“多数房地产谈判都是在买方和卖方之间进行……他(执政后)将美国看作是一种资产,不愿这种资产在多边场景下遭到稀释。”
查理·拉德曼(Charlie Lader-man)和布兰登·西姆斯(Brandan Simms)也试图从特朗普的人生轨迹中寻找答案,二人在所著的《唐纳德·特朗普:一种世界观的形成》中写道,“在特朗普出生的1946年,美国的力量前所未有的强大。”
“在特朗普的脑海里,有很多固定思维都来自于上世纪50年代。”美国驻英国前大使金·达洛奇(Kim Darroch)也认为,“这其中包括对美国独霸时代的憧憬:煤矿的工作是满负荷的,生产的是人人都会买的美国产品。在某种程度上,‘让美国再次伟大(特朗普的竞选宣言)就是要重现美国当时的黄金时代。”
1987年,特朗普还是一名房地产开发商,他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波士顿环球报》等美国主流媒体上购买整版广告,呼吁美国政府“应该停止为那些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国家出钱。几十年来,日本和其他国家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
2016年竞选前,特朗普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又抱怨说,美国正在为别的国家埋单,本国经济却因此被削弱,“如果美国是一家公司,它早就破产了。每年,美国为日本、沙特等国的防务花费两千亿美元。”
上台后,特朗普对于多边主义的厌恶和排斥变本加厉。
“特朗普主义就是想和世界脱离,但又不愿意接受随之而来的权力损失。他想让美国成为帝国,但又不承担殖民统治所带来的麻烦。”美国《大西洋月刊》评论说,“这些矛盾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处处可见,它产生的结果就是偶尔的胜利、出人意料的后果、大量的破坏和无聊的战略停滞。”
从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到“美国优先”
从美国外交史来看,“退群”并不是特朗普的专利。冷战时期,里根总统也曾以维护海洋霸权利益为由拒绝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还曾以腐败和亲苏立场为由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1年至2009年,共和党总统小布什在其任期内更是连退三“群”,包括拒绝签订《京都议定书》、退出《美苏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催动特朗普做出“退群”决定的“美国优先论”思想更不是他的独创。“美国优先论”可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是共和党人当时提出的竞选口号。此后,“美国优先论”开始与孤立主义如影随形,它在安全政策上主张不干涉原则,在经济上则倡导最大程度地限制与外国的交流合作。
时隔百余年后,美国政治评论员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又一次将“美国优先”作为2000年大选的竞选口号。那一年,同样在参加总统竞选的特朗普则攻击布坎南为“希特勒的爱慕者”。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在2016年的大选中重新拾起布坎南的“美国优先论”,并将其作为外交政策的灵魂。
不过,特朗普的“美国第一”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孤立主义,他的政策更接近单边主义。英国伦敦大学美国文学系教授莎拉·丘奇维尔(Sarah Churchwell)认为,“他代表了某些美国人的思维方式,那种思维方式根植于深远的历史。”
二战后,美国建立了以多边合作国际机制为基础的霸权秩序。其间,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北约等国际机制应运而生,成为美国治理和控制国际社会的重要抓手。
“这些机构和多边主义领导风格,对美国赢得冷战至关重要,从而造就了一个空前的、全球相对和平与繁荣的时代。”美国驻联合国前大使、高级政策顾问亚历克斯·帕斯卡尔(Alex Pascal)直言不讳。
多年来,奉行多边主义一直是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共识。2012年,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的民调表明,两党的支持者对多边主义持认可的态度,但也有一定的分歧:共和党人更重视主权的价值,而民主党人则更关注如何通过多边合作来解决个体存在的脆弱性。
“在特朗普执政下,这一共识出现了破裂。”布鲁金斯协会国际秩序和战略项目高级研究员托马斯·莱特(Thomas Wright)认为,“特朗普总统不断质疑盟友,怀疑其在亚欧和中东前线的军事存在是否有效,并对民主国家间的合作表现得不屑一顾……到目前为止,他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多数共和党人的认同。”
2020年9月17日,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就两党支持者的对外政策进行民调,大约有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应该积极参与世界事务。其中,民主党人赞成国际主义、外交及合作,强烈主张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来解决全球问题;共和党人则倾向于独立自主,不愿支持国际组织参与解决问题。
返“群”在即?
从孤立主义到“美国优先”,从单边主义到多边主义,美国外交再一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
“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以及与各国交流方面,拜登是最熟悉外交的美国总统。”莱斯大学研究总统制方面的学者道格拉斯·布林克力(Doug-las Brinkley)认为,“没有人像拜登这样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
从1972年首次当选参议员到2009年被任命为副总统,拜登还两次担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不仅亲历了数十年来重大国际事件,至少还与全球50多个国家的150名领导人会面。
2020年11月24日,拜登首次公开他的6位内阁成员。其中,两人将会负责拜登政府的外交工作,他们是被提名为国务卿的托尼·布林肯(Tony Blinken)以及被提名为国家安全顾问的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
二人都是美国外交领域的“老手”,均在奥巴马政府担任过高级职务。布林肯和拜登的合作可追溯到20年前,沙利文则在2015年的伊核协议谈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在拜登担任副总统的奥巴马政府中担任国家安全顾问。
“这个团队反映了一个现象,即美国回来了,准备领导而不是抽离这个世界。我们将再次坐在首席位置,准备对抗我们的对手并且不排斥盟友,准备捍卫我们的价值观。”拜登在当天的组阁亮相中信誓旦旦。
受到拜登提名的国务卿布林肯也强调,“美国无法单独解决全球面对的问题,我们必须同其他国家合作。”
“特朗普持续不断地对国内外的规范和制度发起攻击。如今,美国要做的首先是要服别人,它可以再次领导世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艾伦·大卫·米勒(Aaron David Miller)和理查德·索克利斯基(Richard Sokolsky)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网站上撰文提出质疑,“但美国如何能够领导一个它不再统治的世界?”
文章还写道,过去的四年里,美国不再是那个世界霸主,美国的民主已经被玷污;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不力处理损害了美国能力的声誉,“退群毁约”更是让人们对美国的信任支离破碎。与此同时,世界的形势也发生了巨大改变,亚太地区的美国盟友都在走自己的道路,欧洲盟友也在寻求着更大的战略自主权。
“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会跟拜登合作,欢送特朗普的‘反复无常主义,”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莱特对未来的预判仍难掩纠结,“但盟友们对事情的走向总会有挥之不去的疑虑。”
“简单来说,美国在许多问题上已经失去特别地位了,它可以提出问题却无法解决问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两位研究员提醒道,“美国的外交政策设计者需要以审慎、智慧和谦逊的态度行事。最重要的是,不要只看到他们想要的世界,而是要看到世界的实际情况。”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近日还发誓,要在上任百天内尽可能多地修复损失,尤其要撤销特朗普签署的一系列“退群毁约”的行政命令。
最近,美国前国务卿约翰·福布斯·克里(John Forbes Kerry)被拜登委任为气候变化特使。克里对《纽约客》杂志表示,上任之后,拜登准备立刻重返《巴黎气候协定》,与世界卫生组织重新谈判以形成应对大流行更有力的举措,并计划延长与俄罗斯仅存的军控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拜登政府还希望和英法德及中俄在《伊核协议》上加强合作。
从拜登的外交团队及其主张来看,新一届美国政府将在外交上重返多边主义。英国《卫报》评论认为,重返多边主义之路并不容易,尽管特朗普留下来的一些宿怨比较容易解决,但最棘手的问题将是来自美国国内的压力,尤其是若共和党保住了对参议院的控制权,它可能会阻挠拜登的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