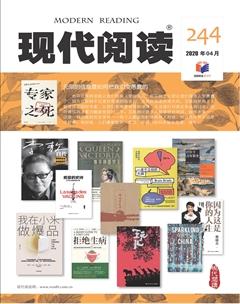帕特农神庙


勒·柯布西耶,20 世纪法国伟大的建筑师,也是优秀的作家、画家和城市规划大师。1911年5月,年轻的勒·柯布西耶开始了他为期5个月的东方旅行,途经中东欧、巴尔干、土耳其、希腊和意大利。
我心里涌动着一股激情。我们是在上午11点到达雅典的,不过我想出种种借口,不想立刻就去“那上面”。最后我向好朋友奥古斯特解释,我不会与他同上卫城。因为我心里有事,感到焦虑、亢奋,他最好把我留下,自己先去。于是我整个下午都泡在咖啡馆,阅读从邮局取来的一大包邮件。最早的邮件寄到这里有5星期了。然后我就在街巷里乱转,等待日头西落,计划到“那上面”去结束白昼,然后下来只需上床睡觉就行了。
雅典卫城一直是我们的一个梦想,虽说我们没想过怎样实现它。我也不大明白,这个小山冈为何就体现了艺术思想的精粹。我知道那些神庙美在什么地方,我承认其他任何地方的神庙都没有这样独特非凡,我早就同意这里保存了神圣的标准,是所有艺术批评的基础。为什么是这里的建筑,而不是别处的?我希望是这样:这里的一切有逻辑,都是按照最简洁最不能省略的数学公式设计出来的。有时并不情愿,却还是被带到这里。为什么我们现在把心带到卫城的山冈上,带到神庙脚下?在我心里,这是一个无法解释的问题。
……
帕特农那巨大的身影一出现,就让我挨了当头一棒似地愣住了。我刚刚跨过神圣山冈的山门,就看见孤孤单单、方方正正的帕特农稳立在眼前,用那铜色的立柱高高地举起它的石头楣构、石头檐额。神庙下方,有二十来级台阶充作基座,将其拱抬。天地之间,除了这座神庙,以及饱受千百年损毁之苦的石板阶地,别无他物。这里也看不到半点外部的生命迹象。作为唯一看得见的存在,远处的彭特利库斯山是神庙这些石头的提供者,至今山腰上还留着当年采石的创口,而伊米托斯山则通体披着大富大贵的紫红袍。
神庙下方的台阶太高了,不是为人类度身打凿的。上了那些台阶,我就踏着第四与第五根石柱之间的中轴线,进入神庙大门。我转过身,从这个从前只留给诸神和神职人员的位置,把整个大海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尽收眼底。大海被晚霞烧得彤红,远山已经罩上阴影,很快就会被日头这个大圆盘咬住。山冈的峭壁和山门石板地上高耸的神庙,遮掩了所有现代生活的痕迹,突然一下,两千年的历史就被抹掉了,一首粗粝的诗一把将你攫住。你把头埋在掌心,无力地倒在神庙的一级台阶上,听凭那诗将你猛烈地摇撼,于是你周身开始震颤。
夕阳将把它最后一道余晖投在这陇间壁和光滑的过梁上面,穿过立柱之间,射进前屋后侧敞开的门。阳光唤醒了躲在顶盖塌陷的神殿深处的阴影,可惜很快就弥散了。立在神庙北面的第二级台阶上,也就是立柱止步的地方,我顺着第三级台阶的水平线望出去,看到了爱琴海湾的那一边。在我的左肩,耸起一道想象的高墙。那是一根根立柱上鲜明的凹槽不断重复,才形成了这种虚拟的印象。它像铜墙铁壁一样坚不可摧,而托檐石滴水,就像铜墙铁壁上的铆钉。
山冈顶部的轮廓是封闭的,用团团转转的台阶将神庙围得水泄不通,并把神庙那参差不齐、排列紧密的立柱向天空投去。通往帕特农的山路陡峭,台阶是在山岩上直接凿出来的,这成了游览路上的第一道障碍。不过这还算不了什么,悬突于台阶之外的大理石高坎,才是最难攀登的。神职人员从神殿里出来,站在门廊下,侧旁背后都感受到大山的怀抱。他们的目光从山门上方平射出去,直达大海和临海的远山。帕特农耸立在一个小港湾中段的幽深之处。太阳从早到晚,不停地描画自己移动的路线。傍晚,气温炎热,光线就在神庙的中轴线上衔接大地。高台周围嵯峨的石山自有本事,把一切生命迹象剔除得干干净净。敏捷的精神飞到一个不可能再造的过去,惊喜之余,便一头扎了进去。即使这些外在现实——那海,那几座神庙,那山,那所有的石头,那水——即使它只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大脑一时的英雄般的梦想,也是美丽的。多么神奇的事物啊!
身体的感受非常舒畅:深吸一口气,舒展了胸腔。让欢悦推着你在裸露的、没有了昔日铺路石的岩体上行走,并让你由欢乐而生出景仰,推着你从智慧女神密涅瓦的神庙走到雅典王厄瑞克忒翁神庙,再由那里走到山门。从山门门廊,看得见帕特农在其稳坐高处的实体内,将水平额枋的影子投得很远,并将自己的西立面盾牌一样迎向这片协调的景色。神殿上方残留的一段饰带,雕刻着敏捷的骑士奔驰的画面。我的眼睛虽然近视,却也看见他们在那高头策马疾行,就和近在手边一样清楚。浮雕凸起的厚度,与承载它们的墙体比例十分贴合。8根圆柱服从一个一致的法则,一齐从地面冒出来,似乎不是被人一截截垒起来的,而是让人以為它们就是从地心深处长出来的。它们开槽的表面猛烈地上拉,把眼睛引向无法估量的高度,在那儿,光溜溜的额枋压在托石之上。一排滴水下面,陇间壁和三陇板的组合把游人的目光带往神庙的左转角——对面方向最远的柱子,使得他一瞥之间抓住一个体块,一种从下到上,以机器主义者所能做到的精确数学笔直切割的巨大几何体块。而西面山花的尖部标志着这一片空间的中心,其与山海日月的同在,强化了立面以及所朝方向的亘古不变。我认为可以把这种大理石与新铸的青铜来做比较,除了这样来描绘大理石的颜色之外,还希望青铜一词能让人想到这座奉一道威严神谕而建造的大厦里那轰然的鸣响。这片废墟含有那么多谜,让人无法理解,它就像一把锋利的铁锹,不断掘宽心灵感觉与理智衡量之间的鸿沟。
离那里百来步,有一个为桀骜不驯的巨神接受的存在,那就是有着4张面孔的快乐神庙,即厄瑞克忒翁神庙。它坐落在四面光墙的基座上,周身开满大理石花卉,有血有肉,朝你微笑。
其风格是爱奥尼亚样式——而额枋是波斯波利斯式的。昔日曾有人说它是用黄金镶嵌宝石、象牙和乌木建筑的;庙宇的亚洲趁它认为能够让人开颜一笑的时候,出其不意但又诱人地将一丝困惑投入这道自信的目光。不过,谢天谢地,时间自有其理性。我向眼前恢复了这片单一颜色的山冈致敬。在此,有必要指出6个女雕像的神态。她们都穿着衣服,面对上文描述过的帕特农神庙,托着石头齿饰楣构。这是阿提卡地区首次出现的。这些女子格外严肃,似在沉思,但是身体僵直,看上去似乎在微微发抖——也许此处最最具体地表现出了显赫的权势与威风。于是乎,有4张面孔的快乐神庙给每一边天空呈现的是不同的面容。雕刻着睡莲和茛苕叶的饰带,与棕榈叶这超自然的素材合在一起,装饰着神殿。额枋上清晰可见的榫孔,证明上面曾经安装过一些载歌载舞的女雕像。那些刻有浮雕的大理石板材肯定藏在哪家博物馆里,但到底是哪一家,我却记不起来了。而在神庙北面,巨大的陡岭上,笔立着由产自比雷埃夫斯城的石头砌就的围墙,石块其间夹杂着一截截古代砌柱子用的鼓形石墩。至于这个会让人油然生出伤感的四柱前廊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我就不清楚了。不过心情平复之后,我还是愿意在新砌的石墙保护之下走回山门,在满地的残石断柱之中,去解读帕特农。
当遗址看守者的哨声把我们从梦境中拉回来,我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我曾说过,这个时候,山门下已是夜色初起,一片苍茫。
(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东方游记》 作者:[法]勒·柯布西耶 译者:管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