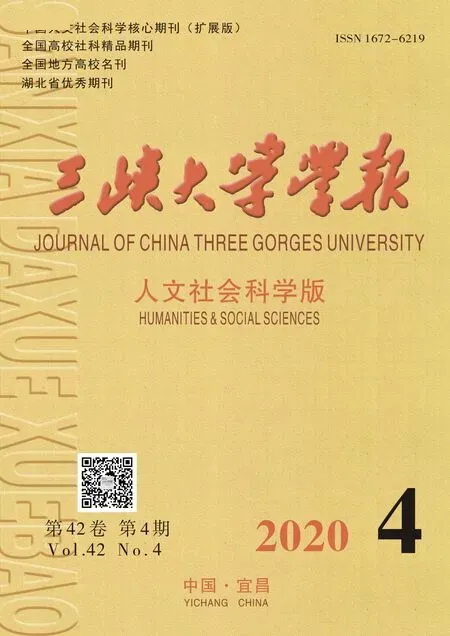长阳南曲不唱长阳
——再论长阳南曲的源流问题
陈琼, 杨容
(1.三峡大学 艺术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2.宜昌市外国语小学, 湖北 宜昌 443002)
长阳南曲是诞生于长阳、五峰等地的一种土家族民间传统曲艺,距今约有两百八十多年的历史。按理说生于斯长于斯的长阳南曲唱颂长阳、五峰本地的风景名胜、风俗习惯、历史掌故应是理所当然。然而该曲艺却反其道而行之,让“不唱长阳、五峰的风景名胜,不唱长阳、五峰的风俗习惯,不唱长阳、五峰的历史掌故”成为长阳南曲的标志性特征①。很显然,“后三不唱”隐含着一个事实:长阳南曲与生俱来对自己诞生地的认同感不强,且弥漫着“故意”和“敌视”的意味。这种“故意”与“敌视”到底隐含着一个什么样的真相呢?
一、问题的提出
一个曲艺品种对自己诞生地产生不认同感,往往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曲艺的诞生地不是自己的原生地,而是从“彼故乡”(祖籍地)流落“此故乡”(诞生地)继而生成的曲艺,无论是艺人和曲艺本身都有“迫不得已”的情绪夹杂其间;二是本土艺人和艺术本身的不认同。很显然长阳南曲在第二种可能性上的几率非常小: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建立在乡愁文化基础之上,中华民族虽民族众多,但“儿不嫌母丑”的优良传统是每一个民族都高度认同的,况且长阳南曲诞生时期正是清朝鼎盛时期,清政府对土家族民族政策仍是“怀柔”与“宽容”居多,“不认同”的几率应该很小。
通过这些年对长阳南曲的深刻接触与研究,发现这种现象的出现仍与长阳南曲的源流问题有直接关联。如果历史不明,源流不清,长阳南曲存在的诸多问题仍很难得到解释。弄清源流问题仍是解决以上问题的唯一“钥匙”。在目前还没有找到历史记载的直接证据前提下,长阳南曲的“后三不唱”艺术特点在其形成过程中所遗留的历史轨迹仍是我们寻找其源流的重要方向和切入点。
目前,关于长阳南曲的起源学说主要有两个:“本地说”和“外来说”。“本地说”中以田玉成的“容美土司宫廷说”极具代表性,黄权生、吴卫华等人的“土家民歌和戏曲说”也有一定影响力;而“外来说”则主要以陈洪等人主张的“明清俗曲说”最具影响力,同时还有“湘西堂戏说”,“水磨调说”,“《桃花扇》学说”也有一定代表性,其中尤以“《桃花扇》学说”为甚。
1.“本地说”的源流主张
“容美土司宫廷说”。主要观点:一是认为长阳南曲的鼻祖有可能出在五峰、长阳本地,认为“龚复让不是长阳南曲唯一的‘祖师爷’,而他在沙市碰到的那位能用左手拨弦的李姓艺人则极有可能是天池河和五峰一带、与他同时代的另外的南曲艺人”,“李姓艺人出生地当属土司管辖范围——清江以南属于当时的容美司,清江以北属于当时的玉江司和麻栗司,所以我们可以基本否定南曲是由汉人传进土家山寨之说了”[1]17-19。二是认为长阳南曲纯粹是由容美土司文化直接繁衍而来的文化体裁,认为容美土司完全有能力孕育出“曲高和寡”的“荷花曲”,理由是“土家并非‘文化浅薄、知识简陋’,当时管辖五峰、长阳等地的容美土司代代都‘知书识礼’,其子女皆‘高材识学’……再加上土家人‘喜歌舞’的民族个性的遗传基因作用,当然有可能创造出南曲这种高雅艺术品来”,长阳南曲具有的是容美土司这个“小宫廷”而非清王朝那个“宫廷”的音乐特性[1]17。三是认为除五峰、长阳等地外没有发现与长阳南曲有联系的曲种,“在各地都没有‘正史’记载的情况下,别处没有我独有的、民间传承下来的、实实在在的艺术和艺人便是‘起源地’最有价值的佐证了。”[1]18-19
“土家戏曲、民歌说”。黄权生、吴卫华虽认同长阳南曲出自长阳、五峰等地,但与田玉成的观点有较大区别:一是土家族居住区域喜竹枝词,认为从巴渝流传过来的竹枝词是一种与击鼓、舞蹈紧密相连的一种文艺形式,清前期的长阳歌舞戏曲文娱活动十分盛行,为南曲发展提供了生长的土壤[2]57-59。二是认为明末清初的“两广填两湖,两湖填四川”的人口大迁徙,使得鄂西土家文化与汉文化得到了充分交融,认为“长阳南曲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当地方言、土家民间音乐相结合,经过土家以人为主体的世代相袭和长期流传演唱。”[2]62三是认为五峰、长阳等地的民间古曲与小调是长阳南曲产生的文化基础,而容美土司宫廷对戏剧文化的爱好和土司家乐引导性的推动,对长阳南曲的形成搭建了外部推动力。
2.“外来说”源流主张
“明清俗曲说”。持此学说的学者为数众多,认同长阳南曲与明清俗曲有关,但在源于具体哪一种明清俗曲上又产生了分歧。胡绍华认为“长阳南曲属于曲牌体唱腔,主要曲牌渊源于明、清的俗曲,部分曲调来自江南吴歌杂曲”[3]。陈金祥认为“明清俗曲及其昆山腔中的诸多曲牌如《寄生草》《银纽(绞)丝》《哭皇天》《西江月》等均为长阳南曲唱腔曲牌所在,由此可见“现存的长阳南曲与昆曲有着相同的遗传密码”,并在各自地域的方言表达形式、表演形式下延展,属“同源异流”[2]21。胡德生认为“南曲源自明清俗曲,是和‘汉滩小曲’(今湖北小曲)等丝弦小曲同源同宗的老曲牌”,五峰、长阳是鄂西出往省都府的重要关口,是商业重镇,文化氛围浓郁,随着商人而来的还有“汉戏”和“楚调”。南曲艺人唱汉戏就会操汉腔,久而久之,艺人就把汉味融进了南曲,形成了该地区独有的“长阳南曲”[2]81-84。杨涌泉认为“各地商人的经商与定居,将外来音乐文化汇聚在长阳资丘这个商业兴旺的水陆码头,使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龚复让如鱼得水,并迅速掌握相关说唱音乐技能,从而使各种南北曲艺形式在长阳等地得以存活,并形成了今天的长阳南曲,尤其河北、浙江两省商人带来的牌子曲,对长阳南曲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2]125。在这些众多不同主张中,陈洪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长阳南曲系容美土司‘改土归流’(1735年)后引进而‘土化’的艺术品种,“根据其曲牌、曲体等方面的历代流行情况,可以看出它与明清俗曲有渊源关系,在我国整个曲唱艺术总的源流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4]。
“湘西坐堂戏说”。陈红、田冲认为一是资丘镇岩洞内有“武陵古洞”摩崖石刻,证明“武陵世家”龚氏是从湖南常德迁移过来的,而长阳南曲的祖师爷龚复让则是龚氏的后裔;二是以西皮和二黄两个声腔作为“基点”,发现“湘西坐堂戏”来源于二黄而成“南路”和“北路”,这两路后来均成为长阳南曲全部曲牌的重要组成部分[2]103,109。
“水磨调学说”。张伟权主张:魏良辅改良昆山腔发展出“水磨调”,它是一种唱曲艺术,不是剧场艺术,采取了南戏里的歌曲……也就是说水磨腔同长阳南曲一样,也是一种坐唱的清唱形式,随着水磨腔传到长阳,并吸收长阳、五峰一带的地方民歌及地方戏曲,与当地方言土语相结合,形成了高度土化的艺术(即今天的长阳南曲),但它仍然继承了“水磨调”的演唱题材、曲牌唱腔、曲体结构和弦式板式。以此推断,昆山腔的水磨调应是长阳南曲的雏形”[2]47,51。
《桃花扇》学说。目前该学说的研究成果较多,都认为长阳南曲渊源于容美土司时期司主田舜年、田昺如、田旻如对昆曲《桃花扇》的移植和扶持。从演唱题材看,长阳南曲显然具有引进曲种的本质,从艺术特点来看属于“阳春白雪”,与明末清初的昆曲艺术有近似特征。其中,王峰认为“长阳南曲渊源于容美土司时期土司主田舜年、田昺如、田旻如对昆曲《桃花扇》的移植和扶持”[5],长阳南曲的“后三不唱”特征“也说明长阳南曲应该是引进曲种,长阳、五峰两县并不是它的缘起地”[2]132,这个“三不唱”现象是该学者认为长阳南曲缘起《桃花扇》的重要证据;王作栋认为“孔尚任著成传奇剧本《桃花扇》……与其后成型的南曲曲种相关联”[2]2,4;孟修祥认为“《桃花扇》进容美是构成南曲唱词文雅、唱腔优美之‘雅乐’的起点,它对南曲的影响主要来自它的折子戏,由于受精彩程度与时间限度的制约,折子戏逐渐代替整部戏曲的演出,因为那些最精彩唱段的反复演唱,为长阳南曲作为‘丝弦雅乐’的转化准备了条件[2]150。本文作者则认为1699年在京城被禁演、1701年前后被容美土司王田舜年引进的《桃花扇》与长阳南曲有着浓厚的血缘关系:剧目被引进后,田氏父子利用在容美盛行的南戏形式对之进行了改编并在容美上演。后来孔尚任戏剧的导演顾彩于1703年底来到容美,在田舜年父子的帮助下结合容美当时的文化元素,将《桃花扇》重新进行了修改,此后该剧在容美盛演三十二年而未衰。雍正末期,由于容美土司被迫“改土归流”,加之《桃花扇》涉及清王朝统治“禁区”而遭禁演,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几乎遭受毁灭性破坏。很显然那些《桃花扇》艺人们也惨遭遣散,这些被遣散的优伶们可能就是长阳南曲的“祖师爷”,而《桃花扇》中的那些经典折子戏以及曲牌有可能就是今天长阳南曲经典唱段和各种曲牌的前身[6]。
3.两种起源主张能否解答“后三不唱”
“儿不嫌母丑”是“本地说”所要解释的问题。很显然,“容美土司宫廷说”是把长阳的政治、历史、文化连同地域整体划入容美土司的统治和势力范围了,用这种“整体打包”方式来分析长阳南曲和长阳历史、文化与典故的关系,是脱离了容美土司与清王朝之间的政治前提。在容美土司被迫“改土归流”之前,长阳、五峰只是容美土司的附属辖地。如果容美土司真把长阳、五峰看成自己的故乡,这种“后三不唱”的历史情怀就不在情理了。“土家戏曲、民歌说”认为长阳南曲就是长阳土家族民自己的文化,是来自他们自己的生活、由他们自己创造,这种前提下的“后三不唱”在其历史文献、县志和民间记述中也没有找到任何的记载。
从“独为异乡为异客”的角度来看,“外地说”几乎都符合“后三不唱”的客观条件,但在结果上各不相同,甚至是大相径庭。其中“明清俗曲说”、“水磨调学说”、“湘西坐堂戏说”三者多是从曲艺的形式形态、流布地区、传承过程、文化渊源等角度来阐述二者之间的存承与延续关系,并未见民族情感上的是非纠葛。在其政治、历史、文化领域上,唯有在容美土司盛演的《桃花扇》的命运变迁与长阳南曲的诞生地有着“理还乱”的关系。在已有的文献资料记载中,长阳南曲与传入土家族的南曲有关系,与容美土司王田舜年时期发展起来的南剧有紧密关联。在目前关于长阳南曲源流的研究成果中,王峰是对其源流指向最为明确、也较早提出该观点的学者之一,虽对《桃花扇》演化成为长阳南曲的可能性、可行性以及在其演变过程的内引外联系没有考证和说明,但提出了“后三不唱”的概念。
长阳南曲作为一个距今近三百年、又只在长阳五峰等地具体存在的文化事项,一定与它所存在的历史阶段、文化背景、政治氛围、地理环境、生活方式等因素有密切相关,绝不可能是一个“飞来峰”。艺术源于现实生活,无论从其缘起、发展到最终成为一种完整结构和特性鲜明的艺术品种,她必定承载着和具体反映着人们的生活情感与历史意愿。从最直接、最表象层面看,“后三不唱”对其诞生地不认同感,说明长阳南曲是一个“外来艺术”的事实。它既然不唱长阳、五峰本地的人文、风景、历史,那她到底要唱什么地方的人文、风景、历史呢?准确探寻到这些问题的源泉,方可得知她缘起于何种文化,又为何会只在长阳、五峰等地诞生而不在其它地方生根繁衍,就会解释她为什么“不待见”诞生地等一系列至今仍无确切回答的问题。
本文试从容美土司入世前后的地缘关系、改土归流、政治变迁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二者之间由于地缘政治和历史文化变迁对长阳南曲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二、容美土司与长阳南曲诞生地历史渊源
容美土司地处古楚之西南:它东联江汉,西接黔渝,南通湘澧,北邻巴蜀。到元末时,其疆域面积约在两千平方公里左右;明末清初鼎盛时期达七千平方公里以上,包括今天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鹤峰县大部分地区,巴东县野三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恩施县、建始县清江以南的部分地区,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大部分地区,湖南省石门县、桑植县与之接壤的部分地区;至清朝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其疆域缩小在四关(东百年关、西七峰关、南大崖关、北邬阳关)和四口(洞口、三岔口、三路口、锦鸡口)之内,总面积意在四千平方公里上下[7]1。很显然,在其历史上容美土司与长阳南曲诞生地的地缘政治、文化关系都是比较源远流长的。
1.“入世”前容美土司与长阳南曲诞生地的地缘关系
容美土司古称容米,又称拓溪,是容米部落的后裔。容米部落是一个古老的、具有母系氏族社会遗存特点的原始部落,最早出现在长阳县资丘镇附近的清江南岸天池河口的“旧容米洞”②。后来,容米部落沿天池河索源而上,穿过五峰境内,逐步深入到鹤峰一带,建立了第二个容米洞,史上称之为“新容米洞”。史料记载:容米部落的活动中心范围主要是在今天鹤峰县的容美镇,其活动范围北到清江以南,南到南渡江以北,西到上下爱茶司,东至五峰县的石梁司,约有60%的面积属于清江流域[8]。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容米部落从诞生开始就与长阳南曲诞生地有着天然的地域“血缘”关系。
元大德末年(1300年前后),容米部落经常向周边扩张,引起周围郡县的高度警惕。当时巴东县知县唐伯圭向皇上撰写奏章,建议派军讨伐。容米部落第一次被国家写入正史就始于至大元年(1308年)唐伯圭上奏的《招捕总录·四川门》里面,自此容米部落正式出现在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中。后人把这个记载时间称为容美土司的“入世”。
2.“入世”后容美土司与长阳南曲诞生地的地缘政治关系
从至大元年(1308年)到至正十年(1350年),容米部落一直实施“向外扩张、发展壮大”的战略目标,直到至正十年,容米部落被元政权招安,被升为“四川容米洞军民总管府”[9]。这一“招安”标志着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的容米部落社会正式结束,新容美土司制度正式建立,容美土司自此势力日益壮大。
田世爵是容美土司兴盛时期代表人物,他在位时积极“推广汉文汉语,并不断开拓中兴之路”,“结交官府,构建良好的外部环境”,并得到了官府的积极回报,朝廷对容美土司疆土扩张的默认与退让就是一个典型范例。在田世爵执政期间,曾统兵千余人驻扎长阳等地,至明末清初年间几乎占领了长阳县清江以北的大片土地。正是明王朝对容美土司扩疆行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宽广胸怀”,也让这一时期的容美土司王对大明王朝“感恩戴德”并“誓死效忠”。很显然,大明王朝的这种“恩惠”最终成为容美土司臣民不认同长阳南曲诞生地是其故土的政治根源,这也为长阳南曲形成“后三不唱”艺术特征埋下了伏笔。田楚产父子(田玄)掌管容美期间,父子二人创建了容美土司的最鼎盛时代,主要标志之一就是“控制地域最广”。他们在位时对长阳、五峰的侵占越来越频繁。至天启元年,田楚产就侵占菩提寨(五峰长乐坪附近的谢家坪)和长毛司(长阳长毛关);到田玄坐镇容美土司时,侵占力度进一步加大,还利用明末的混乱出兵勤王之机,竟把长阳县的大部分地区据为己有。此时,父子二人统治下的容美土司疆域达到鼎盛时期,几乎涵盖了整个五峰和长阳。
明末清初容美政权势力开始走向衰落,疆土不断萎缩,田舜年田昺如父子为了挽回颓废之局,保住疆土不受挤压,对所辖安抚司实行剿灭和直接管辖:以唐公廉与水浕安抚使唐继勋联合反对容美土司为借口,对石梁安抚使(今五峰县的石梁荒一带)唐公廉实行围剿,将唐氏杀害,派自己的胞弟田庆年以唐氏女婿世袭安抚使一职,并将石梁安抚司署迁至容美中府(今鹤峰县容美镇),遥领其地;为了将五峰安抚司(今五峰县的五峰山地区)掌控在自己的手中,田舜年将世袭五峰安抚司继承人张彤昭以“殒厥祖祀”之罪处死,让自己的儿子田翟如以张氏女婿之名,袭五峰安抚使一职,同样将五峰安抚司署迁至容美中府,遥领其地;对五峰县的水浕源安抚司(今五峰县水浕源、天池河的水浕司一带)以“图谋不轨”的罪名将安抚使唐继勋处死,让自己的孙子田图南以唐氏外甥袭安抚使职,仍将水浕源安抚司署都地迁到容美中府,遥领其地[7]70。到最后一代土司田旻如时期,容美土司仍在为容美与长阳边界的分属争执多年,雍正三年(1725年),在容美土司与长阳县接界处建立了“汉土疆界碑”,解决了容美土司与长阳县边界的三大争端,理清了容美土司对长阳和五峰等地的管辖地界,给双方土民百姓一可行之规。
3.小结
从鹤峰出土的部分文物分析来看,具有母系氏族特征的容米部落从长阳的旧容米洞迁徙到鹤峰的新容米洞最迟应在秦灭巴以前。据《汉书·地理志》记载:黔中郡更名为武陵郡后,在郡内设迁陵县、酉阳县、零阳县、充县、沅陵县、佷山县,其中的佷山县所辖区域就是今天的长阳、五峰。东汉之后,建制并无变化。三国至隋唐时,由于社会持续的动荡分裂,武陵郡势力范围未扩反减。自秦汉至唐宋再到元末,容米部落既未独立建制,也未被划属周围任何一个郡县。自公元前三百多年秦灭巴,容米部落就一直在此繁衍生息到元朝至大三年(1310年)的一千六百多年时间是容米部落编年史的“空白期”,也是容米部落处于“世外桃源”的状态。正是由于这个漫长的历史“空白期”,它“入世”前的政治特征、历史特征、文化特征均无从考证,也导致后来诸多容美文化现象的出现也无从追溯,长阳南曲“缘起何物”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代表。但不可否认的是:“空白期”的容美部落与历史上的五峰、长阳在疆土地域与政治隶属上还是有非常多的交集,它们之间的政治、历史、文化“血脉”还是客观存在的,它蕴含在容米部落的日常生活与劳作之中。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长阳的资丘、渔阳、天池河等地虽然曾是容美土司的发源地,但在其入世后,由于历代容美土司深受当朝的恩惠,尤其对自己土司府所在地——容美十分眷顾(几乎未曾派兵进驻和镇压),鹤峰容美镇成为历代土司苦心经营的府邸和辖地,因此容美在历代土司眼里具有神圣不可替代的位置,田舜年时代的三个“遥领其地”充分说明鹤峰容美镇才是容美土司心目中的第一故乡,才是他们的“根”,才是他们的真正“王道乐土”。很显然,入世后若干代容美土司王对“第一个容米洞”的记忆随着上千年时间的流失已是十分模糊和完全淡忘了,在他们眼里曾经多次占领的长阳、五峰仍只是一个附属之地,已不再是容美土司的“故乡之域”,否则也就不会有历次的“侵占”与划疆之说。
三、改土归流后容美《桃花扇》的归宿——长阳南曲
“改土归流”是清雍正年间在土司地区推行的一种“收复纳降”政策,其目的就是消灭土司制度,用朝廷任命的流官来代替土官世袭。采用的政治手段主要有:自请归流、直接“裁废”和被逼归流。其实早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时,对容美土司实行改土归流的意向就已经提出,由于田舜年的“冤死”③,康熙帝的“愧疚”与“仁慈”,改土归流才一直未曾实施。但到了田旻如当政初期,朝廷大员“奏章不断”,要求朝廷对之实施改土归流的愿望极为强烈。但雍正考虑“不要好大喜功”,执行“兼顾情、理、法三原则的妥善解决”原则,因此也一直延缓未办。到田旻如当政后期,容美土司的强盛势头引起朝廷警惕,强硬官员占上风,最终对容美用兵,田旻如被迫自缢身亡。容美土司政权瞬间分崩离析,被迫改土归流。在清政府“斩草除根”的策略中,容美土司经营四百多年的政治、历史、文化等遗产几乎“消失殆尽”。这种毁灭式的改土归流对容美土司文化传承的消极影响是空前的,在容美土司盛演三十二年④之久的《桃花扇》及其艺人就是深受影响的典型代表。
1.田舜年父子与《桃花扇》
昆剧《桃花扇》乃是汉族大戏剧家孔尚任的得意之作,因戏中有“反清复明”思想,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在京城舞台上昙花一现后旋即被打入冷宫。身处万山丛中的容美土司田舜年却投诗盛赞《桃花扇》,孔尚任亦称赞容美土司王田舜年把《桃花扇》演得“旖旎可赏”⑤。为了引进《桃花扇》,田舜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派舍把唐柱臣游学京城拜访孔尚任。孔尚任冒险为田氏舍把传授《桃花扇》。田舜年诚邀戏剧家顾彩访游容美,顾彩则细心指导田舜年父子排演《桃花扇》, 而且还教容美土司的戏班排演自己改编的《南桃花扇》。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桃花扇》在“关公诞,演戏于细柳城之庙楼,连演三天”[10]233。《桃花扇》在关公诞辰的演出,不仅代表着容美土司戏剧文化的最高成就,也对后来的地方戏剧文化产生深远影响。长阳南曲的形成与这一文化事象的历史变迁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
2.改土归流对《桃花扇》及其艺人的影响
第一,对《桃花扇》的影响。
雍正二十一年(1733年)土司王田旻如的自杀,标志着容美土司自治政权的瓦解,也标志《桃花扇》在容美土司舞台上的消失。这一政治事件给容美土司的文化存承带来了几乎毁灭性的灾难,带给《桃花扇》的破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由于容美土司政权被清朝任命官员毛俊德所替代,涉及“反清复明”思想的《桃花扇》直接触犯了清朝政权切身利益,重演《桃花扇》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其二,原容美土司中大部分土民都“自请归流”⑥,容美土司政权人心向背,演出的人文环境不复存在;其三,原来忠于土司政权的大部分官宦和部分土民(亲信)绝大数被放流他乡,流散各地的男优、女伶重聚一起会演此剧的机会不复存在。
第二,对《桃花扇》艺人的影响。
鉴于容美土司被迫改土归流,雍正对容美土司族民采用的是“宽严并用”措施:
特免田旻如戮尸,妻妾子女父母兄弟并田畅如及阉人刘冒等,均免死,照例分发陕西、广东、河南三省安插,节均给家资,以资养赡,俾结斯案于不蔓不扰之中,对土司的大小头目,必须调离原籍,以其“罪恶”大小,或“远省安插”,或“近省安插”,或“安插附近州县”,以免“土人情恋故主”[7]98。
非常明确的是:《桃花扇》艺人应该就是以上被遣散“近省安插”或“安插附近州县”的对象,原因是:虽然他们是容美土司田舜年父子身边最亲近的人,但他们在容美土司社会仍属于社会地位最低的人群。那么这些艺人最后“就近安插”到哪些地方了呢?很显然,长阳、五峰等地是其第一选择。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五峰、长阳原本就是容美土司下属土司府第,地处容美镇东南,是容美土司靠近汉族地区最近、与外界交流最活跃的地方,也是与上级政府湖广总督府武昌紧密联系的主要通道。二是相对容美土司其它地方而言,五峰、长阳已是富庶之地,商贸往来频繁,经济发达,文化繁荣,部分《桃花扇》艺人因自请归流而受清政府特赦或奖励,让之移民于富饶之地是合乎情理的。三是应该归结于田舜年父子执政期间对外扩张的行为。在田舜年父子统治下的容美土司常因疆域、经济、人口等利益纷争,多次对与本司有姻缘关系的永顺、保靖、桑植土司爆发冲突和战争,使得容美土司与以上土司的关系极为紧张,甚至交恶。这是导致改土归流后《桃花扇》艺人们“不敢去、不能去、没有去”[11]其它土司辖地的直接原因。很显然,以上原因是《桃花扇》连同艺人一起来到长阳、五峰等地的直接动因,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长阳南曲会在长阳、五峰等地诞生和传播。
3.“后三不唱”中的秘密:长阳南曲艺人与《桃花扇》艺人的情结重叠
“后三不唱”中蕴涵着容美土司臣民们诸多情绪与情怀:有“怨恨”、“仇恨”和“清高”的情绪,有“忠君”与“乡愁”的情怀。而这一切则要归咎于明、清朝代更迭时清王朝对容美土司王的压制与轻视,雍正、乾隆两位皇帝对容美土司实施改土归流时善后制度上的严重压制有关。
一是乡愁情结。据史料记载:在长阳、五峰还不是容美土司辖地之时,土司常因这两地的管辖权与汉族地方政府发生冲突,只因清王朝当时政局未稳,无暇顾及,为了暂时安抚容美土司不要生事,故对容美土司侵占长阳、五峰的扩张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725年,清政府与容美土司在长阳树立一块结束容美土司与长阳边界争夺的“汉土疆界碑”,充分说明在改土归流前夕容美土司对争取长阳、五峰的管辖权的行动还在上演,尤其是田舜年时期的三个“遥领其地”充分说明:在容美土司眼里,容美土司所在府第才是他们的第一故乡,是他们心灵与乡愁寄托的地方,而长阳、五峰只不过是“异域他乡”,由此对它们的“敌意”也是“与生俱来”。这些土民中就有《桃花扇》中的戏剧艺人,他们深受改土归流之害而被遣散或流放到长阳、五峰等地,虽然出于生计而不得不继续卖艺度日,但艺人们不唱长阳的“名胜、风俗和掌故”乃是他们骨子里的一种本能反应,是一种“乡愁”情结使然。
二是怀念旧主。虽然容美土司政权一直实行的是“农奴”制度,到田旻如时代也未有多大改变。但由于田氏家族历来重视文化、并利用文化对族民进行教化。在田舜年父子当政期间,由于他们对戏曲的过分痴迷,也由此带来对土司内戏班和戏曲艺人格外重视,而那些有幸被选入戏班的戏曲艺人们则深感田氏父子的知遇之恩,对他们的主人感恩戴德,继而怀念旧主也是符合常理的,因此他们“不唱长阳”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三是仇恨情绪。应该知道田舜年当年引入具有“反清复明”思想的《桃花扇》,其主要原因是自己与孔尚任“与生俱来”就肩负着“反清复明”的大任⑦,也由此可知《桃花扇》中的政治动机对容美艺人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尤其对雍正改土归流时逼杀土司王田旻如、无情遣散驱赶《桃花扇》戏曲艺人的恶行感到反感与仇恨,只是因为身处社会底层,敢怒而不敢言。他们对被迫来到长阳、五峰是有很深的抵触乃至反感情绪,故借“不唱长阳”发泄心中愤懑之情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四是艺人的“清高”。长阳南曲艺人的“清高”基因应该来自容美《桃花扇》中的“大雅”气质[12]。田舜年对《桃花扇》的引入和顾彩对《桃花扇》的移植,使得容美土司的戏剧艺术呈现出一个崭新的高度:由人来扮演人物角色,代替以前的木偶、皮影来扮演角色;由真人公开露面来扮演戏剧人物角色,一改傩戏中戴着假面具来扮演神灵的演艺形式,更不同于“梯玛”中那种跳神或做法镇邪的作用;戏曲内容已经从民间的平常生活、道德伦理、降妖捉怪的层面上升到历史兴衰、邦国存亡的深度与广度;已经把吴腔、苏腔、秦腔、巴曲、楚调及容美传统曲调有机结合,并融为一体,彼此之间相互借鉴与较量[10]234。这充分说明容美戏剧艺人的“高雅”是深受《桃花扇》中“大雅”的影响,无论从演出形式、戏剧题材、专业高度,一改土家“粗狂、豪放、率直”而转入“细致、文雅、婉约”。容美戏曲艺人的这种“细致、文雅、婉约”与长阳南曲艺人们骨子里的那种“大雅”气质如出一辙。这种气质促使他们不愿屈从清政府的压制,而对长阳、五峰的“不认同”正是这种内在气质所决定的。这也再次间接证明:长阳南曲的缘起与容美土司的《桃花扇》和艺人们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综上所述,容美《桃花扇》戏曲艺人们由于“改土归流”的原因被遣散到五峰、长阳等地,继而成为长阳南曲艺人的鼻祖是完全有可能的。《桃花扇》从康熙四十三年顾彩进入容美土司开始有效传播,到雍正十二年改土归流时的全面禁演,历时三十多年的时间。毫无疑问,《桃花扇》对土民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如果要在霎那间把她从人们的生活中消逝而不留一丝痕迹,这根本无法做到。禁锢住戏曲艺人的身体,却锁不住歌唱的喉咙,不让唱《桃花扇》,艺人们可以将它们进行改编,换一种新的形式、填写新的唱词、换新的曲牌来演绎,而这种新的演绎中就极有可能有我们今天所盛行的长阳南曲的种子[6]。“长阳南曲来源于容美土司的《桃花扇》”、“长阳南曲艺人的鼻祖是《桃花扇》戏曲艺人”是完全有可能的。长阳南曲不唱长阳、五峰两地的“风景名胜、风俗习惯和历史掌故”再一次印证了这种可能。当然,这也间接说明长阳南曲是一种外来艺术品种,与从容美流传过来的《桃花扇》有着紧密的关系,唯有如此,方可解释得通“新三不唱”的历史成因。
五、结语
从以上容美土司的地缘政治关系和“改土归流”对容美土司《桃花扇》的影响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长阳南曲的诞生地长阳、五峰与容美土司有着极为深厚的地缘关系、政治渊源和文化存承关系。正是清朝政府对容美土司政治制度的严重影响,导致了容美政权的瓦解,从而导致了容美土司文化的分崩离析,伴随着人口的强制迁徙,容美土司《桃花扇》也随之被迁徙和不断变化。但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不可能随着人口的迁徙而消失,而是以另一种文化现象出现罢了。无论它们的面貌如何千变万化,但其内核是不会发生质变的,更不会消失,这也是长阳南曲中呈现出诸多与《桃花扇》相似或相近艺术特性的根本原因。从文化迁徙的角度来看,再次印证了长阳南曲与《桃花扇》之间有着深厚的血缘关系,这也为今天寻找长阳南曲的起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探索途径。
注 释:
① 作者将长阳南曲的“夜不静不唱、有风声不唱、丧事不唱”称为“前三不唱”,将“不唱长阳、五峰的风景名胜、风俗习惯、历史掌故”称为“后三不唱”。此称谓仅仅是为了区分二者,事实上并无前后。
② 相传长阳南曲的诞生地就在长阳资丘镇的天池河口,此处也是长阳南曲最为盛行的地方,这种地缘政治和文化历史印迹应该就是“本地说”倡导者田玉成的重要佐证。
③ 1705年,土司王田舜年与其继承人田昺如(田舜年的大儿子)发生内讧,导致田昺如出逃,湖广总督石文晟借机向康熙参劾田舜年行政罪行,康熙正在派人调查之际,田舜年亲自到武昌见总督申说冤屈理由,石文晟却以“与向长庚(另一下属土司王)互奸,违误钦案”之罪名将其逮捕入狱,不料于次年夏天病死于武昌牢狱。康熙对此甚为不满,亲派大臣南下武昌续查此案,历时数月终以田旻如回司袭职,判石文晟等失职查办而告终。
④ 1700年《桃花扇》在京城被禁演,但于1701年《桃花扇》传入容美土司府邸,田舜年父子就已经进行移植与改编,到1704年初顾彩进入容美土司时,已有三年之久,故此有人说《桃花扇》在容美土司上演有三十二年之久了。
⑤ 孔尚任在《桃花扇》自序之三《本末》有这样一段话:“楚地容美,在万山中,阻绝入境,即古桃源也。予友故天石有刘子骥之愿(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误入桃花源的游客),竟入洞访之,盘桓数月,甚被崇礼。每宴必命家姬奏《桃花扇》,亦复旖旎可赏。
⑥ 1733年雍正决定对容美土司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为“计擒为上,兵剿次之,自献为上,勒献次之”,最后一代土司王田旻如错误估计土民意愿:抗拒归流,土民于1735年初按照自己的意愿自愿归顺朝廷改制。
⑦ 孔尚任乃孔子六十四代玄孙,又是明朝重臣的后代,与生俱来的两种身份让他在明清朝代更迭中处于处于艰难选择的境地,侍清有违文人骨气和家族“反清复明”的祖训,不侍清又难违历史潮流;田舜年与孔尚任一样,同样处在尴尬境地:侍清有违“反清复明”的祖训,不侍清又不能阻止朝代更迭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