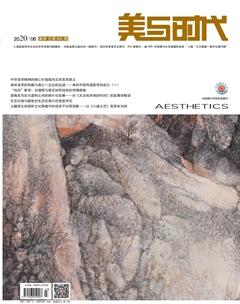浅析石涛北游受挫原因
蓝月 韩文文
摘 要:明遗民画家石涛北游京城三年,以精湛的画艺流连于达官贵人之间,却再未得到皇帝垂青,终南返扬州。这样的结局是北游前已受到康熙礼遇的石涛始料未及的。石涛北游受挫,惨淡南归的结局是多种因素导致的,当时京城紧张的政治文化环境造成遗民士绅处境艰难,石涛作为明宗室遗民的贵胄心理也使其难以进一步屈从于清初的文化正统,而他狂傲的艺术个性又为官方画派所不容。石涛“欲问皇家问赏心,好从宝绘通知遇”希冀的破灭,看似是时运不济所致,其实偶然中早已蕴含着必然。
关键词:石涛;北游;受挫
石涛为明宗室遗民,在崇祯十五年满门遭难,石涛时年四岁,后遁入政治僧人旅庵本月门下。北游前,石涛的许多作品都展现出对新王朝的肯定,甚至两次在扬州为康熙接驾。他北上无外乎是要走与自己的师父、师祖相同的道路——受到皇帝的赏识,成为德高望重的禅师。然而彼时京城的政治风向与画坛审美都对石涛的诉求十分不利,石涛自身似乎也不愿向所谓“正统”妥协。
一、外部原因——政治与文化环境
石涛北上时希望依托政治僧人的身份谋求高位,然而清初的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其中佛门的氛围并非云淡风轻。石涛属临济宗一系,其内部斗争激烈,最主要的是天童圆悟和汉月法藏之争。法藏认为禅宗五支派系各有其宗法,强调的是对禅的义理化解读,这是对临济正宗的创新与反叛。法藏系同情明遗民,许多遗民画家诸如八大山人、弘仁等很少讲“法”,更崇尚“理”与“道”,这与他们更多受法藏系思想影响是分不开的[1]。石涛是“清初四僧”中唯一的天童临济派,但他的艺术理念显然与被官方正统思想所支配的“四王”派背道而驰,他的理念与其所属宗派思想事实上是矛盾的,而“四王”的艺术主张却与同为官方代表的天童临济理念一脉相承。
石涛北游期间,同属幻有正传门的圆修一派十分得势,其中玉林通琇与圆悟一系的木陈道都受到顺治的青睐。通琇一派气焰嚣张,时常仗势欺人,其系绵延至乾隆时期,因其徒孙与师祖同样行为不端受到皇帝训斥才渐渐式微。玉林属磐山系,与天童系相互颉颃,以好辩著称。当石涛终于到达燕京时,作为怀有亲近朝堂之心的道之孙,必然会受盘踞朝中的通琇一党刁难。
除了京城激烈的僧诤,当时的文化意识形态对石涛的计划也十分不利。康熙继承了先辈对汉族的怀柔政策,尊重并学习、吸收汉族传统文化,其登基之时,中国正处于民族文化矛盾激化的时期,而他却否定了所谓“返归淳朴旧制”的主张,通过开博学鸿词科等举措拉拢汉族士绅,自然也包括明遗民群体。康熙帝对汉人的怀柔政策鼓舞了石濤北上,但石涛北游时却是清政府对汉族文人管控最为严格的时期。
“清初帝王尊崇朱学,自康熙始”,清朝的崇儒之风从康熙时期开始兴盛。然而,康熙虽在《朱子全书》中赞扬尊孔崇朱的文化理念,实际上却不允许朱子所承担的“道统”超出皇家权力所能控制的范围,他的真正目的并非推动儒学发展,而是利用儒学在汉人中独特的文化地位来制约其思想。康熙二十八年五月,游离于陆王与程朱两宗之间的翰林掌院学士李光地被康熙斥责为冒名道学,被撤销职位。数月后康熙明确指出李光地属于陆王一派[2]。这次罢免事件可看作一个政策信号,即清朝官方确定程朱为正统儒学派别。
石涛于同年北上,此时康熙的文化政策直接导致了官方主流审美倾向的明确,清初“四王”以正统独秀于各个画派。“四王”艺术讲究仿古,以中正为美,强调画面中的仁和宽厚之气以及与宋元名家一脉相承的精深笔墨功力。“四王”的代表人物几乎都得到了清统治者的认可。王翚在康熙二十八年南巡时被提名作《南巡图》,受到太子胤的接见,并得赐字“山水清晖”。四王中年纪最小的王原祁也以画供奉内廷,深得康熙帝器重,受命编纂《佩文斋书画谱》。
在四王拟古风气盛行的阶段,反观石涛17世纪80年代的画作与画论,可以发现当时他的艺术观念与所谓清初正统画派理念是背道而驰的。这一时期石涛最重要的画学观点是“我自用我法”,在1684年客居宣城时,他针对南北宗论题跋:“今问南北宗:我宗耶?宗我耶?一时捧腹曰:我自用我法。”[3]其艺术中主体意识十分强烈。北上京城后,石涛于1691年作《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卷》有跋:“纵横习气安可辩焉?自之曰:此某家笔墨,此某家法派,犹盲人之示盲人、丑妇之评丑妇尔,赏鉴云乎哉。不立一法,是吾宗也,不舍一法,是吾旨也,学者知之乎。”从中可以发现石涛采取了更为中立的态度。
由“我用我法”转变为“不立一法,不舍一法”,这样的变化也许是石涛入京后在显贵府中窥得历代名家作品后所产生的。然而无论如何,石涛画学坚定地反对泥古不化,即使其画跋中并未严厉批评信效古人的作画法则,但必将为以得古人“脚汗气”为荣的四王派所不容。
二、 内部原因——石涛的坚守与个性
除了文化环境的限制,石涛北游受挫与他在艺术上坚定的立场不无联系。
石涛作为明宗室遗民却屡屡向康熙献媚,遁入空门却仍追求做一个政治僧人,历史上许多人认为他是一个自相矛盾、摇摆不定的人,但石涛在绘画理念上却出乎意料的坚定。
与石涛同时期的王原祁作《仿高房山山水图》,题画首句便是“此图仿高尚书云山……”点明摹古的主旨。其画仿元高克恭笔法,以横点皴染,笔墨苍润,沉静典雅的气质与石涛恣意挥洒的风格相左。王原祁在《雨窗漫笔》里明确指出:“明末画中有习气,恶派以浙派为最。至吴门、云间,大家如文、沈,宗匠如董,赝本溷淆,以讹传讹,竟成流弊。广陵白下,其恶习与浙派无异,有志笔墨者,切须戒之。”[4]“四王”的艺术思想直接继承了明末董其昌的南北宗论,有很强的派别意识,认为已派是正宗,排斥被归为北宗的浙派。王原祁上文所述将南京、扬州等地区画习与浙派相提并论,明显带有不屑的意味,耐人寻味的是南京与扬州都是石涛书画活动最为活跃的两个地区,也是石涛的扬名之处,让人很难不联想到此类评价是针对石涛的。
而石涛在京期间,虽然应友人邀请作过几幅符合宫廷趣味的书画作品,最终反而不遑多让地在康熙三十一年《山水册》上书写跋语:“夫茫茫大盖之中只有一法,得此一法则无往非法,而必拘拘然名之为法。情生则力举,力举则发而为制度文章。其实不过本来之一悟,送能变化无穷规模。吾今写此数幅,并不求合古人,亦并不定用我法,皆是动乎意,生乎情,举乎力,发乎文章、以成变化规模。”[5]中心意思即所谓“法”并不非由古人之法或“我法”为尺度,天地间存在“一法”,可动乎意,生乎情,举乎力,发乎文章,与以古为尊的四王艺术主张大相径庭。石涛旅居京城“欲问皇家赏心”,但是理论姿态却从不放低,在当时紧张的文化环境中自然是很难得到官方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