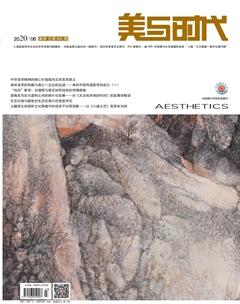从翻译主体探析文化移植中的信息不对等现象
王圆圆 黄华
摘 要:翻译过程中,由于存在多种跨文化因素的干扰,造成两种语言负载的文化信息不相匹配,这就是文化的不对等移植。从翻译主体的角度探析文化移植中的信息不对等现象将以《小城之恋》英译本为例,通过具体分析英译者孔慧怡的文化身份和文化态度,及在翻译中对异化、归化、侵入等策略的运用,探究译者在文化移植过程中对信息传递的影响,以期对王安忆作品的翻译以及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有价值的经验参考。
关键词:《小城之恋》;孔慧怡;文化移植;信息不对等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教委面上项目(SM201710028002);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9WXB005)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国家大力推进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海外传播成为学界共同关注的話题。翻译位于传播的源头,是影响作品海外传播的基础性因素。
翻译活动不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将源文化中蕴含的一些信息,通过合适的途径迁移到另外一种文化环境之中,并确保蕴含的信息内涵得以保留,这就是文化移植。在这一过程中,译者扮演着两种文化的协调者角色,他们的文化身份和文化态度,决定了翻译立场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从而对文化信息的移植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选取王安忆的《小城之恋》为个案,通过具体分析英译者孔慧怡的文化身份和文化态度,及在翻译中对异化、归化、侵入等策略的运用,探究译者在文化移植过程中对信息传递的影响,以期对王安忆作品的翻译以及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有价值的经验参考。
一、译者的文化身份与翻译立场
《小城之恋》的英译者孔慧怡(Eva Hung)博士是当代香港翻译界的领军人物,学贯中西,曾译过王安忆的《荒山之恋》(1990)、香港女作家西西的《我城》(1993)等作品,精通英汉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从文化身份来看,作为较早受到西方女权主义影响的翻译家,孔慧怡曾在访谈中谈到自己在翻译女性作品时,有种每一个细胞都投入的感觉,女作家作品无论在知性、感性和直觉等方面都牵引着自己。女性经验的相似让孔慧怡倾向于选择女性作家的作品来翻译。在作品翻译的过程中,也突出了女性主义立场。
这首先体现在为《小城之恋》添加了前言。加写“前言”可以用来解释原文的主旨和创作特点等,从而起到引导读者阅读方向的作用。孔慧怡在《小城之恋》的英译本“前言”中写道:“作者通过男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探讨爱情的意义以及女性在面对重大情感危机时的精神力量。”通过添加“前言”,孔慧怡凸显了原作的女性主义立场。
除“前言”外,译者在文本的翻译中也强化了女性主义表达,如下面两处:
(1)她对照着前后左右的镜子,心想以为她丑陋是绝对不公平的,以为她粗笨也是绝对不公平的。(王安忆,2001:111)
She looks into the mirrors around her, and thinks to herself:its unfair to say Im ugly, and its unfair to say Im clumsy. (Hung. 1988:7)
这句话是“她”练功房里对着镜子观看自己舞蹈动作时的自我安慰。由于长期练舞动作不科学“练坏了体型”,变得肥胖粗壮,被其他演员嘲笑,只有当衣服一件件脱去,只剩下一件练功服时,身材才略微匀称起来。
译者在这里将第三人称“她”替换成第一人称的“我”,一改原文中客观而疏离的笔法,让女主人公直接发声,更有力地表达了她因长期饱受嘲讽的不满和怨愤。同时显示了译者强烈的性别意识,及因此产生的对主人公的同情和认同。通过在翻译中加入性别这一参照系数,增加了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张力,拓宽译作的表达空间,凸显女性意识。
(2)可是他是那样刻骨地想念她,她虽不像他那样明确地想念,却是心躁。(王安忆,2001:131)
Yet how he yeans for her! And though she does not long for him as obviously as he does for her, she becomes agitated. (Hung. 1988:35 )
译者将原文的两个“想念”分别译为“Yeaning for”和“long for”,一方面是为了减少用词重复,但两个英文短语在内涵上的细微差别也值得注意。“Yeaning for”是指“to want sth. very much, especially when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get”,而“long for”是指“desire strongly or persistently”(牛津词典),由此可以看出,他此时想念的程度虽然强烈,但心中已经做好了不可得的准备;而她的想念更持续,即便短时间内看不到希望也会坚持下去。此处可以洞悉译者在翻译时明确识别了男性和女性在情感与理智上的不同,暗示了对男性的薄情以及对他随时可能逃离的谴责,表达出对女性坚贞于爱情的赞赏,相较于原文,更突显出了女性主义立场。
孔慧怡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女性主义身份和立场带入翻译,但这与作者的本意相违背。王安忆本人一再否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我确实很少单单从女性的角度去考虑东西,好像并不是想在里面解决一个女性的问题,我没有这样想”。显然,在《小城之恋》英译过程中,译者的文化身份和翻译立场强化了女性主义表达,产生了文化信息的不对等移植。
二、译者的文化态度与翻译策略
翻译活动是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译者的文化态度在其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它与翻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有关。因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从来就不是平等的,在这种交流之中,翻译者就像一个谈判代表,代表着某种特定的文化势力,因而他们往往会对他的谈判对手采取不同的策略,即译者对目标语文化持有的态度,直接影响到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文化态度本身固有的多歧性往往导致译者做出能动的适应与选择,实施灵活多变的翻译策略。
从当前的翻译研究来看,如果译者较为认同源语文化价值,其翻译策略便趋向异化;如果译者更看重本土文化传统,其翻译策略则多以归化为主。而实践中由于译者文化态度的歧义和多变,异化和归化两种策略通常并存。
首先,为了让读者更好地感受作家风格,孔慧怡在翻译中采取了异化策略。异化是指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的翻译。这种策略通过对源语文化的保留,会增加读者的阅读和理解难度,但能较好地保留原文的异域性。在《小城之恋》中,异化策略的运用,再现了原作者的语言风格,如以下几处:
(1)或开路般的走在前边,或压阵似的走在后边,叽哩呱啦地说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话。(王安忆,2001:127)
She either walks in front of the group as if she is clearing the way for an army, or walks at the back as though to make sure that everything is all right, all the while babbling about irrelevant things.(Hung. 1988:30)
此處描写女主人公跟大家一起去迎接外出学习的人归来,她很激动,因而原文中用了两处比喻,“或开路般的走在前边,或压阵似的走在后边”,而译文在翻译时保留了这两个比喻:“as if she is clearing the way for an army”(为队伍的前进扫清道路);“walks at the back as though to make sure that everything is all right”(走在最后来确保队伍一切正常)。译者通过两个比喻的运用,将异国因素“吸收”进入译文,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原文的生动性和形象性,同时让目的语读者体验到汉语表达的独特趣味与无穷魅力,以及原作者善于运用绵长句式的语言风格。
(2)汹涌澎湃,气震山河,一切卑微琐细的声响都被吞没了。(王安忆,2001:127)
Seething and swelling, its strength would shake whole nations, and all small and hum.(Hung. 1988:39)
经历了长久的折磨,这是他和她终于压抑不住内心的欲望,第一次拥抱和亲吻在一起,作者在形容这一场景时,运用了两个夸张“汹涌澎湃”和“气震山河”,而译者在此采用了异化策略,保留了原文的夸张手法。“Seething”是指“foam as if boiling”(牛津词典),即像水沸腾一般地汹涌翻滚着;“swelling”是指“the movement of the sea when it rises and falls without the waves breaking”(牛津词典),即海平面上升或下降引起的巨大震动。这两个词看似简单,却最大限度地将原文的特色呈现了出来,使读者能更好地感受到原作的语言风格。
其次,归化策略即改造外来文化,使之本土化,可以使目标语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欣赏母语作品的亲切感,便于对原作内容的理解。因而归化策略有助于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但有时却造成原作中地方文化特色的流失。王安忆被称为当代海派文学传人,她对上海及东方的语言、生活、韵味熟稔于心,因而在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具有东方特色的语言和文化元素。归化策略难免会减弱源语国的风格,如以下两处。
(1)上南边买草的马车“得得”的当街走过,车上张着被单作帆。老马低着头吭哧吭哧的走…(王安忆,2001:110)
A horse-car rattles along the street, heading south to buy hay. On the cart a bed sheet is hoisted as a sail. The old horse labors on, head down……(Hung. 1988:5)
汉语语言中,有很多我们自己熟知但西方并不了解的词语,特别是拟声词,在翻译过程中是一项挑战。如此处的“得得”“吭哧吭哧”,对于前者,译者试图按自己的理解进行阐释,通过同化策略将其处理为“rattles”(发出咯咯声响),不免有失源语特色;而后一个拟声词“吭哧吭哧”没有翻译,虽然在意思表达上与原文无差,但在氛围的营造上却少了一种俏皮轻松的因素,不能更好地展现东方的民俗风情。
(2)有那单身的光棍儿,便来不及起床,提起扁担就抡,却是抡也抡不开的,犹如出生就长在了一起。(王安忆,2001:114)
Some bachelor jumps out of bed, grabs a shoulder pole and hits at two cats blindly, trying to separate them, but they seem to have been glued together since birth.(Hung. 1988:12)
这里作者描述晚上的小城,成千上万只猫则沸腾着,扰得人不能安眠,半夜起来赶猫。译者将“单身的光棍儿”翻译为“bachelor”,将“扁担”翻译为“shoulder pole”,采用的都是归化策略,能准确表达原文的含义,但缺少了东方的文化特色,或许可以直接处理为“Guang gun”和“Bian dan”,然后添加注释更为妥当,可以带给读者具有东方特色的词语,增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相比之下,王安忆的代表作《长恨歌》在海外引发很大的反响,英文翻译者白睿文(Michael Berry)为让原作中上海风格最大化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他多次走访上海,亲身感受摩登城市上海的城市精神和文化风情并真切体验弄堂人家的日常生活。故而其英译本《长恨歌》里不乏地道的上海表述,例如在处理“弄堂”这个上海典型建筑时,译者没有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这一词汇下新定义,而是采取异化策略,直接处理为汉语拼音longtang,然后加以解释,最大化地向读者展示上海风情。而《小城之恋》的译者孔慧怡,出生于香港,后在伦敦大学就读,毕业后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长期与大陆生活的隔阂,不免对翻译中地方特色表达有疏离感,这导致其翻译忽略了王安忆作品中最有特色的部分——蕴含在文字中的东方风情。
总的来看,在文化态度的指引下,异化策略的使用展现了原作者的语言风格,然而较多归化策略的存在,造成了归异失衡,没有精准传递王安忆作品中的东方元素,从而产生了文化信息的不对等移植,妨碍了作品的海外传播。
三、译者的“现形”与“侵入”翻译方法
孔慧怡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及:小说译者并没有受到必须“忠实于原著”思想规范的影响,他们肩负着两种文化的中介人的职责,通过小说翻译实践教化民众的任务。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译者在翻译的具体过程中,量体裁衣,增删去补,甚至把个人的主观意志融入译本中。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不但是译者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由此可见,孔慧怡在翻译中主张实现译者的“现形”,通过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实现再创作,拓宽原作的表达空间,这体现为“侵入”的翻译方法。
(一)积极的侵入:实现视域融合
斯坦纳翻译理论认为,“侵入”的过程也就是译者对原文本的认识与解释,通过对原文的解码,侵入原文世界获取信息。而“积极的侵入”是指在这一理解过程中,虽然带有生成性和创造性,但能准确传达原文内涵,使译文更好地被读者接受。在《小城之恋》的英译本中,主要有以下几处:
(1)这时,她开始穿衣服了。推开门,阳光刺痛了眼,犹如热烈而粗暴的抚摸,她幸福极了。(王安忆,2001:113)
Now she starts to put in her clothes. She pushes the door open; the sunlight hurt her eyes like the touch of the passionate and violent lover. She is so happy!(Hung. 1988:9)
此处描写的是,在经历了一天的艰苦训练后,温暖的沐浴带给她的舒适。原文中写的是阳光“热烈而粗暴的抚摸”,而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处理为“lover”(恋人)的抚摸,既符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和表达习惯,又很好地暗示了下文二人成为恋人的情节。
(2)当他又一次重重的从人背上跳下来的时候,那人再止不住怨言了:“你是太重了。”他红了脸,转而反击道:“你是太熊了!”(王安忆,2001:113)
When he clumsily jumps off his partners back time and again, his partner can't help complaining,“You really are too heavy.”He turns red, countering, “you're just chicken!”(Hung. 1988:30)
男主人公终于有了新的角色可以演,但那舞蹈里有很多托举动作,可是看上去瘦小的他,“老红军”背不动他,排练时一次次地从对方的背上摔下来。当对方埋怨自己太重时,他回击道:“你是太熊了。”在这里作者运用了地道的表达,而译者考虑到西方读者难以理解,便采用侵入的策略,将其处理为西方的经典表达方式“You're just chicken”,让读者有阅读本国语言的熟悉感。
(二)消极的侵入:语言逻辑的减弱
由于译者无法不对他的时代和背景妥协,因而主体性的发挥是建立在译者的知识结构以及历史背景构成的一种“成见”的基础上。由于受到“偏见”的制约和影响,使得译者的理解具有历史性,无法完全客观地再现原文或穷尽对原文的理解,因而有时这种侵入并非都是积极的,在译者发挥主体性进行创造性表达的同时,有时会对原文的逻辑和心理刻画等造成一定的破坏,从而引发阅读障碍。如下面几例:
(1)她便作出满不在乎的傲慢样子,更高的昂首挺胸撅腚,眼珠在下眼角里不看人似的看人。(王安忆,2001:108)
She puts on a proud and disdainful look, holding her head high, throwing her chest out, and looking at others out of the corners of her eyes as though they were beneath her.(Hung. 1988:4)
这段是写众人在省艺校老师的带领下,一起查看她变形的身体,她感觉到了难堪,为了克服羞耻而装出一副高傲的样子。原文用了三个动词“昂首挺胸撅腚”,而译文很明显只翻译了前两个词语,应该是有维护目标语读者的审美体验的考虑;作为一名舞蹈演员,肢体的形态是他们向外界展示自己的名片,当她面对嘲讽时,便会选择用身体来作为对抗和回应;但译者却没有翻译“撅腚”这一看似粗俗却十分重要的一个特征,减弱了原文中“傲慢”姿态的形象性。
此外,“撅腚”也间接地反映出她不够完美的体型特征。在Aamer Hussein看来,舞者残缺不全、发育不良的身体,可以被解读为一个隐喻,象征着王安忆和她的角色所属的迷惘的一代漫長而荒废的岁月和发育不良的情感。因而译者对“撅腚”的漏翻,减弱了此种表达效果。
最后,因为她不完美的身材,在崇尚美丽和优雅的文化中便处于不利地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选择芭蕾作为自己的职业——这一职业体现了女性气质的精髓。尽管她是一个有天赋的舞蹈家,但她的职业前景注定是要失败的。因而“撅腚”更能反映出她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感到愤怒,故意蔑视所有传统的女性标准,为下文她打破性禁忌、与他发生关系做了铺垫,漏翻“撅腚”便失去了此效果。
(2)她长成了个大人似的,却依然是孩子脾性,说喜就喜,说悲就悲,喜过即悲,悲过即喜,转瞬万变,却自然得如同夏日的天,并不令人觉得无常和虚假。只是憨得可以。(王安忆,2001:115)
Though she looks like an adult she is still very childish. She never hides her feelings. She will be laughing one minute, crying the next, as changeable as the summer weather, and yet you don't feel that she's abnormal or affected, simply nave.(Hung. 1988:12)
参考文献:
[1]Aamer Hussein. Roots and affinitie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1, No. 4, Ethnicity in World Politics (Oct. 1989), p301.
[2] Sylvia Chan. Book Review: Love in a Small Town[J].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 26,July 1991.
[3]程福干.译者文化态度的多歧性与翻译策略的生态杂合——兼评许渊冲对昆明《大观楼长联》的翻译[J].河池学院学报,2015(4): 68-72.
[4]胡敏捷.孔慧怡女性主义翻译实践特点——对其《小城之恋》和《荒山之恋》翻译作品的解读[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4(3):30-32.
[5]贺晓旭,李艳.从乔治·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理论看译者主体性——以辜鸿铭《论语》译本为例[J].英语广场(学术研究),2013(2): 20-21.
[6]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7]卢峰.浅析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理论[J].文教资料,2011(5):32-33.
[8]穆雷,孔慧怡.翻译界:男性的一统天下?——香港女翻译家孔慧怡博士访谈[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2):108-111.
[9]苏秀云.中英翻译中的文化移植现象及策略探讨[J].福建茶葉,2019(3):255-256.
[10]吴赟.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传播与接受——白睿文访谈录[J].南方文坛,2014(6):48-53.
[11]吴义勤.王安忆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12]王东风.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J].中国翻译,2000(4):3-9.
[13]王岫庐.译者文化态度的多歧性及其对翻译过程的影响[J].中国翻译,2014(4):21-25+128.
[14]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见传人[J].读书,1996(6):37-43.
[15]朱振武,杨赫怡.《长恨歌》的归异平衡与汉学家的上海想象[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81-92.
[16]张广花,李建军.论对外翻译中的文化移植[J].浙江科技学院学报,2017(2):130-133.
作者简介:王圆圆,首都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黄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匹兹堡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海外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