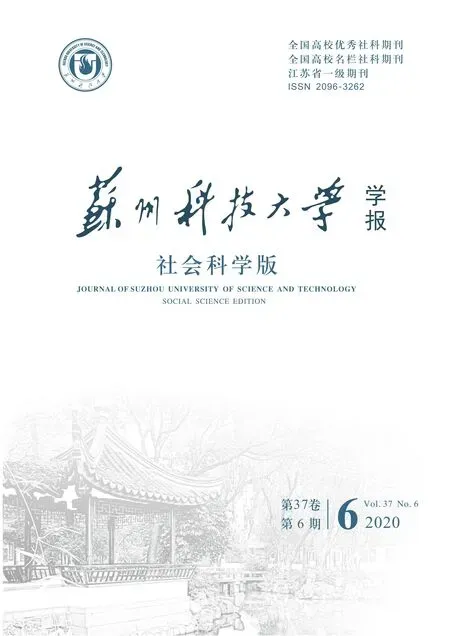论钱基博对桐城派的接受及其不拘骈散的文章观*
莫山洪
(南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299)
钱基博(1887—1957)是近现代著名的学者,著述甚丰,其在文章学上的著述较多,涉及骈文与古文,其中有名的著作如《骈文通义》《韩愈志》《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等,其《中国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史》等著作中也都涉及古文与骈文,而其对于桐城派的接受,既体现在其与李祥、陈赣一、冯超等人的信件之中,也体现在其一些文学史著作中。钱基博这些信件及相关著作体现出的不拘骈散的文章观,是在“五四”以来文化转型下的一种新型文章观念。
一、与李祥等人书信中体现出的钱基博对桐城派的接受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场围绕桐城派的讨论在几位学者之间展开,而引起讨论的文章是钱基博《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及《后东塾读书杂志》。这场讨论,核心人物是钱基博,先后有李祥、冯超、陈赣一等人参与其中。
首先看看引起李祥与钱基博展开讨论的《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一文到底提出了怎样的观点。
《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一文刊登于《弘毅月刊》1925年第1卷第2期,是钱基博为学生所作的一篇读书指导文章。钱基博对姚鼐的《古文辞类纂》颇为推崇,称“姚氏以《文选》之‘序’‘史论’‘史述赞’并入‘序跋’;‘表’‘上书’‘弹事’并入‘奏议’;……实较昭明为简当”[1]16,并且对桐城派还有这样的评价:“夫桐城派之起,所以救古典文学之极敝也”[1]18,“独念桐城派,让清一代文学之中坚也”[1]21,“独于姚氏此纂,虽病其规模少隘,然窃以为有典有则,总集之类此者鲜”[1]25。在全文中,钱基博引用了李祥讨论桐城派的文章:“近来兴化李祥论桐城派,以为程语斥曾非是,然姚序并称程周,语意甚明,普特遗程耳,不必李之为是而曾之为非也。”[1]19钱基博引用李祥的文章,意在否定其观点,自然也就引来了李祥的回应。
李祥(1859—1931)字审言,江苏兴化人,是晚清民国时期著名的骈文家,其辈分高于钱基博,所著《学制斋骈体文》影响颇大。李祥在看到钱基博的文章后,给钱基博写了一封信,对钱基博的一些观点提出了商榷。李祥以为,“足下张桐城之帜,仆扬甬东之波,为不同耳”[2],即两人是属于不同的阵营。确切地说,李祥以为自己是骈文派的,而钱基博则是桐城派的。鉴于钱基博对桐城派的极力推崇,或者说钱基博对姚鼐《古文辞类纂》的推崇,李祥称:“弟何敢诋诃桐城,但观以《古文辞类纂》为总集大成,置考据义理于不问,质则具矣,文于何有?”“贵同年林琴南,舍同乡前辈朱梅崖学问不顾,乃一意周旋马通伯及姚氏昆弟,将桐城派致之九天之上,其意云何?不过为觅食计耳。”[2]李祥对林纾等人给予了极大嘲讽,显示出骈文家的本色。对于姚鼐《古文辞类纂》中存在的重八家轻汉魏六朝文这一事实,李祥又说:“先生试寻秦汉以至北宋初元,有方今之文邪?抑前人皆非,而八家为初祖邪?”[2]直指桐城派的弊病。对此,钱基博回了一封信,对李祥颇为推崇,称:“大制《学制斋骈文》,渊懿粹美,文质相宣,近承容甫之嗣绪,远振学标之逸响,天下文章,其在扬州矣!”[3]程晋芳、周永年对姚鼐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而钱基博则称“天下文章,其在扬州矣”,可以视为其对李祥文章的肯定。同时,钱基博也表明了自己与李祥观点上有一致之处:“博早承父兄之教,年十五,即以萧选相课诵,略长,泛滥四部之书,自知文字蹊径,与桐城异趣,论古文亦以为取材宜富,效法宜上,窃自喜与先生论骈文之旨不谋而合也。”[3]后来钱基博果然作《骈文通义》,表现出其对骈文的钻研。李祥认为钱基博推崇姚鼐及桐城派,钱基博针对此也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近日斯文坠地,卑之无甚高论,即桐城文字,自今日学子视之,已以为奥诰雅谊,索解不得,若再高言汉魏,有不骇走且僵者耶?乃世人不察,誉之者以桐城嗣法见推,而后生不学,亦且与畏庐之桐城谬种,等量齐观。二十年来,蒙此不白之冤,实则桐城诸老,从前如姚姬传,并代如马通伯,容与闲易,未尝作态,自饶别趣,求之古集,政未易得。”[3]钱基博认为自己与桐城派并无直接关系,“博生平与桐城诸老,未尝有所因缘”,但是,“博服膺马通伯之桐城派散文,犹之服膺先生之选学”[3]。也正因如此,钱基博被人误解为桐城派中人,但他认为对此不必过多辩解:“世人既不我解,以桐城目我,则亦如庄生之呼牛呼马,以桐城应之,不愿以口舌相拄持。”[3]这番言论得到了李祥的高度认可,以致李祥有“钱子泉诚可为我友矣”[4]的感慨。在此基础上,钱基博又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文章观。在《再答李审言先生书》中,钱基博说自己“论文不立宗派,在曩时固不欲附桐城以自张,而在今日又雅勿愿捶桐城已死之虎取悦时贤”[5]3,表现出不受世俗影响的独立不迁的文章观念,而钱基博与李祥也因此成为文友。
不过,钱基博既表示了自己不受桐城派的影响,撇清自己与桐城派的关系,又很容易让人觉得他属于骈文派。于是,借着他的《后东塾读书杂志》发表之机,冯超又从桐城派的角度参与到这场讨论之中。
冯超字静伯,江苏通州人,为范伯子的再传弟子。冯超对钱基博《范当世范伯子文集十二卷》一文中对范伯子的界定提出了质疑。范伯子为江苏通州人,被视为桐城派后期作家。在《范当世范伯子文集十二卷》中,钱基博以为,“范氏力推桐城,而文章蹊径,实不与桐城相同”,“不过铺张桐城门面语”,“而其门人徐昂后序遽称以为传桐城之学,何啻皮相之谈”[6]。因为这句话,冯超以为钱基博判断有误。他认为,范伯子是“师武昌而友冀州,其学一本于桐城义法”,而钱基博“之于范先生之文其未尝一读而遽志之”[7],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对此,钱基博给予了一定的解释,认为自己的言论是诵读范伯子文章的感悟,“范先生风流文采,照映人间,博不过本研诵所得,抒其臆见”,之所以认为范伯子不与桐城相同,则是“而辞有抑扬,此乃博不敢自欺处”,自己诵读的结论如此,并非有意贬损。同时,钱基博也表达了对自己观点的坚持:“见仁见智,博不敢强人以从同,然亦不欲苟徇风气以张门户。”结合之前与李祥的讨论,钱基博也表达了自己被误解的尴尬:“李审言先生怪博抱一《古文辞类纂》,而不能高谈汉魏。足下乃谓博不得当桐城,此亦索解人难得之一也。”[8]6-7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钱基博的无奈。如前所述,李审言因《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一文认为钱基博是桐城派的,可是冯超又说他“不得当桐城”,确实是难以辩解。桐城派批其不为桐城派,骈文派也不认其为骈文派,都看出了问题所在,却都不知道钱基博其实是兼取众长、不拘骈散,旨在建立一种大格局的文章观。
其后,冯超又在《再与钱子泉论文书》中进一步指出:“今日与足下所讨论者,桐城学也。乃举《晋书》《南北史》自解,则方苞氏所谓古文中不可入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南北史》佻巧语,足下其忘之乎?抑未之知也。”[9]因此,他仍认定钱基博并未认真通读范伯子的著作,而只是“于范集或仅读前后两叙耶”。不过,冯超的观点于无意中恰好说出了钱基博的文章观,即不拘骈散,不受制于任何一种文体。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钱基博以给《青鹤》主编陈赣一写信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于桐城派的观点以及自己不拘骈散的文章观。在《复陈赣一先生论文书》(1)钱基博《复陈赣一先生论文书》,《青鹤》1933年第1卷第14期第1~7页,此文在《光华半月刊》(1933年第8期第10~12页)以《复陈赣一先生论桐城文书》为名刊发。中,他首先表达了对冯超信中所谈问题的关注及解释:“仆推大南通以别出于桐城而独树一帜,而冯君必欲卑之无高论,以附庸桐城为荣,则亦听之而已,……若真以仆之论为足轻重于伯子者,则岂仆始计之所及料哉。”钱基博在文章中表明,自己之所以将范伯子置于桐城之外,实则是对范伯子更大的推崇。对于冯超对自己的质疑,他也提出了非常尖锐的反驳意见:“冯君称伯子先生师事张武昌,奉手吴冀州,而以为出于桐城之证。此所谓鹪鹏已翔于寥廓,而弋者犹视乎薮泽也。冯君亦知吴冀州之所以论张武昌者,固明推之为开宗之一祖,而不敢以桐城之附庸目之乎。”正如“韩公得扬马之长,字字造出奇崛,欧阳公变为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后儒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则才气薄弱,不能复振,此一失也。曾文正公出而矫之,以汉赋之气运之,而文体一变,故卓然为一大家。近时张廉卿又独得于《史记》之谲怪,盖文气雄俊不及曾,而意思之恢诡,辞句之廉劲,亦能自成一家”,所以,“是皆由桐城而推广之,以目为开宗之以祖,所谓有所变而后大者也”。有改变才有创新,也才能体现出大家风范。“推是以论,则吴冀州已不安于桐城之学,而所以极推张武昌者,徒亦以其不落桐城窠臼。”这样的推导,最后当然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故仆推而大之,以异军特起于桐城之外而别名为派,犹之李审言先生之题,目曾文正为湘乡派,而谓是非桐城所得限。”
《青鹤》主编陈赣一对此也作了相应的回应,其《论桐城派》一文称:“文章无所谓派,亦非可以派囿之也,……苟必拘拘于门户之见,谓为文者宜作古文,古文尤宜学桐城,不学桐城,则不足言文,而非古文之正宗,奚翅会四渎之水于一流,不曰江河淮济之水,而统曰某水,可乎?岂料周氏一时兴到之言,而流毒及今,为文人学士聚讼之口实。桐城派与否之争,吾犹见其人闻其声矣。”他认为文章不应分派别,否则不利于文章的发展。同时,他声称:“古文不难为,择古人之书而熟读,而研讨,则古文自通,加以师承于文之法,尤可睹。是安得有派?派而不可说也,则桐城派之称不亦可已乎?”[10]这一论述比较公允。陈赣一不拘文派、不受某一派别限制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对钱基博是一种积极的支持。
二、钱基博不拘骈散的文章观
从钱基博的这些书信可以看出,对于桐城派,钱基博既肯定其成就,也指出其不足。钱基博认为,就当时而言,确实没有更合适的或者说更好的选本能如姚鼐之《古文辞类纂》那样,对学写文章的人能有足够的帮助。从这一意义上说,桐城派对于文章的传承功不可没。但是,文章创作一旦落入“派”的窠臼,就很容易出现停滞,不利于文学的发展。因此,钱基博对桐城派的存在又持否定态度,希望后学不断创新,超越所谓的“派”。这就是钱基博对桐城派的接受。
从钱基博与李祥、冯超及陈赣一等人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借助对桐城派接受的意见,钱基博主张文章的创作要有创新发展,不能囿于某一具体派别,文章创作应兼取众长,不拘骈散。
首先,钱基博主张文章当有创新,才有发展。要有创新,必须打破原有的格局,不受门户的限制。清代古文自形成桐城派之后,加上姚鼐及其四大弟子的推动,“天下文章其出桐城”,桐城派确实占据了清代的文章领域,成为影响最大的清代文章派别。“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文学中,就有“桐城谬种”之称,可以看出其影响之大。但是,文学创作的发展是必须要有所创新的。文学往往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的,继承前人是前提,是基础;创新是目标,是方向。没有继承,当然也就无所谓创新;没有创新,自然谈不上发展。众人以桐城派目范伯子,看到的是范伯子对桐城派的继承,这当然也没有疑问。钱基博在《后东塾读书杂志》中称范伯子“实不与桐城相同”,他抓住的正是范氏“瘦硬盘屈而出以绵邈”,并以此戏称“南通派”,指此派“以瘦硬盘屈取劲”,这也正是范伯子与桐城派“纡徐澹荡”的不同之处。这个不同,也就是范伯子的创新,是范伯子之为范伯子的原因。按照钱基博的认识,桐城派影响之下的曾国藩,形成“湘乡派”,这是曾国藩的创新带来的:“曾国藩……由桐城派而恢广之,以自为开宗之一祖,殆桐城刘氏所谓‘有所变而后大’者耶?”[11]曾国藩正是因为有了变化,才成就了“湘乡派”:“及其(曾国藩)自为文章,盖诵说桐城姚鼐之义法,至列之《圣哲画像记》曰:‘国藩初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然寻其声貌,略不相袭。大抵以光气为主,以影响为辅,力矫桐城懦缓之失。探源扬马,专宗韩愈。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谊,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异军突起,而自成湘乡派。”[12]曾国藩之所以能“异军突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略不相袭”。可见,钱基博论文最重创新。有创新,也可成为一派。桐城派影响之下,再出现一个“南通派”,这当然也是一种创新了。这样,范伯子显然还是有一定的创新,并不囿于桐城派的窠臼。
其次,钱基博认为,兼收并蓄、不拘骈散乃为文章正道。钱基博自己的学习经历,“五岁从长兄子兰先生受书,九岁毕《四书》《易经》《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古文翼》,皆能背诵。十岁伯父仲眉公教为策论,课以熟读《史记》,储氏《唐宋八家文选》。而性喜读史,自十三岁读司马光《资治通鉴》,毕沅《续通鉴》”。其所学多为古文,“为文初年学《战国策》,喜纵横不拘绳墨。既而读曾文正书,乃泽之以扬马,字矜句炼;又久而以为典重少姿致,叙事学陈寿,议论学苏轼,务为抑扬爽朗”[13]1-2,由此可看出其学习兼取众长,不拘骈散。他曾自题楹联云:“书非三代两汉不读,未为大雅;文在桐城阳湖之外,别辟一涂。”[13]3在评价韩愈的时候,他也特别重视韩愈的兼收并蓄:“韩愈议论学贾谊、董仲舒,序跋似刘氏向、歆,传记模《国策》《史记》,碑表出班固、蔡邕,而运之以司马迁之灏气,泽之以扬子云之奇字。韩文起八代之衰,只是集两汉之成。”[14]显然,对于韩愈的成就,钱基博更愿意相信他是在兼取众家之长的基础上实现的。钱基博因推崇姚鼐的《古文辞类纂》,被李祥视为桐城派人物,并与之展开讨论。而钱基博对范伯子的评价,又被人质疑,认为他不懂桐城派,诋毁桐城派。实际上,钱基博文章观念为博取众长,不拘骈散,他称自己的文章是“取诂于许书,缉采学萧选,植骨以扬马,驶篇似迁愈”[13]3,这也正是钱基博兼取众长、不拘骈散的主张与其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正因为如此,钱基博的文章在当时影响颇大,一些前辈名宿对其颇为推许,如“南通张謇以文章经济,为江南北士流所归重;及读基博文而叹曰:‘大江以北,未见其伦!’吴江费榭蔚曰:‘岂惟江北,即江南宁复有第二手!’而謇尤广为延誉”[13]3。
基于以上观点,钱基博主张摒弃门户观念,对桐城派及骈文派的态度不偏不倚,保持相对独立性。钱基博认为,文章的发展,创新是基础,兼取众长、不拘骈散则是方向。因此,文章的发展首先要摒弃门户之见,不立宗派。钱基博与李祥的讨论,是因为李祥认为钱基博在为桐城派大张旗鼓。为此,钱基博不得不阐明自己的主张:“博生平论文不立宗派。”[5]3“不立宗派”就是不以桐城派或骈文派自居,不按照两派的标准去评判文学,而是“兼收并蓄”[15]。钱基博主张学习他人长处,不受制于某一具体派别。所以,他在跟冯超论辩时,也进一步阐明了这一观点:“范九于并世稍稍能文章者无不以师礼事之,转益多师是我师,可为范九咏也。”[8]7“转益多师是我师”就是钱基博的文章发展主张,就是不能限定在一个派别之内发展,而是要多学习,学习不同的派别,不同的风格,这样才有可能创新,才有可能发展。
从文章发展来看,无论是桐城派还是骈文派,优秀之作往往是兼取众长,或骈中有散,或散中有骈。钱基博注重创新,不囿于某一派别,不拘骈散,更能认识到文章写作的真谛。
三、钱基博不拘骈散与时代的文化转型
钱基博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由近代转向现代的时期。西方文化的涌入,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也带来了冲击。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发生这样的争论,也是符合不破不立的发展规律的。
骈散相争,自清乾嘉以来,经阮元等人推波助澜,日臻激烈。但随着桐城派刘开等人比较宽容的理论的出现,骈散相争趋于缓和,且出现了不拘骈散的观点。进入20世纪,一些在骈文上有较大成就的作家,持论相对公允。即使如孙德谦,也主张融合骈散。他在《六朝丽指》中就曾谈到这样的观点:“夫骈文之中,苟无散句,则意理不显。……骈散合一乃为骈文正格。倘一篇之内,始终无散行处,是后世书启体,不足与言骈文矣。”[16]孙德谦是晚清民初的骈文大家,与李祥并称,其观点在当时颇有代表性。不过,他仍然是从骈文的角度来谈骈散合一,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李祥固守骈文派的传统,冯超一味强调桐城派的传承,都不是文学发展的方向。相较而言,陈赣一在这一方面表现出的则是比较中和的观点,也是于钱基博大力支持的姿态。
钱基博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也是西学东渐的时代。文化转型,从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变,是这一历史时期重要的文化现象。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固守原有的文化传统,固然有故步自封的局限,一味西化,也并非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如何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结合起来,寻找到符合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方向,这是当时文人所面临的问题。钱基博虽自幼学习传统文化,但他却不为传统文化所限,他积极投身时代变局之中,展现出一定的革新。他曾受聘于革命军,“历任援淮军司令部陆军第十六师副官参谋,授职陆军中校,调江苏都督府”,又辞谢直隶总督赵秉钧、江苏都督冯国璋的招聘[13]1-2,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思想。这样的经历,铸就了钱基博创新的文学观念。因此,他对当时的文学发展也有这样的意见:
民国肇造,国体更新,而文学亦言革命,与之俱新。尚有老成人,湛深古学,亦既如荼如火,尽罗吾国三四千年变动不居之文学,以缩演诸民国之二三十年间,而欧洲思潮又适以时澎湃东渐,入主出奴,聚讼盈庭,一哄之市,莫衷其是。榷而为论,其蔽有二:一曰执古,二曰骛外。何谓骛外?欧化之东,浅识或自菲薄,衡政论学,必准诸欧;文学有作,势亦从同,以为:“欧美文学不异语言,家喻户晓,故平民化。太炎、畏庐,今之作者;然文必典则,出于尔雅;若衡诸欧,嫌非平民。”又谓:“西洋文学,诗歌、小说、戏剧而已。唐宋八家,自古称文宗焉,倘准则于欧美,当摈不与斯文。”如斯之类,今之所谓美谈,它无谬巧,不过轻其家丘,震惊欧化,降服焉耳。不知川谷异制,民生异俗。文学之作,根于民性;欧亚别俗,宁可强同。李戴张冠,世俗知笑;国文准欧,视此何异。必以欧衡,比诸削足,履则适矣,足削为病;兹之为蔽,谥曰骛外。然而茹古深者又乖今宜;崇归、方以不祧,鄙剧曲为下里,徒示不广,无当大雅,兹之为蔽,谥曰执古。[17]9-10
“骛外”即全盘西化,以欧美之标准为标准;“执古”即故步自封,自以为是,完全不接受西方的观点。对于这两种情况,钱基博当然是不会赞同的。不“执古”,也不“骛外”,相较于当时的一些学者,钱基博所持态度更为公允。即使与20世纪30年代奠定现代骈文史观的刘麟生相比,钱基博也更开明,不像刘麟生那样过于强调中西的对抗[18]。因此,在文章创作的观念上,钱基博主张不拘骈散,“一阴一阳之谓道,用偶用奇以成文”,“文之骈散,不相废而相济也”[19],骈散相辅相成,不必拘泥于其中某一方面,这也体现了时代发展的影响。不随俗,保持相对独立,这也正如钱基博自己所说:“余耽嗜文学,行年六十,诵记所及,辄有撰论,不苟同于时贤,亦无矜其立异。”[17]10与其早年所称之“在曩时,固不欲以附桐城以自张,而在今日,又雅勿愿捶桐城已死之虎取悦时贤”[5]3何其相称,这也充分体现了钱基博独立的学术人格。
文化转型时期,新文化建设本来就处在探索之中。钱基博以丰富的国学基础,应对西方文化之影响,不局限于传统文化,追求创新,体现了特定时期开明学者的风范,也展现了合理的文章观念。其骈散观虽不能称为具有现代意识,却是文化转型下的文人自觉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