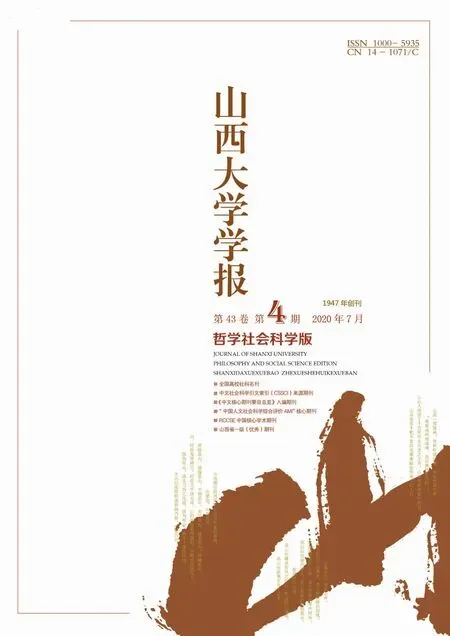论以新冠疫情作为中美商事合同的免责事由
刘 瑛
(武汉大学 国际法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2)
2020年1月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以下简称COVID-19)疫情已经并仍在持续对全球人类健康和生产生活造成重大影响,中美两国为应对疫情所采取的停工停业、国际运输阻隔等措施,也势必给中美当事人之间的部分国际商事合同的履行带来困境。本文拟对COVID-19及中美的疫情防控措施是否可以成为迟延或不履行国际商事合同的事由试做分析。
一、COVID-19及中美影响国际商务活动的措施
2020年1月23日,中国开始对当时的疫情中心武汉采取封城措施,整个中国内地随后采取了全面的居家隔离措施。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总干事谭德赛(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宣布COVID-19在中国的暴发符合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PHEIC)的标准(1)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tatement on the second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2005) Emergency Committee regarding the outbreak of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30 January, 2020),available at https://www.who.int/news-room/detail/30-01-2020-statement-on-the-second-meeting-of-the-international-health-regulations-(2005)-emergency-committee-regarding-the-outbreak-of-novel-coronavirus-(2019-nCov).。这一阶段,中国率先从中央到地方采取了严格的防控措施,包括隔离、停工停产、旅行限制、加强边境检查等措施,而且这些限制措施被严格执行,几无例外,中国的生产和与贸易密切关联的远洋运输受到了实质性限制,影响了中国当事人履行制造、交通物流、能源、金融服务等多个领域的国际商事合同。而在这一阶段,为有效防控疫情,美国早在2月2日即一般性禁止来自中国的人入境,进一步给中美两国商务带来重大影响,给商务合同履行造成困难。
进入2020年2月下旬,中国除湖北以外的其他省市逐渐复工复产,正在加紧履约之际,但COVID-19在世界范围内暴发,美国也是重灾区。3月11日,WHO宣布COVID-19为全球性流行病(2)WHO Director-General’s opening remarks at the media briefing on COVID-19 - 11 March 2020. Retrieved March 11, 2020, from https://www.who.int/dg/speeches/detail/who-director-general-s-opening-remarks-at-the-media-briefing-on-covid-19-11-march-2020.,已经取得疫情防控阶段性胜利的中国不得不再次面对输入型病例的严峻形势,于3月28日起暂停持有效中国签证、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入境,3月29日开始将所有国内外航空公司来往中国的国际客运航线压缩为1条,每周1个班次,国际商旅进一步受到限制,国际商事合同和国际协议履行势必继续受到影响。3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依据《国家紧急状态法》第201和301节和《社会保障法》第1135节宣布COVID-19在美国的暴发构成国家紧急状态(3)Proclamation on Declaring a National Emergency Concerning the Novel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Outbreak,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proclamation-declaring-national-emergency-concerning-novel-coronavirus-disease-covid-19-outbreak.,此后美国加州、纽约州封州,多城封城,非重要的生产和商务全面停顿,进一步造成供应链和产业链的断裂。3月18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为启动《国防生产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铺平道路,《国防生产法》要求私营企业将政府合同的执行优先于商业交易,公共卫生部已获得授权指导私营公司分配其业务、资源来满足危机应对工作的关键生产需求,必将影响国际商事合同履行。这一阶段美国企业出现大量撤单、履行延拓等违约行为。受影响企业面临交货困难、成本上升、资金链紧张、订单延期、货物拒收、企业用工难等多种困境,供给和需求端都受到影响,制造、建筑、采矿、商品市场、航运、旅游、航空、石油和其他能源行业影响尤大,已经订立的国际商事合同或不能履行或难以按期履行。虽然进入5月,美国各州开始逐步解封,但这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且受疫情影响,限制措施的解除和经济恢复都是一个缓慢过程。
在疫情的不同阶段,中美两国采取的抗疫措施既有阶段性区别也有重叠交叉的部分,尽管在线商务依然在进行,但由于中美措施具有绝对性的共同特征,几无例外,不可避免地,部分商务合同的履行受到直接的、难以克服的限制性影响。中美之间经贸往来频密,中美两国当事人可否以COVID-19本身及中美两国采取的防控措施为由主张未能完全履行合同的免责(exemption)(4)由于CISG第79条使用了“免责”这一中性表述,也鉴于中美两国在相关法律术语上存在较大差异,中国法主要使用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和情势变更(matters so standing),美国法主要使用受挫(frustration)、不可能(impossibility)、不可行(impracticability),中美商务合同也各有不同表述,本文就使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中立的“免责”这一表述来指代受影响当事人可以免于承担违约责任和主张重新谈判合同的规则。呢?
鉴于WHO只根据流行范围来界定“大流行”(5)Pandemic Influenza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a WHO Guide, pp.10-11, https://www.who.int/influenza/resources/documents/PIPbrochure.pdfua=1.,而PHEIC还从特定疾病本身的特征来做界定,以本文的写作内容计,仅考察WHO对PHEIC的界定。WHO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IHR)将PHEIC定义为“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构成对其他国家的公共卫生风险,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的不寻常公共卫生事件”,认定标准有:(1)情况严重、突然、不寻常或意外;(2)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3)可能需要立即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6)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art. 1(1) (2005).。被定义为PHEIC的COVID-19因此具有暴发上的突然和性质上的严重、不寻常等基本特征,可以以此与可能适用的法律规则所规定的免责事件做比对。
关于是否可以将COVID-19及中美两国的应对措施视作不可抗力或类似性质的事件从而为违约免责,存在不同的认识(7)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壳牌公司和安道尔公司拒绝了中海油以COVID-19作为不可抗力主张延迟收取货物的主张,Stephen Stapczynski, Shell, Total reject China’s force majeure on LNG shipments, World Oil (Feb. 7, 2020), https://www.worldoil.com/news/2020/2/7/shell-total-reject-china-s-force-majeure-on-lng-shipments.,中美商事主体是否可以以COVID-19为由主张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合同,需要依法进行考察。
二、合同免责条款及其解释
市场经济下的民商事法律以意思自治为核心[1],因此,首先需要考察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
在明确规定缔约方权利和义务的同时,国际商事合同和公私伙伴关系合同(8)世界银行公司伙伴关系法律资源中心(PPPLRC)对此类合同中不可抗力条款的介绍,https://ppp.worldbank.org/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overview/practical-tools/checklists-and-risk-matrices/force-majeure-checklist#checklist.中普遍设有条款规定一方当事人在合同订立后遭遇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事件,可以依据该条款主张不履行或迟延履行合同并且免于承担违约责任。能否以COVID-19为由主张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合同,首先需要考察合同中的免责条款。
免责条款可以详尽列明免责事由,也可以概括地规定免责事由的特征,如任何超出当事人合理控制范围的事件或情况,或者列举加上概括性条款兜底。清单通常包括自然事件,如洪水、火灾、地震、飓风等,和政治或人为事件,例如战争、内乱、入侵、暴动、罢工等。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科技进步,COVID-19所属的传染病大类,对全球绝大多数地区,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商贸活动已不构成大的影响,因此在西方主导的合同模板中,不再将传染病纳入免责,例外的是造船合同和租船合同。与COVID-19相关的政府行为,则比较有争议,但出于把政府行为列为免责事项是一种对政府滥用行政权力的包容,国际商事合同中通常也不将政府行为列入免责范围。而且部分政府行为是可以预见的,合同当事人应有时间通过各种途径获知,部分政府行为则可以克服,如提请行政机关重新审议、修改或撤销政府决定[2]。 免责条款还可能包括排除事件列表,例如财务困难(9)Westlaw Practical Law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General Contract Clauses: Force Majeure, available at https://1.next.westlaw.com/.,如此则难以以COVID-19造成资金紧张来主张迟延支付或取消购买。
以COVID-19主张免责,首先需要确定COVID-19本身还是政府因为COVID-19采取的措施属于合同约定的免责事项,判断应以合同约定为基准。如果合同的免责条款写入了传染病/流行病或者政府行为,则可直接主张,否则则需要考察合同的概括性约定,如其他订立合同时难以预见且影响难以避免和克服。按照一般用语,即COVID-19是否是订立合同时不可预见并且超出当事人合理控制范围的事件。WHO的PHEIC认定标准的第一项即是情况严重、突然、不寻常或意外,突然、不寻常或意外特征表明,对在1月31日WHO宣布认定之前订立的合同,应一般性视为符合不可预见性,而是否超出当事人合理控制范围,则需要主张的当事人来证明,尽管PHEIC的标准中有严重一项,但依然需要视该当事人的具体情况,是否有补救或替代措施,毕竟COVID-19在中美有不同的发展时间线和对应程度。
但是需要注意,如果适用法是美国法,即便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有概括性的兜底规定,只要列举中没有COVID-19可以确定归入的传染病/流行病或者中美政府防控措施所属的政府行为,也难以通过兜底规定把COVID-19纳入。以美国当事人最青睐的纽约州法律为例,司法实践表明,免责条款应狭义解释,免责事件必须是免责条款所明确考虑的(10)Phibro Energy, Inc. v. Empresa De Polimeros De Sines Sarl, 720 F. Supp. 312, 318 (S.D.N.Y. 1989) (citing Kel Kim Corp. v. Central Markets, Inc., 524 N.Y.S.2d 384, 385 (1987)).,必须不可预见且超出各方控制范围(11)In re Cablevision Consumer Litigation, 864 F. Supp. 2d 258 (E.D.N.Y. 2012).,即使发生极端和不可预见的事件,当事人通常必须论证事件属于合同用语所定义的免责事件(12)Reade v. Stoneybrook Realty, LLC, 63 A.D.3d 433, 882 N.Y.S.2d 8 (1st Dep’t 2009).,主张方通常还要证明该事件带来超出其控制范围的负担,并且其没有过错或疏忽(13)Phillips Puerto Rico Core, Inc. v. Tradax Petroleum Ltd., 782 F.2d 314, 319 (2nd Cir. 1985).。也即,当免责条款在特定事件外,还包含一个扩展的兜底条款,也只承认与列举事件同类的事件,而不是赋予兜底条款广泛的含义(14)Team Marketing USA Corp. v. Power Pact, LLC, 839 N.Y.S.2d 242 (3d Dep’t 2007).。
而如果适用法是中国法且中国法院作为管辖法院,则无论合同是否有免责条款,COVID-19都可以被认定为免责事件,进而结合合同具体情况来判定当事人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免责。因为尽管法律并未明示中国法中的不可抗力规定是否属于强制性规范,但最高人民法院在卓盈丰制衣纺织(中山)有限公司与广东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15)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一抗字第20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卓盈丰案”)中表示:“不可抗力是法定免责事由,它不因当事人的例外规定而免除”,并因此判定施工过程中的台风和暴雨属于不可抗力事件,当事人将不可抗力排除在免责事由之外的约定无效。但是,这个判断是在具体案件中,并非司法解释,该案也不是根据《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各级法院应当参照的指导案例,因此只具有参考意义。2020年2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发言人、研究室主任臧铁伟在解答COVID-19相关法律问题时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了保护公众健康,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疫情防控措施,对于不能履行合同的当事人来说,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16)http://www.xinhuanet.com/2020-02/10/c_1125556153.htm.。尽管发言人的解答本身不构成解释,但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主要的立法机关,该解答对中国执法和司法机关判断COVID-19和中国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是否构成不可抗力势必有直接影响。如果管辖法院选择依循卓盈丰案中最高法院关于中国法上不可抗力条款优先于合同的约定的判断,再结合发言人对COVID-19的定性,中国法院可能在合同约定外认定COVID-19本身和政府防控措施构成不可抗力。
最后,即使没有明确的免责条款,合同中的其他条款也可能会影响以COVID-19主张免责,如合同中关于风险分配的规定,又如法律变更情况下的重新协商。
三、依据CISG障碍条款主张难度较大
中国和美国都是《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CISG)的缔约国,CISG第1-6条规定了CISG的适用范围,则营业地分别在中国和美国的当事人之间订立的有形动产买卖合同,将依据CISG第1(1)(a)条直接适用CISG,除非双方当事人依据第6条(17)CISG第6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不适用本公约,或在第12条的条件下,减损本公约的任何规定或改变其效力”。排除了CISG的适用。CISG作为对缔约国有强制约束力的国际条约,是典型的硬法,在符合适用条件时应优先用以解决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争议[3]。美国签署了CISG,CISG因此成为美国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根据美国《联邦宪法》第6条,国际条约CISG应优先于州法律和联邦法[4]。中国也尊重民商事条约的优先适用,因此,除非国际货物买卖当事人合意排除或减损CISG条款的适用,则CISG应优先于中国法和美国法,适用于当事人间的交易[5]。 因此,对中美当事人的货物买卖合同,CISG适用的可能性较大,应当首先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需要明确,虽然CISG的适用主体主要为商主体,但主流的学说认为,在政府采购协议或国有企业作为一方主体的买卖中,当符合CISG适用条件时,也可以适用CISG[6-7]。
由于CISG第6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减损CISG的规定,因此在CISG作为适用法的情况下,如果合同中有免责条款,则首先依据合同的免责条款来判断COVID-19是否构成合同中的免责事件,而如果合同中对此没有规定,则适用CISG第79条(18)第79条并没有特殊性,依然后位于合同约定,这一论断为CISG成案所证实,也与卓盈丰案中认为不可抗力是强制性规则,与中国法上不可抗力规定相冲突的合同约定无效不同,参见UNVITRAL Digest of Case Law on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2016 edition, para.23, p.379.。此时,由于中国法并不是适用法,不能以中国法上的不可抗力条款排除合同免责条款的适用。
按照CISG第79条,如果不履行义务是由于一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能考虑到,也不能控制、避免或克服其后果的障碍(impediment),则可以免于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关键在于判断COVID-19及中美采取的防控措施和应急处置措施能否构成第79条所规定的障碍。
关于可预见,经常需要考察免责事件发生时间和合同订立时间的关系。在一个ICC仲裁案件(19)ICC Court of Arbitration7197/1992,1992,http://www.unilex.info/cisg/case/37.类似的,在一起保加利亚工商委员会仲裁庭裁定的案件中,尽管乌克兰政府对煤炭出口的禁止确实构成了卖方无法控制的障碍,但因为订立合同时该禁令已经生效,乌克兰卖方因未满足可预见条件而不能成功主张第79条免责,进而卖方也不能以矿工的罢工而被豁免,因为当时卖方已经未能如期交货违约,该违约排除了以后对免责事由的依赖,Bulgarska turgosko-promishlena, palata56/1995, April 24, 1996, http://www.unilex.info/cisg/case/422.中,奥地利的卖方和保加利亚的买方订立了销售合同,约定买方在预定时间开具跟单信用证,卖方在买方开证后四周内边境交货,但买方并未如期开证并以保加利亚政府暂停了外债支付为理由主张免责。法院认为,买方并没有证明未开立跟单信用证是保加利亚政府下令中止支付外债的结果,而且政府禁令在合同订立之时已经宣布,因此买方可以合理地预见到开立跟单信用证的困难,障碍不成立。因此,如果中美当事人之间的商事合同签订早于1月30日,可以认定COVID-19疫情及其防控措施一般意义上构成合同当事人无法预见的障碍,而由于中美两国政府都采取了绝对的强力措施,也可以构成无法预防、无法克服的障碍。从CISG的成案来看,卖方依赖供货的第三方供应商未履行义务不构成障碍,难以成功援引第79条免责(20)这方面的案例很多,参见UNVITRAL Digest of Case Law on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2016 edition, note 62-64, p.382.。
虽然有障碍存在,即使合同当事人可以有克服的方法或替代方案,仍然不能免责。在美国仲裁协会的一个仲裁裁决(21)Macromex Srl. v. Globex International Inc., American Arbitration Association, 50181T 0036406, December 12, 2007.中,一名美国卖方和一名罗马尼亚买方签订了几份出售鸡腿肉的合同,合同规定卖方不迟于2006年5月29日交付鸡肉,然而禽流感的暴发促使罗马尼亚政府禁止所有截至2006年6月7日未通过认证的鸡肉进口。卖方延迟发货,且未按时提供所有鸡肉的认证,买方依然接受了,并建议卖方将剩下的部分运到罗马尼亚境外的港口,但卖方拒绝,理由是罗马尼亚政府的禁令构成不可抗力事件,应终止合同,卖方后将未交付的货物卖给了另一位买方,获得了可观的利润。独任仲裁员认为,罗马尼亚政府的决定超出了卖方的控制范围,是双方在订立合同时无法合理考虑到的情况,但是卖方可以通过将货物运至买方提议的替代港口而合理地避免该禁令,因此仲裁员认定卖方不能依据CISG第79条免责。在一个报告的CISG仲裁案件中,仲裁庭的分析前提是把联合国对南斯拉夫的禁运视为障碍(22)CLOUT case No. 163, Arbitration Court attached to the Hungari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Hungary, December 10, 1996.,但美国依据《国防生产法》的优先生产应急物资只是顺序问题,美国生产方必须证明在优先完成政府合同的情况下,无法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或完全没有资源再进行商事合同的生产交付等。
值得注意的是,CISG第79条第3款明确规定,所规定的免责仅对障碍存在的期间有效,则需要仔细考察中国当事人主张不履行或迟延履行时,是否已经停工停产停止跨境支付或者与美国的运输清关受到了无法预防或克服的措施限制,类似的,美国当事人主张的免责也需要做时间与措施的对应性考察,特别在中美两国疫情发展和防控措施有时间差的情况下。尽管现在中国的疫情情况有所缓和,但美国已经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多州多城停止生产和货物运输,依然构成对中美商事合同的履行障碍,需要做阶段性细分考察。同时,因为COVID-19及政府的防控措施具有阶段性,可以先援引第79条主张迟延履行而不是直接主张完全不履行协议,例如中国的逐步复工复产就令依据COVID-19主张无法生产和提供货物的免责成为一个阶段性的事由,而如果对方当事人对时间的要求较高,则可以提出终止合同,双方都免于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整体而言,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CISG概要,第79条常被援引但成功的例子并不多,在5个缔约国上报的案例中,卖方成功地依据第79条免除了未履行义务的责任,但至少在另外27个判例中,法院驳回了卖方的免责要求;买方也4次被准予按照第79条规定免除责任,但至少在另外 14 个报告案例中此种请求被驳回。在2004年至2012年期间的CISG案件中(23)UNCITRAL Digest of Case Law on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2016 edition, paras. 7, p.375.,美国法院适用第79条十分谨慎,且无直接涉及传染病疫情为不可抗力的第79条适用案例。[8]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发言人已经表示COVID-19本身及政府防控措施构成不可抗力,如果中国法院适用CISG,则较有可能认定COVID-19本身及政府防控措施构成障碍从而获得对应程度的免责。
四、结合合理替代措施理解美国法的商业履行艰难
英美法恪守有约必守的原则,对不履行合同持严格的态度。以前文写到的合同免责条款为例,尽管美国各州的解释规则有所不同,但普遍不允许将免责默示地引入合同,即除非合同明确规定,不能认为缔约方默认某些事件可以作为不履约的理由。在合同没有约定免责条款的情况下,如果适用法是美国法,美国法上也提供了一些免责事由。
为适应商业实践的需要,在合同没有约定免责条款的情况下,为避免绝对履行可能导致的不公正结果,美国法终究还是认可了“无义务为不可能之事”(impossible Nulla Obligation Est),先后接受了英国法院所确立的“履行不能”(physical impossibility)和“目的受挫”(frustration of purpose)理论。履行不能即合同标的灭失使得履行从客观上不能实现,即完全不能履行[9]。根据一些州的法律,如果发生合同签订时未曾预料的事件导致无法履行义务且该方没有任何过错,则该方可以免除合同义务(24)Restatement Second, Contracts § 261; see also Consumers Power Co. v. Nuclear Fuel Services, Inc., 509 F. Supp. 201, 209 (W.D.N.Y. 1981).。这里的事件限于完全无法预见且客观上使履行无法实现的事件,没有预料到的困难是不够的(25)Phibro Energy, Inc. v. Empresa De Polimeros De Sines Sarl, 720 F. Supp. 312, 318 (S.D.N.Y. 1989).,如果只是难度或成本水平的变化,例如更高的工资,不足以免除合同义务,同时如果主张方的疏忽对于该事件造成的损害有贡献,则该方也不能免除责任(26)Team Marketing USA Corp. v. Power Pact, LLC, 839 N.Y.S.2d 242 (3d Dep’t 2007).。目的受挫则为可能履行的合同的不完全履行提供理由,如果对主张方而言,新发事件已经损害了合同履行的预期目的则可诉诸目的受挫(27)RFF Family Partnership, LP v. Link Development, LLC, 962 F. Supp. 2d 344 (D. Mass. 2013).。在COVID-19疫情本身及防控措施本身,都难以满足履行不能的要求,目的受挫倒是可能的,例如买方购买本是为了用于再生产、再售或提供服务,但因为停工停业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能实现。目前,中国外贸企业正遭遇退单潮,其中不乏美国企业因为州政府禁足令而取消订单,如果适用美国法,可能主张目的受挫。
然而在有的情形下,合同仍可履行并且合同目的仍可实现,但是由于意外事件出现,按原合同继续履行会导致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不均衡,而履行不能规则的条件过于严苛,于是美国在契约受挫制度(contractual impracticability)下又创设出商业履行艰难(commercial impracticability)规则(28)虽然目的受挫、履行不能和商业履行艰难定义各不相同,但都属于“契约受挫”制度,参见:Peter J.M. Declercq, Modern Analysis of the Legal Effect of Force Majeure Clauses in Situations of Commercial Impracticability,Journal of Law and Commerce, Vol.15, 1995, p. 213.。商业履行艰难首次出现在1916年Mineral Park Land Co. v. Howard案中,加州最高法院判决称,“当一件事需要过高且不合理的成本才能完成,其履行是艰难的,而履行艰难属于法律上的不能履行。”(29)Mineral Park Land Co. v. Howard - 172 Cal. 289, 156 P. 458 (Cal. 1916).该案中创设的履行艰难一词后来出现在1932年《美国合同法第一次重述》第454条中,规定“履行不能不是指严格意义上不能履行,而是指由于极端或不合理的困难、成本、损失所导致的履行艰难。”(30)Restatement (first) of the Law on Contracts, 1932, p. 454.此后,Mineral Park Land Co. v. Howard案所发展的富有弹性标准的履行艰难理论在美国《统一商法典》(Uniform Commercial Code, 以下简称UCC)第2-615条中以成文法的方式予以明确,规定如果由于发生了订立合同时作为基本前提条件而设想不会发生的特殊情况,致使卖方确实难以按约定方式履约,则卖方在满足及时通知及最大程度履约的前提下,其延迟交付或瑕疵交付的行为不构成违反买卖合同义务,也不因违反合同义务承担责任。然而依该条规定,不能履行免责条款似只可由卖方主张,条文未明确规定买方是否可依此条主张免责。但UCC评论第9条建议商业履行艰难也可适用于买方,学者对此也多持肯定态度(31)U.C.C. § 2-615 Comment. 9 (2013); Thomas Black, Sales Contracts and Impracticability in a Changing World, St. Mary’s Law Journal, Vol. 13, No.2, 1981, p. 257; Richard W. Duesenberg, Exiting from Bad Bargains via U.C.C. Section 2-615: An Impracticable Dream, UCC Law Journal, Vol.1, pp. 32-35 (1980).。在COVID-19疫情及中美防控措施下,生产原料供应、劳动力到位、运输物流速度、通关手续办理等都全方位受到影响,履行难度和成本都有较大增长,是可以尝试主张商业履行艰难的。
需要强调的是,UCC第2-615条的履行艰难需要与第2-614条所规定的以替代方式履约结合起来理解,因为第2-615条的前言规定了除非第2-614条另有规定,由此可以推出,如果有替代方式履约,则不能主张履行艰难。第2-614(1)条规定了在商定的入泊、装货、卸货设施和船舶无法使用或获得,约定的交付方式难以完成时,如果有合理的商业上的替代方案,卖方应提示买方且买方应接受该替代方案,关于这一条有大量案例做了细化说明,并将替代方案扩展到买方的合理建议(32)American Trading & Production Corp. v. Shell International Marine, Ltd., 453 F.2d 939, 942-43 (2d Cir. 1972); Eastern Air Lines, Inc. v. McDonnell Douglas Corp., 532 F.2d 957 (5th Cir. 1976); Fabrica Italiana Lavorazione Materie Organiche, S.A.S v. Kaiser Aluminum & Chemical Corp., 684 F.2d 776, 778-79 (11th Cir. 1982); Jon-T Chemicals, Inc. v. Freeport Chemical Co., 704 F.2d 1412, 1416-17 (5th Cir. 1983); Camden Iron & Metal, Inc. v. Bomar Resources, Inc., 719 F.Supp. 297, 309 (D.N.J. 1989); United Equities Co. v. First National City Bank, 52 A.D. 2d 154 (N.Y. App. Div. 1976.。因此,在当事人以COVID-19疫情及中美防控措施所造成的履行艰难来主张免责时,需要用尽自己所能设想的和对方提出的商业上的合理替代措施,否则就不能成功。
五、依据中国法主张不可抗力免责难度相对较小
中国法上广义上的免责条款主要是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
2020年5月28日全国人大通过的《民法典》在合同编“违约责任”章第590条规定,当事人因不可抗力而不能履行合同的,可以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全部或部分免责。进而,《民法典》在合同编“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章第563条明确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诚如前文所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发言人已经明确表示,对合同当事人而言,COVID-19这一突发公共事件及中国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系不可抗力。尽管这一表述并不构成正式的立法解释,但鉴于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作为我国的重要立法机关,应对前述法律的解释具有直接指导意义。
中国法上的不可抗力的构成要件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此次COVID-19疫情,结合WHO对PHEIC的认定,其发生具有突然性、意外性,而中美两国采取措施也具有果断、决绝的特征,且两国在疫情暴发和政府措施时间上有先后的同时更有重叠,因此如果合同签订于PHEIC认定之前,应认定为双方无法预见,而且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严格的人员流动、物资运输和商业生产管控措施,美国联邦已经启动《国防生产法》进行战时生产管制,各州越来越普遍施行禁足令,这样的疫情防控措施是商事主体不可避免和不能克服的,属于不可抗力应不存在争议。
与CISG的免责相对应(33)主流观点认为,CISG第79条包括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由世界范围内代表性学者组成的咨询委员会也持这一观点,参见The CISG Advisory Council-Opinion No. 7, Exemption of Liability for Damages under Article 79 of the CISG, 12 October 2007, paras.26.,中国法上除了不可抗力,还有情势变更。情势变更制度最初见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6条,也为《民法典》合同编“合同的履行”章第533条纳入(34)《民法典》合同编第533条: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所谓情势,指一切为法律行为成立基础或环境之客观事实[10], 变更即重新磋商的过程,其制度目的在于,当合同赖以正常履行的客观事实发生不可预见变化、继续履行原合同会对当事人一方造成巨大的不公平时,应合理分担风险,最大化保障合同双方利益的平衡。
中国采取的二元规范模式将情势变更制度与不可抗力制度分别作了规定,不可抗力并不是情势变更的原因,但在具体法律适用中却突破了该种限制,法院在诸多个案中已经将不可抗力事件纳入可以适用情势变更制度的范围[11]。仅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期间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关审判、执行工作的通知》为例,该通知规定,“由于‘非典’疫情原因,按原合同履行对一方当事人的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合同纠纷案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适用公平原则处理”;“因政府及有关部门为防治‘非典’疫情而采取行政措施直接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者由于‘非典’疫情的影响致使合同当事人根本不能履行而引起的纠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7条和第118条的规定妥善处理。”前者的措辞近似情势变更,后者因为直接援引《合同法》条款应解读为不可抗力,同样的事由,既是不可抗力,又是情势变更,适用于民商事合同。
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之所以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做到泾渭分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两项制度具有较大的共性,均规范当事人难以承受的、支配领域外的风险。[12]鉴于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发言人的明确态度,将COVID-19及其防控措施都视为不可抗力,则在适用中国法时,被认定为不可抗力几无争议,可以主张对应程度的免责。但结合下文对同样分别规定了不可抗力和艰难情形《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解读,以及中国的司法实践,将COVID-19带来的不可抗力作为情势变更的一种,进而依据情势变更主张重新协商和变更、解除合同,在中国法院管辖下,也是一种可能的路径。
六、运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辅助解释适用法主张免责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Unification of Private Law, UNIDROIT)制定和通过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 PICC)是由UNIDROIT组织、制定并颁布的特殊的国际法律重述,不具有强制约束力,但按照其序言的规定,当事各方同意其合同受PICC或一般法律原则、商人法或类似法律约束时,可以适用PICC,当事各方未选择任何法律来管理其合同时,也可以适用PICC,PICC还可以被用来解释或补充国际统一法律文书和国内法,作为国家和国际立法者的榜样,典型的如解释或补充CISG。UNILEX数据库(35)UNILEX数据库由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Italian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资助,提供CISG和PICC的文本解释、案例库和研究成果,网址见http://www.unilex.info。显示,美国法院较多使用PICC解释其他国际法律文件(36)例如,美国法院援引PICC条款解释《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公约》,Koda v. Carnival Corp.,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S.D. Florida, 06-21088, March 30, 2007, available at http://www.unilex.info/case.cfm?id=1528; Nikola Krstic v. Princess Cruise Lines, Ltd.,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S.D. Florida, 09-23846, March 25,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unilex.info/principles/case/1526; Amanda Matthews v. Princess Cruise Lines, Ltd.,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S.D. Florida, 10-60830-CIV, July 7,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unilex.info/principles/case/1631.,伊朗-美国联合仲裁院的裁决将PICC作为适当的法律规则适用并依据其第7.4.9(2)将利率确定为以支付地当前主要货币向主要借款人贷款的平均银行短期贷款利率(37)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V.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ranian-U.S. Arbitral Tribunal, July 2, 2014, http://www.unilex.info/principles/case/1856.,美国海外私人保险公司在行政决定中也援引PICC第2.1.1条来确定美国企业与投资所在国阿根廷政府之间是否成立合同(38)Administrative Determination of 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DB/OL].[2020-04-20].http://www.unilex.info/principles/case/1125.,中国法院则有一个案件(39)Hengxing Company v. Guangdong Petrochemical Subsidiary Company, Shaoguan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ShaoZhongFaMinErChuZi n.8, April 28, 2005, available at http://www.unilex.info/case.cfm?id=1120.运用PICC解释情势变更,同时在另一个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40)Xiamen Xiangyu Group Corp. v. Mechel Trading AG, Xiamen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XiaMinRenZi No. 81, December 14,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unilex.info/case.cfm?id=1121.中,法院裁定仲裁当事人可以合意选择PICC作为合同准据法。可见,中美两国都对PICC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运用,在因COVID-19引起的中美当事人的商事合同纠纷中,法院和仲裁庭也可能会以不同方式适用PICC,包括但不限于用PICC补充解释作为适用法的CISG和作为适用法的中国法或美国法,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当事人选择PICC普遍可以被接受,仲裁庭还可能在当事人选择一般法律原则、商人法时,将PICC作为一般法律原则、商人法惯例的体现加以适用。
相对于CISG,PICC的规定更为详尽,可以用来解释和补充CISG,而且其调整对象不仅包括CISG调整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还包括服务贸易合同等各类商事合同。PICC第7.1.7条的不可抗力与CISG第79条的免责在规则上如出一辙,只是PICC第7.1.7条第4款细化了另一方当事人的救济权利,即宣告终止合同、暂不履行或索取利息。[13]前文已经分析过,COVID-19本身及其防控措施是否构成不可抗力,得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但整体上也是从严掌握。首先所主张的事件一定是订立合同时不可预见的。在乌克兰高等商业法院的一个判决(41)High Commercial Court of Ukraine, 42/90-10, November 30, 2010, http://www.unilex.info/principles/case/1700.中,乌克兰卖方与俄罗斯买方签订为工业加工供应14 000吨玉米的合同,但由于俄罗斯联邦兽医和植物检疫控制局拒绝签发所需的进口检疫许可证,俄罗斯买方要求卖方停止装运,后主张终止合同,卖方拒绝并提起诉讼。经过五轮诉讼,法院认定,买方订购的玉米数量已经超过了其先前已获得的进口检疫许可证的进口数量限制,而且买方应该知晓俄罗斯当局不太可能授予其额外数量的许可证,而买方此前没有遵守规定的检疫隔离措施的行为也是俄罗斯当局拒绝新的许可证的原因之一,因此不构成不可抗力,法院判决的法律依据中包含PICC第7.1.7条。其次,具体到什么事项能构成不可抗力,得从事件本身的特征,是否可以避免和克服来考察。直接影响合同当事人的政府禁令可能构成不可抗力。在俄罗斯科米共和国上诉法院的一项判决(42)Second circuit Arbtrazh Court of Appeal, A29-296/2012, August 31, 2012, http://www.unilex.info/principles/case/1833.中,一家俄罗斯公司与俄罗斯公路局签订合同,由俄罗斯公司沿道路砍伐树木并应公路局要求额外完成燃烧利用剩余树木的工作,但在合同履行中国家制定了一项特殊的防火方案,俄罗斯公司因此无法完成合同所约定的额外工作。上诉法院推翻了一审判决,依据俄罗斯《民法》和《商业程序法》、PICC第7.1.7条确认了新的防火制度的生效相当于不可抗力,无须支付合同约定的不履行罚金。再次,如果可以通过商业安排,则政府禁令不能构成不可抗力。在常设仲裁庭的一个案件(43)Granuco S.A.L. v.The 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AA 286, April 3, 2009, http://www.unilex.info/principles/case/1881.中,卖方是一家在西班牙设有工厂的黎巴嫩公司,它与买方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订立合同销售特定规格的动物饲料,买方在卖方未遵守交货条款并催告无果的情况下终止了合同,卖方反对终止合同,称合同订立后,欧盟禁止出口合同约定的饲料类型到第三国,而买方就是要再转口到被禁止的伊拉克。合同约定适用非任何国家法律制度的一般法律原则,仲裁庭没有直接讨论法律适用,但在裁决中实际适用了双方在文书中援引的PICC,最终认定欧盟禁令并不构成绝对的执行障碍,正如卖方能够将生产地从西班牙工厂转到巴西的工厂以规避欧盟的禁令,该案中的禁令并非不可克服,尽管没有指明条款,但从分析来看,是PICC第7.1.7条。最后,与CISG成案类似,供应商不履行合同通常不作为不可抗力理由。如在立陶宛最高法院判决的一个案件(44)Supreme Court of Lithuania, 3K-3-10-421/2015, February 4, 2015, http://www.unilex.info/principles/case/1890.中,两家立陶宛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买卖在俄罗斯生产的150辆货车,随后立陶宛卖方宣布无法交货,因为俄罗斯制造商基于俄罗斯政府禁止从乌克兰进口生产其所需的零件而无法如期生产,卖方主张不可抗力,法院依据《立陶宛民法典》第6.212条和PICC第7.1.7条判决买方胜诉,认定分包商之一未能履行合同不构成不可抗力。
与CISG的单一免责条款设置不同,PICC第6.2.2条和6.2.3条规定了艰难情形。艰难情形指由于发生意外事件使得一方履约成本增加或所获履约的价值降低,导致合同双方的利益均衡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而该事件在合同订立之后才发生或才为受到不利影响的当事人所知悉,且受到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能合理地预见到该事件,不能控制该事件,该事件的风险也不由受到不利影响的当事人承担。第6.2.3条进一步规定了发生艰难情势的后果,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有权及时请求重新谈判,若谈判不成,任何一方有权诉诸法院。
对分别规定的两分法,PICC第6.2.2条的注释6专门解释道,可能存在一些事实情况同时被视为不可抗力和艰难情形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应由受这些事件影响的一方决定采取哪种补救措施,当事人援引不可抗力是为了免责,援引艰难情形则是为了重新谈判合同的条款,以便使合同按修订后的条件继续存在。
七、结论
作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全球流行病,COVID-19本身和世界各国采取的防控措施,给全球商业活动造成了巨大障碍,中美两国也先后面临疫情大暴发,分别采取了诸多商业限制措施,中美商事合同主体可以以此为由来主张免责。
首先考察国际商事合同,各方应评估是暴发本身还是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阻碍履行或导致合同义务履行延迟,并结合合同的免责条款来衡量主张什么免责事项,毕竟免责条款的设计各不相同,在条款的示例列表中明确包含的事项更有可能成功。特别需要注意,在美国法下,抽象概括的兜底免责条款并不被赋予超出列举事项的含义,只能试图将所主张的免责事由解释进列举事项。相反,如果适用中国法,则即便合同无约定,如果管辖法院选择依循卓盈丰案中最高法院关于中国法上不可抗力条款优先于合同约定的判断,根据中国法上的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规则,再结合发言人对COVID-19的定性,中国法院在合同约定外认定COVID-19本身和政府防控措施构成不可抗力的可能性较大。也因此,当合同有免责条款且合同免责条款并未列入流行病或政府行为时,适用法比较关键。如果当事人约定适用中国法或美国法,该约定通常都能得到尊重,而如果没有约定,由于中美两国均为CISG缔约国,则适用CISG的可能性较大。
CISG第79条规定了免责,COVID-19和相关政府措施必须是主张方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且直接造成合同无法全部或部分履行。从成案来看,需要考察免责事件发生时间和合同订立时间的关系,即便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但只要合同当事人可以有克服的方法或替代方案就不能认定为不可克服,其中卖方依赖供货的第三方供应商未履行义务、财务负担或利润下降、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减少通常不构成障碍,违约在先亦不能以后发的障碍为借口不履行义务。PICC除了可以帮助解释和补充CISG,还可独自适用,中美法院和国际仲裁中都曾运用PICC的不可抗力和艰难情形规则,而根据PICC第6.2.6条的注释,当COVID-19和相关政府措施同时符合其不可抗力和艰难情形的要素时,当事人可以选择其中一项来主张。中国同样是两个事由并立,在国际商务纠纷中,可以以PICC作为支持当事人选择权的资源。无论CISG还是PICC,都有一些支持政府禁令作为免责事项的成案,中美两国严厉的管控措施几无例外,只要与主张的违约行为之间具有对应性,应能主张免责,但未见传染病本身免责的成案。
美国法上的目的受挫和商业履行不都可资援引免责,其中商业履行不能需要与替代方式履约结合起来理解。中国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发言人肯定了COVID-19本身和中国政府管控措施构成中国法上的不可抗力,应有指导意义,而出于对等原则,对美国政府的管控措施也可能做相同的认定。
本文建议,无论是依据合同条款还是不同的适用法的规定来主张免责,都紧扣WHO对PHEIC定性的特征来证明事件的不可预见、避免或克服,毕竟《国际卫生条例》是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定。相反,尽管2020年2月2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向受COVID-19影响的中国公司颁发了首份不可抗力证书,并对认证平台进行改造以新增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的在线申请功能(45)中国贸促会商品认证平台,网址为http://www.rzccpit.com/.,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出具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证书是否能影响到美国法院或者国际商事仲裁庭对免责事件的解释,还有待观察。
得益于中国政府的强有力措施,中国的COVID-19疫情已经基本被控制,经济活动正在复苏,政府的管控措施逐渐缓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执行官预计我国经济可能在第二季度回到正轨(46)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Remarks by IMF Managing Director Kristalina Georgieva to G20 on Economic Impact of COVID-19, available at https://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20/02/22/pr2061-remarks-by-kristalina-georgieva-to-g20-on-economic-impact-of-covid-19 (Feb. 22, 2020), visited on March 7, 2020.,因此未来中国当事人主张免责的难度会增大,相反美国商事主体相对更容易成功。但这是现阶段,公共卫生专家提醒新冠病毒或将长期存在,考虑到疫苗研究周期,在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内,随时可能反复,未来形势并不明朗。因此建议商事主体在合同中写入免责条款,并明确列举流行病和政府禁令。鉴于政府禁令在适用法上的接受度已经较好,重点是参考国际商会推荐的免责条款,其中第5段写入了“瘟疫、流行病”(47)Act of God,plague, epidemic, natural disaster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violent storm, cyclone, typhoon, hurricane, tornado,blizzard, earthquake,volcanic activity, landslide, tidal wave, tsunami, flood, damage or destruction by lightning, drou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