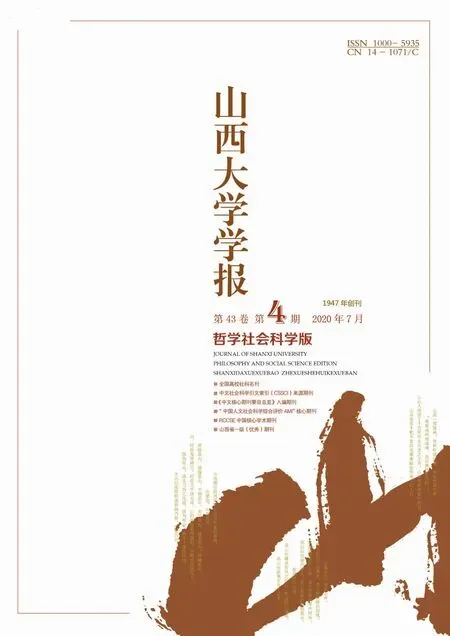教材的意识形态及其理解
张建琼,岳定权
(四川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作为一种法定文本,教材是传承人类知识文化,培养社会公民,凝聚民族精神与性格的重要载体。新时代以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道路,教材建设也在借鉴国外经验与总结本土经验的基础上,以“三科教材”统编为标志,通过政策导向、知识准入与教材使用等途径加强了意识形态建设。这对教师的教材理解提出了新的挑战,教师只有在正确认识教材的意识形态特征,深刻把握教材中意识形态的存在方式基础上深入理解教材中的意识形态,才能在课堂上真正实现有价值的教学。
一、教材的意识形态特征
意识形态概念产生于西方哲学家在批判中世纪神学与经院哲学过程中对如何形成正确观念的执着追求。在这一过程中,培根(F.Bacon)在指出错误观念来源的“四种谬见”基础上,认为“用真正的归纳法来形成概念和原理,毫无疑问这是排除和肃清谬见的良药”[1]。洛克(J.Locke)在《人类理解论》中则认为观念起源于经验,并受制于文字的运用与人的判断力,只有在经验的基础上,准确使用文字和严格进行判断,人的观念才可能成为科学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法兰西研究院的托拉西(D. D.Tracy)在其著作《意识形态的要素》中首次提出了意识形态概念,并期望基于意识形态概念建设一门基础性的哲学理论,专门探讨人的正确观念形成问题。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是意识形态研究的重要成果。马克思从社会学出发,基于唯物主义立场,运用唯物史观思考与看待意识形态问题,找到了意识形态存在的社会根源,并将意识形态与人类社会发展、阶级斗争等整合起来,为意识形态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功能与价值进行了科学定位。俞吾金在《意识形态论》著作中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内涵概括为:“在阶级社会中,适合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起来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其根本特征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用幻想的联系来取代并掩蔽现实的联系”[2]。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来看,意识形态具有三重内涵。第一,意识形态形成的根源是经济基础。这一内涵明确了意识形态的发生学基础,使意识形态从一个虚假概念转变成了一个中性概念,指明了社会生活、社会生产等经济基础是形成意识形态的根源。第二,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是阶级性。这一内涵明确了意识形态的根本属性,使意识形态从认识论转向实践论,指明了意识形态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思想价值体系。第三,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这一内涵明确了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指明了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主要精神手段,它由统治阶级创造、建构、传播,促使社会成员认同,进而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
依据马克思意识形态内涵,教材的意识形态指在教材的政策导向、知识准入与具体使用中必须体现国家和政府所倡导的思想价值体系。这种思想价值体系一方面来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现状与未来构想,体现的是国家与政府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通过教材政策制定、教材知识准入以及教师教材使用规范等方式渗透于教材之中,希望学生在教材学习过程中能够对这种思想价值体系进认识、认同与践行。
从研究来看,教材的意识形态特征早已被研究者所揭示。阿普尔(M.W.Apple)在《意识形态与课程》中明确指出“教育并非一个价值中立的视野……教育工作者不应该把他们的教育活动与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和支配我们先进工业经济的各种意识形态完全分裂开来”,[3]意识形态通过合法性、权力与语言修辞等方式存在于课程之中,构成了课程的基本特征。派纳(W.F. Pinar)等所著的《理解课程》开启了“课程理解”范式,通过把课程视为一种符号表征,而使教材可以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文本,“我们可以说把课程理解为符号表征的努力,在相当程度上确定了当代课程领域”[4]。随着知识社会学的发展,教科书的意识形态研究也逐步深入。近年来,我国对教科书意识形态的研究逐渐增多,主要采用“主题——量化”研究方法,对教科书中意识形态特征及其渗透方式进行了量化分析与价值判定。[5]总之,教育作为社会子系统,必然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体现着政治性特征,而教材作为教育内容的核心载体,其建设与发展必须服从于国家发展战略,体现国家意志,展现意识形态特征。
在我国新时代的教材建设中,教材意识形态的内容也逐步确立,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坚持文化自信。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它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状况,是建构民族精神信仰、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其根本,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第二是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分别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阐述了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应该具有的价值观念和基本责任,是维持、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是教材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环节。第三是坚定政治信仰。“政治信仰是人们对理想的政治理念、政治活动、政治制度、政治目标等的确信、认同、敬仰和追求”,[6]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蕴含着一种特定的政治信仰。就我国而言,共产主义理想是其核心的政治信仰,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指向,它要求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以人民为中心,以民主与法制为基础,共同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二、教材中意识形态的存在方式
从教材建设过程来看,教材的意识形态主要通过教材政策制定、教材知识选择与教材使用规范来实现,这凸显了教材中意识形态存在的三种基本方式,即政策性存在、知识性存在与使用性存在。
(一)政策性存在
教材政策是“国家和政府在一定区域内、一定时期内,为实现教育目标对教材的编纂、审查、出版、发行、选用,按照一定的程序制定的规范准则”[7]。教材政策作为引导教材改革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是从法定意义上对教材的建设理念、方向目标、内容途径等的基本规定。国家与政府主体通过制定教材政策规定教材建设需要体现什么样的思想价值体系便构成了教材意识形态的政策性存在方式。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教材政策所体现的意识形态特征逐步加强。在经历了从国定制到审定制转变后,到2014年,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正式提出对《道德与法制》《语文》《历史》三科教材进行统编,教材进入了国定制与审定制并存的局面。郑富芝在2017年教育部“教育新春系列发布会”上强调:统编三科教材是“立足于党和国家的全局,实现长治久安,做出的一项重大的决策部署”[8],统编三科教材成了新时代国家和政府加强教材意识形态建设的标志性事件。为了进一步明确和加强教材意识形态的建设方向,2016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强调了“教材建设作为国家事权”的重要性。依据该文件精神,2017年国务院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教育部成立教材局,以“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贯彻党和国家关于教材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在这几年时间里,国家纷纷出台相关教材政策,系统确立了教材意识形态的建设方向与组织管理制度体系,党对教材建设的领导权、支配权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具体而言,教材意识形态的政策性存在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理念性存在,即通过政策文件对教材建设的基本理念与价值取向进行规定,如《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加强思政课教材体系建设”,要求“国家教材委员会统筹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建设,科学制定教材建设规划,注重提升思政课教材的政治性、时代性、科学性、可读性”。第二种是标准性存在,即通过学科课程标准对学科课程的性质、理念、目标等进行规定来保障教材的意识形态特征,如《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确立了“学生通过历史学习,增强对祖国和人类的责任感,逐步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贡献的人生理想”的学科理念。第三种是管理性存在,即通过管理体制与制度的建立来保障教材的意识形态特征,如2017年国务院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教育部成立教材局。
(二)知识性存在
作为教材的主要内容,选择什么样的知识,以及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知识进入教材是权力主体影响的结果,体现着教材的意识形态特征,也是教材意识形态存在的重要方式。
阿普尔的“谁的知识最有价值”成为当代课程研究的重要维度。在福柯(M.Foucault)提出“知识就是权力”命题以后,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角度探讨教材知识的选择问题逐渐成了课程研究的重要领域。福柯认为,“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9]知识的生产与证明只有依靠作为社会权力网络的知识团体做背景才有可能,社会权力以拒斥与造就的方式来承认和发展知识,知识与权力相伴相生。瑞士的莫里茨·罗森蒙德(Moritz Rosenmund)教授在探讨课程知识选择问题时认为,课程过程把知识和社会的条件与对未来社会的一般状况尤其是未来的教育形式的期望联结起来,[10]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性质等社会条件构成了课程知识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在权力的影响下,教材知识的准入过程并不完全是一个自然结果,它始终伴随国家和政府等权力主体通过建构知识、确立依据、挑选代言人与审定教材等形式介入进来,[11]国家与政府将会依据国家性质、当前的社会发展状况以及对未来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预判,对选择什么知识、如何组织和使用知识进行权力干预,以期实现教育的社会功能。
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角度可以发现教材意识形态的知识性存在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教材知识的选择,即不管是从合理性还是从合法性来看,国家与政府权力主体介入了教材知识的选择过程,教材知识必然体现国家与政府的思想价值体系。第二种是教材知识的组织。教材知识的组织是对教材知识的结构与程序性安排,主要表现为教材知识的呈现逻辑及其排列结构。这种呈现逻辑与排列结构隐含着知识学习的目标与过程,也渗透着意识形态。第三种是教材知识的话语。话语是特定情境中的言谈方式,不同的话语方式深植于不同的文化情境,体现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与价值信念。教材知识正是通过不同的话语方式来选择或指向某种特定的思想价值,使教材知识隐含着“谁的知识最有价值”的意识形态问题。
(三)使用性存在
教材使用是教师把教材从静态的课程文本转向动态的教学活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师既要维护教材的权威性,遵循教材的基本要求,也要通过对教学资源、教学活动的创造性开发与设计,促进教材的情境化、活动化、学习化。教材意识形态的使用性存在正是教师在教材使用过程中对意识形态所进行的情境化与创造性拓展。
新课改以后,对于如何使用教材形成两种基本认识,即“教教材”和“用教材教”。“教教材”指教师严格按照教材目标、内容与方法的预设开展课堂教学,维护教材的权威性与统一性,秉承的是一种忠实取向;“用教材教”指教师把教材视为一种资源与手段,教师可以依据自身的教育理解与教学实践探究,自主改变教材安排,开发课程资源,创设教学活动等,秉承的是一种创生取向。从二者关系来看,也存在“对立说”“粘连说”与“一致说”三种基本认识。[12]面对实践中教师与教材关系的认识不清,2018年《教育部教材局关于开展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检査工作的通知》提出“经教育部审定通过的国家课程教材,未经许可不得擅自修改”的基本要求,以维护教材的权威性与严肃性。在这一要求下,“教教材”和“用教材教”构成一种递进关系,即教师在教材使用过程中,首先要尊重教材的权威性与严肃性,按照教材的基本安排与设计开展教学,但在此基础上,教师需从特定的教学情境出发,合理地使教材情境化,创造性地开展教学活动。这样,“教教材”构成了“用教材教”的前提与基础,“用教材教”构成了“教教材”的创造性实现。由此,从意识形态来看,正是教材使用的情境化与创造性为教材意识形态的生成开创了巨大的空间,教师可以在教材意识形态的指引下,依据具体教学情境,去拓展、丰富教材意识形态。
具体而言,教材意识形态的使用性存在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是教材意识形态的情境化转化,即将教材政策、教材知识的意识形态具化到教学情境之中,使之转化为可视化的行为方式与生活化的思想价值,如政治信仰可以具体化为对烈士的瞻仰活动,培养学生对革命烈士的尊敬之情。第二是教材意识形态的创造性拓展,即对教材知识进行价值创生,使学生在认识的基础上建构意识形态的价值情感,如在小学语文字词教学中,“休”字可以在其基本含义与构词法基础上,从情感态度价值观层面可以创生为“休息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与为服务社会”。
三、教师理解教材意识形态的实现路径
(一)在意识形态建设的总体趋势中把握教材政策精神
教材政策是意识形态的宏观层面,它指明了教材建设的基本价值方向,准确把握教材政策精神是进一步理解教材意识形态的前提和基础。
教材政策产生于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与趋势之中,是教育政策在教材领域的具体化。因此,准确把握教材政策精神需要具有宏观视野,要依据国家与社会发展状况,在意识形态建设的总体趋势中去系统分析、仔细揣摩才能实现。从当前来看,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要求要立足中国传统与中国国情,借鉴与吸收世界各国的改革与发展经验,建设成为具有坚定政治信仰、发达经济水平、强烈文化自信、自强民族性格的现代化国家。只有在这一宏观背景下,教师才能够准确把握教材政策初衷,才能对教材政策所提倡的建设理念、方向目标、管理制度、结果预期等不同方面系统理解。同时,教师需要深入、仔细研读课程标准。“在新的制度框架下,课程标准才是国家法定政策文件,是国家对学生在某阶段学习结束后需要掌握的学习结果的硬性规定,体现着国家意志”。[13]课程标准是意识形态与学科内容、教学的结合,需要从意识形态维度去解读学科课程的性质与地位、理念与目标、结构与体系等,探寻学科课程与意识形态结合的关键点,如历史课程与唯物史观,语文课程与文化自信,道德与法制课程与社会主义公民等。
(二)从价值观层面透析学科知识的意识形态意图
知识的核心是价值,对教材知识意识形态的理解需要从价值观层面透析学科知识选择、组织与话语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意图。
第一,透析学科知识选择的意识形态意图。对不同学科知识选择的本质是对不同知识价值的选择,是国家对不同学科知识的价值判定与价值预期。如在统编本小学语文教材的篇目选择中,小学6个年级12册共选古诗文124篇,占所有选篇的30%,比原有人教版增加55篇,增幅达80%,革命传统教育的篇目也占较大的比重,小学选了40篇,初中29篇。[14]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篇目的增加意味着国家对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的重视,对学生形成文化自信的殷切期望。第二,透析学科知识组织的意识形态意图。学科知识的组织方式具有引导学生学习方向,预设目标的基本作用,体现着意识形态意图。如统编本的《道德与法制》从组织理念上看,采用了以学习活动为核心来组织教材内容;从组织方式来看,采用了单元、正文、栏目、儿童的教材设计方式。这种组织方式体现了《道德与法制》从“教德”向“学德”的转换,[15]希望培养学生的道德自主学习意识与能力,使学生能够在日常生活情境中自发地进行道德思考与道德养成。第三,透析学科知识话语方式的意识形态意图。不同的话语方式表达着不同的情感与价值指向。统编本《历史》七年级第14课的标题是“沟通中外文明的‘丝绸之路’”,相对于人教版的标题“汉通西域和丝绸之路”具有不同的话语方式。而这种话语方式的变化体现了丝绸之路不仅是“汉通西域”的单向文化流动,更是“中外文明”的双向文化交流。这与我国重建丝绸之路,加强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参与世界发展的意识形态意图是一致的。
(三)基于学生生活挖掘教材的意识形态意蕴
黑格尔(G.W.F.Hegel)认为:“意蕴总是比直接呈现的形象更为深远的一种东西”[16]。从本质上说,意蕴也是一种意义,但它不是作品所直接呈现的,甚至不是作者所想要表达的,而是读者自身所体悟到的。
教材的意识形态意蕴并非由教材政策所规定,也不由教材知识直接指向,而是教师在不违背教材政策规定与教材知识指向下,基于学生生活,对学生学习教材的意识形态目标的创造性建构,是教师教学自主性与创造性的表现。如进行科学实验,不仅要求掌握实验的基本原理与操作规范,还可以设计“学习科学知识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与社会”的价值目标。对于教材意识形态意蕴的阐发需要:第一,要确立教育知识观,即教材知识是一种价值性知识,是旨在促进学生建构生命意义的载体,而非呈现一种事实;第二,要把握意识形态方向,将国家和政府所倡导的思想价值体系与教材知识的意义建构关联起来,判断与创建恰当的意识形态目标;第三,要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依据学生生活经验体验、价值理想来设计意识形态的教学目标,创设教学活动,避免空洞的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