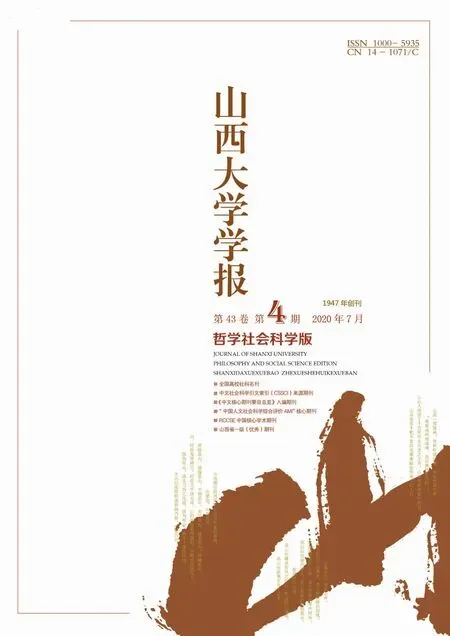论唐代的“言辞辩正”
何亦凡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2)
一、问题的提出
唐代铨选对官员的形象和文化有四个方面的考察,《唐六典》:“一曰身,二曰言,三曰书,四曰判。”[1]27杜佑分别为“身”“言”“书”“判”注明了具体标准:“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词论辩正。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优长。”[2]360《新唐书》所记与杜佑略同,唯有“言”,解释为“言辞辩正”,与“词论辩正”语义相差不大(1)后世文献中多从《新唐书》作“言辞辩正”,本文暂从。[3]1171。“言辞辩正”包含两个方面的考察:内容上,语音典正;形式上,语言优美。显然,“正”即正确,是重中之重。本文要讨论的就是唐代的正音问题(2)“正音”,作为名词,意为雅乐,亦指标准语音;作为动词,表示矫正语音。汉民族在历史上早已形成民族共同语,在唐宋就是“正音”。(张玉来.近代汉语官话语音研究焦点问题,近代官话语音研究[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7:16-41.李新魁.汉语共同语的行程与发展[M]∥李新魁自选集.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266-295)储泰松认为:“唐人所谓的正音就是雅音,以字书、韵书为标准。”(储泰松.唐代的方言研究及其方言观念[J].语言科学,2011(2):113-123)但在历史考察中,难以想见唐代士人能够较普遍地在口语交流中准确地践行字书或韵书的规范,而更可能的是,在唐代政府系统内和社会士人中,超越方言的“共同语”被使用,并且交流无碍。。
贞观元年(627)唐太宗与群臣论选官之法,杜如晦云:“比者,吏部择人,唯取言辞刀笔。”又云:“今每年选集,尚数千人,厚貌饰词,不可悉知。”[4]1580所谓“言辞刀笔”和“厚貌饰词”都与参选者的语音相关。杜如晦、魏征这些名臣都曾反对如此选官,但基于“身、言、书、判”的四项选人标准仍在继续,从客观上反映了这些标准的重要性。安史乱后唐代士大夫痛定思痛,认为祸在选人之法,大历十四年(779)沈既济上言:“然考校之法,皆在书判簿历、言词俯仰之间。”又云:“安行徐言,非德也。”[2]443,[3]1178虽然他强烈反对“言词俯仰”“安行徐言”这样的表面功夫,但此种语音表达和语言习惯正是当时参选者所具备的或追求的,这也是“言辞辩正”所带来的文化和行为反应。史载唐初温彦博“善于宣吐,每奉使入朝,诏问四方风俗,承受纶言,有若成诵,声韵高朗,响溢殿庭,进止雍容,观者拭目”(3)[5]2361类似的还有武则天时期的中书舍人毕构,史称此人在朝堂朗读表文时“声韵朗畅,兼分析其文句,左右听者皆历然可晓。”(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113.)。人们羡慕、赞美温氏的语音、仪态,正说明这是唐人心目中的理想官员形象。所以,即便唐代反对“言辞辩正”的声音一直存在,但这项标准已然被唐代士人默认接受。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评价这项制度,仍需审度。
宋人洪迈曾论:正是因为“书”“判”成为铨选的考察对象,唐人才普遍工楷法、善属文(4)洪迈说:“既以书为艺,故唐人无不工楷法,以判为贵,故无不习熟。……自朝廷至县邑,莫不皆然,非读书善文不可也。”[6]129。可见铨选标准对于士人素质和社会文化风气的影响。但洪迈的着眼点在于“书”和“判”,没有关注“言”的部分。而依据洪迈的逻辑,“言辞辩正”理应对唐代士人的读书生活、文学创作、行为修养产生很大影响。然而,语音毕竟与“书”“判”的形态不同,难以留下物质数据,而学者也较少讨论唐代的“言辞辩正”及其社会文化意义。
日本学者平田昌司将汉语语音演变与中国文化制度尤其是科举制相联系,著有系列文章,是汉语史与制度史结合的典范,但其中一些观点或有可商。其中《〈切韵〉与唐代功令》一文曾论:唐代吏部铨选在阻止庶族入仕和保护文化规范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言辞辩正”是士族阶层阻止社会流动的手段[7]7-35。事实上,在九品中正制等维护士族特权的制度被废黜之后,基本情形正该相反。唐代铨选所表现的是:以国家制度的力量扩大文化共同体的努力,而“言辞辩正”则可以看作是其推行正音的手段。此外,平田认为:“历经玄宗治世、安史之乱的唐代后期到北宋初期之间,口语能力好像已经不包含在作为官僚的必备条件。”[7]243但事实上,即便不是所有官员都能具备良好的口语能力,“言辞辩正”努力的方向和士大夫的追求始终是一致的。考虑到中国统一王朝的运作方式和方言的广泛存在,唐代铨选中“言辞辩正”的重要性就很容易理解,而从平田的研究看,一些基本问题仍有待厘清。
1925年,日本学者进行了以现代史学方法研究语音问题的尝试,并提出:中国古代士人取用标准语音而不取方言乡音已成自然之势[8]691-708。关于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语音发展的整体趋势的判断是正确的,然而论述过程稍显疏略。可以视为范式的则是陈寅恪的系列文章,尤以《东晋南朝之吴语》《从史实论〈切韵〉》《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为代表[9]304-309,[10]382-409,55-77。新近研究有史睿的《北朝士族音韵之学与南北交聘》,揭示并解释了“担任聘使的北朝士族,多出自语音雅正之家”这一历史现象,十分重要[11](5)此外,还有美国学者谭凯(Nicolas Tackett)的研究,认为“铨选中的语言评估环节更有可能青睐带特定的京城口音之人”。(谭凯.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47)虽然这一推测还有待证实,但语音典正对于唐代的参选士子而言无疑是一大优势。。可见,历史上的语音问题是可以通过史学方法解决的。但以上成果多集中在唐代以前,而对于唐代的相关制度讨论仍多空白。
苏力从中国法制学的角度论证了“语同音”是构成中国文化共同体的重要制度,关乎中国的构成。他认为:“语音不通,单靠书同文,不可能长期维系一个稳定的政治文化共同体。”[12],[13]344-387这确实是极具启发性的论断。但苏力更强调社会在维系语言共同体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共同语不可能也无法由国家直接维系,必须在社会中自我再生产,借助政府力量的强行推进也只可能在后世[11]83,86。这或许忽视了国家制度对社会文化的引导作用,至少与唐代的历史情形不符。唐代在国家制度层面对中国汉语共同语及文化共同体的推动具有重大意义,草此小文,祈教方家。
二、语音与文化身份
南北朝时期的士族以语音为文化优势,颜之推云:“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他还对于那些丧失语音优势的公侯权贵扼腕叹息:“古人云:‘膏粱难整。’以其为骄奢自足,不能克励也。吾见王侯外戚,语多不正,亦由内染贱保傅,外无良师友故耳。”[14]639,682南齐胡谐之家族的例子,正可以佐证颜之推的观点,也可以说明分裂时期的中国南北,都存在语言雅正的问题。《南史》载:
建元二年(480),[谐之]为给事中、骁骑将军。上方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傒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二年后,帝问曰:“卿家人语音已正未?”谐之答曰:“宫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宫人顿成傒语。”帝大笑,徧向朝臣说之。[15]1176
胡谐之本人的语音情况史载不详,但即便做不到言音典正,正常交流当无问题。但其家人却语音不正,可能就是颜之推所说“内染贱保傅”所造成的,甚至影响了联姻行为。于是齐武帝派人赴胡家正音,然而两年过后,不仅胡家众人未习正音,就连派来的“老师”也都“入乡随俗”说方言了,遂成为笑谈。足见方音难改。北朝著名经学家李业兴曾经因口音而被嘲笑,《北史》记“业兴家世农夫,虽学殖,而旧音不改。梁武问其宗门多少,答曰:‘萨四十家。’使还,孙腾谓曰:‘何意为吴儿所笑!’对曰:‘业兴犹被笑,试遣公去,当着被骂。’”[16]2724唐长孺先生曾评论:“在南北朝时语音常常是判别士庶的标准之一,李业兴虽三世孝廉,说他旧音不改,就意味着他还不是士族。”[17]146(6)史睿认为,李业兴属于士族(史睿.北朝士族音韵之学与南北交聘[J].文史.2016(4):60),但史籍明言其“家世农夫”,所以还不宜将其当作标准的文化士族,此处仍遵从唐先生的观点。则知语音在士族社会中的文化分量。由又可见,中国的方言问题普遍存在,即使在分裂时期的中国南北朝,也为各个政权所重视。
隋唐一统,方言对国家行政运作的阻力也随着疆域的扩大而增强。贞观十五年(641),太宗诫朝集使曰:“若南方诸州,多统夷獠,官人于彼言语不通,里吏乡首侵渔。匹庶不胜忿怨,挺刃相仇。因是叛亡轻犯,州县兴兵讨捕,即致杀伤。”[18]1896由于南方州县的胥吏、里正只说方言,官员又不通当地语音,于是胥吏之流得以欺上瞒下、鱼肉百姓,终酿叛乱之祸。则知统一的语音系统对行政运作与社会管理的重要作用。然而,地方胥吏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终唐一代,尤其在南方地区,日常语言沟通依然困难重重。贞元二十一年(805),韩愈被贬连州阳山令,记录了当地的情况:“县郭无居民,官无丞尉。夹江荒茅篁竹之间,小吏十余家,皆鸟言夷面。始至,言说不相通。画地为字,然后可告以出租赋、奉期约。”[19]1139(7)柳宗元被贬永州时也有语言上的不适应,在给萧俛的信中说:“楚、越间声音特异,鴂舌啅噪,今听之恬然不怪,已与为类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哓哓,昼夜满耳,闻北人言,则啼呼走匿,虽病夫亦怛然骇之。”(新唐书:5133)韩愈与当地胥吏之间言语不通,最后只能靠文字表意。这是利用汉字克服方言的例证,同时也证明了通用语的重要性。
看来,语音从士、庶身份的屏障而变成了官、吏沟通的壁垒。除了方言不通之外,“官”“吏”之间的语言习惯也有很大差别。唐人封演记录了这样一条逸闻:
裴子羽为下邳令,张晴为县丞,二人俱有声气而善言语。曾论事移时,人吏窃相谓曰:“县官甚不和!长官称雨,赞府即道晴;赞府称晴,长官即道雨。终日如此,非不和乎?”[20]97
裴子羽和张晴“有声气而善言语”,应当是言音典正之人,而手下的胥吏不懂他们的说话方式,将裴子羽所自称的“羽”错听成了“落雨”的“雨”,又将张晴所自称的“晴”而误认作是“阴晴”的“晴”,因此闹成了笑话。可见,地方胥吏即便能够听懂字音,仍是不懂语义,这是官、吏之间语言沟通的另一个问题。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吏”提出语音要求并不现实,但对“官”要求正音却是必要的,事实上作为制度的推行也一直在进行中。我国幅员辽阔,官员从他乡入仕很常见,在行政系统内部克服方言是一个漫长的历史任务,历代都在尝试削弱方言对政治管理和信息传递的影响,例如明代有《洪武正韵》,清代有正音书院,等等。
在南北朝至隋唐的历史进程中,使用正音或共同语(通用语)的文化意义发生了变化。到了唐代,不再是所谓“音韵家族”的文化“族徽”,而是国家选官制度和社会文化环境对唐代士人的普遍要求。语音的意义也从“士”“庶”之判逐步演变为“官”“吏”之别。在国家推动与社会参与的共同作用下,唐代成为古代中国加强社会沟通与管理的重要历史阶段,不断为统一国家打造更为牢固的文化基础。
三、唐代的口试与正音
口试是唐代科举的一项发明,并在唐代完成了制度化。所谓口试,就不是书写答案,而是口答,这便关系到了语音。关于唐代口试的具体规程已不能详明,相关研究也比较有限。前揭苏力《文化制度与国家构成》文中提及中国历史上维系官话的诸种因素:汉字的特点、人口迁移与流动、“异地为官”制度、官学系统、儒家教材、戏曲讲唱、诗歌韵文、“小学”的发展以及“反切”法[11]86-90,[12]376-379,但最能直接代表语音考察办法的唐代口试却未被提及。唐代明经科口试在开元二十五年(737)确定,文曰:
明经每经帖十,取通五以上,免旧试一帖;仍按问大义十条,取通六以上,免试经策十条;令答时务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与及第。(8)“仍”,即“乃”。《唐会要》标点本句读有误。又,《旧唐书》置于开元二十六年正月,《册府元龟》置于开元二十五年正月,《资治通鉴》置于开元二十五年二月,本文遂置于开元二十五年。[2]356,[4]1631,[5]209,[18]7671,[21]6826
封演的记载与此对应:“开元二十四年冬,遂移贡举属于礼部……其后明经停墨策,试口义。”[20]16知开元二十五年明经科以口试代替墨策。“言音典正”一直为经学所崇,可以追溯到东汉太学的雅言,也就是所谓的洛阳旧音。唐代明经科的口试固然也是对正音的考评,不仅仅为了考察经义,否则笔书即可。这样的国家行为势必会产生社会效应,考生因此也不得不重视对正音的掌握。而且不仅明经科,其他考试科目也有口试。
童子科以记诵为要,也不免口试,要求“卷诵文十”[3]1162。唐开成年间生活在闽地的林杰,“幼而聪明秀异,言发成文,音调清举。年六岁,请举童子。”[22]1301-1302可见“言音典正”是童子科的一项重要优势。此外,《新唐书》载长庆二年(822),谏议大夫殷侑奏“每史问大义百条”[3]1162,这是史科的口试。书学科则要通过口试之后才能参与墨试[1]45,109,[3]1162。就连看似与语音关涉不大的算学科也有口试,对于《记遗》《三等数》的考核,《唐六典》载“读令精熟,试十得九”,《新唐书》则记为“帖读十得九”[3]1162,二者虽略异,但仍属口试的范畴。凡口试,必然涉及语音考察。而所谓帖读之法,指题目中要求考生填空若干,其特别之处在于,考生需要“读”出答案,而不是单纯地写下来[23]122。口试既是对考生专业内容熟悉程度的考察,又是对反应能力的测试,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作弊。同时,不可避免地呈现出语音典正与否。
对于弘文馆、崇文馆学生和国子监大成(9)所谓“国子监大成”,即贡举及第由考功简试合格者,授散官,并于学内习业。而言,口试的标准要求更高[24]29。弘、崇两馆考生不论经史,要求“读文精熟、言音典正”;对于国子监大成而言,须“日诵千言,并口试”,业成之后,吏部简试还有口试,且要十条通九方可[1]46,110,[3]1163。在口试中,学馆生徒相对于乡贡有很大优势,因为生徒平时有全面的口试训练,尤其是年终口试,可以当作参加尚书省试之前的模拟考试,《新唐书》载:
〔弘、崇两馆生〕旬给假一日。前假,博士考试,读者千言试一帖,帖三言,讲者二千言问大义一条,总三条通二为第,不及者有罚。岁终,通一年之业,口问大义十条,通八为上,六为中,五为下。[3]1161
直到宪宗元和二年(807)礼部罢口试,明经科曾一度回归到笔书的方式了[5]423,[3]1165。但据《旧唐书》,文宗大和七年(833)进士科贴经之后还要口试经义,“其进士举宜先试帖经,并略问大义,取经义精通者放及第”[5]551。知口试制度在晚唐仍在进行。
口试在唐代几类科举考试中占有一定分量,而语音作为口试最直接的反映,是考察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在方言普遍存在的背景下,口试是有针对性的制度设计。
四、唐代进士科与举子语音
唐代进士科的诸场考试亦与语音相关,主要在策问和杂文的诗赋中体现。唐初进士科只有时务策一项,以骈文写成,讲求声律。永隆二年(681),进士科加试杂文,但策文仍然是进士科考试的主体[24]131-149。所以也关系到举子对正音的运用。
杂文专试诗赋在天宝年间确定,诗赋成为进士科取人的决定因素也是在天宝时。玄宗天宝十四载(755)颁布用韵规范《韵英》,以取代《切韵》(10)王国维认为《韵英》是以当时的秦音为基础的,与《切韵》音系不同。(王国维.天宝《韵英》陈廷坚《韵英》张戬《考声切韵》武玄之《韵铨》分部考[M]∥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385-392),这是国家层面对正音的确认。以上两件事实当高度相关,亦可证明唐朝对于正音的追求是有明确意识的国家行为。亲历者韦述记载:“上以自古用韵,不甚区分,陆法言《切韵》又未能厘革,乃改撰《韵英》,仍旧为五卷。……分析至细,广开文路,兼通用韵,以示。宰臣等上表陈贺,付诸道令诸郡传写。”[25]265《新唐书·艺文志》亦载玄宗令集贤院抄写《韵英》,由诸道采访使传布天下[3]1451,[4]768。足见唐朝政府以《韵英》取代《切韵》的决心。而此前虽有众多官私韵书试图替代或补充《切韵》(11)兹举数例:唐初许敬宗等因《切韵》韵窄,请奏合韵。(封演.封氏闻见记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13)所以清人认为,唐人用韵定自许敬宗。(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367)仪凤二年(677)长孙讷言为《切韵》作注。中宗时,王仁昫作《刊谬补阙切韵》。开元间,孙愐修《唐韵》,天宝十载再修。大历十二年(777)颜真卿献《韵海镜源》(旧唐书:313)。[26]3715-3716,但都基本没有被认定成规范,玄宗推行的《韵英》才是唐代官方承认的官韵。若没有安史之乱及诸多因素的影响,各地举人很可能将《韵英》视为标准,其对全国的影响不言自明。虽然《韵英》夭折,客观上《切韵》在唐代的官韵地位并未动摇,但足可见唐代官方推行正音的努力。
对于来自全国各地的举子而言,熟习正音、准确用韵并非易事。在唐人笔记小说中有一则故事流传甚广,甚至产生了数个版本:“宋济老于词场,举止可笑。尝试赋,语失官韵,乃抚膺曰:‘宋五又坦率矣!’因此大著。后礼部上甲乙名,德宗先问:‘宋五坦率否?’”(12)此处为《唐语林》的版本,《唐摭言》将此事系在玄宗朝,当为误置。[27]49宋济参加进士科考试,一生未成,主要原因就是他的诗赋常常“落韵”,甚至因此成了科场笑谈。他把押韵失误说成是“坦率”,很可能是难以克服地使用了方言。但如果考生精熟官韵,考场作诗则十分顺利,史载温庭筠:“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28]89,[29]433-435,其“温八叉”的绰号即由此而来。唐代还有“百韵诗”,《唐语林》:“开元中有李幼奇者,以艺干柳芳,念百韵诗。”[27]311“百韵诗”具体为何不易得知,但从名称来看,应当是与立意关涉不大,而是能汇集众多韵脚的诗,这或不失为一种克服落韵、记忆韵脚的方法。
考场上对韵书的使用也侧面体现了当时举子用韵的困难。《唐会要》记载:
乾元初,中书舍人李揆兼礼部侍郎,揆尝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实,徒峻其堤防,索其书策。殊不知艺不至者,居文史之囿,亦不能摛其词藻,深昧求贤意也。及其试进士文章日,于中庭设《五经》及各史,及《切韵》本于床,而引贡士谓之曰:“国家进士,但务得才,经籍在此,各务寻检。”由是数日之间,美声上闻。[4]1634(13)《通典》的一则记录也十分重要:“〔礼部〕阅试之日,皆严设兵卫,荐棘围之,搜索衣服,讥诃出入,以防假滥焉。”(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357.)
依李揆的看法,求贤在于治国安邦,不在于文史细节,所以考试中应当提供参考书。长庆元年(821)白居易奏:“伏准礼部试进士,例许用书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则思虑必周,用书策则文字不错。”[30]1290看来,白居易与李揆的想法一致。洪迈认为唐代进士科允许携带书册[6]31-32,傅璇琮先生则认为所允许带入的书策就是韵书[31]100-102。但是,唐代虽有提供参考书的现象,但是否是制度化的,是否是普遍化的,存在疑问。如果试诗赋提供《切韵》,那就不会有宋五坦率的故事了。准确用韵的确是举子考试的困难之处,但不如此或许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毕竟入仕者多是流官,无法想象一个仅会说方言的官员入职另一方言区该如何工作。
“韵”是进士科考试成败的一大关键。在考场上,因为应试诗本身有时间和韵脚的限制,很难靠“文意高低”去判别高下,故而在实际操作中,较容易也较客观地评估办法就是“检韵”。《云溪友议》记载:
宣宗十二年(858),前进士陈玩等三人,应博学宏词选。所司考定名第,及诗、赋、论进讫,上于延英殿诏中书舍人李潘等对。上曰:“凡考试之中,重用字如何?”中书对曰:“赋忌偏枯丛杂,论即褒贬是非,诗即缘题落韵。”[32]121
所谓“诗即缘题落韵”,知“韵”是作诗最容易出错的地方。而且诗赋重在检韵已经成为官方认可的评价方式。唐人对于此种评判方式也有反思,贾至指出:“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唯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乎?”[5]5030然而,从《云溪友议》的记载来看,这一评估办法在贾至之后依旧延续。故而《新唐书》总结说:“[进士科]因以谓按其声病,可以为有司之责,舍是则汗漫而无所守,遂不复能易。”[3]1166至宋代仍如此,《宋本广韵序》云:“悬科取士,考覆程准,兹实用焉。”[33]1清人毛奇龄说:“律者,专为试而设。”[34]448“韵”在应试诗评价中的特殊意义,从唐至清,一直重要。看重评价诗歌的技术性,从而为考官工作提供便利,这似乎有些道理。但为什么这一颇受争议的标准能够长时段地延续?或许不该忽略此一办法对于克服方言问题的作用。
正音的掌握与士子本身的方音是分不开的。以“吴音”为例:唐人所云之“吴音”一指江左六朝旧音,与《切韵》接近,为人所崇;二指南朝庶族所用的吴地方言,因循至唐代,是正音的反面,为人所鄙(14)王国维云:“六朝旧音多行于江左,故唐人谓之吴音,而以关中之音为秦音。故由唐人言之,则陆韵者,吴音也。”(观堂集林:388)此外,《朝野佥载》记载一则故事亦需参考:“余杭人陆彦夏月死十余日,见王,云:‘命未尽,放归。’左右曰:‘宅舍亡坏不堪。’时沧州人李谈新来,其人合死,王曰:‘取谈宅舍与之。’彦遂入谈柩中而苏,遂作吴语,不识妻子,具说其事。遂向余杭访得其家,妻子不认,具陈由来,乃信之。”(张鷟.朝野佥载[M].北京:中华书局,1979:44-45)此处余杭人所说的“吴语”就应当属于地方方言。。江东人陆畅元和元年(806)登第,以诗闻名,还被认为带有南朝陆氏家族的遗风。史载其“辇毂不改于乡音。……内人以陆君吴音,才思敏捷,凡所调戏,应对如流”(15)《酉阳杂组》记陆氏“语多差误”,是指他经常说戏谑之语,并非语音问题。(段成式.酉阳杂俎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15:1665)[32]83-85,[35]1422。陆畅的口音在生活中颇具特色,甚至带有戏剧效果。从他个人的经历来看,他所说的“吴音”不应当是鄙俗方言,而是与《切韵》接近的吴音,这对作诗押韵而言,也是先天优势。但如果士子的语音属方言性质的“吴语”,在进士科考试中就处于劣势了。《唐摭言》载:
〔郑〕光业常言及第之岁,策试夜,有一同人突入试铺,为吴语谓光业曰:“必先必先,可以兼容否?”光业为辍半铺之地。其人复曰:“必先必先,咨仗一杓水。”光业为取。其人再曰:“便干托煎一碗茶,得否?”光业欣然与之烹煎。居二日,光业状元及第,其人首贡一启,颇叙一宵之素。略曰:“既取水,更煎茶,当时之不识贵人,凡夫肉眼;今日之俄为后进,穷相骨头。”[36]92
史料中特别记录这位举子“为吴语”,他落第后还自嘲“穷相骨头”,看来他的“吴语”很可能不是与《切韵》相近的吴语,而是吴地方言。从这些描述和此人的言谈来看,其对官方话语系统地掌握可能大有问题,这在举场之中绝不是优势。
相似的历史情境后世依旧。章学诚《定武书院教诸生识字训约》,有助于理解唐代的情状:
至唐宋制科专重诗赋,于是声律对偶,令式所颁,即非一家言矣。《广韵详定》《雍熙韵略》,系名礼部,是则官有法程,士遵绳墨,金科玉律,不可易也。今科举诗帖平仄拈背,本非难解,而土音不同,平仄讹舛,致乖律吕。即经书文义,虽体制迥与词赋不同,然以场屋所需,不能不参排句偶调,以归庄雅。乃以方音不合,易致音节聱牙,辞意虽工,亦遭按剑。以是知音韵之学所以不可废也。[37]681
此段文字的前半,可见国家制度引导社会文化的一面,即科举制对士人语音的影响。之后,章氏又用心良苦地告诫学生,诗赋用韵本非难事,但由于考生受到故乡方言的牵绊,仍易落韵。而且,就连看似与用韵关系不大的经义文章,方言仍然有碍于顺利写作。章学诚所论科场成败与语音的关联切中肯綮,虽与唐人时隔千载,但据此仍可想见唐代举子也会遇到同样的语音问题,且其困难程度相比清人可能有过之无不及。唐代的进士科势必会沙汰大量语音不正之人,从而客观上保证了正音在国家行政运作和官僚群体中的地位。
五、语音观念与历史书写
唐代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南北朝以来的语音文化观,语音不正颇受当时人的鄙视,而且对于那些士大夫眼中历史形象不佳的人物,往往在其历史书写中会着重描述他们语音不正的一面。武则天时期的著名酷吏侯思止即属此类。《大唐新语》载:
侯思止出自皂隶,言音不正,以告变授御史。时属断屠,思止谓同列曰:“今断屠宰,(鸡云)圭(猪云)诛(鱼云)虞(驴云平)缕,(俱云)居不得(吃云)诘,空(吃)结(米云)弭(面)泥去,(如云)儒何得不饥!”侍御崔献可笑之。思止以闻,则天怒,谓献可曰:“我知思止不识字,我已用之,卿何笑也!”献可具以鸡猪之事对,则天亦大笑,释献可。[38]190
《旧唐书》云:“思止言竟不正。时人效之,以为谈谑之资。”[5]4845此是概括言之,与《大唐新语》所云基本无异。而《新唐书》则对其语音不正之事加重笔墨:“思止本人奴,言语俚下”,又云:“思止音吐鄙而讹,人效以为笑”[3]5909。此处当是士大夫阶层对其进一步的丑化。侯思止出身卑微,目不识丁,语音不正,亦是当然之事。
关于王伾语音的丑化过程,亦颇可考。王伾是杭州人,关于他的语音,正史的记载可以追溯到韩愈《顺宗实录》:“伾以侍书幸,寝陋,吴语,上所狎。”[26]5672此处对王伾音貌的形容词是“寝陋”“吴语”,《资治通鉴》沿用了这一表述[21]7609。至《旧唐书》,则记载“伾阘茸,不如叔文,唯招贿赂,无大志,貌寝陋,吴语,素为太子之所亵狎”[5]3736。《旧唐书》除了保留以上史料已有的形容之外,又加入了“阘茸”一词(16)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字林》云:“阘茸,不肖之人”。(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2493)颜师古注《汉书》:“阘茸,猥贱也。”(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728)。《新唐书》载:“伾本阘茸,貌陋,楚语,无它大志,帝亵宠之。”[3]5126《新唐书》将原来史书中所用的“寝陋”改为“陋”,将“吴语”改为“楚语”。王伾为杭州人,此处的“楚语”并非指唐代楚地的方言,而是加重丑化王伾语音的书写方法(17)在南北朝的士族社会,语音不正几乎就代表了对某人文化素养的全面否定,尤其用“楚”一词,兹举二例,《世说新语》:“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刘义庆.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7:699)又如,《宋书》:“〔刘〕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462)陈寅恪先生认为,“楚”为形容词,相当于“都邑”“文雅”的反义词,与“夏”相对,有“非正统”之意。(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上海:三联出版社,2015:388-390)。胡三省又为丑化王伾再填笔墨,《资治通鉴》胡注云:“状貌寝陋,常操乡音,不能学华言。”[21]7609但王伾在东宫侍书之前,“以书待诏翰林”,与侯思止的文化水平绝不相同,即便口操方言,但亦不至于如后世史家所言。这样的历史书写,实质上是抓住了王伾语音不正的缺点而抒发史家褒贬立场的表现。
这样的书写方式在唐末宰相卢携的身上更为明显。五代人孙光宪始言卢携“语亦不正”:
唐大中初,卢携举进士,风貌不扬,语亦不正,呼“携”为“彗”,平声。盖短舌也。韦氏昆弟皆轻侮之,独韦岫尚书加钦,谓其昆弟曰:“卢虽人物甚陋,观其文章有首尾,斯人也,以是卜之,他日必为大用乎!”尔后卢果策名,竟登廊庙,奖拔京兆,至福建观察使。向时轻薄诸弟,率不展分。所谓以貌失人者,其韦诸季乎![28]99
通读整条史料,主旨在于褒扬韦岫的识人之能。卢携虽然其貌不扬、语亦不正,然善于作文。孙光宪似乎并没有过多贬抑卢携的意图,其“风貌不扬”只是说卢携的样貌没有过人之处,十分普通。《旧唐书》未提及卢携语音不正之事。《新唐书》则将卢携“语不正”的缺点正式纳入正史的书写系统,这仍然与《新唐书》的褒贬立场相关[3]5398-5399。然而,卢携之父卢求,宝历初登进士第,卢携大中九年(855)进士擢第,授集贤校理,出佐使府。乾符四年(977)拜相,累加门下侍郞,兼兵部尙书、弘文馆大学士[5]4638。从其家世及其个人履历来看,卢携的文化素质与前文所论的侯思止、王伾之流绝不相同,其进士及第且善文章,自当详于声律、熟习正音,按孙光宪所言,卢携语音不正的原因是“短舌”,并不是方言问题。对于卢携这样的历史人物,史书也难免“天下之恶皆归焉”。唐代历史书写中对于人物的语音描述往往暗含褒贬之意,揆诸史籍,其例甚多,以上采择身处不同文化层次的三个历史人物,略作说明。
唐代与南北朝时期不同的是,品评语音可以被广泛应用于各类官员,而与他们的出身无关,这恰恰说明正音已被默认是入仕者应具备的文化素质。虽然以上史传的编撰者多处于唐末五代或宋时,但其语音观念的产生亦有其历史因由,若没有整个唐代的官方正音过程,士人的语音环境势必改变,那么史书中是否还会有如此的评价方式,实难确知。而后代的历史书写者之所以能够以语音褒贬官员,正说明“语音不正”在以精英士大夫为主体的统一政府中为人不齿,而此种文化环境的产生与唐代长期推行正音密不可分。同时,这种历史书写方式也是社会对国家制度的反映,是理解唐代正音的重要部分。
综上所论,唐人所追求的“言辞辩正”对地域和家族的标榜减弱,更多地代表个人的文化素质及官僚群体的行政素养。在方言广泛存在的历史前提下,这一过程的实现是唐代国家制度与社会观念双向作用的结果。顾炎武云:“五方之语虽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士而操一乡之音,亦君子所不取也。”[39]1648读书人为了参与国家政治、寻求更高的个人发展,克服旁人难懂的方言、学习并使用共同语是历代中国士大夫所共有的文化自觉。士大夫作为政治参与和社会文化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文化训练,包括理论素养、文化素养和社会价值观,对于国家统一和社会管理都发挥了支撑作用。唐代选官制度强调的“言辞辩正”并非孤立,其与科举制中的口试制度、进士科检韵制度配套而行,不仅体现了唐代制度设计中良好的关联性,而且能够有效地向社会推行正音,这对中国汉语共同语及中国文化共同体的贡献是可以大书特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