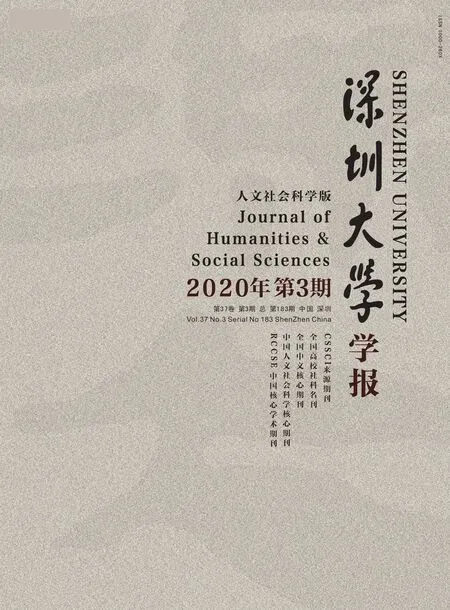张载理学价值观的主题、体系定位及最高原理
林乐昌
(陕西师范大学关学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062)
引言:“尊礼贵德”是张载理学价值观的主题
张载(1020~1077,字子厚,学者称横渠先生)是北宋理学的共同创建者,也是关学宗师。 长期以来,学术界研究其价值观的成果甚少①。 任何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都是人的动机和行为的准则,同时也代表人的信念或信仰。 价值涉及的领域很广泛,就中国古代的价值领域看,主要包括道德、礼仪、政治、艺术、宗教等②。 价值准则是有其根源乃至终极根源的,包括形而上的、神圣的、道义的、理性的、规范的等不同根源。 价值观既有导向或约束功能,又有激励或支配作用。 价值理论作为一门学问是20 世纪初西方开始建立的,但是关于价值的思想,无论古代东方或古代西方,都早就存在了[1]。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也不乏对价值问题的思考[2];甚至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部分是价值观”[3]。
《宋史·张载传》称,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4]。 其中所谓“尊礼贵德”,说的就是张载的价值观。 在中国古代,“尊”和“贵”都是与价值意义相当的名词③。 张载理学价值观的内容相当丰富,这从他常常使用的名词可以看出,包括“礼”“德”“仁”“义”“智”“信”“恭”“敬”“诚”,等等。 在张载经常使用的所有道德价值名目中,依据其重视程度和使用频率可知,“礼”和“德”是其价值观的两个基本类型。 据此,有理由把“尊礼贵德”视作张载价值观的主题。 尊礼重德、礼德并用,是西周的传统[5](P469,472)。 张载因应儒学复兴的时代呼唤,对西周原本作为“德政”的德-礼体系从价值观角度进行新的诠释,系统阐发了“尊礼”价值观和“贵德”价值观。 值得注意的是,张载的价值观在其理学体系中地位独特,并发挥着上通与下贯的作用。 “尊礼贵德”价值观在生活世界中的方向确定和实施有度,遵循的是作为最高原理的“中正之道”。本文对张载理学价值观的探究,将以“尊礼贵德”这一主题为中心,从张载的“尊礼”价值观、“贵德”价值观、价值观的理学体系定位、“中正之道”是“尊礼贵德”价值观的最高原理等4 个方面加以阐释。
一、张载的“尊礼”价值观
北宋是礼学的兴盛时期[6]。 在北宋礼学家中,张载的礼学思想独树一帜。 在他的存世著作 《正蒙》中,有论述礼学的《乐器》《王禘》篇,《经学理窟》中有论述礼学的《周礼》《礼乐》《祭祀》《丧纪》篇;在他的散佚著作中,有《仪礼说》《礼记说》《周礼说》《横渠张氏祭礼》《冠婚丧祭礼》等。 张载特别“尊礼”,并有诗句云:“圣学须专礼法修。 ”[7](P368)后来王夫之评价说:“张子之学以立礼为本”[8](P297)。 张载所谓“礼”,不仅是实现仁、孝等道德价值的途径,而且其本身也具有强烈的价值意义,其性质属于规范伦理或规范价值。 张载礼学具有多重价值功用,包括国家治理的价值功用、地方自治的价值功用、个体成德的价值功用。
(一)礼的国家治理价值
张门弟子吕大临在其《横渠先生行状》中指出,张载“慨然有意三代之治”[7](P384)。 张载认为,国家治理要“以礼乐为急”[7](P317),因为“三代之治”的基础正是礼乐制度。在他看来,礼是“圣人之成法”,天下之常道[7](P264),首先关乎典章制度、礼乐兵刑等内容,都与国家治理有关。
礼治怎样才能够落实于国家治理,以发挥其价值功用? 张载的思路是,首先要扭转“上无礼”的乱象,改变“治忽”“德乱”的局面。 张载用“治所以忽,德所以乱”来描述当时国家治理的病相。 他认为,导致这一局面的根源在于“上无礼以防其伪,下无学以稽其弊”[7](P64)。 这是说, 国家作为社会的上层,未能落实“礼”以防范各级官员的虚伪欺诈;而社群作为国家的下层,则没有推行“学”以杜绝社会风气的种种流弊。 “上无礼”,不仅是国家的弊病,也是全社会的弊病。 在张载看来,清明的政治必须“礼教备,养道足,而后刑可行,政可明,明而不疑”[7](P214)。 否则,便会导致社会“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7](P384)。
程颢、程颐兄弟曾对张载说:“关中之士,语学而及政,论政而及礼乐兵刑之学,庶几善学者。 ”[9](P1196)这不仅是对张载及其弟子以礼乐兵刑论政的高度肯定,也敏锐地看出在张载那里“学”“政”与“礼”之间的密切关系。 正因为如此,对于国家治理,张载不仅认为亟待扭转“上无礼”的乱象,而且还强调必须杜绝“下无学”的流弊。 张载所谓“下无学”的“下”,指的是国家下层的社群和民众;“学”,指的是学校教育,也包括民间教育。 程颐在总结张载的教学方法时说:“子厚以礼教学者,最善,使学者先有所据守。 ”[9](P23)程颐对张载教学宗旨的评价,在其后宋、元、明、清学者的征引中被浓缩为“以礼为教”四字④,以更简明的话语彰显张载教学实践的特质。 “以礼为教”表明,张载所谓“下无学”的“学”是以“礼”为核心内容的。
(二)礼的地方自治价值
张载晚年退居横渠,远离朝廷,除了讲学授徒之外,他最大的关切是乡村秩序的重建和社会风俗的整顿。 为了实现这一地方治理的愿景,张载特别重视民间教育以培育学者。 他说:“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学者,则道可传矣。 ”[7](P271)由此可知,张载把讲学传道、培养学者视作“功及天下”的头等大事。在他看来,“学”及教育的内容首先指“学礼”,强调向学者传递和推行人文价值观。 司马光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评价张载的教育特点说:“教人学虽博,要以礼为先。 ”[10](P131)
张载所处的时代,人们普遍“不安于礼”,社会风俗中“礼意犹有所缺”[11](P373)。 面对这一环境,张载与其弟子们不向习俗妥协,下决心“用礼成俗”“化民易俗”[11](P359),运用礼仪发挥调节宗法关系和改良风俗的作用,在地方社会推行礼仪不遗余力。张载曾经这样与程颢对话。 张载说:“关中学者用礼渐成俗。”于是,程颢评价说:“自是关中人刚劲敢为。”张载则补充说:“亦是自家规矩宽大。”[12](P771)可见,张载在民间社会努力推行古礼,“用礼成俗”“化民易俗”,不流于习俗,使“礼”成为民间社会秩序的有效调节机制。 这种“刚劲敢为”的勇气,表明张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很有自信的。 对于张载在家族和乡里推行儒家古礼的工作,司马光是这样评价的:“好礼效古人,勿为时俗牵。 ”[10](P131)
对张载在家族和乡里推行儒家古礼的情况,其门人吕大临是这样描述的:
近世丧祭无法,丧惟致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之变;祭先之礼,一用流俗节序,燕亵不严。 先生继遭期功之丧,始治丧服,轻重如礼;家祭始行四时之荐,曲尽诚洁。 闻者始或疑笑,终乃信而从之,一变从古者甚众,皆先生倡之。
其家童子,必使洒扫应对,给侍长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亲祭祀,纳酒浆,皆所以养孙弟,就成徳。 尝曰:“事亲奉祭,岂可使人为之! ”[7](P383)
由于张载在其乡里努力推行古礼,“于是关中风俗一变而至于古”,取得了“关中学者用礼渐成俗”[12](P664,771)的成效。
张载注重地方秩序的整顿,催生了地方社会自治模式的形成。 其门人吕大钧兄弟一起撰写了《吕氏乡约》,并在家乡京兆蓝田推行。 这是吕氏兄弟把张载礼学落实于地方自治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案例,对后世的基层社会治理影响很大。
(三)礼的个体成德价值
张载说:“以礼成德,故曰盛德。 ”[11](P344)这是礼作为个体成德价值的集中体现。“以礼成德”的过程,包括学礼、知礼,尤其是“行礼”[7](P266)。 “行礼”包括行为庄敬、举止得体等。 礼的个体成德价值,关注的是人自身精神气质和日常行为的转变,以不断提升德性。 这样,行礼在本质上就展现为个体自我教育的过程。 正是在此意义上,张载强调“进人之速无如礼”[7](P265)。 他认为,“行礼”践履是人性不断提升的过程,而人性的成长需要礼仪规则的约束。 康德指出:“在教育中人必须受到规训。 规训意味着力求防止动物性对人性造成损害。”人的“天性没有被置于规则之下,这才是恶的原因”[13](P9,10)。这里的规训(discipline),与儒家的礼仪精神是一致的。 康德对规训或规则的深刻洞察,有助于理解张载学礼要求在个体成德修养中的积极作用。
张载认为,“行礼”必先“知礼”,而“知礼”和“行礼”都指向个体的“成性”目标。 他所谓“成性”的涵义,是指通过相应的修养工夫对人性加以调整、转变使之趋近于德性。 据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记载:“学者有问,多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7](P383) 这是张载为学者总结的两种基本修身工夫形态。 首先,关于“知礼成性”。 “知礼成性”中的“礼”,指礼仪规范;而“知礼成性”,则指理解礼的本质, 在此基础上进而与道德实践相统一的整体工夫。 张载所谓“知礼成性”与他的另一说法“以礼成德”,其意涵是一致的。 其次,关于“变化气质”。 表面看来,“变化气质”工夫与“礼”并不相干,其实不然。 张载指出:“但拂去旧日所为,使动作皆中礼,则气质自然全好。 ”[7](P265)可见,“使动作皆中礼”,是“变化气质”工夫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它还能够与“知礼成性”工夫配合使用。 张载把个体的道德修养实践划分为3 个阶段,即学者阶段、大人或贤人阶段、圣人阶段,每个阶段的修养工夫要求有所不同。 此外必须强调,“知礼成性”是贯穿并适用于所有不同阶段的修养工夫。 张载提出:“圣人亦必知礼成性。 ”[7](P191)又提出:“学礼,学者之尽也,未有不须礼以成者也。 学之大,于此终身焉,虽德性亦待此而长。惟礼乃是实事,舍此皆悠悠。圣、庸皆由此途,成圣人不越乎礼,进庸人莫切乎礼,是透上透下之事也。 ”[11](P310)
张载强调,“行礼”实践应当以“洒扫应对”等基本工夫环节为起点。 他说,“洒扫应对是诚心所为,亦是义理所当为也”[7](P287)。 以此为起点,“从基本一节节实行去, 然后制度文章从此而出”[7](P288)。张载这一说法表明,礼的个体成德价值是礼的国家治理价值和礼的地方自治价值的共同基础。
二、张载的“贵德”价值观
张载既教人以“礼”,又“教人以德”[7](P382)。 郭沫若提出:“在卜辞和殷人的彝铭中没有德字,而在周代的彝铭中如成王时的班簋和康王时的大盂鼎都明白地有德字表现着。 ”[14]陈来认为,从西周到春秋的用法来看,“德”的含义主要指“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心意”[15]。 可见,张载所谓“贵德”源自西周的尚德传统,并继承了《易传·系辞上》“崇德而广业”、《礼记·中庸》“尊德性”、《孟子·公孙丑上》“贵德而尊士”、《礼记·曲礼上》“太上贵德” 等思想。“仁”“孝”,是张载“贵德”价值观的核心。 张载的“仁”“孝”价值,首先是用以规范个体行为的,进而还为社会秩序奠定文化基础。 以下,把张载的“贵德”价值分为仁德价值与孝德价值两部分加以论述。
(一)仁德价值
张载的仁德价值,在其著名的短论《西铭》中表现得最为充分[16]。 在他那里,“仁”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价值概念,因而需要关注仁德与“得礼”、仁德与国政的关系,以全面理解张载的仁德价值。
1.《西铭》与仁德。 孔子最早把“仁”确立为儒家的核心价值。 与早期儒家有所不同,《西铭》是基于“乾父坤母”这一宇宙根源说“仁”的。 张载说“仁”的新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突破了早期儒家强调基于血缘的差等之爱。 《西铭》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7](P62)这句话后来被浓缩为“民胞物与”这一被广泛引用的成语。 “民胞物与”,已成为张载仁爱观的标志性话语,与张载在《正蒙·诚明篇》提出的“爱必兼爱”完全一致。 “民胞物与”和“爱必兼爱”这两个口号是对儒家传统仁爱观的突破。 张岱年先生认为,张载的仁爱观“综合了孔子的仁与墨子的兼爱”[17]。 张岱年先生在论及“兼爱”的原则时说:“兼的原则是爱人如己。 ”[18]张载关于“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7](P32)的说法,与“兼爱”的原则是相符合的。 张岱年先生把张载的仁爱观称作“泛爱”思想,认为这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19]。程颐也意识到,以血缘为根据的仁爱易导致“私胜而失仁”[9](P609)。 这就准确地揭示了《西铭》的立论支点。 “民胞物与”的理念,为纠正“私胜而失仁”的偏向提供了可能,使人们能够调动理念的力量,引导仁爱实践的范围不断扩大。 二是扩大了“仁”的实践范围。 “民胞物与”的“物与”理念是指,面对乾坤父母,人类应当把一切自然物视为自己的伙伴,以仁爱之心相对待。 这就扩大了仁爱施与的范围,从限于人类谈仁爱,到不限于人类谈仁爱。 这是张载对儒家仁爱观的重要发展。 把宇宙间一切自然物都视为人类伙伴的观念,可以作为人类平等对待自然万物、与万物共存共荣的重要价值准则。
2.仁德与“得礼”。 在价值意义上,“仁”与“礼”是有内在关联的。 对于“仁”与“礼”的关系,张载首先强调“礼”的优先作用。 他指出,仁“不得礼则不立”[7](P274)。 张载的一句佚诗说:“若要居仁宅,先须入礼门。 ”[20]粗看起来,张载对“礼”的重视,超过了作为儒家最高价值的“仁”。 但仔细分析则发现,张载对礼的重视,只是就教学步骤的优先性这一特定角度而言的。 他认为,若要实现仁德的价值,一定要通过“学礼”“得礼”和“行礼”的路径,而这与“仁”在儒家价值系统中的最高地位是不冲突的。
3.仁德与国政。 张载认为,仁德与国家政治的关系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君王的“成德”和“治德”。他指出,君王“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7](P33)。 张载还把这一要求提升到“帝王之道”的高度。 他依据孟子“唯大人能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国定”的论述[21](P525,526),主张:“能使吾君爱天下之人如赤子,则治德必日新,人之进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学与政不殊心而得矣。 ”[7](P349)张载衡量理想政治的标准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王是否具有“父母之心”,亦即张载所指出的:“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于百姓,谓之王道可乎?所谓父母之心,非徒见于言,必须视四海之民如己之子。 ”[7](P349),在张载看来,“吾君爱天下之人如赤子”,“推父母之心于百姓”,“视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这都是把仁德落实于国家政事的首要原则。 而且,君主的“治德”不仅是衡量君主统治是否具有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君主是否能够发挥道德表率作用从而影响臣僚道德的一个重要标准。 因此,张载说:“仕者入治朝则德日进,入乱朝则德日退,只观在上者有可学无可学尔。 ”[7](P282)张载提出“推父母之心于百姓”,当然并不希望君主“徒见于言”,而是希望经由“为政者在乎足民”[7](P47)等具体措施加以落实。
(二)孝德价值
1.《正蒙》与孝德。 在《正蒙·诚明篇》中,张载特别重视《中庸》所谓“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君子诚之为贵”等思想资源,他提出:“天所以长久不已之道,乃所谓诚。 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诚身,不过不已于仁孝而已。故君子诚之为贵。”[7](P21)张载认为,“不已于仁孝”,是以“天所以长久不已之道”也就是“诚”为宇宙论根据的,这要求人们以“仁孝”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仁人孝子”⑤,是人在宇宙间所应当承担的角色;而“事天诚身”,则是人所应当履行的神圣信仰和伦理责任。 张载虽然是 “仁”“孝”合说的,但本文这里所强调的则是其中的孝德价值。 二程和朱熹一直贬《正蒙》而褒《西铭》,其实二者的义理是一致的。 于此,对比《正蒙》与《西铭》有关孝子及其孝德的论述,可以看得很清楚。
2.《西铭》与孝德。 《西铭》的基本义理是:以“乾坤”大父母为表征的宇宙根源论,以“仁孝”为核心的道德价值论,以“仁人孝子”“事天诚身”为担当的伦理义务论和伦理责任论。 “事天诚身”中的“诚身”,是君子效法天道之“诚”的修身实践。 此外,张载继承西周“敬天”、孔子“畏天”、孟子“事天”的传统,并充分调动了儒家的“事天”资源,为我所用。在《西铭》中,他说:“于时保之,子之翼也。 ”“于时保之”,源自《诗经·周颂·我将》“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朱熹的学生黄榦在其《西铭说》中强调,《西铭》“‘于时保之’ 以下, 即言人子尽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22](P1000)。 明儒刘儓解释说,《西铭》“‘于时保之’至末,皆言事天之功,即孝子之事”[22](P911)。 黄榦和刘儓都把《西铭》所谓“事天”作为“孝子”的伦理义务和伦理责任,畏天和事天属于“尽孝之道”和“孝子之事”。 于是,就把在家庭中对生身父母(包括祖先)行孝,扩大到宇宙范围,对乾坤父母行孝[23],使人成为“天地孝子”[24](P57)。孝德实践范围的扩大,意味着为其注入了神圣性,从而使孝德成为宗教信仰的重要维度之一。
晚清关学大儒刘古愚指出,《西铭》“不泥父母之身以为孝。此言出,闻者必大哗,以为邪说乱道”。他还指出,“俗传‘二十四孝’,史策所称皆不出服劳、奉养之外。 惟张子《西铭》以事亲言事天,则能事天方能事亲,不至能事天,不足以满养志至量”。 因而,“自汉以来, 儒者于孝之理未尽莹也”[25]。 由于《西铭》使孝德成为信仰的维度,因而当代著名学者杜维明把《西铭》视为“儒家的信仰宣言”[24](P56)。
三、张载价值观的理学体系定位
张载理学的体系特征十分突出。 海内外学者大多肯定张载理学有其完整的理论体系。 台湾著名学者韦政通在比较周敦颐、邵雍、张载的学说之后指出:“三人中对儒学真能登堂入室并发展出一个新系统的,就是张载。 ”[26]这里所谓“新系统”,也就是新体系的意思。 美国学者葛艾儒认为:“张载的著作散佚很多,不过,留存至今的还是足以让我们勾勒出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27](P1)。
张载于50 岁时自述说:“某近来思虑义理,大率亿度屡中可用,既是亿度屡中可用,则可以大受。某唱此绝学亦辄欲成一次第。 ”[7](P329)这里所谓“成一次第”,指张载所倡导和创建的理学已经于思想成熟期形成了严整有序的体系。 应当看到,张载的理学体系是有层次结构的。 张载指出:“知崇,天也,形而上也。 ”[7](P37)“‘形而上’,是无形体者也,故形以上者谓之道也;‘形而下’,是有形体者,故形以下者谓之器。 ”[7](P207)又指出:“运于无形之谓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7](P14)在张载看来,世界的存在是分为“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层次的。 这是《易传》以来古代哲学家的思考方式,也是张载的思考方式。 与张载“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划分相对应,有理由认为他的理学体系也有两个层次,即“形而上学”的层次与“形而下学”的层次。 具体言之,其理学体系的形而上学部分,包括天道论和心性论,而本体论则是形而上学的顶层,是形而上学的最高体现;作为其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的礼学,除其根源属于形而上学外,其主要内容都属于其理学体系的形而下学。
如果将张载价值观置于其“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这两个层次的任何一个层次,似乎都不合适;如果将张载价值观置于其“形而上学”顶层的本体论,则更不妥帖。 为了解决张载价值观在其理学体系中的定位问题,有必要对张载理学体系的层次进行重构,在其理学体系的“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这两个层次中间,增加一个“形而中学”的层次。 当然,对此还需要加以论证。 本文的这一重构,受到徐复观、庞朴、方东美等前辈学者相关研究的启发,拟把张载价值观定位于其理学体系的“形而中学”,从而对传统的“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的两层划分提供一种补充。 具体言之,本文重构的方案是:把张载理学体系划分为3 个层次:(1)处于上层的是,以“天”或“太虚”为本体、以天道论和心性论为主要内容的“形而上学”;(2)处于下层的是,通过思考自然、社会和人生而形成的古代自然知识、政治思想、教育思想和修养工夫论的“形而下学”;(3)处于中层的是,人的价值观乃至境界观,这是张载理学体系的“形而中学”。
台湾学者徐复观和大陆学者庞朴先后从不同角度使用过“形而中”或“形而中学”的说法。 先看徐复观的用法。 在解释《易传·系辞上》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时,他认为,“这是以人为中心所分的上下”。 徐复观指出,“假如按照原来的意思把话说完全,便应添一句‘形而中者谓之心’。 所以,心的文化、心的哲学,只能称为‘形而中学’,而不应讲成形而上学”[28]。 在这里,徐复观用“形而中”的说法指“心”的存在,用“形而中学”的说法则指“心”的学说,包括“心的文化”和“心的哲学”。 古今学者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句中的“形”字,都解释为世界中的“形质”“形象”或“器用”[29];而徐复观则将此“形”字,解释为人的形体,并以人为中心划分世界的上与下。这与《易传》的本意相差甚远。
再看庞朴的用法。 冯友兰认为, 中国古代的“天”有 5 种意义,即“物质之天”(天空)、“主宰之天”(天神)、“命运之天”(天命)、“自然之天”(天性)、“义理之天”(天理)[30]。 庞朴把冯友兰所说的这5 种意义压缩为3 种:“物质的天(天空、大自然)、精神的天(主宰、至上神)以及本然的天(本然意义上的物质,如牛马四足天性;被当成本然意义上的精神,如天理;以及本然意义上的气质,如天真)。 ”庞朴还认为,这3 种意义的“天”“分别为形而下的、形而上的和形而中的”[31]。 在他看来,形而上、形而下和形而中所说的都是“天”,而“形而中”指的则是“本然的天”。
庞朴所谓“形而中”,对应的是“天”这一存在的特定涵义,并不涉及如何对特定学说体系进行层次分析,与本文的着眼点和问题意识无关。 徐复观在承认以“道”为“形而上”和以“器”为“形而下”的同时,强调以“心”为“形而中”,以“心”的学说为“形而中学”。 这与本文同样关乎理学体系的分层,但分层的指向有别:徐复观的意图是强调,应当把“心学”定位于“形而中学”层面,而不能把“心学”定位于“形而上学”层面;本文则认为,就张载理学而言,“形而中学”指的是其理学体系中的价值观乃至境界观层次。 本文的这一认识,对其他理学家价值观的体系定位,或许也有参考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方东美在论及中国古代哲学体系时认为,居于上层的“天”与下层的“物质世界”“中间”的是“生命流行的境界”,人的生命可以充分利用物质条件,“生命可以发展它本身的创造性”。在“生命创造性里面”,人可以“从知识上作充分的发展,从价值上作充分的努力”[32]。 方东美的论述,着眼于世界的存在论和人的实践论,认为处于形而上的“天”与形而下的“物质世界”“中间”的是“生命的流行”,人需要“从价值上作充分的努力”。 这些说法,与本文对张载价值观的理学体系定位比较接近。
本文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方案,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理由。 首先,张载的价值观与其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之间有性质之别。 虽然张载所建构的以 “仁”“孝”“礼”为核心的人文价值也是无形的,但价值观毕竟与形上学的本体论有别。 作为形而上学顶层的本体存在,是具有至上性、根源性、“至一”性的⑥,而人文价值却并不具有这些性质。 在宋代理学各学派中,对本体的称呼各不相同,而且各个学派所认定的本体都是独一无二的。 例如, 张载以 “天”(“太虚”是“天”的别称)为本体,程朱以“天理”为本体,而陆九渊则以“本心”为本体。 但这几个学派在价值论上又无不认同“仁”“义”“礼”“智”“孝”等多样化的价值观。
其次,在张载的价值观之上有其形而上的哲学宇宙论根源。 张载所建构的以“仁”“孝”“礼”为核心的人文价值,毕竟要以作为宇宙本体的“天”以及作为宇宙生成力量的“道”“性”“神”为其根源。 这有儒家经典作为根据。 在《论语·述而》中,孔子自信“天生德于予”。 《易传·文言》宣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 《中庸》第二十章则提出“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 孔子与这些早期儒家经典的表述,意味着德性价值是根源于天、道、性等宇宙根源的。 据此,张载提出:“天所以长久不已之道,乃所谓诚。 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诚身,不过不已于仁孝而已。故君子诚之为贵。”[7](P21)在张载看来,“仁人孝子”“不已于仁孝”,是以“天所以长久不已之道”亦即“诚”为宇宙论根据的。 在《西铭》中,张载使这种观念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张载不仅认为 “仁”“孝”价值原则有其宇宙论根源,而且还认为,作为规范价值原则的“礼”也有其宇宙自然根源。 他说:“或者专以礼出于人,而不知礼本天之自然。 ”“知礼之本于自然,若顺而行之,则是知礼也。”[11](P342)因此,如果把“礼”和“仁”“孝”这一价值系统视作张载理学体系的形上学的本体论层面,则有可能导致其体系分层的错位。
最后,张载的价值观与形而下的现实世界及其学说有别。 虽然“礼”和“仁”“孝”等人文价值对于现实的生活世界具有直接的范导作用,但价值观毕竟是抽象的存在,与现实生活世界是有区别的。 因而,不能把“礼”和“仁”“孝”等人文价值系统与张载理学体系的“形而下学”层面等量齐观,将二者置于理学体系的同一层次。
总之,张载价值观在其理学体系中的地位,与形而上学尤其是其本体论,以及反映现实世界的形而下学说,都是有所区别的。 就张载理学形而上学尤其是其本体的作用看,它难以直接作用于形而下的现实生活世界;形而上的本体若要作用于形而下的现实世界,必须通过价值观这一中介才能够发挥作用。 这就使张载的价值观具有“上通”与“下贯”的特点:“上通”,指“礼”和“仁”“孝”等人文价值都与其哲学宇宙论相通,都有其宇宙本体论根源或宇宙生成论根源;“下贯”,指“礼”和“仁”“孝”等人文价值能够向下贯通于现实世界,能够对现实世界发挥直接的范导作用。 就是说,有理由把张载理学体系视作由“形而上学”、“形而中学”和“形而下学”这3 个层面构成的完整体系,把他的价值观定位于其理学体系的“形而中学”层面。 对于其价值观的体系定位问题,这可能是一个有效的观察视角。
四、“中正之道”是“尊礼贵德”价值观的最高原理
在《正蒙·中正篇》中,张载指出:“中正然后贯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 盖得正则得所止,得所止则可以弘而至于大。 ”[7](P26)据此,可以把这里所引用的张载所谓“中正然后贯天下之道”这句话概括为“中正之道”。 结合对张载所有著作相关论述的理解,可以视“中正之道”为张载价值观的最高原理。 把“中正之道”确定为张载价值观的最高原理,这是从整体视域加以理解的结果。 但也应当看到,“中正之道”原理当中的“正”与“中”,其意涵和功能是各有侧重的。
先看“正”的意涵和功能。 王夫之在解释上引张载所谓“得正则得所止”说:“所止者,至善也,事物所以然之实,成乎当然之则者也。 ”[8](P133)“得所止”与《大学》所谓“止于至善”有关。 对此,张载这样解释:“‘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此是有本也。思天下之善无不自此始, 然后定止, 于此发源立本。 ”[7](P328-329)他认为,“至善”是道德价值的根本,也是实践“天下之善”的开始。 将“至善”视作道德价值的本始,然后才可能“定止”。 因此,所谓“知止”“得所止”或“定止”之“止”,都指价值的方向。美国学者葛艾儒认为,张载强调“知止”的用意,是避免“‘止’错了地方”[27](P107,108)。 葛艾儒的这一看法是很确切的。 在张载看来,只有首先把“至善”确立为道德价值的方向,才能够进一步使之发扬光大。 总之,在张载的理学价值观中,“中正之道”之“正”,其基本意涵是至善,这是终极价值,能够总摄其他一切价值目类,例如总摄礼和仁、孝等价值。
次看“中”的意涵和功能。 张载对“中”有很多解释。 他说:“失之多,过也;失之寡,不及也。 止有两端,无三也。 凡学不是过,即是不及。 无过与不及,乃是中矣。 ”[11](P362)在这里,张载虽然是就“学”言“中”的,但这也适用于道德价值实现的“中”。 张载把价值实现意义上的“中”,也称作“中道”。他说:“今闻说到中道,无去处,不守定,又上面更求,则过中也,过则犹不及也。 ”[7](P266)张载把“至善”,也称作“极善”。 他说:“极善者,须以中道方谓极善,故大中谓之皇极。 盖过则便非善, 不及亦非善。 ”[7](P332)明儒刘儓在解释张载所谓“中”与“正”二者关系时说:“中而止于正也。 ”[22](P409)总之,“中正之道”之“中”,其基本意涵是规避过与不及的方法准则。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反复强调“德性就是中道”;“中道是一种决定着对情感和行为的选择的品质”;“中道在两种过错之间,一方面是过度,一方面是不及”[33](P32,34,38)。 张载与亚里士多德对“中道”意义的理解,非常接近。
总之,张载所谓“中正之道”,其“正”指至善,是总摄其他一切价值的终极价值;其“中”作为落实“正”的方法准则,能够发挥规避过与不及的作用,使价值的实施有度。 以下,基于“中正之道”的“中”这一方法准则,看它对“礼”和“仁”“孝”价值是如何发挥规避过与不及的调节作用的。
第一,中与礼。 儒者学“礼”,最容易出现的偏差是把礼仪规范视作矫揉造作的外在教条。 程门弟子谢良佐与弟子论学时,批评张载“以礼教学者”说:“横渠教人以礼为先,大要欲得正容谨节。 其意谓世人汗漫无守,便当以礼为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门人下稍头溺于刑名度数之间,行得来困,无所见处,如吃木札相似,更没滋味,遂生厌倦,故其学无传之者。 ”[34]所谓“吃木札”,是形容只知被动和机械循礼的贫乏无味。 在这里,谢良佐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在行礼实践过程中怎样才能够避免把礼仪规则当作外在的僵化教条? 其实,张载在推行以“礼”教人的过程中是用“礼”“敬”兼修来解决这一问题的。 他指出:“‘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 ”[7](P36)所谓“敬”,指人的内在精神气质,是行礼过程中主体的虔敬态度。 与“敬”相近的精神气质还有“诚”。 张载说:“此心苟息,则礼不备,文不当,故成就其身者须在礼,而成就礼则须至诚也。”[7](P266)但另一方面,“敬”“诚”也须在行礼中才能够得以彰显,张载说:“诚意而不以礼则无征,盖诚非礼无以见也。 ”[7](P266)张载认为,礼与敬、礼与诚这两个方面不可偏废,“诚意与行礼无有先后,须兼修之。 ”[7](P330)因此,他主张:“修持之道,既须虚心,又须得礼,内外发明,此合内外之道也。 ”[7](P270)所谓“合内外之道”,是强调学礼的途径在于把握内外“兼修”的原则,使内在精神价值与外在礼仪规范在行礼实践中获得平衡。 后来,元儒许衡评论这一问题时指出:“横渠教人以礼,使学者有所据守。 ”“然横渠之教人,亦使知礼之所以然乃可。 礼,岂可忽耶? 制之于外,以资其内。 外面文理都布摆得,是一切整暇身心,安得不泰然? 若无所见,如吃木札相似,却是为礼所窘束。 ”[35]许衡认为,张载首先要求学者基于对“礼”的充分理解,在此基础上处理好内外两方面的关系。 若如此,在行礼实践中就能够身心“泰然”,避免出现谢良佐所谓教人以礼“如吃木札相似”的结果。 许衡的论析,有助于回答谢良佐对张载以礼教弟子的质疑。
第二,中与仁。 仁爱,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儒家对“仁”之根据的认识,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包括孟子在内的早期儒家强调仁爱的血亲根据,北宋以来的理学家则重视仁爱的宇宙根源,或将其置于形而上学的基础上。 程颐较早意识到以血缘为根据的仁爱易导致为己之私,他指出:“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 ”[9](P609)《西铭》是张载仁爱观的纲领,体现了儒家在仁爱观方面的更加宏大的视野,为儒者提出了平等之爱的理想。 此外,张载在其《正蒙·诚明篇》中还提出了“爱必兼爱”的口号。 于是,儒家的仁爱理论在其理想与现实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张力。 张载的意图是, 调动平等之爱这一理想的力量,扩大仁爱的范围,以矫正“私胜害仁”的偏差,化解仁爱实践中的“公”与“私”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在差等之爱的现实面前止步。 正如熊十力所指出的:“夫日以兼爱之道警惕其心,犹不胜私情之弊也,而况可非兼爱以护其私乎? ”[36]但另一方面,张载在提出“爱必兼爱”的同时,并不否认差等之爱有其合理性,主张“施爱固由亲始”[7](P311)。 可以认为,张载以自己的方式使这两种不同层次的爱实现了一定的平衡。
第三,中与孝。 自从张载在《西铭》中提出基于宇宙根源的孝德之后,人们在“事天”与“事亲”的关系问题上便出现了分歧。 这从王夫之对周敦颐《太极图说》与张载《西铭》的误解中可以看出。 先看王夫之对周敦颐《太极图说》的误解。 王夫之把周敦颐《太极图说》的宗旨,归结为“推本天亲合一”[8](P313)。 而他对“天亲合一”是深表质疑的,指出,《太极图说》对宇宙万物生成的推演所导致的结果是,“人可以不父其父而父天, 不母其母而母地”[8](P313)。 此外,王夫之还指出,周敦颐认为人物以“乾坤为父母”,是“从其大者而言之”,问题是必须“从其切者而言之”。 怎样才能够 “从其切者而言之”? 王夫之主张,“别无所谓乾,父即生我之乾;别无所谓坤,母即成我之坤”。 因此,不能“舍父母而亲天地”。 王夫之认为,天、亲不应当是先天后亲的关系,而应当是先亲后天的关系。 再看王夫之对张载《西铭》的误解。 其实,王夫之对周敦颐《太极图说》的误解必然导致对张载《西铭》的误解。 他把天与人的关系模式概括为“天人相继”,作为对周敦颐“天亲合一”模式的替代[8](P314-315)。 通过他对周敦颐的批评可知,其“天人相继”模式在“事天”与“事亲”关系问题上,强调的是“事亲”的优先性,而这与张载《西铭》的宗旨是相悖的。张载门人吕大临指出:“人者,万物之灵,‘受天地之中以生’,为天地之心者也。 能知其所自出,故事天如事亲。 ”[37]吕大临对《西铭》的解读,与《西铭》基于宇宙的乾坤根源以确立新孝德是一致的。 总之,一方面,张载基于乾坤大父母的宇宙根源,用先天后亲为天、亲关系定位;另一方面,他在现实生活中强调事天如事亲,事亲如事天,以避免在天、亲关系上出现偏差。
注:
①赵馥洁先生撰写的《张载“太虚”之气的价值意蕴》(载加拿大《文化中国》2002 年第20 期),是国内学术界研究张载价值观最早的重要成果。此后,似再未见到与这一专题有关的研究。
②W.K.富兰克纳在其《价值和评价》一文中引用了培里和泰勒列举的八大价值领域:道德、艺术、科学、宗教、经济、政治、法律和习俗或礼仪。中国古代的价值领域,与此有不少交叉重叠(刘继编选.R.B.培里等.价值和评价——现代英美价值论集粹[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3.)。
③ 张岱年先生认为,在哲学上,“贵”和“尊”指应当尊重的高尚品质或事项。 例如,孔子弟子由子说“和为贵”,老子所谓“道之尊、德之贵”,都是指有价值(张岱年.思想·文化·道德[M].成都:巴蜀书社,1992.69,118.)。
④宋代学者吕本中、吕祖谦、朱熹、真德秀,元代学者胡炳文,明代学者吕柟,清代学者顾炎武、颜元等,都以各自的方式揭示了张载“以礼立教”或“以礼为教”的教学实践和教育哲学宗旨。
⑤ “仁人孝子”观念,源于《礼记》。 《礼记·哀公问》曰:“仁人事亲也如事天,事天也事亲,是故孝子成身。 ”
⑥关于本体的至上性,张载说:“天德即是虚,虚上更有何说也。 ”(张载.经学理窟·气质[A].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269.)在张载的话语系统中,“天德”是太虚本体的别称;“虚”,是“太虚”本体的简称。 关于本体的至一性,张载说:“静者,善之本;虚者,静之本。 静犹对动,虚则至一。 ”(张子语录·语录中[A].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