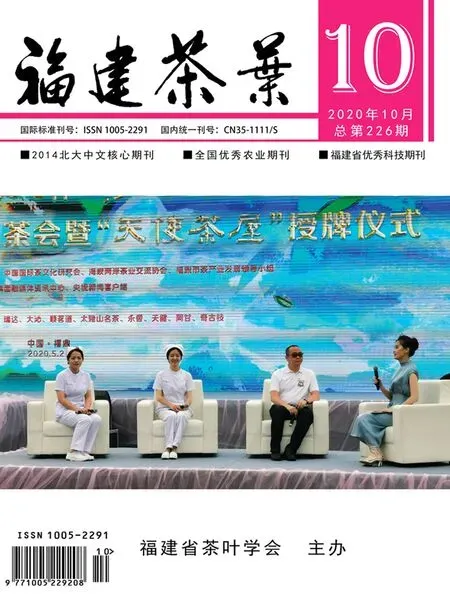魏晋风度背后的士人哲学人格微探
——茶文化的视角
吴 珍
(内江师范学院党委办公室,四川内江 641100)
纵观中国历代文化系统,魏晋文化无疑是让现代学者常谈而常新的话题。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呈现复杂交融的特点——道法趋于破裂,玄学向极端发展,佛教盛行等,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而这些复杂交融的文化现象的倡导者正是魏晋士族阶层。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的文明,绵延不绝而且愈益勃发。每个历史文化阶段的人们都对这一文明做出过贡献,在这一点上,魏晋士人在文化传承方面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处于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垄断地位的士族阶层的哲学观念与思想,进一步助推了魏晋文化的复杂、丰富与繁荣。
对于魏晋风度的内涵界定,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一谈及魏晋风度,我们头脑里闪现的便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多情男儿,酣畅淋漓后,寄情山水,逍遥放旷,抚琴吟唱。这在今人看来是多么令人神往。桃园兰亭、风神潇洒、竹林神韵、通脱玄远、药酒不羁的潇洒气质和“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反抗意识。遵循这个思路,我们可以大胆地给魏晋风度的基本内涵以及士人哲学人格做一个初步描绘的。
1 魏晋风度的社会背景和内涵
魏晋风度一般认为是魏正始年间到东晋灭亡这两百年间名士们所表现出的风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中记载的品评词语如“风貌”“风骨”“风流”“风神”等都与“风度”相似。人们从重视外貌服饰再到气度,又渐渐转向一种人的精神气质,如《世说新语》中的“识鉴”“赏誉”“品藻”“容止”等篇的记叙,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体现了个体存在意识的觉醒和张扬个性的自我发现。这一风度背后,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乱世。正如宗白华所言“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魏晋时期,三国鼎立以及西晋短暂统一之间的频繁战乱,士家大族兼并土地逐渐掌握实权并形成门阀世族,政权不断更迭,统治阶层的权力斗争从未间断,同时伴随着血腥杀戮,故言魏晋名士少有全者,就是这个道理。政治上的动荡和生命的朝不保夕,严重影响了魏晋名人士大夫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态度。如此一来,他们在政治上表现得不再那么关注,逃避现实以求明哲保身。思想上,他们质疑儒家思想,开始非汤武而薄周礼,倾心与《老子》《庄子》《周易》,接受“越名教而任自然”,以自然为尊,逐渐接受了消极避世但又含有思想解放的老庄思想。他们开始乐于清谈,转而把视角放在思考宇宙世界与生命个体的存在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寻求新的思辨方式。因而,人们也常说魏晋时期是“文人”觉醒的时代,他们敢于与礼教分庭抗礼,独树一帜,表达自我。我们所熟知的“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向秀、阮咸、刘伶、山涛和王戎,他们大多崇尚庄老之学。对当时社会现实有着比较清醒认识的他们,怀才不遇,自知没有值得辅助的明君,无力扭转乱世,也只得以不事修饰、逍遥放旷的外在行为来遮掩内心的孤寂、愤懑、和无奈。有人在思考魏晋风度时,也曾质疑其是否带有矫情和苟安的思想成分。其实,说矫情和苟安,也正是他们想遮掩真实内心逃避现实的体现。这不足为怪,更不至于成为污贬他们的借由。我们应当知道,魏晋风度绝不仅指士人的言谈举止和姿态风貌这些显性的东西。魏晋名士的交往,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文人墨客相遇相互的切磋,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那就是重情和纵情。比如嵇康,最是集风流才华于一身。他不仅吟诗酣酒,也纵情花场,多情于女子。与女子交好的他,也遇到了不少才貌并举的红尘佳人,比如身世坎坷红尘多舛的才女薛涛。在与薛涛的交往过程中,他们的思想碰撞并闪耀出火花,薛涛的才气让嵇康惊叹赞赏。而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相互之间的思想会相互接纳或抵触,并使各自思想观念通过双方人际关系圈,双双得到再度传播以致蔓延开来。鲁迅先生将其描述为一种率性任情、反抗礼教的文人心态和时代精神。李泽厚《美的历程》说“饮酒任气,高谈老庄,双修玄礼,既纵情享乐,又满怀哲意”。而冯友兰将之精炼地述为“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可谓一语中的。
故而魏晋风度是指魏晋时期士人们表现出来的风度。他们其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中占有统治地位,发挥主导作用,他们所持有共同的或相似的,反抗虚伪礼教、追求个性自由和率真人格,探寻生死和宇宙有无的思想观念集中表现成魏晋时期中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处变不惊、镇静自若,旷达傲世、任率自然,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超入玄心、表里澄澈,一往情深、天然风流等都是魏晋风度的表现形态。
2 魏晋风度下的士人人格形成
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因此,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藉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魏晋时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乱世,而生活在乱世中的人,不管是位高权重的统治阶级、风雨飘摇的名人墨客,还是卑微贫寒的平民百姓,都不可避免的要遭受既定生活环境带来的影响。统治阶级为权利而进行的不休止的惨烈混战,对他们的追逐迫害,日益伤害打消了士人们的报国出仕之心,越来越使他们憎恶社会、国家、世族等这些丑陋的代言人。然而,除了混乱政治,更是“社会上最痛苦”之际,诚可谓雪上加霜。据《后汉书》记载,魏晋时期多自然灾害,饥荒、虫灾、山崩、水灾、旱灾、地震、和瘟疫等,频频发生。仅瘟疫这一种惨绝人寰的灾害,不仅难以遏制而且死伤无数。“剩民百遗一”、“家家有僵尸之痛”的人间悲剧,尤其在建安时期的诗人的字里行间里展现得淋漓尽致。士人们面对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生活凄凉满目疮痍的社会惨象,曾经满怀的壮志豪情忧国忧民情怀早已被深深刺伤。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生命的朝不保夕,使得士人们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了无尽恐忧和深重伤痛。他们有的顺应政治形势,以求安身立命之本;有的纵情山水,以求暂时的精神解脱或麻痹。对在战乱与灾难的双重压迫威胁下,士人们深感个人之力变得十分渺小,流亡与死亡触目可及,生命无常的意识逐渐让他们开始明哲保身,只关心一家一人之安危,息声安身立命了。一如《阮籍传》言“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就是对他们生存环境的最好概括。
然而也是在这个最混乱、最多苦痛的年代,却是“精神史上极其自由、极其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士人不仅热衷于辨“自然”与“名教”的关系,还受着各种思潮的影响,同时在各自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独特心性、道德品质、实践行为指导下,通过内外化作用形成了各具风格魅力的哲学人格。
3 魏晋茶文化与士人的哲学人格
茶从古至今一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中国茶文化是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上孕育起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中国文化连绵延嗣的重要纽带,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关研究表明,从药用到饮用,茶文化的萌芽最早应该追溯到魏晋时期,在这个时期人们逐渐在茶中喝出了精神文化的微妙。
魏晋时期充满动荡和战乱,而在这一时期的茶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求和”的儒家思想,与儒家的精神追求却达到了完美契合。中庸思想是儒家思想的精髓,讲求适度,即在不偏不倚、不过不及的基础上确保事物始终处于最佳的状态,是儒家修身养性的重要原则和重要要求。具体到为人处世层面,中庸思想要求人们能够保持自身立场、尊重他人见解,做到恭敬谦虚、求同存异。儒家不仅爱茶,而且将茶作为修德、自省的有效依托,在此过程中,儒家的中庸思想与茶文化发展实现了紧密融合,并促使茶文化同样具备了强调与重视中庸的文化特点。而茶文化的精髓也可以用一个“和”字来概括,处处体现着“温、良、恭、俭、让”,传达着和生、和处的儒家价值观,逐渐形成儒家重视修身与自省、提升人格魅力的态度。此外,受儒家清廉、礼仪思想的影响,茶文化还能够帮助人们催生智慧、拒绝浮躁,形成稳重诚信的人格,培养良好的人际交往观念和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总之,魏晋风度下的茶文化对士人情怀寄托和文化传承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4 魏晋士人的哲学人格微探
每一种文化的形成都与这一文化所处的时代紧密相关。既然说魏晋风度是一个时代所内涵着的整体风尚和气息,那么我想,我们就不应将风度限制在名人士大夫身上,同时哲学人格这个词也不应只用以描述那些名士,而应该认同接纳处于社会统治地位的政治家、处于社会下层的卑微农民以及像薛涛那样的身处红尘却才貌横溢的风尘佳人。当然,魏晋风度的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和主体地位的,魏晋名士一直被人们颂为潇洒清远的存在。
魏晋士人身处动荡社会之中,生命稍纵即逝,又为繁琐礼教所负累。他们饮酒、服五石散,不泥于行迹,不拘于礼法,心随自然。尽管我们说清名淡利是魏晋名士的精神诉求,但我们深知,做为从红尘乱世中跌跌撞撞爬出来的他们,怎可能忘却少年壮志和抱负?也就是说,他们生为忧国忧民生,死亦为忧国忧民死。如此,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使命和特质。意即,无论他们表现出来的是多么豁达明朗、洒脱纨绔、清心寡欲、纵饮吟唱、服药求仙等,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是不为人知的矛盾、苦痛和折磨。他们一直在入世与出世,务实与超脱之间痛苦徘徊。
人是一个矛盾体。更何况是魏晋那些富有哲学思辨的士人呢?所以,正如之前说到的,面对无力扭转的社会现实,尽管他们表现得与政治背离甚或对立,只能将意识角度转向关于宇宙与有无、生命与价值等精神层面的内容上。魏晋士人,如王谢世家大族的后人王弼,“以无为本”、“得意忘象”、“崇本息末”,人们似乎很难剖析他们到底要表达什么。他们高谈老庄,大兴清谈、思想玄远、虚若飘渺,他们或被称为气质与才华并存的才子,也或被称为一群不务正务的闲人。事实上,他们意识里还是强烈的执著于现实与人生,因而他们变得异常的矛盾无助。那种矛盾与无助,是如今的我们无法深切感知和体会的。正因为无法感知,使得那段封尘褪去的历史,深刻地深重。
淡名薄利和率真自然是魏晋风度的内在追求和应有之意;而潇洒豁达和放旷不羁是魏晋风度的外化表现。内外两面是相互作用相互蕴藉的,共同体现了魏晋风度的深刻内涵。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思想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魏晋风度因其独特时代背景和独特气质,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此外,它的魅力无限,吸引着后世人们不断探寻追随,越探越深越爱,尤其是对后世的哲学家和文学家等的哲学文化思考,产生了不可替代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