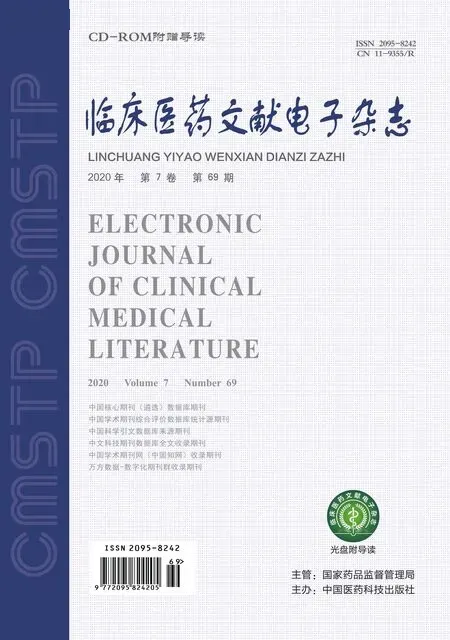中医运气学说的内经源流及后世阐发
刘儒鹏,张 云,卫万一,王鸿红*,孙怀聪*
(1.广西中医药大学壮医药学院,广西 南宁 530200;2.广西中医药大学赛恩斯新医药学院,广西 南宁 530200;3.北京鼎盛外经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100000)
中医学说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财富与重要构成,运气学说是我国中医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理论之一,对《内经》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不断丰富,形成了独特的中医病情诊断与治疗方式。
1 运气学说来源发展
运气学说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有所体现,《六节藏象论》中在记载一些古代的天文历法的同时,对运气学说有一定阐述,有针对运气学说较为明确的经文,经文在沿袭了五行学说的基础上,通过气候的观察与判断而得出人体疾病的发展变化趋势,以此促进对人体疾病的预测、判断与治疗,所运用的原理较为朴素而简单,与七篇大论中所阐述的理论较为相似。《六节藏象论》在运气学说研究与运用过程中,只提出五运之说,而并无六气之说,六气可运用于对人体风寒暑湿燥火的判断。运气学说中一个运气周期为一个气候年,从立春之日即开始计算。在对人体发病情况以及一年中气候的判断层面并非运用较为繁琐的术数推算,而是有效分析立春日的气候,以此预测一年气候的可能性情况以及对人体身体素质可能造成的影响。由此在对术数的推演层面并没有使用较为机械而的计算方式,运用的推演方式较为朴素而客观[1]。
2 中医运气学说内涵
运气学说理论中,综合运用天干地支与木火土金水等来分析天地气候的变化对人体机能的影响,包括主运、大运以及客运。运气学说中在分析疾病对人体影响层面没有道教中体现的部分迷信与术数层面的信息,而是提出气候对人体疾病的影响“所胜则微,所不胜则甚”。《六节藏象论》中论述的运气学说中,从天文历法的角度解读疾病与人体的影响,构成了中医学对人体疾病分析的重要理论雏形。七篇大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较为完善而系统性的运气学说理论。《六节藏象论》中形成了关于运气学说的基本理论术语,包括六气、太过、平气`、五运、不及等。
在对《内经》理论进行进一步继承与发扬的基础上形成了七篇大论,并构成了较为完善而系统性的运气学说。在《内经》中一贯强调自然、天地与人之间的一种相互参应关系,在运气学说中对此进行了阐发,提出人体生活活动的进行与疾病的发生受到周围自然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天地之间的运动对气候变化对人体具有较为深远的变化与影响,因此中医理论中,在对人体疾病的研究与治疗层面从气候变化情况入手进行分析,以此判断疾病的发展趋势以及可能采用的治疗方法。中医运气学说为此在治疗层面,将自然科学知识与医药学理论知识进行了有效融合,对天文历法知识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挖掘,由此创建了一套独特的中医疾病治疗理论知识[2]。
《内经》的早期篇章中已经具有关于运气学说的相关内容,提出了病痛发病机理、阴阳五行、病症以及治则治法的相关原理。运气学说的理论框架为阴阳五行理论,《五常政大论》中提出了运气学中运用的相关元素,包括五季、五气、五数、五色、五音、五味、五谷、五虫、五畜、五藏、五窍、五体。运气学说中具有太阴、太阳、少阳、少阴、太阴、厥阴。在《内经》中蕴含了大量关于阴阳五行的知识,以此丰富运气学说[3]。
在《内经》学说中有关于疾病方面的机理、疾病名称以及病候的介绍,讲述了气候与疾病之间的关系,《至真要大论》中提出“民病洒洒振寒,善伸数欠,心痛支满,两胁里急,食饮不下,扁咽不通,食则呕,腹胀善嗯,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身体皆重”,以此讲解泉、淫胜复病候的相关知识,《邪气02者,腹胀,胃脱当心而痛,上支两胁,隔咽不通,食饮不下”,两者在对胃病机理阐述本质一致。《内经》中在对中医病机理学的研究上提出了“六气”病机,有效总结了脏腑的发病机理。七篇大论治疗中提出了因时制宜的治疗方式,分析泉司天、淫胜复治疗中六气的作用,结合五味阴阳五行属性辅助研究结论的得出。《素问·标本病传论》中论述了六气标本中气的治疗原则。
3 七篇大论运气学说
运气学说在我国中医治疗中有着重要体现,整体层面契合了人与天地相参的意识与观念,在《内经》中已经具有较为简单而初步的运气学说基本内容,在对《内经》中相关理论学说进行沿袭并结合阴阳五行的基础上形成了病因诊断与疾病诊断原则与诊治理论。将《内经》中形成的病因病机病证、阴阳五行、治则治法等理论体系与天文历法知识进行了有效糅合,以此在对疾病诊断、病情发展预测过程中运用了气候变化的相关知识,由此重构了《内经》中较为朴素而简单的疾病治疗与预测方法,形成了较为完善而系统的疾病治疗体系,能够推算出较为一段时间内气候的变化发展情况,并对人体发病趋势运用五运六气学说进行分析、判断与预测。在中医治疗中,从语言文字、内容结构等层面对《内经》中的内容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索,构成了中医治疗中重要理论体系之一[4]。
4 中医运气学说后世阐发
根据运气学说理论,五行与天干具有相同的属性,能够体现一年间气候的变化特征,包括太过与不及,两者的判断依据是天干奇偶性,偶数天干表示气候不及,奇数天干表示气候太过。起运节点为大寒,在运气太过或者不及情况下,与五运、五行以及人体五脏分别具有相应的对应关系,由此通过相应气候的变化能够反应出人体相应脏器中的疾病情况。例如木运太过的壬年,风气较为盛行,会出现风证,在土与木两者因素共同影响之下,会导致人体容易出现脾土疾病。在木运不足的丁年,一般可见燥气多发现,反应在人体机能上容易出现燥证、肺金疾病以及寒证等。但是在水运不及的辛年,湿邪较为明显,反映在人体机能上表现为湿证、脾系疾病等。天干与地支中的司天之气在生克情况下较易出现平气之年,对人体机理也会产生相应的影响。在天干太过而地支司天会对此对此进行一定抑制而出现平气之年,例如金运的平气之年有庚午年、庚子年,火云的平气之年有戊戌年、戊辰年。同时在天干不及地支司天之气的情况下,后者也可以补助前者,司天之气与大运属性相同的年份包括乙酉年与乙卯年,能够补助不及的大运。在疾病治疗过程中可以结合对当年气候的分析进行,这是中医治疗过程中的重要理论之一。运气学说对中医治疗提供了重要视角[5]。
5 结束语
大运不及或者大过均会反应在气候层面,并对人体疾病产生相应影响,通过对运气的研究能够反应出人体疾病的发病规律等,《内经》中体现的运气学说经过不断丰富与发展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而系统的发展体系,能够通过对特定时间内气象与气候的观测而判断其给人体可能造成的影响,从而预测可能出现的疾病,形成了一些气象与物候方面的疫病分析、判断方法,以此丰富了现代中医治疗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