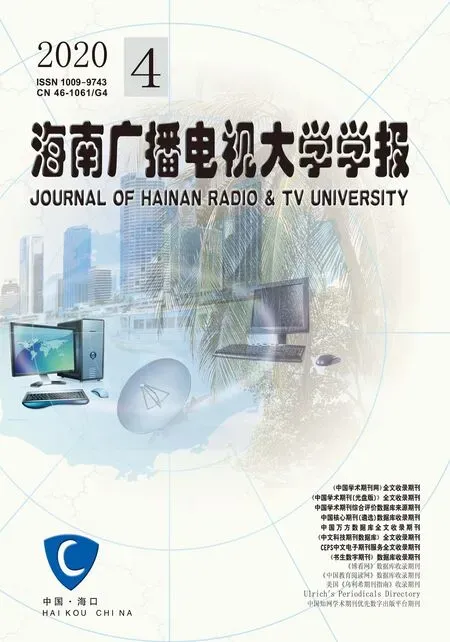释《文心雕龙·诸子》篇“混洞虚诞”
柯月吟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刘勰在《文心雕龙·诸子》篇论述诸子之文的“纯粹之类”与“踳驳之类”时,有如下一段话:
然繁辞虽积,而本体易总,述道言治,枝条五经。其纯粹者入矩,踳驳者出规。礼记月令,取乎吕氏之纪;三年问丧,写乎荀子之书:此纯粹之类也。若乃汤之问棘,云蚊睫有雷霆之声;惠施对梁王,云蜗角有伏尸之战;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谈,淮南有倾天折地之说:此踳驳之类也。是以世疾诸混同虚诞。
其中“是以世疾诸混同(洞)虚诞”一句引发诸多学者不同见解,但对此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却寥寥无几。现有对《诸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诸子》征引文献考,《诸子》文体批评研究,刘勰的“宗经”“离经”思想,刘勰的子学观,刘勰对某些诸子学派的辨析与讨论,以及对经子关系、史子关系、子论关系的论述等。
只有庞瑞东在《〈文心雕龙·诸子〉辨疑》一文中,对争议颇多的“混同(洞)虚诞”一词作了简要释疑。庞瑞东认为按“混同”本义解或释为“混沦不分”是最适合刘勰原意的。且根据刘勰“览华而食实,弃邪而采正”的辩证观,及他对诸子著作所持的肯定态度,推测出他旨在批评世人而非诸子[1]。然而,此文论据稍显单薄,且作者对该词的最早版本是“混同”还是“混洞”尚存疑问。因此,究竟哪种见解最合刘勰本意,还需从文本出发,以探明“混洞虚诞”一词的具体内涵。
一、“混洞虚诞”的多种阐释
《文心雕龙校证》注称:
“世疾诸子,混洞虚诞”,原本無“子”字,何校云:“诸”下疑脱“子”字。《读书引》有,今据补。王惟俭本“子”字作空白。黄注本,“洞”改“同”,谢删此七字。纪云:“是以”句有譌脱。范云:诸下脱一“子”字……案范说脱“子”字,与《读书引》暗合。下文云:“按《归藏》之经,大明迂怪,乃称羿毙十日,嫦娥奔月。殷易如兹,况诸子乎!”上下文正相照应[2]。
依王利器所言,《读书引》中“诸”后有一“子”字;且“诸”后有“子”字才能与下文“况诸子乎”相照应。因此王利器、范文澜等皆认为“是以世疾诸混同虚诞”句中“诸”后脱一“子”字。
诚然,上文所提《吕氏春秋》《荀子》《列子》《淮南子》皆为诸子之作,“诸”后加一“子”也正好前后呼应。众学者对此虽无太大争议,但对“混洞虚诞”4字的理解却大相径庭。
不同注本在“洞”与“同”的取舍上也存在分歧。如沈岩引何校本“洞”改“同[3]641-642”。黄叔琳在《文心雕龙辑注》中作“混同(一作洞)虚诞”,却未对“洞”与“同”进行辨析。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虽写作“同”,又言:“一作‘洞’,铃木云:诸本作‘洞’。”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亦作“混同虚诞”。而詹瑛《文心雕龙义证》、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王运熙《文心雕龙译注》等注本中作“混洞虚诞”。在各家注本中,因“洞”字与“同”字相异也产生了不同释义。
(一)释“混同”为“鸿洞”
扬雄认为诸子多有辩辞,范文澜引此为例,将“混同”释为“鸿洞”,又将“鸿洞”释为“繁辞”。仅仅是“疑当做”,又只引扬雄对待诸子的态度为证,考证稍显不足。且联系《诸子》篇原文,刘勰虽提及“繁辞虽积”,但与范文澜所谓的“文辞繁多”似有所区别。刘勰也从未提及诸子书文辞繁多,反而对《列子》《淮南子》等诸子书的文辞风格进行大力褒扬。范文澜注称:
混同,疑当作鸿洞。鸿洞,相连貌,谓繁辞也。《汉书·扬雄传》:“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詆訾圣人,即(王念孙曰:即,犹或也)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或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4]。”
陆侃如、牟世金注与范文澜注相似,但没有深入说明缘由,其注为:
混同当作鸿洞,相连的样子,这里指文辞繁多[5]。
(二)释“混同”为“混淆、等同”
林杉认为若将“混同”当作本意来解,是最符合刘勰原意的。其译为:
因此世人憎恶诸子,把他们之作都混同于虚妄怪诞之说[6]。
吴林伯之注解则有失偏颇,其将“诸”释为“于”,一则未考虑到前后文所讨论的对象为诸子;二则将论述对象范围扩大,即把诸子中的荒诞之说扩至所有含有荒诞之说的事物。其译为:
疾,恨。诸,于。虚诞,指上述神话、寓言。世人所恨者,虚诞与真实混同而不分[7]。
(三)释“混洞”为“混沦不分”
周振甫注本稍显随意,其将“混洞”译为“好坏混杂”,“虚诞”译为“虚假”,无根无据,不免显得有些牵强附会。其译如下:
因此世人批评诸子书,好坏混杂而多虚假[8]。
(四)释“混洞”为“杂乱、空洞(虚)”
虽然戚良德注本、王运熙注本皆为“混洞”、“虚诞”各2字并列,而杨明照注本为“混”“洞”“虚”“诞”各4字并列,但两者释义基本相同。
戚良德注本译称:所以世人痛恨诸子之作,正因其杂乱空洞和虚妄荒诞[9]。王运熙、周锋注本译称:因此世人讨厌诸子书的杂乱空虚、荒诞不实[10]。杨明照《校注》从4字字义解释入手,并从构词法方面反驳了“鸿洞”的释义:“混洞虚诞”四字并列而各明一义:“混”谓其杂,“洞”谓其空,“虚”谓其不实,“诞”谓其不经,皆就“踳驳”方面言。若作“鸿洞”,则为联绵词,(与澒洞、虹洞、港洞同)与“虚诞”二字不类矣[11]168-169。
二、“混洞虚诞”释义辨析
关于“混洞”与“混同”该取何者,杨明照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中做过细致考证:
范谓“混同”当作“鸿洞”则非。元本、弘治本、活字本、汪本、佘本、张本、两京本、何本、胡本、王批本、训故本、梅本、凌本、合刻本、梁本、祕书本、谢钞本、别解本、增订别解本、清谨轩本、冈本、尚古本、文津本、王本、张松孙本、郑藏钞本、崇文本并作“混洞”;《子苑》、《古论大观》引同,黄氏改“洞”作“同”,非也[11]168。
杨明照引27个古本(包括元至正本)为例,皆证明其为“混洞”;且在《子苑》《古论大观》两书中也引作“混洞”。黄叔琳无故改“洞”作“同”,则是不经之谈。因此,多家注本皆取作“混洞虚诞”,应是无误的。
学术界对“混洞虚诞”的解释大致不出4种。周振甫注本将“混洞”释为“混沌不分”,明显带有臆测成分,不具说服力。范文澜注本与陆侃如、牟世金注本释“混同”为“鸿洞”,意为文辞繁多:此种说法似乎显得捉襟见肘,且与刘勰对待诸子的态度不符。林杉注本、吴林伯注本作“混同”,只凭猜测,难以自圆其说。
而戚良德注本、王运熙注本、杨明照注本皆将“混洞虚诞”看成是并列结构。《文心雕龙》用骈文写就,讲究字句对仗。杨明照所言“混洞”2字与“虚诞”2字相类,或许是考虑到这一点。
《说文解字注》中对此4字解释如下:“混,丰流也,盛满之流也……训为水浊,训为杂乱[12]546。” “洞,疾流也……引伸为洞达、为洞壑[12]549。” “虚,大丘也……虚本谓大丘,大则空旷,故引伸之为空虚……又引伸之为凡不实之称[12]386。” “诞,词诞也……释诂、毛传皆云,诞,大也[12]98。”段玉裁从字本身着手,将“混”引申为杂乱,“洞”释为“洞壑”(洞、壑中皆为空),“虚”引申为空虚、不实,“诞”为没有根据的话。这些与杨明照所注“‘混’谓其杂,‘洞’谓其空,‘虚’谓其不实,‘诞’谓其不经”正相符合。
因此,无论是从构词方面,还是字义方面,杨明照的注释无疑都是最具说服力的。之后在论述刘勰对待诸子的矛盾态度时,还将深入探讨这一问题。
三、“混洞虚诞”观之意旨探疑
詹瑛在《文心雕龙义证》中曾引王金凌语:“刘勰此语是针对《庄子》《列子》《淮南子》的寓言而发,寓言总是借荒唐之语表达其意,但刘勰宗经,故诋为踳驳、虚诞[3]642。”
王金凌所言并不全然正确。一者,刘勰确实宗经,但他的文学思想是复杂的:于宗经之外,他又提出了正纬和辩骚,因此不能仅从宗经角度而将寓言归为“荒唐之语”;二者,“诋”字有贬抑倾向,而刘勰的褒贬态度在此并未表现得十分明确。
其实,刘勰并非对世人眼中“混洞虚诞”的诸子之作表示不满,他颇为不满的是诸子著作中商鞅弃仁废义的“六虱”之说、韩非子欺罔人主的“五蠹”之论,这些明显背弃儒家经典的内容是与他“征圣”、“宗经”思想格格不入的。此外,公孙龙“白马非马,孤犊无母”的观点,无异于儒家的巧言令色之谈,更是与《原道》篇中刘勰所谓圣人“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的观点背道而驰。因此王氏之言是有失刘勰本意的。
(一)刘勰的矛盾态度
刘勰却是在宗经思想引领下认为诸子中的一些神话存在驳杂之处,但他在论述诸子之作时,对其所谓的“踳驳之类”既不完全肯定,又不一味排斥。他并未直言“是以诸子混洞虚诞”,而是用了“此亦是,彼亦是”态度来述说“是以世疾诸子混洞虚诞”,他阐述了世人的普遍观点而隐匿了自己的见地。“按归藏之经,大明迂怪,乃称羿弊十日,嫦娥奔月。殷汤如兹,况诸子乎!”之后,刘勰指出了圣人经典《归藏易》中存在的“大明迂怪”之例,并用其中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的神话来为《诸子》进行辩护:连圣人经书尚且如此,更何况是诸子之书!刘勰以圣人经书为范式,并用经书中类似的例子来说明诸子神话的“踳驳”是可以理解的,从而表现出他对诸子的宽容。
除《诸子》篇外,《文心雕龙》的《正纬》篇与《辩骚》篇也提及了神话。《正纬》篇:若乃羲农轩皞之源,山渎钟律之要,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后来辞人,采摭英华。纬书中出现的灵应传说、符验祥瑞,虽背于经书,有伤于雅正,但刘勰却称赞其奇异瑰伟、辞采华丽。刘勰在肯定纬书“事丰奇伟”之时,与其在《宗经》篇中提到的“事信而不诞”的说法显然又有所矛盾。
《辩骚》篇里举了“异乎经典”者四事,前二事如下: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前者是屈原借神话人物设辞取譬,后者列举了共工怒触不周山、后羿射日等神话,刘勰虽然将其分别归为“诡异之辞”和“谲怪之谈”,但对此并未持反对态度。与论《诸子》篇的“踳驳之类”相似,在他看来这些不过是与儒家经典相异的内容。
可见,刘勰一方面受到宗经思想影响,依经立义;一方面又不囿于成见,借经护子。他发现了“文学发展中任自然的思想潮流,并重感情、重才性、重自我在文学创作中的价值;又提出宗经的主张,为文学立下不变法则,以防止离经叛道:他处处把这两者相统一,以建构自己的体系[13]333-334”。
(二)“依经立义”观
刘勰认为“五经为群言之祖,一切文章以五经为宗[13]327”。《宗经》篇谓: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刘勰在此以极其崇高的视角来看待“五经”。所谓“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即后世诸种文体的变化皆尊奉“五经”的法度。
罗宗强认为宗经的思想基础是圣人崇拜,“董仲舒把儒家圣人的地位提到与天相配的高度,尊圣也就是奉天之命以法古[14]45”。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圣人所定“五经”上升至主流位置,其余诸子百家则处于次要地位。人们在论述诸子时,往往会将其与儒家经典相比较。如《汉书·艺文志》中提及诸子百家时称: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弊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王充在《论衡·超奇》篇中以王者与相的关系来取譬儒家经典与诸子之作:然则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诸子之传书,素相之事也。汉代以来,以儒经为最高,具体评判诸子书时,也以是否合乎经书为标准。譬如,刘向曾言《列子》书中《穆王》《汤问》两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非君子之言”即有不符儒家经典的含义。班固在《离骚序》中谈及神话传说时称:《离骚》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
当然,刘勰本就从宗经的角度来审视其他文学著述,他对诸子的看法,更是受到了其所处时代依附于经义上的神话观的影响。因此,刘勰在《诸子》篇中称“纯粹者入矩,踳驳者出规”,并将“移山跨海”等神话归为“踳驳之类”,还陈述了世人认为诸子“混洞虚诞”的普遍观念。
(三)“借经护子”观
《论语·述而》云:“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不谈“力不由理”的怪力与“神不由正”的乱神,并非代表他对神异鬼怪皆无敬畏之心。刘勰也是如此,虽主张“事信而不诞”,把移山跨海等神话归为违背经书法度的“踳驳之类”,但他对待世人所称诸子书中带有“虚诞”成分的神话,或许抱持的是一份敬畏与欣赏之心。
“刘勰的宗经思想,是较为开放的。它兼容着文学与学术分流之后发展起来的艺术经验,与拘于‘经’、绝对尊崇‘经’的思想、完全回归于经的写法的守旧思想有别[14]49。”刘勰是颇有主见的,虽不离征圣、宗经思想,但却懂得运用“借经护子”技巧,依儒家经典为诸子中驳杂的神话作辩护。由此可看出刘勰对诸子所持的矛盾态度,此种矛盾态度使得他在宗范儒家经典与推崇诸子著作中各执一端。其推崇诸子之由,一者在于他企望与诸子一样,能通过著书立说来扬名立万;二者在于他个人所持有的缜密的辩证思维。
《诸子》篇开篇提到: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在《序志》篇也有相同的论述: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立言,岂好辨哉?不得已也!
刘勰在《文心雕龙》多处地方表达出的欲通过著书立说以求不朽之名的强烈愿望,称赞诸子“英才特达”“俊乂蜂起”“辨雕万物,智周宇宙”的溢美之词,以及对诸子文章风格的褒赞之情,都足以看出刘勰对诸子所持有的欣赏态度。其实《文心雕龙》一书可以说是被刘勰当做子书来写的,正如曹学佺和钟惺所言,刘勰乃在“以子自居”。另外,刘勰虽认为诸子著作有“入矩”也有“出规”,还曾不满于“六虱五蠹”之说、“白马孤犊”之论。但在分析诸子之作时,他却劝诫识见广博之人勿要囿于一偏,而应认真看待诸子之作中的差异,汲取诸子之作中的精华,以便拥有一个宽广的视野。然洽闻之士,宜撮纲要,览华而食实,弃邪而采正。极睇参差,亦学家之壮观也。
虽然刘勰所谓的邪说与正说还是未跳出儒家思维的圈子,但相比同时代学人而言已是独具慧眼了。因为“强大的思想传统和强大的现实思潮同时左右着他,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都得同时接受。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思想家,他以最彻底的反传统的面目出现,而他自己身上,却处处是传统思想的印记,反之亦然[13]334。”
总之,学界诸人对“混洞虚诞”一词的理解虽各持己见,但将“混洞虚诞”4字并列而分别释义一说,无疑是最契合刘勰本意的。对世人认为诸子著作“混洞虚诞”之说,刘勰所持的是一种矛盾态度:他既宗范儒家经典,用儒家经义来评判诸子著作;又别具慧眼,用儒家经典为诸子中的神话进行辩护。正因此,才引得诸家在“混洞虚诞”一词上众说纷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