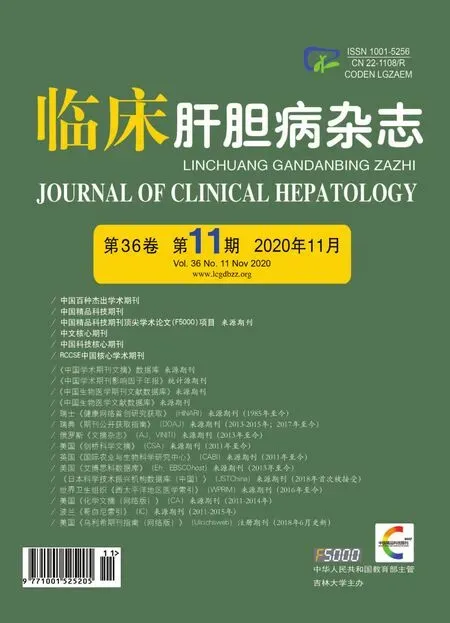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到代谢性脂肪性肝病
——基于疾病异质性角度的分析
林思岑, 冯 巩, 刘军林, 严琴琴, 弥 曼
西安医学院 a.外国语学院; b.全科医学研究所; c.党委宣传部, 西安 710021
早在1980年,Ludwig等[1]便提出了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用来描述在没有大量酒精摄入的情况下出现的脂肪性肝病,然而,诊断的命名和标准一直没有被重新讨论过。随着NAFLD发病率的上升,它对社会的医疗和经济等方面造成了重大影响。目前,全球约有10亿NAFLD患者[2],同时,儿童和青少年的NAFLD发病率也不断上升,并且会造成许多肝外并发症,这给个人、家庭和卫生保健系统带来了巨大的负担。此外,有效的治疗药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获得批准。到目前为止,一些2b期和3期临床研究尚未达到当前要求的组织学终点,处于开发中的各种药物的疗效也不佳,部分原因是由于疾病定义不准确,并且疾病存在异质性,从而缺乏精准的治疗药物。许多不同的疾病途径可以导致相同的组织表型,然而目前的试验招募是基于组织学分级和分期,没有明确和区分主要的致病途径[3-4],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目前研究药物的应答率为20%~40%,与安慰剂相差10%~20%[5]。
考虑到NAFLD命名带来的异质性等负面影响,相关学者建议将NAFLD改名为代谢性脂肪性肝病(metab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MAFLD),这将能够通过应用更精确的遗传、人体测量和代谢表型方法来适当地对患者进行分层。反过来,详细的疾病表型将有利于建立个性化的风险预测和预防策略,推动临床试验设计的完善。
1 NAFLD异质性对临床实践的影响
首先,NAFLD的异质性会对肝纤维化状态无创性评估造成影响。非侵入性纤维化评分通常用于识别或排除脂肪性肝病患者的显著或晚期纤维化。然而,最近的一项研究[6]表明,NAFLD无创性纤维化评分,如NFS评分和FIB-4评分的诊断效能会受年龄的影响,其中老年人的特异性较低,年轻人的准确性较低。非侵入性评分和瞬时弹性成像的诊断效能也会受不同种族人群和特殊亚群(如糖尿病和肥胖者)的影响。例如,已有研究[7]表明,与欧洲人相比,南亚人的血液生物标志物的准确性较低。因此,在设计和应用风险分层无创诊断评分和算法时,应考虑影响NAFLD异质性的因素。
其次,NAFLD的异质性会对临床试验设计和开发新的有效治疗方案产生影响。在缺乏有效的药物治疗的背景下,NAFLD的临床试验数量从2013年的仅8项跃升至2018年的300多项[8]。然而不幸的是,药物应答率仍然不高,不到20%~30%的参与者表现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消退和纤维化消退。这种低反应可以归因于许多因素,包括群体选择的异质性,缺乏基于潜在疾病机制的分层,以及安慰剂效应等[9]。因此,没有考虑疾病异质性的标准临床试验设计可能不是研究复杂疾病的最佳选择。一旦了解了疾病相关特征和治疗目标之间的关系,未来的临床试验可能会针对具有特定特征(性别、激素状况、遗传倾向、代谢和微生物区系特征以及是否存在共病情况)的患者。考虑到NAFLD在种族和地理区域的异质性,关键试验应考虑进行区域分层或在不同地理区域进行单独试验。
2 NAFLD异质性的来源
NAFLD临床表现和病程的异质性体现在许多方面,首先,NAFLD是一种具有复杂和不同病因的表型;目前的术语NAFLD代表了多个潜在亚型的总称[10-11]。疾病严重程度和自然病史的广泛范围,以及整个范围内患者之间的巨大变异性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肝脏脂肪变性非常普遍,但只有一小部分人在任何时候都会出现炎性损伤;更重要的是,即使在很短的时间内,个体也可以在脂肪变性和脂肪性肝炎之间摇摆[12]。其次,尽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脂肪性肝炎患者更有可能出现与肝脏相关的并发症(即肝硬化和癌症),但其进展不是不可避免的[13-14]。此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没有肝硬化的情况下,脂肪肝可以发展为肝细胞癌。即使在脂肪性肝炎患者中,似乎也有明显的快速纤维化进展和天生缓慢纤维化进展的个体[15]。最后,疾病演变可以通过外源性干预(例如,生活方式的改变)[16]、叠加的疾病状态(例如,2型糖尿病)[17]、遗传易感性[18]来改变,甚至可以“自发”退化,目前尚不清楚NAFLD进展的倾向是否会在一生中有所不同。例如,NAFLD在儿童和青少年中的患病率迅速上升,但不确定他们的自然病史是否与那些在成年、中年甚至老年时患病者的发展轨迹不同。脂肪肝的临床表现和病程的异质性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下面对NAFLD异质性的来源进行总结。
2.1 年龄和性别 NAFLD的患病率、肝和肝外并发症的风险,以及总体和疾病特异性死亡的可能性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19]。随着年龄的增长,肝脏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包括肝脏血流量、肝脏体积和肝功能的下降,胆汁酸合成的减少和胆固醇代谢的改变,以及线粒体数量的减少和随后氧化呼吸的增加。细胞衰老也牵涉其中[20-21]。衰老往往伴随着身体成分的变化,包括肌肉质量减少,腹部肥胖增加和异位脂肪沉积,胰岛素抵抗增加和代谢综合征的流行[22-23]。新出现的证据[24-25]表明,即使在调整了BMI和胰岛素抵抗后,肌少症也与NAFLD相关的进展期纤维化有关。据推测,衰老最终还会导致脂肪性肝炎和纤维化的发生。
最近的一项综述[26]表明,脂肪肝的许多方面,如危险因素、患病率、纤维化程度和疾病结局方面都受性别的影响。一般来说,女性的患病率往往较低,主要是在疾病的早期阶段,而绝经后女性的疾病频率增加[26]。同样,月经初潮后女性的脂肪肝患病率低于男性[27]。同样,与男性和绝经后女性相比,绝经前女性的肝纤维化并不严重,存活率更高[28]。在患有脂肪肝的绝经后女性中,雌激素缺乏的持续时间越长,纤维化的可能性就越高。在动物模型中,进一步的研究[29]表明,不同性别相关的途径导致了雄性和雌性小鼠的脂肪变性和纤维化(雄性主要是炎症,雌性主要是氧化还原状态的改变),尽管终点相似。显然,性别和绝经状态影响疾病结果,在治疗过程中需要分层,因为治疗反应可能有很大差异。
2.2 种族 基于种族人群的数据显示,脂肪肝的患病率存在种族差异;最近的一项荟萃分析显示,NAFLD的患病率和NASH风险在西班牙裔中最高,白人中居中,黑人中最低。然而,纤维化风险没有根据种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30]。NAFLD在亚洲人口中也在迅速增加[31]。以前的研究表明,与其他种族相比,亚洲人倾向于在较低的BMI下积累肝脏脂肪。与非亚洲人相比,亚洲人的病程似乎更严重,与其他种族相比,他们往往有更多的小叶炎症和更高级别的气球样变[32]。NAFLD疾病风险存在种族差异的原因尚不完全清楚。合理的解释包括遗传易感性、新陈代谢属性、文化和社会经济因素、饮食和锻炼习惯、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以及环境风险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种族之间的遗传有很大差异:在西班牙裔(49%)中最常见Patatin样磷脂酶区含蛋白3基因的风险等位基因的变异,其次是非西班牙裔白人(23%)和非裔美国人(17%),至少部分解释了这种种族差异。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脂肪肝相关基因变异的影响大小支持不同种族之间的差异,特定的遗传和环境因素(例如饮食因素)或修饰的风险变量对疾病发病机制的相对贡献在不同种族之间可能是不同的。
2.3 轻度和中度饮酒 自首次描述轻度和中度饮酒以来,酒精的摄入量被认为是NAFLD有别于酒精相关性肝病的重要标志,酒精摄入量阶段值为,男性每天的酒精摄入量为30 g,女性为每天20 g。截断值背后的假设是,低于这些阈值的酒精摄入不会导致肝脏脂肪变性,也不会对肝病的进展和预后产生有害影响。目前规定的酒精摄入限制量尚存在争议。一些报告[33]表明,适度饮酒,即使在对以前的大量饮酒进行调整后,也与血管并发症的减少相关。其他研究表明,适度饮酒(女性每天2杯,男性每天3杯)与降低NASH和晚期纤维化的患病率有关。与此相反的,一些研究[34]强调,对于脂肪肝患者,即使是低酒精摄入量,不仅与疾病进展的风险增加有关,而且与晚期肝病和癌症的发生有关,与脂肪变性和NASH 的改善率降低有关。饮酒对肝病演变的影响可能具有剂量-反应关系。
2.4 膳食摄入量、肠道微生物区系和胆汁酸 膳食摄入量、肠道微生物区系和胆汁酸及其相关代谢物与脂肪肝的发病密切相关。西方饮食的特点,包括脂肪和果糖摄入量的增加,加剧了肥胖症和脂肪肝的形成。相比之下,采用地中海饮食模式的NAFLD患者肝脏脂肪会减少,心血管风险也会降低。肠道微生物的组成可以根据饮食模式的类型变化而发生改变,无论在小鼠还是人类,肠道微生物群均参与脂肪肝和脂肪性肝炎的形成。新出现的数据[35]表明,在NAFLD中,微生物组和肠道微生物组衍生的代谢物可以预测晚期纤维化和肝硬化。肠道微生物还参与调节胆汁酸及其代谢物,进而调节葡萄糖、脂肪和胆碱代谢,以及能量平衡[36]。然而,要将饮食的影响及其对肝病的相关结局与饮食诱导的微生物群改变所介导的影响区分开来,并确定在这些相同条件下的因果关系,仍具有挑战性。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提出了人类遗传变异和种族在驱动微生物群差异中的作用。
2.5 瘦者NAFLD 目前,瘦者NAFLD被定义为在没有“显著”饮酒的情况下,BMI<25 kg/m2(或亚洲人BMI<23 kg/m2)的肝脏脂肪变性。虽然首先在亚洲人群中被描述,但人们认识到5%~45%的NAFLD患者是瘦的;即使在欧洲人中,也有约20%的患者被认为是瘦的[37]。尽管与相应的肥胖受试者相比,那些瘦者NAFLD有更好的代谢和组织学特征,但他们的自然病史定义不明确,一些数据表明他们的结果可能更差,加速了疾病的进展[38],而另一些数据则表明没有差异,甚至有更好的结果[39]。最近的数据表明,瘦者NAFLD包含一个与肥胖受试者截然不同的病理生理状态,这不仅仅是BMI的简单差异。在这项研究中,与肥胖患者和瘦健康对照者相比,瘦患者有不同的代谢和肠道微生物区系特征。具体地说,他们有完整的代谢适应能力,通过增加胆汁酸和法尼醇X受体活性来应对肥胖环境,这可能有助于他们保持抵抗肥胖的表型。此外,在遗传因素方面,Fracanzani等[40]的研究表明,TM6SF2风险等位基因在瘦者NAFLD中的比例明显高于肥胖或超重患者。TM6SF2风险等位基因与瘦者NAFLD密切相关[41]。
2.6 家族性风险 来自双胞胎队列的家族性风险数据显示,肝脏脂肪和纤维化都是可遗传的特征[42]。此外,回顾性的以家庭为基础的研究[43]表明NAFLD和肝硬化存在家族聚集性,最近一项包括NAFLD肝硬化及其一级亲属的前瞻性研究[44]一致地表明,肝硬化患者一级亲属发生进展性纤维化的风险为18%,远高于一般人群中肝纤维化的风险。
2.7 表观遗传因素 表观遗传的失调与几种疾病有关,包括NAFLD。大量的microRNAs(miRNAs)与NAFLD相关。最近的一项荟萃分析[43]表明,特别是miRNA-122、miRNA-34a和miRNA-192可能是脂肪肝疾病的生物标志物。与健康对照组相比,NAFLD组miRNA-122和miRNA-192表达上调,miRNA-34a在NAFLD组也表达上调,且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45]。关于长链非编码RNA(lncRNAs)和其他类型的非编码RNA在NAFLD中作用的数据有限。一些数据表明NASH中的lncRNAs发生了改变,包括肝特异性Lnc18q22.2[46],富含棕色脂肪的lncRNA1(Blnc1)[47]和转移相关肺腺癌转录本1(MALAT1)[48]。在较大的队列中,lncRNAs在脂肪性肝炎中的作用仍有待进一步阐明。一些研究[49]表明,在NAFLD患者中,肝脏和外周血源性DNA的甲基化特征发生了广泛的变化,包括关键代谢途径、炎症途径和纤维化途径的调节位点。也有证据表明,DNA甲基化可以作为NAFLD纤维化分层的生物标志物。
此外,各个疾病阶段的定义不是十分明确、肥胖与代谢健康等也是NAFLD异质性的来源[50]。
3 NAFLD异质性的启发
NAFLD的异质性表明,不能将它们作为一种单一的疾病来考虑或管理,并采用“一刀切”的方法进行治疗。缺乏对异质性影响的考虑,将削弱准确定义脂肪肝表型的自然病史以及对临床实验的合理设计。此外,虽然在临床实践中将NAFLD患者分为NASH患者和非NASH患者,但这是否合适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正如大家所知,MAFLD在一生中具有巨大的可塑性,并且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纤维化是不良结果的主要决定因素,而非NASH。基于上述考虑,将NAFLD更名为MAFLD,是消除疾病异质性的漫长道路上的第一步。
此外,不断优化的NAFLD诊断方法,也是降低其异质性的一种有效策略。例如,MRI-质子密度脂肪分数(PDFF)对单纯脂肪变性有非常准确的诊断价值,但对脂肪性肝炎以及肝纤维化的诊断似乎有所欠缺。在临床检测过程中,MRI-PDFF诊断中度或重度脂肪变性患者大多有不同程度的转氨酶升高过程,提示这些患者可能已经有不同程度的肝脏炎症。未来MRI-PDFF联合肝穿刺活检或许是诊断脂肪性肝病确切疾病程度的有效手段[51]。
4 结论
过时的NAFLD命名、诊断标准、缺乏对风险分布和治疗反应异质性的充分考虑是阻碍有效治疗进展的障碍。MAFLD准确地反映了目前与代谢功能障碍相关的脂肪肝疾病的知识,应该可以取代NAFLD/NASH。未来应该进一步确定疾病及其驱动因素的特征和亚型,以此作为设计更合适的临床试验和患者管理的必要前提,并考虑最新的命名法对临床实践和公共卫生政策的影响。
作者贡献声明:林思岑负责文献翻译以及论文书写,冯巩负责论文修改以及文献资料收集,刘军林、严琴琴以及弥曼负责拟定写作思路,指导撰写文章并最后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