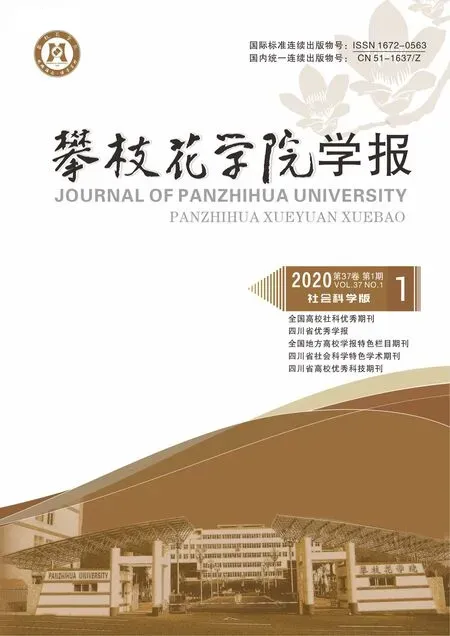青年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出场逻辑研究
闫兴昌
(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1)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曾言,信息化时代谁控制了网络,谁就拥有整个世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互联网发展置于战略全局的高度。2014年11月19日,习近平在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词中提出“网络命运共同体”概念。2015年12月16日,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开幕式中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设想,并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四项原则”和“五点主张”。随后又多次在国内外不同重要场合倡导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就是在思想上把整个网络空间作为一个整体,以国家或者其他集合体为代表的、为整个网络空间谋求发展的、或至少应该限制有碍于整个网络空间利益的人类活动。当前处于信息化时代的青年群体是网络这个“第五疆域”里最具活力的群体,他们不仅是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也是部分西方国家极力拉拢的潜在对象,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故而,对“Z世代”群体进行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与“合格公民”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是实现网络强国战略和互联网有效治理的必然要求,还是人类能动性实践的历史选择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何以必要:青年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出场的内外生成逻辑
(一)青年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出场的外生逻辑
全球化浪潮助推青年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出场。“一切划时代思想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思想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544“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出场绝非偶然或空穴来风,而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谈到,较之于社会那种机械的聚合和人为的产物,共同体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有机体。”[2]154它既是一种自然联合体又是一种思想联合体。根据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自然的产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方面,当前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出于共同利益而形成的“志愿者联盟”不断涌现,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全球化日益催生网络化,网络化也日渐加速全球化,二者相生相克、相得益彰。作为“第五疆域”的网络空间自然也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便是全球化与网络化生存现实的彰显。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鸡犬之声相闻”的地球村的同时也会引致网络空间的“互嵌”式风险。“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3]35资本全球化日臻成熟。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根本后果之一是全球化。”与陆权和海权时代那种“帝国”野心笼罩下的旧经济全球化相比,现代的新经济全球化虽然从“主——客”的国家交往范式转变成了“主体际”的国家交往模式,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人’又一次不存在了,”[4]152-153逐步被个体性所掩盖。零和博弈、冷战思维、“相互奴役”的逆全球化思潮不断冲击着人类的“第五空间”共同体,“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5]日益加剧着国际社会的原子化倾向,形成一种“反向合力”。但是网络空间的脆弱性使得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独立御敌”,网络恐怖主义、网络极端主义、网络治理等全球性危机以其普遍性和整体性特征映射出“类大国”在这一领域的共同利益。因此,在风险“互嵌”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是治愈网络空间原子化症状、进行网络空间治理、催化“正向合力”的必然选择。
(二)青年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出场的内生逻辑
时代化风暴催化青年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萌生。“凡益之道,与时偕行”。首先,从网络本身的特性来看,网络空间的内在张力始终是客观存在的。作为从人化自然中分离出来的“第五疆域”,网络这一人工自然物使人类同时面对传统的自然物理与虚拟的网络双重空间,就像尼葛洛庞帝所言那样,在这个穿着“马甲”的匿名性空间里,“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台。”[6]一方面,信息“共产主义化”与“数字剥削”共生共存。信息“营养过剩”带来的是信息“共产主义”式的假象,“数字剥削”的存在使得网络这一劳动工具新变式成为了一种异己的而非联合的力量。另一方面,网络自由与网络秩序相生相克。“自由是秩序的目的,秩序是自由的保障。”[7]534习近平指出:“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但运用网络空间的主体是现实的。”[7]534在网络这个“无主之地”里,“Z世代”群体的行为应该表现为自由与秩序的统一。正是由于网络这一“公共领域”里存在着信息“共产主义化”与“数字剥削”、网络自由与网络规范的内在张力,才激发了“Z世代”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加速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出场,正如马克思所言,“就单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8]306其次,从社会变迁来看,社会的基本“细胞”——单位共同体日渐式微。自滕尼斯提出“共同体”概念以降,“共同体”概念被不断嵌入到各种具体语境中,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就是“共同体”概念在网络化时代的具体延伸和时代表述。互联网魆风骤雨般的发展,加速了“Z世代”群体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过程,“机械团结”为主导的社会中那种充满温情和“集体良知”的共同组织日趋瓦解,而代之以“纯粹个人”为主体的“有机团结”社会正悄然而至。与“机械团结”那种单位共同体相比,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虽然是一种更为高级的人的现实的类存在方式,但由于原子化式的“社会人”日益增多,青年群体依旧缺乏那种“本体安全感”,尤其在畸形的“群体抱团”下,更容易引发青年“自我中心主义”的崛起和自由意识下的“共意”消解,加剧网络空间中个人本位与集体本位、道德自由与伦理认同的矛盾。因此,在国内的时代化风暴下,青年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呼之欲出。
二、何以为继:青年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出场的理论逻辑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青年“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出场的理论根源
启蒙运动以前,西方先圣大哲未曾明确提出“共同体”概念,但却有过“世界城邦”、“上帝之城”等思考人类命运的概念。随着启蒙运动时期人文主义的兴起,托马斯·莫尔为此幻想过“乌托邦”、康帕内拉擘画了“太阳城”,其间不仅有康德从纯粹理性高度设计的世界大同主义理想,还诞生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当前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不仅吸纳了西方哲学的精髓要义,最重要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首先,“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根植于马克思的类哲学。西方很早就出现了类意识的萌芽,但类意识在中世纪被过度神秘化了,基督教将人的类本质抽象化为“上帝”,使得人迷失在这种颠倒的类关系中,虽然费尔巴哈对这种扭曲的宗教神学发起了猛烈的批判,但未能跳出“种”的差别规定,实质是将人的本质抽象化了。与费尔巴哈所理解的“类”不同,马克思则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从实践的角度去理解“类”,他认为“人是类的存在物,”[9]47“类本性”是一种人所特有的、内在的生命本性,并根据人发展的三个阶段提出了相应的“自然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不仅是人的类本质的理论逻辑路径,更是人类社会形态更替演进的理论逻辑路径。概而论之,“类化的存在”是人类所追寻的目标,其价值旨归不仅仅是寻类本性之真、求类利益之善,更在于造类文明之美。当前增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便是新时代条件下推进人类真正实现类本质所必经的历史阶段。其次,“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是对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的时代化映射。马克思曾说:“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个人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9]82人只有在交往实践中才能彰显出人自身的本质属性,人可以在交往中满足自我的生存需求,在交往中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在交往中丰富“完善自我”。离开交往的生产是不现实的,离开交往的人类也是不具体的,归根结底,交往的本质就是人们的生活样态与生存方式。当前,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巴别塔”不仅使天各一方的人们不再“老死不相往来”,还使得“天涯若比邻”成为了客观现实。这一理念不仅丰富了“人的本质就是社会联系”的具体内涵,更是对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的时代化阐述。
(二)中国传统“和”文化是青年“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出场的文化根源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当前青年“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出场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追本溯源,“和合”文化始终是贯穿中华古今文化的一条主线。这主要体现在:第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其认为天人关系应该是一种天人合德、天人相应的本真状态。天即宇宙是人伦道德之源泉,“天地之大德曰生”,其不与天人之分同向而行。儒家通过效法天地之道,将其内化为人德,董仲舒更是提出了天意与人事交感相应之说。天不仅是仁义礼智的本性,亦是可敬可畏的大自然,“天人合一”便是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对于网络这一人工自然物,人类自然也要顺天而动,在尊重、顺应“天意”的前提下实现与网络的和谐共生。第二,“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其旨在通过“保合太和”以求“万国咸宁”、“天下和平”。在“诸侯万国”、“天下万邦”的中华大地上,自古便有“民胞物与”,“仇必和而解”的“和合”理念。而当前有着深厚技术沉淀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在网络空间里较高的话语权却肆意践踏他国网络主权,大肆发表网络“无主之地”的言论,将其技术优势转变为霸权优势,甚至形成网络空间里的“马太效应”。面对全球化进程中的网络主权、网络恐怖主义、网络分裂主义等问题,唯有增强“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方能趋利避害,实现“天下大同”。第三,“和而不同”的社会观。“和”意为多样性,“同”意为单一性,“和而不同”便是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形成相对的统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便是在当前无边界、无国界、差异并存的虚拟场域中寻求“最大公约数”的时代化诠释。第四,“平正擅匈”的道德观。“和合”文化同样包含“人心向善”、共生共存、共立共达的道德观。《墨子·兼爱》提到“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然而网络化个人主义崛起却引发了青年“集体意识”的式微,无序自由意识导致了青年“集体良知”的弱化,社会日益呈现出原子化倾向,因而增强青年“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就显得兹事体大。第五,“义以为上”的价值观。《论语·阳货》曰,“君子义以为上”,墨子认为,“义,利也”。儒家主张动机之上不能以义求利,但结果上可以因义得利。网络虽然是现实空间的虚拟化延伸,但网络的主体依旧是现实的人,这种虚拟化活动所造成的后果同样是现实的,故而,对于网络诈骗、网络侵权、网络失信而言,“义以为上”、“取利有道”的价值观同样适用于网络化生存。因此,当前青年“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出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三、何以作为:青年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出场的实践逻辑
(一)以德润身:自觉内化“共同体”意识,重建“Z世代”“信念伦理”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一方面,“Z世代”群体要自觉将“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升华于情。哈拉尔认为:“世界不是由分离的单位构成的,而是一个由相互联系在一起、彼此从对方获得生命的社会系统组成的无缝网络。”[10]314当前从人化自然中分离出来的“第五空间”,在将“自我”与“他人”不可孤立的联结起来的同时,由于其不可察觉的时空位置与不可触摸性,也产生了网络化生存中个人主义与共同体、道德自由与伦理认同的矛盾。“出现了各种强有力的抗拒性认同,它们龟缩在公共天堂里,”通过“选择在抗拒的过程中建立自己的独立性,”[11]412-413处处以“我”为标准,将“他人”与“自我”处在一种对象性的张力之中,这种长期将“他人”看做是对象性工具,“他人”仅具有工具性价值的行为,只会招致“共同体”的分裂与瓦解,追根溯源,问题的关键不外乎是网络主体在思想与认识上出现了信任危机,因而,青年的网络化生存与发展亟需一种“共同体”的利益与责任意识来维系。另一方面,“Z世代”群体需重塑“信念伦理”,以实现“自我统一性”。第一,提升其道德自律能力,以笃定“自我统一性”。《礼记·中庸》开篇即言:“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当前以“马甲”等虚拟符号拼凑而成的“第五疆域”使得传统社会那种“他律”在面具化与匿名化的网络主体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唯有“慎独”才是重建网络道德体系的治本之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同样适用于网络化生存的主体即“Z世代”群体。第二,培育其道德情感,以夯实“自我统一性”。道德教育的最终旨归在于青年群体的情感教育,而情感教育的终极目的必定以青年群体的幸福为指向,因而,道德情感的升华亟需德福一致幸福观来加以引导。道德与幸福本是相伴相生的辩证关系,道德是前提,幸福便是结果,然而一些“无主之地”的生成与延伸却加速了德福分离,使其呈现出德福相悖的态势,重塑德福一体、德福合一不仅是实现“自我统一性”的关键,更是培育青年“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
(二)以文化人:加强青年“世界意识”教育,充分发挥高校“头雁效应”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罗兰·罗伯森曾指出,世界意识是一种既指世界的压缩,又指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这种概念的全球化就是将“天—地—人”看作一个整体系统,具体表现为国家平等的意识、全球利益的意识、世界整体的意识、交流合作的意识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9]276在“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各个民族和单位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被裹挟进全球化的洪流中,全球化带来的不只是商品、机器等有形的东西,还有信仰、价值观等无形的东西,世界意识就是这种全球化发展下的产物。近代中国的世界意识最早发轫于魏源的“师夷长技制夷”,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历史也证明了欲通过“灭夷”、“排夷”与“制夷”等器物层面的效仿是根本行不通的,“心病”的调治才是救亡图存之根本。当前兵器制衡、制度扼杀那种“裸露的血肉”式竞争虽已消逝,但代之而起的却是更隐蔽的文化、意识形态等隐形较量。“奶头乐”陷阱、“意识形态终结论”、“修昔底德陷阱”、“网络自由”等西方“耦合思潮”频频泛起,尤其在社会原子化的加速下,处于“第二人生”中的青年群体趋于从各种共同体中剥离出来,而成为独立的个体存在物,亟需一种涂尔干式的“集体良知”扭转颓势。鉴于此,高校凭借着先天性的“主渠道”优势,自然要充分发挥其“头雁效应”,但也要“分寸感”拿捏适度。首先,高校在为世界意识教育提供新机遇的同时,要避免沦为“西化”与“分化”教育的场域。其次,高校在增强青年多元文化理解力的同时,要避免切断中国“和合”文化的承接。最后,高校在进行世界意识话语建构的同时,要避免世界意识教育中的人本缺失。唯有这种横向与纵向思维的整合、隐性与显性教育的配合、共性与个性文化的“和合”,才能使得青年对世界意识从认知转向认同,进而上升为网络虚拟空间里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擘画出“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世界”。
(三)以规束人:构建知行合一的德礼机制,夯实虚拟场域中的“共同体”意识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反复谈到了“自我节制”精神。“因为一个懂得自我节制的人心目中必定拥有某种生活准则,无论何时何地,他说话办事都按这一‘尺度’。”[12]162在网络空间的“无主之地”中,这个“尺度”具体就表现为“德”——网络空间的道德“尺度”与“礼”——网络空间的规范“尺度”。一方面,构建“从直从心”的道德共同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德”即“惪”,释为“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从直从心。”原子化社会的到来与“第五疆域”的开辟使得人类尤其是“Z世代”群体在度越时空界限、发现“新大陆”之际亦生成了网络空间中贪、嗔、痴、慢、疑等不良心理,亟需“直心”即和善之心、正直之心、公平之心、公正之心、敬爱之心来裨补缺漏。这种兼具“内圣”与“外王”功夫的“德”自然是网络空间主体所必备之素养。另一方面,构建“天下有道”的网络空间秩序。“不学礼,无以立”,秩序就是“礼”的具体体现。“秩,常也;秩序,常度也。”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中提到“礼治秩序”、“差序格局”之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作为现实世界的虚拟化延伸,网络“先天”的虚拟性、开放性尤其是青年网民的匿名性与功利性,加速了网络空间里“把关人”角色的缺失及网络秩序的失控。尤其在资本逻辑及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网络空间这个和合共生之体更易于被宰割与肢解,进而异化为积聚内生破坏力的新工具。网络并非“法外之地”,“天下有道”也并非一种臆测度谋,而是能致的大同境界,唯有构建“天下有道”的网络秩序,明镜照形,古事知今,其命维新,才能使网络空间从昔日的“天下和合”转向未来的“和合天下”,唤醒青年群体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概而论之,网络空间中的“礼”与“德”是圆融的,“礼”作为行为规范,是把“德”作为其内涵的指导原则和标准尺度,无“德”的“礼”是虚礼,无“礼”的“德”是虚德。当前,全球正在成为一个太极图式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共同体结构,无论是虚拟化的理想之境,还是信仰化的现实之域,都需要“德”与“礼”的刚柔并济。
四、何以为用:青年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出场的价值逻辑
(一)重构:助推“Z世代”群体网络伦理精神的构建
罗素曾言:“人类种族的绵亘,取决于人类能够学到的为伦理思考所支配的程度。”[13]159不论是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本身,还是它出场的理论逻辑和价值逻辑,都强烈地把青年导向了网络伦理的话语体系并加速了“Z世代”三大群体性意识的出场。第一,网络共生意识。网络共生是一种网络中独立性、主体性与合群性、共生性的对立统一关系,主要包括网络中人与“自我”的和谐共生、人与“他者”的和谐共生以及人与虚拟世界的和谐共生。社会原子化视域下,网络霸道主义者的霸权横行、“数字鸿沟”、网络主权、国家治理等给网络主体的能群能动性及合群共生性提出了挑战,然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出场不仅体现了信息智能革命时代的人“之所以为人”,还提出了区别于动物的特有生存方式,即以“共在”、“共生”方式存续的人的类本质。第二,网络共享意识。习近平指出,我们开发互联网,其目的是让全人类共享互联网的发展成果。然而虚拟世界“先天”的可分享性优势却在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道德自由与伦理认同的张力中挣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出场正是为了寻求网络世界的利益支点,其不仅是权利与利益的共享,亦是风险与义务的共担,是一种真正的“共命运”感的存在,最终旨在度越那种“形骸而分尔我”的界限。第三,网络和合意识。“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上下之益,在能相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是对当前互联网问题的时代性回应,是在人类多样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样态中寻求一种“普世伦理”即和实生物、民胞物与的共同体思想的时代性尝试。这种和生、和处、和立、和达而非孤生、孤处、孤立、孤达的共同体意识在多元文化并存的虚拟场域里以一种符码语言的方式重新诠释了“和合天下”的时代性意义。这种类存在意识不是乌托邦式的想象,而是将“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的观念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升华于情。
(二)优化:加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与发展
习近平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要“推动网络空间实现平等尊重、创新发展、开放共享、安全有序的目标。”[14]这不仅为打造互联网“清朗空间”、开展网络治理等突出问题提供了指导性原则与思想性引领,也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化升级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和新要求。第一,平等尊重原则力促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转变。马克思、恩格斯说:“平等是人在实践领域中对自身的意识,也就是人意识到别人是和自己平等的人。”[15]264这促使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从主体性——主体对象化与自我中心化倾向转向主体间性——试图以平等参与方式实现主体间的视阈融合最后到他者性——借“他者”审视“自我”,以保证主客交往中“他者”的他性范式的转变。第二,创新发展原则助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建构。“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作为劳动工具新变式的网络,在给“Z世代”“肉身隐退”无视时空界限的同时,也给传统“被投放”式教育提出了挑战,亟需用创新发展原则指导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时代化建构。第三,开放共享原则加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优化。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由于时空的局限面对当前天地一体、万物互联、人机交互的网络化时代显得苍白无力。在网络“共在”、“共立”、“共达”的“共享”原则下,网络新媒介的分权与赋权对于优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载体、文化载体、管理载体功效显著。第四,安全有序原则推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净化。网络是全球化发展的催化剂亦是风险社会的加速器,当前全球网络空间呈现中心——外围的分布格局,发展中国家处于网络的“低端锁定状态”,在西方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理论的浸染下,网络空间的“金德尔伯格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黑天鹅事件”等时有发生,给我国主流舆论生态蒙上了一层暗纱,这不得不迫使高校环境、同辈群体环境、大众媒介等环境的优化被提前摆上日程。
(三)度越:扭转网络虚拟空间的社会原子化倾向
网络社会原子化是社会原子化在网络空间的逻辑延伸,是一种虚拟世界里的群内“抱团化”、群外“碎片化”的社会危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作为“集体良知”在网络空间的时代化表述自然有助于扭转网络虚拟空间的社会原子化倾向,具体表现为:第一,改善网络空间个体本位强化、集体本位弱化的情况。一方面,有效遏制“粗陋的利己主义者”与“唯我主义”者于网络空间中余烬复燃,缓解“Z世代”群体“集体良知”弱化、人际关系疏离化。另一方面,有助于填补原子化个体与网络世界之间的“真空”地带,防止因“社会资本”流失而带来的情感纽带松弛化与群体交往隔绝化。第二,缓解网络空间道德规范解组、“群体抱团”异化的状况。首先,在“去单位化”的网络话语背景下,网络空间的这种类存在意识,自然有助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平稳过渡,减少“双重道德人格”现象,防止“道德密度”的稀释化与网络社会的碎片化。其次,畸形抱团是原子化社会中相对于群外“碎片化”的另一种极端现象。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在组织群外松散“电子”的同时必然牵带着对群内“原子核”的优化即克服“群体抱团”的裂变化与“独立王国化”。第三,扭转网络空间“中介权威”消泯、无序互动加剧的境况。网络社会的原子化倾向在于恶性组织或联结机制乘中间组织乏力空场之机肆意填补这一“真空”地缘所致。网络空间的共同体意识正是为了填补网络空间的这一“中介性领域”、树立“中介权威”、减轻网络社会的无序互动。概而论之,网络原子化社会中不论是群内与群外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还是个人与“自我”的关系都可以借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进行修复与维系。
总之,青年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是全球化浪潮与时代化风暴下的产物,这种网络空间的类存在意识不仅是马克思类哲学和交往实践理论的时代化映射,还是中华优秀传统“和合”文化的时代化表述,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网络空间的逻辑延伸和精细化阐释,因而,青年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出场必将有利于网络化时代青年“合格公民”教育的进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结构的良性变革以及网络强国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