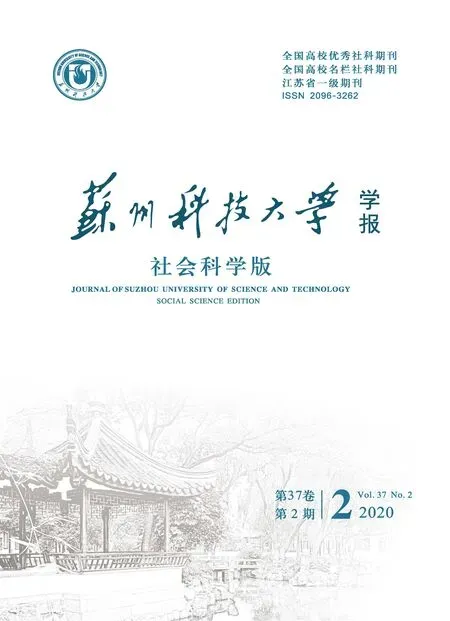论英国政府与第三次康藏冲突的爆发*
朱昭华
(苏州科技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民国时期,西康(1)“康”这个藏语名称是唐代以后才出现的,据藏文史书记载,“康”并无固定疆域,习惯上是指西藏丹达山以东一带地区。这一地区从清初起就划入四川省建制,清廷仍利用原有的土司和寺院集团进行统治。1906年清政府设立川滇边务大臣,统辖四川打箭炉厅(今康定)及所属各土司地区的政务,并拟建置西康省,未成。民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将该地区划为川边特别区,受四川省节制。参见格勒《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地区之间先后发生过三次规模较大的康藏纠纷。相比于前两次康藏纠纷的研究,1930—1940年第三次康藏纠纷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学界主要就第三次康藏纠纷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藏地方政府,以及康、青(海)地方军阀在这次纠纷中的态度与对策、康藏纠纷的善后及其影响等问题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2)代表性论著参见杜丽娴《试析1930—1940年中央与西藏地方之关系——以第三次康藏纠纷为例》,中央民族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郎维伟《国民政府在第三次康藏纠纷中的治藏之策》,《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第81~89页;刘国武《南京政府对康藏纠纷的定性及解决措施分析》,《史学集刊》2004年第2期第33~39页;王燕《浅析第三次康藏纠纷》,《民国档案》2003年第2期第105~108页;王川《近代康藏史上的“大白事件”及其解决》,《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20~26页;林孝庭《战争、权力与边疆政治:对1930年代青、康、藏战事之探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4年第45期第105~141页;周伟洲《1930—1933年西藏与康、青战争之研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1~10页;王海兵《康藏地区的纷争与角逐1912—1939》第五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等等。其中,关于英政府在这次康藏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研究成果不多且存在争议。长期以来,康藏冲突都被视为英帝国主义分裂西藏的一个明显例证。对于第三次康藏冲突,有学者认为,1930年英国驻锡金政务官威尔入藏“访问”的一个结果,即为达赖命令藏军向康区进攻,以此为条件换取英国命令尼泊尔停止侵藏战争,其目的是破坏日益发展的汉藏关系。当时达赖迫于英人淫威,不得不接受英帝国主义的条件。[1]1930年威尔入藏与第三次康藏冲突的爆发具有深刻关系,是英印政府制造康藏冲突的重大举措。十三世达赖因其利诱,在大白事件发生后,“即插手此事,援助大金,打击白利,并与西康驻甘部队直接冲突,扩大为康藏之战”[2]。但也有学者不认同这一观点,认为英印政府对十三世达赖于1931—1932年在青康边界发动战事,感到十分不悦。(3)林孝庭《战争、权力与边疆政治:对1930年代青、康、藏战事之探讨》一文虽表达了此观点,但全文主要围绕战争探讨中国西南边疆地方政权与国民中央政府之间的互动与因应,未能对英国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展开分析。当时奉国民政府之命,作为中央特派专员赴康调解康藏纠纷的唐柯三在其日记中指出:
综观此次事变,始误于甘孜县长之畏葸贪庸,不善处理,继误于康军之轻敌偾事,铸成大错。至外间所传有英帝国主义者之背景,并有英人在前线指挥供给械弹等事,皆驻军故意张大其词,以自掩其失败之咎。或未明康军真象者,见藏军之侵略康地,似有预定计划,遂认为关系国际问题。其实皆非也。[3]494-495
因此,如何看待英政府在第三次康藏冲突中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通过该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20世纪30年代英国政府的对藏政策及中英藏三方的微妙关系。
一、“大白事件”:康藏军事冲突的导火线
1913年西姆拉会议流产后,因川藏之间未划定一条明确的边界,川军与西藏地方时常因一些细故发生冲突。1917年至1918年,双方就曾爆发过一次严重的军事冲突(一般称之为“第二次康藏纠纷”)。藏军乘胜东进,不仅赶走了金沙江以西的全部川军,而且渡过金沙江,进一步占领了金沙江以东的德格、邓科、石渠、白玉等县,一直前进到甘孜附近,囊括了当时英政府所主张的“内藏”大部分土地,而这些地区自西姆拉会议以来都由川军占据着。1918年,川军与藏方达成协议,划定临时停战线。此后,川藏边境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平静,直至1930年第三次康藏纠纷大规模爆发。此次康藏冲突的直接导火线是,西康甘孜县大金寺与白利土司因争夺庙产而发生纠纷。
大金寺与白利村均位于川军控制的甘孜县境内。大金寺建于明末清初,距离1918年川藏停火线上的绒坝岔仅10里,控制着西康对藏贸易的北路,有喇嘛2000余人,以僧侣众多、实力雄厚闻名,是康区最有势力的黄教寺院。
此寺骄横万分,时与官府为难,论其人不及甘孜寺之多,论其势不及甘孜寺之大,而敢公然为恶者,有两因在:一此寺地接藏番,一旦有事,可引为奥援。二此寺生意最大,西康各寺,当以此寺为最富,用其所窖黄金,可供全寺驻军十年薪饷之用。彼自以为有钱有势,一切都不怕也。[4]
由于大金寺曾在民初驱逐川军的行动和第二次康藏冲突中积极援藏,并立下汗马功劳,因此大金寺与西藏当局的关系十分密切。
白利土司所属白利村在大金寺以东30里。白利村有白利寺、果能寺、亚拉寺3座寺院,均为土司家寺。当时,亚拉寺活佛都图转世于属大金寺管辖的林葱乡,与大金寺关系紧密。亚拉寺因曾有恩于白利土司,故分得15户差民,立有字据。1927年白利老土司去世,其女继任土司,与亚拉寺活佛多次发生冲突。亚拉寺活佛遂带15户差民投靠大金寺,白利不服,向甘孜县政府投诉。大金寺以契约为凭,拒不交还差民。1930年6月18日,大金寺纠集200余人,武装占领白利,大肆焚烧抢掠。当时西康特区由四川省主席刘文辉以川康边防总指挥名义兼辖,刘文辉遂令川康边防军旅长马啸派人前往甘孜调解。但大金寺拒绝服从,马啸又派兵前往镇压。1930年8月,大金寺僧侣开枪击毙边防军排长李哲生,挑起战端,驻甘康军大举反攻。经过两个月激战,康军克复白利村,包围大金寺。大金寺遂向西藏求援,十三世达赖一面令藏军向东推进,一面电请中央制止康军进攻大金寺。10月下旬,在蒙藏委员会的一再敦促下,康军撤兵。与此同时,藏军却暗中增兵,相继进攻甘孜、瞻化、理化等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西藏当局在康藏问题上的态度更为强硬,于1932年2月开始向康区大举进攻,康藏纠纷愈益扩大。[5]“大白事件”演变成川藏战争。
“大白事件”发生时,中英藏三方的关系已有微妙变化。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基本沿袭了北京政府的对藏政策,一方面严正立场,以国家立法的形式明确西藏的主权归属,设立管理西藏地方的中央机构——蒙藏委员会。另一方面采取行动,主动与达赖喇嘛接触沟通。1929年至1930年,国民政府先后派出雍和宫总堪布贡觉仲尼、国民政府行政院藏族官员刘曼卿以及蒙藏委员会委员谢国梁等访问拉萨,宣传中央对藏政策,疏通双方关系。此时,西藏当局迫于经济重负,也希望通过与国民政府高层的联系,向西南军阀势力施加影响力,划定川藏边界,缓解军事压力。因此,对于国民政府所采取的接触行动,西藏当局做出了积极回应。按照美国学者梅·戈尔斯坦的分析,国民政府的主动疏通导致了两大重要进展:
第一,西藏人不再要求英国人插手西藏与国民政府间的协商谈判,在西藏和国民政府间作出任何一项最后决议时不再需要英国人充当保证人。这一条是西姆拉会议协商失败之后达成和解的最大障碍。第二,达赖喇嘛恢复了同国民政府的正式关系,……并在南京、北平和打箭炉(西康的康定)建立了办事处。[6]
与此同时,1926—1930年,拉萨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对英国非常冷淡。[7]
如果说“大白事件”是川边、西藏地方由于教俗产权之争而发生的一次冲突,那么在上述汉藏频繁交流互动、藏英关系出现嫌隙的背景下,十三世达赖何以会违背既有的停战协议,越过停火线,出兵援助大金寺,使康藏边境再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
二、1918年康藏停战协议埋下的划界隐患
如上所述,大白纠纷是此次康藏冲突的直接导火线,然而,康藏冲突发生的根本原因仍是西姆拉会议遗留下来的康藏划界问题。1918年第二次康藏冲突发生后,英国政府为巩固藏军东进的胜利果实,曾指示其驻华使馆副领事台克满出面“调停”。台克满于1918年8月抵达昌都,先后与藏军统帅噶伦喇嘛、川边军驻巴塘分统刘赞廷进行会商,达成停战和约十三条,对“汉藏暂时交界地方”做出规定:
巴安、盐井、义敦、得荣、理化、甘孜、瞻化、炉霍、道孚、雅江、康定、丹巴、泸定、九龙、定乡、稻城等十六县,与该处施(迤)东之地方,归汉官管辖,藏军文武不得驻扎该处之境内。查类乌齐、恩达、昌都、察雅、宁静、贡觉、武城、同普、邓科、石渠、德格、白玉等县,与该处迤西之地方,归藏官管辖,汉军文武官员不得驻扎该处境内。……至云南、青海,仍以旧界,现在不改。[8]2441-2442
刘赞廷签订此约时,川藏两军还在绒坝岔激战。川边镇守使陈遐龄以此约为刘赞廷个人私定为由,宣布无效,打算战胜藏军后再图议和。然而,川军迟迟未能战退藏军,陈遐龄只好派代表与台克满及西藏代表谈判,于1918年10月签订绒坝岔“停战协定”。协议要点是汉军退驻甘孜,藏军退德格境内,“自退兵之日起,南北两路,汉藏各军不得前进一步,停战一年,听候大总统与达赖喇嘛允否昌都交涉”(4)关于此停战协议文本,各种文献的记载的确存在略微差异,但原则上都是汉军退驻甘孜,藏军退驻德格,而不是如一些书中所写的“汉军退出甘孜,藏军退出德格”。绒坝岔协议的英文条文可见Parshotam Mehra, The North-Eastern Frontier: A Documentary Study of the Internecine Rivalry between India, Tibet and China: Vol 2, 1914-195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9-10。,退兵期限从中历10月17日至10月31日,即藏历9月12日至9月26日止。[9]54绒坝岔协定实际上与刘赞廷所订昌都协议相同,都是承认了藏军占领的事实。协定的结果使藏军的防线向东移动约400英里。[10]随后,川军退守甘孜、瞻化、巴安、盐井四县。
由于停战协定达成的界线和西姆拉会议上英方拟议的“外藏”边界差不多,英政府十分希望依靠外交施压,迫使北京政府重回谈判桌,就此解决汉藏划界问题。然而,北京政府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对谈判进行了拖延,(5)中英之间的详细交涉可参见拙文《“五四运动”前后的中英西藏界务问题交涉》,《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83~88页。但害怕停战期限到期后又发边患,遂决定派员入藏疏通。1919年北京政府令甘肃督军张广建派遣李仲莲、朱绣等人入藏,联络感情,磋商川藏事宜。经过五个月的活动,使团取得了很多成果,其中之一便是缓解了川藏对峙的紧张局势。1920年3月,经双方讨论,结果仍依据1918年暂行停战条件,略加修改,取消停战期限,并声明川藏两军暂以雅砻江为界,嗣后川藏两军若无大总统及达赖喇嘛之命令,不得前进,所有各事,静候中英藏三方面特派全权代表在拉萨或察木多会议解决。[9]58整个1920年代,川藏局势基本保持了平稳。
昌都停战协议除了划分汉藏交界地方,也对退守后双方应遵循的一些原则做出规定,其中第三款涉及大金寺,条款指出“甘孜、瞻对所有藏兵概行退回之后,汉兵不得操扰达吉更巴喇嘛寺等处”(6)关于昌都停战协议的具体内容,不同档案资料收录的条款叙述,稍有出入,文中所引为川边镇守使陈遐龄1919年1月7日给中央呈文的附件。参见《晚清民初西藏事务密档》,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10年版第344页。。这里的“达吉”即指大金寺。“大白事件”发生后,甘孜地方政府处理不当,调停未果,使双方兵戎相见。康军对大金的讨伐,在西藏当局看来明显违背了该条款的规定。当时,西藏驻京代表就表示康藏冲突的起因“一为白利达结(即大金)两寺宗教争执,未依喇嘛寺庙惯例办理,遂致风潮扩大”[11]。
此外,西藏当局认为康藏纠纷的升级是“有人利用边军潜助白利寺攻夺藏地”。1918年的绒坝岔协定除了认可昌都协议的汉藏划界,还规定了四款停战退兵条件,其中一条是“汉军退甘孜,兼守白利要隘,停战期间,不得过白利上前一步”[12]。这一规定使得白利成为川军队驻扎西边的最前哨,白利与大金寺之间的地区处于川军的控制范围之外。实际上,这是以间接的方式对昌都协议做了有利于藏方的修改。[13]68这一点在第三次康藏纠纷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大白事件”发生后,刘文辉认为白利、大金皆在甘孜辖境,面对冲突不断升级,决定采取军事手段,调集军队云集甘孜,反攻收复了白利失地,并包围了大金寺。然而,根据上述绒坝岔协定的停战退兵条款,川军越过白利要隘进攻大金寺,即突破了汉军防线,是对绒坝岔协议的破坏。因而,在藏方看来,本应由达赖喇嘛解决的大白纠纷演变为军事冲突,很大责任在于川军的背约进攻。
当时达赖、班禅两大系统矛盾尖锐,十三世达赖对九世班禅在中国内地的活动,尤其是其返藏努力十分敏感和疑惧。大白纠纷发生后,班禅驻康办事处的积极调停也被达赖集团过度解读,将冲突的不断升级归咎于班禅集团的“阴谋”怂恿。(7)该论点可参见王海兵《大白事件与第三次康藏纠纷的起因问题》,《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5~9页;魏少辉《边疆政治与第三次康藏战争的爆发》,《贵州省党校学报》2017年第3期第118~123页。
西藏当局在收到大金寺的求助后,先是给予大金寺武器支援,在获悉川军包围大金寺后,藏军随即接到噶厦命令,立即派兵前往,积极援助大金寺。至12月间,藏方援军陆续开至,与大金联合,大举猛攻川军,不仅将其驱逐出白利,而且占领了整个甘孜地区。大白纠纷进一步发展成为康、藏两军的战争。
三、英国驻锡金政务官的入藏与康藏冲突的爆发
从“大白事件”爆发到康藏、青藏停战协议达成期间,英国驻锡金政务官(8)1888年英国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后,锡金沦为英国的保护国,英印政府开始在锡金设立政务官(Political Officer),至英国殖民势力退出印度,锡金政务官一直在中国西藏地方的政治发展中扮演着活跃的角色。威尔曾先后于1930年8月、1932年9月两次入藏。考察英国在第三次康藏冲突中扮演的角色,不能不深入探讨威尔的两次入藏行动。
1930年威尔首次入藏是在汉藏关系得以明显恢复的背景下,以增强英藏友好关系为目的展开的。1924年以后,随着西藏亲英将领擦绒未遂政变(9)擦绒·达桑占东(?—1959),平民出身,以护卫十三世达赖出走印度,一跃而为贵族。1924年以藏军总司令身份,阴谋发动政变,未得逞。的发生,中印中段边界围绕桑、葱莎地区的边界纠纷(10)英印政府称之为Nilang-Jadhang地区,1919年后开始遭到英国入侵,经西藏地方政府多次交涉,一直未能达成协议,至英国殖民势力撤离后,印度政府继承了这一侵略遗产。,以及藏尼冲突(11)1929年西藏与尼泊尔之间围绕尼泊尔在藏的治外法权问题发生了严重冲突,西藏甚至进行了积极备战。考虑到当时的尼泊尔已为英国所控制,尼泊尔的兴兵侵藏无疑对英藏关系提出了挑战。的爆发,十三世达赖对英国的猜忌日深,英藏关系亦不断降温。根据英国驻藏代表黎吉生的描述,十三世达赖晚年对英国的政治态度发生了转变:在印度受过军事训练的藏官都被免职,另派职务;江孜的英文学校被关闭;为英国商务代办处开办的汽车邮递也在西藏政府的要求下停办了。达赖喇嘛进一步断绝和英国联系的迹象,还表现在对班禅的事务上。九世班禅有几次非正式地请求英国出面调解他与拉萨之间的关系,英国最终向达赖喇嘛提出这一建议,却遭到达赖喇嘛冷淡的拒绝。[14]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随着汉藏频繁沟通,双方开始重新讨论悬置多年的西藏地位与汉藏划界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英印政府急于派出锡金政务官,以积极姿态介入汉藏问题交涉,重新获取达赖喇嘛的信任与倚靠。
1930年4月,英印政府借助对当时藏尼冲突的成功调解,收到了十三世达赖关于派遣一名英国代表前往拉萨的邀请。印度事务部在与外交部商议后,批准了英印政府提出的派遣驻锡金政务官威尔前往拉萨的提议。随后,英印政府就威尔所应采取的对藏方针,请求印度事务部给予指示。1930年7月28日,印度事务部大臣韦奇伍德·本(Wedgwood Benn)在备忘录中指出,印度事务部认为在西藏问题上所应采取的立场是:
同西藏与中国一样,多年来我们一直急切地希望能就中藏间的关系达成最终的解决方案。我们所提出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是承认西藏为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地(an autonomous state under Chinese suzerainty)。1919年恢复的以中方提案为基础的谈判似乎让人看到了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前景,但主要由于外部因素,会谈于1921年破裂,至今没能恢复。[15]41
印度事务部和英国外交部均认为,当前努力恢复谈判不会取得任何有利的结果,主要的困难在于中国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且中央政府完全专注于内部事务。
这一观点也为印度政府所接受。印度政府指出:
如果我们有必要建议西藏政府推迟谈判,直至谈判会有一个更好的前景时,西藏人很可能会提出获得必要的物资设施援助的要求,以便在汉藏边界有争议的某些地区保持现状。如果遭到我们的拒绝,西藏将会从(对我们极为不利的)其他途径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因此,我们必须准备好突破我们所设定的限制,满足他们合理的物资,尤其是军火方面的要求。当然,这一供应是有偿的,而且是和以往一样有条件的,即西藏政府应做出书面保证,这些军火将仅用于自我防御和内部治安工作。
对于印度政府的提议,印度事务部在与外交部商议后给予了同意,但建议应同时告知西藏当局,英政府的政策依旧是:
一旦时机成熟,将使中藏之间达成友好妥协;如果达赖喇嘛提出该问题,我们的代表应明确表达这一立场,这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的代表对于供应武装给西藏以巩固其对抗中国的地位这一类提议应保持沉默,并且告知西藏当局,购买所想要的物资与维持当前汉藏边界的局势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15]41-42
可见,面对汉藏双方频繁往来互动,英国政府倍感担心。无论是印度事务部还是英印政府,都认为以《西姆拉条约》为基础解决西藏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维持当前的汉藏边界现状,直至该问题获得正式解决,符合英藏双方的利益。威尔的出访就是要使十三世达赖也能接受这一观点,避免汉藏双方在排除英国的情况下达成任何协议。
1930年8月4日,威尔抵达拉萨(10月1日离开),成为国民政府成立后英国政府访问拉萨的最高级别官员。尽管西藏当局给予周到、隆重的欢迎与接待,但双方交流冷淡。威尔抵达拉萨近3个星期后,十三世达赖才于8月22日同他就具体问题进行了交谈。针对达赖提出的是否可以与国民政府协商解决西藏划界问题,威尔极力表明恢复谈判或修订《西姆拉条约》的时机还未成熟,并让达赖放心,一旦时机到来,他完全可以依靠英国政府的友好支持。为了取得达赖信任,威尔按照英印政府的指示,在武器供应、西藏羊毛专卖权等问题上向达赖做出了允诺和让步。最终达赖接受了这一观点。[15]43
威尔入藏期间,正值“大白事件”发生、康藏纠纷逐步升级之时,而把随后康藏战争大规模爆发视为威尔入藏怂恿的结果,似有不妥。
首先,从袁世凯政府时期开始,英政府就一直希望能在康藏划界问题上与中国政府达成一致,以落实《西姆拉条约》。1917年第二次康藏战争结束后,西藏势力得以大大东扩。根据台克满调停线,西藏所占据的范围已经比1914年西姆拉会议上划给它的还多,这也是北京政府始终不愿承认台克满调停线的根本原因。因此,在判定中英藏三方谈判解决西藏问题的时机还未成熟的前提下,无论是伦敦政府还是英印政府,都认为维持康藏分界现状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
其次,如上所述,“大白事件”发生在威尔使团赴藏之前的1930年6月,由于甘孜地方官员的处理不当,危机不断升级。威尔从藏方获悉此事后首次向英印政府报告是1930年9月份。当时,印度政府和英国驻华使馆均认为,白利、大金都位于1918年台克满调停线的汉方一侧,英国可以暂时安然地忽略这一问题,到11月份才开始意识到仍需补充某种停战协议。[13]195可见,在威尔出使拉萨期间,由于英国政府认为康藏纠纷发生于台克满调停线川边一侧的甘孜境内,威尔使团的任务主要是增进英藏之间的谅解与友谊,防止西藏当局在没有英国介入的情况下与国民政府就西藏问题达成谅解。尽管随后在1931年8月康藏战争进行时,英印政府向西藏提供了一批武器(12)包括l门山炮、1350枚山炮弹、2挺机枪、500支步枪和100万发子弹。参见周伟洲《西藏通史(民国卷)》上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5页。,并被运用于后来的战争中,但这是按照英藏既有协议向西藏提供武器,是威尔使藏前英政府内部就已确立的方针,旨在有助于威尔的拉萨之行,说服达赖接受英国维持汉藏现状的观点,不能把因果关系颠倒,将它看作英政府怂恿西藏东扩的明证。
所以,不应夸大威尔使藏在康藏冲突爆发中的作用。根据1930年11月陪同国民政府专门委员谢国樑入藏的谭云山回忆:
当余在拉萨时,西康战事已发作,……至外传内中有英人指使等情,据余个人观察,恐未为事实,盖英人在藏,并无若何势力,达赖亦善于利用之。[16]
战争初期由于藏军连连得手,英印政府也乐见其成。而在1932年夏康藏战局出现转折,藏军在康、青(海)军队的联手反击下,失去了很多地方,英国政府便开始按捺不住,开始积极干预战事,威尔再次被派往拉萨。
四、威尔的二次使藏
康藏战争大规模爆发后,南京政府为缓和局势,于1931年3月25日任命蒙藏委员会委员唐柯三、专门委员刘赞廷前往西康,负责调处。唐柯三与刘赞廷于6月11日到达打箭炉,此时汉藏边界的形势已变得对藏方极为有利。5月21日藏军攻占瞻化。随后,藏军一面进占朱倭,一面在探知理化并无驻军的消息后进一步占据了该县的穹坝、霞坝。当时,蒙藏委员会只想就事论事,对大白纠纷进行调处,而西藏地方则凭借军事上的优势,要求一并解决康藏划界问题,“将大白事件与康藏界限作为一谈”。因此,唐柯三的调停最终无功而返。
在康藏问题悬而未决时,西藏地方政府又在青海玉树地区发动了新的进攻。1932年3月24日,藏军攻占大小苏尔莽地方;4月4日占领囊谦,围攻结古(即玉树)。马步芳认为结古若失,青边危急,下令驻军死守,等候援军。7月,青海军队准备就绪,进行反攻,不仅解了玉树之围,而且相继收复大小苏尔莽、囊谦。与此同时,刘文辉也趁藏军在青作战,力量分散,对藏军展开反攻,康藏战事再起。1932年4月,康军攻占甘孜;5月,攻占瞻化;6月,进占白利,围攻大金寺;7月25日,康军分三路向藏军发动总攻击,藏军失利,退驻金沙江以西,德格、邓科、石渠、白玉全为康军占据。[3]283-284康、青军队获得反攻胜利后,开始互相联络,会攻昌都。
在康、青军队反攻态势下,藏军节节败退,失去了民初以来在康区所保有的领土与军政优势。达赖迅速致电锡金政务官威尔,请其前来讨论汉藏关系及班禅喇嘛的地位问题。英印政府经过慎重考虑,虽然同意威尔使藏,但认为英国不应对西藏给予直接军事许诺,插手汉藏纠纷,这从财政和外交原因来讲都是不可能的,只能以中间人的身份提出有关汉藏划界问题的解决办法。[17](13)对于藏方在战事逆转之后提出的军事支援要求,英政府未全然同意,英印政府按照1921年的英藏协议分别于1932年7月、1933年6月两次向西藏当局出售了武器弹药,其数量之多,远远违背了所提供的军火仅用于西藏自卫和内部治安的协议精神。为缓解藏方的军事压力,英政府更愿意在外交层次上向南京政府施压,以期早日停战。1932年9月初,威尔抵达拉萨(12月初离开),不同于1930年西藏当局显露出的冷淡,威尔此行受到了各方面的热情欢迎。在与达赖和噶厦官员的谈话中,威尔表明了英印政府的上述立场,并对达赖喇嘛的军事扩张政策表达了不满,认为藏军东扩违反了1914年条约和1918年绒坝岔协议。达赖虽对大白纠纷的升级进行了解释,但也随即向前线的藏军发布命令,切勿越过金沙江与川军发生进一步的战斗。[13]205-206
在与西藏当局沟通后,威尔向英印政府表示,西藏当局对和平的希望十分迫切,但达赖与噶厦多次表达了他们不相信“中国人”的诚意,并指出如果没有英国政府作为中间人给予援助,西藏不可能与国民政府达成任何协议。他们迫切希望对1914年《西姆拉条约》的界线做出修订,使国民政府能尽早批准接受这一条约,并认为耽延下去将可能导致冲突的重新爆发。[15]61-62在威尔的影响下,1932年12月6日,西藏民众大会致函印度总督威灵顿(Lord Willingdon),表示希望英方能就汉藏边界问题的解决做出如下安排:(1)汉藏双方立即签署1914年的《西姆拉条约》;(2)召开以英政府为调停人的汉藏代表会议;(3)威尔上校应作为出席会议的英国政府代表,因为他了解这一事情的全部事实。[15]561932年12月13日,达赖又向蒋介石发出由英国充当调停人进行汉藏谈判的电报。
这些行动意味着西藏当局在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立场上出现了明显倒退。国民政府成立初期所进行的汉藏沟通,已使藏人不再要求英国人插手西藏与国民政府间的协商谈判,在双方做出任何一项最后决议时也不再需要英国人充当保证人。[6]164西藏地方态度的转向,不能不说是威尔二次使藏的重大“成果”。
在重新获得西藏当局的倚赖后,为避免战事继续延长,英国政府开始向南京政府施加外交压力。1932年10月7日英国驻华代办英格拉姆(Ingram,或译为“应歌兰”)前往国民政府外交部,声称青海军队逼近昌都,与1914年北京外交部派员与英藏两方在西姆拉会议上所订立的“尊重外藏疆界之完全”的原则不相符合,现在川青军队准备会攻昌都,即包括在外藏范围以内;要求国民政府应设法劝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并提出英政府愿意调解。[8]2581国民政府以汉藏问题纯属内部事务,拒绝英国插手干涉,但为稳定西南边疆局势,蒋介石下令青海、西康不准发兵。不过,真正让康藏战事停下来的还是四川内战的再度爆发。
四川自辛亥革命之后,二十余年间几乎年年有战争。1932年冬到1933年夏,“二刘”(刘湘、刘文辉)之战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刘文辉当时名义上为四川省主席(兼任川康边防总指挥),但各军防区都是各自为政。由于利益之争,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兼任四川军务善后督办)联合二十八军邓锡侯、二十九军田颂尧反对刘文辉,双方动员兵力达30万人,四川大小军阀几乎全部卷入。为集中力量应付川局,刘文辉急于结束西康方面与藏军的战事。1932年刘文辉与西藏方面签订《岗拖停战协定》,约定双方以金沙江为界。1933年青海马步芳也与西藏签署停战协定,双方在玉树划定了一个非战区,西藏方面丧失了康北石渠、邓科与德格一带。康藏纠纷的最终解决虽然延至1940年,但汉藏边界的划分这时基本确定下来,此后主要是处理大金寺的善后问题。
五、结 语
民国史上三次大规模康藏冲突的发生都与康藏划界问题密不可分。康藏划界本属中国内部的行政区划,由于英国政府横加干涉,提出中国政府对西藏所谓的“宗主权”,制造内、外藏概念,并将“高度自治”的“外藏”界线扩大到原川边和青海南部广大藏区,从而使川藏划界问题带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也使得英国借调停之名,干涉汉藏关系的发展。1918年在英国干预之下达成的川藏停战协议,一方面将甘孜划为川军辖地,一方面又规定川军防线不能越过白利要隘,使得地处甘孜境内的大金寺理论上归川边管辖,但川军要越过白利进攻其西边的大金,又违背了彼此达成的停战协议。1930年夏,“大白事件”因甘孜地方官员处理不当,川军越过白利防线进攻大金寺,在西藏当局看来,就是对藏地的侵夺,并将影响到西藏在康区的政教权威与税收。因此,西藏出兵支援大金寺,并凭借军事上的优势,想一并解决康藏划界问题,从而使康藏边境又陷入多年的战争动荡中。
第三次康藏冲突的爆发,就英国方面来说,无论是印度事务部还是英印政府都认为以《西姆拉条约》为基础解决西藏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在中英藏三方划定汉藏边界的时机到来之前,保持1918年的调停线是最佳选择,符合英藏双方的利益。西藏当局东扩并不符合英国政府的利益,因此,第三次康藏纠纷的爆发难以说是英政府唆使的结果,不应夸大威尔使藏在康藏冲突爆发中的作用。当然,在1932年夏康藏战局出现转折,藏军处于劣势后,英国政府便开始积极干预,威尔二次入藏,利用西藏当局对英国援助的倚赖——包括军事援助和外交干涉,扭转了自1920年代后期开始不断下滑的英藏关系,使西藏当局与南京中央政府的关系出现了明显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