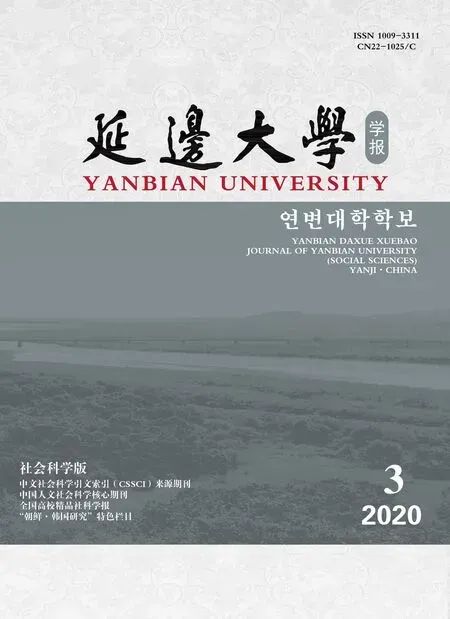民国时期吉林禁烟与地方执政
——《盛京时报》视野下的考察
舒 畅 王国栋
《盛京时报》于1906年创办,发行范围以东三省为主,兼及京津、华北各地,是日本人在华所创办历时最久的一份中文日报。其存续38年期间,对于吉林地区有较大篇幅的报道。这些记录20世纪前半叶吉林地区的文字,是研究吉林地区的珍贵史料。这些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对于近代吉林及东北地区的近现代史、中日关系史、区域史和边疆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鸦片泛滥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其影响的复杂性、广泛性和长期性,在历史研究的意义上,早已超出社会问题的范畴。近代吉林地区禁烟问题涉及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本文拟通过《盛京时报》刊载的相关事件,以民初至“九一八”事变之前吉林地区的禁烟问题为研究对象,分析民国时期吉林禁烟基本情况与地方执政能力,明确禁烟实施对于吉林地方执政近代化及区域发展的影响,从中得到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民国时期吉林禁烟与地方执政面临的问题
吸食鸦片摧残民众的身心健康,败坏社会风气,更加剧了国家的贫困化。就吉林地区而言,清末至“九一八”事变之前,始终贯彻以禁为主的总体政策。但在地方政府落实禁烟政策的过程中,面临着复杂的执政环境。庞大的鸦片吸食人数,众多烟馆的利益纠葛,私种、私售、私运的管控难度,外国势力的干涉,共同构成了民国时期吉林禁烟管控的现实困境。鸦片的泛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吉林近代社会存在的深刻危机。
(一)鸦片吸食群体庞大,烟馆林立
民国初期,吉林地区的烟馆数量众多,民众习以为常,管理机构控制低效。《盛京时报》曾报道:“镇守使署后胡同、审判厅西胡同、西三道街旧筹边使署院内、四道街田家大院及马营子计有若干家私卖鸦片,开灯供客毫无顾忌,迭经各报纪载,该管警署置若罔闻,长此以往不惟地方治安有碍,即禁烟前途将不堪设想矣。”(1)《烟馆》,《盛京时报》,1921年11月9日。
民众吸食鸦片必然会催生烟馆,早在清代中叶烟馆就已经存在了。鸦片泛滥之后,吉林地区的烟馆遍及城市乡村。烟馆也分高低贫贱,迎合了不同阶层的需要,导致民众的健康每况愈下。吉林地区兼有铁路权丧失的问题,“吉长路界外大小烟馆约十数家,黑窟连毗,乌烟弥漫,间有华妇盛装招待,备极殷勤,生意因而大旺”“吉长路局员多藉此以为消遣之所,烟花迷人,日久沉沦,金钱之损失尚不足惜,精神之消耗岂可言喻。形销骨立,为患无穷,未识有管理责者,亦有所闻否?”(2)《烟馆林立》,《盛京时报》,1927年4月6日。以铁路沿线发展起来的“铁路市”,日俄势力盘踞,俨然成为毒窝,极难解决。
禁烟管控面临对象群体庞大,普通民众吸食鸦片自不必说,军人也屡有染指,极大地破坏了军队的战斗力和纪律性。《盛京时报》曾报道:“今日(二十六)下午三时许,吉长路第三次票车内,有一少年军官,系鲁军工程队第一旅第三团团长”,在遇到“突来检查巡警数人,询明来历,将其所带物件逐一检査”,“于袋内搜出烟土一包,烟具一套。该军官明知违法,语阻色变。闻至吉林,再送官惩办云”。(3)《军人嗜烟被检查》,《盛京时报》,1926年6月29日。可见,当时的军人明知吸食鸦片违反法律规范,但是并没有约束自身行为。在最强调纪律性的军队尚且如此,鸦片在社会泛滥和渗透一窥可知。
(二)禁烟管控矛盾突出,鸦片贩运猖獗
民国时期,吉林地区烟贩遍布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军阀豪绅、官僚政客、土匪黑帮乃至贫苦百姓为牟取暴利均有所染指。民国早期在日俄势力范围内,鸦片贩运活动极为猖獗。《盛京时报》曾报道:“本埠日租界私贩烟土者,日有所闻,屡被查出,以及被俄车夫役等窃去。日昨,有鲁省商旅贩来数包烟土,被站洋兵查去。该客则当时买票回哈,声言将向洋兵头高大孟索要。所谓利令智昏,虽触犯法纪,而不以为意也。”(4)《私贩烟土者何多》,《盛京时报》,1916年11月14日。更有甚者,一些鸦片贩卖者或是勾结土匪、依靠黑社会势力进行或明或暗的武装走私,或是贿赂军政当局为其大开绿灯,甚至与军政当局中的官员沆瀣一气,共同纵毒,导致基层社会控制低效的情况蔓延。毒犯与黑恶势力交相混杂,致使腐败蔓延,正义难以伸张,社会风气渐坏。
除此之外,官商勾结涉毒的现象也屡见不鲜。管理机构的腐化,反映了地方执政系统阶段性的低效。参与者为争夺烟土利益知法犯法,管理机构人员贪墨,极大地打击了禁烟机构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盛京时报》曾报道:裴其勋身为旅长,又兼镇守使,禄位不可谓不重,被人告发收商人巨资保险,运输大批烟土,“继竟反颜,将烟土扣留,不予照发”,造成“五人自刎而死”。(5)《裴旅长被控之原因》,《盛京时报》,1919年11月2日。此案轰动各处,无人不晓。烟贩“相继来省呈控,并赴北京控告裴氏之劣迹”。(6)《裴旅长被控之原因》,《盛京时报》,1919年11月2日。随着案件的发展,通过裴旅长牵扯出吴湘贤营长等“被裴旅长按名送呈吉林督军公署严加惩办”。(7)《军官亦犯烟案耶》,《盛京时报》,1919年12月5日。至于吴营长是否替人受过,难免让人联想,贪污腐化竟然如此肆无忌惮。
吉林地区有专门的禁烟机构,但涉及禁烟问题,权属管辖涉及多方,会出现职责不清、推诿争利的情况。军队甚至出现了因利益分配引起的开火事件。“兵士抢劫烟土,互相开火。除将某连长等绑缚外,计伤毙兵士二十余名。”(8)《包运烟土之暴露》,《盛京时报》,1922年10月4日。军人贩烟现象确实存在,“南满车于六日早由长春开来,经日警查出军官张威和私贩烟土一百余两,当即带去,未知如何法办矣”。(9)《军官贩烟》,《盛京时报》,1923年12月8日。这导致社会评价越来越差,甚至军署派人查获烟土,险被舆论误认为是军官贩烟。(10)《拿获烟土案续志》,《盛京时报》,1923年7月7日。
由此可见,无论是军阀、官僚、政客,还是土匪、地痞,均能成为运输、销售鸦片的主体。特别是当时军阀割据比较混乱的时期,地方恶势力和军、政、警相互勾结,共同获利,为吉林地区禁烟工作的实施带来了阻碍。
(三)外国势力的渗透,禁烟管控受限
日俄通过铁路沿线城市和商埠的渗透,形成了在吉林地区事实上的势力范围。这就造成了吉林地区禁烟政策执行中的涉外干涉。日本管辖的南满铁路沿线烟毒尤甚,《盛京时报》曾报道:“头道沟日本站烟馆林立,不下百数十家,均以华捕为辅,公然开设,而警务署长官不知也”。(11)《日警捣破烟窟》,《盛京时报》,1921年6月18日。吉林地方政府无法直接处罚,只能通过上级政府采用外交手段或者引渡毒贩的方式加以管控。“头道沟附属地日本警务署,日前拿获烟馆人犯,现已审问明晰,录取口供,解交中国法厅罚办云。”(12)《烟贩引渡中国惩办》,《盛京时报》,1919年2月19日。这些案件一经查处,往往涉及多方势力,极大地增加了执法成本,使得地方政府颇多顾忌。“日站有俄商由东清车到长,带来大宗红纸包烟土,值价羌洋约万余元之数。下车后已将运入于俄旅馆矣,竟被日警署查觉。该俄商见势不佳,当即夺路而逃,未被捕获,只将该土呈交警署充公。”(13)《拿获大宗烟土》,《盛京时报》,1917年7月19日。一案涉及三方势力,竟然如此复杂。“似此现象,春城终无净绝希望也。”(14)《禁烟不到日租界》,《盛京时报》,1917年5月20日。
1919年之后,情况有所改善,说明中国的外交努力有所收获。涉外禁烟问题如若处理不好,会降低政府的公信力。这种状况始终存在于民国时期的吉林地区。张学良主政后积极恢复路权,虽有所改善,但直到“九一八”事变,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1930年,仍然有烟贩被遣送的情况。例如:“本埠附属地头道沟日警察署,于昨六日早,在附属地内大行搜查,捕获烟犯、吗啡犯一百十七名,带署内审讯一次,即送中国公安局,转交教养工厂教养。”(15)《引渡大批烟犯吗啡犯》,《盛京时报》,1930年11月11日。
二、民国时期吉林地方禁烟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纵观民国时期的吉林禁烟政策,总体方向是以禁为主。张作霖执政期间,在1927年放开烟禁,唯独当时主政吉林的张作相,依然采取坚持禁烟的态度,保持了吉林禁烟政策的连续性。
(一)一以贯之的禁烟政策,配套制定地方法令
烟毒祸国殃民,是近代中国肌体上的毒瘤,鸦片带来的深重灾难早为国人所深恶痛绝,因此有识之士大力提倡制定并颁行禁烟法规,对禁烟的各事项和细节等均进行了较为严格而详细的规定,从而使禁烟之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吉林省也多次颁布禁烟的法令,进一步细化禁烟细则。吉林在民国初年基本沿袭清末禁烟的政策,强调“禁烟功令甚严,关系至重,表面虽云禁绝,而私种私吸仍有所闻。推其原因,未始非地方官办理不力所致”。(16)《饬禁鸦片》,《盛京时报》,1916年3月22日。随着计划禁烟期限届满,“吉林尤为禁绝省份,自应切实断绝根株。自此令行后,查有吸贩种运烟苗,并买卖吗啡等情,即惟该管官警是问”。(17)《严禁吗啡鸦片令》,《盛京时报》,1917年3月14日。可见吉林地方当局态度十分坚决,要求切实严禁。另外,在禁烟工作的实施期间,吉林要求“自应切实断绝根株”,全面检查烟苗种植、贩卖与运输情况,一旦发现私自销售鸦片的现象,将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据调查,1925年全国鸦片“行禁止者,全国只吉林、山西两省而已”。(18)《民国成立后之禁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四一(2)24。值得关注的是,张作霖主政时期,迫于军费压力,于1927年1月开放烟禁。而主政吉林的张作相依旧坚决禁烟。吉林地区在1927年后,密集颁布了吉林地区禁烟法令,贯彻禁烟思想。在军阀混战、禁烟废弛的大环境中,吉林地区显得独树一帜,尤为难得。
1927年颁布的《吉林省禁烟令》,共计二十条。针对吉林地处奉黑之间、东北地区开放严禁的现实情况,颁布了三个方面的针对性政策。首先规定了禁种、禁运、禁吸等一切禁令“依照从前”“无所变更”。其次,强调了吉林地区坚决禁烟的一贯政策。针对奉黑两省烟料运输问题,规定“只准通过,不准售吸”,并在省交界及交通要冲地带设立禁烟药料检查所专治办理检验事宜,要求入境烟料详细备案,领取一次性通过证,限时检查离境。没收的禁烟药料定时焚毁。最后,强调了依法治罪和处罚标准。情节严重,如伪造通过证,可处以应纳捐数30倍到50倍的罚金。(19)《禁烟令已竟颁布》,《盛京时报》,1927年4月26日。
各种具体禁烟条例的颁布,使禁烟活动权责明确,奖惩有据。同时,吉林省禁烟章程所规定的事项,通过结合地方实际,进一步配套并加以细化。政策更加规范严密,禁烟活动得以有序地展开。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部就以通令的方式,拟订禁烟细则九条。细则明确了管理机构和管辖范围,护路军铁路沿线的检查所设立和通过证办理办法,没收烟料、正捐及罚金的分配办法,进一步细化了处罚细则。(20)《协办禁烟之细则》,《盛京时报》,1927年5月22日。这种明确的配套属性,在吉林地区禁烟进程中,保障了相关规定良好的可实施性。《吉林省禁种烟苗暂行简章》(21)马模贞主编、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写:《中国禁毒史资料(1729-1949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46页。十五条规定的出台,进一步强调“净绝根株”,彻底解决禁种问题,对于私种的处罚和官员、军警的包庇行为加重处罚。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吉林地区在1929年4月相继颁布《吉林省禁种鸦片暂行办法》(22)鲁仁、孙贵田:《辅帅逸闻纪实:记张学良的老佐臣张作相》,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92页。《吉林省军、警、团禁种鸦片奖惩条例》(23)鲁仁、孙贵田:《辅帅逸闻纪实:记张学良的老佐臣张作相》,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93页。。法规进一步强调了严查私种鸦片,以禁烟管控的实际成绩作为政绩考核的依据;通过派员私下调查的方式,避免因利益产生的瞒报漏报;甚至通过邻里之间的“十家连坐法”,互相监督,力求将烟毒从根清除。
这些政策的出台,一方面坚定贯彻了禁烟理念和政策,展现了区别于当时奉系开放禁烟的姿态。同时,也体现了吉林地区实施禁烟的积极行动,彰显了政府的决心。另一方面,彰显了当时吉林地区在禁烟问题上有法可依、依法治烟的特色。
(二)禁烟实施采用强制手段,多种奖惩措施并用
自清末禁烟运动开始,政府在禁烟过程中,基本采取了禁种、禁吸、禁运、禁售等措施。吉林地区的禁烟实施过程,随着时间的推进各阶段侧重有所不同。
民国初期,继承了清末严格禁烟的各项措施,但清末禁烟未解决的问题也遗留了下来。民国初期主要以禁种为主,通过加大核查的方式,以期解决根源问题。“现值禁烟期满,由省署派出专员查验,有无私种之,倘遇有违禁私种者,不惟将烟苗铲除,种者处罪,且将该管县知事严加营戒云。”(24)《专员查禁烟苗》,《盛京时报》,1917年05月31日。1922年,为了巩固禁烟成果,并进一步杜绝种植鸦片,甚至采用了一经发现私种者,土地充公、邻居连坐的强制手段。“省公署下令禁烟,去岁终年已数次矣。近恐各县知事及各警察,对于禁烟一事,日久玩生,不认真查禁”,“调查有私吸私卖者,务认真拿获,不准稍苟情面,致有玩忽禁令之罪;如有私种者,先将其地充公,再传其左右邻,而以知而不举之罪为之究办”。(25)《公署又下禁烟令》,《盛京时报》,1922年2月8日。其后种植鸦片的问题提及甚少,客观上说明了禁种鸦片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
由于张作相在1927年吉林实施禁烟的政策中,针对性地提出了禁运的办法,此后政府禁烟实施的重点在于禁售、禁吸。此间发生的案件也多以查处吸烟、贩烟为主。“佟进及张玉亭二人,正在卧吸烟之际,被该管巡官王凯南遇见。因案关违禁,当将该二犯并烟具烟炮一并带所,据情转送署部核办云。”(26)《吸烟被捕》,《盛京时报》,1926年12月8日。至于贩售鸦片,此后期间查处甚多,甚至出现了当时少见的女性贩烟的案件。“长春四区巡长杜宝珩”,因行色可疑,盘问查明“王袁氏,年卅八岁,锦县人(系属久贩者)。带来此货,托朋友曹某代卖,未得卖妥,欲带往别处再为出售,不意被捕”,(27)《妇女贩烟》,《盛京时报》,1926年12月11日。并审讯录下笔录,移送法办。
为打破禁烟在基层执行的阻力,执行机构采用适当灵活性惩戒办法,进行多种惩罚责任并处。《盛京时报》曾记载了通过判处苦工、处以罚金、查封窝点等方式艰难推行。“日昨由中东火车运到大宗烟土八十余斤”,“连人带土送交日警署,乃罚以三个月不准营业云”。(28)《贩烟土罚停营业》,《盛京时报》,1919年12月16日。对于吸食鸦片的处罚,“长春城里北大街成文厚后院住户张敬轩”,因为吸食鸦片,“昨闻业经判决,竟处罚大洋二百五十元云”。(29)《吸烟受罚》,《盛京时报》,1927年3月22日。在实施过程中,还具体规定了“罚代赎者最低价格按大洋六十元追缴”。(30)《禁烟严厉》,《盛京时报》,1924年10月17日。随着禁烟形势的迫切性和政策严格程度的不同,结合犯罪事实及其影响,吉林地方执政采取灵活的惩罚手段,试图从手段上缓和矛盾,更好地进行有效管控。同时,奖励作为正向激励的手段,在近代社会控制中并不多见。吉林地区在查处鸦片的过程中,曾主张“遇有吸贩鸦片者,准许投函,指名控告,函内注明姓名、地址,以待将该犯拿获之后,由罚款内提出,充当赏钱”(31)《禁烟布告》,《盛京时报》,1917年4月29日。奖励的方式,这样可以更广泛地调动社会资源,推进禁烟的执行。
三、吉林地方执政与禁烟成效的多维透视
总体而言,吉林地区自清末至1931年日军入侵东北之前,禁烟成效基本保持了清末民初的禁烟成果。在其他各派军阀纷纷弛禁的情况下,吉林地区能取得如此成绩已是实属不易,是颇为值得肯定的。
(一)吉林地区禁烟的直观效果显著
对于查获鸦片的处理,严格按照当时的规定进行定期焚毁。民国期间,到1931年为止,《盛京时报》中明确记载焚毁事件共13次。长春地方检察厅一次焚毁记录中,仅1922年12月到1923年7月,8个月内“计烧烟土一千零九十三两五钱又卅七斤,又一万五千三百七十一斤,又十贯烟灰及料子共一千六百九十斤,又烟泡及膏子、吗啡等共六百七十五包,又烟具一律焚毁”,(32)《检察厅焚毁烟土》,《盛京时报》,1923年9月12日。并“函知各机关届时到场监视,以表大公云”。(33)《检察厅焚毁烟土》,《盛京时报》,1923年9月12日。
另外,管辖机构如吉长镇守使署“丁镇守使将十三年稽查处所捕获各案没收之违禁物品,一律焚烧,已志前报。今特详志违禁物品之数目,以及焚烧时之情状,以享阅者。总计没收烟土共重五千八百七十一两三钱,烟料子五十两,外有一包烟膏五两,烟灰一包,烟具一套,灯罩四个,烟斗一个,吗啡麻药暨假吗啡共十二两九钱四分,吗啡针三个,纸牌一百五十冲”,(34)《焚毁违禁物数目》,《盛京时报》,1925年2月17日。并同样“函知各机关,届时各皆齐集,尚禀请吉林督办特派军法官焦金声为监视员,莅场检验”,“直至将该违禁物焚成灰烬,始回署。”(35)《焚毁违禁物数目》,《盛京时报》,1925年2月17日。
在此阶段,烟土等违禁物的处置程序比较规范,而且邀请了各机关代表及报界新闻媒体监督,目的是扩大舆论宣传,引导民众自觉禁烟,从对民众动员的角度来看,比清末民初更具广泛性。
吉长镇守使署在“自去年八月一日起至本年一月卅日止”不到半年时间,除“获有人犯者六十三案,计人犯八十五名,无主承认者二十七案”外,“统共没收烟土连皮共重四千三百九十七两,烟膏连皮共重一百卅八两五钱,烟料连皮共重十五两,烟泡五十一个,……均行火焚,黑烟滔滔,观者如堵云”。(36)《违禁物焚毁数目》,《盛京时报》,1926年2月11日。如此短的时间内,查处案件和缴获的烟毒数量相当可观。
吉林地方政府推行的禁烟政策,保持了基本理念的一致性和政策的连续性。不同阶段执政者对于禁烟政策推进,有效传导到了地方,取得了明显的直观效果。对于吉林地区的社会风气、社会秩序以及农业恢复也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今天的禁毒工作和社会治理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吉林禁烟控制视角下的地方执政
民国时期,吉林地区烟毒泛滥是一种社会失范的现象。地方政府通过落实禁烟政策,在多个维度展示了执政能力和社会控制能力,以期达到有效管控烟毒的目的。
首先,上级政府禁烟政策的实施压力和绩效考核方式,通过细化落实,对吉林地方政府起到了内化的推动作用。民国期间,吉林地区禁烟政策整体上是向前推进的。但在不同的阶段,政府政策导向和考核体系的变化,会对烟政的实施产生直观的影响效果。尤为明显的是张作相主政吉林期间,他在1927年颁布并细化了吉林地区禁烟法规,厉行禁烟。自1927年5月,《盛京时报》整月只报道了1起烟毒查处案件。但从1927年6月开始,案件数量迅速增加,每月平均6件;8-10月份达到高峰,最多时每月10件;到12月逐渐下降;至1928年1月恢复到每月1-2件的水平。(37)《盛京时报》,1927年6月—1928年2月。案件数量必然与查处力度有关。这是厉行禁烟政策增大烟政考核在地方政绩考核中权重的结果;客观上,也是政府在政策执行上与媒体互动,从而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对不法分子的震慑。
其次,吉林地区地处奉黑两省之间,在禁运、禁售等管控环节制定了针对性的有效政策。处在特殊的地理位置,政策的针对性是禁烟政策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吉林巡按使查知,鸦片人犯之私吸私贩者,多在长春、哈尔滨等处”。(38)《重申烟禁》,《盛京时报》,1916年3月16日。一方面贩烟查处压力较大,另一方面,“长春处三省中枢,交通孔道,对于私贩烟土以及其它违禁物品,不可不专设机关,从事查禁”。(39)《长春设置稽查处》,《盛京时报》,1924年7月13日。针对性体现在统一禁烟政策下,强化对烟毒贩运的管控;吉林单独实施禁烟时,强化烟毒过境管理。地方长官的个人能力和视野,对于禁烟的政策细化实施有着特殊的历史价值。吉林地区执政者能够坚定执行禁烟政策,保证了吉林禁烟政策的持续性。
第三,外国势力的干涉贯穿于民国时期吉林禁烟始终,吉林地方政府能够积极地开展对洋交涉。在此过程中,执政机构逐渐适应近代外交规则,取得了一定成绩。从早期的日俄干涉禁烟事务问题开始,禁烟管辖地区问题、日本辖区烟馆问题、俄国辖区租地种烟问题、烟贩引渡问题等陆续出现。地方政府对外强势与否,关乎政府在统治区的权威性与公信力。1917-1921年期间,吉林禁烟的报道多为南满铁路沿线烟毒泛滥的记载。吉林地方政府采取积极态度解决了问题。早在宣统元年,《吉林西路兵备道为请在南满、东清铁路界内禁烟事同日、俄交涉之移文》(40)马模贞主编、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写:《中国禁毒史资料(1729-1949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79页。就记载了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外交努力,解决涉洋烟务交涉问题。其后历届执政机构,为有效解决涉洋烟务问题也多有交涉。“头道沟驿日本警务署,现又派人严查烟馆,凡遇有烟具或烟土者,即时革捕送交警署,以凭核办。外间传闻,系中国行文交涉,始有此举云。”(41)《日警严查烟馆》,《盛京时报》,1927年7月18日。这种接触,在具体禁烟执行过程中更是频繁。1922年后,查处案件和训令增多,也是对外交涉取得成果的有力佐证。
第四,针对内部机构人员腐化的问题,吉林地方政府能够通过机制化的纠察,进行适当控制。《盛京时报》曾报道:“长春警察厅张厅长自接事以来,整顿内外勤务,目不暇给。昨十日,该厅特发传单,告诫属员不准吸食鸦片。”(42)《警察厅传令禁烟》,《盛京时报》,1923年3月17日。“查警察人员均负有查禁之责,不但不能正人,而反不能责己,实属有违法令。自兹以后,凡本厅属员如果查有吸食鸦片者,定行惩力不贷。”(43)《警察厅传令禁烟》,《盛京时报》,1923年3月17日。官员和执行机构自身违法,腐败问题一直存在。多起案件的公开,也说明了吉林地方政府在管控自身贪腐方面,有一定的机制保障。机制性的反腐纠察和前置性预防同样重要。
第五,在禁烟实施的方法上,通过多样化的奖惩手段,以首要政务为着眼点,强化了奖惩力度。对于民众同样采取了土地充公、邻居连坐与举报授奖并行的方式。(44)《禁种鸦片之通令》,《盛京时报》,1924年1月12日。这种强化惩罚的措施,在现代执政体系下,过于严苛,手段僵化。而通过执政系统内外部的奖励方式,不失为一种进步。一方面,吉林地方在禁烟实施的过程中,强化禁烟成果的作用,以达到“此番又查获此案,均属重要,谅必获得上赏云”。(45)《缉获巨土》,《盛京时报》,1923年9月11日。另一方面,执政考核强调以禁烟绩效为导向,并可给予奖励。“与其禁之于既种以后,莫若禁之于未种以前,如其境内烟苗肃清,自当从优奖叙云”。(46)《禁种鸦片之通令》,《盛京时报》,1924年1月12日。地方执政对于民众同样采取了土地充公、邻居连坐与举报授奖并行的方式。
最后,机制性的定期销毁查处的赃物,对外公开,强化了宣传与震慑效果。《盛京时报》曾报道:“本埠检察厅所拿获之烟土以及他项违禁物品,向例每按春、秋两季一律焚烧。今届时期,是以审厅鲁厅长暨徐检察长用公函通知各机关齐集该厅,共同监视焚烧云。”(47)《焚烧烟土》,《盛京时报》,1924年10月15日。基本都能达到“参观者不少”的效果。通过强制性的案例宣传,普及禁烟政策和禁烟知识,能够逐渐改变社会风气。长春西头道街住户张砚田已有68岁高龄,吸食大烟“因大便走血,服药罔效,故迄今未能戒除”。警察发现后,法庭堂讯“判罚金五百元,具保释出”。“闻该老者自出庭之后,痛悔交加,病势日渐加重,且云:宁死决不能再吸此冤孽物也!其子现为其各处征求良医云”。(48)《吸烟受罚》,《盛京时报》,1926年11月26日。这样的案例也许不合人情,却能起到警醒的作用。
四、结语
近代中国,禁烟问题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其所承载的民族救亡与近代革新的双重意义,始终伴随着执政者的现实困境。吉林地区的禁烟进程中完整地保持了严禁方针,尤其是在1927年东北地区开放烟禁的情况下,展现了吉林地区独有的时代特征。
民国时期,吉林禁烟的实施,从统治者的角度,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控制和执政系统。在此过程中,执政者本能地寻找最为切实可行的执政路径。如果缺乏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没有权威性政策和坚定的立场,无效的群众动员和公民的普遍素质偏低,一项社会工程必然面临巨大的困难。通过内化政策实施压力、制定针对性的政策、交涉外部冲突、强化内部纠察、采用多样化的基层实施手段、良好的舆论互动,吉林地方的执政导向得以坚持,禁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随着执政能力的强化,在禁烟进程中,体现了更为有效的社会控制能力,吉林地方政权的近代化革新得以徐徐展开。在时间线索上,吉林地区的禁烟执政呈现出由严查“禁种”到重点逐渐转向严控“禁售”和“禁吸”的阶段性特点。面对复杂的禁烟社会环境,不同的执行机构和执政者其施政的结果也有较大的差别。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