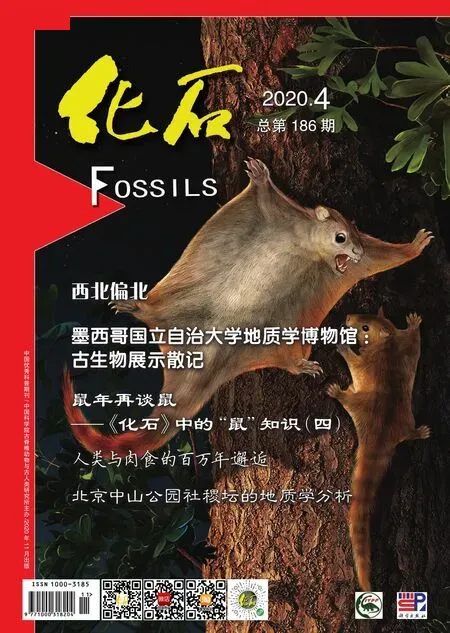泥河湾
——我与旧石器考古的不解之缘
陈 云
泥河湾,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圣地,也被誉为“东方的奥杜威峡谷“,从20世纪20年代被发现以来,以其丰富的文化面貌和古老的地质环境吸引着海内外不同学科学者们的关注。笔者作为一个初入旧石器考古学大门的“菜鸟”,有幸前后三次前往泥河湾参与考古发掘。今年因为种种机缘巧合,笔者在阔别泥河湾两年之久后得以再次前往参加发掘工作,在此将笔者的诸多经历和收获整理出来,与读者分享。
在泥河湾的经历
相信对于每一个学习史前考古的人来说,泥河湾都是他们永远也绕不开的话题。记得是在2017年的6月,河北省文物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河北师范大学泥河湾考古研究院、阳原县人民政府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了“首届旧石器时代文化节”暨“首届高校石器打制比赛”。笔者彼时还是在河北师大就读的一名大二学生,当时出于对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满腔热情,和几位同学报名参加了大会中“原始人”的角色扮演。为了形象逼真,我们扮演的“原始人”不仅要穿上“兽皮”,披散着头发,还需要用颜料把脸上涂得花花绿绿,以更加贴近“原始人”的粗犷形象。
尽管扮演“原始人”的工作在现在看来有几分傻气,但当时我们是将其当成一项重要任务来完成的。因为“原始人”不仅要扮演好“演员”的角色,即兴表演,营造氛围以吸引参会媒体和观众的眼球;还要承担起“礼仪员”的任务,为旧石器文化节的公众考古环节——“打制石器比赛”、“用石器肢解动物”等提供服务。这段有趣的经历也成为了我学习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契机。
真正去到泥河湾参加发掘是在2017年的7月底,彼时笔者和另外几名同学一道跟随河北师大的牛东伟老师参加了怀来县珠窝堡遗址的发掘工作。怀来县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的东南,属于广义的泥河湾盆地的东部。“泥河湾盆地”这一概念最初是在20世纪20年代由美国地质学家巴尔博等人提出,最初被认为是包含在桑干河盆地之中,分布在河北省阳原县东部。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现在学者们一般认为广义的泥河湾盆地就是桑干河盆地。卫奇先生曾指出,广义的泥河湾盆地包括了河北张家口的阳原、蔚县等地,山西大同及朔州等地,面积达9000多平方公里,桑干河及其支流壶流河是盆地内主要的河流。
在怀来的发掘工作持续了一个半月之久,也正是在这里笔者体会到了学习旧石器考古的初心和快乐。彼时作为一名完全的田野新手,正是在老师和技工师傅的教导下学会了清理标本、使用全站仪建站、记录标本信息、测量产状、绘制地层和遗物图、做好田野日记以及室内的整理和观测,等等。这些知识对于当时完全是新手的笔者而言,无疑是新奇且有趣的,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夏天我不仅学习到了田野知识,更是在心底播种下了一颗学习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种子。
而在大三上学期的田野实习当中,笔者参加了泥河湾盆地蔚县东沟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和第一次参加田野工作不同,此次可以算是有几分经验了。东沟遗址的发掘从九月中旬一直持续到了十一月中旬。犹记得考古工地刚开始时我们还穿着短袖挥汗如雨,到了后期在探方边瑟瑟发抖,民工大叔们还为我们在附近的空地上支起了火堆。
如果说第一次参与田野发掘我们还抱着完全学习的心态,那么田野实习时我们则将其当成了一次真正的田野训练。从遗址的发掘到后期整理,再到管理民工和记录工地各项支出、购买各种生活和工作物资等,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不断积累、快速成长,也真正体会到了考古既是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生活的过程。做好考古工作不仅仅需要勤奋努力,更需要一些敬畏和温度。
再回泥河湾,我与旧石器考古的不解之缘
作为一名考古学系的学生,在大四时几乎都面临着考研的选择,而对于当时的笔者而言,旧石器考古无疑是艰深且复杂的。班上的同学们几乎都选择了历史时期考古方向,或是科技文保类等方向。而当时国内新石器时代考古大热,重大发现接二连三地进入人们的视野,受到大环境影响,笔者当时几乎是选择了新石器时代考古作为今后的学习方向。或许是心中埋下的旧石器的种子并没有因此停止生根发芽,在进入研究生阶段之后,笔者对于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学习方向反而更加明朗,旧石器考古就像是一簇火焰,开始引导着笔者主动去探索一个又一个陌生的知识领域。
今年夏天因为机缘巧合,笔者又再次来到了泥河湾,参与了蔚县蔡家沟遗址的发掘工作。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裴树文老师的团队连续六年在蔚县开展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相关工作,目前已经先后发掘了前上营、吉家庄、蔡家沟等多处遗址。据裴老师介绍,这些遗址年代都在中更新世早中期前后,多数为河湖水退去后,古人类反复活动形成的文化堆积。
和众多泥河湾遗址的发掘工作一样,蔡家沟遗址B地点采用的是小探方发掘法,在近30平米的面积里以1米×1米的小探方为单位提取标本和记录信息。这种以小探方为单位进行编号和收取的好处在于可以有效防止遗物漏编,并且还能够有效记录遗物的相对位置信息,便于以后查找。
因为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多数是以5-10厘米为一个水平层向下进行发掘,在土质坚硬的情况下,和南方地区使用手铲就能够原地留存遗物大不相同。泥河湾的发掘需要经验丰富的民工根据遗物的大小留出合适的土台,然后我们再用竹签、刷子等再将遗物的原貌一点点揭露出来。因为遗物往往都需要拍摄出土照,因此修好土台和剔除遗物就是泥河湾工作者们的一项基本功。要在保存遗物完整性和不改变原位置的情况下剔除遗物并不容易,因为土质坚硬,用力过大会导致整个土台垮掉,遗物位置发生变化,前功尽弃,所以把握好力度也十分重要,剩下的也就是细心再加耐心了。毫不夸张地说,有时常常要跪趴在地上半下午仅仅只为了剔出一根完整的动物肋骨。
除了细心和耐心以外,掌握必备的考古测量技术也是基本技能之一。除了利用全站仪测量、相机拍摄标本照片和建模外,利用无人机对遗址地层和大环境进行拍照也是必不可少的。在开工前需要对蔡家沟遗址所处的大冲沟及遗址所属台地使用无人机进行拍照,每一层发掘结束,在对遗物进行编号和测量以后还要用无人机进行航拍记录。对于笔者而言,从开始的胆战心惊到后来能够熟练地操控无人机进行航拍也是今年夏天来到泥河湾最值得开心的收获之一。
除了发掘遗址以外,我们还会配合着对遗址周边地区展开一些调查工作。说起调查就不得不提起我们工地上,一名身怀绝技的人——技工宋存瑞师傅,我们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宋叔。宋叔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技工,他的足迹几乎已经跑遍了泥河湾大大小小的河谷阶地,发现了诸如蔚县东沟、怀来珠窝堡、大同南坡、杜庄等旧石器时代遗址。
只有真正参加过旧石器考古的野外调查才知道要找到一处适合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有多么不容易。一处适合发掘的遗址,首先需得发现有一定厚度的文化层堆积;其次就是剖面得出露一定数量的文化遗物。在调查的过程中,可能有时运气好能够在地面发现有零星化石或是石制品,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就有收获了!首先需得判断这些化石和石制品的年代,一般来说,早期的动物化石的石化程度都比较深,从外观上来看,一般微微泛黄,重量也比晚期的动物骨骼要略重一些。从石制品来看,除非石器具有某些特别明显的技术特征,比如勒瓦娄哇技术、石叶技术、细石叶技术等,否则一般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另外,还需要判断这些出露物是否属于原生地层。因为史前时期,尤其是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受到自然环境的改造是非常强的,另外水流的冲刷以及风力等作用长年累月也会对遗址的本来面貌造成极大的改变。一般而言,原生地层堆积的遗物相对来说会更加丰富一些,地层也比较清楚,在调查时仔细找寻往往还能够有意外收获。
旧石器时代的调查比任何一个时期的调查都要困难,往往走上一整天也毫无收获!我们几个学生毕竟还是年轻,不太沉得住气,跑上一整天没有收获难免有些怏怏不乐,每当这时宋叔就会耐心鼓励我们。在宋叔的鼓励下,我们打起精神继续沿着一个又一个剖面仔细查看,有时我们几个还会打赌,下一个剖面会不会有东西发现,有时确实没有发现我们也并不气馁,还会颇有兴味地开玩笑道“这地层比我今天洗的脸都还干净呢!”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
当然,收获也是会有的。有一天我们在刚刚走出遗址不远的冲沟里进行复查时,就听宋叔说道,这个地方他去年来过,当时就发现了几块动物化石。闻此我们都很是振奋,因为从堆积来看,这里显然是一处原生地层,要是再能有所发现,其很有可能就是一处极有潜力的发掘地点。果不其然,我们刚刚低下头去仔细查看时,就听得有同学兴奋地喊道“我这里发现了一块石片!”我们连忙凑过去看,果然是一块燧石原料打制而成的石片。有了这个开端大家都很是振奋,我们四散开来沿着附近细细找寻。一低头,便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一块灰白色的东西,用手轻轻拨开泥土,果然是一块动物化石。我们将采集的东西放在一起——有石片、碎屑、还有一些哺乳动物化石,毫无疑问,这里是一处旧石器地点。我们将东西放在原地拍好照片,封装好,又做好记录方才离开。
在我看来,无论是调查也好,还是发掘也罢,旧石器考古所体现出来的魅力绝对不小于任何时期的考古工作。当然,任何一个时期的考古工作都有着外人不能体悟的艰辛和收获,这也许正是考古工作本身所带给我们的幸福和满足感。
泥河湾,东方人类的故乡
如果让我们描述泥河湾的意义,可能绝大多数人想到的正是那句“东方人类从这里走来”。诚然,作为国内最富盛名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泥河湾目前发现了大大小小300多个遗址,年代早的有马圈沟、小长梁、东谷坨、岑家湾等遗址,中期的有许家窑-侯家窑遗址、板井子遗址等,晚期则以虎头梁遗址群为代表。除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址群外,泥河湾还以更新世动物群、古生代以来连续的地质地层等闻名于世,可以说,泥河湾不仅是史前考古学者们的圣殿,同样也是地质学者、古环境学者们的学术天堂。
除了发掘、调查工作以外,我们这次还有幸参观了新建成的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并不是笔者第一次参观遗址公园,在2017年笔者曾经和师友们来参观过泥河湾遗址群,彼时的泥河湾遗址公园尚在修建之中,遗址广场也还是一片土泥路。而如今的遗址公园已然换上新妆,气势恢宏。
笔者等一行人在裴老师的带领下,一边翻山越岭,一边津津有味地听裴老师耐心细致的讲解。很奇妙,尽管泥河湾已经很大程度上被开发为一个遗址公园,但是也许是因为它有太多故事,也太过于传奇,我们踩在这片土地上心中竟然隐隐升起了一种在破坏遗物的“犯罪感”。
站在栈道上向西边远眺,可以看到大小两道并排的沟梁,这就是著名的大长梁和小长梁遗址所在地,二者均为更新世早期的遗址,遗址的年代已经超过了一百万年,然而据裴老师介绍,我们脚下踩着的不起眼的红色岩层却是千万年前某几次岩浆喷发而形成的火山沉积物,泥河湾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活动也不过两百万年,而早在人类之前这里就已经蕴育出波澜壮阔的自然奇景,实在不能不令人心潮澎湃。
我们经过小长梁一路向东而行,看到一处几近倒塌的剖面颇为惊讶,经过裴老师介绍才知道这就是四十多年前发掘过的一处遗址,不禁令我们对这不起眼的小小探方肃然起敬。再往前,我们依次或眺望或经过了一个个耳熟能详的遗址,石沟、马圈沟、岑家湾、飞梁‥‥‥这些遗址的剖面垂直耸立在一个个沟渠漕梁之上,清楚明白地向参观者们昭示着它们并不平凡的过去。这些遗址或新或旧,有的甚至相隔仅有数十米,如此种种显示出一代代人前赴后继从未停止过对于泥河湾的探索。
我们经过东谷坨遗址时正好赶上今年东谷坨遗址的发掘开工,不巧的是我们到达时已经将近11点,遗址上已经没人了。我们同行的有去年参加过东谷坨遗址发掘的同学,这才知道原来正好赶上了下工时间。东谷坨遗址发现并最早发掘于20世纪80年代,同时也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首次中美联合的涉外考古项目,东谷坨遗址的意义不可谓不重大,目前东谷坨遗址已历经了数次发掘,而目前围绕东谷坨遗址的研究已经涉及到了石器技术、原料分析、动物化石研究、环境研究、年代测定等多个方面。如东谷坨这般做过许多研究的遗址在泥河湾不在少数,相关的科研和学术成果也多已发表,对于泥河湾来说,也是一大幸事。
泥河湾有今天的新貌与无数在泥河湾辛勤奉献和工作的人密不可分。卫奇老师自20世纪70年代在泥河湾参加工作,到如今已然近半个世纪,也是较早将泥河湾推向世界舞台的学者。笔者曾与卫奇老师有过一面之缘,至今仍然记得卫奇老师叮嘱笔者要勤写文章,幸福生活,多向世人介绍和宣扬泥河湾。卫奇老师的这番嘱托也是笔者写作这篇文章的一点初心和缘起。
后语:泥河湾是笔者考古梦想开始的地方,这里承载着笔者太多田野青春和美好回忆,这些珍贵回忆将是笔者一生都难以忘怀的。笔者将在泥河湾的经历付于纸上,一则是对于美好事物的追述,二则是希望凭借笔者微薄的文字让更多人知道前辈今人们在泥河湾的工作,如果笔者的文字能够给予读者些许触动,对于笔者来说也是一件无比幸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