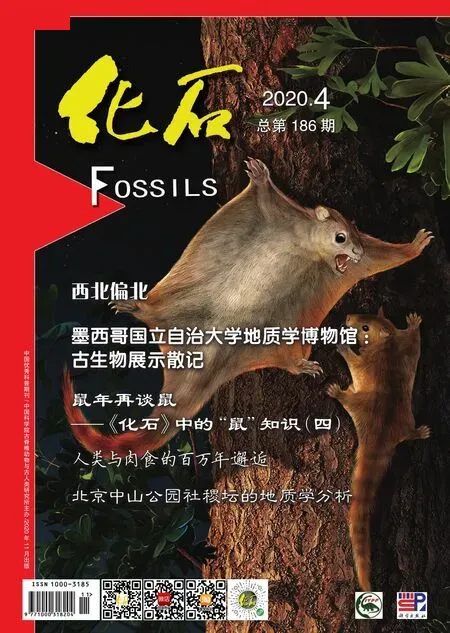人类与肉食的百万年邂逅
杜雨薇
现代人的日常饮食已经和肉密不可分了,红烧肉、培根、熏肉……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将我们钟情的肉食变为不同口味的美味存在。如若追本溯源,我们的先祖们什么时候开始广为接纳肉食,奠定它们不可或缺的地位呢?又是为什么迷恋肉食,使得人类的演化历程与食肉行为紧密相连呢?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在大约340万年以前,生活在埃塞俄比亚Dikika的古人类在享受着一场对他们而言难得的肉食大餐。也许是他们当日的运气极佳,碰上了一只被鬣狗或其他肉食动物吃剩的大型有蹄类动物,或是成功围捕到了一只年幼弱小的牛科动物,这使得他们得以享受一场“饕餮盛宴”。早期人类最初是利用坚硬的石质工具对动物尸体进行切割获得肉食资源,用砸击骨骼来获得其中营养价值极高的骨髓。肉食似乎是推动人类演化的一种点石成金之术,它的出现使我们祖先的食谱逐渐向高热量、高脂肪转化,这可能在促进人类脑容量增大、智力提升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人类最早吃肉的考古证据是怎样的?谁又是这个证据的制造者?相较于杂食的先祖与近亲,古人类为何将肉食更加主动地纳入食谱?肉食会带给古人类更小的生存压力吗?这些问题自提出伊始就深深地吸引着各路学者们,直至今日仍受到广泛热议。
古人类食用肉食的最早证据
推测古人类是否存在肉食行为的考古学证据有很多,主要包括烧骨或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等线索。在人类演化的早期阶段,祖先们还没有学会利用火烧熟食物,考古学家很难获得烧骨这样的直接证据来证明他们的食肉行为,而这一阶段对古人类食肉证据的推测更多来源于观察动物骨骼上是否保留明显的切割、刮削与砸击痕迹,是否有大量残缺的动物骨骼分布于人类频繁活动的地区,或者出土的动物骨骼周围是否有一定数量的石制品工具等间接证据。
这种推测很快有了结果,2015年8月,Nature杂志刊登了一篇引起考古学界热烈讨论的文章,考古学家P. McPherron等人在埃塞俄比亚Dikika遗址出土的四块残缺的动物骨骼上发现了明显的石质工具切痕与砸击痕迹,它们可能分别来源于获取动物身上的肉食与骨髓资源。年代学分析表明这些动物骨骼的年代可能早于339万年,是迄今为止最早的人类获取肉食资源的考古记录。以其中最为典型的DIK-55-2与DIK-55-3两个标本为例,其分别是一只大型食草类动物的右部肋骨碎块与一只年幼牛科的股骨骨干碎块。两个标本上均有多种石制工具痕迹,后一标本骨骼上分布的痕迹尤为密集,包括切割、刮削与砸击痕迹。然而困扰考古学家的是,整个Dikika遗址都没有明显的石质工具出土,所以这些痕迹与石质工具的关系显得扑朔迷离。Dominguez-Rodrigo等人提出,遗址化石埋藏后被其他动物踩踏,或化石的偶然移动都可能是样本骨骼上留下痕迹的原因,甚至有些切割痕迹可能由骨骼本身附着的血管痕迹经过埋藏作用造成。但是因为DIK-55-2等典型标本的出土环境非常“干净”,缺少附着的胶结黏砂磨蚀导致痕迹的条件,所以仍然不能完全排除人类对这些动物骨骼产生影响的可能性。令考古学家们对这一食肉证据更加充满信心的是,在同年的Nature杂志所报道的位于肯尼亚West Turkana的Lomekwi 3遗址出土了目前已知的最早石制品,年代为距今大约330万年,这增强了Dikika遗址动物骨骼上痕迹是人为的可能性。
距离Dikika遗址不远的Bouri遗址同样出土了数个表面有石质工具痕迹的动物骨骼,年代大约在距今250万年前。Bouri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上保留的人工痕迹主要是切割痕与砸击痕,其中一个中等大小的牛科动物的左侧下颌骨内侧就伴有三个连续的曲线条纹,这可能是由于使用锋利石片切割动物舌头部位导致的;再向南196米出土的一个没有关节部位的胫骨骨干上也保留着切割痕、砍砸痕迹以及数个石锤的敲击痕迹;大约1米以下的地层里还出土了一个完整的三趾马股骨,骨骼表面上的石质工具切割痕迹表明可能存在对其肢解与分割等行为。有趣的是,Bouri遗址也没有出土大量石质工具,只有个别简单的石核—石片工具出现。de Heinzelin等人认为可能由于环境因素制约而缺少制作石质工具的原材料(地处湖畔地区缺少被强力水流带来的砾石石料),这与Dikika遗址缺少石质工具的缘由也是相似的。
距离Bouri遗址约96千米的Gona遗址区内同样有一批带有切割痕迹的动物骨骼出土,并且年代大致与Bouri遗址相似,在258-210万年前左右。作为最早的奥杜威工业遗址,Gona遗址出土了大量奥杜威石质工具与动物骨骼遗存,其中能够证明二者在功能性联系的证据就表现在带有切割痕迹的骨骼这一形式上。这种清晰的人类食肉行为主要发现在Kada Gona,Ounda Gona等地区的EG13,WG9,BSN6,OGS6,DAN1与DAN2的遗址点。动物骨骼上的切割痕迹呈现为骨骼表面明显的线状痕迹,少数为单个出现,多为成组出现。骨骼出土环境周边沉积物以粉砂与黏土为主,可以排除踩踏与偶然移动等导致的刻划痕迹。生活在Gona的古人类所选择的肉食以牛科为主,体型主要为中等及大型,而且出土样本中的所有肢骨集中在上部(如股骨、肱骨)与中部(如胫骨、腓骨),切割痕迹也都保留在骨干上,由此表明Gona的古人类可能不是被动的食腐者,否则肢骨上部与中部的骨干部分在他们开始享用之前就被大型食肉动物们啃咬、分割到一定破损的程度了。
250万年到175万年间有一定数量的遗址有石制品与动物骨骼的同时出现,如位于肯尼亚的Lokalalei 1与Lokalalei 2C遗址,但是目前没有在动物骨骼上发现有明显的人工痕迹。而在175到100万年之间的一些非洲考古遗址(如位于Olduvai Gorge的Bell’s Korongo)出现了大量的石质工具与动物骨骼,更振奋人心的是,石器边缘的微痕分析与骨骼上的直观痕迹都为这一阶段人类食肉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但在出现年代更早、更清晰以及更丰富的证据之前,我们需要谨慎地评判与界定这些人类食肉行为的具体阶段。
谁是最早吃肉的“人“?
距今1000万年-500万年对人类演化来说是一个关键的时间段,在这期间,部分非洲人族世系向外辐射而产生了大猩猩族(Gorilla)与人族(Hom i n i n),其中人族包括黑猩猩(Chimpanzee)、各种已经灭绝的古人类与现代人,而后两者才是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大猩猩是安静的素食主义者,主要依赖一些树叶与果实来在森林中生活。而黑猩猩是与人类亲缘最近,作为杂食动物,吃肉这一行为对于黑猩猩来说是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其中昆虫占据肉食的主要来源,但是有时其他小型的脊椎动物如小型的猴与羚等,对它们来说也是青睐的肉食来源。黑猩猩与人类的亲缘甚至表现在一些简单的行为举止上,比如前者也出现食物的分享、简单的猎物捕捉等现象。这些说明,在人猿分离之前,甚至我们很多的灵长类近亲都是杂食的,“吃肉”似乎并不是我们人类独有的特点。但是从哪些灭绝的早期人类开始,在食肉的主动性、使用石质工具带来的更高效率,以及猎物的体型选择上开始区别于我们的先祖猿类与近亲黑猩猩?关于对这些食肉的早期人类的研究,对古人类学与考古学有着重大意义。
早期人类获得其他脊椎动物肉食的行为可以从一些考古证据上得到支持。前文提到,大约340万年前的Dikika遗址中发现了带有切割痕迹的动物骨骼,这可能与这一地区DIK-1-1地点发掘出的一个3岁南方古猿阿法种(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头骨有某种联系,因此,学者P. McPherron等更倾向于把这一采用工具分割并食用哺乳动物的行为归功于阿法种。但是由于Dikika的发现现今还有一定的争议,并不被广泛接受。
在埃塞俄比亚Middle Awash地区的Bouri遗址所出土的有蹄类动物骨骼上所保留的切割与砸击痕迹被广为接受是人类食肉遗留下来的证据,因此Bouri Formation地层中发现的南方古猿惊奇种(Australopithecus garhi)似乎更普遍地被认为是最早能够屠宰动物并加以食用的人类。同样,在Gona遗址出土的带有不同切割痕迹的大中型牛科动物骨骼也与南方古猿惊奇种有某种可能的联系,因为惊奇种骨骼遗存出土的地层与一些有痕迹的骨骼出土的地层是相同的。有趣的是,Gona地区EG13地点出土了一个带有切割痕迹的肋骨残片,它来自于一个中等大小的牛科动物,且保存良好,切割痕迹位于肋骨上靠腹部的一面,Dominguez-Rodrigo等人认为这是早期人类为了取出动物内脏而导致的。而且Gona出土的动物肢骨上出现的切割痕迹主要集中在骨干部分,研究者们认为早期人类可能比其他大型食肉动物更早接触这些动物尸体。换句话说,当时这些动物死亡后,是生活在这里的人类先祖首先接触到它们的尸体的,而不是在大型食肉动物吃完这些动物尸体后古人类再吃剩下的腐肉。也许早期人类恰好碰到了生病或是幼小而不能反抗的猎物,并对它们进行了狩猎,当然也不排除他们只是等待这些猎物自然死亡然后食用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能回到200万年前遇见最早的人属(即能人Homo habilis),它们的外表似乎与南方古猿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但是现今主要的古生物与考古学证据表明这一物种相较南方古猿来说更擅长处理肉食。这一饮食变化可以从能人的头骨形态变化中得到证明,比如,能人后牙大小相较南方古猿减小,表明他们的咀嚼功能复杂度有了较明显的降低,并且能人手指的变化使得他们能够有力地抓握并精确地操控物体,能使他们制造更复杂的工具,从而加强他们获取并处理肉食的能力,获得有更丰富能量的高脂肪食物。
根据对早期人类牙齿化石的微观磨损(microscopic wear)与稳定同位素(stable isotope)等研究发现,他们仍然以水果等植物果实为主食,但是相较猿类追捕小型动物的行为来说,生活在300多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具体可能是阿法种南猿)就将体型更大的有蹄类纳入食谱。现今看来,或许更多的证据支持南方古猿惊奇种是最早的主动且有目的进行食肉行为的早期人类。
肉食资源——早期人类的“魔杖”?
风靡全球的小说《哈利·波特》中有一个关于魔杖的话题:是魔杖选择巫师还是巫师选择魔杖?这或许与动物资源与早期人类之间的关系有些类似,是周围环境资源限制人们只能更多的选择肉食,还是人类主动接纳肉食资源进入自己的食谱从而宁愿放弃一些植物食物?与“魔杖之问”不同的是,前者有我们耳熟能详的答案,即魔杖选择巫师而不是巫师选择魔杖,它会根据你的特点来选择你。但是后者我们至今也不清楚它的答案是什么,或许是动物资源丰富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人类的主观选择与意愿,或是两者都有,当然也不排除未来发现别的可能,这需要学者们未来的不断研究。
虽然很难通过早期人类的化石来建立它们的饮食与当时周边环境的绝对关系,但是环境因素是理解早期人族开始增加食谱中肉食比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大约450万年前地猿始祖种(Ardipithecus ramidus)与南方古猿湖畔种(Australopithecus anamensis)等早期人族生活的环境里,广泛生长着喜爱温暖湿润的C3植被(木本植物),它们的食物主要包括在树上的各种果实。孢粉与碳同位素分析发现在上新世最早的阶段(距今500-400万年)C4植被(包括湿地与干旱环境下的草本植物)出现在非洲东部,虽然在距今400万年左右C4植被又减少了一定数量,但是到距今390到370万年左右,这类植被又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增长。与他们先祖不同的是,南方古猿阿法种等在C4植被扩张时期生活在更为干旱的环境里,从而缺少他们更能够习惯的食物来源,但是更开阔的C4植被却是有蹄类动物生存的天堂,所以最初Dart等一些学者认为动物资源对古人类的重要性因此增加了很多。
但是现今的发现表明,距今420万年之后的南方古猿以及最早的人属似乎更偏好在C4植被扩张的环境下生存。来自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E. Levin等人对埃塞俄比亚内中央阿法尔裂谷(the central Afar Rift)西部的Woranso-Mille发现的人类化石进行了稳定碳同位素研究,此处出土的化石种属介于南方古猿湖畔种与南方古猿阿法种演化过程之间,部分可以被定为阿法种。这些化石的碳同位素数据显示这里的早期人类最早在376万年前就将大量的C4资源纳入他们的食谱中了。这与之前C4植被进行扩张的时间段相一致,似乎表明与其祖先相比,南方古猿的食谱范围因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从以C3资源为主到C3与C4混杂,甚至C4资源可以占据主导。
我们不能清楚且准确地分辨出这些古人类食谱中C4植被的具体种类是什么,但是因为在更加开阔的环境里生存,早期人类获得C4食物的主要来源包括草的果实与根茎、莎草、CAM代谢的植物(Crassulacean acid metabolism,代表性植物为仙人掌)以及食用C4资源的有蹄类动物。单单凭借其中的一个独立来源是很难形成部分南方古猿如阿法种以C4明显占主导的食谱数据结果,所以更多的可能是食谱范围扩大,多种途径共同构成了南方古猿的食物来源。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狒狒等非人灵长类,早期人类为了维持更大的大脑,很难再缺乏其它高质量食物(high dietary quality)补充的情况下,只依靠莎草根茎等低饮食质量食物(高纤维、低蛋白质和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长期生活。这与之前湖畔种南猿食谱中较高营养的水果与坚果食物来源是迥然不同的。所以简单来说,充满草茎的热带稀树草原与湿地(savanna and wetland)环境可能给早期人类(尤其是最早的人属)一定的压力,从而去探寻更多高质量的食物,其中就包括来自于其他脊椎动物身上的肉食资源。
我们也不能排除早期人类食用脊椎动物食物是因为他们喜欢或是需要吃其中的一些部位。除南方古猿粗壮种(Australopithecus robustus)以外,根据保留下来的牙齿形态与肌肉附着痕迹来看,大部分南方古猿更适合吃软的东西,脊椎动物的脑子、骨髓和其他软组织可能更受他们的偏爱,这或许可以从一些遗址(如Dikika)中因古人敲骨吸髓而形成的砸击痕迹上得到证明。脊髓等动物软组织是南方古猿与早期人属所倾向的高质量食物,这或许是它们食谱中正需要获得补充的。当然,以上内容更多的是学者们的猜测,现今虽没有具体的模型与实验去探索肉食在南方古猿的食谱中的具体地位,但我们也不能盲目地自行猜测南方古猿主动选择肉食资源这一可能性。
捕食者与被捕食者:人类与其他食肉动物的竞争关系
在早期人族生活的时期,虽然要时时刻刻面对大型肉食动物的危险,但是他们也会作为“清道夫”追随在“大型猎手们”身后捡拾其吃剩的动物残骸。有时可能运气好,成功猎杀一只幼年或是病弱的猎物供大家一起分享。在还没有主动用火与复杂工具的时代,早期人族在与大型食肉动物的竞争中仅能维持住生存,他们一方面需要努力避免被食肉动物捕食,另一方面却要和食肉动物竞争,获得对其他脊椎动物肉食的所得权。这种游走在生与死之间的冒险史若是能流传下来,完全可以形成一本不亚于《奥德赛》的人类伟大史诗。
因为环境的变化频繁与简单工具的开始使用,古人类食谱中的肉食比重逐渐扩大。这意味着在一些开阔干旱的稀树草原环境下,古人类势必在食肉上与一些大型食肉动物形成竞争关系。但是在人类演化初期,不发达的心智与落后的技术装备使早期人类很难抵御大型食肉动物的凶猛。即使古人类可以以群居的形式共同抵御外来的袭击,但如果群体数量不多或是有零星落单,有可能会被机敏的食肉猎手抓住机会而成为它们的美餐。C. K. Brain就在现代非洲的野外调查中发现豹子捕食一些洞穴中群居的灵长类的现象。至于考古发现,我们虽然没有发现古人类被食肉动物捕杀的场景遗存,但是一些痕迹提供了一些可能性。比如科学家在奥杜威峡谷发现了被食肉动物咬过的人类骨骼。甚至直至中更新世时期,人类已经有了足够顺手的石质工具,并且有足够能力消耗大量的其他有蹄类动物的肉食资源,仍然可能出现大型食肉动物捕食人类的现象。比如在北非摩洛哥一个洞穴内,Daujeard等人发现了距今50万年左右带有鬣狗啃食痕迹的人类股骨。
考古学家也会根据动物骨骼上残余的痕迹与断裂的方式来研究古人类与大型食肉动物竞争肉食资源的现象,因为人类与食肉动物遗留的痕迹一般是不同的。C. K. Brain与M. C. Stiner通过观察现代非洲与欧洲野生食肉动物(如鬣狗、豹子等)的狩猎与进食过程,尝试总结了一些食肉动物遗留在被捕食动物尸体上痕迹的普遍规律,比如它们习惯食用的动物尸体部位是什么?一般食用后残留下来的骨骼部位是哪里?以及残留下的动物骨骼上能遗留下什么痕迹?经过大量的野外观察与控制实验,Brain和Stiner认为残留有蹄类动物骨骼的长度一般大于5厘米,骨骼边缘参差不齐,多保留完整肢骨,或是有明显动物咬痕。早期人类的食肉行为除却前文提到的骨骼上的切割、砍砸痕迹等证据外,动物骨骼周边伴生出土的石制品、长度较小的骨骼碎片、有棱角的骨骼边缘、保留较多的动物掌跖骨等,都能让动物骨骼堆积的线索更多指向人类行为。
但是因为我们与早期人类之间存在巨大的时间沟壑,加上糟糕的骨骼保存状况与模糊的遗留痕迹,使得早期人类活动的研究变得复杂无比,尤其在判断人类是否进行了主动狩猎上十分艰难。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根据遗留在动物骨骼上的切割痕迹等特征推测人类有没有食用这一动物尸体,但是很难判断这些动物是不是这些“食客”杀死的,因为捡食食肉动物的猎物与自然死亡的动物尸体也是人类重要的食物来源。哪怕有大量的动物骨骼堆积在一个遗址之内,并伴生出土一系列的石器与碎片,我们也不能完全确定这是古人类的杰作。例如,肯尼亚Koobi Fora Formation的FxJi50遗址中出土了伴有一系列石器与碎片的至少属于17种哺乳动物的2000多块骨头,部分骨头上有明显的砸击与切割痕迹,但是同时一些骨骼上也不乏食肉动物的啃食痕迹,这有可能是食肉动物捕获猎物后被人类赶走,也有可能是人类为了减少食肉动物的威胁主动将猎杀后的新鲜骨头丢给逡巡的食肉动物。事实究竟如何,我们已无法事无巨细地了解,只能尽可能地从蛛丝马迹中辨明可用的证据。
总而言之,在古人类演化的早期阶段,因为自身能力与周围环境因素,他们更像是肉食的机会主义者,更多地依靠捡食一些动物尸体或是大型食肉动物啃食的残骸。当古人类的心智与工具制造能力逐渐加强,也许他们会更加化被动为主动,在狩猎与肉食资源分配上更加占据主动。
未尽的故事
在探寻早期人类食肉的故事上,科学家们要做的还有许多,就像是罗马城不能够一日建成,几百万年前人类日常生活的图景也不能够在短时间内依靠有限的遗址发掘内容而描绘完毕。令人欣喜的是,随着更丰富的早期遗址材料、更精准的科学检测方法、更合理的模型不断出现,学者们越来越注重从多角度研究早期人类食谱这一课题,并且不断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当然我们也要意识到,关于早期人类行为研究道路也是漫长的,而推动研究行进的动力之一就是不断提出新的问题。也许在未来的考古学看来这些问题如同几千年前屈原仰望天空所发出的《天问》一般质朴与懵懂,但是毫无疑问它们将成为我们摘得早期人类研究桂冠的垫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