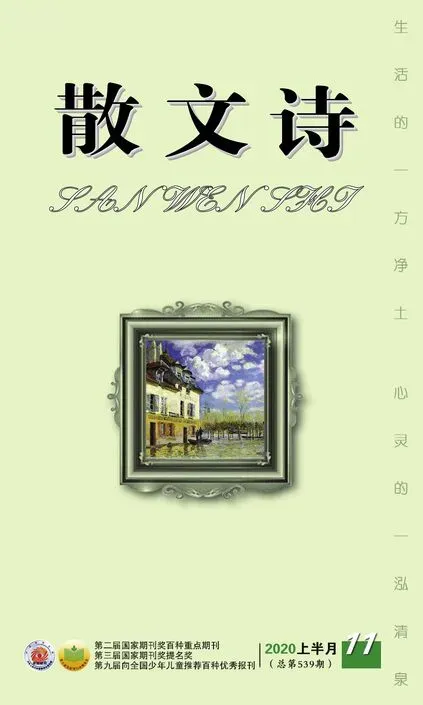昆虫世家
◎潘志远

散文诗应该比新诗更灵活、更自如、更潇洒地行走,出手成诗。眼界、格局、情怀、哲学、神性……都是散文诗不可或缺的元素。创作散文诗应像庖丁解牛,透视内里,游刃有余。
作茧自缚,只是暂时,有什么好揶揄和讥讽?
当你破茧化蝶,飞向蓝天的一刻; 多少人在自我陶醉中,错过了这一瞬,忽视了你的英勇!


蚂蚁:隐忍力量的楷模
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嘲笑,蚂蚁从不反驳,也不气馁。
一如既往撼它的大树。撼不动,就往上爬,一直爬上树顶,宣示占领的意义。
这意义,仅对蚁族而言,仅它们能懂;对于它物,依然是厚厚的隔膜。
彼此碰碰头,便有了新的举措。
一个伟大的发现,一个伟大的计划,在一瞬间达成。多年后,当大树訇然倒地,那是它们隐忍力量的必然结果,也是它们惊天动地的欢呼。
不要说它们懵懂,当大雨铺天盖地而来,谁也不知道该逃往何处?搬家的路线无法勘定,也来不及勘定。
茫然是一定的。恐惧,也不稀奇。但因为蚂蚁的渺小,它们的恐惧也很渺小。
对粮食一往情深,倍加珍惜;在这一点上,很像我们的父母和先辈。
最反对捏死一只蚂蚁的残忍。再弱小的生命也是生命,生存不只是人类的专利,也应当隶属于宇宙间每一个生灵。
蜘蛛:一网风雨,一网星光
织网也有三种境界。
以乡村为背景,以屋檐为支点,倾腹中之丝,结一张小网。
小网恢恢,也可以疏而不漏。
不强求,是昆虫们自己撞上去的,成为蜘蛛的美味,怪不得任何人。
坐等是一种悠闲,也是一种劳累。漫长的等待,是一种苦;此苦到蜘蛛这里,差不多已登峰造极。
一网风雨,不图清凉,不图沐浴,只为检验一下蛛网的牢固。天下经纬也莫过如此。
摆下八卦阵,与算命无关。算命受制于八卦,但八卦左右不了它们的命运。
一网星光,多么好!虽然不能果腹,但可以让饥饿看到希望。蛛网夜夜闪烁,一丝,是一思;一思,又不是一丝。
互不关联,在一声平调里体验一种情感。撇下,与撇不下,都是一种牵扯。
蝴蝶:在自由和爱情间轮回
吐丝。结茧。
茧是爱情的产物,茧是你的安乐窝。
为了获得更广阔的天地。有更广阔的天地,才有更广阔的爱情、更广阔的自由。
必须突围出去,哪怕历经千辛万苦的蜕变。
翩翩,是祝英台的舞姿。
翩翩,是梁山伯的脚步,是探望,是追随,或者是永生永世的相伴。
是一把刀,劈开黑暗和混沌。
是一颗砝码,有了它,世界才为之平衡。
是一把打开季节的折扇,扇动花海,芬芳澎湃。
是一把钥匙,打开自由,打开爱情,打开今生和来世……
在自由和爱情之间轮回。洁白若雪,灿烂如霞。介于两者之间,游弋于两者之间,我始终以为这是最好的状态。
蜻蜓:点水,一种错误的假象
轻盈是你的优势。
也是你的缺陷。因为这,你压不住春天的阵脚。
立于夏。夏递来一支尖尖小荷,试探你的诚心。打开翅膀是飞翔,也是休憩。动静如此完美,是一首诗,也是一个典故。
提升夏天,夏天是一种按捺不住的躁动。
复眼,多方位的洞悉万物,关键时又视而不见。有选择的盲视,是生存的智慧,被一些人发挥到极致。
点水。一种错误的假象,与水的深浅无关,与水的清澈和浑浊更无关。
柔软的产床,多么适合分娩蜻蜓世世代代的梦想!
蚯蚓:模范的耕耘者
生于土,食于土,也世世代代耕耘于土。
像先辈的影子。
不要嘲笑无骨者。无骨者的坚韧,比有骨者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蚯蚓是最有说服力的诠释。
惊蛰之雷是上天发来的贺电,雨水是乌云倾吐的情谊绵绵的密语。
耕耘开始,以肉躯为犁,翻开一垄垄板结的泥土,让农人播下春天的种子;当希望回青返绿,信心扬花吐穗,垂下一枚枚金色绶带。
蚯蚓无言,露珠滴答着秋天晶莹的喟叹。
瓢虫:身负北斗七星的使者
圆形突起,是一种昭示吗?我不得而知。
红、黄、黑,是三种颜色,更是三种语言,三种难以预测的命运。
搏击于一身,也和谐于一身。
我喜欢:胖小,红娘,花大姐,金龟,这些充满乡土气息的称呼!回到从前,弥漫着一种幸福。
二十八星瓢虫,背负着星象、宇宙。
斗柄不转,你就带着七星一起旋转,红尘深处荏苒的光阴,悄然倒流。
你这来自中侏罗纪的古老标本,也是迄今还活着的标本,娇小玲珑,演化着一部绚烂历史。
一部活着的教科书,不止一次被我捧于掌心。
昆虫北斗,照亮我的犹豫和无助……
天牛:牛在不牛
是牛,都要耕地。
以此为标准考量,你辜负了牛的美称。
何必千篇一律、呆板、顽固、不开化呢?我觉得有牛的外形,或者某些部分酷似即可。
何况你是天牛,从天而降,某些特征可以淡化,可以蜕变;何况你长着翅膀,能够轻松飞翔,让所有耕地之牛望尘莫及。
你有太多的称呼:啮桑、啮发、八角儿、花妞子、苦龙牛、蛀柴龟……这些,我都愿意忽略;我只看重一个“牛”字,牛气冲天,何等傲气。然而,目光被你的美丽色彩诱惑,忘了你对植物的危害,并认为是一种偏见。
迷恋你的触角,总想借此一用。
你的足带着铆钉,任何时刻都可铆紧一棵树、一茎草、一片叶,你拥有不打滑的季节和人生。
发出“咔嚓、咔嚓”之声,享有“锯树郎”的绰号。但我喜欢用方言喊你“老牯牛”,不耕地就不耕地吧!我一次次递过去青草,检验你的锯齿,并就此获得极大的快乐。
也曾将你投入水中,看你是否会游泳。童心的残忍在举手投足之间,缺乏思考,更谈不上阴谋和陷害。
天牛,牛在不牛。拗口,谲诡。直到今天,须发花白,我还半懂不懂。
螳螂:惊艳的拟态生存策略
喊你的学名:螳螂,你不要答应,因为那是一件很拘谨和枯燥的事情。
让我喊你刀螂,用一种你熟知的乡音。在自然的环境中,我们不期而遇,也许在柴门外一株灌木旁,也许在老屋边一棵苦楝树上,你的花衣,与夏天一色。
当你举起前臂,真像祷告的少女,有人称你为祷告虫,并视你为先知。不止一次听闻你的传说,螳螂捕蝉,但从未见过。前半部分已道听途说,后半部分更不希望发生。也许就是一个杜撰,用来吊世人的胃口。
当我读到中华大刀螳、狭翅大刀螳、广斧螳、棕静螳、绿静螳这些名字,恍若看到一队武士,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征。
绝对的帅哥和靓妹……
当雄螳为爱、为后代,将自己义无反顾地喂饲于雌螳,当成悲剧,不免偏狭;当成颂歌,又不落忍。
最佩服它们的生存策略,拟态成花,拟态成叶,拟态成水滴,拟态成帆船……不一而足。如此美妙的捕食,倘若被我撞见,我将三生有幸!
蝗虫:拥有人类一样的习性
我不关心什么纲、科、目、属,就像不关心一个人的背景和来路。
撇开形旁,从声旁里,我读到它们的前世和来生,曾有的或将有的辉煌。不要动不动就说,秋后的蚂蚱。揭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是否也该用在此处。
像我们一样食小麦、水稻、谷子、玉米、豆类、烟草、芦苇、蔬菜、果木,杂草的叶子、嫩茎、花蕾、幼果:好胃口,恍若人类的前身,或千万年前人类的另一种造型。
群居,拥有人类一样的习性。长距离迁徙,为生计所迫,与人争食,也无可厚非。
成为飞虾,被人大快朵颐,并津津乐道营养丰富、肉质鲜嫩、味美爽口,听不到一点怜悯和叹息。
可炒,可焙研,可煲汤……用于食疗,能治愈惊风发热、抽搐痉挛,亦可止咳平喘;而人类的加害,总是振振有词,无往而不胜。
蜗牛:踟蹰在前行的路途
说出蜗牛,已不同凡响。
说出驼包蜒蚰,想象力更加超人。而能悟出“蝇头小利,蜗角功名”,一定非大智者莫属。
让别人去命名、比喻、诠释吧,蜗牛只喜欢我行我素。
独自上路,身体是它的房子、它的盔甲、它的亭子、它的床和旅馆……永远只住它一人。
一座宝塔,踟蹰在前行的路途。
一只陀螺,自己鞭笞自己旋转。
一个圆锥,测量自己的体积,也衡量世界万物,产生悬殊的对比。
一个球,一场自己和自己的赛事,从生到死。
偶尔还抽上了烟斗……
眼睛长在头部后一对触角上,不是目中无人,而是景仰宇宙。
行,必伸头看路;受到惊吓,缩进甲壳之中,对外界的保守,不仅诠释了它的胆小,更诠释了它的善良。
怕阳光直射,悬于叶下,小聪明大智慧合而为一。垂涎三尺,不是贪婪,而是画出行走的轨迹。数万颗牙齿,不用于咀嚼,成为其他昆虫的笑柄。
背着房子上路,像房奴,其实与房奴相差万里。
迁感受于他物,并且热衷于编排和杜撰,是人的长处,也是人的短板……
蜣螂:我想拜你为师
你郎,我也郎。
黑褐色皮肤。多年前,我们对牛粪、马粪、猪粪,喜而不避,趋而宝之,足以让我们称兄道弟。
现在,我们越走越远,早已形同陌路。
你还保持着你的习性,粪堆旁穴居,化解粪臭,疏松土壤,抱着“清道夫”的美称,熙熙而乐。
我爱洁净,业已成癖,斩断过去,一去不返……
你利用月光偏振定位,以太空中银河导航取食,是我所不具备的,也是我无法比拟的。后知后觉,我一直低看了你,小看了你。蜣螂,我想拜你为师。
能治愈前列腺疾病,预防治疗肿瘤,抑制非特异性炎症……亦药亦医,更让我望尘莫及。
我的优越感消失,我和你的差距,不只在人虫之间。
虫不言,人好自诩;只是自诩时,一定不要忘了自知之明。
有一个词,是专门为某些人准备的,叫恬不知耻。
青蚨:填补人类文化的精彩和空白
每一个别称,都是一种经历、故事或者传说。
并不比人的逊色,也能填补人类文化的精彩,甚至某些空白。
蚨蝉,文雅,似乎还滞留在贵族阶层。
蒲虻,只着眼于表象,有误解的嫌疑。
鱼父,谁在那沉思,想入非非,有几分自我陶醉。
鱼伯,夸大之辞,以讹传讹,这里面肯定少不了仰慕。
一声田鳖,是什么心理在作怪?蔑视、嫉妒参半,抑或兼而有之。
含蓄一点吧,蜮,短狐……多留一点想象,多留一点韵味,于他人有益,于己无害。
除非发小,且没有第三者在场,否则不要喊水知了;这样的尴尬,还是少一点为好。
桂花蝉,多么浪漫的昵称,可少有人深知其中的残酷。
青蚨还钱,尽管是一种杜撰,可一旦杜撰了,就是另一种真实,且胜于真实。
“得其子则母飞来,煎食甚辛而美。”这是《异物志》里的记载。每读至此,我眼前便晃动罪恶的嘴脸。
萤火虫:赋予光崭新的功能
以翅为轮,一辆甲克虫,是你的私驾,车和你合而为一。
喜欢在黑夜出行,路是四面八方;四面八方都是目标,随时发动,随时启程。
一盏尾灯,不是警示转向,不是发生故障,是害怕造成追尾。
属火,但不具备火的特性:不能取暖,也不能加工食物。
属光,但不用于照明。
警戒、恫吓、诱引……赋予光崭新的功能。
闪光信号,且是编码,有点高深。闪光信号模式,且有诸多参数……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了它的莫测。
雌萤只对0.13~0.16s的闪光做出回应:情有独钟,还是两心相悦,我无法断定。
囊萤早已过时。当一只萤火虫,携一团冷光,悄悄飞来;我目不转睛,只想记取黑暗里,它生命的画图和闪亮的轨迹……
豆娘:越叫越心生爱怜
瘦小,弱不禁风的样子,仿佛一阵风就能将她们吹走。
可事实上,风吹来吹去,将自己吹得无影无踪了,豆娘还栖息在草尖,翅膀叠敛在背上,那么静,那么稳。
像一个斯斯文文的小女子,身材窈窕,服饰鲜艳。
瘦西施,只此一喻。
赵飞燕,翩舞的姿势,有过之而无不及。
喜欢中流击水,像侠客,或勇士。
静水照影,但决不孤芳自赏。
看不出有什么高超的本领,却是捕食小飞虫的能手。给你点水,你依然不知水之深浅;水面漾开的涟漪,是一个个圈套。
雌雄交配呈心字造型,那一刻,天地静美。
绝对女性化的名字,叫千遍不厌,叫万遍不腻,越叫越心生爱怜。
螟蛉:成就了蜾蠃的大义
“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诗经》犯下的错误,千百年后,才得以更正。
更正者,是炼丹家,也是一位医生,更是一个诗人,一句“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让人永远记住了他的大名:陶弘景。
更正归更正,仍有更多的人蒙在鼓里。就让他们蒙在鼓里吧。一辈子不知道真相,有一辈子不知道真相的幸福。早知道真相,有早知道真相的懊悔。
朝闻道夕死,怎么说都显得可悲。
其他的名称都免了吧,我只喜欢双带夜蛾这一美称,每次叫,都像轻唤一个女子的芳名。
喜食水稻、高粱、玉米、甘蔗、茭白有什么错?关键是不该在人之前下口。喷药毒杀、装灯诱杀,尸横累累,没有人同情,反而喜不自胜。
螟蛉子,成就了蜾蠃的大义。当谜底最终被揭开,再看土蜂,它的细腰,不再是美的象征,而是恶的彰显。
螟蛉,蜾蠃!一段家仇了结,不受他人挑拨,没有演变为两个种族的血恨……
蟋蟀:更多的争斗来自某些人的挑拨
1.4亿年历史,需要多少名字和故事,才能将这漫长的时光填满?
故事慢慢消隐,只留下一串名字;一个个名字就是一个个故事,像一把把锁丢失了钥匙,无法打开。
我痴迷于这些名字,一如痴迷于诸多失传的典故。
蛐蛐,夜鸣虫,将军虫,秋虫,斗鸡、促织,地喇叭,灶鸡子,孙旺,土蜇,和尚……
平铺直叙者有之,娓娓道来者有之,悬念迭起者有之。
土洋结合,雅俗参半。
诗一样的促织,栩栩如生的地喇叭,谜一样的孙旺,忍俊不禁的和尚!
田野蟋,家蟋,我滞留在二元思维。针蟋,树蟋,蚁蟋,钲蟋,灌木蟋……我陷于混乱;大棺头,油葫芦,灶妈子……很难一统于传统的概念。
鸣不在口,而在翅,时而警告,时而求偶。
听不在耳,而在前脚节上,将我们的传统彻底掀翻。
生性孤僻,为爱而战,咬斗是为自己;但更多的争斗来自某些人的挑拨……
蝈蝈:一任它的歌吟爬满我的神经
把蝈蝈和蝗虫统称为“螽斯”,商周人不分,还情有可原。而宋朝人将蝈蝈与纺织娘混为一谈,就不胜荒谬。
三大鸣虫,说法太过笼统。
哥哥,聒聒,蝈蝈,拟声命名,形象,却终究搁浅在表层。
《七月》 《草虫》 《螽斯》,诗经里有关蝈蝈的篇章,我一读再读,仍有些迷惘。 “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载歌载舞的图腾,划过眼帘,最后定格于螽斯衍庆,不免狭隘。
荀子说禹跳,扬雄说巫步多禹。大禹对它崇拜,并以此取名,顿时使我有触电的感觉。
清人曰“百代”,又曰“千婴”,掀起的蝈蝈潮,可以视为国运衰颓、玩物丧志。
还是按色泽分类吧,绿、黑、山青、草白、红褐、蓝绿、金黄……真是一个五彩王国。
如果说选膀,不失为一种绝活,那么,通过点药于不同部位来改变蝈蝈的叫声,就沦为了变态。
感冒时,可喂食阿司匹林,享受了人类生病的待遇。饮食不宜太油腻,宜多投新鲜蔬菜和水果,则蒙上了养生的况味。
分辨蝈蝈,你去沉迷你的“六看”,我惟愿一听。在风清月白的窗下、庄稼地、土墙根,只身一人,六根清净,一任它的歌吟爬满我的神经……
桑蚕:生存本能让人类获益无穷
一声蚕宝宝,凝聚着多少怜爱。从五千年前原始蚕驯化而来,染色体28对,一对不少,但贡献却天壤之别。
从卵到幼虫到蛹到成虫,经历四个形态上和生理机能上完全不同的发育阶段,可谓真正的变态性昆虫。
也是寡食性昆虫,只对桑叶情有独钟。
也是经济性昆虫,食下桑叶20-30克,却能吐丝700-1500米,成本之低廉,利润之高昂,首屈一指。
一眠,二眠,三眠,大眠,体重增加1万倍。这1万倍里,有多少是茧的重量,我无法估算。
至五龄后,成为熟蚕,食欲减退,完全停食,体躯缩短,变为透明,开始昂首吐丝结茧;适应环境和生存的一种本能,让人类获益无穷。
作茧自缚,只是暂时,有什么好揶揄和讥讽?
当你破茧化蝶,飞向蓝天的一刻,多少人在自我陶醉中,错过了这一瞬,而忽视了你的英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