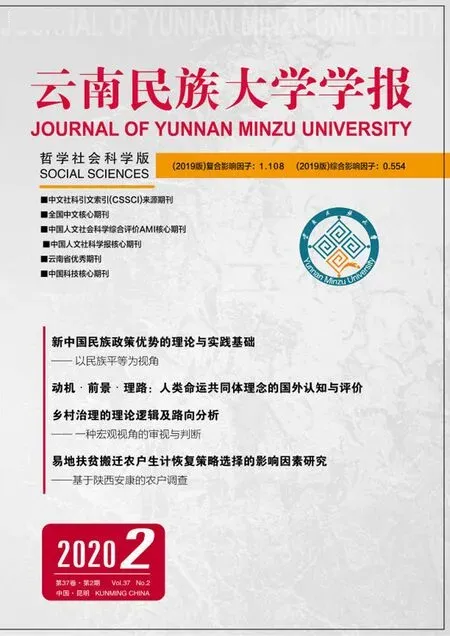族源神话的展演及其象征性
——白依人历史记忆的器物承载、身体实践与仪式操演
解 语
(1.云南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2.云南民族大学 人事处,云南 昆明 650091)
历史记忆是一个族群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形成并逐渐为本群体所共享的意识,其展演方式主要表现在物质载体、文字刻写、身体实践和纪念仪式等维度。物质载体是记忆的承载和具体化表述,它是历史记忆的基础。历史记忆的展演方式指向了特定的意义系统,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表述方式。物质载体是具体的事物,也是一种符号化表达;文字刻写本身是一种意识的符号化过程和结果;身体实践是身体的一种动作,也是一种带有特定意义的姿势;纪念仪式是整合物质、符号、身体以表达某一特定意义的行动过程。卡西尔认为,语言和象征性是人类文化的基本特征,象征是表述人类意识的主要功能,是认识人类生活、语言、历史、科学、神话和宗教的基础。(1)[美]布林·莫里斯:《宗教人类学》,周国黎译,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页格尔茨进一步发展象征理论,认为“文化是一个有序的意义和符号体系,社会的互动依据它而发生”(2)[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96页。从象征视角出发,阐述历史记忆的展演和呈现方式,分析其意义系统成为理解特定族群深层文化意识的突破口。
居住在滇西鹤庆县六合乡境内的白依人是彝族的一个支系。作为无文字民族,白依人族源神话在社会生活中以乐器、服饰、舞蹈、古歌、仪式等器物和行动呈现。这些文化要素是族源神话的延伸,在白依人社会中形成了与族群历史记忆关联的一套生活实践方式。本文在田野调查和文献梳理基础上,从神圣器物、身体实践及仪式操演等三个维度阐述历史记忆在白依人社会中的展演方式,分析器物和行动的象征性及其意义系统,探讨族群表达其深层文化意识的策略。
一、白依人社会概况
白依人是彝族支系,世居于鹤庆县城东部六合彝族乡的夸萼山区,与汉族、白族、苗族、傈僳族等民族杂居。据2007年统计,白依人总人口为6135人,占六合乡总人口的37%。白依人多居住于高山缓坡地带,房屋依山而建,传统建筑为木楞房。河东村、五星村、南坡村,上萼坪村等四个村委会为白依人的主要聚居地,周边乡镇也有少量分布。
白依人自称“夸萼氏”(也写作“夸恩斯”)。“白衣”译意为白色的衣裳,“白依人”因穿白色火草麻布衣而得名,“白衣”同时也是“伯彝”的谐音。关于白依人的族源问题,较为通行的看法认为他们源于唐时的施蛮、顺蛮。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民族识别,遵照本民族意愿,统称为彝族。(3)鹤庆县志编纂委员会:《鹤庆县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3页。
白依人拥有本族群的族源神话、原始宗教信仰,并在此基础上融合了白族本主崇拜,构建了该族群以本主崇拜为核心的宗教文化体系。在白依人的宗教文化中,族源神话中的祖先神与白族本主属于两种不同的信仰体系。从白依人族源神话和迁徙历史的文献中可以看到,他们并非夸萼山的原住民,而是后期迁入的族群,白族本主崇拜是后期嵌入的宗教信仰。白依人通过神灵之间的姻亲关系将两种宗教整合为一个体系。因为族源神话的展演及其象征性是本研究的主要问题,所以本文将围绕白依人族源神话在社会生活中的展演方式及其象征性的意义系统进行分析和讨论。
二、白依人的族源神话及其寓意
族源神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族群对于历史的观念和认知。列维-斯特劳斯总结了神话的一般性规律:“在不同地区收集到的神话显示出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又是与上述明显的任意性背道而驰的。”(4)[法]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陆晓禾,黄锡光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43~44页。族源神话具有多样的表达方式,其本质还是回归特定的社会意义阐释。白依人族源神话有不同时期的版本,在内容和情节上有所区别,但是祖先迁徙记忆是其中不变的主题。方志文献的记述说明了白依人从外地迁入夸萼山的历史事实。(5)鹤庆县民族宗教事务局:《鹤庆县民族志》,大理:大理天龙印务有限公司,云新出(2011)准印内字N083号,2011年版,第68页。
章虹宇于1969年收集整理出了白依人族源神话的文字版。该神话文本采录于1969年,由时年68岁的白依人歌手绞胜讲述,为白依人族源神话较早成文的版本。祖先莲姆老祖住在莲瓦塔鲁,为逃避山火以竹管操控蜜蜂,经过漫长的迁徙来到夸萼山。在迁徙过程中,莲姆老祖和子孙失散,白依人就在夸萼山定居下来。莲姆老祖在朝霞山拼命吹竹管(唢呐)寻找失散的子孙,嘴里吹出的血变成了火草。白依人把竹管做成唢呐,逐渐形成了《得胜令》《过山调》《蜜蜂过江调》《迎宾调》《生产调》《猎歌》《敬酒曲》和《踏鲁调》等36个曲牌。(6)章虹宇:《庆及周边地区民族民间故事选》,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106页。20世纪80年代末期,原云南民族学院教授杨知勇带学生到白依人地区做民俗调查,在早期文字版神话基础上增加了新材料。(7)在文末,杨知勇记载:“这份调查报告,使用了章虹宇同志提供的部分材料。”可见关于族源神话的基本内容还是源自章虹宇整理的文字版。
……江水响声盖住了竹管声,驮着莲姆和儿女的蜜蜂飞散了。失散在石宝山上的子孙,现在发展成大福地彝寨;失散在西山的子孙,现在发展成安乐坝、浑水塘等黑话人;失散在夸萼山的子孙,就是今天居住于鹤庆六合公社夸萼山上白依人的祖先;莲姆老祖则死在朝霞山上。传说白依人为纪念莲姆老祖兴建了白依庙,庙下边的珍珠泉是莲姆老祖眼睛变的。(8)内容根据原文整理。详见杨知勇:《彝族支系白依人的精神文化》,载政协鹤庆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鹤庆文史资料》,2003年版,第125~126页。
神话内容反映了白依人先民在大灾难中被迫迁徙的过程,围绕着族源地、祖先迁徙以及蜜蜂等要素展开。首先,关于白依人的起源之地,白依人原本生活在称作莲瓦塔鲁(9)经部分学者考证,“莲瓦”可能是今永胜县六德乡莲瓦村(分上莲瓦和下莲瓦)。“塔鲁”是族群名称,可能是现在的他留人。的地方。其次,白依人的祖先是莲姆老祖。在迁徙的过程中,莲姆老祖和子孙失散,她的血变成了火草。再次,白依人是因大火(灾难)被迫迁徙进入夸萼山。最后,蜜蜂帮助了白依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蜜蜂与白依人之间的密切关系。神话内容解释了鹤庆白依人与大福地彝族、西山黑话人,永胜他留人等几个彝族支系的关系。这些关于族源地、祖先、迁徙以及蜜蜂等神话要素都在现代白依人的社会生活中逐一展现。
三、白依人历史记忆的器物承载
历史记忆是社会群体共同建构的结果,体现出一个社会中历史记忆内容的选择性。物质载体如同其他记忆方式一样(包括历史书写),也是社会对记忆内容进行选择的结果,承载了一个社会群体对于自己群体及其历史的认知。在白依人社会中,火草衣和唢呐的功能不仅作为实用器物,而且也承载着历史记忆,象征着特定的意义系统。
(一)火草衣的服饰记忆与象征性
火草衣作为一种实用的生活衣物,也是白依人婚丧仪式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穿戴和馈赠礼物。火草衣以火草为原料,需要经过采火草、绩麻、纺线、织布、缝衣等主要工序最终制作完成。一般有“匹亚抓”“匹亚都”和“匹亚波”等三种款式,分别具有不同的功用。“匹亚抓”款式比较庄重严肃,穿上它一般需配以麂皮挎包。“匹亚都”实际上就是火草衣褂子,穿着较为方便。二者属于日常生活穿戴。“匹亚波”是孝衣,送葬时披,只披不穿。(10)高金和等:《鹤庆白依文化研究文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218页。
火草衣承载了关于祖先的记忆。莲姆老祖在朝霞山上吹着竹管召唤着自己的儿女,口中的鲜血溅到朝霞山上变成了火草。这个神话的情节让白依人去朝霞山上采火草具有了特殊的意义。莲姆老祖最后就是在朝霞山去世。那里曾经有一座白依庙,就是专门为纪念莲姆老祖而建。所以,一直以来白依人都有去朝霞山采火草的习俗。虽然距离较远,但是白依人依然翻山越岭上山采火草。今天白依庙已经不复存在,但这一习俗至今依然未曾改变。
白依人服饰包含了模仿蜜蜂的文化元素,这是白依神话中蜜蜂带领族群迁徙记忆的体现。白依人的服饰紧身细腰、长幅开叉,与蜜蜂细腰长身的体态非常相似,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形似蜜蜂触角的头帕。(11)高金和等:《鹤庆白依文化研究文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5版,第46页。白依老人绞莲秀讲述的《女人为什么不会飞了》传说,就提到白依女人会飞翔的特性,“妇女如不束腰,就会长出双翅飞走。所以皇帝下令让白依妇女束腰、戴帽子,不让他们飞走”(12)高金和等:《鹤庆白依文化研究文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300页。,这揭示了白依文化把白依女性视为蜜蜂的隐喻。
(二)乐器中的族群历史记忆
在白依人的大部分仪式典礼之中总会伴随着音乐演奏,其中最常使用的乐器是唢呐。在关于莲姆老祖的传说中,莲姆老祖用竹管控制蜜蜂和召唤孩子,后来竹管就演变成了唢呐。唢呐曲调的命名和白依人神话中的族群迁徙事件关联。《得胜令》源于蜜蜂驮着白依人聚拢飞过火海时的情节;《过山调》源自蜜蜂听到竹管声,精神振奋飞过高山的情节;《过江调》则是源于蜜蜂飞过金沙江的情节。
唢呐在白依人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首先,它是一种具有告知性的工具;其次,唢呐是办事方与其他人之间协作秩序的象征;最后,唢呐是白依人恰当安排社会事件进程的手段。白依人的结婚过程由唢呐演奏不同的曲调来进行协调。如《三吹三谈之头牌》就是暗示其他人这里要办婚事了;《迎客调》就是客人来的时候吹的调子,欢迎客人,也告诉主人家客人已到,要准备出来待客了;《出菜调》彰显的是出菜的过程等。唢呐在白依社会中还具有指令的作用,就像神话中表达的一样,是白依人维持仪式秩序的重要手段。
四、白依人历史记忆的身体实践
身体实践是无文字民族历史记忆传承的重要渠道,“在习惯记忆里,过去似乎沉淀在身体中”。保罗·康纳顿将身体实践记忆分为刻写实践和体化实践,刻写实践是指在身体举动之外,记录信息行为的结果;体化实践是指通过身体举动来传递信息的行为。记录行为的结果表现为独立于身体之外的文本、符号和线条等,属于刻写实践记忆。动作或是口述发声均是借助身体来完成,属于体化实践记忆。“在所有文化中,对于权威的编排,大多通过身体的姿势来表达。在这项编排中,有一整套可辨认的姿势,由此,直立的身姿表现出诸多有含义的弯曲,让许多姿势操演变得有意义。”(13)[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1~92页。两者对于历史记忆的传承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白依人的身体实践主要表现为体化实践记忆,即舞蹈和古歌。
(一)“苏别阿哩噜”的舞蹈记忆
舞蹈是一种仪式的表达形式之一,这是一个群体对于自己族群历史记忆的外化。“苏别阿哩噜”是白依人每年正月初三进行的群体性祭祀舞蹈。整个舞蹈全程分为三场,第一段主要叙述了从莲瓦塔鲁迁徙而来的过程。第二段主要反映白依人生活在天地间,与恶劣环境抗争的故事。第三段主要表达一年的主要节气以及相关农事活动。
“苏别阿哩噜”起源神话所赋予的神圣性使得该舞蹈仪式成为了白依人消除灾难的一种固定集体仪式。高金和、绞雄才收集整理“苏别阿哩噜”的起源神话有五个版本。主要内容是白依人字、罗两兄弟捡到了金沙江对岸永胜莲瓦塔鲁的人送瘟神用的两只羊,导致全村的羊都得了瘟疫,后来朵觋(巫师)让大家跳“苏别阿哩噜”驱走瘟疫。从故事的叙事内容看,“苏别阿哩噜”的起源神话涉及白依人的迁徙、瘟疫主题。舞蹈表演中的内容与神话中的情节能够逐一对应,以身体动作和表演回溯了白依人族源神话的族源、迁徙、瘟疫的记忆。
(二)“苏别阿哩噜”的古歌记忆
在“苏别阿哩噜”舞蹈中,白依人咏唱特定歌词旋律的古歌。古歌也分为三段,叙述了白依人族源、迁徙和农事活动的历史记忆。
正月到哟正月到,正月初三办大会,我们今天来聚会,我们是从哪里来,
我们从莲瓦塔鲁来,大山深箐都跨过,下坡遇到大江隔,金沙江上划船过
……
正月到哟正月到,正月一到我们到,今天来到好地方,正月初三办大会,
我们今晚大聚会,为因大会才相遇,谁个有情我有情,谁个能干我能干
……
正月到哟正月到,正月过了二月到,二月一到春分到,春分之前春雀到……(14)高金和等:《鹤庆白依文化研究文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242页。
从古歌主体结构来看,白依人族源神话、社会文化和生产习俗等被贯穿在二十四节气的描述中,这体现了白依人借用其他民族的文化来建构本族群文化的痕迹。古歌从形式上看似乎是一种久远的记忆,但是这种记忆的建构却与他们同其他族群的交流互动历程关联在一起,如同一种为实现族群文化建构而被发明出来的传统,是一种身体动作与口述表达的结合,延续了传统的娱神与祭祖作用,同时为白依人的历史记忆提供了延续空间,族群历史记忆在其中传承、延续和深化。
五、白依人的婚丧仪式操演
康纳顿认为仪式不仅是表达性的,而且是程式化的;不仅是形式化的,而且是实质性的;其效用不限于仪式场合,也渗透在非仪式性行为和心理中。(15)[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仪式不仅是作为一个回忆对象的象征性存在,而且是作为那个对象本身的延续存在。通过神圣空间和时间中的仪式过程,回忆对象在此世中被回溯和唤起。白依人对唢呐和火草衣有着特殊的情结,神圣器物和身体记忆贯穿在族群的生活庆典仪式中。
(一)婚礼仪式
婚礼是人生的三大过渡礼仪之一,对于社会成员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白依人婚礼仪式的主体、构成要素和仪式过程均体现着神话中的祖先记忆。白依人婚姻形式主要有“男娶女嫁”和“上门”两种。婚礼程序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天,用松针搭棚,进行准备活动;第二天,祭门神、送火草衣、待客、演板凳戏;第三天,祭祖。在祭门神环节,白依人会唱着歌送杉木。因为在白依语中,“杉”与“伤”谐音,意思要把不吉利的送走,免除灾难。歌词的汉语大意如下:“开花金蜂飞来采,采到金花成一对……”体现了对蜜蜂在迁徙路线中的作用及其后世影响。在送火草衣环节,女方会给男方直系亲属每人织一件火草衣。另外,还要给介绍人、唢呐师傅、总调度等赠送火草布。在婚礼期间伴郎要用这块火草布绑一朵花在手臂上,以表明自己代表着新娘在场。(16)高金和等:《鹤庆白依文化研究文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219页。婚礼中的《赠衣调》在拜堂后吹奏,此时女方要双手将火草衣举过头顶,赠送给男方直系亲属。在待客环节中,唢呐师傅按照顺序吹奏《迎宾调》《敬烟调》《敬茶调》《亲家好调》《安席调》《上菜调》《敬酒调》和《慢吃慢饮调》等,服务人员也按照此顺序招待客人。唢呐的吹奏曲调变化代表着宴席进行的不同阶段。
(二)丧葬仪式
丧葬是社会成员去世之后,亲属或者亲密关系的人为其举办的追悼性质聚会。丧葬仪式不仅是一个群体对待逝者去往另外一个世界的态度,也是一个群体宗教观念和人生态度的体现。白依人丧葬普遍实行土木棺葬。他们十分看中丧葬仪式,仪典也极为隆重,可分为穿衣、入殓、祭奠、送灵和上坟等步骤。
白依人葬礼中的火草衣是对族群祖先记忆的回溯,揭示着与死者的亲戚及其它社会关系的网络。白依人一般会为老人准备白依语叫“目旺铺”的孝布(火草布)。老人去世后,家人拿孝布给逝者的姑爷和后家缝制孝衣(匹亚波)。葬礼当天,孝子跪在灵柩前双手托着孝服向姑爷送孝服。逝者要穿戴火草衣,之后用棉絮包裹遗体,以火草布盖脸。出殡前最后祭奠和送葬仪式中,已婚孝子、逝者平辈和下辈已婚男亲戚,都要披“匹亚波”孝衣,葬礼结束收拾好装在柜底。每个已婚的男人终生都只有一件“匹亚波”。葬后第七天要上坟祭奠,葬礼当天接受孝服的家庭,要牵一只山羊来坟上祭奠,都要着火草麻布孝衣。
丧礼仪式中以唢呐曲调来调控仪式进程,这些曲调与白依人的迁徙记忆具有某种关联。如丧礼中的《过江调》展现了白依人迁徙的神话。唢呐师傅认为“我们从莲瓦他鲁来,我们在永胜住,蜜蜂把我们带来这里,我们的祖先都要把它的灵魂送回去。”吹《过江调》的意义在于回溯族群的迁徙过程,并将亡者的灵魂送过金沙江,回到莲瓦塔鲁。
六、结论
历史记忆是一个群体所共享的文化和思想意识,但这种抽象的意识不是封闭和不可理解的。人们通过象征手段来表达关于文化和观念等意识的意义系统。因此,历史记忆也可以运用具体的象征性符号、行动和仪式过程表达,即通过器物载体、身体实践以及仪式行为等存储和传承文化信息。我们通过探讨象征性表述中呈现的意义系统,可以理解在器物和行动背后所要表达的深层文化意识。
白依人族源神话是以象征性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的呈现,主要承载于神圣器物、身体实践和仪式操演等层面。在器物层面上,唢呐作为莲姆老祖控制蜜蜂的工具,后延伸成为庆典和社交场合中的重要乐器;火草衣是白依人日常生活中的服饰,也是仪式典礼中的礼服和礼物;女性衣服款式模仿蜜蜂,日常头饰更是蜜蜂形象的象征表达。在身体实践层面上,白依人的群体性祭祀舞蹈“苏别阿哩噜”以身体实践的方式将历史记忆沉淀在身体中,内容、结构以及组织方面均与白依社会中的族源神话关联在一起。其中较为典型的白依人渡江、飞翔等象征性动作,均是对其族群祖先和迁徙记忆的回溯。在仪式操演层面,婚礼、丧礼中整合了器物和神话情节等记忆要素,唢呐作为婚礼和丧礼中的主导,控制着仪式的进程和对应内容。火草衣作为仪式中的重要礼物在不同的程序中出现。白依人族源神话是整个族群历史记忆的基石,其中唢呐象征了引领整个族群的工具,火草衣则是对祖先记忆的回溯。围绕着族源神话,白依人的历史记忆在生活实践中传承,他们生活中的观念和行动等很大程度就是历史记忆的影响和再现。
白依人世代传递的历史记忆具有其内在的意义系统,它以象征性展演方式呈现着关于族群的特定文化意识。这种象征性的展演方式是族群表达关于社会生活根本性问题的重要策略。因此,白依人以象征方式在生活实践中展演自己与祖先之间的关联。一方面他们在此世时空中,实现了人际间的沟通,达成意识的统一,完成社会整合。另一方面,他们也在此世中,与彼岸祖先建立关联,实现祖先在此世时空中的延续,发展出与祖先关联的人生观念、社会生活态度以及对彼岸祖先的期待。白依人在族源神话的象征性展演中,建立了一种此世族群与彼岸祖先相互关联的社会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