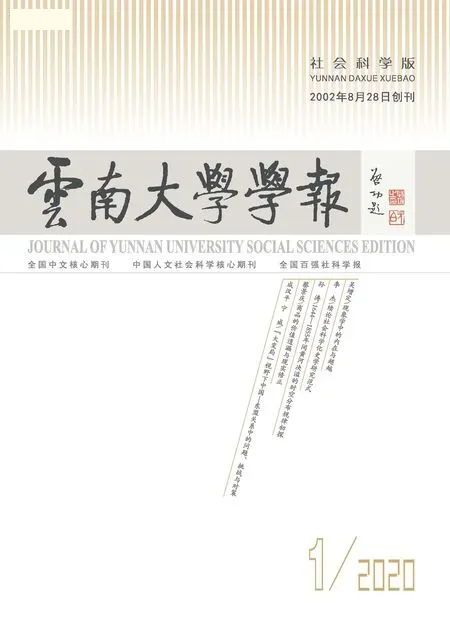试论冯友兰与唐君毅的道德观之异同
——以《新原人》与《道德自我之建立》为中心
欧阳祯人,李 想
[武汉大学,武汉 430072]
冯友兰在完成《中国哲学史》后,转向理论创作,在抗战的刺激下,“当百代之巨变,对千古之遗踪,昔所怀而未达,今受感而始通”,(1)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4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96页。他先后撰出后来的《贞元六书》,提出以“道德之理”和“觉解”论道德与人生境界的独特见解。同一时期,唐君毅有感于人生的困惑,开始将对道德与人生的反思写出,其后结集为《道德自我之建立》,他用“自觉”论道德及其超越。冯、唐二人面对人生问题所给出的相异的观察与思考,不啻为“新理学”与“新心学”的典型看法。现代新儒学内部的这种对道德问题的不同观点,是进一步思考儒家道德哲学的源泉活水。
一、 以觉解和心之本体的自觉论道德
冯友兰本着“新理学”的实在论倾向提出道德之理,称:“一切道德底行动之所同然者是:一社会之分子,依照其所属于之社会所依照之理所规定之基本底规律以行动,以维持其社会之存在。此可说是道德之理之内容;依照道德之理之行动,是道德底事。”(2)冯友兰:《新理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11页。冯友兰认为道德属于社会,不能离开社会论道德,依据道德之理而行,就是道德的行为。可见,他是从社会的角度或客观的角度论道德,但道德需要落实到人的主观,从而有“觉解”说:“人是怎样一种东西?我们可以说:人是有觉解底东西,或有较高觉解底东西。若问:人生是怎样一回事?我们可以说,人生是觉解底生活,或有较高程度觉解底生活。”(3)冯友兰:《新原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2-13页。“凡可称为道德底行为,必同时亦是有觉解底行为。”(4)冯友兰:《新原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7页。冯友兰认为人是有觉解的动物,解是概念活动即理性认识,觉则是一种心理状态,惟人有觉解的行为,才能有道德行为,否则至多有客观上合乎道德的行为,不能有主观上出于道德的行为。正因为人之觉解不同,宇宙人生才会呈现不同的意义,人遂有不同的境界,所谓的自然、功利、道德和天地境界生焉:“境界有高低。此所谓高低的分别,是以到某种境界所需要底人的觉解的多少为标准……自然境界,需要最少底觉解,所以自然境界是最低境界。功利境界,高于自然境界,而低于道德境界。道德境界,高于功利境界,而低于天地境界……至此种境界,人的觉解已发展至最高底程度。”(5)冯友兰:《新原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50页。他以觉解的不同划分境界的高低,自然、功利、道德和天地境界依次增高。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这一价值次序的增高,可视为“我”之发现历程,如人在自然境界中依顺习惯本能行动,不知有我,但“就有我无我说……在功利境界中,人有我。在此种境界中,人的一切行为,皆是为我……在道德境界中,人无我,其行道德,固是因其为道德而行之,即似乎是争权夺利底事,他亦是为道德目的而行之。在天地境界中,人亦无我。不过此无我应称之为大无我”。(6)冯友兰:《新原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54-55页。在他看来,在功利境界中出现“我”即有对“我”的偏爱,只可名之为“有私”,道德境界时则能超越“有私”之我而动,可谓“无我”,天地境界中时人能“大无我”从而“有大我”。冯友兰所谓“觉解”程度的高低也是“我”或“真我”“大我”之由隐而显的过程,“上所说底四种境界,就其高低的层次看,可以说是表示一种发展。此种发展,即是‘我’的发展”,(7)冯友兰:《新原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56页。可见,冯友兰对觉解与“我”的关联有清晰的认识。
“大我”并不代表冯友兰承认超越的“本心本性”,他强调从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论道德,人心不可离开其结构而论:“我们不能承认有宇宙底心……心之实际底有,必依一种实际底结构,即所谓气质者。心理学或生理学所讲之神经系统等,虽不即是此种结构,但可是其中一部分,或至少亦是此种结构之所依据。”(8)冯友兰:《新理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07页。冯友兰认为心必须依赖气质,只有动物或高级动物才有实际的心,虽然它有知觉灵明,仍不能无物质的限制,故不承认“宇宙底心”,不认可本心概念。他以为不可脱离所属的社会来阐释人性:“人于‘知性’时,他知社会不但不是压迫限制个人底,而且个人惟在社会中始能完全……不但是社会底是人的性,人并且能觉解是社会底是人的性。他有此等觉解而即本之尽力以做其在社会中应做底事。此等行为即是道德底行为,有此等行为者的境界是道德境界。”(9)冯友兰:《新原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06-108页。在他看来,人是社会的一分子,在社会中人才成其为一完整的人,因而人性必然包含群的成分,即“是社会底是人的性”,而且人也能觉解到这点,自觉到人性必然包含群性,准此觉解而遵循社会之理以尽其责任就是道德行为。由此可见,冯友兰的觉解是限制在社会之中的觉解,而通过觉解能更好地实现社会之理。所以,冯友兰虽然认识到人之觉解意味着“真我”的发展,但他并不将“真我”挣脱社会宇宙大全的限制,不将“真我”判为无限,“真我”随其觉解对象的扩大虽有所发展或提升,但它永不能突破所觉解的对象,不能为所觉解到的社会之理与大全。
唐君毅则从另一角度考虑道德,主张其本质为“自觉的自己支配自己”,(10)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唐君毅全集》(第四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14页。唐君毅对于道德本质的界说表明道德关联于自律,其中,“自觉”乃异于纯粹的生物本能,“自己支配自己”即支配的本源在己在内,“自己支配”为令由己出,“支配自己”即令由己从,所以他称:“我界定道德生活,为自觉的自己支配自己之生活,亦与其他哲学家,所谓……道德生活是自律的生活,而非他律的生活之说同。”(11)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唐君毅全集》(第四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5页。唐君毅虽也强调“自觉”,但其“自觉”所强调的是心之“能”,异于冯友兰的“觉解”对心之“所”的强调。唐君毅关于“自觉”的关注,更多地展现为对道德行为的共性即“超越现实自我限制”的阐释,尤其是对“超越”的阐发。他认为对时空中世界的流转或生灭产生不满,蕴含着人有超越现实世界的愿望:
然而当我想到我之此要求亦可由生而灭时,我对其可由生而灭之虚幻性,又有一种不满,而表现出一更高的要求……因我之此要求,如果只是一现实世界之心理事实,它如何能永远位于现实世界之上,对于整个现实世界,表示不满?……我于是了解了:我之此要求,必有其超越所谓现实世界以上的根原,以构成其超越性……我想它不能在我自己之外。因为我不满意我所反对的现实世界之生灭与虚幻,即是我希望之现实世界生灭与虚幻,成为像此恒常真实的根原,那样恒常真实。我之发此希望,即本于此恒常真实的根原,渗贯于我之希望中……我于是了解了,此恒常真实的根原,即我自认为与之同一者,当即我内部之自己……此内部之自己,我想,即是我心之本体。(12)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唐君毅全集》(第四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72-73页。
在他看来,人对流转与生灭产生不满,遂有使此世界真实、善和完满的要求和心愿,它不能仅是现实世界中的心理事实,它若也随现实世界而流转或生灭,人怎能对整个现实世界产生不满,以至于对不满的消失亦产生不满。这一不满不因现实自我的流转、虚幻而改易,必有超越的根源,此根源又不能在自己之外,不然我何以产生对现实世界之生灭与虚幻的不满,我希望虚幻生灭的现实世界能像恒常真实的根源那样完满真实,我只能本此恒常真实的根源来希望,或此恒常真实的根源渗贯于我的希望之中,质言之,恒常真实的根源是我内部的自己,就是心之本体。由此可见,唐君毅通过观照人心的存在状态,揭示出他所认为的心之本体为人之恒常真实的根源,心之本体是无限的、至善的,道德行为在于超越现实的自我而复归到形上自我,复归超越的心之本体。
然而,无限的心之本体何以要在现实的限制中表现,何以不直接表现出其无限性而免除人之无知与罪恶,唐君毅称:
当我想到这问题时,于是我又想到我以前所说的有限与无限之联系的问题了。原来有限与无限,是一不可分的结,无限之所以是无限,即在它之破除有限。它必有限可破,然后成其无限。于是我想到了:善之所以是善,即在它之恶恶。(13)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唐君毅全集》(第四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98页。
它之无限,同我之有限,乃是一不可分的结……我不能单就它之本身看它之无限,而当自它之破除我之有限上,来看它之无限。……它必有它所破除之限,又必有对此限之破除,唯合此二者,而后它成为它……所以它本身一方超越一切限,而它本身之表现又内在于一切限……至于我们所要求的所谓它之积极的无限之表现,即等于要求它不在限中活动,此即无“限”可破。……我们当一方面,就它本身说它是积极的无限,而在另一面就它表现说,它只是不断的克服破除限,只具消极的无限,不断的使限渐无,然终若余限在外。(14)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唐君毅全集》(第四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87-89页。
第二段论述了第一段中提到的“不可分的结”这一问题,无限有特定的表现形式,不能将无限与有限分开来看,亦即无限之为无限要表现于对有限的破除。唐君毅认为无限的心体联系于有限的身体为一事实,心体的无限含义是不受限,但要在有限中活动,换言之,它表现于对现实自我的层层限制的超越,因此,现实自我的限制就在这一超越限制的活动中得其意义,其意义就在于将被破除、超越,反之,若无这些限制,就无限制可破,无限也将无以表现其活动。因此,肯定无限时也要肯定有限的必要性,要知道其消极的无限乃表现于对限制破除中的无限。由此可见,唐君毅所论的自觉是心之本体对现实自我的限制的超越与突破,这一过程不能悬空设想,因为积极的无限无所表现,心体的无限要通过对身体的限制的突破来表现,心之本体虽然是超越的,却表现为渐进的呈露,需经历不断地超越限制才能呈现心的无限性。可以说,唐君毅对心之本体无限的描述虽然未采用“内在超越”一词,但已充分展露出他所认为的心之本体的超越性为内在的超越性。
冯、唐二人对道德关注的着眼点并不相同,冯友兰侧重从社会的角度和道德之理的角度理解道德,唐君毅则从主体的角度来立论,前者将道德隶属于特定的社会,道德标准在于特定社会之理,目的是合乎社会之理;后者将道德诉诸人之自觉自律,表现为超越现实自我的限制,目的在于对本心本性的复归。冯友兰的觉解是在社会宇宙之理等框架下的认识体验活动,所重的是觉解的对象,此中虽有彰显“真我”的可能,但冯友兰不强调这一方面,而突出外在之理的规范作用,人性不能够离开具体的社会而论,人心的觉解活动也受制于社会之理、更不能等同于社会之理,人通过觉解社会之理而自觉遵循之即有道德行为,道德的觉解被限制在社会之理之内,其所重为理智的心灵。唐君毅则重“真我”,他通过对心的存在的观照而认定“心之本体”的存在,道德行为就展现为心之本体的无限性突破现实自我限制的过程,心体的自觉是就心之“能”上立论,自觉面对限制而又不断超越限制,其所重为道德的心灵。
二、 恶的根源
一个完善的道德理论,必会对恶的根源问题给出解释,冯、唐二人也或多或少地论述到恶的根源。冯友兰认为道德的行为是觉解行为,但依觉解的程度可划分不同的境界,在自然与功利境界中,人由于觉解程度较低甚至无觉解,至多关注于自身的利益,尚不能完整觉解到人之为人的本质,未觉解到人必要依赖社会才成其为人,故此他们的行为并非道德的行为,冯友兰称:“在自然即功利境界中底人,在表面上看,虽亦可有尽伦尽职底行为,但其行为,只是合乎道德底,而不是道德底。一个人的‘我’的高一部分所作底选择,就其人自己说,都是无所为底。一个人的‘我’的高一部分能作无所为底选择,即是所谓意志自由……即中国道学家所谓自作主宰。”(15)冯友兰:《新原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22-133页。在冯友兰看来,自然和功利境界中的人缺乏真正自作主宰的“我”,功利境界中所觉解的只是“我”的较低部分,其行为虽然能够合乎道德律,但并不是道德的,道德的行为要出自“我”的较高部分的自作主宰,即出于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可见,冯友兰实际上所要表述的是自然与功利境界根本缺乏真正的道德主体,即未觉解到“我”的较高部分,不能视为有道德的行为。故冯友兰不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这些行为,他称:“在自然境界及功利境界中底人,对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并无觉解……是在梦觉关的梦的一边底境界。在道德境界及天地境界中底人……是在梦觉关的觉的一边底境界。”(16)冯友兰:《新原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50页。
在道德行为中,人虽然有真正的道德主体,对社会之理有充分的觉解,但仍不免有“知而不行”或不当行而行等不道德行为的发生,冯友兰阐释道:
为尽伦或尽某职,应该做些什么事,即平常人亦很容易知之。他们虽知之而不能行之。这是因为他们是“自私”底。就所谓“我”的“自私”之义说,他们是有“我”底。明道《定性书》又说:“人之患莫过于自私而用智。”人有时虽明知某种事应该做,但因受“自私”的牵扯,而不能做之。他有时虽明知某事不应该做,但因受“自私”的牵扯而不能不做之。人于此等时,往往要找许多理由以为自己解释。这许多理由就叫“用智”。为自己解释,若向别人说,即是欺人。若向自己说,即是自欺。(17)冯友兰:《新原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51-152页。
冯友兰敏锐地觉察到人对某些事明知应做而不做,某些事明知不应做而未免于做,过恶就这样产生,他将过恶产生的原因归于人之“自私”,联系到他将“我”区分为较低部分与较高部分,则所谓人的“自私”则是人颠倒了道德主体的位置,本应作为道德主体的“我”的较高部分退出了道德行为,而“我”的较低部分却充当了道德主体,可以说,冯友兰实际上将恶的根源归咎于道德主体的颠倒,这是“自私”说的真正意涵。由此又衍生出“用智”,“用智”是用似是而非的理由对“自私”的文过饰非,虽明知“自私”之不应该而又文饰之,对应当之事则诋毁之,以此欺人与自欺,故而有错误的道德判断。可见,恶的根源根本原因还在于“自私”说所蕴含的道德主体的颠倒。故而,他称:“求自己的利,可以说是出于人的动物的倾向,与之所以为人者无干。”(18)冯友兰:《新原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14页。所谓“人之所以为人者无干”意谓恶出自人的动物倾向,而“真我”未能作主宰,但这句话并不包含“真我”不必负责之意,因为道德行为依赖着人之觉解到“我”的较高部分,觉解到人之为人必不可离于社会,且觉解到此觉解,否则不能视为道德行为,故而,求利等过恶之为恶就意味着要先有对“我”之较高部分的觉解,然后,此“真我”未能作主宰,颠倒了主从次序才有过恶产生。实际上,冯友兰对此的观察是相当深刻的,康德对根本恶的探讨,追溯恶的根源也不过是颠倒了道德动机的次序,(19)康德著:《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8页。当然,冯友兰以觉解这一认知的方式是否能构成他的道德洞见是另外的问题。
唐君毅认为人性是善的,他认为一切的人类活动都是精神的活动,不仅同情、节欲、求真、求善等是善的行为,“即使求个体生存之欲、男女之欲本身亦非不善。人有求个体生存及男女之欲,而后有人的生命之继续存在……求个体生存及男女之欲,间接便是高贵的精神活动之实现者。求名求权,就其最初动机言,是求人赞成我之活动,亦是求一种我与他人之精神之接触,便亦不能说定是不好……所以我们说人性根本是善的。”(20)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唐君毅全集》(第四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118-119页。唐君毅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在实质上皆具有一种超越自身的意义,即如饮食男女虽似卑下,但其却可有接触超越现实之上的生命精神的价值,借此可表现高贵的精神活动,就此而言,饮食男女的实现代表着高贵精神的间接实现,求名求权的行为亦是如此,实际上唐君毅认为一切的人类活动皆是如此,故而他主张人性根本是善的。唐君毅既然深信人性之善,就必须面对恶的根源问题,对此他论述道:
为什么人有罪恶?罪恶自何来?我们说:罪恶自人心之一念陷溺而来……我们所需要的只是解释此一念之陷溺。为什么人类由一念之陷溺,便成无尽之贪欲?……人之可以由一念陷溺而成无尽之贪欲,只因人精神之本质,是要求无限。人精神所要求的无限,本是超越现实对象之无限,然而他一念陷溺于现实的对象,便好似为现实对象所拘挚,他便会去要求现实对象之无限,这是人类无尽贪欲的泉源。(21)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唐君毅全集》(第四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120-121页。
在唐君毅看来,罪恶实际上源于人心的一念陷溺,人心之“能”本是无限的,但陷溺于心之“所”即对象上后即为该对象所限,或以此对象为无限,这便产生了无限的错置,因为人的精神所求的无限,是超越现实对象的无限,但囿于所执的对象后,以此对象为无限,事实上这误植于对象上的无限是一种虚妄的无限,这反映出,无限的精神与有限的现实自我之间的矛盾,也显示了无限的精神强烈的无限要求,但此精神的真实无限的要求未满足时便投身于现实的对象以追求无限,此就是一念陷溺的实质。这表明人之饮食男女、求权求名这些欲望本身并非恶,恶的根源不能够追溯于这些欲望,人心的陷溺才是罪恶,唐君毅称:“苦痛错误罪恶之存在根据,乃在我们之把有限的身体当作无限用。”(22)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唐君毅全集》(第四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96页。这意味着身体不是罪恶的根源,由身体而生出的欲望也非罪恶的根源,根源在于主体误把它们视为无限的。质言之,罪恶的根源就在于精神之无限妄执这些有限的对象为无限,无限黏滞于有限,自我限制于有限中,关键就在于自我限制,由此才有相应的道德责任,否则,根本谈不上罪恶,故而唐君毅称:“我们陷溺于我们之任何活动,均是罪恶。”(23)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唐君毅全集》(第四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128页。陷溺的根源既然是精神自身,那么,超脱此陷溺的根源或力量也就在精神自身,唐君毅称:“善之为善,永为人之良知之所知,自己之良心的判断与贪欲不能并存……贪欲只能在善之掩饰下的夹缝中存在,而贪欲终当为良心之光所照透。”(24)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唐君毅全集》(第四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123页。唐君毅以为贪欲终当为良知所照透、驱除,这意味着人能赖其自身而从陷溺中超脱。由此而论,恶之产生从道德行为的共性来审视则由于一念的陷溺,但若自道德生活的本质来说未必不可表述为道德自我放弃自我主宰权,亦即失却其自觉的自我支配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唐君毅的一念陷溺与冯友兰的自我颠倒有异曲同工之处。
冯、唐二人对恶的根源有深刻的观察,均以为恶之根源关联于能负责任的道德主体,冯友兰表述为“我”的较高部分,唐君毅则是精神或心之“能”。在此基础上,冯友兰倾向于以道德主体的颠倒来解释恶的根源,唐君毅则归于无限的精神妄执于有限的对象即自我限制。但二者实有可沟通之处,如唐君毅认为未能践行善的原因为:“如果你感有应当之命令又有服从他之自由,而你终不用你的自由去实现它,唯一的原因在你失去你的自由,即你为你过去所流下之盲目的本能冲动欲望所支配,亦即你已不自由。”(25)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唐君毅全集》(第四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45页。这里为盲目的本能所支配,亦可视为冯友兰所言的“我”的较低部分,如此看来,冯、唐二人皆强调不为感性活动牵引,以免丧失自主性。
三、 天地境界与精神实在
冯、唐二人均认为道德究其极不仅是社会或人生的问题,道德必要延伸到超道德的领域,有超道德的境界或意义存在,这就是冯友兰的天地境界说和唐君的精神实在论。冯友兰认为人在自然与功利境界中尚未觉解到人之为人,所以对“我”的较高部分没有觉解,而道德和天地境界中则对此有充分的觉解,所谓的天地境界是:“人对于宇宙有进一步底觉解时,他又知他不但是社会的分子,而又是宇宙的分子。”(26)冯友兰:《新原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32页。“在此种境界中底人,了解于社会的全外,还有宇宙的全,人必于知宇宙的全时,始能使其所得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尽量发展,始能尽性。”(27)冯友兰:《新原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48页。在冯友兰看来,随着人的觉解的提升,认识到人不仅是社会人,还隶属于宇宙的全,宇宙在人的性分之内,社会和宇宙均与个人不相对立,人恰恰要在宇宙之全中实现人性,才能将人之所以为人者尽量发展出来,觉解到此,人将不仅对社会要有贡献,亦负有宇宙的责任。随着人的觉解的提升,实际上“我”也由隐而显、由不充分发展到完全,冯友兰称:“在道德境界中底人知性,知性则‘见真吾’。‘见真吾’则可以发展‘真我’。在天地境界中底人知天,知天则知‘真我’在宇宙间底地位,则可以充分发展‘真我’……人的‘真我’,必在道德境界中乃能发展,必在天地境界中,乃能完全发展。”(28)冯友兰:《新原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55页。依冯友兰之见,“真我”惟有在道德境界中始获发展,但只有进一步升进到天地境界,觉解到人为宇宙的一分子,才能使“真我”得到充分的发展,可见从“我”之发展的角度看,道德境界必须升进到天地境界。随着人的觉解程度的提升,具有社会价值的道德行为将提升到具有宇宙价值的超道德行为,此中的缘由冯友兰论道:“人的肉体,七尺之躯,诚只是宇宙的一部分。人的心,虽亦是宇宙的一部分,但其思之所及,则不限于宇宙的一部分……自同于大全,不是物质上底一种变化,而是精神上底一种境界……在精神上他可自同于大全。”(29)冯友兰:《新原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44页。冯友兰在肉体与心之外,又开辟出一精神的领域,一方面心可以大全为对象而知有大全,另一方面又知道大全不可思考,合此两面冯友兰得出人之精神可以自同于大全,这是冯友兰的深刻洞见,如此精神似能超脱气质的限制,但他强调精神应属于心本身的功能或认知作用,仍不应视之为超越的“真我”或本心本性。
然而,人有高一层的觉解升进到天地境界后,其行为并没有改变,所改变的是行为本身的难易及其意义,冯友兰论道:“在道德境界中底人,于不计较对于自己底利害,以有道德行为时,他须作一种特别有意底选择,须有一种努力……在天地境界中底人,行道德底事,则无须如此……利害不足以介其意,并不是由于他是冥顽不灵,而是由于他觉解深,眼界大。”(30)冯友兰:《新原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52-153页。冯友兰认为人因觉解深、眼界大,行为可以由“应该”行转为不勉而中。道德行为的意义也可因此提升,他称:“尽人职人伦,是道德底事。但天民行之,这种事对于他又有超道德底意义。张横渠的《西铭》,即说此点……此篇的真正好处,在其从事天的观点,以看道德底事。如此看,则道德底事,又有一种超道德底意义。”(31)冯友兰:《新原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38-139页。冯友兰认为天地境界所改变的是人的觉解程度以及看待事物的观点,天地境界中人是从宇宙、大全、理和道体的角度看待道德行为,道德中的尽伦尽职,获得了天伦天职的超道德意义。所以,冯友兰所强调在道德领域外,还有一超道德意义的领域,这就是天地境界,人生的意义世界不为道德价值所封限,必要透达到超道德意义的领域。
唐君毅认为人从外面看是时空中的物质存在,但自内部看,则为精神存在,他称:“人的精神不是有限,因为人要求无限,表示他要求自由……人在根本上是精神、是自由、是无限,而非物质,非不自由。”(32)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唐君毅全集》(第四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107页。“人的宇宙是一群精神实在,互相通过其身体动作,而照见彼此之精神的‘精神之交光相网’。由此精神之交光相网,而见有一共同之形而上的精神实在之存在。”(33)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唐君毅全集》(第四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108页。在唐君毅看来,人从内部看是一超时空的精神存在,人虽然有时空中的物质存在,但人在根本上是精神、自由,因为身体是精神的表现途径,甚至身体所关联的一切外物也可称为精神交流的媒介,身体的意义在于表现精神为精神所渗贯,人们之间通过精神的交流互见对方精神的流注,由此看出有一共同的形而上的精神实在存在。可见唐君毅以精神与身体的交织并存论述精神,故而他将心之本体转为精神实在,他认为精神实在和现实不即不离,他称:
所以超越的精神实在与现实世界,自始是相连。只是又不能由它们之相连,而说他们是一。它们是二,而后才有所谓连。它们之相连,又不是有连之的第三者,而是即在现实世界之向上超越的关键上,便连起来。但因为它们相连,故就此连处说,又不能说它们是二,它们是二,是二而不二。所以精神实在即现实世界之本体,现实世界即精神实在之表现或妙用。(34)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唐君毅全集》(第四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126页。
依唐君毅之见,超越的精神实在与现实世界始终相连,但并不能因之视它们为一,它们之相连非因第三者而相连,是在对现实世界的超越上表现精神实在,即就此相连以见出超越关系。对现实世界的重重超越突破也是精神上升之路,每人的身体结构与所处环境不同,精神上升之路容有不同,但都是不断从陷溺中超脱,由陷溺到不陷溺的天理流行过程,均为对私的逐渐化除,逐渐超升于表现为最纯粹的精神活动、最纯粹的爱,最后将形而上的精神实在实现于人格,唐君毅决不主张人出世以接触和实现形而上的精神实在。这表明,精神实在不仅是人的本体,而且是现实世界的本体,现实世界是精神实在的妙用,就此而言,物质形色的世界可视为人我精神交光的媒介,物质可化为精神之用,即物质而不见物质而见精神实在。可以见出,唐君毅认为人的道德行为实际上即是逐渐实现超越的精神实在的过程,唐君毅称:“天性,要使之扩充,然后其量乃大,大至其极,是为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之仁心。”(35)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唐君毅全集》(第四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116页。“我们只要不陷溺于我们之活动,则我们一切之活动,便都是形而上的精神实在之表现,便都是上升于形而上的精神实在之活动,而超越现实世界之活动。”(36)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唐君毅全集》(第四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131-132页。这一充其极的过程,以精神实在为依据与目的,经由道德意志的自觉、人格的自觉,以有真正的自尊和自信,从而信人,最终归结于爱人之德和爱人以德,共同体现人我合一的形而上的精神实在,忘物我之对峙,顺理本身而活动,甚至就是理通过人心在活动。这就是唐君毅理解的最纯粹的爱的最高表现,表明人的道德行为将精神实在表现于人格,接近绝对和谐的理想圣贤人格,从而不同的人格能相互了解、欣赏,唐君毅称:“各人努力求其人格之上升至真实的态度,与不同人格间互相欣赏之审美态度,合以助各人之实现至善,使各种人的人格以其心量互相贯通涵摄,以化社会为真善美的社会,是即为统一的精神实在之至真至美至善之实现的道路。”(37)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唐君毅全集》(第四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134页。所以,唐君毅认为道德精神上升之路通达于这一表现真善美的人格世界或道德世界,即道德而现超道德界域。
冯友兰认为道德境界要进到天地境界,才能使“我”有充分的发展,而从天地境界看道德行为,它就有超道德的意义。唐君毅将道德行为视作对现实世界本体的复归,道德行为有其超越的形上本体的依据,亦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就此而言,二人颇为相近,均不以道德为限,而思考道德所具有的超道德或形而上的意义。
四、小 结
冯友兰从人的觉解与社会之理来论道德,关注的更多是心所觉解的对象;唐君毅则从心之本体与精神实在来看道德,从心之能方面寻绎。可以说,一重理智的心,一重道德的心,二人形成绝大的反差。但在恶的根源问题上,二人均表现出深刻的洞见,又有可沟通处,不仅如此,二人对道德行为的超道德意义与形而上意义的关注也颇为相近。冯友兰由于其后的处境阻滞了其思想进程,唐君毅则迎来了曲折的思想进境,不能不使人有“旸谷”与“崦嵫”之叹之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