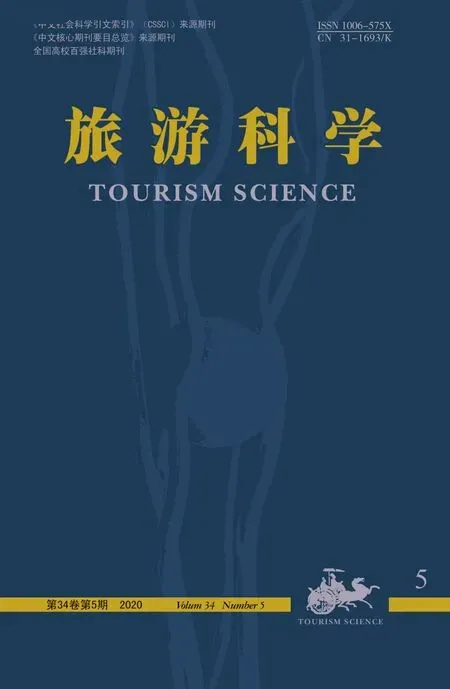话语阐释与权力实践:国家公园的理论旅行
李正欢 赵宇辰
(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天津 300222)
0 问题的提出与理论分析工具
“国家公园”一直被称为“美国人的发明”(Nash,1970),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设立“国家公园”,这一概念也跨越不同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扩展,并逐渐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生态保护模式。有趣的是,众多国家在官方话语层面上均接受了“国家公园”这一普遍概念,但又彼此心照不宣地根据自身的经济、政治、自然、社会等实际情况进行话语重构与实践,使得这些形式不同的“国家公园”在看似统一的名号之下都可以“相安无事”。这一现象同萨义德(Said)于1982 年提出的“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有许多相似之处。“理论旅行”认为各种观念或理论能通过有意或无意地影响、创造性借用或大量挪用等形式,实现人际间、境域间及时代间的穿梭旅行,一种理论到了不同的环境中,总是要经历一些改变,以适应新的环境,发挥新的用途(萨义德,2009)。萨义德(2009)使用历史分析方法提出了理论旅行的基本步骤:第一,有一个起点或类似起点的发轫环境,使得观念能够在其中生发并进入话语;第二,有一段得以穿行的距离,一个充满各种语境压力的通道,使观念从之前的时空点移向后一个时空点,并使其重新凸显出来;第三,在新的时空下,观念将会面对各种所谓的接受条件或抵抗条件,也正是这些条件才使被移植的理论或观念无论显得多么异样也能得到引进或宽忍;第四,完全(或部分)被容纳(或吸收)的观念因其在新时空中的新位置和新用法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理论旅行”自提出后迅速成为人文社科领域考察概念与理论之跨时空旅行的重要工具,不少研究据此梳理各领域相关概念或理论的跨时空旅行(翁时秀,2018)。在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国从国家层面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意味着国家公园这一概念及其相关体系即将在中国落地。因此,本文以“理论旅行”为理论分析工具,从历史分析的角度了解国家公园概念的发展缘起及其在全球各国流动与生产的图景,探索其旅行的规律和主导因素,为中国发展国家公园提供一个借鉴视角。
基于对现有文献的考察,运用“理论旅行”工具来考察国家公园概念的跨时空扩展,需要厘清4 个核心问题:(1)何种理论会发生旅行?萨义德的“理论旅行”专注于探讨某种理论或概念在不同时空是如何被转换和接受的,但为什么有些理论或概念会流动,有些又不会流动?如果是自然流动,为何有些国家接受而有些国家不接受?为何不同国家接受的时间存在差异?如果不是自然流动,国家公园这一诞生于美国的概念为何可以流动到其他国家?是否这一概念本身具有某些能够流动的特质?(2)理论旅行的路线如何展开?萨义德主要关注的是理论在欧洲范围内的“线性”旅行,但当国家公园概念在全球进行扩展时,旅行的路线显然是“非线性的复杂组合形式”(闵冬潮,2014),尤其是国家公园概念能从美国流向其他国家,首先源于不同国家对这一概念的价值诉求,继而得以突破地理边界,实现跨国旅行。因此,有必要考察国家公园概念的旅行路径,并分析其是否具有一定的规律性。(3)是什么在推动理论的旅行?在萨义德看来,“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既无起点也无终点的过程。当国家公园概念旅行到另一个时间和空间,会被选择、接受、转换、应用(或拒绝)(闵冬潮,2014)。但不同于其他概念的“理论旅行”,国家公园概念在新的时空语境中不仅仅只是单纯的理论知识生产,还需要将新生产的知识话语落地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话语,实践性使得权力成为推动或阻碍旅行的中介机制,因此有必要研究国家公园概念旅行中的权力实践。(4)如何批判地审视旅行中的理论?萨义德强调对待旅行中的理论必须时刻保持批判意识,如果不加批判地、重复地、毫无限制地使用一种理论,它就完全可能在旅行过程中被简化,或被编码,或被制度化(翁时秀,2018)。理论旅行要求的批判意识本质上需要捕捉到建立于各种具体情境之上的经验阐述及其对于理论的抵抗能力,要使理论向历史现实敞开,向社会和人的需要与利益敞开,而不是盲目接受理论(闵冬潮,2014)。因此,在中国语境中,亦需基于具体时空情境来发展国家公园,使之能向中国的历史现实敞开。
基于上述4 个视角,理论旅行为考察国家公园概念在全球的扩展提供了一个分析视角,本文也围绕以下4个问题来展开:(1)国家公园这一概念为何诞生于美国,从而成为萨义德所说的“理论”。(2)国家公园概念如何从美国到达其他国家?其旅行路径是否存在规律性?(3)国家公园概念在全球得以旅行,是什么参与和控制了这一概念的知识生产与话语阐释过程?主导这一过程的权力实践是什么?(4)中国应如何对国家公园概念保持批判意识,从而建立适应于中国国情的国家公园理论。
1 创造于荒野:国家公园概念的“无中生有”
任何一个概念或思想的诞生都是某种时代背景之下的产物,国家公园的诞生亦具有鲜明的“美国特色”。
1.1 荒野的“无用之美”
美国的历史与荒野息息相关,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历史被视为文明与荒野的关系史(滕海键,2012)。然而,早期欧洲传统文化一直存在着抵制和征服荒野的偏见,北美大陆的早期移民更是延续和强化了这一偏见(Woods,2017)。对自然与荒野的征服导致美国出现了日益严重的资源利用危机,使得美国开始重新思考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美国的荒野中除去有利用价值的“荒野”,还有大量在功利主义者看来毫无开发价值的“无用之地”。受18 世纪末期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荒野等自然从“恶的象征”转而成为文学、艺术、哲学、美学等领域欣赏与赞美的对象(高科,2019),精明的实用主义者也早已发现了拟建国家公园所处荒野的美学价值、环境价值与游憩价值。因此,在浪漫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推动下,大量的“无用之地”成为国家公园诞生的潜在条件。杨锐(2003)更是将美国国家公园运动的缘起归于土地资源的保护。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猛烈浪潮引发种种社会问题之时,人类中心主义所带来的“发展之痛”使人们开始转向追寻生态中心主义所构建的“无用之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被重新审视,美国广袤的荒野应运成为这个年轻国家独具特色的宝贵财富。因此,美国的国家公园不仅仅是对荒野的保护,也是“无用之美”的极佳表现形式。正是在这种“无用之美”下,国家公园的美学价值与环境价值同实用价值与游憩价值融合在了一起,使得所有人都能在形式上成为它的拥护者。
1.2 “自然景观”的风景民族主义建构
“无用之美”使得荒野成为大众欣赏的自然景观,但自然景观从来都不仅仅是自然的存在。景观人类学的相关研究已经阐述了自然景观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双重互构关系(葛荣玲,2014),作为一种话语形式和一种现实的实存与再现,自然景观一直以叙事的方式隐喻地渗透在民族精神塑造的各个层面之中。而将每个不同的个体变成一个民族的关键,便是构建一种能够维持民族内部普遍归属感的“大众符号”(苏锑平,2015)。显然,国家公园是成为这一大众符号的最佳载体。国家公园为美国公民提供了用以民族想象的物理空间和素材。“国家”二字将国家公园与州立公园在规模与地位上都做出了显而易见的区分,并且象征着国家共同体的自然化身,而以国家的名义指定国家公园,本身也意味着民族国家的重建与团结(沈兴菊等,2018)。国家公园的设立不仅为美国编织了一条维系民族国家的纽带,也为其他国家想象美国提供了载体。不需要去迎合那些强势表征者为满足他们欲望而构建的“想象的地理”(安宁等,2013),在“脱离”欧洲而寻求文化独立与国家认同的过程中,美国的国家公园很好地表征了“美国性”(Americanness)。与国家公园配套出现的探险、登山、野营、极限运动等活动,也被视为自由、冒险、开放等美国精神和文化的一部分。在自然保育思潮和生态政治学逐渐兴起的时代,借由诞生于自然荒野的国家公园,美国终于找到了能够同欧洲文化遗产相媲美的国家象征。在美国国家层面的诠释与解读下,国家公园成为美国向国民与国际社会宣布民族身份的自然表达,成为宣扬美国独立自由精神的民族纪念碑,成为建构风景民族主义的重要载体与媒介(李政亮,2009)。
1.3 “国家的公园”与“民众的公园”
1872 年美国国会通过《黄石国家公园保护法案》(Yellow Stone National Park Protection Act),强调黄石公园是出于“人民的利益与愉悦”而被批准成立的公众公园(public park)及游乐场地(pleasuring-ground),这一表述从法律层面保障了国民尤其是普通公众访问国家公园的权利。“公园”一词的诞生本身就意味着园林从特权阶级的私人产物变成了人人可以享用的公共空间,这也是欧洲景观民主思想落地开花的典型表现(高科,2019)。景观民主思想也推动了美国城市公园与国家公园的建设,强调“为了人民的利益与愉悦”而保留公共土地的国家公园运动是美国景观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早期成立国家公园的一个重要面向,由此也奠定了国家公园兼具国家主导性和公益性的特点(陈耀华等,2014)。
1.4 “保留在自然状态”与“被社会建构的自然”
美国最初建立的国家公园强调的是“保留在自然状态”的保护方式(高科,2019),黄石国家公园便强调其设立是为了保护自然奇观和自然美景,目的是为了游客的享用。早期美国国家公园的建立虽然有基于改变自然资源利用方式及保护自然的考虑,但彼时的国家公园更多被建构为“无人之荒野”(蔡华杰,2018),而世代生存于这片土地的原住民却被排除在国家公园之外。可见,美国早期创建的国家公园更多是出于对自然景观这一物质层面的保护,而附着在“自然”之上的各种意义表征使得国家公园呈现为“被社会建构的自然”。因此,美国国家公园的诞生,内嵌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审视、国家意识形态、国家利益与阶级利益等复杂因素,从而得以成为美国具有自然保育价值、风景民族主义象征、景观民主主义表征和游憩价值等多重价值面向的国家符号工具。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所提到的4个方面,实际上是合而为一的,荒野的“无用之美”是载体,风景民族主义是象征,而国家主导与全民共有是内涵,它们统一于自然保育这个核心之下,在当时时空条件下共同催生演化出了世界上最初的国家公园理念与实践。
2 “接受”与“抵抗”:国家公园在全球的初始旅行路径
Nash(1970)在解释国家公园诞生在美国的原因时,提出了4个缺一不可的因素:国民对自然和荒野的独特体验、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大量未开发的土地和足以支撑国家公园建设的财政资金。显然,大多数国家并不具备这4个条件,但国家公园概念却在诞生不久之后迅速地由美国向其他国家扩展,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公园作为一个国家符号工具,其多重价值表征基本能满足不同国家的价值诉求,使得这一概念得以在不同的时空语境旅行。弗罗斯特等(2014)曾将国家公园在全球的扩展历程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期之前,美国设立了一批代表性的国家公园,而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移民定居社会也接受了国家公园的理念;第二阶段是20世纪前半期,瑞典、意大利、罗马尼亚、希腊、西班牙、冰岛、爱尔兰和瑞士等欧洲国家也都纷纷设立了国家公园,而英国、法国这些传统的欧洲强国却选择不同程度地在其亚洲或非洲殖民地,而非在其本土设立国家公园;第三阶段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家公园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张海霞等(2010)亦参照此划分阶段对国家公园在全球扩展的阶段进行了细化。本文基于弗罗斯特等(2014)和张海霞等(2010)划分的阶段,结合文献资料对不同国家最初建立国家公园的核心价值取向进行了梳理,从时间、空间和价值取向3个角度分析了国家公园在全球扩展的路径规律,发现了4种代表性的旅行路径:游憩实用主义、风景民族主义、景观民主主义与自然生态保育主义(见表1)。

表1 国家公园在全球扩展的阶段划分与初始旅行路径
2.1 游憩实用主义:“无用之地”的旅游业之用
由表1可知,游憩实用主义大多出现在国家公园概念初创期。美国创造的“国家公园”一经诞生,便被澳大利亚(1879 年)、加拿大(1887 年)、新西兰(1887 年)等新世界国家迅速采纳,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与美国有着极为相似的背景:以英语为官方语言;拥有大量辽阔的未开发土地;拥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新近从欧洲移民过来的“移民定居社会”,故拥有更强的“民族国家意识”(弗罗斯特等,2014)。因此,这些国家效仿美国,用浪漫主义的审美价值和实用主义的休闲游憩价值,将那些看上去“毫无价值”的土地以“国家公园”这一新的方式利用起来,从而演化出游憩实用主义这一价值理念的国家公园。
加拿大的第一个国家公园是位于落基山脉北侧的落基山国家公园(后改名为班夫国家公园),它的设立反映了早期加拿大国家公园“无用之美”与“无用之用”的特征,即设立在没有价值的土地之上,而自然景观保护价值、经济价值与游憩娱乐价值是早期加拿大国家公园设立的3 条主线(博伊德等,2019)。新西兰国家公园的诞生看中的也是“无用之地”的旅游之用,新建立的国家公园只能位于那些没有农业生产价值的土地,可供定居的土地要优先于景观土地的保护,农业发展优先于旅游业的收益,故新西兰的13 座国家公园中有10 座都在无法农耕的山区之中(Warwick,2004)。并且,新西兰第一批国家公园内均设立了旅馆和招待所,可见其国家公园从诞生之初便是通过旅游业来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
2.2 风景民族主义:用风景衡量的存在
国家公园能在全球实现扩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家公园那吸引人的名号(霍尔等,2014),尤其是“国家”二字,通常意味着对民族国家身份的认同和民族主义的确认。国家公园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向外部世界发出行使领土主权的信号,或者是当某一时期国家的价值观出现危机时,将其用作唤醒民族凝聚力意识的重要工具(梅迪娜,2014)。因此,国家公园作为新世界美国的发明,却很快被与美国自然、社会、历史、经济、生态条件迥异的部分旧世界的欧洲国家所接受,其中重要的缘由之一便是看中了“国家”二字的符号表征,由此演化出了风景民族主义这一价值理念的国家公园。
由表1可知,风景民族主义盛行于20世纪初到二战结束前,采纳这一理念的国家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以瑞典(1909)、瑞士(1914)和西班牙(1918)等国家为代表,这些国家基本没有海外殖民地,并且在国际政治格局中试图保持中立,凭实力无法跻身于欧洲大国之列,但是它们认为自己国家所拥有的独特自然景观是其他国家无法企及的奢侈品,因此试图依靠国家公园制造出一种象征性的权力。例如,1898 年美西战争的失败让西班牙丧失了最后的海外殖民地,宏伟梦想的破灭让西班牙陷入了国家认同危机,于是希冀通过国家公园来增强民众对国家民俗、历史和传统的尊崇,激发爱国情怀。1918 年12 月8 日,西班牙第一个国家公园——皮科斯德欧罗巴(Picos de Europa)国家公园正式建立,这一天也恰好是西班牙宗教历史和民族独立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科瓦东加战役的1200 周年纪念日(梅迪娜,2014)。这样的时间选择显然是有意为之,反映出西班牙希望通过国家公园来唤起民族复兴主义的意识,克服国家当时所面临的价值危机的意图。第二类以冰岛(1930)、波兰(1932)、罗马尼亚(1935)、希腊(1938)等国家为代表,这些国家都曾在一战期间被欧洲其他强国击败甚至占领过,希冀通过国家公园的设立来强化其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身份(弗罗斯特等,2014)。国家公园被当作“政治处方”而成为民族文化和民族自豪感的鲜活象征。甚至在当代世界,对于置身于冲突中的国家和民族,风景民族主义依然可以作为设立国家公园的主要目的,例如2009 年阿富汗第一个国家公园班达拉米亚(Band-e-Amir National Park)在战火中成立,安宁和极致的国家公园美景不仅是国民精神舒缓的良药,更是表达国家身份的重要符号。可见,推崇风景民族主义价值的国家总是将设立国家公园与实现民族认同,彰显国家身份或强化国家认同联系在一起。
2.3 景观民主主义:公共游憩福利
风景民族主义使得欧洲小国在国家公园建设上走在了欧洲传统强国的前面。欧洲传统强国英国、法国、德国直到1951 年、1963 年、1969 年才分别在自己的本土设立了国家公园。这些国家迟迟没有接受“国家公园”这一概念的原因被归为“缺乏公共土地,缺乏美国荒野型国家公园的壮丽景色、文化自信及其他优先事项(如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和其他政治事件等)”(弗罗斯特等,2014)。以英国为例,早在美国创立国家公园之后不久,英国就采取自然保护区或野生动物禁猎区等形式来保护生态环境,并在其附属殖民地印度、斯里兰卡、苏丹、埃及等地设立了形态多样的国家公园,但直到1951年,英国才在其本土设立了首个国家公园,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折中的结果。二战结束后,战争的创伤使人们渴望得到心灵修复,重复无趣的劳动与恶劣的工作环境使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迫切需要休闲放松的场所,城市化对集体价值和民族身份造成了威胁,现代性所造成的人的异化激起了人们的怀旧心理和对自然本真的追求(MacCannell,2008)。看到美国等国家纷纷设立国家公园,英国的民众也期待拥有自己的国家公园。但英国国家公园建设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土地所有制问题,尤其是乡村土地的私有制。因此,英国试图将这二者杂糅进国家公园这一名词之内,其1949 年颁布的《国家公园与乡村进入法》(National Parks and Access to the Countryside Act 1949)便是这一理想的产物。英国通过国会法案将国家公园的土地“国有化”,但英国的国家公园实际上既不是“国家”的,因为土地并非国有;也不是“公园”,因为大面积的私人农田仍然禁止他人入内(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园管理办公室等,2015)。可见,英国国家公园理念体现着一种妥协,无论在土地权属、管理主体、经营机制方面,还是在管理运营上。这种妥协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民社会的设定下,国家当权者向公民公共休闲游憩需求的妥协。因此,英国、法国这些欧洲发达国家早期建立国家公园的目的偏向于对国家公园“公共性”“公益性”价值的挪用,从而演化出景观民主主义这一公共游憩价值理念的国家公园。
2.4 自然生态保育主义:自然资源保护与生态保育
如果说上述三条路径分别代表不同国家对国家公园经济属性、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侧重,那么对自然生态保育价值的重视则是对国家公园生态属性的强调。不过,对自然生态保育主义的认识存在自然资源保护与生态保育的分野。如前所述,美国早期创建的国家公园更多是出于保护自然景观这一物质层面考虑,这一考虑也成为众多国家最初成立国家公园的价值选择。由表1 可知,20 世纪初至二战结束属于国家公园概念的扩展期,欧洲国家在其殖民统治的一些亚非拉国家成立国家公园,其目的大多出于对当地自然资源的保护,尤其是野生动植物资源,甚至有些国家最初建立国家公园就是为了保护野生狩猎动物,以更好地发展狩猎旅游。例如,1926 年南非颁布的《国家公园法》将国家公园定义为“基于游客的权益和目的,既可以对野生动物、海洋生物进行保护和研究,也可以进行考古、历史、民族研究及其他教育科学研究的区域”(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园管理办公室等,2015)。在南非一些国家公园中,即使是狩猎这种与生态保育完全相违背的营利性项目也是被允许的。即使在国家公园的繁荣期(1945 至今),不少国家最初建立国家公园的目的仍然以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为主。
国家公园理念随着时间演进,在经历各国自身纵向发展的同时,在横向上也受到国际自然保护思想的影响。一些拥有自然保护传统或较晚设立国家公园的国家,最初设立国家公园便是看重其生态保育价值。例如韩国设立国家公园的重要思想基础便是崇尚自然的传统,加之智异山滥砍滥伐森林的现象十分严重,当地村民迫切希望能够从国家的角度保护山林的优美自然风光,由此诞生了韩国第一个国家公园——智异山国家公园(Jirisan National Park)(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园管理办公室等,2015)。日本于1934年设立了第一批国家公园,尽管有人将之解读为军国主义的象征(霍尔等,2014),但日本的国家公园将保护独特的自然生态作为首要目的,其颁布的《国家公园法》关于自然保护的条款、对破坏自然景观的惩罚及对相关环境指标的控制和监控,相较于大多数国家来说都是十分严格的(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园管理办公室等,2015)。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和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等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在推动国家公园从强调自然资源保护到自然生态保育转向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致力于构建全球认可的自然保护话语体系,为世界各国国家公园保护提供经验指导与资金支持(Thomlinson,2012)。1959 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发出了建立国家公园的呼吁,1962 年在美国西雅图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公园大会,使得1961 年至1980 年共有45 个国家或地区在其本土首次设立国家公园(吴承照,2015)。在国际组织和各国国家公园实践推动下,自然生态保育成为全球国家公园概念的共同核心话语。
国家公园在不同国家的理论旅行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4 条旅行路径反映出各国最初建立国家公园时对美国国家公园不同价值的“借用”。值得一提的是,4 条路径反映的是各国在初创国家公园之际的价值排序而非单一的价值选择,在众多国家的实践中,基本都有对自然生态保育、风景民族主义、景观民主主义和游憩价值等方面的多重考量,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会不断调整价值排序,使之成为顺应本国经济、政治、社会、生态价值发展需要的工具。第二,“国家公园”这一概念在全球的扩展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即各国的理论起点并非都是美国,而有可能受彼时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影响。第三,相同路径中不同国家所设立的国家公园也会呈现出要素的变异,如果从字面上来理解“国家公园”,“园”可理解为国家公园的物质载体,而“国家”与“公”则是对这一物质载体的社会建构,在不同的时空语境中会形成不同的要素组合(见表2),从而演绎出不同类型的国家公园发展形式。这些变异同样反映了理论旅行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抵制”,即国家公园概念被置于一个新的时空情境之后,会结合具体情境中的自然、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对与原始情境相冲突的具体经验或解释做出各种反应。

表2 “国家公园”理论旅行中的变异要素
3 国家公园理论旅行中的权力实践
如果把国家公园在美国的诞生视为其理论旅行的起点,那我们知道“国家公园”这一概念本身并不具有自流动性,即其不会从美国自动流动到其他国家。国家公园概念之所以能从美国扩散到其他国家,也源于这些国家对国家公园理念的价值诉求,而且各国在建立自己的国家公园时,并非简单移植其他国家的经验,而是基于各自国情对其价值进行截取或是实质性改造。也就是说,国家公园概念在时空传播的过程中,并没有形成一种教条式的权威,而总能在新的社会情境中被重新阐释而不断获得活力,这如同萨义德所说的理论旅行的最佳模式——“理论超越”(transgressive theory)(Said,2000)。这种“超越”不仅表现在物质载体的变化上,还表现在意义赋予与实现方式上,其得以成功实现在于国家公园并不是由各种科学定义组合起来的合成物,而是一种如福柯所说的“表述系统的话语”(辛斌,2006)。这种话语系统与权力紧密相连,拥有“生成其他东西”和“表达一个机构的意义和价值观”的独特功能(辛斌,2006)。
作为一种国家符号与工具,国家公园概念进入一个新的语境,需要对其进行话语阐释,包括理论层面的知识话语阐释和实践层面的实践话语阐释,这一较强的“实践性”要求各国必须结合自身国情做出“与起点不同的再现和制度化”(Said,2000),故大多数国家需要通过国家层面的权威制度来实现。权威制度的权力实践主要体现在政策、法律、规章制度等方面的制定、执行和反馈中,一方面可以通过其“合法性”来决定话语的应用条件及固化话语的内容、形式与言说程序等,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褒奖与惩罚机制、合法与非法的区分来保障或抵制话语实践,以体现制度的“排斥性”这一本质特征。可见,权威制度更多表现为国家意志对话语的强势权力实践,具有操纵性、控制性和权威性(刘伟,2018),但也会因为过于强硬而生发反抗和抵制意识。伴随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权力不再单纯倚重威权的强势手段,而日趋依靠隐匿的、不易察觉的方式来建构意义和形塑理解(李智,2017),从而在话语阐释中实现权力的隐喻表达。
3.1 权力的规制:权威制度话语的国家在场
当国家公园这一概念进入新的时空时,必然关涉特定历史时期的话语阐释:什么是国家公园?建立国家公园的目的何在?谁有权对国家公园进行控制、利用、表征、再现、改造和管理?谁又被排除在国家公园之外?考察各国家最初建立国家公园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过程,法律、法规、管理政策等权威制度对各国国家公园概念的界定及国家公园话语体系的形成都起着规制作用。以加拿大为例,国家公园概念1872 年在美国诞生后,加拿大于1883 年便制定了《自治领土地法》,使得公共土地得以归于内政部的管辖,为后来国家公园的建立奠定了制度基础。1887 年加拿大成立了第一家国家公园——落基山国家公园,并借鉴黄石经验制定了《落基山国家公园法》,该法案明确了落基山国家公园的保护目的、保护重点及其对游憩功能的重视,从而确认了加拿大在政治体制上建立国家公园的可行性。1911 年加拿大出台了《自治领森林保护区和公园法》,并规定所有国家公园都归自治领公园处管理,由此成为国家公园体系的开端(博伊德等,2014),比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的出现还早了5年。这一过程既反映了加拿大对美国的“理论接受”,也反映了其在“理论上的超越”。
尽管各国建立第一家国家公园的时间不同,但是每一个引入国家公园概念的国家,都没有选择照搬照抄别国的模式,而是结合自身的国情及彼时全球国家公园发展的阶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模式。例如,俄罗斯虽然于1983年才成立了第一家国家公园,但早在1916 年便建立了第一个严格的国家自然保护区,并发展了自然保护地体系,俄罗斯的国家公园便是在自身已经成形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体系上建立的,旨在分担环境教育及法定许可的旅游游憩等功能,且大多数国家公园都符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对国家公园的界定。在权威制度上,俄罗斯也没有效仿其他国家制定专门的国家公园法,而是在基本法的基础上整合了国家公园建设与保护相关的政策,最后形成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基本法,如《土地法》《民法》《行政法》《刑法》《森林法》《水法》《联邦自然保护地法》《联邦环境保护法》《联邦野生动物法》《联邦文化遗产法》等;二是战略规划文件,主要是指根据《联邦自然保护地法》制定的法律文件及关于自然保护的总统令和政府行政令,如《2012—2020 国家环境保护项目》等;三是关于国家公园的政府行政令和部门规章,如联邦自然资源和环境部批准的单个国家公园规章及管理章程等(天恒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等,2019)。
3.2 权力的隐喻:政治修辞下的意义赋予
除了利用法律政策等权威性话语进行外在的“规训”,各国在建设国家公园时同样会借助隐喻式的政治修辞来完成由话语实现权力的过程。所谓政治修辞是指政治主体利用一定包含各种修辞格或修辞手法的政治语言,在政治过程中获得政治合法性、实现政治说服的手段,是增强公民政治认同,以及发挥政治权力的有效途径(刘文科,2008;唐慧玲,2016)。国家公园理念虽然绝对不能够划分到政治领域之中,不过却并不妨碍国家通过国家公园话语来实现国家的政治认同构建,甚至使得政治权力实践借助话语的隐喻而更具隐蔽性。
国家公园作为权力话语的一种隐喻式实践,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体现为国家公园的命名。通过划定某一保护区或是为某地方命名,可以彰显政权与所有权的影响力,同时也可以是向世人昭示究竟是谁在管理此地。南非共和国历史上第一座国家公园“克鲁格国家公园”(Kruger National Park)是1889 年由当时布尔共和国的最后一任总督保尔·克鲁格(Paul Kruger)创立(Carruthers,1994)。当时英国从荷兰和法国的手中夺得了南非沿海的殖民地,在此之前到达这里的荷兰、法国和德国殖民者的后裔(布尔族人)由于不满英国的统治而向内陆迁徙并建立了布尔共和国,他们选择以统治者的姓氏来命名国家公园毫无疑问是对自身统治合法性的宣称,一方面试图通过这种话语同英国在此地统治分庭抗礼,另一方面不断向当地原住民灌输殖民者的文化与政治影响。
在殖民地建立国家公园曾是欧洲殖民者渗透他们政治影响的方式之一,它包含两方面的作用。其一是通过国家公园来彰显被殖民国家的身份,以粉饰他们对这些国家的殖民统治,从而平息当地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一点在亚洲的殖民地更为明显(霍尔等,2004);其二则是将国家公园保护地作为殖民势力在此地的象征(Kelly,2013)。这二者本质上并无差别,虽然客观上都宣称是为了保护殖民地未受破坏的自然环境或历史遗迹,但利用建立国家公园来延续他们的殖民统治同样是其重要意图。
权力的隐喻还可以体现在当权者对国家公园意义的赋予上。例如,澳大利亚的乌鲁鲁巨石在被划定为国家公园之前,曾是当地原住民阿南古人心目中最为神圣的景观。在阿南古人的语言中这个神圣的景观被称为“梦境”,是他们文化的根基和宗教、人际关系、道德体系、生活方式的源泉(扬,2014)。阿南古人将自己与乌鲁鲁的自然景观视为彼此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然而西方移民者却强调乌鲁鲁首先是一个自然遗址,并将其建构成民族国家身份而非原住民文化景观,旨在为发展诸如旅游业之类的“国家利益”寻求合法的理由。乌鲁鲁·卡塔曲塔国家公园通过对原住民话语的“征用”来进行意义的再表征,使得这片自然景观完成了由原住民话语中的意义向国家赋予的新意义转换,却使原住民丢失了他们自己的文化中心及身份。
4 结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借助萨义德“理论旅行”这一理论分析工具,本文梳理了国家公园的源起与旅行路径,指出了主导各国国家公园概念发生变异的核心要素是国家意志的权力实践。回归理论旅行工具本身,相关研究结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如下。
4.1 位置的政治:中国对国家公园理论的价值诉求
在理论旅行中,探讨理论为何发生旅行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国家公园在美国的诞生及其在全球得以扩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可归于Rich(1987)所提出的“位置的政治”(politics of location)。Rich(1987)认为以西方为中心的理论难以突破“中心-边缘”的知识生产关系,使得西方一直能够成为占据中心的理论生产者,而其他只能被迫处于边缘。她建议用“位置的政治”来消解西方的中心意识,使每一种政治位置均有其知识生产的权力。
首先,美国国家公园概念的兴起就类似于“位置的政治”。国家公园思想的诞生虽然深受欧洲环境保育思想、浪漫主义思潮和景观民主思想的影响,但相较欧洲一直处于文化自卑的美国人却在自然荒野中找到了能与欧洲文化遗产相抗衡的国家公园概念,成功地突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知识生产”传统,使之成为美国人发明的最好的理念(Ross-Bryant,2010)。
其次,国家公园概念之所以能从美国扩散到其他国家,也源于这些国家对国家公园理念的价值诉求,而这些价值诉求之所以能变成现实的理论接受,也受“位置的政治”的影响。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这些新世界国家与美国有着较为相同的“位置”,由此成为国家公园这一新概念最早的拥护者。传统上处于知识生产中心的欧洲大国由于对其古老文化的自信甚至是自负,并没有对美国发明的这一新概念做出快速响应,但又在它们的亚非拉殖民地进行了这一概念的知识生产,以满足其在殖民地的利益。而欧洲小国和亚洲部分国家也积极行使自己知识生产的权力,通过国家公园这一概念生产来反映自身的价值诉求。总而言之,美国发明的“国家公园”概念并没有成为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而是以自由开放的形式进入不同国家,使得处于各种位置的国家都能够打破传统的“中心-边缘”知识生产桎梏,拥有了对国家公园理论进行知识生产的权力。
再次,“位置的政治”强调理论会被不同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知识所在位置的诉求所影响,从而形成了对理论的不同的价值诉求,这也得以解释不同国家在最初建立国家公园时为何侧重不同的国家公园理念,从而形成了实用游憩主义、风景民族主义、景观民主主义和自然生态保育主义4条旅行路径。
最后,“位置的政治”也为理解中国引入国家公园的背景提供了视角。其一,全球国家公园发展已有近150 年的历史,众多国家已进入国家公园体系完善与科学管理的阶段,所以对于中国而言,应该置于当前全球国家公园发展阶段来予以考量,国家公园理论旅行的起点并不是美国经验,众多国家的经验均可为中国所用。其二,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方面的知识所在位置也会影响其对国家公园的价值诉求。从官方话语角度,如果仅仅考虑“国家公园”这一称谓,地方省区市(如云南)、原国家林业局、原中国环境保护部和原国家旅游局等部委也先后批准挂牌成立过一些国家公园,但2017 年9 月26 日出台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明确提到各地区、各部门不得自行设立或批复设立国家公园,并会适时对自行设立的各类国家公园进行清理。这也意味着“国家公园”这一概念必须是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而不能囿于地方层面或部委层面的运作(苏杨,2014)。从知识话语角度,1980 年起有部分研究者开始引介国外国家公园的发展模式与经验,但在2013 年国家公园官方话语提出之前,对国家公园的学术探讨都还比较零散。从政治与生态话语层面,我国自1956 年便开展了自然保护工作,但一直存在各类保护地交叉管理、多头管理、自然产权不清晰、保护地分散、自然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对立等生态管理问题与体制问题。从经济话语层面,我国目前对国家自然保护区财政投入过低,资金约束与人地关系不协调是自然保护面临的较大瓶颈。从社会文化话语来看,我国已经有自然保护区、国家风景名胜区等各种实践形式,但并非都属于代表性的国家名片,同时社会的发展也促使国家更加关注公民的公共福利。显然,基于各种发展现实,中国对发展国家公园有着实际的价值诉求,分析“位置的政治”,有助于更好地解析中国发展国家公园的背景。
4.2 接受、抵抗与超越:国家公园理论在中国的落地思考
对国家公园在全球的旅行考察后发现,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种“接受”和“抵抗”的条件不同而造成的“语境压力”不同,国家公园在传播与流动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旅行路径与变异模式。而且,国家公园话语阐释离不开国家意志层面的权力实践,其中既有通过权威制度话语而显现于外的“规训”手段,也有通过隐匿的话语来实现意义的赋予和权力的隐喻表达。
当国家公园概念进入中国语境,同样应批判性地思考:在新的时空中,会面临哪些接受与抵抗条件?又该如何建立适应于中国语境的国家公园话语体系与实践体系?
在接受和抵抗上,中国需在横向上协调与国际标准及其他国家经验之间的关系。第一,对于中国而言,面对国家公园这一新概念,应将自身置于全球国家公园发展的对话体系中,而不应该局限于“中国化”或“本土化”的范围(闵冬潮,2014),否则极易遮蔽全球化过程中国家公园概念生产与流动的大图景。换言之,我们对国家公园的有限认知还不足以提供处理这些问题的手段,也没有必要舍弃全球国家公园的发展成果而另起炉灶。因此,中国应遵照国际共识,参与全球国家公园发展的大对话,并对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保持开放接受的心态。第二,话语总是处于一定的时空背景即社会历史情境之中的(李智,2017),中国国家公园发展一定要基于现有社会历史情境,在借鉴其他国家经验时需时刻保持批判意识,需意识到各国的国家公园都是一定历史情境下体现其国家意志的产物。因此,我们应该谨慎地度量其他国家经验在中国安顿的能力,并加以有条件的“抵抗”,使理论向中国历史现实敞开(闵冬潮,2014)。
理论旅行最大的魅力不仅仅是对理论的接受与抵抗,还在于理论的超越。因此,国家公园的理论旅行必定牵涉到与起点不同的再现和制度化过程(Said,2000),这也是对萨义德所提出的“理论超越”的回应。在相应对策上的思考包括:
第一,理论的超越会涉及制度化过程,制度化过程亦是话语阐释与权力实践的产物,其生产都必须按照一定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传播(李智,2017),因此权威制度话语的构建是国家公园实践落地的重要依据。中国应该在纵向上协调好与现有保护地体系的关系,利用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契机和中央政府对生态保护的重视,从根本上理顺我国的自然保护地立法、管理和分类体系。但权力可以建构话语,话语同样可以强化权力。例如对于有权者而言,话语的生产会强化表征与认同,进而强化他们的权力意志,而对于无权者而言,则可能会因不符合有权者所规定的意义表征而被排斥出去。因此,在权威制度话语的权力实践上,应考虑中国国家公园对策与实践两个层面的治理结构和利益结构,从对策层面要把握国家公园保护和利用的关系,构建多种形式的利益共享机制和统一管理下的多方共治机制,使得国家公园的多方利益相关者能成为有话语权和利益共享的利益共同体,从实践层面则必须通过权威制度来设计具体的操作细则(苏杨,2019),使之成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话语。
第二,理论的超越必然涉及与起点不同的再现,因此中国建设国家公园的目标不是把中国作为外国理论的试验田,而是要基于全球国家公园发展实际与中国的历史现实,参与到国家公园理论与实践的“改造”中,使之融入全球国家公园的对话体系,贡献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回望国家公园的诞生及其在全球的扩展,大多是将国家公园当作自然建构的产物。正如Adams等(2007)所言:自然是完全可塑的,并用来满足人类的需要,尤其是现代国家为了社会利益,可通过严谨的知识、适当的话语阐述及权力实践,使自然得以被理解。因此,在众多国家的国家公园实践中,基本都有对自然生态保育、风景民族主义、景观民主主义和游憩价值等方面的多重考量。所以我们不仅要关心国家公园的“自然”本身,也要关注附丽在自然上的“意义”建构,因此,可巧妙利用话语阐释和权力隐喻,使之成为彰显我国生态治理智慧的重要载体和讲好中国故事的话语高地。
本文以国家公园概念为研究对象,展示了“理论旅行”分析的另一个进路。闵冬潮(2014)与翁时秀(2018)的研究均表明,“女性主义”与“想象地理”这类理论性较强的概念,如果在理论旅行过程中缺少反思与批判意识则容易产生体制化的话语霸权。相反,国家公园作为一个实践性很强的概念,在理论旅行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理论开放性,既没有形成知识生产的话语霸权,又因为实践落地的需要,总是能不断地适应于各国的价值需求而保持活力。因此,借助理论旅行,不仅有助于把握国家公园的全球演化规律,也为中国语境下的国家公园话语体系与实践体系建设提供了分析的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