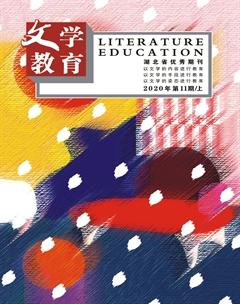存在主义关照下的《变形记》
李晓婷 赵宇
内容摘要:在20世纪欧洲文学批评发展史上,先后出现了很多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如心理分析法,种族主义文学批评方法,存在主义批评方法,形式主义批评方法,文学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及接受美学和语用学的批评方法。这些方法有的如昙花一现,有的则有较深远的影响,但即使是昙花一现,也有着其独特的特点和价值。本文运用存在主义的批评方法对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进行了解读。
关键词:存在主义 变形记 孤独 生存
存在主义原是一个哲学概念,它是由丹麦神学家和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提出的。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创立了“存在本体论”哲学,宣称存在首先是个人的存在,它是一切存在物的根基。可是这种哲学表现了强烈的悲观主义思想情绪,对人生的烦恼和恐惧,孤独、绝望和死亡构成了这一思想体系的全部因素。[1]存在主义文艺的基本特征,是将人变化不定的存在状况以及在生存过程汇总所产生的种种摆脱不开的思想情绪,如焦虑、烦恼、失落、陌生感、荒诞、痛苦、恶心表现出来。他们认为这些情绪是每个孤独的个体从实际生活中亲身体验过的,因而对自我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和冲击作用,使他真正尝到生命中的痛苦。[2]
卡夫卡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西方社会处于世纪之交的转型时期,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精神上毁灭性的打击,整个欧洲社会都处于无望的悲观情绪中。卡夫卡的作品如实地再现了当时处于孤独无望境地的西方人生存的困境和悲惨的遭遇。
卡夫卡的《变形记》是一部有寓意的小说,在叙述中渗透着隐含的意义。小说一共分为长度大致相等的三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间间隔了一天,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之间则间隔了较长的一段时间。每一部分都是以一场灾难为高潮,并一次比一次升级。第一次是以公司代理人的出现为起因,以父亲用棍子和报纸将变成昆虫的儿子赶回屋里而结束。第二次,是清理房间中的家具引起的,在一场残酷的苹果轰炸中结束的。第三次是以妹妹的小提琴演奏为开始的,以格里高尔自愿的离开结束。第一次的灾难使得格里高尔“深沉的昏睡”,第二次导致他昏厥,并有生命危险,第三次是他自愿死去。
这种恰当的结构也体现在对空间描写的准确性上,就像在魔幻现实主义中,对物体的密度和对客观的精确性的过分描述,导致它总是进入非现实或超现实的状态。小说从这只甲虫的角度将格里高尔的房间渐渐展示出来:摆满纺织品样品集的桌子以及它上面的画;窗户开向狭窄的,被晨雾笼罩的街道,尽管之后雾气渐渐散去,却依然只是依稀能看见“无穷无尽的灰黑色的房子的一部分——那是一座医院——这部分房子上规则地排列着一个个打开的窗户”;盒子上的闹钟,床头附近的门,以及左右两边的侧门。接着是地毯,侧面的屋子里面的沙发,放有餐具的桌子,对面墙上格里高尔的摄影,以及“通往楼下的楼梯”等等。
“当格里高尔·萨姆莎从烦躁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他在床上”小说以这句话开始,看似一次很平常的醒来,接下来则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折“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甲虫。”这样一个不显眼的事情稍后又被强调了一遍,“格里高尔寻思,代理人是否也可能发生类似今天在他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人们必须承认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第二段的开始进一步明确了这是现实:“我怎么啦!格里高尔心里想道,那不是一个梦。”
他的内心过程首先是不断的努力,好像他只是身体不适,他必须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他由于莫名其妙的变形而被排除在正常人之外,这也使他处于一个非真实的状态。他起初还是按照原来的思维方式:
“他回忆起来,过去在床上经常感到有些轻微的疼痛,这或许是由于睡眠姿势不良引起的。在起床时又觉得这种疼痛完全是一种幻觉。这次他在床上也觉得有点痛,而且声音也变了,但起床时,却没有什么幻觉了,都是实在的事。他很紧张,这种声音的变化不是别的,而是受了凉的表现,是一个旅行者的职业病的表现,这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他的这种自我安慰会阻碍他认识到自己无法擺脱的真实状况。虽然他依然能够理解别人,但别人已经无法理解他了,他必须知道,该怎样自己照顾自己,并不断适应新的角色。即使人们一开始还照顾他,随着情节的发展,则异化和冷漠愈发表现出来。妹妹一开始还精心为他挑选菜肴,到后来直接“用脚将一些随便什么样的食物,踢进格里高尔的房间,不管格里高尔喜欢不喜欢吃——大多数情况是原封未动——晚上妹妹将扫帚一摇,这些食物就又被全部扫地出门。”一开始妹妹还为他打扫房间,到后来打扫房间的次数越来越少,以至于房间变得越来越脏,最终那间房用来做了储物室。
在格里高尔变形之后,人们对他的称呼由“他”变成了“它”。女佣在格里高尔死后所说的和所做的基本上符合所有人的想法,只是她毫无羞耻的表达,导致了她立刻被解雇,因为她的行为让每个人都感觉到他们隐藏在内心的想法被揭露了出来。最终,当房间第一次对外打开,格里高尔的家人将格里高尔的东西都扔了出去,象征着他们的生活终于从沉重的负担中解脱出来,重新回归正常。“这对他们来说是他们新梦想的一个印证。当达到目的地的时候,女儿第一个站起来,显现出了她年轻的身材。”
格里高尔身边的人可以按照扭曲的等级分类。母亲是唯一一个对弱者还保持着同情的人,妹妹则是多面的,她带着天真的骄傲和固执,照顾变形后的哥哥,既有源自内心的关心和责任感,也满足了她潜在的虚荣心和权利欲望。父亲则开始重新振奋,因为他需要再儿子变形后,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并借此机会恢复他在家中的威望。小说中的配角也可以按此分类:代理人是一个现实的,不断向上爬的角色,人们必须向他献媚。老女佣,“这个身子骨硬朗的寡妇在长期生活中已经承担起了这份令人头痛的工作”。对于三个房客的刻画则像是漫画:“这三个严肃的先生”都长着络腮胡子,当他们吃饭,抽烟,抱怨并最终离开的时候,他们的行为就像是木偶。
因为小说没有叙述故事的背景,我们只能通过字里行间推测其背景意义,有一个地方给出了一些提示,即被妹妹的小提琴声吸引的格里高尔:“他要是一个甲虫,音乐能如此感动他吗?他好像觉得再往前爬就是在向着能看见、却不认识的食物爬去。”音乐在这里是不认识或者无法认识的事物的象征,这些事物被当作是对自由和解脱的一种向往:这也恰好符合Wilhelm Emrich的观点,在卡夫卡的小说中真实的和原始的始终都表现为音调和歌声,音乐和声音。如果我们接受上述对卡夫卡的描述,那么就可以看到小说中省略掉的背景:“从某一个点开始便不再有退路。这个点是可以达到的。”
我们设想一下:从习惯的生存中作为特例而显现出来,从我们的生活中脱离出来,这个变形的人一遍一遍地尝试,保持原有的生存方式,直到渐渐地灰心认命并最终死去。因为它把这种变形理解为一个违背本意的,不幸的事件,它无法理解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一种对不认识的事物向往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是打破命运对生活的约束和生存的束缚,得到解脱,回到一种原始的,真正的,纯粹的存在。就像卡夫卡的作品中向来都没有出路,只在远处或者拐角处感受到一丝光芒,作为在这个像是被诅咒的,无法解脱的世界的绝路中的一点恩惠。人们在极端的情况下感受着深深的,无法摆脱的孤独:他不属于这个由低俗的目标和空虚的消遣组成的表面的生活,不属于忙碌的生活,而是属于最终命运,这种命运是超越一切的进入到完全不同的世界,进入到永恒,这就是这种孤独的基础。卡夫卡也曾说过:“开始认知的第一个标志就是想死的愿望。这种生活看上去无法忍受,另一种又无法达到。人们不再觉得想死是耻辱的事,人们请求,将他们憎恶的旧的躯体变成一个新的,一个要去学着憎恨的躯体。”回顾卡夫卡的变形记,虽然他没有指明出路,但是人们也可以间接的感觉到。
存在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注,有着它积极的一面,它涉及神学,宗教,哲学等深奥的领域。关注人的生存,关注存在与实在的区别,认为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是一种非本真的存在。因为存在主义是对现实生活的关注,所以在战后曾一度成为欧洲国家人们的一种心灵慰籍。
存在主义的文学批评方法曾在20世纪的欧洲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為文学批评开辟了新的途径,将另一个学科融入到了文学批评中,使得文学作品的内涵更加深刻。
参考文献
1.Hubert Ivo, Valentin Merkelbach,Hans Thiel.Methoden der Literaturanalyse im 20.Jahrhundert.5.,überarbeitete Auflage.Verlag Moritz Diesterweg,1979.
2.周忠厚.文艺批评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王一川.批评理论与实践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注 释
[1]周忠厚.文艺批评学教程.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33页。
[2]同上,334页。
(作者单位:青岛科技大学中德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