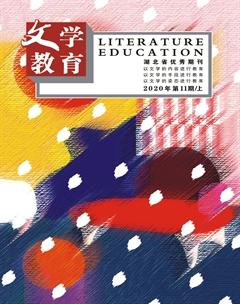虞公山
徐则臣
要从一个鬼魂说起。
不管你信不信,那三个人的确看到了卢万里的鬼魂。他们用手指着脑门对我发誓:“千真万确,如有半句瞎话,仝所你拿枪打我这里。”三个人在不同时间点,经过卢万里家的院门前,都看见他在烤火。卢万里缩着脑袋蹲在地上,面前是一个火盆,他正理着湿衣服在火上烤。在火焰和冒着水汽的湿衣服后面,他们三人都看见了卢万里瘦骨嶙峋的上身和那张憔悴的脸,他冷得直哆嗦。卢万里显然比活着的时候更瘦了。三个目击者的表述区别仅在于燃料:一个说,盆里烧的是木柴;第二个人说,烧的是火纸;第三个承认他没看清楚,火太大,几乎把整个火盆都吞没了。烧的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死去的卢万里突然回到家门口来烤火。
雨一直下,大的时候像老天漏了底,小的时候如满天的蜘蛛在吐丝,缠缠绵绵半个月没消停。所以,尽管现在是大夏天,如果鬼魂衣服湿透了,感到冷也很正常。反常的是,死去的卢万里为什么要回到家门口来烤衣服。
死人回家我没见过,但鹤顶这地方此类传闻从来没断过。算命的老赵多年来的口头禅就是:水边嘛,湿气重,阴气也重,出啥事都不稀奇。也就是说,鹤顶就是个神神道道的地方。所以卢万里的儿子把这件事作为报案的原因之一,我根本没当回事。他说有人动了他父亲的坟墓。他说不仅有三个街坊看见了他爸在院门口烤衣服,冻得直哆嗦,他还亲自梦见了父亲。在他的梦里,父亲穿着的正是在院门口烘烤的衣服,卢万里抱着胳膊对他说:
“儿子,我快冻死了。衣服全湿了。”
在他梦里,父亲的衣服的确是湿的,湿漉漉地正往下滴水。他做梦的时间在三个目击者看见烤火的场面之后,可见,父亲的衣服在烤干之后又湿了。第二天早上,他把这个奇怪的梦说给母亲和老婆听。母亲听了心酸得不行,跟邻居们说起时,止不住流下眼泪;老婆则当成个笑话,说给姐妹们听时自己都忍不住笑出声来。然后,作为反馈和回应,三个目击者看见卢万里烤火的消息陆续传到了他们家。里应外合,卢家就不能不上心了。卢万里的儿子想起来,清明给父亲上坟时是有点潦草,没烧几张纸。一定是父亲在那边缺钱了,所以衣服湿了也没得换。第三天,他一口气买了十刀火纸,每张纸上都摞满了金元宝,装在一个大号塑料口袋里捆到摩托车上,冒雨去给父亲上坟。
离坟墓还有二十米,穿过雨帘他就发现父亲隆起的坟堆缺了半边。再往下看,有人在坟墓旁边挖了一道深沟,雨水汇成激流,正从深沟里流过。浑浊的流水不停地冲刷父亲的坟墓,棺材一角浸泡在水里,流水撞击到黑色棺木上,激起泛白白的水花。卢万里的儿子骑上电驴子转身就跑,背着一口袋的火纸直接到了丁字路口。他结结巴巴地对所里的值班警员说:
“有有有人,盗盗盗了我爸爸的的墓。”
我们觉得这事不可能,卢万里又不是啥大人物,平常到不能再平常的一个坟,盗它,谁吃饱了撑的?本来下雨天也干不了活儿,大家想趁机打个瞌睡,他非要我们去破案。为了表示兹事体大,且有预兆在先,他把卢万里湿了烤干、烤干后又湿了的衣服和哆嗦喊冷的事给我们颠三倒四地讲了一遍。好吧,上车。
快到现场,一摊烂泥地,车过不去。下了车他让我们走在前面。他说天暗,他有点怕。
就是在那天的大雨里,我们发现了未遂的盗墓案,当然,盗的不是卢万里的墓。
卢万里埋在一个好地方。这一片高地,鹤顶人叫虞公山。传说甚多,有说古时候一个姓虞的人曾在这地方住过;也有说这地方埋过一个姓虞的大官;还有的说,一个姓虞的外乡人来这里修行,最后坐在山尖上飞升成了神仙。反正跟一个姓虞的人有关。这种传闻鹤顶人都懒得信,但凡跟别处有点区别的地方都有类似传说。如果都是真的,那咱们鹤顶早就仙迹处处,哪还会穷得如此叮当响?虞公山周围是片荒地,尽管没生老赵那样的慧眼,鹤顶人也看出来这地方风水不错,但因为离镇子实在有点远,人死了也极少长途跋涉埋到这地方。这两年不少人家鸟枪换炮,有了摩托车、电动三轮车,交通工具改变了距离的概念,虞公山周围才慢慢出现几座新坟。
我们围着卢万里的坟墓转了几圈,确定没人动过那口黑漆漆的槐木棺材。它露出一角,还有坟山垮掉半边,完全是雨水冲刷所致。卢万里的儿子拍胸脯保证,若非意外,他爸坟边绝不会出现水沟。坟墓的左侧低于右侧,虞公山上的雨水再凶,往下流也只会从他爸的左边走。他说得没错。坟墓周围荒草丛生,尤其是那些抱住大地不放的巴根草,拿铲子都未必能将它们连根拔起,仅靠雨水的冲刷,十天半个月怕是搞不定的。有人帮了忙。
这好办,我们继续在附近转悠,等同事开车回去取来几把铁锨。然后挖土筑坝再引流,让水从卢万里的左边走。果然,水落之后,在坟墓的右侧发现了铁锹切挖过的隐约痕迹。荒无人迹,谁会无聊来这地方模仿大禹治水呢。我提着铁锨绕虞公山的边缘走,十步之外看见了雨水没有冲刷干净的新泥。
虞公山说是山,其实就是个大一点的土堆子。也许姓虞的那人当初成仙或者刚埋下地的时候,虞公山确有一些气势,比如巍峨宽阔,那风吹日晒雨淋了不知多少年后,它已然也被消磨成了一个土丘。我跟着断断续续残留的新泥走,发现土丘坡上有一丛灌木尤为稠密。大雨把灌木洗得干凈,同一丛灌木竟长出两种不同的枝叶。我用铁锨毫不费力就挑起了部分枝叶。再来一锨,剩下稍微牢靠一点的灌木也被从泥土里掘出来。一例都没有根。它们是被砍断了根插进土里的。
灌木清空后,再铲掉插灌木的一堆泥,土丘的肚子里似乎有个洞。我招呼大家过来,清除洞口堆积的虚土,再往里挖。果然一个黑灯瞎火的洞。铁锨在洞的深处撞上坚硬的东西。卢万里的儿子想出个招,打火机点着,系在铁锨头上往洞里探。洞中氧气稀薄,但奄奄一息的火光中,我们都看见了刚才铁锨撞到的什么。打磨光滑的巨大条石。
以在派出所工作多年的经验,我知道遇上大事了。我把所有人集合到跟前,发布如下命令:
任何人不得走漏风声;
立刻原样封堵洞口,恢复伪装;
现在就协助死者家属培筑好坟墓;
我现在就给有关部门和领导汇报,在相关决定下达之前,咱们所一定做好现场保护,不能有半点闪失。
省文化厅接手了剩下的工作,天还没晴透就派来考古队。他们认为虞公山下可能藏有古墓。他们与县史志办及有关历史学家交流研判之后,初步达成共识:虞公山的传说或许非虚,这地方真埋葬过姓虞的历史人物。安保工作由县公安局牵头,我们所全力配合。同时,责成我们所尽快侦破该起古墓盗窃未遂案。
我们手头的线索只有两个:一是这起盗挖跟卢家的关系。大雨之后的现场线索几乎消失殆尽,但两者之间若无必然联系,那只能说太过巧合。第二个,就是县公安局提供的两个过滤嘴烟头,他们在洞里找到的。一个古怪的牌子,蓝旗。
第一个问题好解决,警员作了拉网式查访,卢万里家人、亲戚,街坊邻里,甚至随机采访了跟卢家毫无关系的人。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卢万里生前口碑甚好,他的左邻高度赞扬了卢万里,那个老大爷说:“我就一个标准:凡是万里说有问题的,那人肯定有问题;凡是说万里有问题的,一定是那人有问题。我认识万里几十年了,这标准从没错过。”卢万里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整个家庭,卢家家风挺好,门楣上还钉着“五好家庭”的牌牌。他们家没仇人,没做过亏心事,儿子、儿媳妇、女儿、女婿,人缘都不错,至少在查访中没听到任何负面评价。足够了。
在乡镇,除非深仇大恨不共戴天,谁会干掘人祖坟这种损阴德的事。更不会有人抽风,要去卢万里坟边开一道深沟解闷。所以我们维持先前的判断:此事跟盗墓相关。
我把查访详情向县公安局做汇报。县局表示赞同,他们也发现,两者很可能关联密切。盗墓必须掘土,盗墓还得隐蔽,掘出的土不能露馅,运土也不能太麻烦,怎么办?现场解决。如何解决?被雨水冲走。自然便捷,神不知鬼不觉。卢万里的坟墓是距盗墓口最近的一座坟,山丘与坟堆之间正好有个凹槽,高处的雨水下泻,那地方是第一个下水口。为了加大水流带土的能力,盗墓贼掘开草皮和地表,人为地开了一条深沟。他们没想到,雨大流急,这个更有效的挖掘机阔大深沟的同时,把卢万里的坟墓也给摧毁了半边,露出棺木。已经在干燥温暖的棺木里安睡三年的卢万里突然落了水,感到了冷。盗墓贼失算了,提前惊动了鬼。
剩下的两个烟头。作为一个老烟鬼,很惭愧,我真没听说过蓝旗这个牌子。警员们去镇上各个商店买蓝旗烟,全都空手而归。店主们跟我一样孤陋寡闻。这方面见多识广的只能找满天下乱跑的人。住滨河大道边上的老苏长年跑长途客车,他也说不清,答应下一趟跑车时帮我问问。我把鹤顶在外工作、求学、做生意和游荡的人名单找出来,能联系的都联系了一遍,没一个人知道。结果显示,他们大部分人都不怎么抽烟,更不会带烟回来。这很好,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副所长想起运河街上常年跑船的吴斌,这家伙烟酒都是大户,没准知道。他老婆在家,听说找吴斌,没好气地说:
“死了。”
“死了?”
“早死了。”
“啥时候死的?”
“一年到头连家都不着,跟死了有什么两样?”
副所长出了口长气,拿出烟头照片,“你见过吴斌带回来这个牌子的烟吗?”
吴斌老婆瞥都没瞥,“人都见不着,哪还见得着烟?”
副所长知道再问也是瞎耽误工夫,赔个笑转身要走,被叫住了。
“本来也懒得问,”吴斌老婆说,“赶上了我就多一句嘴。我家那兔崽子好几天不着家了,你们能不能帮忙找一下?”
“什么兔崽子?”
“我儿子,吴极。”
“失踪了?”
“谁知道。学校也打来电话,三天,哦,今天第四天,没上课了。”
“平常他会去哪儿?”
“谁知道。跟他爹一个德性,四六不着的货。”吴斌老婆摊开手对着房间挥了半圈,“这个家就是个旅店。”
副所长答应着,出了吴家。正经事没干成,倒添了桩新业务,回到所里就跟我抱怨。抱怨归抱怨,还是给镇中学打了电话。教务主任说,有这事,家长再不给出合理解释,按有关规定,可以开除了。教务主任又说,咱这鹤顶,一到下雨天事就多,吴极班上还有个同学也旷课四天了;班主任说,他俩好得穿一条裤子。
“两个孩子平时表现如何?”
“俩孩子性格都偏孤僻,”教务主任电话里的口气有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太合群。听说经常抽烟喝酒。”
我和副所长对视一下。我们的判断步子可能大了一点,有枣没枣来一竿吧。
吴极的同学叫安大平,住在运河街的另一头。父母都在家,老实得像闷瓜,见了警员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放。除了回答我同事的问题,多一个字都没说,连句客气话都没有。据邻居反映,他们两口子常年如此,相对无言。如果不是拴在墙根的那条狗偶尔发出几声叹息一般的叫声,这个家可以一整天不弄出任何动静。两口子说,大平去他姑妈家走亲戚了。
“课也不上了?”
“大平没说上课的事。”
好吧。我同事问,可不可以看一下安大平的房间,两口子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对着一扇关着的门指指,门上贴着奥特曼。一个高二男生的房间,墙上贴的还是初中生口味的招贴画。没有烟味。在一个半开的抽屉里,同事看见一盒本地产的运河牌香烟。打开烟盒,剩下的五根烟里,有一根蓝旗。同事合上烟盒,对两口子笑笑,问,大平他姑姑家远吗?
从安大平家出来,他们直奔运河街的那一头。吴斌老婆正锁门要去菜场,这个时候肉會便宜点。她给了我同事一个白眼,不耐烦地说:
“你们到底想看什么?我都半个月没吃上肉了。”
“就看看你儿子的房间。没线索怎么帮你找儿子?”
吴斌老婆用钥匙打开儿子房门。吴极平常出门就上锁,不许母亲随便进他房间。因为门窗紧闭,浓烈的潮霉味中混杂着没能散尽的烟味。地上有烟头,没错,蓝旗牌。同事顺手翻了写字台上的一堆演草纸,有张纸正面演算了一道数学题,反面画着一个山包。山包的半腰上有一扇打开的门,一个粗暴的箭头指向门里。纸的右下角写着“祖宗”两个字。
“这是什么?”同事试探着问吴斌老婆。
“我哪知道?”她心不在焉地说,“一天到晚跟没魂儿似的,出了这扇门就像梦游。跟他老子半毫米不差。我说你们能不能快一点,再晚便宜肉都卖光了。”
同事回到所里汇报之后,驱车去了安大平姑妈家。
可能因为电视里正在播放侦探片,那俩孩子扭头看见三个警察进了门,立马从并排坐的椅子上跳了起来。安大平的姑妈也吓坏了,他们家从没来过戴大盖帽的。她跟在我同事后面说:
“他俩可啥坏事都没干啊,坐在这里看了一天的电视了。”
我同事说:“没事,我们就了解一下情况。”
俩孩子个头都不小,杵在那里一个挠鼻子,一个拧着手指头。
“有烟么?”
吴极脸上长满了青春痘。他从口袋里摸出挤皱的半包蓝旗。
“哪来的?”
“我爸上次带回来的。”
“带给你抽的?”
“我偷的。”
一个同事堵在门口防止他们溜掉。另一个同事指着椅子,“坐。”
他俩坐下来。安大平姑妈关掉电视,让我同事坐到旁边的木制沙发上。
“别紧张,就是了解点情况。旷课可不是个好习惯。”
“吴极说不想上了,我就陪他出来了。”安大平怯怯地说。
“为什么不想上?”同事问吴极。
“心慌。”
“吃坏肚子了?”
“不知道。”
“再想想。比如看見谁,害怕了?”
吴极低着头,翻起眼看眼前的两个警察,然后扭头往后看。堵在门前的我同事,像逆光中矗立的一座黑塔。
“嗯。”
“看见谁了?”
吴极低头不吭声。
“大平,要不你来说说?”我同事说。
安大平看看吴极,后者没反应。安大平犹豫之后小声说:“你们。”
“戴大盖帽的?”
安大平点点头。
“在哪儿?”
“虞公山。”
“哦,”我同事说,“吴极,你俩一块儿?”
吴极突然站起来,脸涨得通红,“那就是我们家的地方!我本来姓虞!”
两个孩子被带回所里。
副所长把审问结果报送给我时,哭笑不得,这是他从警十八年来见过的最有意思的案子。如果嫌疑人不是未满十八岁的少年,他敢断定这会是本年度全中国最荒唐的案件,没有之一!
虞公山那个洞是吴极和安大平两人掘的,为寻找古墓。卢万里坟墓旁边的水沟也是他俩挖的,如我们和县局推断的,是为了就近把掘出的新土冲走。那个小坟里埋的是谁,他们根本不关心,甚至都没认真看一眼卢万里的墓碑。俩孩子交代,他们利用中午和下午放学后的空闲时间来干活。刚开挖不久就下起雨,本以为雨天对工程不利,黏黏糊糊到处是泥,但发现雨水可以迅速将掘出的新土冲走,他们倒希望雨一直下下去了。因为不会留下明显的痕迹。尽管此地荒僻,若非逢年过节,扫墓上坟的人都见不着,他们还是谨慎为上,每次工作结束,都要把洞口伪装妥帖。大雨帮了他们的忙,踩出的泥泞也很快被雨水抹平;小丘上杂草也多,被踩趴下了,喝了一肚子水后,腰又迅速地挺起来,所以我们第一次去那里,完全没留意这些疑点。
“为什么盗墓?”我问副所长。
“嗨,他们根本不认为是盗墓。”副所长拿出提审记录,“吴极认为他只是在挖自家的祖坟。他说吴斌一直跟他说,他们原来姓虞,当年老祖宗虞公出差途中意外病逝在鹤顶,天热,遗体没法久存,只能就地下葬,埋在了虞公山。虞公山其实就是个大坟堆。只是天长日久,历史演进,鹤顶人把虞公墓这事给忘了,虞公山成了一个大土丘的名字。吴斌跟儿子说,他们这支‘吴跟本地的吴姓没关系,他们从‘虞字来。当年虞公是清朝康熙年间的大官,起码相当于现在的省部级干部。因为是皇帝的宠臣,死后才备极荣华,有如此规模的大墓。虞公客葬异地,他的二儿子是大孝子,便迁居鹤顶,长年为父亲守墓。因为是从家族中分出来,如同从‘虞字里拆出个‘吴,这一支虞公后代就以吴姓在鹤顶繁衍开来。”
“听上去挺是那么回事的。就算真是吴家祖坟,吴极这孩子为什么现在突然开挖了?”
“据安大平说,吴极跟一个姓吴的同学闹矛盾,对方说,‘有种别姓吴。为撇清跟对方‘吴的关系,这小子血直往脑门蹿,竟然要到老祖宗的坟墓里找证据。吴斌跟他说过,虞公落葬时,带了一部家谱进地下。”
这算不算“儿戏”?他还真就这么干了。这孩子都没意识到,即便真有家谱陪葬,几百年过去,也不知道腐烂多少回了。而且,找到家谱就能证明他是虞公的后人?
“吴斌跟吴极说,他们家有一部吴姓家谱,打头的是虞公的二儿子,只要两部家谱衔接上,齐了。没有比这更有力的证明了。”
家谱这么复杂的东西我不懂。我爹给我留了一本,让珍藏,我放抽屉里后再没拿出来过。但以我对家谱粗浅的了解,很多家谱开头都会有一段大帽子,历数自家姓氏的沿革,吴极完全可以拿出自家的家谱嘛。
“这个我也问了。”副所长问我要了根烟,“吴极说,他把家里翻了个底儿掉,没找着。就给吴斌的船上打电话,父亲醉醺醺地跟他说,早不知放哪儿了,回到家再说。他一趟船经常要跑三四个月,吴极等不了,找到一部算一部。头一次见到这么仓促上阵的盗墓贼。找了几本盗墓小说翻了翻,围着虞公山转了三圈,觉得哪个地方顺眼,一锹插下去就开干了。担心一个人忙不过来,就把好朋友拉过来帮忙。哦对了,他不同意盗墓这个说法。”
“不盗墓他们怕啥?”
“我们的人守在那里,大盖帽总还是有点震慑力的嘛。他俩就跑了。”
“口供跟现场都吻合?”
“核对无误。挖掘工具藏在旁边的小树林里,也找到了。”
确实有点意思。我想找个时间跟吴极这孩子聊聊。他爹我见过,跑船回来,经常摇摇摆摆穿过运河街,一大早看上去也是醉醺醺的。
专家们确认虞公山下有座古墓。墓主人虞凤常,字鸾翔,湖北宜昌人,仕宦生涯主要在清康熙年间,官至大理院少卿。也就是大理寺卿的副手,佐正卿总理全院事务并监督一切事宜,正三品,够大的官儿。专家查阅大量史料,证实了本地的传说。大理院少卿虞凤常确系陪侍康熙皇帝沿运河南巡,船队行至鹤顶时病逝。虞少卿是康熙的爱臣,他的突然亡故,让皇帝十分悲痛,其时天气尚热,尸体不宜久存,长途迁移更是不妥,便御旨厚葬于此。当年一定是立了墓碑,碑文很可能还是康熙御笔,但很遗憾,不知道在哪个年代弄丢了。很可能因为墓碑的失散,导致本地人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开始漫漶,最终成了众多漫不经心的传说之一。不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虞公山,否则,早不知道被那些职业的盗墓贼光顾多少次了。
我们把吴斌的“吴自虞来”一说报给专家,他们讨论之后,表示存疑。现有的资料完全不能支撑吴斌的说法。虞氏一族,在北京和宜昌都有后人,子孙繁茂,有案可稽;至于鹤顶的这一支,真没听说。
考古发掘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鹤顶在运河边上,千百年来,无数历史人物在运河上穿梭,无数的大事在水上与河边发生,大大小小的遗迹不能算少。在这方面,鹤顶人还是见过一点世面的。开始几天,大家围观考古现场的热情挺高,里三层外三层,等专家们找到此系虞公墓的確凿证据,即一块镌有“虞少卿”字样的石头后,人群就慢慢散了。热闹不能一直看下去,自己的日子还得好好过。我们继续提供必要的安保,所里的日常工作也逐步恢复。
跟县局协商之后,对吴极和安大平做过批评教育,把他们送回了课堂。我知道吴极没有想通。说实话,我也挺好奇,于是决定,干脆把它当成不是案子的案子继续办下去。周末下午,吴极母子俩都在家,我敲响了他们家的门。
儿子挖了虞公山,当妈的觉得挺没面子;但因为儿子这开山的几锹,引来一场轰轰烈烈的考古,还坐实了虞公墓,当妈的又觉得儿子给自己长了脸。不过此外,“吴从虞来”又让她哭笑不得。你爸整天云里雾里,瞎话张嘴就来,你也信?当妈的又十分来气,这事用膝盖想都觉得荒唐啊。我到吴家时,没说上两句,吴斌老婆又训开了儿子:
“好的你没学,脑子抽筋倒学得挺快。不过那死鬼也没啥好的可学。”
吴极小声嘀咕:“我爸没瞎说。”
“他不瞎说?嫁给他十八年,我算明白了,从头发梢到脚指甲盖儿,他从头到脚都是个骗子!”
“我爸不是骗子!”
“他要不是骗子,你妈我就是七仙女,就是王母娘娘。”
“我爸就不是骗子!”
“好了,老娘懒得跟你争了。你真是你爸的亲儿子。”
我赶紧打圆场,表示想跟吴极单独聊聊。
“随便!”吴斌老婆手一挥,“能带回家聊到管饭更好。”这婆娘拎起织毛线的袋子去邻居家串门了。
我问吴极:“你爸知道这事吗?”
“不知道。电话打不通。”
吴斌跟着一个外乡人跑船,每年回来两三次,吴极掰着指头数,在家撑死了也就待一个月。活儿多?谁知道。他喜欢在水上跑,说在陆地上走不稳,上岸就要摔跤。他悄悄跟儿子说,别告诉你妈啊,我两条腿不一样长。吴极想看看两条腿差多少,吴斌刮了一下儿子的鼻子,站着是看不准的。可是吴斌一躺床上就是前腿弓后腿蹬,两脚从来不齐,那姿势像在跑路。过去吴斌有过两个便宜的手机,一个喝多了不知丢哪去了,一个站在船边撒尿时,不小心滑进了水里。干脆不要手机了,反正没人找。吴极找他,都是打船老大的电话,那差不多也是个不靠谱的酒鬼。
吴家的房子不大,就这样也没塞满,客厅里的摆设稍显清冷,感觉这家人随时都可能搬走。“喜欢爸爸吗?”我问。
吴极低着头,“不知道。”
“想爸爸吗?”
“不知道。”
“爸爸回到家都干什么?”
“喝酒。跟妈妈吵架。给我讲故事。”
“都讲了什么故事?”
“什么故事都有。”这孩子突然有了自信,眉毛都跳了起来,“我爸爸一肚子故事。真的,他什么都懂。他去过很多地方,每个地方都能带回来一大堆故事。不信你问安大平。我爸一回来,他就待在我家不愿走。他说我爸是他见过的最会说笑话的人,每次他都笑得两个腮帮子疼。”
“你妈妈喜欢听吗?”
“我妈说,都是吹牛,鬼话连篇。然后就吵架。有时候还会打起来。”
“你爸都跟谁一起喝酒?”
“他自己把自己喝醉。一年有十一个月在外头,哪来的朋友。”
鹤顶镇上姓吴的有好几家,跟他们家都不是本家和亲戚。吴极往上四五代,都是单传。他爸说,跟他们不一路。
“你们家的家谱你看过?”
吴极摇摇头,“我爸都忘了放哪儿了。但是我看过这个。”他去自己房间抱回来一本破旧的县志,砖头一样大。他熟练地翻到折页的地方,递给我看。
纸页泛黄,印刷效果也欠佳。那一页介绍虞公山的传说,列出四种:虞氏住地说;虞氏修仙说;虞公墓说;还有一个愚公说。第四种意思是,这地方原来真有座山,堵在某人家门口,这家也出了一个愚公,誓将此山夷为平地,可惜天不假年,快削平的时候累死了。大家就把剩下的这个土包叫愚公山。已经有个跟王屋和太行两座山耗到底的愚公,本地人想,还是别弄重了,分不清彼此也麻烦,于是改叫虞公山。虞公墓说,指的就是虞凤常落葬于此,名之虞公山。吴极只在此一说的文字下,用圆珠笔画了两条歪歪扭扭的线。
“这个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我说。
“我相信我爸的。”
吴极说这句话时,内向、羞涩和躲闪都不见了,一脸单纯笃定的孩子气。我摸了摸他的脑袋,感觉像在摸我们家的那个小混蛋。儿子高中毕业后,再不让我摸他脑袋了。“挺好,挺好。”我说,“你爸这么说,一定有他的道理。想吃什么?”
他想吃羊肉串,如果可以,还想把安大平也叫上。没问题,我说这顿一定管饱。我們在镇上最好的羊汤馆等安大平。他们想吃的全点了。分手的时候,我要了吴斌的船老大的电话。
那人姓秦,山东口音,说话充满梁山泊的豪气。我们聊得很好。船停在码头,他留守船上,吴斌上岸溜达了。他说吴斌这兄弟不错,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每顿都离不开那二两猫尿,可惜了一肚子的才华。秦老大说到猫尿时嘿嘿地笑了,他也好这口。水上跑惯了,不喝两口真顶不住那寒湿,还有“孤独”。他说到“孤独”时舌头打了个结,不习惯这样文气和矫情的表达。
“一肚子才华?”
“也是一肚子鬼话。”秦老大吐了一口痰,在电话里说,“那真是个聪明人,说什么像什么。他要不跟我搭个伴,这一年到头在运河里跑上跑下,我还真不知道时间怎么打发。”
“你知道他祖上姓虞么?”
“那得看他喝到哪儿了。喝到位了,也姓过昊。”
我不知道接下来该问啥了,便随口说:“一肚子鬼话那你还信?”
“信了能翻天?你们可能不了解他。聊透了,你就知道,这人让你心疼。对,心疼,就这个意思。”
我头脑里立马出现一个清瘦的男人,还有点病病歪歪的。事实上,我见过的吴斌虽然块头算不上多大,但绝对是个结实的汉子。
“我可能没说清楚。反正这兄弟真不是坏人。他不过是张嘴就来。你要是跟他敞开了说上一个小时,我担保你会认为他跑船是屈才了。我一直觉得他能干很多高级的事。能干什么我也说不好,反正他经常没魂儿的样子既让我冒火,又让我愧疚,觉得委屈了他。但他又能干什么呢?所以这些年我一直收留他。要是别的船老大,早换个更年轻能干的了。不好意思,啰啰嗦嗦的,也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他的声音突然远了,一段空白,他一定是捂住了话筒。很快山东口音又回来了,“吴斌回来了,又喝多了。你要跟他说吗?”
“不必了。我就随便问问。谢谢。”我竟然有点慌张地挂了电话。
这次通话之后不到一个月,准确地说,二十八天,考古发掘还在进行,秦老大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吴斌死了。昨晚喝多了,可能夜里起来撒野尿,一脚没踩好,栽进了运河里。今天一大早尸体浮在水上,幸亏没漂太远,要不都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现在他正加足马力把他运回来,明天就到鹤顶。他觉得先给我打个电话,可能比上来就通知吴斌老婆孩子要妥当。为什么妥当,他也不知道。这个山东汉子,在电话里露出了哭腔。他说,吴斌无论如何是个好兄弟。
由所里出面,找了一辆车去接吴斌。我以为吴斌老婆会拒绝去码头,没有,她坐在车上一声不吭。如此安静的母亲,吴极也有点不适应,他下意识地抓着妈妈的胳膊,他的手不停地抖。
吴斌被水泡得变了形,头发稀疏,白多黑少。他长一张瘦脸,跟肿胀的身子完全不成比例。吴斌老婆没有哭出声,只是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吴极也一样,因为控制不住的惊恐,他连眼泪都很少。秦老大年轻时肯定是个壮汉,此刻两鬓斑白。他擦眼泪的时候不得不擤鼻涕。
一切从简。最后关头,再整理一下死者仪容。吴斌脸上蒙一沓火纸,这是鹤顶的风俗。旁边站着五个人,他老婆、他儿子、秦老大、我和安大平。就在殡葬工要把他推进炉子里的那一刻,吴极抓住了父亲。他把父亲的两条腿直直地并到一起,握住父亲的两个脚踝。为了看得更清楚,他弯下了腰。
(选自《芳草》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