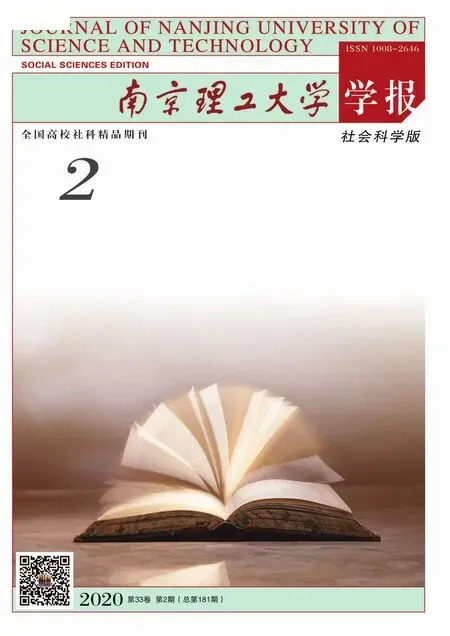彼岸之花:在“人语”和“物语”之间
——兼论中国现代诗歌创作中的“唯物主义”
薛世昌
(天水师范学院 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王维诗《鹿柴》云:“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其“人语”者,即人说的话。人说的话,当然以人自己为说话的立场、中心与旨归;人说的话,当然要“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文学是人学”这一理念之所以不证自明、拥泵甚众,与其“人本”之尊崇大有关系。诗人也是人,诗人说的话——诗歌——所言之志、所抒之情,毫无疑问也是人之志、人之情。但诗歌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人语其特殊之处在于:诗歌是一种时刻试图叛逆人语的人语,是一种时刻以所谓“天籁之音”“神来之笔”“思出尘表”为追求的人语。杜甫《赠花卿》有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如果置换“曲”字为“诗”字,则“人间难得几回闻”者,正是诗质高洁之谓——此“诗”只应天上有。如此则“诗学”也就不仅仅是“人学”,还应该是“神学”。诗歌如果不能“通神”而只是一种“美言”——人语之美者,丧失了超迈的精神,那这样的诗歌徒有其名。然而,诗歌从“人”而通向“神”的必经之路,却是“物”,那些引领我们思出尘表的诗人,无一不既知人,更知物。刘勰说:“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文心雕龙·神思》)一个诗人,他当然要言说他人之不能言,但是他复要言说本我之不能言,更要言说超我之所欲言,甚至要言说万物之所欲言——要传达出神示与天启。诗评家张德明说:“(现在)越来越多的诗人们乐于自说自话,他们习惯于将文本写作变成抒发自己个人情绪的狂欢。”[1]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也是“唯我主义”盛行的诗坛现实,但却是对诗歌法则即诗歌自然律的违背,也是对诗歌道德即诗歌唯物主义精神的违背,其结果就是诗歌中神性的与日俱丧。
一、现象:人性出现的时候神性消失
闻一多在评说《春江花月夜》时提到了该诗一种“迥绝的宇宙意识”[2]17。他在接下来谈到刘希夷《白头翁》中的“诗谶”之“泄漏了天机”时又说:“所谓泄漏天机者,便是悟到宇宙意识之谓。”[2]17他的“宇宙意识”以及他的“天机”“本体”“无限”等概念,其实都是“天籁”,亦即“神奇的永恒”[2]17,是“诗人与‘永恒’猝然相遇”[2]18。闻一多对诗歌艺术的感悟是敏慧的:诗歌就是这一邂逅时分一种神秘的人神对话,是诗人对物语的倾听与转达。王家新早年的诗论《人与世界的相遇》,英雄所见略同。优秀的诗人,大概都认识到诗歌创作的这一深潜:潜入到人与世界“一番神秘而又亲切的,如梦境的晤谈”[2]18。而这样的晤谈,不是人与人的晤谈,而是人与神的晤谈。人与人的晤谈用的是人语,而人与神的晤谈用的则是物语;人与人的晤谈,需要的是“社会意识”;人与神的晤谈,需要的则是“宇宙意识”。
其实《春江花月夜》能当得起“宇宙意识”之赞者,只是它的前半部分。
《春江花月夜》从“春江潮水连海平”起手,而以“海上明月共潮生”接句,至“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这一大段所谓“写景”的部分,堪称“诗人低头向宁静的大自然里深深潜沉的过程”[3]12这一过程也确实描绘出“一个飞翔着精灵的充满着神性的大自然”[3]13。这个“充满着神性的大自然”当中,似乎也有“人”,但他们却只是大自然与山同静的一部分:“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这些碧水悠悠、让人心醉神迷的句子里回响着一种亘古的、亲切的声音。这声音忽一日又出现在幽州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这短短一首小诗,竟获得了泣动千古的力量,这力量,同样在于它清越超迈的神性——张若虚和陈子昂写罢他们的诗,抬起头,眼睛里茫然一片,物我两忘,洞若无视,只有心底响着一曲让人身心震颤的乡音——大自然对我们所有人的温柔安慰。
然而,张若虚接下来却慢慢地、不由“神”主地实施了“我”的出场,进行了从“无我”向“有我”的转变——从写景物向写人事的转变。从“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开始,一步步坠入“人本主义”的浩浩尘世——话语重心落到了“思妇”。这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普遍语法,这种话语重心的落到“思妇”,也是中国古代诗歌一种不无辛酸的“政治正确”——“思妇”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常常并非“相思的妇女”,而是一种隐喻(隐喻怨臣谪客,甚至常常就是“有所思”“有所怨”的作者自己)。沈德潜说《春江花月夜》“后半写思妇怅望之情,曲折三致。”[4]暴露了他的老眼光,他所谓的“曲折三致”对“思妇怅望之情”的步步推出,其实全无新意,只是一种驾轻就熟的“自动化”言说。
中国古代诗歌也是有“主旋律”的,这个主旋律就是“温柔敦厚”,就是“厚德载物”(而不是厚物载德)。所以中国古代诗歌的布局,从来都以“借景抒情、由景而情”为主流。而且这一情形直到现在也并无多少变化,传统的思维定势仍牢牢地操控着人们的言说程式。即以2018年张桃洲的《在夏天》第19首《悼诗人辛酉》为例:“在夏天,村旁/无名小河的水位/再次上涨/没过了河中间用于/踏脚的圆石//连续的降雨/让南方的空气粘稠/岸边的芨芨草变得湿滑/平日清澈的河水/突然凛冽/暗淡的天色里不宜写诗”,这不正是以写景而为全诗的开端么?直到“暗淡的天色里不宜写诗”。从这儿开始,习惯而又自然地,作者的思路发生了偏转,转向了“他”:“他俯身贴近河面的姿势/像一个渴饮的人/在试探水温/又好似初学者在练习蛙泳/略显臃肿的身躯/如一个放大三倍的亚兰”,如同一条缓缓的河流来到了湍急之处,在这一节诗里,作者连用三个想象急速地推进了他的言说,于是高潮来临:“也许,我们都是/这世上的难民,偷渡客/试图躲过浪涛的啸声”。这首诗就这样稳稳当当地、同时也一如既往地,收笔于人的生存状态与人的生存反思。全诗由景而人的套式,可谓老马识途;全诗的完成度,也可谓“老成持重”。
这就是中国人言说过程中无处不在的潜意识、潜规则:先物而后人、轻物而重人、物语为辅、人语为主。著名的学院教授张桃洲之“知识分子写作”不幸落入罟中,不著名的网络诗人潘向建之“民间化写作”可惜也同罹此厄。
潘向建,名不见经传,他有首八行短诗《三圈》:“我绕着槐树走了一圈/槐花全开了//我绕着村庄走了一圈/小鸟全醒了//我绕着田野走了一圈/春天消失了//我犯了什么罪啊//我仅仅走了三圈”。诗写了三个“圈”:1.“我绕着槐树走了一圈/槐花全开了”;2.“我绕着村庄走了一圈/小鸟全醒了”;3.“我绕着田野走了一圈/春天消失了”。这三个从小到大的“时空圈”,让诗的意境如石击水、波浪渐开而至于辽远。在这圈圈荡漾的过程中,支撑着三个“时空圈”而不致使其空洞的,还有每小节内部的艺术张力:“我绕着槐树走了一圈”,这个小小的空间性过程,强烈地对比着“槐花全开了”这一巨大的时间性过程;“我绕着村庄走了一圈”,这个小小的空间性过程,同样强烈地对比着“小鸟全醒了”这一巨大的时间性过程;“我绕着田野走了一圈”,这一小小的空间性过程,同样也强烈地对比着“春天消失了”这一巨大的时间性过程。这种张力让我们感受到一种非同寻常的逻辑:仅仅因为“我绕着槐树走了一圈”,居然产生了“槐花全开了”这样意外的结果。这不可思议的逻辑,这想象与抒情的真实,表达出人们对奇迹的渴望。这个逻辑和张枣的《镜中》有异曲同工之妙:“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这当然不是现实逻辑,而是感受逻辑,是艺术逻辑,是一种诉诸于美的逻辑——它说出了一种其乐陶陶的美丽幻觉。刘熙载有言:“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人籁悉归天籁矣。”[5]他的意思是:人要尽量地自己少说话,要尽量地无我,而让事物自己多说话……而在这首诗的前六行,作者几乎做到了这一点:“物语”优先。
但是,成功停止的地方,失败开始:“我犯了什么罪啊//我仅仅走了三圈”。作者当然以为他的这种结束语是极具“完成度”的,然而,恰恰是这样的按部就班,却让他的诗章落入了俗套——美丽的光圈转瞬即逝。
和所有“卒章显志”的写作模式如出一辙的是,这首诗在第四小节即最后一节,煞有介事地让一种自认为有价值的“人性”隆重登场而试图得到某种意义的“升华”。在他隐隐的观念里,似乎人不自责、不自我批判,就不是人的觉醒,就没有人的价值,也就没有诗的意义。然而不幸的是,这种“人性”的出现,在这首诗的写作中,却同时意味着“神性”的消失——“我绕着槐树走了一圈/槐花全开了”,这样的“我”是人还是神?这样的三个小节所描绘的意境是“人境”还是“神境”?这是多么妙手偶得之的、天簌般清新自然的诗歌意境,然而到了第四小节,却因为道德与忏悔这样“人性”的出现而神韵顿消。他说“春天消失了”,可是真正消失的,却是神性——天籁悉归于人簌,天簌清音变成了道德忏悔。他试图说出一种自以为是的价值,结果却掩盖了另一个更为重大的价值。这就像冯骥才小说《意大利小提琴》里所描写的,那个拙劣而又无知的小商贩,用一种廉价的油漆,破坏了一把世所罕有、天生丽质的小提琴。
显然,由于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歌教养,文之将“终”,其言也善,已成为我们民族话语方式中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潜意识与潜规则,就像《三言二拍》一样,他们不在小说的结尾祭出忠孝节义,他们不道貌岸然一番,他们就会觉得忐忑难安。这种“人性”对“神性”的伤害,往往具体地表现为“解说”对“描摹”的伤害。马拉美说:“直陈其事,这就等于取消了诗歌四分之三的趣味。”[6]“直陈其事”尚且如此,那么“直陈其意”呢?直陈其意、直抒胸臆,那简直就是对诗歌的屠杀。欧阳江河《玻璃工厂》有句:“我来了,我看见,我说出。”有人借用此语描述诗歌言说的动作条令,然而这样的条令是对“意”的突出强调同时是对“物”的严重忽视。即以《玻璃工厂》为例,如果并不经由玻璃而直接说出“从看见到看见……物质并不透明……劳动是其中最黑的部分……事物坚持了最初的泪水……凝固,寒冷,易碎,/这些都是透明的代价……两次毁灭进入同一永生”,这显然不再是诗,因为它太意志、太唯心、太“直陈其意”了。事实上,他是看见了玻璃、贴近了玻璃并顺从了玻璃的物性,他也才最终说出了玻璃——他是绕道“物”最后才到达了“我”。
在绕开“人”的过程中,有一个必须冲过去的开阔地——王国维所谓的“无我之境”。
二、问题:“无我之境”与“事实的诗意”拒绝着什么?
“无我之境”的诗歌事实早已存在,“无我之境”的诗学命名却始于王国维《人间词话》之“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王国维《人间词话·三》)他认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是“以物观物”。以物观物,即不是“我”高高在上地俯瞰,即不追求主观性及解说性,而追求对物的充分相信——信而托之,从而最大程度地归于自然、倾听天籁——倾听事物的言语。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对这句话最准确的理解应该是:天地有大美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准确的破译。谁读懂了“天地之大美”并且破译了它,谁就说出了“天籁”。
一如王国维之所看到,“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王国维《人间词话·三》)换言之,大多数人总是按捺不住“我要说我”的冲动。而另一方面,这应该也与倾听大自然的窃窃私语之难度有关。苏轼曾将这一神与物游的努力名之为“求物之妙”,且认为:“求物之妙,如系风捕景(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苏轼《答谢民师推官书》)但是,这样追求“无我之境”的人毕竟还是史不绝人,因为中国古人对这种天籁式的物语之向往与追求由来已久,从庄子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天下》)句,到刘勰《文心雕龙》的《物色》篇,这一“神与物游”的传统历久而不衰。即以当下中国诗界而言,至少在诗歌的观念上,于坚的“A是A”诗说和“回到事物本身”诗说以及伊沙“事实的诗意”等理念,分明就是对王国维“无我”诗学一脉相承的接盘。
“事实的诗意”为伊沙最早提出并为陈仲义所解释:“这与陈超说的‘用具体超越具体’有一定相通之处。所谓事实的诗意,是面对人、物、事、理的‘事实性’,保留其全部的准确、具体和充盈。完全的‘事实性’,大可不必用意象化手段抽绎经验,铸炼象征,而是在近乎客观、通明的语境中打开‘事实’本身就可以了。”[7]而沈浩波《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先锋诗歌》对“事实的诗意”阐释得最为清楚明白:“伊沙对于‘事实的诗意’的概括和命名,令‘后口语诗歌’对于‘具体’和‘及物’的强调变得更加清晰。……自古以来,诗人的努力,就是用‘象’来实现‘抽象’,英美现代主义诗歌中的‘意象派’,就受惠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象美学。‘事实的诗意’的提出,在诗人们所不断强调的‘意象’‘形象’‘物象’之外,又多了一个‘事象’。现代诗歌的诗意凝着物将不仅仅在于‘意象’,‘事象’比‘意象’有更充分的‘具象’特点,并能包含‘物象’与‘形象’。”[8]显然,“事实的诗意”这一概念对“事实”的强调,无疑是对王国维“无我之境”在所谓“现象学视域”下的发展与丰富。
于坚的诗学里至少有两个“拒绝”:拒绝升华、拒绝隐喻。于坚在总结“拒绝隐喻”命题时申明:“我强调的是通过对陈词滥调的再隐喻的拒绝而复活神性的‘元隐喻’。我说拒绝隐喻,一般来说,就是要拒绝A是B。”[9]215-216于坚拒绝“A是B”的同时倡导的是什么呢?他倡导的是“A是A”:“心是语言建立起来的,心是先验的,而不是语言将某种心的观念说出来。A是A,就是相信心的先验,相信读者。”[9]215其实,隐喻往往也是人们信托于物的一个主要方式,但是于坚却对其进行了严格的辨析:陈词滥调的隐喻是必须拒绝的,是“神性”已死的,只有“元隐喻”才有望复活“神性”。所以,于坚另一个与“拒绝”相对应的诗学关键词就是“回到”:回到常识、回到事物本身。
于坚的这种“回到”说和海德格尔的“本源”说异曲同工。海德格尔曾经区分过“诗性言述”和“非诗性言述”。他认为传达了“神言”的“人言”是“诗性言述”,而纯粹的“人言”则是“非诗性言述”。海德格尔是用荷尔德林的诗句进行描述的:“依于本源而居者/终难离开原位”[10]73所谓“依于本源而居”,就是让事物回到它的原初,让事物呈现自己的本相。为此他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一开头就说:“本源一词在此指的是,一个事物从何而来,通过什么它是其所是并且如其所是。某个东西如其所是地是什么,我们称之为它的本质。”[10]1而“还原”或“回到”的潜台词则是:有一个先在的“离开”或者“丧失”。
没有事物是原地不动的,没有事物未曾离开它的本源。离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晓得回归。所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所以“浪子回头金不换”。基于这样的中国哲学而形成的中国美学认为,艺术之境界有三:一曰艺术实境——是山是水境(只是事物),二曰艺术幻境——非山非水境(离开事物),三曰艺术化境——亦山亦水境(回到事物)。《红楼梦》黛玉说诗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红楼梦》第48回)她说的其实正是这第三个诗歌境界:亦山亦水境。它看起来“无理”、“俗”,因为它与第一境界是那么的相似。当代诗人于小韦的《火车》也是如此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旷地里的那列火车/不断向前/它走着/像一列火车那样”。它是“无我”的,但它同时似在大喊:这就是我!我要回去!这大喊就是它的价值。海明威谈《老人与海》时曾言:“大海就是大海。老人就是老人。孩子就是孩子。鱼是鱼。鲨鱼就是鲨鱼,不比别的鲨鱼好,也不比别的鲨鱼坏。”[11]而他真正的意思是:“我试图描写一个真正的老人,一个真正的孩子,真正的大海,一条真正的鱼和许多真正的鲨鱼。然而,如果我能写得足够逼真的话,他们也能代表许多的事物。”[11]海明威的话传达着这样一个观念:回到事物正是为着彰显意义。
顾城有一个创作谈,可为上述这一切“返乡”之旅的注脚。
顾城《红太阳》有句:“别加糖/在早晨的篱笆上/有一枚甜甜的/红太阳”。“红太阳”何以是“甜甜的”?顾城夫子自道:“有一次,我看到太阳——新鲜、圆、红、早晨等等一连串的观念和直觉一瞬间一掠而过,直接到达了草莓——甜而熟的草莓,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句诗:‘太阳是甜的’。”[12]顾城这一创作谈最让人兴味盎然的倒不是“甜甜的/红太阳”这一诗人想象的最后落槌,而是诗人对那些习见感觉(新鲜、圆、红、早晨)的“一掠而过”。顾城虽然说得“轻巧”,但这一过程却是传说中诗人艰难的还乡之旅。如同面对着一块“多年生”的铁,诗人要一下一下敲掉它上面的斑斑铁锈,才能让我们看到铁本来的样子。这一“放过前八拍”的对“陈词滥调”的拒绝过程,需要诗人既要有烟云过眼的耐心,也要有追根溯“元”的的决心。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无我之境”,无疑也就是“拒绝旧我之境”——诗人因此就是世界上最见不得“旧世界”的人。
然而,这天地之间哪有那么多的“新世界”呢?既然事实上这天地间是无我而不在的,是无往而非旧我的,那么,我又将何为呢?孙绍振用“无动于衷”四字回答了我们对“无我之境”的疑惑。在一次讨论中西诗歌对情感与理智的关系之不同处理时,他认为中国诗歌较好地处理了诗歌中情感与理性的关系,没有放纵情感,对抒情有所控制:“……不是情动于衷,而是无动于衷,也成为杰作。比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还有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13]古人说,大隐隐于市,孙教授的“无动于衷”四字说出了“无我之境”的一个高境界:无我,故空灵,故自然,故真实,但那尚不是空灵自然的臻境;有我,却仍然空灵、自然、真实,那才是高境界——这个境界需要这个在场的“我”人虽在场,但是“无动于衷”:在,等于不在。这就是“无我之境”的高一级境界:“忘我之境”。这种“忘我之境”,也就是“身心脱落”之境。日本中世纪杰出的禅僧道元君有言:“学道之人须贫”。这里的贫,不单指生活的清贫,更指一个人面对世界万物时的身心空灵:“学佛道,学自己也;学自己,忘自己也;忘自己,证万法也;证万法,使自己及他已身心脱落也。”[14]而所谓“身心脱落”,也就是苏东坡“空静”的意思。苏轼《送参寥师》句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静下来,才能对一切的动了然于心;空下来,也才能对一切万物容纳于胸。明人谢榛认为:“韦苏州曰:‘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白乐天曰:‘树初黄叶日,人欲白头时’;司空曙曰:‘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三诗同一机杼,司空为优:善状目前之景,无限凄凉,见于言表。”[15]为什么他会认为司空曙之诗为优?因为司空曙只是陈列事物让这种陈列自己说话,而不是像前两位那样主观毕现:“将老”“已秋”“人欲”。用影像学术语来表述,司空先生的“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就是蒙太奇之“空镜头”,既“静”且“空”。静却似有群动,空却如有万境——回到了事物、推出了事物、突前了事物,而事物则恰恰是此处无声胜有声!在中国古人的诗歌境界说里,这就是所谓的“禅”。什么是禅?禅即是无我!我呢?我走了!我走到哪里去了呢?我走到物那里去了!
王阳明有句云:“闲观物态皆生意,静悟天机入窅冥。”(王阳明《睡起写怀》)只有把玩事物,才能读懂事物。只有贴近事物,才能倾听事物。所以那些通神的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天下》),所以那些神与物游的诗人在自然面前无不表现得谦逊低调,既不在情感上有骄傲的表现,也不在理性上拘泥于人间的是非。在“物的人化”和“人的物化”之间,他们宁肯选择“人的物化”。他们当然不选择人与物的对立,而是选择人与物内在的、隐秘的沟通,然后与大自然“和其光,同其尘”(老子《道德经·56章》)并最终到达物我不分的不知何者为“人语”何者为“物语”的境界。
以上对“无我之境”的梳理与认识,可以初步这样总结:只有作为言说者的“我”的“身心脱落”,然后经过“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文心雕龙·物色》)的描写,事物的本相才能水落石出般不遮不蔽地澄明于我们面前,才能破除“我执”之障,最大限度地减少个人意志对于事物的僭越。马克思说,人“在他所创造的世界里直观自身”[16]。类似的话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也早说过:“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
三、批评:你们所谓的“神性”究竟是什么意思?
余光中《剪掉散文的辫子》有言:“可是我们生活于一个散文的世界,而且往往是二三流的散文。我们用二三流的散文谈天,用四五流的散文演说,复用七八流的散文训话。偶尔,我们也用诗,不过那往往是不堪的诗,例如歌颂上司,或追求情人。”[17]余光中的话虽然尖刻了些,但所斥并非不是事实。所谓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实在并不准确,我们连一个好的散文的国度都算不上。我们的大部分文字,人气冲天,以心傲物,人情炼达但是疏于“物理”。我们的文化人好不容易来到了诗歌之中,却仍然汲汲于言志、抒情甚至议论(如宋诗)、说明(如汤头歌诀),甚至高谈阔论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如玄言诗),却唯一不能静下心来面对自然。即使偶尔写上一些面对自然的东西,那也为了逃避、转移、喘息。他们很少主动地潜下心“与物相刃相摩”(《庄子·齐物论》)。绝大部分的中国人确乎是生活得非常现实,然而这现实中却又夹杂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事”而“满口仁义道德”,更诡异的是,这“人事现实”里偏偏又罕有“精神现实”,更罕有灵魂的“独自远飏”。一言以蔽之,中国的诗人当中,能体贴事物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神性写作”者,毕竟少之又少。
虽然少,但终归也有,比如李白。李白之所以获誉“诗仙”,不是他的诗没有歌颂过上司,也不是他的诗没有追求过情人,而且也不是他写了那么多的“神仙”,甚至也不是李白满足了普罗大众对于“神”的理解:喜夸张——动不动就是“尔来四万八千岁”(《蜀道难》)、动作侠——动不动就“别时提剑救边去”(《北风行》)、语言洒脱——常常奔放如“日月照之何不及此?惟有北风号怒天上来。”(《北风行》)……贺知章惊呼李白为“天人”,那是因为他的诗歌出色地做到了与事物的神奇对话,带领我们来到物语的神界。他著名的《将进酒》劈头盖脸第一句就是:“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君不见”,其实是“请大家看”的意思。看什么?看一个人世之外的秘密:黄河之水,从天而来;他在《金乡送韦八之西京》中有句:“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他在《与夏十二登岳阳楼》中有句:“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他在《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中有句:“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军直到夜郎西”;他在《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中有句:“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他《月下独酌》中的句子更是脍炙人口:“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他在《待酒不至》中说:“山花向我笑”;他的《独坐敬亭山》之“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更是齐物精神与天籁之声的杰作……李白作为一个诗人是称职的,他代言了那么多的事物,说出了那么多事物的“悠悠我心”。
那么李白与杜甫谁更伟大?谁更厉害?谁更诗人?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各持所见。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杨义的《李杜诗学》以及其他不可胜数的研究著作,或见仁,或见智。但是在中国的普通大众层面,人们脱口而出的千古诗歌第一人,却不是“诗圣”杜甫,而是“诗仙”李白。这是一个事实:“圣”让尊于“仙”、人间烟火稍逊于仙风道骨、更具社会性和道德性者次之于更具自我性和艺术性者……人们之所以如此抑杜而扬李,表现出一般大众在事物品鉴时的一种“宰熟”心理:对于“异质”的东西,人们普遍感到喜欢,表示尊崇,而对于“同质”的东西,就感到似曾相识,态度轻慢。而什么才是我们最“同质”的东西呢?我们最“熟悉”者,莫过于“人”,最“审美疲倦”者,也莫过于“人”。于是这种“宰熟”的极致,就是“宰人”——就是对“人语”的厌倦,也就是对“物语”的向往。于是人们对于诗歌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要求:诗歌当然要说人话,但是诗歌最好能说出“神来之笔”。神来之笔越多,说明这个诗人越有才华,越容易受到大众的尊敬。时世移易,但是我们的这一要求却从来没有改变。我们读顾城《早晨的花》,面对那奇崛如闻天簌的想象、温凉如沐天风的语调,我们只有把他“惊为天人”。
事实上在大众的心目中,诗人略等于“超人”(至少不是一般人),或者说诗人即使在大部分的时间是个一般人,但是他们也应该在某些时候表现出非同寻常的特质——比如在他们醉了的时候。正是李白的“醉”让李白“浪得虚名”。其实李白“神”的时候不多,“醉”的时候却不少。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开卷第一句话就说:“读李白的诗使人感觉着:当他醉了的时候,是他最清醒的时候;当他没有醉的时候,是他最糊涂的时候。”[18]1郭沫若对李白的这一“辩证”描述,在闪烁的词语之间,有其微熏的真意:诗人的醉,是诗人独有的清醒,是诗人诗性的觉醒。杨义把诗人这样的状态称之为“微醉”之后的“微幻”:“微幻思维,幻得精微,它容纳超越性于现实性之中,容纳抒情、议论于叙事之中,以庄与谐、沉着与空灵的配比变化适应着忧患和冲淡的各种主题,从而成为中国诗学中以理节情、由幻返真、含蓄而中和的一种思维方式。”[19]而比微幻程度更低的一种状态,就是“疑”。李白诗里多“疑”,如“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等。田子馥说“李白诗中多有疑团,‘疑’表明李白对于任何事物也不人云亦云,能够独立思考,独立观察,‘疑是银河落九天’‘疑是地上霜’,这是李白的个性所在。”[20]真是望文生义。李白的“疑”,分明是“好像”“如同”的意思,分明引领着李白一种飘逸的想象,其与“怀疑精神”还真是有些风马牛不相及。
郭沫若喜欢的另一个诗人就是王维。
王维,人称“诗佛”。由于王维的诗歌比较“高冷”,颇不为一般的“热心”大众所关注,但郭沫若早年有过一个对唐代诸诗人的表态:“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18]300郭沫若让王维坐了唐诗的第一把交椅,究竟是何理由,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个原因想来不可排除,那就是王维的“神性写作”——王维也是一位时时刻刻倾听、破译且欣赏着世间“物语”的人。比如他的《鹿柴》之“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其中的三个动词就很是蹊跷:谁“返”、谁“入”、谁“照”?显然,不是“人”。王维显然看到了人之外的幽微事物的小动作。他这眼,堪称“诗眼”。这样的诗眼让他在《竹里馆》中窥见了这样的“明月”:“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而他的“空林独与白云期”(王维《早秋山中作》),空林,就是主语,不是我们在空林中与白云期,而是空林人家自己与白云有个约会。这就是典型的“观自在”。王维如果不能“观自在”,王维的内心如果不是杳冥空无、一片禅寂,他又何以如此超然“人”外?
优秀的诗人都是这样敬物、爱物而纯任自然的,如王维《观猎》的最后,“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千里暮云”,用具体超越具体,人生的万般胸臆,被言说得滴水不漏。这就是宗白华所谓“使客观景物作我主观情思的象征。”[21]“象征”是几乎人人皆知的文学动作,但是却几乎人人做不到位,盖因人人都放不下那个“人本”的、“唯我独尊”的自己,而不能虚怀若谷、悦纳万物。所以,如果仅仅从想象是否飞扬、主观是否沸腾这样的角度,很难品鉴王维的诗。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为例,十个字中,王维的“主观”之词有几个呢?王维的诗歌对主观的介入有着分明的节制,且他对诗歌中的自然似乎也尽量地保持着不介入、不改变、不改造的态度。在王维的诗歌里,物自身得到了极度的呈现:事物是那么的突出、前出、高亮,而自我是那么的隐蔽、退后、低调,这就是王维的诗歌,这就是他诗歌的超然物外。王维当然没有听到后来弗洛伊德学派精神分析师卡恩医生的名言:“熟悉人类是份脏活”,但在王维的思想当中,隐隐但是分明地有一种对“人”的敬而远之。王维的诗歌之所以后来获誉“诗中有画”,根由可能也在这里,即对王维的“诗中有画”,应该有这样的理解:第一,诗人用历时性的线性语言描绘出了共时性的事物状态,推出了事物本身,而让事物直诣“无我之境”,从而最大限度地做到了“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王国维《人间词话·五二》),并构成宛然如画、历历在目的视觉形象;第二,是指王维诗歌中如“画”的那些视觉形象,是作者“回到事物”的造型,即它们并非是自然主义的而是经过了作者的主观渗透。法国哲学家雅克·马利坦就看到了这一点:“尽管东方艺术只关注于事物,然而它却与事物一道隐约地展现了艺术家的创造的主观性。”[22]第三,王维诗歌中事物的丰盈和自在,源出于作者对事物的尊重与体贴。王维的“诗中有画”之“画”,不仅仅是“形象逼真”那么美术,还应该是“回到事物”这么哲学。
那么被称为中国20世纪最后一个“神性写作”者的海子,他的“神性”又“神”在何处呢?
孙绍振在讲到海子《麦地》时,把海子同冯至、穆旦进行了比较:“不像冯至那么深沉,那样带有哲理的意味。他也不像穆旦那样,用了那么多的形容词,很复杂的修辞手段。”[23]这无疑是对海子的表扬,因为一个诗人如果沦落到需要通过哲理与修辞来过日子,那一定是他的羞耻,至少是得了严重的“语言的抽象病”。海子《麦地》所写,都是“麦地上的事情”。麦地上会有些什么事情呢?或者说海子为什么能荣膺“麦地之子”的光荣称号呢?因为海子有一双神一般的“诗眼”——他看到了“碗内的月亮”,他听到了这月亮的“一直没有声响”,他发现连夜种麦的父亲“身上像流动金子”。更为诡谲的是,他还发现了月亮下飞过麦田的十二只鸟,它们有的衔起麦粒,有的则迎风起舞,而且“矢口否认”(莫非月光里的麦地上空发生了什么讨论与争辩?)。海子这样的诗句更是充满了物我对话的意味:“月亮照我如照一口井”。而下面这四行更是海子天才般的想象:“家乡的风/家乡的云/收聚翅膀/睡在我的双肩//麦浪——天堂的桌子/摆在田野上”。接下来海子继续调动他的麦地体验:“麦浪和月光/洗着快镰刀”。海子对曾经的麦地生活记忆犹新,“妻子们兴奋地/不停用白围裙/擦手”、“这时正当月光普照大地/我们各自领着……孩子/……洗了手/准备吃饭”。西川说海子:“他的语言非常好,好得让人嫉妒,太好了;我说的还不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样的诗,这首诗我倒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海子晚期诗歌里的语言已经到了毫无道理的那种霸占的程度:‘在豹子踩出的道上豹子的灵魂蜂拥而过’,什么叫‘豹子的灵魂蜂拥而过’?不可思议。”[24]而我这里不厌其详地叙述海子《麦地》诗里的发现,也是想申明:海子诗歌中的“神”,正是他对事物体贴入微的观察与描述,正是他对事物的神奇想象。要知道海子当时是那么年轻,假以时日,还不知海子会爆发出多么惊人的创造力。也许,正是因为海子差点就要说出宇宙的秘密了,所以上帝这才把他紧急召回了天庭(而让那些永远也窥不到天籁、说不出天机的人苟活在世上)。
四、结 语
学者刘永认为,“神性”这个词,有着“宗教血缘和玄学气质的词语出身”[25]。本文一直回避着“神性”的此一意指及其它类似的意涵。本文使用的“神性”一词,不是“凡俗”的反义词,主要是“人性”的对立面,更多是“事物”的反义词。在此意义上的“神性写作”即指:人们把自己的话语中最接近于神性的那一部分,命名而为诗。人们在这样的诗中保持着与事物之间古老的对话。当一个诗人展开他的想象去行使他对世界的命名职权——当他重新创造一个世界时,神就会出现,因为神就是创造的别名。神性在彼岸,人性在此岸。人性是此岸之花,神性是彼岸之花。神性引领着人性回归自然,而不是人性引领着神性告别天地。这一过程要求诗人对待事物的态度是谦卑的、进入的、忘我的、齐物的——心与物齐、以物观物。所以优秀的诗歌都重视意象,亦即指向着物语,“人性融化于美感,理解力融化于感觉力”[26]。如果说科学让我们尊重着物性同时与世界作战,那么诗歌就让我们欣赏着物性同时与世界和解。诗人应该“在自然面前放下身段,以谦卑的姿态去重新面对明月大海,去重新倾听鸟语蛙鸣,达到天、地、人之间的和谐。”[1]而所谓诗歌的“唯物主义”也就意味着:诗歌建立在对物的观察与体认之上,诗歌以充满人性的心灵,感应事物并借以折射人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