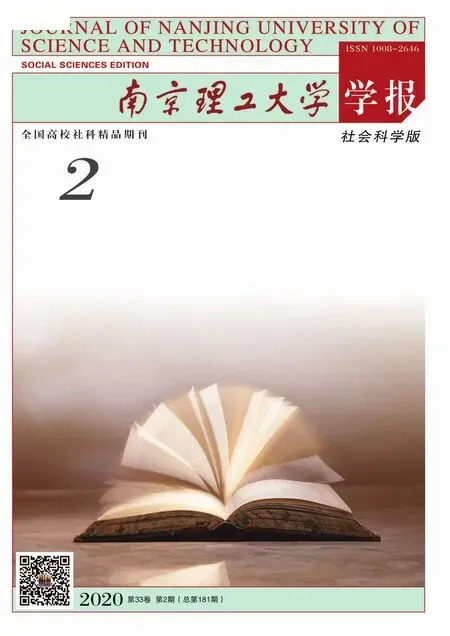南社女作家曾兰文学创作思想研究
杨 萍,许文伯
(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南社是20世纪初成立的一个革命文学团体,是伴随着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而成长壮大起来的。据柳亚子《南社纪略》统计,南社有女社员68人,有小说家曾兰,政论文学家唐群英、吕碧城,文学翻译家张昭汉等。南社中的女性多数是时代的精英,她们或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士,或是女权运动领军人物,作为先觉者,她们从改变自身命运和建构民族国家的需要出发,弘扬女权,提倡男女平等,主张女性独立和解放。
曾兰(1876—1917),字仲殊,号香祖,四川华阳人,南社社员,蜀中名士曾阖君之姐。自幼饱读诗书,有良好的家学传统,“用功深细,《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南史》《资治通鉴》皆读数过,二十四史《隐逸传》尽取读之,尤好老、庄、列、文四子。”[1]15岁时嫁与同乡吴虞为妻,受吴虞影响较深,读书学习不辍,他们不仅是夫妻,还是文学上的知音、挚友。她性情温恭平和,喜好庄子和游侠隐逸史传,“系君性温恭,笑我气纵横。怀中战国策,闭户独自精。勤探庐孟理,始觉邱轲轻。每嘉游侠传,亦慕沮溺耕。素质见庄严,圣心自神明”[2]。曾兰能文善书,常为吴虞誊写文稿,题写书名,为乡邻书写对联。吴虞在五四前后积极撰文反孔非儒,被誉为“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和“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名噪一时。
1912年4月,曾兰在成都创办了四川第一家妇女报《女界报》,并自任主笔,同时也为《娱闲录》撰稿,是彼时成都著名的女文人。曾兰“为文谨严”,其政论文《女权评议》被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登载,《女界报缘起》刊入王蕴章主编的《妇女杂志》;小说《孽缘》刊载于恽铁樵主编的《小说月报》,引起轰动,恽铁樵称赞道“《孽缘》叙事明晰,用笔犀利,甚佩甚佩! 箴砭社会,洵小说之职志。”[3]她的历史人物传记小说《铁血宰相俾斯麦夫人传》是依据发表于1913年《神州女报》第4期余姚坎镇严整翻译的传记《俾士麦克夫人传》创作而成,多幕西剧《经国美谈》剧本( 第一部) 改编自日本明治时期著名作家矢野文雄(龙溪)的同名政治小说。1917 年曾兰去世后,吴虞整理其遗文汇编成《定生慧室遗稿》二卷。
一、书写女性情感,关注女性权利
据目前文献记载,曾兰创作的小说有两篇,一篇是1914年在《小说月报》第6卷第10号上发表的《孽缘》,署名吴香祖女士,后连载于《娱闲录》(《四川公报》增刊)第 7、8、9 册,署名定生慧室;另一篇是1914年在《娱闲录》第2、3期上连载的历史人物传记小说《铁血宰相俾斯麦夫人传》。《孽缘》描写了封建包办婚姻造成的女性婚姻悲剧;《铁血宰相俾斯麦夫人传》则记叙了女性自主婚姻带来的婚后夫妻生活的和谐美满,两篇作品都书写了女性的情感生活,赞美歌颂了自主婚姻的幸福美好,表现了作者对女性权利的关注。
小说《孽缘》讲述了主人公味辛女士因屈从于包办婚姻而导致不幸的人生悲剧。味辛“美丽聪慧有才学”,人人都以为她会找一个如意郎君结婚生子,不料却被父母许配给暴富浅陋的田芋。味辛嫁到田家后,“看见他家中的人都是鄙陋龌龊,房屋器具陈设,都不脱那乡坝里三费局绅团总老爷,土头土脑的气习。”[4]43这种落差使她倍感痛苦,公婆凶恶,丈夫粗鄙无能,夫妻二人的私生活也要受到翁姑的严格看管,夫妻不得随便接近,生活没有半点自由,毫无乐趣。后来丈夫渐渐被人引诱到处闲逛,吃喝嫖赌样样学会,“甚至在外面看上了一个娼妓张珠儿,终日在珠儿家里,打牌饮酒,抽烟过瘾,还要在别处招邀些娼妓来,一同顽笑,闹得个不亦乐乎,就是天塌下来,他也不管了。”[4]45她几番劝阻丈夫无果,只好泪湿罗襟,暗暗悲欢,最终性情愚黯的翁姑还为他们的宝贝儿子把娼妓娶回了家。本来味辛已经惨痛不堪,受到翁姑、丈夫、小妾的虐待,不想家里又来了两位同样刻薄的亲戚,乌女士和王女士,二人见风使舵,察言观色,偏向小妾珠儿,用谗言诋毁、构陷味辛女士,翁姑更加欺压虐待她,让她操持干不完的家务。味辛在这深重的痛苦中日渐憔悴,疾病缠身,“本想不去医治,任随身体早日消减,离去浊世的苦恼,以达他当年归隐的目的。”[4]51可为了年幼的儿女,她只得忍辱负重地活下去。
小说开篇就把造成味辛婚姻不幸的根源归为“亲权无限”的封建包办婚姻:“因为我们中国,自古传来亲权无限,结婚一事虽是女子终身所系,也只得随着父母的爱憎,独断独行,不但不须女子本人许诺,并不许女子稍得预闻末议。”[4]41味辛的婚姻遵从父母之命,父母包办终铸成悲剧。那如何避免悲剧的产生呢?曾兰在小说的结尾呼吁重视女子教育,“我想味辛女士,生得这等聪慧,使他自幼便受文明国的教育,必能成就一极有学问的人,即使遇人不淑,凭着他的学问,也可以独立谋生,又何至过这样困苦的日子。可惜中国向来不讲究女子教育,把这样的人都废弃埋没,岂不可叹!”[4]52她认为女子教育是实现女性权利的重要途径,如果味辛接受过文明国的教育,有学问有文化,即使遇人不淑,也不必依附于丈夫过苟且屈辱的生活,可以独立谋生,追求自己的幸福。
19世纪末以来,随着西方启蒙思想的传入,西方婚姻恋爱观念也渐渐影响中国,在20世纪初期,形成了传播和学习西方婚恋观的热潮,国内一批先进知识女性及进步男性积极投入到婚恋自由的宣传之中。1901年4月19日,凤城蓉君女史在《清议报》第76册上发表《婚姻自由论》,斥责中国封建婚姻的野蛮,大力赞扬西方国家的文明婚姻;1904年汪归真在《女子世界》刊发《论婚姻自由的关系》一文,也以西方国家的自由婚姻为例,倡导中国向西方学习。受此影响,曾兰在她的历史人物传记小说《铁血宰相俾斯麦夫人传》中描写了一位与《孽缘》中的味辛女士命运截然相反的德意志女性俾斯麦夫人传奇的人生。
《铁血宰相俾斯麦夫人传》发表于1914年《娱闲录》第2、3期。俾斯麦早年年少轻狂,放荡不羁,坏了名声,他向亨利的女儿求婚,遭到亨利夫妇的拒绝。亨利夫妇认为此少年浮浪轻薄,了无前途,然而亨利的女儿却独具慧眼,钟情于俾斯麦,在父母面前一再坚持要嫁给俾斯麦,亨利夫妇钟爱女儿,允诺了女儿的要求。婚后俾斯麦夫妇恩爱幸福,俾斯麦夫人宜家宜室,既为俾斯麦营造了温暖的家庭港湾,又为他生育了一女二子,恪尽母亲之责,教导儿女皆有成就,女儿嫁给了麦利伯爵成为伯爵夫人,长子哈巴脱和次子威利阿姆皆封伯爵。俾斯麦夫人不仅是丈夫生活上的伴侣,更是他政治上得力的助手,常常在政治漩涡中帮助丈夫化解危机,“不久与威廉第二复合,隐然为黑幕。宰相夫人在中间周旋,自始至终不稍懈怠,公爵同威廉第二所以能够重行和睦,都是夫人善于调停的力哩。”[5]30俾斯麦夫人不仅帮助丈夫与威廉二世皇帝重修旧好,而且还运用智慧保护丈夫免遭暗杀。“公爵多仇敌,欧洲各国想得公爵而甘心的不知道有多少国,所以一生常有刺客俟候着他,就是最信用的心腹人,有时也图谋害。到公爵已死的时候,还有暗杀的人在大门外依着徘徊未去,却竟没有遭横死,且能够从从容容建设日耳曼帝国的基础。……都是由夫人暗中保卫扶持,这就可见夫人真是非常的妇人哦。”[5]18小说肯定并赞美了俾斯麦夫人的政治才能和非凡魄力。
《孽缘》和《铁血宰相俾斯麦夫人传》中的味辛与俾斯麦夫人生活在不同的国度,自幼接受的是不同的教育,味辛传统守旧,一味顺从,俾斯麦夫人思想开放,独立自主;两人的性格也截然相反,味辛胆小懦弱、逆来顺受,俾斯麦夫人目光远大、坚强果敢。从两人不同的结局处理上反映了作者的女权思想,提倡西方的自由婚恋观,倡导女性自由选择伴侣,自主婚姻,批驳了封建的包办婚姻。曾兰在发表小说《孽缘》前,已撰写了不少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猛烈抨击儒家男尊女卑的观点,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主张学习西方,争取女权,男女平等,在四川妇女界中引起较大反响。但曾兰的女权思想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冲突,味辛连续不断的妥协说明了曾兰对其女性全面平权主张的犹疑与矛盾,女性婚后大多都陷入婚姻家庭的羁绊之中,只能规避现实逃入虚无,默默忍受。俾斯麦夫人在“日耳曼帝国没有夫人自由运动的余地”的情况下,管理教育儿女,“以家为国的家政”,这也是女性实现权利和价值的可能途径。“可以看出曾兰在对女权的认识和追求上已作了相应的变通,基于女性本身的自然属性以及现时的社会环境,全面实现女子平权是有困难的,立足于家庭,从家庭开始考虑角色和身份的价值与意义”。[6]9曾兰在论述女性与家国关系时,不自觉地把女性作为一种功能上的手段,而忽视了对女性权利本身合法性的论证,更为重要的是曾兰的女权思想的远大理想在现实社会环境中难以实行,她自己也清楚女权主张践行的艰难,因此用《俾斯麦夫人传》表达女性变通实现个人价值与权利的可能。
曾兰这两篇小说显示出清末民初人们对婚姻关系的反思,表明自由婚恋观念正在广泛扩散。
二、呼吁民主政治,反对独裁专制
曾兰创作的多幕西剧《经国美谈》( 第一部),从1914年《娱闲录》第5期开始连载,至13期,为全本14幕白话话剧。《经国美谈》(第一部)故事素材源自明治时期日本著名作家矢野文雄(龙溪)的同名政治小说《经国美谈》,由周逵译成中文,先连载于1900年2月至1901年1月的《清议报》,后由广智书局于1907年出版单行本。《经国美谈》一经译出,在中国知识界受到热烈欢迎,与《佳人奇遇》《雪中梅》等其他日本政治小说共同对中国近代文学观的转变和晚清小说界的繁荣起过促进作用。
小说《经国美谈》的故事框架由两组并行且交织在一起的矛盾构成。一组是民主政治与独裁统治的矛盾,另一组是国家独立与卖国求荣的矛盾。主人公巴比陀代表的正党主张民主政治和国家独立,奸党则不惜卖国来推行独裁统治。这两组矛盾的激化形成了故事的冲突,相互间力量对比的消长则演化成故事的曲折变化。小说一开始就冲突迭起,正党坚持要人民参政实行民主政治,而奸党则坚决反对,暗地里勾结独裁政体国家斯波多,借斯波多的军队夺取了政权。同时,在政变中斯波多也趁机控制了齐武的主权。在这里国家主权与民主政治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最后消灭奸党与赶跑斯波多军队也是同时进行的。小说的这种结构同作者的政治主张密不可分。作者矢野龙溪是明治时期的政治家,亲自组织过改进党,积极推进立宪政治。在依傍正史进行小说创作的过程中,他宣扬了改进党的这种政治观点。近代著名小说家李伯元曾将《经国美谈》改编为传奇杂剧《前本经国美谈新戏》,先后发表于1901年10月的《世界繁华报》和1903年5月至1904年8月的《绣像小说》,全剧18出,似乎未完,但基本上保持了原作的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完整性。但李伯元在改编时把《经国美谈》当成一个恢复国家主权的故事来理解,民主政治的部分则被淡化了。在交代故事起因时,省略了正党与奸党之间的政治分歧,将主要矛盾放在国家独立与否这一点上。
1914年曾兰再次将这部政治小说改编成剧本,曾兰的剧本也并非直接译自日文原书,通过对比其与《清议报》所刊小说《经国美谈》,基本可以断定曾兰所采用的底本正是周逵中译小说的前编20回。比较曾、李两种剧本,则可发现曾兰改编的《经国美谈》(第一部)与李伯元改编的剧本《前本经国美谈新戏》在本质上存在重大区别。
首先,李伯元在改编时把《经国美谈》当成一个恢复国家主权的故事来理解,剧本着意突出了原作中的争取国家独立和主权,驱逐外来统治的主题,而淡化了要求民主政治的主题。曾兰的剧本表达的主题是恢复齐武民政,维持希腊自由政治,诛杀推行独裁专制的奸党,救国民于水火,成就济民大业,突出了民主政治的主题。如巴比陀在阿善议会上慷慨陈词:“如今斯波多在齐武既得了志,未必就满了他鲸吞蚕食的念头么。那怕不然,必定还要侵略阿善,今日无阿善,明日更无齐武。今日齐武亡,明日阿善必灭,我两国如唇齿相依,必要互相援助,才可以免灭亡之患,所以救齐武国难,便是救阿善国难的先声。救齐武就和救自己本国一样,况且从前士武良回复民政的时候,敝国也曾尽过一点微劳。今齐武国难,贵国却坐视不一援手,我想诸君,必不是这样忘背的。还有一层,斯波多不喜人民参政,是虎狼的邦国,我们西国贵人民参政,是有道理的邦国,所以斯波多、阿善、齐武三国的盛衰,不止是三国的盛衰,实是专制政体自由政体的盛衰。这个关系,要影响及于希腊全土的国民。”[7]
其次,李伯元的《前本经国美谈新戏》,虽然也采用了大量的对白,但究其实质,仍是需要演唱的“旧剧”戏曲。与李不同,曾本标为“西剧”,采用了现代分幕法与幕表,标明剧场布景,角色不分生旦净丑,语言纯用白话,剧情完全依靠对话推进,无唱段,基本完成了戏曲到话剧的转变。
晚清戏剧改革是朝着两个方向展开的。一个是对戏剧的旧体制作一些改动,以适应新时代的审美趣味。另一个是创立戏剧的新品种——话剧。李伯元的《前本经国美谈新戏》台词多而较自然,从结果上看,促进了话剧诞生,但曾兰的剧本真正完成了戏曲到话剧的转变,在戏曲的革新上大大地跨越了一步。这既说明《经国美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表明民初戏剧与西方戏剧接轨,迸发了崭新的力量。
三、提倡女子教育,主张男女平权
1916年12月,曾兰在《新青年》卷3期第4号上发表了《女权评议》的长文,锋芒直指孔子“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主张一夫一妻制,提出在家庭和社会的地位上应男女一律平等。她在《女界报》上发表的《女界报缘起》,也猛烈抨击儒家男尊女卑的种种观点,主张学习西方,提倡女权,重视女子教育。曾兰的文章在成都产生了很大反响,使她成为成都最早提出妇女解放的人。她的《女子教育论》论述中国封建社会女子备受极苛极繁的礼教压迫、束缚的黑暗情形,并详细介绍欧美、日本女子教育的发展历史和经验。她提出兴办女学,细举兴办女学的重要性,女学的兴办又全在女子教育,“女子教育不昌,不惟将一国女子尽弃为无用之物,并且累及一国男子皆归于无用之地”[8]11。而“女子教育之方法则当以女学会、女学报、女学校数者并举”[8]11。
曾兰把女子教育作为实现女性权利的重要途径,她认为女性权利可以通过自我提高而实现。对于女性来讲,女子当同男子平权,同时女性自身也要用实际行动来实现这种权利,“女子当琢磨其道德,勉强其学问,增进其能力,以冀终得享有其权之一日,同男子奋斗于国家主义之中,追踪于今日英德之妇女,而固非与现在不顾国家之政客、议员较量其得失于一朝也”[8]11。 曾兰由女子教育而延伸到女权,由女权的获得而延伸至民族国家的兴建与发达,“女学不明则女权不伸,而平等自由之幸福亦即无其资格享之。”一旦女子通过教育获得女权,女子就能在社会和国家层面担当更为重要的角色、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在社会则妇女当为丈夫之顾问,言教育则妇女尤为幼稚之导师”。这样一来,“全国之民智民气,妇女皆可以转移之,吾辈自当一扫从来屏息低首宛转依附深闭幽锢卑鄙污蔑之戮辱桎梏,发奋而起以光复神圣之女权”[8]12。
曾兰之所以关注女性权利及家庭伦理问题,这与她自身的性别身份和现实处境是分不开的。尽管曾兰与吴虞青梅竹马,婚后夫妻恩爱美满,如吴虞所说,他们婚后生活得很幸福,“予与香祖,喻濠梁之云乐,信缨冤之忘怀。无取刘安,自解毁玉之理; 宁侍邹阳,方识投珠之惑。流连风月,栖息烟云”。但在实际生活中,曾兰忍受了太多家庭之累。曾兰嫁给吴虞后共生了10个孩子,尤其是夫妇二人被吴虞父亲撵到新繁老家居住的那段时间,曾兰几乎累垮,身体每况愈下。吴虞脾气暴躁,遇事总是心急火燎。一日,吴虞在书房写作时,却怎么也找不到所需参考书,便叫曾兰帮其寻找。吴虞书房三面皆是高大的书架,藏书上万册,且未列书目,很难查找。平时吴虞所需之书,曾兰总会很快找到并放于书案,可那日寻遍书架也不见踪影。吴虞焦躁生气,将长期压抑于胸中的恶气与愤懑一股脑地泼向妻子,并恶语相加。曾兰始料不及,慌乱中跌下竹梯,顿时不省人事。吴虞和丫鬟急将曾兰救醒。恰在此时,省高等审判厅法官、留日同窗好友欧阳理前来透露臬台转来川督缉捕吴虞的批文以及审判厅的拘签,并劝吴虞快逃。曾兰忍痛叫丫鬟收拾行李,并拿出银钱交予吴虞,催其快跑。吴虞被迫逃到双流县乡下,得到时为哥老会首领的舅舅刘藜然的庇护,才幸免为囚。不久,四川保路运动爆发,武昌起义成功,清王朝随之被推翻,成都军政府成立,清政府对吴虞的通缉令自然作废,吴虞获得自由,他从乡下回到成都。这期间,都是柔弱的曾兰带病料理家务,照顾子女。
吴虞还有诸多恶习,比如嫖妓、纳妾等,曾兰不但都默默忍受,有时还得强打精神讨好奉承吴虞,处在如此压抑的男权话语的家庭环境下,曾兰怎能不心生哀痛与感叹。虽然从观念理想上曾兰认识到男女全面平权的重要性,甚至主张女性要走出家庭,积极投入到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但是其现实生活的境遇,又使她无法超越性别身份的束缚,循规蹈矩地结婚生子,抚育子女,经营家庭,甚至还不得不承袭诸多旧习俗,做一个克己复礼旳贤妻良母。“她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她的一生又有太多隐忍与压抑,其志未能伸展。这种相互纠缠的矛盾始终贯穿在曾兰的女权思想中,也体现于她文学作品中,成为曾兰女权思想的显著特征。”[6]12
四、结 语
曾兰作为南社中的女社员,她的文学创作,无论是小说、西剧还是政论文都鲜明地体现出她的觉醒意识和女权思想。她从自身的现实经验和阅读思考中,探明了一条可见的理想之路,同时又注意到这条路上铺满了荆棘。无论是她的女权思想还是她自己的生活经历,都具有极强的案例特征,它反映的是社会转变时期旧式家庭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可能与限度,尤其是地处偏远的成都,曾兰的意义就更加凸显,她基于自身的性别属性和属地经验,有限度地推进女性权利和价值的实现,具有明显的历史过渡期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