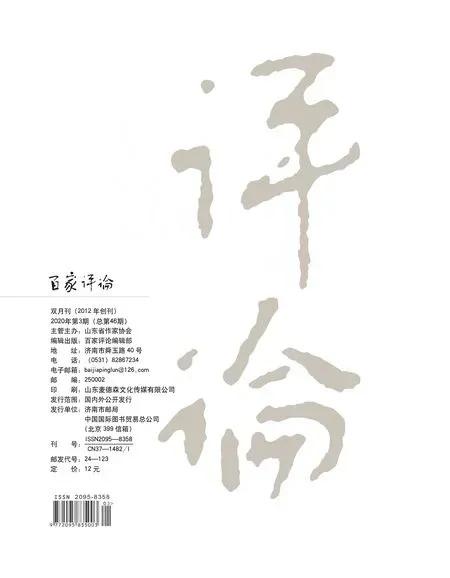“被辛酸浸淫着的幸福”
——迟子建小说短论
内容提要:迟子建的小说,温润如玉,她以无言大爱溶解人间苦难和悲痛。通过迟子建的小说,我们得以在一个喧嚣嘈杂的现代社会,体味那被辛酸浸淫着的幸福,在机械工业时代去亲近那些有情有灵的苍生万物。万物有灵、上善若水的悲悯,在迟子建的笔尖,以涓涓细流汩汩涌溢而出。
“被辛酸浸淫着的幸福,一定像撒满晨露的蓓蕾一样让人心动。”
——迟子建
一、破损的“残缺”或现实一种
任何一部小说都有它的腔调,而一部好小说对读者而言,“更像一位知心的朋友,而不是教师爷。”①读迟子建的小说,我们恰如与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久别重逢,聆听她细述这些年来生活的辛酸或无奈,感动或苦痛。迟子建小说语言艺术的过人之处,或许正在于,她能将小说的那种书面腔调,尽量化为充满生气的口语来讲述——这种讲述既包涵丰饶的诗意,也蕴含着一种内敛的张力。在她的小说世界中,读者能自然地走近那一个个卑微而又真实的人生,感受生活的悲喜凉热,体味人间的情爱冷暖。
“小说家的任务,不是叙述重大事件,而是把小小的事情变得兴趣盎然。”②迟子建的小说,似乎总是有意识地回避那些风起云涌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一心专注于呈现普通人特别是底层人的日常生活。在爱的濡染中,一种被辛酸浸淫着的幸福,像撒满晨露的蓓蕾一样让我们心动。综观迟子建的作品,我们会发现她的小说,总会在细腻温婉的笔触牵引下,不期然地将读者带至一个心酸而同时又漫溢着幸福的生活视域。
在作家精心营建的小说情感现实中,“残缺”则是她常写常新的一个表现主题。或许很多评论者都会将此与迟子建本人的人生经历联想起来,当然这种因果联系也不是说没有一点道理——但据笔者对其2002 年前后作品的对比阅读来看,其实在此之前,迟子建的作品,也是多取材于带有哀伤气息但同时又不乏温暖的底层生活,所不同的是,从她2002 年之后的作品中,我们能更真切地感受那种哀凉与残缺的真实,那种隐隐作痛的刻骨铭心。换言之,迟子建一以贯之的表现主题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写作的日臻成熟,以及个人生活阅历的积累丰富,她的审美捕捉力和艺术表现力越发见功力。
或许是因为作家现实生活中最丰富、最真切的体验,夫妻情感往往是迟子建小说最密集的表现主题之一。我们看到,迟子建小说的人物关系设置最常见、最主要即是夫妻关系。而迟子建小说中的夫妻,或是两人异地分居,或者阴阳生死相隔,很少有能成天厮守缠绵直至一生白头到老的圆满图景,但或许也就是这份纯真执着中的“残缺”才让人心动心酸。当然,迟子建的高明之处,不止在于其对悲痛哀伤抒写的淋漓尽致,更表现在她在抒写忧伤时,自然流露的那脉脉温情。
在《踏着月光的行板》中,作家将东北小城“那一列列果绿色的慢车”和松花江上夕阳映射水面而形成的“一派辉煌”一起搬上了小说的画面。小说写的是一对普通农民工夫妻,在八月十五中秋节这天,各自获得了一天的休息假期,为了给对方一个节日惊喜,他们不约而同地踏上了去往对方所在小镇的火车。于是我们看到,在一再擦肩错过的奔波慢车上,一段动人心弦的牵挂之旅展开了,这对普通的农民工夫妻,用最无奈的错过,表达着最浓稠的惦念。最终,他们仅是在两辆慢车相互交会的一瞬间对了一眼,而在这对充满无限爱意的小俩口看来,就是这短暂的一眼,也足以让他们感到知足与幸福了。在小说缓缓的叙述中,我们感受一种幸福的温暖同时,心间也会不经意流淌一泉淡淡的忧伤与辛酸的细流。没有团圆的“残缺”就像“半残的月亮,不管它多么的明净,总不如满月的光辉那么激情四射、光华动人。”③,但“满月”终究不是生活的常态,“残月”或“无月”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在生活中,人们每每为追逐“满月”而疲于奔命,但毕竟一个月只有一天是“月圆”的十五。重要的或许不是圆月本身,而是在追逐满月的时候,我们能保持一颗淡定的平常心,“残缺,也许就是生活和艺术的真谛。”从这个意义上说,“残缺”不再是一种表现主题,而成了迟子建洞彻人生的生存哲学。
值得一提的是,在表现“残缺”的夫妻感情时,尤为令人称道的是作家的细节刻画或场景描写。比如像《青草如歌的正午》,小说不止一次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主人公陈生用青草,在正午太阳下为死去的妻子编织手工品的动人情景:
“陈生坐在木墩上,垂着倭瓜似的扁圆的头,十分卖力地编着缝纫机。由于编得不顺利,他先是骂手中的青草是毒蛇变的,然后又骂正午的阳光像把钢针一样把他的头给扎疼了。”④
“陈生从地里回来下了一碗面条,然后又垂着倭瓜似的扁圆的头,坐在正午的阳光下用青草编织东西。他觉得阳光就像一张雪白的网罩着他,而他则如网底的一条青鱼。他编着一件菱形的包。”⑤
“陈生渐渐又能下地了。他也能在正午时垂着倭瓜似的扁圆的头,坐在木墩前用青草编东西了。青草在他的膝上灯影般跳跃着,仿佛要给他黯淡的生活投上一缕亮色。”⑥
陈生为亡妻杨秀织缝纫机、包,甚至还要编织为杨秀动手术的医学仪器,炽烈的太阳给人带来的种种生理上的不适,并没有让他停下手来,这些在外人看来反常的举止,通过小说用心的细节刻画,在小说主人公那里显得是那样的自然。通过主人公执拗的动作,当作者有意将“倭瓜似的扁圆的头”与“青草”等细节同时展现在读者面前时,人们似乎也能隐约感受到陈生对妻子的一片痴情。一个稍显笨拙的普通农民,在表达内心世界的感情时,既不会用华丽的辞藻,也不会向他人寻求倾诉,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以一种孩童似的天真,为妻子默默编织生前喜爱的物件。但恰恰是这种稍显笨拙的方式,带给我们一种心悸的感动,而无声的沉默难掩的则是一种辛酸的幸福。
就现实而言,生活在“残缺”中的我们,并不是无可逃遁,而是需要以一种艺术的方式来掩盖或者遗忘残缺。唯此,我们才能领略生活的种种美好。而生活的残忍就在于,有时候“残缺”会以一种狰狞的面目,猝不及防地出现在你面前,让你堕入万劫不复的痛苦深渊。在迟子建的笔下,生者对亡灵的哀思和天各一方的感情倾诉,也并不总能通过某一物件得以成全。从这个角度而言,哀思有所寄托的陈生,还算是幸福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女主人公蒋百嫂无处言说的撕心裂肺之痛,或许才最让人揪心。在男人“失踪”之后,蒋百嫂酗酒、撒泼、摔东西,甚至明目张胆地领男人回家睡觉,凡此种种,似乎都在暗示我们:蒋百嫂不是一个“好女人”。可随着小说情节的蔓延深入,当我们最终知道在她家的冰柜里就停放着自己男人尸体的时候,不仅能理解为什么每晚她会跑去陈绍纯的画室外,默默坐在那听悲歌,她停电时的疯狂举动也一下子找到了根源答案。在丧夫的蒋百嫂眼里,她无时无刻都得面对婚姻中残忍的“残缺”,所有的白天对她来说,无不都是黑沉沉的夜晚。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似乎都压在了蒋百嫂一个人身上——如果说小说中的“我”以及生活中的我们,还有机会去掩饰残缺,忘记残缺,那么,对蒋百嫂来说,她不得不在残缺中受尽非人的折磨。也正是在这一对比下,小说中“我”的痛苦得以稀释,所以才会在小说的结尾,出现那只轻柔的蓝蝴蝶:一只带有湖蓝色翅膀的蝴蝶无声地落在我右手的无名指上,仿佛要为我戴上一枚蓝宝石的戒指。
其实在此之前,迟子建对生活的“残缺”早已有自觉的表现。比如迟子建早期小说《白银那》写乡长妻子卡佳的意外死亡,乡长原本完整的家庭,因女主人的突然离世出现了“残缺”,而也恰恰是这逝去的“残缺”,让追悔莫及的乡长及马占军一家人明白了生命的重要;《鸭如花》中一直沉浸在丈夫自杀阴影中的徐五婆,三十年来一直抱守残缺,守寡不嫁。当徐五婆有次从老院长口中证实丈夫是因为“花”的夭折而弃绝尘寰的时候,她的内心除了伤痛外,或许还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落寞与失望——为之苦苦守寡的丈夫,居然没有一天爱过自己!但话说回来,谁又会怀疑徐五婆对丈夫的这份忠贞不二呢?
写作照进生活,恐怕是作家始料未及的最残忍的残缺。正如迟子建所说的那样,在小说集《越过云层的晴朗》中,“我其实是写了一条大黄狗涅槃的故事。我爱人姓黄、属狗,高高的个子,平素我就唤他‘大黄狗’。他去世后的第三天,我梦见有一条大黄狗驮着我在天际旅行,我看见了碧蓝的天空和洁白的云朵——那种在人间从来没有见过的圣景令我如醉如痴。最后这条大黄狗把我又送回地面。”⑦,或许正因这种切肤之痛,迟子建将《越过云层的晴朗》中的“大黄狗”的涅槃才表达得那样情真意切。整篇小说都是以一条狗的视角俯瞰人类的生存世相,将人性的丑恶通过狗的眼睛传达出来,而在狗对主人的忠诚衬托下,人世似乎显得浑浊而丑陋——如果说狗的涅槃获得的是越过云层的晴朗,是天堂的滋润,那么谁又来拯救人呢?迟子建后来也一度自责道:“我这不是写一条狗涅旳的故事么?如果我最初对小说的设计不是这样的,爱人是不是还会在人间呢?”从这段话中我,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尽管丈夫的离去与自己的写作不存在丝毫因果联系,但迟子建还是抱有深深的歉疚。难道写作和生活竟是这般两难?
当然,简单机械地将作家写作路径的变化,直接与其生活变故联系起来,未免显得牵强附会。如果说作家个人的生活变故,真给小说带来了某种变化,那么在笔者看来,在经历那场巨大的生活灾变后,迟子建的忧伤与痛苦,只是表现得更加细腻更加真实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迟子建对“残缺”的表现经由写作回归生活,再由生活返照写作,无疑已经上升到了写作路向和生存哲学的高度。
二、苍生有情,万物有灵
迟子建的小说,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是,我们发现作家给很多动物留下了余裕的情节空间,迟子建笔下的马、狗、猫、鱼、鹿等小动物与小说人物构成一种互证的存在。在描述人之常情,讲述人之常理时,迟子建总会为她的主人公配设一个不可或缺的动物角色:《一坛猪油》中的“蚂蚁”、《青草如歌的正午》中的王来喜家的“马”、《鸭如花》中徐五婆的“鸭子”、《越过云层的晴朗》中的“大黄狗”、《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的蒋百嫂家的“狗”、《零作坊》中的“猪”以及《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鄂温克人的“驯鹿”和“黑熊”等等。
这些动物角色的设置有着举足轻重的意味,它们是作为一种独特的功能性意象在小说中存在,而并不是可有可无。它们不仅作为通常的小说情节或结构的转捩点而存在,且往往带有一种灵性与神性,从而在小说中与人的存在形成一种诗性互证。从某种程度上说,“苍生有情,万物有灵”也正是迟子建小说偏爱表达的一个主题。
迟子建早期小说中的动物角色设置,一般来说,都限于人类喂养的家禽家畜。比如像《晨钟响彻的黄昏》中的猫,小说中“我”与“本本”(猫)与相依相伴,以“我”对“本本”的倾诉来呈现城市人的生活状况;《青草如歌的正午》中的马也是如此,在小说中,主人公陈生与马一样都是不被重视的存在。当陈生去看望王来喜家的马,并站在动物的立场来为马说情,告知王来喜用马过度时,马似乎跟陈生心有灵犀,一下就停止了流泪。非但如此,马似乎也懂得同情陈生,当陈生执意为亡妻编织做手术的医用仪器而被村人视为精神不正常时,马居然也为陈生的处境淌下了眼泪。当村人都渴盼陈生来杀马,并享用鲜美马肉的时候,没有人会关注陈生内心的痛苦,当然更没有人会为马的流泪而心存怜悯——从这一意义上说,小说中主人公陈生与马无疑构成一种互证的存在。与《青草如歌的正午》中马的角色相近的还有《鸭如花》中徐五婆喂养的鸭子。作为村里的冥婆子,守了三十年寡的徐五婆,平时她与乡邻的接触全凭着“死人”来维系。日常生活中与她相依相伴的,是那些她喂养多年的鸭子。徐五婆懂鸭子,每当安静地看着她那些鸭子玩耍嬉戏的时候,她内心得到一种莫大的安慰,多年的情感更是让徐五婆舍不得宰杀一只鸭子,而鸭子似乎也像是徐五婆亲生孩子一样,一直忠实伴随着她的起居生活。小说中,鸭子成了这名孤独无靠寡妇的全部寄托,看似笨拙而又可爱的鸭子,在迟子建的笔下,摇身一变成了徐五婆最要好的朋友。在小说的结尾,鸭子甚至甘愿为罪犯的坟墓当一朵“美极了的花”。反观人类,相形之下,在一个惟利是图钻营操作的社会,大多数人在社会交际时,往往会因贫富贵贱而势力地选择交往对象:要么选别人,要么被人选,因此也就常生出一种人心不古、世态炎凉的生存感——人世间的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甚至让人异化得连禽兽都不如。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的蒋百嫂家的那只狗反倒成了人的一面镜子。在这只“狗”身上,迟子建将人畜的依存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的狗,首先是作为一道助推情节发展的线索出现的,在“我”到蒋百嫂家与之谈心并发现蒋百死亡的秘密之前,为激起读者的阅读兴味,迟子建将一只狗的反常行为,穿插在小说的叙述进程中。村人从狗的种种异乎寻常的寻主行为中,萌生了一种蒋百已死的猜测:蒋百或许早已死于那次矿难。因为狗一般都会从哪里送走主人,就会在哪里迎接主人的回来,而蒋百嫂家的狗每日所去的地方,正是它接送蒋百的矿车停靠地。如此,下文蒋百的死亡真相大白也就显得有理有据,整部小说的叙述逻辑与节奏也不再那么突兀。当然,小说中的狗并不是一件情节道具那样简单,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小说角色,蒋百家的狗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小说人物的众生相。狗在蒋百失踪后每天仍然去矿场接蒋百,尽管每次都是失望而归,但这似乎并不妨碍它日复一日一年四季地坚持下去。找而不得的失望以及由此而致的寝食不安,都写在了狗的脸上,狗的有情有义,令那些为继承家产而嫁到这来的外地女人无不赧然。
当然,迟子建在诸多小说中精心设置的动物角色,不仅仅局限于用来表现其与小说主人公的情感,有些小说中的动物角色,也是为衬托底层人的真实生存困境与生活状态。如《零作坊》中的“猪”,它首先是作为人类职业的一种象征,是非法的制度之外的存在,也因此,它未来的命运或许就不得而知了。小说中刻画最多的,不是猪垂死的挣扎,而是写猪被宰时所发出的嚎叫声,就像音乐一般随着人物心情的好坏而奏着不同的乐章。作者并没有对猪做过多言外之意的阐释,而是通过猪的嚎叫与人的欢笑的两相比对,来透视人物的内心生活。再如《白银那》中的“鱼”,百年不遇的鱼汛,让当地人欢天喜地紧张忙碌着,而大量待价而沽的鱼,最终因鱼贩子的迟迟未到而变成一种储存负担,为了让鱼不变质坏掉,每家都需要大量的食盐,这正好给盐贩子大捞一把提供了机会,于是盐贩子肆意哄抬盐价。乡长的妻子想储存好家里的鱼,但又舍不得花高价买盐,只好去山里搬冰,而最终被小公熊伤了性命。追溯种种因果关系的根底,鱼在小说里竟成了一种潜在的杀人道具,而之所以会酿成悲剧,说到底,还是因为人的贪婪与嫉恨。表面看似是鱼引起的一场命案,实则却是人类的贪婪与偏狭导演的一幕悲剧。但迟子建坚持了一以贯之的温暖文风,小说最后的悔过与和解,无疑为小说哀伤的基调增设了一道希望的色彩。
从《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开始,迟子建小说所设置的动物角色,开始越出人类家庭界限,来到了野外的大自然。《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结尾出现了一只神秘的蓝蝴蝶,一只带有湖蓝色翅膀的蝴蝶“无声地落在‘我’右手的无名指上,仿佛要为‘我’戴上一枚蓝宝石的戒指”。这种魔幻的表现至《额尔古纳河右岸》时,得以进一步加强:动物成了人的精神图腾,人反过来成了森林中驯鹿的仆从。无疑,驯鹿是《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另一隐蔽主角。
驯鹿是鄂温克人的守护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驯鹿决定了鄂温克人的生存生活状态,他们随驯鹿的迁移而迁徙,根据驯鹿的食物来源地选择他们的居所。鄂温克人与驯鹿之间的关系,绝非一般的人与动物的役使关系。小说写激流乡干部为劝鄂温克人出山定居,对驯鹿出言不逊,并且让驯鹿像猪马牛羊那样冬天吃干草夏天吃嫩树枝,鄂温克人对干部们的言行表现出无比的反感。在鄂温克人看来,“驯鹿在山中采食的东西有上百种,只让它们吃草和树枝,它们就没灵性了,会死的!”,“我们的驯鹿,他们夏天走路时踩着露珠,吃东西时身边有花朵和蝴蝶伴着,喝水时能看着水里的游鱼;冬天呢,它们扒开积雪吃苔藓的时候,还能看到埋藏在雪下的红豆,听到小鸟的叫声,猪怎么能跟它相比呢!”⑧。驯鹿是鄂温克人的精神图腾,“驯鹿一定是神赐予我们的,没有它们,就没有我们。虽然它曾经带走了我的亲人,但我还是那么爱它。看不到它们的眼睛,就像白天看不到太阳,夜晚看不到星星一样,会让人在心底发出叹息的”⑨。在外人看来,驯鹿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动物,但在鄂温克人眼里,驯鹿比他们自己的生命还珍贵,当看到部族的精神图腾遭遇粗暴待遇时,他们内心的恐惧直露无遗。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鄂温克人的命运,不仅始终与驯鹿紧密相连,也与森林里的其它动物休戚相关。如小说的叙述者“我”与两任丈夫的缘分就与森林里的黑熊有关:“我和拉吉达的相遇始于黑熊的追逐,它把幸福带到了我身边;而我和瓦罗加的永别也是因为黑熊。看来它是我幸福的源头,也是我幸福的终点。”⑩从这带有些许哀伤与浪漫的叙述口吻中,我们看不到一丝人对黑熊的埋怨,“我”丝毫没有将不幸遭遇,怪罪于黑熊的意思。显然,鄂温克人愿意遵从自然的安排——哪怕是与死亡不期而遇,他们也乐意将自己的命运与动物、与自然联系到一起。当然,在鄂温克人眼中,驯鹿之所以带有灵性,完全是因为驯鹿与大自然之间存在的默契与依赖,驯鹿是大自然的赐予,驯鹿和黑熊都吸取天地精华,领受自然的万物灵光。因而人与驯鹿、熊的命运的紧密相连,其实也就相当于与大自然一体。这也就牵引出了小说表现的另一主题:苍生有情,万物有灵。
《额尔古纳河右岸》无疑是表现游猎民族敬畏自然的一部力作。《额尔古纳河右岸》写的是鄂温克人的原生态生活,小说在展现鄂温克人的善良淳朴、率真勇敢的同时,也处处表现出鄂温克人对自然与生俱来的敬畏与热爱。鄂温克人从来不对一棵参天古树,做任何不敬的事情,也不会亵渎地往火堆里扔任何杂物。他们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物我合一,敬畏自然苍生,尽心护卫神圣“火种”。在鄂温克人眼中,大自然的造物都是带有灵性的。尽管,大自然有时会给他们带来意外的灾难,甚至粗暴地剥夺部族成员的生命,但鄂温克人仍习惯将自我生存托付给原始森林,与自然不离不弃。鄂温克族的每个部族,都设有萨满这样一个与上天沟通的职位,但萨满的所作所为,无非也是些应和自然规律的事情。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以全新的生态审美观的视角进行艺术的描写,在她所构筑的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中,人与自然不是分对立的,‘自然’不仅仅是人的认识对象,也不仅仅是什么‘人化的自然’、‘被模仿的自然’、‘风景如画的自然’,而是原生态的,与人构成一体的存在意义上的自然”。
当激流乡人以工业时代的文明眼光,打量鄂温克人的原始生活时,在他们看来的恩赐“拯救”,实则是将鄂温克人推向了一个万劫不复的绝地。不可否认,激流乡人俯视鄂温克人简朴游猎生活的异样目光,尽管也包含着真诚的同情和怜悯,但他们浑然不知的是,恰恰是这所谓的“文明”,给鄂温克人带去了不幸的绝望与无尽的痛苦。正如迟子建在《土著的落日》一文中所说,“面对越来越繁华和陌生的世界,曾是这片土地主人的他们,成了现代世界的‘边缘人’,成了要接受救济和灵魂拯救的一群!……我们心安理得地看着他们为着衣食而表演和展览曾被我们戕害的艺术;我们剖开了他们的心,却还要说这心不够温暖,满是糟粕。这股弥漫全球的文明的冷漠,难道不是人世间最深重的凄风苦雨吗!”。
综观《额尔古纳河右岸》及迟子建其它有关生态题材的小说,作家将习惯了五光十色的工业文明的都市中人,从霓虹灯的照耀下拉回到自然静谧的原始森林,让现代人布满尘垢的污浊身躯得以洗涤,让骚动而又浮躁的魂灵获得一缕清泉的慰藉。在现代性的强势入侵下,人类变成了利欲熏心的奴隶和科学技术的囚徒,对传统文化、对自然万物的态度越来越粗暴不恭,对宇宙秩序更没有了原始敬畏,早已丧失了仰望星空的兴趣。生死不再是意义事件,而成了一道进出社会的机械程序,由此,无根的灵魂变得日益空洞与虚无。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全球性的文化消沉衰颓与精神涣散萎靡早已是人类共识。
正如同行对迟子建的评价:即使对迎面拂过的风,迟子建也充满感念之情。迟子建的小说,文如其人,温润如玉,上善若水,她以无言大爱溶解掉人间的苦难和悲痛。通过迟子建的小说,我们得以在一个喧嚣嘈杂的现代社会,体味那被辛酸浸淫着的幸福,在机械工业时代去亲近那些有情有灵的苍生万物,厚德载物、天下为怀的悲悯在迟子建的笔尖,以涓涓细流汩汩涌溢而出。迟子建的小说带给我们的又何止是精神上的种种慰藉?在她的小说中,我们不也同样听到了当代技术文明的隐隐警钟么?
注释:
①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花城出版社1981 年版,第8 页。
②[德]托马斯曼:《小说的艺术》,刘小枫选编:《德语诗学文学·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193 页。
③迟子建:《踏着月光的行板》自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 年版,第2 页。
④⑤⑥迟子建:《青草如歌的正午》,《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127 页,第163 页,第185 页。
⑦迟子建:《后记:一条狗的涅槃》,《越过云层的晴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年版,第28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