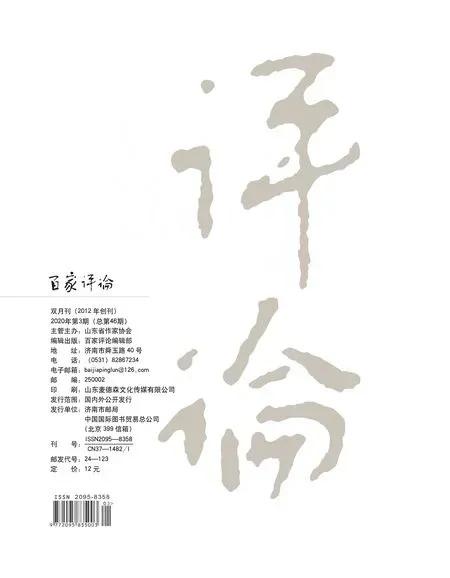诗评家吴开晋的诗歌创作
内容提要:吴开晋一生钟情于缪斯,是卓有成就的诗评家兼诗人。他虚心地多方吸取营养。改革开放后,其诗歌创作和诗学研究都进入新的境界。他的诗作是他的诗学主张的实践和印证。思想解放带来心灵自由,常以神话思维进入创作,大至星球、小至花草在他的诗中都富有灵性。基于生命意识的觉醒,他创作了一系列表现生命诞生、成长、衰老的动人诗篇,并把诗的触角伸向感觉领域。他善于把事态结构和意象抒情融合起来,且能用于重大题材的写作。
吴开晋先生(1934-2019)从15岁就开始写诗,一直钟情于缪斯,直到最后一次重病住院,才不得不放下诗笔。他出版了三本诗集,依次是:《月牙泉》(1994 年),《倾听春天》(1998 年),《游心集》(2004 年)。没有收入诗集的作品还有很多。他从没有在国内、省内申请过评奖,也没有为他的诗歌创作开过研讨会。他是默默的、卓有贡献的诗坛耕耘者。但他总是自认为业余诗歌爱好者。他长年在大学讲授和研究诗歌,“坚信一点:研究和讲授诗歌的诗评家,如果没有一点创作实践体会,是很难把握诗之灵魂和它的精奥之处的”。(《月牙泉·后记》)从某一方面说,诗歌创作是他从事诗歌教研活动的辅助,是他的诗学主张的实践和印证。
他是革命队伍中的红小鬼,从小接受革命教育,也曾信奉“诗歌是炸弹和旗帜”的流行观念。但出于禀性,一直厌弃假大空的风气。改革开放后,在思想解放的春风吹拂下,他的诗歌观念也拨乱反正,逐渐贴近了诗之为诗的本真面目。作为高校的诗歌教研人员,他密切关注诗坛动向,不断充实自己的诗学体系。同时,他的诗歌创作也不断推陈出新,突破自我。他不仅向名家名篇学习,而且虚心向让他写序的青年诗友和学生学习,“感谢一些青年诗友(包括我的学生)以他们青春的创作朝气给了我若干启示”(《月牙泉·后记》),确实不是他的客套话。甘做小学生的“转益多师”的态度,使他能够永葆精益求精的创造活力。
一
20 世纪80 年代初,神州大地政治气候乍暖还寒。以“人的觉醒”为灵魂、以意象艺术为手段的朦胧诗崛起,引起诗坛乃至整个文化界的争论。吴开晋虽然没有置身于朦胧诗人的行列,在争论中却是朦胧诗的坚定支持者。他自己的诗作如1984 年发表于《诗刊》的《永不衰老的歌——忆母亲》已经吸收了朦胧诗的意象化技巧,较好地把借事抒情和意象抒情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他像朦胧诗人们一样,诗作不再作为载道工具,真正成为了灵魂深处发出的音响。此后,他不再作任何配合时政的歌咏,而是按照心灵的指引,更多地抒写大自然的大大小小的万千景象,在涉笔于现实和历史时,也总会发出不拘陈规的感悟。随便举几个例子吧:他笔下的厦门完全不同于郭小川心目中的剑拔弩张的《厦门风姿》:“厦门岛静卧在眠床上/裹着蓝色的绒被/那绒被是那样厚大/包着它彩色的梦……”(《波音机上望厦门》)。在他看来,勾践也并非值得大力赞扬的奋发图强的典范:“从一颗苦胆中走来/你踏着万顷湖波/一声长啸/吞没吴宫的丝弦/把千古遗恨/化入竹简”。(《太湖泛舟怀勾践》)在吴越两国的交战中,美女西施的悲剧的确是值得“化入竹简”的“千古遗恨”,勾践不就是这悲剧的始作俑者吗?历史细节的强调,显出了诗人的独特视角。在写到自己时,也不再是按照规范要求,惭愧于革命性还不够坚强,而是惭愧于“为什么我不能像你一样袒露胸怀?”(《致桉树》)过来人都知道,这可不是无关紧要的变化。
对于诗歌创作来说,更有关键作用的是,吴开晋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伴随着心灵自由状态的获取,他似乎越来越趋向万物有灵、天人呼应的神话思维,请看他的自我描述:
“面对千山万壑/我合十/十个指尖绽出十朵莲花/飘绕于蓝天/突然,我觉得/河流激向山巅/大地吻抱苍穹/山和水在合十/天和地在合十/宇宙化为冥冥”(《合十》)
“我踏着天干地支的方位/穿过浩渺的太阳系/地球月球身后涌过/金星水星涌过/火星木星涌过 土星涌过/还有天王星 冥王星//……银河系的传奇早长入耳膜/多想去检验它的真伪/牛郎织女超然人世的田园/定可去做一次拜访”(《星海漫步》)
这就是艾青心往神驰的“诗人的世界”呀:“自然与生命有了契合,旷野与山岳能日夜喧谈,岩石能沉思,河流能絮语……”(艾青:《诗人论》)心理学把这种状态叫做“移情”,按美学家的术语就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统一。这种心态让吴开晋不由得和意象艺术(朦胧诗的艺术核心)有了亲和感。
于是,吴开晋在诗作中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幅如此神奇的景象:黄山是一个渴望爱情的少女,面对着一个个追求者却又严格细心地挑选(《黄山印象》)。黄海“真后悔过早离开母亲赭黄的乳峰”,却牢记母亲的“庭训”(《黄海潮》)。英武巍峨的鸣沙山以不屈不挠的日夜守卫赢得了月牙泉的甜美爱情(《鸣沙山之魂》)。天池一心思念蓝天,绝不旁鹜,而周围的一座座山峰仍对她痴情到白头(《天池之思》)。长白美人松“琥珀般的珠泪/从亭亭玉身渗出”,源自她对远方亲人的思念(《长白美人松》)。香山红叶“如今高歌在霜风之下/每一片叶子都举起一座秋天”,是因为“有云的呼唤雷电的喧哗/奔腾于叶脉之间”(《香山红叶》)。即使常人连设想也难以设想的天体,吴开晋却对它们熟悉得知根知底。如《冥王星》:“你在遥远的太空踽踽而行/用二百七十六年苦恋作一次赤诚旳奉献/你的爱并不比金星火星少些/可仍难赢得太阳辉煌的一顾”。于是,“幽蓝的太空”来诱惑和挑拨了:“银河岸将有你耕种的沃野/沃野上将长出你心灵中的乌桕/把你的歌挂上每一片叶子/一首歌一只银亮的星斗/忘掉那缀满泪珠的苦涩的梦吧/太阳,只是浩瀚宇宙中一颗普通的星球”。天文学知识经过作者的神话思维,演绎成痴情的冥王星单恋着遥不可及的太阳的动人故事。第二人称的视角,增强了亲切感,也拉近了读者和天体的距离。
更能体现万物有灵论的是《写在海瑞墓前》:“柏树摇动着古墓的寂寞/阳光轻轻走近石碑/它读着石碑上刀刻的古字/发出叮咚的声音//透过睡石/它也许看见了古墓中那抖动的胡须/和那圆睁的眼睛/眼睛里没有泪水/仍然流淌着青色的烟和红色的火/还有一声沉重的叹息//这眼睛也许会变为种子/在某个雨后长出古墓/在广阔的天地间/怒视着每一片阴影……//弯下手臂,柏树枝开始催促/阳光向石碑、古墓告别/它们走得很慢很慢/拾走了一串串踏在石阶上的脚印”。
柏树,石碑,阳光,古墓中的海瑞,都是有灵性的,活生生的。尤其是阳光,它既能够阅读碑文,又能听到碑文发出叮咚的声音(那是凿刻碑文时留下的声音吧);它不但能够看见古墓中海瑞的种种表情乃至眼睛里“一声沉重的叹息”,还能够看到海瑞的眼睛“也许会变为种子/在某个雨后长出古墓/在广阔的天地间/怒视着每一片阴影”。诗中充满非现实、超现实的细节,有的可以用通感来解释,有的用通感也无法解释。因为整个儿构成了神话境界,在神话境界里这些超现实细节也就获得了艺术合理性,而且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对读者的震撼力。关于海瑞眼睛的种种超现实描写不是有力地烘托了他对一切(当时的和当前的)丑恶现象的义愤和嫉恶如仇性格吗?海瑞的事迹一点也没有写,确实也不必写,读者大都知道,阳光既然读了碑文,当然也就知道了海瑞的事迹。阳光对海瑞作何评价呢?诗中虽然没有说,不过阳光在告别海瑞墓时“走得很慢很慢”,可见有些恋恋不舍,这不就表露了它的肯定态度吗?可资对比的是,海瑞墓在人间却很“寂寞”,来访者稀少。可见,人间的冷淡,不碍阳光的垂青。诗中所写的不是人间的一角,而是宇宙的一角。这里昭示的不是人间道义,而是更高的宇宙法则。人在做,天在看,头上三尺有神明。较之青史留名,老天爷(阳光是代表)的肯定才是更高层次的不朽。这首诗让我们想到苏轼的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两者都是把怀古之情放在比人类社会更悠远宏阔的大自然背景之下,让读者把对于历史人物的怀念和对于大自然的敬畏连接起来。不过两者基调不同,苏词以大自然的永恒衬托风流人物的短暂;吴诗则以阳光的访问昭示杰出人物的不朽。两者写法也不同,作者苏轼在词章里直接出现,完整地抒发了自己回环曲折的内心轨迹,以“我”的情怀感染读者;作者吴开晋却退出诗外,把超现实的神话化场景交给读者去体会。由此可以窥到吴开晋对古典诗歌遗产的继承与发展。
二
“‘第三代诗人’登场以后,某些人认为这种带有忧患感的作品已经过时,似乎和诗的本体特征相违背,而突出强调诗中的生命哲学。有些作品从人的感觉出发,去写一种生命本源的冲动。他们的优秀诗作,确实叫人感到一种内在的生命律动,引起人们对自我生存价值的思索。”“从整个诗坛来讲,忧患意识和生命哲学并不构成矛盾……不论是富有忧患意识的诗也好,或者是充满生命冲动的诗也好,抑或是二者相渗透的诗,都是诗坛上的佳品。”(吴开晋:《蜕变、交融:新诗螺旋式的发展》)这是吴开晋作为诗评家的评析。与此相呼应,他在诗歌创作中,敏锐地接受了“第三代诗人”的启示,生命意识勃发,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持续关注生命过程(包括诞生、成长、衰老和死亡),二是把诗的触角伸向了一向忽略的感觉领域。
他写了多首关于生命诞生的诗,涉及泰山的诞生(《泰山之梦》,《泰山的诞生》),庐山的诞生(《庐山赋》),阳朔群山的诞生(《山之魂》),喷泉的诞生(《涌泉之自白》),大瀑布的诞生(《大瀑布》),孔子的诞生(《夫子洞》),等等。且看《山之魂》。
面对着阳朔山水,觉得这里的群山有的像雄鹰,有的像猛狮,有的像猿猴,有的像巨鲸,有的像骆驼,有的像巨龙……一般人都会有这种感受。如果凭着这样的感受去写一首赞赏阳朔群山各有姿态的诗,未免表面化、一般化。吴开晋的审美意趣没有沿着群山的外表形状前行,而是去捉摸它们相互邻近而形貌各异的背后因由,想到了它们的孕育和诞生过程,这设想就与众不同了。这个思路和作者的地质学爱好有关,更由于他的母爱意识和生命意识在无形中起着心理引导作用。
请看在孩子们(阳朔群山)即将出生时,父亲(太阳)和母亲(地球)的形象描写是何等真切:“要做父亲了/太阳兴奋得摇摇摆摆/伸出无数条光的手臂抚爱地球”。“大地母亲在烈火中痛苦地扭动身躯/……石破天惊地一声呼叫/震裂了天庭/惊呆了群星/大地母亲分娩了”。
这是对群山出生的描写:“群山从灼热的烈焰中挣出了母体/向上,向上/向往飞腾的变为雄鹰/向往奔驰的变为猛狮/向往跳跃的长成猿猴/向往长泳的成为巨鲸/向往跋涉的长成骆驼/向往腾空的长成巨龙”。
出于作者的母爱意识,结尾又有了别出心裁的一笔:“也许,真怕儿女们离体远去/大地母亲又投出一条绿色的带子/于是,漓江日夜抱着这群奇异的儿女/把群山的呼喊溶入碧绿的江底”。
这些画面既栩栩如生,又符合地质学关于造山运动的知识。由于艺术想象既贴合客体特征,又渗透着作者的特有性灵,这首壮美和柔美兼备的诗,在不可胜数的桂林山水咏唱中就显得独具特色,卓尔不凡。
生命在诞生之后如何锻炼成长?吴开晋就此也写了多首诗歌,或强调多方吸取营养,或强调坚韧顽强拼搏,或强调感恩向善,或强调戒备邪恶。更有启发性的是《看海的河流》。河流向大海奔去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困难呢?我们都会想到难免遇到各种各样的阻挠障碍,诗人吴开晋却是另一个思路:这条向往龙宫的神奇、充满看海的欲望的河流(诗中称为“你”),一路上的考验主要不是阻挠,而是一次又一次的诱惑。第一次上当是,“一跃 冲入冰川/排天的冰柱/泛出 五彩之光/心头一阵狂喜/你以为 真的到了龙宫/一睡千年”。睡梦中听了大山母亲的指教,才知道这不是龙宫,“于是 顶破层层冰柱/奋力上路”。又一次上当是,“一跃 冲入戈壁/……沙金闪烁/耀花了双眸/为你编织了/又一个五彩梦/你以为这就是龙宫/一睡万年”。多亏雷电拨开了“你”的眼帘,“你又跃身上路”。终于,“听见了大海的呼吸/听见了海燕的歌唱/大海在前/大海在前”。在商品大潮泛滥、物欲横流的当前,“诱惑”的确比“打击”更危险,因而这首诗更有警钟意义,渗透着饱经沧桑的老者对年轻人的殷切厚爱。
吴开晋关于生命的衰老和死亡的诗篇可以拿短诗《秋叶之歌》为例:“不是残叶溅血/是飘落的夏日的一串串阳光/阳光老了/一片片从树顶落下/心底还藏着跳动的火的记忆/还有蝶舞、鸟鸣和雷电的撞击/深深刻入了每一条叶脉/也许,它还要变成种子/再生长出一枚温热的歌声”。
这里的描写处处扣住了树叶的特征,只是基于万物有灵的思维方式,赋予了树叶以灵性。树叶的血液和活力来自阳光,树叶里储存着阳光带来的活力,树叶残了,不就表示树叶储存的阳光老了吗?正如人之将死,心头会重现经历过的种种一样,当残叶从枝头落下时,当然也会“心底还藏着火的记忆/还有蝶舞、鸟鸣和雷电的撞击/深深刻入了每一条叶脉”。最后两行是说,残叶进入泥土,将化为新芽的营养,新的枝叶间又会有蝶舞、鸟鸣。在这里,生命的延续和不朽比古诗名句“化作春泥更护花”表现得更加鲜丽活泼。我们无需把这首诗看做作者的夫子自道,但其中显然渗透着诗人进入老境的自我体认及其对死亡和不朽的感悟。
“五四”以来,由于诗人们普遍身负使命意识,在新诗发展史上,写感觉的诗甚少。20 世纪90 年代前后的先锋诗人们以感觉入诗,的确有拓荒意义。在他们的启发下,吴开晋的各种感觉的潜能迅速被唤醒和开发出来,写出了不少优美的“感觉的诗”。《幻美之一 ——天色》完全是视觉意象,包括“淡青色的鸽哨远去了/带走了一串碧绿的心音”。鸽哨消溶在淡青色的天际,似乎也染上了淡青色;内心向往着碧绿的树丛,心音似乎也成了碧绿的了。《幻美之二——地音》则完全是听觉意象,包括“露珠从桃花蕊间跌落/溅响了缕缕阳光”。一颗颗露珠在缕缕阳光的映照下从桃花蕊中落下,让人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联想,不是会有“溅响”的感觉吗?这一类纯感觉的诗未必寓有深意,却能把人带入幻美的境界,且能带动读者捕捉和开启自己的微妙感觉潜能。
如果这两首诗还只是短小简单的练习,《春之奏鸣曲》就更加丰富多彩了。既然是奏鸣曲,当然是诉诸听觉的,全篇都是听觉(和联觉)意象的组合。置身于春到人间的氛围,犹如欣赏奏鸣曲一样,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感,这感觉是我们都能体会到的,不过我们的感觉却不如诗人吴开晋那样细致入微。在他的感觉里,春之奏鸣曲既浑然一体,又层次分明:先是“一缕微弱的琴音发自地心”,这是“一股暖流弹出的独鸣”。——继而,“琴音变为和弦,大地响彻起伴奏”,其中包含着“小草胚芽伸展腰肢的声音”,“冻土开始溶解的声音”,“蚯蚓翻身滚动的声音”。——接着,“东风拨响了竖琴/阳光洒下一片珠韵/雁鸣声声,似高音号/吹沸了大地的血脉”。——终于,高潮到来,“春潮奏起了管弦的交响”,迎春花、桃杏花、玉兰花相继绽放(似乎可以听到一片闹嚷嚷),“百鸟合唱起欢乐颂”,“我心中的春天来了”。无需去追寻其中的言外之意,这种只有身心解放才有的春到人间的愉悦感受,不是可以扣动我们的心弦,唤起我们的共鸣或向往吗?
诚如吴开晋在诗学著作中所说:生命意识和忧患意识不构成矛盾,写感觉和思想性也不构成矛盾。请看《笼中画眉》:“精铜的隔条/切割着蓝天白云/在太空纷纷散落/金丝的绦带飘飘/把你破碎的目光轻拂//声声啼鸣 飞射笼外/把渴望投向遥远/但你的歌声又被切割成碎片/忧伤的音符/缀满云雀的羽翅”。
第一节呈现的是笼中画眉鸟的视觉感受。前三行是说,由于笼子“精铜的隔条”的切割,画眉鸟向往的蓝天白云现在连看也看不清了。下面两行是说,画眉鸟厌恶的衣着华丽的参观者又扰乱着它的“破碎的目光”。可见笼中画眉是多么郁闷愤懑。第二节呈现的是作者的听觉感受。不但听得出画眉的啼鸣“飞射”(何等强劲!)笼外,却被笼子的隔条“切割成碎片”,还听得出画眉的忧伤的音符“缀满云雀的羽翅”(可见笼中画眉多么羡慕飞翔的云雀)。这些当然不是普通的听觉感受,而是诗人特有的听觉感受。这些视觉感受和听觉感受,不仅给人以美感,还给人以启迪,至少让人体会到:牢笼,不论多么华美的牢笼,都是摧残性灵的,必须冲破的。这不就是“情绪感觉化”或“思想知觉化”吗?
三
朦胧诗后的先锋诗人,“pass 北岛、舒婷”的艺术手段之一,是以“事态结构”和“冷抒情”取代意象抒情。吴开晋在诗歌创作中,吸取了这些先锋诗人运用“事态结构”的艺术技巧,却没有采纳其“反意象”和“冷抒情”的主张。他在创作中并不故意关闭情感闸门,而是让情感自然地渗入叙事,把事态结构和意象艺术融合起来。抒写社会生活的诗是这样,抒写自然景物的诗也是这样。前面提到的《写在海瑞墓前》所写的虽是一个短暂的场景,却展开了一个相当完整的过程,从阳光到来,到阳光离开,顺序连贯,有头有尾。这过程并不是用日常语言“述说”出来的,而是由一连串饱含着感情的意象连缀而成。
吴开晋写了很多山水景物诗。他赞赏孔孚的山水诗,既赞赏孔孚提倡的“东方神秘主义”,也赞赏孔孚恪守的“减法”。吴开晋的神话思维和孔孚的东方神秘主义相通,但在写法上,并没有效法孔孚的“减法”。孔孚惯于抓住一个最动人的瞬间镜头,以少胜多。吴开晋却惯于展示一个过程。例如,关于庐山,孔孚有《庐山印象》:“雾蓑云笠/挑两湖鱼//被风这个浪荡公子/踢翻了……”。吴开晋有《庐山赋》,写的却是庐山由坐胎到诞生的情景。关于泰山,孔孚为一处处自然和人文景观提供了一幅幅定格的画面,吴开晋却反复写他对于泰山诞生过程的设想(《泰山之梦》《泰山的诞生》),即如《黎明的泰山》,也是写泰山起床前后的几个连续动作。可能是因为吴开晋对天文学、地质学一直有浓厚兴趣,面对日月星辰、山水景物时,不仅欣赏其形态,同时会不由得探究和设想其来龙去脉吧?
20 世纪90 年代前后的先锋诗人之所以标举事态结构,是为了让诗歌不走样地表现日常生活。吴开晋不是这样,他的诗作中所叙的“事”并非不走样的实际的事,而是大大走样的想象的事,神话化的事。他笔下的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鸟兽虫鱼,都是有灵性的。灵性来自哪里?来自他的神话思维。就具体作品的酝酿来说,是来自作者“长期积累,一朝得之”的灵感。
请看他的《方形日出》。诗前小序:“东海某岛,由于湿度光度影响,黎明日出,呈方形……”一般旅游者只觉得这是有趣的天象,兴趣集中于观赏这稀罕的景象。诗人吴开晋关注的却是太阳在海上升起时为什么会变成方形,于是浮想联翩。圆圆的太阳变成方形,一定是受到了挤压,谁挤压太阳呢?既然是“由于湿度光度影响”,挤压太阳的肯定是波涛和乌云。于是在他的想象中逐渐完整地展现了如下的惊心动魄的过程:子夜,太阳在海底做着“椭圆的梦”,而波涛、阴云却在密谋陷害太阳。——天鼓发出警报,太阳惊醒起床。乌云、黑浪拼命挤压太阳火红的身躯。——在天鼓的助威下,太阳奋力挣脱禁锢,四肢挥击,由于受到挤压,呈方形艰难地跃出海面。——乌云、海浪欢庆胜利,宣称“方形的太阳将是我们的俘虏”。——在天鼓的助威下,太阳的血管爆长,深深吸气(这都是恢复原来的圆形的必要准备),一跃而升入云空。——乌云、黑浪偃旗息鼓,火红的太阳滚向苍穹。诗中的情节、场景是虚幻的,又是真切的。诗中说太阳在海底睡眠,然后从海底升起,这和历来的传说及人们的日常感受是一致的。黑浪、乌云作为反面形象,而天鼓为正义的一方助威,这也和历来的传说及人们的习惯一致。诗篇的描述,不论整体和细节,都显得贴切自然,毫无牵强之处。就这样,作者把一种特异的自然现象巧妙地变成了一个壮美的神奇故事。平铺直叙的连贯叙述,并没有减损诗的魅力,反倒增添了质朴感。
“事”的诗化和“叙”的诗化是保证事态结构的诗歌成功的关键,后者又服从于前者。“事”的诗化是诗人“长期积累,一朝得之”水到渠成的结果,如果刻意为之,反而会吃力不讨好。吴开晋偶尔也有这种败笔,如《苏醒的灵魂》。诗前小序说明真实的故事是:“多年前在北京玉渊潭射杀白天鹅的人,出狱后救了一名落水的孩子,后死去。”在诗中却对故事做了如下的改写:被射杀的白天鹅(“你”)死而复生,“有一天又驾乘小舟在飞翔/狂风袭来/你又坠入深渊”。这时曾经射杀白天鹅的那个刑满释放者入水把白天鹅救起,自己却被淹死。这种改写,既不合神话思维的心理逻辑,也不是灵感状态下不由自主的想象,因此颇多漏洞:白天鹅复活后飞出渊底不是轻而易举吗?为什么要“驾乘小舟”呢?一阵狂风怎么就能把白天鹅“倾入渊底”呢?……这些漏洞泄露了刻意编造的痕迹,难免引起读者阅读时的拒斥。另外,“驾乘小舟在飞翔”,“你用心音编织着蓝色的年轮”(意思可能是一年又一年,你心里向往着蓝色天空),“像齐格弗里特王子举起奥杰塔/把你高高托举到云空”,这些意象似过分雕凿。全篇用第二人称的口气向天鹅诉说,这视角的确定也未必恰当。(当然,那个痛改前非的人在入水施救孩子时可能想到几年前被他杀死落水的天鹅,甚至可能把落水的孩子和天鹅在幻觉中叠合起来。如果通过施救者的心态来写这个故事,就要全盘重新酝酿。)
四
吴开晋的心灵自由状态并没有让他放弃重大题材的抒写,反而提升了他把握和抒写重大题材的能力。
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 周年之际,吴开晋献出了政治抒情诗《土地的记忆》。不写人类的记忆,而写土地的记忆,一奇。战争的场景血雨腥风,变幻万千,却集中于写听觉记忆,二奇。难道是作者挖空心思地要避熟就生,追求陌生化效果吗?不是。作者对重大题材举重若轻的、新鲜又深切的审美感受,得益于他的神话思维习惯,也来自无意得之的灵感和精益求精的构思。基于万物有灵、神话思维的习惯,他可以不假思索地就认定土地有对于战争的记忆。进而,这种认定和留声机的印象相遇合,就形成了呈现一处处土地所记忆的各种声音的意象群:“那隆隆作响的/是卢沟桥和诺曼底的炮声/还夹着万千染血的呐喊/那裂人心肺的/是奥斯维辛和南京城千万冤魂的呻吟/还有野兽们的狂呼乱叫/那震人心魄的/是攻占柏林和平型关的号角/还有枪刺上闪耀的复仇怒吼”。这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意象(“平型关”的分量稍轻),涵盖了全球领域的反法西斯战争中正义和邪恶双方的突出战例,既表现了法西斯战争狂人给各国人民所制造的灾难,又表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浴血奋战和来之不易的胜利。作者最后说:“安乐是一种麻醉剂/人们也许把过去遗忘/但土地不会忘记/……每当黎明到来/它便在疼痛中惊醒”。把忧患意识和坚定信念化为富有张力的强烈对比画面,这种写法当然比直抒胸臆的呼吁、号召更有诗意,也更有诉诸读者心灵的渗透力。可见,重大题材不是不能写出好诗,而是要求诗人有更高的诗化它的能力。正如作者所说,“载人民命运之道的’大诗’永远值得提倡;但那要有丰厚的生活积累和对社会的深刻观察,并有不可解的强烈的诗情和高超的艺术手段,不能陷入说教和对某些政治概念的图解”。(吴开晋:《倾听春天·篇末赘语》)在这方面,吴开晋的诗作也给他的诗学主张提供了佐证。
——论交响乐组曲《草原意象》的意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