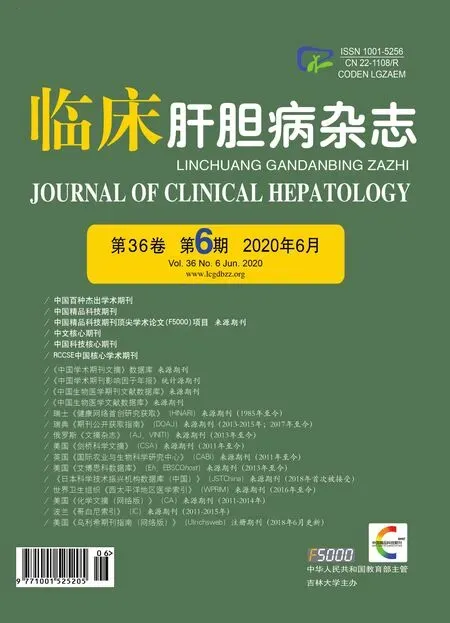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及其配体抑制剂治疗肝细胞癌效果的预测因素
哈福双, 韩 涛, 唐 飞, 闫俊卿, 王浩宇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天津市重症疾病体外生命支持重点实验室, 天津市人工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天津市肝胆研究所, 天津 300170
肝细胞癌(HCC)是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原发性肝脏恶性肿瘤,在过去几十年成为癌症相关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1]。由于患者不适症状出现较晚,难以早期发现,只有不到20%的HCC患者能够接受根治性手术切除、消融或原位肝移植,而大多数进展期HCC患者只能接受姑息性治疗[2]。自2007年引入分子靶向药物索拉非尼以来,HCC的系统性治疗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2017年9月、2018年11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先后批准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1, PD-1)抑制剂纳武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用于治疗进展期HCC以来,HCC的治疗进入了免疫治疗时代。然而数据表明只有少数HCC患者受益于这种治疗方案。目前,大量研究旨在找到免疫治疗的优化人群,从而提高抗肿瘤疗效。
1 HCC患者肝脏的免疫特点
肝脏有肝动脉和门静脉双重血供系统,肝血窦中充满免疫细胞,肝细胞同时暴露在大量肠道病原体及无害抗原如营养抗原中[3]。肝脏为适应这种独特的抗原暴露环境而呈现一种固有的免疫耐受状态[4]。HBV、HCV、酒精等均可导致肝脏的慢性炎症反应,故HCC是在肝脏慢性炎症状态下发生的恶性肿瘤。这种慢性炎症基础促进了抑制性免疫细胞因子进一步抑制免疫反应并有利于肿瘤细胞生长[5]。在HCC进展过程中,由于这些细胞因子的分泌,调节性T淋巴细胞和骨髓来源的免疫抑制细胞也被募集到肿瘤部位,进一步强化了已经存在的免疫抑制状态[5-6]。近年来,人们发现在HCC病灶中常见的几种免疫检查点信号通路受体会上调,使得免疫细胞无法激活并攻击肿瘤细胞[7]。
2 抑制PD-1及其配体(PD-L1)信号通路治疗HCC的疗效
PD-1是一种广泛表达于多种免疫细胞类型的细胞表面蛋白,如CD8+T淋巴细胞、CD4+T淋巴细胞、B淋巴细胞、自然杀伤细胞等[8]。PD-L1与PD-1连接后,可直接抑制T淋巴细胞的增殖和其效应功能[9]。生理条件下,此信号通路用以维持炎症稳态、保护组织完整性并防止不必要的自身免疫反应[10]。在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PD-1/PD-L1信号通路上调,使得肝脏微环境中有效的抗肿瘤免疫监测功能受损[11]。基于CheckMate 040及KEYNOTE 224的研究结果,FDA于2017年9月、2018年11月分别批准PD-1抑制剂纳武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作为进展期HCC的二线治疗用药。尽管新的治疗方案给HCC患者带来了更多的希望,但PD-1/PD-L1受体抑制剂大约在80%的HCC患者中效果欠佳。此外,其治疗费用高昂,药物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较高[12],迫切需要找到治疗效果预测因素,使患者得到更多临床获益。
3 应用PD-1/PD-L1抑制剂治疗效果的可能预测因素
HCC患者应用PD-1/PD-L1抑制剂治疗效果不佳的原因复杂,包括免疫原性的突变、细胞因子信号缺陷和肿瘤细胞上调免疫检查点途径相关信号因子等。迄今为止,关于HCC应用PD-1/PD-L1抑制剂治疗效果的预测生物标志物的报道甚少。本文将回顾在HCC及其他肿瘤类型中进行研究的生物标志物,这些标志物均可能与PD-1/PD-L1抑制剂治疗HCC效果预测相关。
3.1 PD-L1的表达 有研究[13]表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高表达的PD-L1水平与较高的客观缓解率和生存率有关,然而,CheckMate-040研究[14]结果却显示,HCC患者基线肿瘤细胞PD-L1水平对客观缓解率没有明显的影响。在某些肿瘤类型中,肿瘤组织浸润免疫细胞上的PD-L1表达水平可能比肿瘤细胞上的PD-L1表达水平更能预测PD-1/PD-L1抑制剂的治疗效果[15]。因此,HCC浸润免疫细胞上的PD-L1表达水平可能是对PD-1/PD-L1抑制剂反应的潜在标志物。为明确此种假设,需进一步解决以下问题:如何定义PD-L1高表达的界限值[16];统一用于检测PD-L1水平的抗PD-L1 抗体,提高实验结果的可靠性和重复性[17]。
3.2 肿瘤突变负荷和微卫星不稳定 肿瘤在转化和发展过程中获得了不同的体细胞突变,肿瘤细胞的遗传异质性是恶性肿瘤的基本特性[18]。肿瘤突变负荷(tumor mutation burden, TMB)被定义为肿瘤基因组中每个编码区域的突变总数,其范围从数个到数千个不等[19]。体细胞突变如点突变、框移突变或插入、删除突变,产生新的蛋白质或肽序列被称为新抗原。TMB水平较高的肿瘤一般表达了更多的新抗原,这些新抗原可能使免疫系统产生更强的抗肿瘤反应,因此可能对免疫治疗产生更好的效果。高水平TMB已被证实为多种恶性肿瘤应用PD-1/PD-L1抑制剂更佳疗效的独立预测因素[20]。但是,如果TMB未能表达高质量的新抗原则可能导致T淋巴细胞并不攻击肿瘤细胞。例如参与MAP激酶通路活化的KRAS和BRAF基因突变或其他突变,可减少Ⅰ类MHC分子的表达或影响肽合成过程中的重要分子,导致即使在高TMB患者中,抗肿瘤免疫能力依旧不足[21-22]。目前,测定TMB需要进行全外显子测序,费用昂贵且耗时较长[23]。因此,应用TMB预测HCC患者应用PD-1/PD-L1抑制剂治疗的效果,仍需进一步探讨。
微卫星不稳定(microsatellite stability, MSI)是由错配修复缺陷引起的超突变表型,是FDA批准的首个PD-1抑制剂治疗的预测生物标志物[24]。然而目前数据表明,在HCC患者中,很少能观察到MSI[25]。
3.3 肿瘤微环境 目前,普遍认为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的异质性可能是导致肿瘤特异性T淋巴细胞活化、克隆增殖以及肿瘤免疫治疗效果差异的部分原因[26]。肿瘤微环境大体分为两个类型:其一,“热”免疫炎症型TME:表现为更高密度的CD8+肿瘤浸润淋巴细胞;更高水平的干扰素和干扰素刺激趋化因子,如CXCL9、CXCL11等[27]。一项荟萃分析[28]表明,CD8+T淋巴细胞的浸润与多种实体肿瘤类型的化疗和免疫治疗反应的改善有关。有研究[29]显示,肿瘤细胞对PD-1抑制剂的应答需要预先存在CD8+T淋巴细胞,这些细胞受PD-1/PD-L1介导的适应性免疫耐受负调控。故“热”免疫炎症型TME可能预示PD-1/PD-L1抑制剂的治疗获益。其二,“冷”免疫炎症型TME,通常表达与免疫抑制或耐受相关的细胞因子,如IL-10、IL-35、IL-4、TGFβ等,这类肿瘤通常对PD-1/PD-L1抑制剂治疗反应较差[30-31]。但在HCC患者中,对肿瘤微环境的评估仍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首先,此类检查需要肝组织活检,并需要几种抗体的组合、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来验证,实验过程复杂;其次,HCC患者尤其是多灶性HCC患者存在肿瘤异质性,活检样本难以反应肿瘤病灶全貌。因此,现阶段应用TME预测HCC患者对PD-1/PD-L1抑制剂的治疗反应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3.4 液体活检 “液体活检”是指对血液或其他体液进行低侵入性或非侵入性检测以提供患者肿瘤遗传信息的一种检查方法,避免了有创肝组织活检中肿瘤异质性及取样变异性的弊端[32-33]。“液体活检”的肿瘤信息来源包括循环肿瘤游离DNA、循环肿瘤细胞、从体液中(如血清、血浆、尿液、唾液)循环的外泌体等。虽然“液体活检”已经在结直肠癌、乳腺癌和肺癌中用以预测治疗反应和监测复发[33],但在HCC临床应用的数据仍旧有限。下面列举相对有前景的“液体活检”检测项目及目前研究结果:(1)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率是非小细胞肺癌对纳武利尤单抗治疗效果的预测因素之一[34]。(2)在HCC中,PD-1等免疫检查点分子在肿瘤组织中的表达水平,可部分由检测血液循环中免疫细胞的检查点分子的表达间接反应[35]。(3)基线高水平抗炎症细胞因子TGFβ可能与进展期HCC患者PD-1抑制剂治疗后预后差相关[36]。(4)基线高水平可溶性PD-L1水平与HCC患者较差预后相关[37]。(5) 细胞外囊泡如外泌体和微囊泡从包括肿瘤细胞在内的各种细胞释放,并携带影响免疫系统的生物活性分子。有研究[38]表明,对PD-1抑制剂有治疗应答的黑色素瘤患者,在治疗早期循环外分泌体中PD-L1水平增加。(6)有证据表明,评估循环肿瘤游离DNA中的TMB可能是可行的,它避免了肝活检中同一患者不同病灶的肿瘤的异质性和取样的变异性[39]。综上,“液体活检”有可能成为预测HCC患者对PD-1/PD-L1抑制剂治疗反应的重要工具。
3.5 肠道菌群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肠道菌群在肝脏炎症和HCC发生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40]。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原发耐药可能是由患者的肠道微生物成分异常导致的(如抗生素相关的肠道菌群失调)[41]。而且,肠道微生物菌落特性还可能与免疫相关的药物不良事件的发生有关,如治疗导致的免疫相关性小肠结肠炎[42]。目前,肠道菌群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应答的影响尚未在HCC中得到明确验证,仍需进一步研究。
3.6 性别及年龄 一项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随机对照试验进行的荟萃分析发现,男性的总体生存获益明显高于女性[43]。一项回顾性研究[44]指出,与男性相比,年龄<65岁的女性患者对PD-1抑制剂治疗的客观反应率较低。另有研究[45]表明,年龄在60岁以上的患者对PD-1抑制剂治疗有更好的反应。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衰老都与性激素的丧失有关,因此,性别相关的差异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部分消失。目前,关于性别和年龄对疗效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4 未来展望
目前,HCC已跨入免疫治疗的新时代,PD-1/PD-L1抑制剂给HCC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但目前绝大部分患者疗效欠佳。寻找高敏感性、高特异性预测治疗效果的生物标志物,对于优化治疗方案是必要的。尽管目前在其他肿瘤的治疗中已有一些有希望的预测因素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但关于预测HCC患者治疗效果的生物标志物的报道甚少,仍需要大量的研究予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