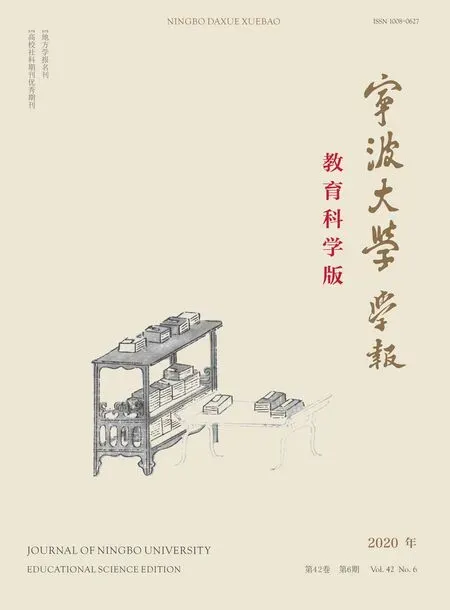价值行为中的知行不一现象及其消解研究
张晓霞,崔岐恩
价值行为中的知行不一现象及其消解研究
张晓霞,崔岐恩
(温州大学 教育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非价值行为与价值行为之间有一个连续的谱系,它们并非泾渭分明,知行不一呈现为多样模态。个体若在生命早期通过教养获得价值行为与情感方面的良好惯习,并不断学习社会价值知识使之内化为生命的一部分,他就很可能变成为“有价值感”或“有价值原则”的人。另外,若他在价值智慧方面同样努力修炼趋于完善,则可能获得心灵的自由,成为应用伦理学中所说“明智”者。人一生若一直处于这种惯习与明智状态下,那么他就能时刻自制自律而使“知”“行”合一。若“知”与“行”都声称自己正当但实践中仍然冲突,则需“善”的斡旋。知行不一不仅拷问个体良心,更是拷问社会良知。知行不一更是社会公正与否的风向标,社会据此不断改良完善,消解外在不当规制措施,从而减少假知和伪行,将低层次的知行合一、表里如一,在持之以恒地内外兼修中,逐步走向有深度的表里如一、有高度的知行合一。知行不一作为一种现象,不仅仅是实在性行为,更是关涉话语实践——在知与行之外,还有语言符号的遮蔽,也即完整的链条应是:知—言说—行。
价值品质;价值行为;价值智慧;知行不一;知行合一
一、引言
在儿童访谈中,笔者发现很多孩子清晰认识到玩电子游戏弊端远大于好处,也能承诺周一至周五不再玩电子游戏。事实是,仍有孩子偷着玩,尽管高度近视。为何呢?简单而言,似乎源于外在诱惑力大于内在自控力。这种知行不一现象非常普遍,好像也无关乎正当和正义问题。但若对于美德论者如麦金泰尔或屈原,知行不一则是难以原谅的,因为那是“好人”“美人”所不齿的品行。而对于严苛的道义论者如康德或孟子,则知行不一乃大忌,因为事关人世间非常重要的一种价值——诚信。他们所秉持的“道德律令”“舍生取义”非常人所能笃行。
“知、情、意、行”是我们熟知的心理—行为模式,“行”即价值行为或德行。“知行不一”是指一个人在认知和判断上明确何为正当的、善的,但却在实际行为中反其道而行之,即价值认知与价值行为相悖逆。规范伦理学一般认为,正当的价值行为应该遵循价值规范和正当性原则,但对背后的动机、主体幸福等并不苛刻追问。德性论一般着重考察人的内在心灵状态和个性修养,而不拘泥于外在规制。功利论主要权衡行为的成本和付出是否值得。“知行不一”固然不同于“表里不一”,后者更加宽泛,暗藏了假知或真知,不过都可以在三种伦理学视域(规范论伦理学、德性论伦理学、功利论伦理学)得到某种阐释——凡事都是合理的,就看合哪种伦理。赵汀阳《论可能生活》从目的论角度提出人的价值行为一般有两个原则:一是行为原则,它要求价值行为合乎外在规范(类似于规范伦理);二是行动原则,即价值行为应该合目的,意味着追求卓越品质(类似于德性伦理)。单纯的行为原则,若刚好体现良好价值,有利于公共福祉,则只是不坏,其价值品质水准远低于合目的性的行动原则。
伦理学中也一直追问:人们知恶而故犯或知善而不为的原因究竟在于缺乏对价值原则、体系的领悟,还是在于践履价值原则的价值智慧不够高明,或是价值品质不够卓越?“知行不一”问题也是这种伦理问题的另一种表征——知道怎么做是正当的、好的却做不到,或者做得相反?明知是恶的事情反而故意去做?
二、知行不一的宏观分析
知行不一是个悠久的历史问题,自从古希腊苏格拉底“美德是否可教”便在西方伦理学、认知心理学、组织行为学领域成为热点题材。中国孟子“恻隐之心”,程朱理学“知先行后”,陆王心学“知行合一”,孙中山“知难行易”等等,都显示出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哲学家如此纠缠不清,而实践层面更是雾里看花。当代心理学尝试实验法、归纳法,结果仍然只是“罗素鸡”的一地鸡毛,实证量化研究难以做出可靠信效度的归因分析。本文只能从伦理学、心理学、认知哲学角度做解析。
(一)价值智慧对价值行为的统摄
张维迎曾说,“人类犯错误或干坏事有两种原因,一是无知,二是无耻。此二者很难区分,许多无耻行为从根本上讲也是因为无知,是缺乏智慧的表现”。[1]理论是干瘪的,而生活是鲜活的,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皆是读书人。有时“知”未必比“无知”更加正当,其价值行为未必有更多的善。精致的利己主义一再受到人们批判,但是否内涵着某种正当的价值行为?在多元化社会,价值冲突是开放的民主社会的必然因子,相爱相杀,互相质疑、批判,最终达至重叠共识。一以贯之地坚持某些正当性价值原则,难保不冲撞另一些价值原则,尽管都有某种意义的正当性。如何能够驾驭不同维度的正当性?也许只能诉诸于高超的价值智慧。
智慧,指个体经由实践经验与内在天赋获得的一种良善而恰当地解决人的问题或人与世界关系问题的多元智能。价值智慧——价值主体在各种情感、天赋、理性和经验的作用下对价值原则进行判断与择取、解构与重构、内化与实践过程中表现出的多元智能。价值智慧是价值品质的灵魂,是价值实践中“正当”“善”“幸福”三者统一的内在保障。价值智慧=价值实践智慧+价值认知智慧。[2]8此假定源于亚里士多德思想,他把良品区分为两类,一是“哲学智慧”(philosophic wisdom),包括明智、技艺、科学、直觉理性(nous of intuition);二是“实践智慧”(practical wisdom)或“道德德行”(如希腊民间流传的勇敢、自制、慎思、公正)。另外,本研究认为,外在价值原则内化为内在价值体系离不开价值认知,这便是“价值认知智慧”的来源;而内在价值原则外化为价值行为就是一种价值实践,这便是“价值实践智慧”的来源。
价值认知智慧能够对价值形势、价值及其具体原则进行察觉、筛选、批判、重构、内化等心理运作,能够辨清何种理域(真理、伦理、法理)或何种正当性。[3]价值实践智慧能够通过理性算计、灵感顿悟、良心发现、本质直观等方式提供与其价值形势相匹配的好的价值实践方式和途径。价值行为是主体在意志自由状态下根据价值原则、运用价值智慧进行的实践活动。
非价值行为与价值行为之间有连续的谱系,它们并非泾渭分明,知行不一呈现为多样模态:(1)不知不行——总体价值智慧缺乏,心理机制中“注意”、价值敏感性等迟滞;(2)行而不知——价值认知智慧的缺乏,外在价值评价的误判;(3)知行相左——价值认知智慧与实践智慧不匹配;(4)知而不行——价值实践智慧的缺乏;(5)知行合一——总体价值智慧的充盈和谐。
(二)知行不一的心理学机制
行为主体的价值智慧卓越,则其价值行为的“最初结果”一般也会好。黑格尔说“意志只对最初的后果负责,因为只有这最初的后果是包含在它的故意之中”。[4]一个行为产生的结果常常包含着次生性的东西和偶然附加的东西,这些与行为本身的本性无关。“最初的结果”就是行为自身的结果,而不包含那种听命于外界力量,且受这些力量把自为存在的行为全然不同的东西与行为结合起来而产生的次生性结果。但在实践中常常会出现价值原则与价值效果间不一致的现象,根本原因在于主观价值预期向客观价值实效的转化中受到诸多制约,如:第一,择取、建构的价值原则是否符合客观事物规律(真理正当性);第二,择取、建构的价值原则是否符合良心和道德准则(伦理正当性);第三,择取、建构的价值原则是否符合契约、法律及其内在逻辑与精神主旨(法理正当性);第四,行为主体的价值智慧运作状况;第五,行为本身的客观环境因素;第六,是否具备各种实践手段;第七,非预期的偶然事件。这些因素都将影响预期效果,甚至可能产生与价值原则完全相反的坏效果。
“知行不一”问题很复杂,从知与行关系的内在心理机制看,存在多个变量,如人格特征、认知类型、个体认知能力、价值判断力、价值敏感性等。基尔戈尔(Killgore)等发现那些睡眠不足的被试更倾向于做出功利性价值判断,[5]但情绪智力较高的被试却并不明显。[6]另一些研究者还发现,沉思型(偏重理性思考)个体、工作记忆能力高的个体更倾向于做出功利性判断。[7]美国心理学家科尔伯格在继承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和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McDougall)学术思想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了道德教育中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学生知行不一。他认为:价值判断与行为的一致性程度与价值判断能力之间显著正相关。心理学研究已经证实:青少年言行不一致的问题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或许因为价值智慧发展了。朱智贤教授认为这种现象并不表明他们有意这么做,而是由青少年心理发展的4个特点决定的:模仿的倾向性;出于无意;以情感代替理智;缺乏价值意志。[8]实际上,随着年龄增大,其价值认知中的价值原则固然越多,但其价值智慧还不足以把这些散乱的价值原则建构为一个适切的、内部一致性很强的价值体系;另外年龄越大,行为的场域和性质则越复杂,而将内在价值原则外化为价值行为尚需高超的价值智慧,价值智慧作为一种实践智慧能够根据情境选择合适的价值原则和行为方式。青少年固然能够快速掌握关于原则、规范的价值知识,但其价值智慧却不能一蹴而就。
“有知识无头脑”是知行不一的一种表征。基于维果茨基的研究,我们认为价值智慧以及人本身都在实践活动中透过内外双向律动而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一是主体客观化即内在价值智力动作外化为实际价值行为;二是客体主观化即外在价值行为内化为高级价值心理机能。[9]这种双向律动对于“知行不一”的启示:内化(外在的价值原则经鉴别、筛选、批判、重构为内在的价值体系或价值秩序)的内容、过程是否符合主观世界;外化(内在的价值体系在价值实践智慧的引导下转化为价值行为)的形式、方法是否符合客观世界;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是否统一。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认识世界)更多的依赖主观世界,当然也关涉客观世界;行(改造世界)更多的依赖客观世界,当然也关涉主观世界。主客二分、物质与精神二元,应该是知行不一的先在性根源。
(三)“良知”作为价值行为的前提
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哲学思想被称为“重知论”,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一直流淌着“重行论”的脉源。行比知更难,故而更重要。《尚书》言“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用在价值品质领域就是说,知悉价值原则容易,而践行价值原则艰难。孔、孟将“知”与“行”两者置于“学”上(修德),从而尽量化解“知”与“行”的距离。至宋代,出现以“知”为进路的重大转向,如陆、王讲心即知,程、朱重格物致知。知者,知悉、知道也。知方能行,知即是行。明清之后,再次转向——恢复了治学上重行的传统。孙中山曾讲“知难行易”,意思是知并不等于行,行更加容易且更重要。中国思想总体上是强调“行”比“知”更困难、更重要的。
古希腊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不正当行为是由于“无意”或非志愿或被动,人并没有明知故犯的道德弱点。[2]7“没有人追求对他显得恶的事物;如果一个人在作恶,一定是因为他不知道那是在作恶;一个人之所以知善而不为,是因为他并不真的知道那是善”[10]。兹后,价值论便与认识论纠缠,宗教哲学、休谟(从事实命题难以推导出价值命题)、康德(先天综合判断)、普特南(厚事实与厚伦理间可互导)等思想的深处都反映了西方一种“真理情结”。价值品质理论可以对此做出一种解释:首先,按照康德“先天综合判断”思想,价值原则与体系若要作为“知识”,则需满足两点:一是个体的感觉经验,二是具有普遍必然性。
第二点姑且悬而不论,我们检视第一点是否满足呢?答案非常悲观。我们的家长和教师习惯于对学生命令“不许乱动”“别胡思乱想”“没有为什么”“这就是唯一的标准答案”“记住就行了”“你应该……”“这是……的规定”“大家都如此的”“本来就这样的”,等等。某些政权管理者排斥公共参与和监督,党同伐异一言堂,公民被暗箱操作潜规则。独断、霸道、宰制、规训,总之剥夺了个体鲜活的生命体验。也即这种模态的价值原则和体系不成其为“知识”,遑论“认知”,所以价值行为的知行统一仅仅是误打误撞的小概率事件。
其次,纵然价值原则与体系通过教授而被个体所“经验”,但价值行为习惯的矫正则比较困难,要坚忍不拔地长期体悟。但是价值行为终究是个体内心价值原则—价值智慧合成运作后的终端产品,而价值智慧是价值品质的核心,是价值实践与行为的发动机。价值原则的觉解与价值智慧运作下的践行之间始终有个鸿沟——这正是价值品质内在张力的体现。
三、教育可否促成知行合一
(一)价值之知是否可教
一般认为,学生学习知识,知识当然可教的。但转识成智自然而然地发生吗?品德是否可教?能力与智慧是否可教?这也是知识的能力性和伦理性研究必须关注和讨论的问题。郝文武认为,不仅知识可教,而且能力和品德也可教。若将教或教育理解为给予,不仅品德、能力不能教和给予,且知识也无法教给或给予。难道真的如一桶水和一瓢水的关系?但若将教或教育理解为启发、引导、指导、影响,则不仅知识可教可导,而且行为习惯、实践能力、品德修养、价值智慧皆可教可导。
知识不是死记硬背的公式定律,不是大量刷题在脑海中留下的残余,而是在包括主观性努力基础上通过泛教育(学校、家庭、网络和社会环境)教化下习得的,当然,也不排除头脑中先天固有的认知模式、情感基因等。
教化的本质是学生从偶然性的自然天性出发,向着普遍性的超越与提升,这种超越的基础正是幼年时期充分发展的自然性,也即个体自然感性生命的充分萌发。[11]幼年时期充分发展的自然生命将个体品德超越性成为一种内在的自我实现。柯尔伯格通过海因兹偷药故事伦理推理,总结学生品德发展的三水平六阶段,说明学生随着身体、心理发育,内在地倾向于更高层次的德性水平。如果已经达到高阶水平,这种水平足以导向一个内心的呼唤“我要知行合一”,那么他会鄙视那些低阶价值行为,也即阻滞了内心知行不一的龌龊想法。布鲁姆、马斯洛等也有大量实证研究发现,学生的心智模式、自我实现的愿望总会随着长大成人,自然而然地跃迁,就如石头压制下的一棵幼苗,总是向阳而生。幼儿成长之路上,应该有自由空间以便自我生命充分地舒展、历练,并实时得到反馈和激励,护佑个体生命真正翱翔起来,才可能有成长后期充分的主体意志、深度反思与生命自觉。
(二)价值品质如何生成
若把基于同一价值原则的所有价值行为看作是同一类价值行为,则可简称为“类价值行为”。“类价值行为”体现价值品质。因为品质追求卓越,而卓越在于其功能的行使。即价值品质作为一种潜在的卓越,它要在价值实践之中才能实现和展开。价值品质是灵魂或精神的一种特殊状况或倾向性特质,是对人进行价值评价的依据。[12]而且价值品质还不仅是一种状况,更是人身上先天禀赋与后天习得的一种稳定的特质。良品特质是一种卓越,是人之为人本性的圆满;这种特质的实现,是指价值品质作为一种倾向性会产生与这种特质相同的正当行为。由于一种品质在概率上更会导致一种行为A,而不会导致行为-A。亚氏在他的伦理学中不断地说要成为公正的人就要做公正的事、要成为节制的人就要做节制的事等等。[13]
良好价值品质的生成原因有二:它的最初的原因是良好的行为与感情习惯通过训导与矫正而形成,进一步的原因是这种良好习惯被随后发展并得到引导的价值智慧理解为好的,理解为人自身的一种善。价值智慧的生成亦有双重原因:一方面,它有一个理智的“种子”;另一方面,这个理智的“种子”只有在良好的实践品质的“土壤”上才能够生长。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价值原则与价值智慧乃相辅相生、共荣共存。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实践是社会关系的本质和基础,一切人类意识都产生于实践。那么价值原则与价值智慧,最终都毫不例外地依赖于实践的性质。知行不一问题追根究底在于其价值实践的状态与性质。
个体若在生命早期通过教养获得价值行为与情感方面的良好惯习,并不断学习社会价值知识使之内化为生命的一部分,他就很可能变成为“有价值感”“有价值原则”的人。另外,价值品质的生成需要个体持久地做出艰苦的努力——为了自身内在的品德,自觉自愿地努力与懒散、颓废、敷衍做斗争,努力做正当之事,努力遇见最好的自己。[14]如果他在价值智慧方面同样努力修炼趋于完善的话,他就能获得心灵的自由,成为应用伦理学中所说的“明智”。[15]人一生若一直处于这种惯习与明智状态下,那么他就能时刻自制自律而使“知”“行”合一。的确,早期的良好引导与教养为个人获得“值得过的幸福生活”奠定厚实基础。维果茨基提出的“最近发展区”“学习关键期”理论,启发我们对青少年进行价值教育时,必须充分了解孩子们的需要并选择最佳的价值教育内容、方法和途径。不同身心发展阶段的优势需要影响着价值品质结构不同部分的学习关键期,教育者只有先了解学生真正需求,方可掌握价值教育“关键期”,进而通过价值实践活动孕育出价值品质。[16]中学阶段是价值品质发展的关键期,他们的身心发展特点使其产生多种价值认识和价值行为上的矛盾(包含价值悖论和价值冲突),为此在对中学生进行价值教育的过程中,应基于其心理生理发展特点和自身的需要,对其进行适切的价值品质培育。
(三)教育的功效
除了关键期,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关涉着价值品质的培育。例如,价值原则中一项很重要的价值是“生命”,而关于生命的价值教育从喂奶已经开始。价值教育绝非个别神圣仪式、崇高榜样或一朝一夕的说教所能完成,而是在日常生活、平凡事件和普通他人形成弥散性情境中侵染、熏陶而成。正如杜威的主张“教育即生活”抑或陶行知所言“生活即教育”。平凡生活中的为人父母者若忽视身边的未成年人,那是天大的错误。卢梭深谙教育之道,故而宁可割舍骨肉亲情将子女丢在育婴堂和孤儿院,也不忍心看到孩子跟着自己穷困潦倒、无力提供好的价值教育环境。非正式的生活细节恰恰是价值教育的重要阵地,孩子“无意中”旁观了成人的口是心非、虚伪势利,进而在游戏、课堂、说教等正式的价值教育中采取阳奉阴违的应付,在这样的交往阅历后,成人若强行推进核心价值观,结果只能激起逆反心理。
石中英认为,如没有在人生早期获得良好的引导与教养,尔后又没有做出长期努力来矫正感情与行为方面不够良好的习惯,当他对价值原则的领悟能力随着年龄与生活阅历的积累而发展时,这种发展就是局限的、不健全的发展,就不会成为较好的价值智慧。[17]因而,他从如此发展的价值品质获得的对实践事务的理解就是不健全的,这是他对实践事务持非常不确定意见的根源。在这种状态下,他的“知”与“行”便会脱节,他就会虽然知道怎样做是好的,也常常由于不能自制而做不到。正像廖申白断言,“我们多数人的实践的性质可能只是中等的、多少具有这种混合性质”。[2]7所以,一个人价值智慧的发展状况常常成为价值品质的发展状况的镜子,反之亦然。如果我们处在后一种情形下,那么,仅当我们借助发展着的价值智慧的理解努力地矫正我们在感情与行为方面的不健全的习惯,并坚持这种努力时,我们的心灵才能逐步获得德性的自由力量,我们对价值品质的理解才能升华为明智。明者,意味葆有价值原则;智者,价值智慧之谓也。
四、知行不一的内在张力与外在消解
(一)知行不一的内在张力
南宋理学大师朱熹认为,知先行后,行重于知。“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18]“若知而未能行,则此所谓知者,亦非真知也。真知则未有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就不是真知,真知没有不能行的”。[19]历史真是巧合,朱熹不正好表达了古希腊苏格拉底“知识就是美德”吗?苏格拉底同样认为,真理正当性是伦理正当性的基础,若能真的了解真相、掌握真知,则一定会践行;若没有践行或错行,则一定没有真知。好的行为是基于好的认知。不过,朱熹始终坚认历史早已既有思想,即知与行两者是决然不同的,而他只是确认了先后之别、轻重之分。儒学传统上,明朝心学大师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最为著名,他曾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20]他认为,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不能分离。他还明确表示知行合一:“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21]“今人却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22]以此观之,王阳明借鉴了佛、道之学,深化了儒学之心学——“心外无物,吾心即宇宙”。[23]故而提出颇有禅意的“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这不暗合了唐朝佛教禅宗六祖惠能“非风动,非幡动,仁者心动。”吗?由此看来,王阳明心学批判朱熹理学所谓知与行之二分,而是知行合体——知中有行,行中有知。
狭义而言,知是死的,行是活的;知是潜在的心理状态,行是现实的肉体机能;知是大脑内含的理论储备,行是身体外显的实践发挥。知行合一或许从来都是可望而不可求的小概率事件,阴差阳错、无心插柳、知而不行、行而未知才是知行不一的常态。知与行之间相隔万里,无论从逻辑推演,或现实经验,二者都没有必然联结。古人讲知易行难,孙中山说知难行易,马克思辩证法认为,知与行必然有相关性,但却没有必然因果性,二者之间尚有无限不确定性。其中,知与行之间的重要因素有:主体自由意志、能力、价值智慧、个体情感情绪、个人得失、事件的难易程度、信息是否透明、情境的利弊等等。其中每一个因素在特定时刻或许都是致命的,实际上心理学、行为学、管理学都有大量针对某一因素的实验研究。在漫长的历史和鲜活的现实表明,知识转化为能力或智慧,或知识转化为道德都是非常复杂的。郝文武创造“知核力”新概念,[24]表达知识的巨大力量和知识转化为力量和能力的过程和方式的复杂程度。知识及其转化为能力和道德等精神的力量的能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只要有人类知核力就会不断发展。
知行不一中最令人费解的是“知”和“行”都声称自己是正当的,那么此时也许需要伦理学中一个核心概念“善”的介入斡旋。罗国杰在其《伦理学教程》中说:“善就是指某一行为或事件符合于一定社会或阶级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所表达的要求;而恶是指某一行为或事件,违背一定社会或阶级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所表达的要求。”[25]本句中关于善的叙述值得推究,根据廖申白对古希腊伦理学中德性、善的考察,发现善是构成美好生活的关键因素,它包含道德的善与非道德的善。显然罗先生仅从道德意义上阐述善。价值行为与善关系密切,因为价值行为就是主体在意志自由状态下根据价值原则、运用价值智慧所做的正当性行为。我们的落脚点还是在行为的正当性——包含真理意义的、伦理意义的、法理意义的,而伦理意义的正当即遵循人与人相处的良心和道德善。真理意义和法理意义的正当性无法排除非道德善。
那么价值行为就是包含道德善以及非道德善的总体的“好行为”(有时总体上的好行为在一个具体情境中就不是好行为,反之亦然),这种好行为是幸福的充要条件。
(二)知行不一的外在消解
按照亚里士多德关于德性的目的论观点,如果说幸福是目的和原因,则总体好行为或价值行为就是第二位的善。价值行为就是合乎卓越价值品质的活动——通往幸福的价值实践,此种意义上的幸福既包括内在善也包括外在善。所以“人类的善理应是心灵合于正当行为的活动;若正当行为不止一种,则人类的善就应是合于最好的和最完全的正当行为的活动。”[26]这便回到前文所述之主张:面临真理的、伦理的、法理的正当选择时,应以厚正当为旨趣;次之,以伦理性正当为最终判据(但须谨记: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答案就在价值智慧根据当时境况所做的审慎取舍中)。伦理学者欧克里对行动与行动者品质作了很好的总结:善优先于正当——对于善的不同理解决定了不同的正当观念和伦理主张,好的品质(在恰当的场合以恰当的方式做恰当的事)本身就是内在善。[27]
品质论强调善优先于正当,规范论提倡正当优先于善。笔者作为品质规范论的拥趸,基于善已经被正当所涵盖(主要呈现于伦理意义的正当性),故认为:首先应该追寻厚正当(真理、伦理、法理的统一性),若追寻未果,则以伦理正当优先。
价值品质是主体基于价值原则、运用价值智慧,在价值行为中蕴含的正当性行为倾向和合善的心理特征。价值品质自身的模糊性、理想性、高标性,必然对价值行为提出苛刻要求,这使得知行矛盾难以避免。所以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必然的、长久的,价值之知与价值之行的统一是暂时而相对的。故而,价值品质、价值智慧的发展必然呈现出由不知到知、半知到全知,由或然性的知到行、必然性的知与行、到知行合一的阶梯演进。价值品质的知行适度张力蕴涵着品德进步发展的动力,理性的道德批判能够起到缓压公民的价值知行紧张性张力的积极作用。[28]知行不一的内在张力不可避免,同时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强力压制只能“口服而心不服”。知行不一更是社会公正与否的风向标,社会据此不断改良完善,消解外在不当措施,从而减少假知和伪行。低层次的知行合一、表里如一,在持之以恒地内外兼修中,逐步走向有深度的表里如一、有高度的知行合一。
价值品质自身的理想性和模糊性等决定了知行矛盾始终存在,故而二者之间的张力具有客观必然性。[29]事实上,生活中人为制造价值行为与价值认知之间矛盾实例不胜枚举。如造假奶粉、伪劣疫苗的生产企业一方面广告宣传重视生命健康,另一方面做的却是草菅人命之事。知行合一不仅拷问个体良心,更是拷问整个社会的良知。一个开放的、民主的、透明的、自由的社会,允许多样化的认知与行为,因为知行不一亦是人性之常态。恰恰如此,反而涌现更多的真实的知行合一。现实就是如此诡谲,只有提供了知行不一的土壤,才能孕育知行合一的果实。
(三)语言符号的遮蔽
实际上,在知行之间,还有一个第三变量,即“说”。两面三刀、八面来风、阳奉阴违、冠冕堂皇、一本正经,皆表达了在知——说——行之间的复杂性。我们评价一个人的价值行为,不仅看说了什么,更在于看其做了什么。大凡成熟的人,总是巧妙的“伪装者”,因为知而不说、不知而说、知而假说、行而不知、不行而假知等等,会使人雾里看花。
符号学家巴特认为,语言符号可以使人巧妙撒谎。典型案例如“善意的谎言”,若按照康德普遍性价值原则(任何时候任何人都应该诚实),那么无论多么美善,也是道德律令所不允许的。然而实践中,人们或许基于功利主义考量,一般会容忍那些善意的谎言。谎言作为一种言说的语言符号,其实遮蔽了知与行的逻辑链条,或者混淆了某种知与特定行的一一对应关系。另一类案例如潜规则中的“能做不能说”“能说不能做”,正是因为正当性不够充分,才被称为潜规则。价值行为的知行不一现象在言说的中介变量中,或许被“洗白”,或许被肢解。知—言说—行,这个完整链条被肢解后重组为:知—言说、或言说—行。如是,内在心理状况的知,与外在显性的行,二者脱节了,但却在言说符号遮蔽下,显示出知行合一的假象。尽管人们知悉“试玉要烧三日满,辩才需待七年期”,但在快节奏的生活实践中,很少有耐心看到“真知”与“实行”喜结连理的那一刻,往往以中介符号做脑补。这种中介符号表现为:思想品德的量化分数、少先队员的星与杠,思想档案、楷模的包装、伟人的塑造,等等。任何”行“都有相应的”知“,但是良知良心难以揣测,故而符号成为知行关系中最简便的操作工具。
知行不一,到底是真不一呢,或是言说符号中的不一,的确很难轻易判断。而言说的主体是谁?基于什么标准和立场?则又成为知行不一现象的次生性问题。
[1] 张维迎. 市场制度最道德[N]. 南方周末, 2011- 07-14.
[2]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廖申白,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3] 崔岐恩. 正当及其合理性阐释[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科版, 2017, 19(3): 88-95.
[4]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范扬,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120.
[5] Killgore W D, Killgore D B, Day L M, et al. The effects of 53hours of sleep deprivation on moral judgment[J]. Sleep, 2007, 30(3): 345-352.
[6] Bartels D M. Principled moral sentiment and the flexibility of moral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J]. Cognition, 2008,108(2): 381-417.
[7] Moore Clark Kane. Who shall not kill?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executive control, and moral judgment[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8, 19(6): 549-557.
[8] 林崇德. 发展心理学[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33.
[9] 维果茨基. 思维与语言[M]. 李维,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
[10]廖申白. 伦理学概论[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407.
[11]刘铁芳. 个体发展的阶段性与哲学教育的审慎[J]. 宁波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20, 42(1): 8-17.
[12]高文强. 老子“味”范畴之哲学内涵的生成及流变[J]. 天府新论, 2008(4): 35-39.
[13]Hutchinson. The virtue of aristotle[M]. Rout led: ge & Kegan Paul Inc, 1986: 22.
[14]金生鈜. 作为生命自觉的“努力”[J].宁波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20, 42(5): 1-10.
[15]米尔斯. 人的权利和人的多样性[M]. 夏勇, 译.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 23.
[16]陶志琼. 学生的限制及自由[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09, 27(4): 1-7.
[17]石中英, 霍少波. 教育公平话语中的教育假设及其反思[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8(6): 10-15.
[18]刘宗贤. 退溪与阳明: 朱熹哲学的不同走向[J]. 中国哲学史, 2006(3): 104-109. .
[19]杨翰卿. 论朱熹重行不轻知的知行观[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10(4): 97-101.
[20]杨国荣. 本体与工夫: 从王阳明到黄宗羲[J]. 浙江学刊, 2000(5): 11-17.
[21]方旭东. 意向与行动——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哲学阐释[J]. 社会科学, 2012(5): 131-137.
[22]胡小林. 朱熹与王守仁的知行观[J]. 孔子研究, 2005(6): 53-58.
[23]董平. 王阳明哲学的实践本质——以“知行合一”为中心[J]. 烟台大学学报, 2013(1): 14-20.
[24]郝文武. 知识的能力性和伦理性及其知核力研究[J].宁波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20, 42(1): 18- 29.
[25]罗国杰. 伦理学教程[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383.
[26]周辅成. 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4: 287.
[27]陶志琼. 中小学生价值教育的关键内容构成[J]. 教育发展研究, 2013, 33(8): 34-41.
[28]黄明理, 王利军. 论公民道德知行关系张力的客观性与调适[J]. 南京师大学报, 2014(3): 5-12.
[29]鲁宽民, 杨尚勤. 当前大学生“知行不一”的理性审视[J]. 社会科学家, 2010(1): 131-133.
On the Resolution of Contradictions between Knowledge and Behaviour
ZHANG Xiao-xia, CUI Qi-en
(School of Education,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There’s a continuous spectrum between the non-value behaviors and value behaviors, which are presented in different and diverse modals. If individuals get a good habit in value behaviors and emotions early in life through education and learning in the social value of knowledge as part of life, they are likely to become a person equipped with sense of value and principle of value; if one equally makes efforts to cultivate value wisdom, he or she will obtain the freedom of mind, becoming wise as known in applied ethics; and if a person’s life has been in such a state of habituation and wise, then one can increase self-discipline and retain knowledge-behavior unity. If the knowledge and behavior legitimate its claims to be right, but present contradictions in practice, the good should be introduced as mediators. The knowledge-behavior contradiction tests both individual and social consciences. A just and fair society provides open, transparent, and free “knowledge and practice” soil that can breed the fruit of the knowledge-behavior unity. As a phenomenon, the incongruity between knowing and doing, an actual practice, is closely-related to the practice of discourse intertwined in linguistic signs, thus being in the complete chain of knowing-saying-doing, presented as complex phenomena.
value quality; value behavior; value wisdom; knowledge-behavior contradiction and unity
G641
A
1008-0627(2020)06-0034-09
2020-02-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对接科技发展和市场需求的英国职业教育变革研究”(BOA190039);浙江教育厅项目“小学生符号意识研究”(Y202043191);中国教科院中央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项目“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外负担的理论与实证研究”(GYD2019001)
张晓霞(1976-)女,陕西西安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特殊教育、符号教育。E-mail: 407930475@qq.com
(责任编辑 赵 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