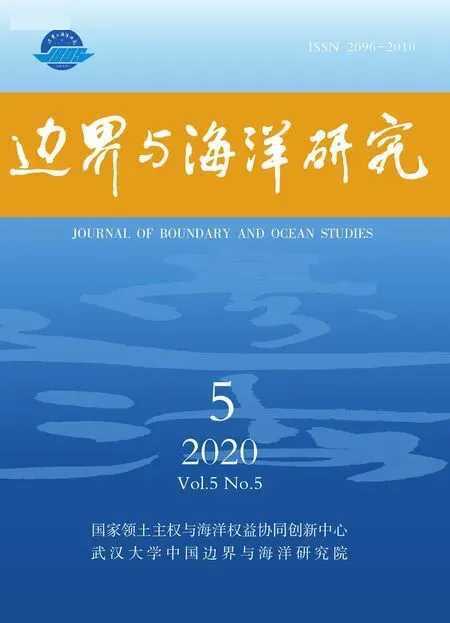区域秩序向度的中国周边外交
李博一 杨文萱
导 言
现时代的国际秩序正面临着自二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冷战终结以来重建的最大可能与有利机遇。(1)[英]安德鲁·赫里尔:《全球秩序的崩塌与重建》,林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6页。以美国等资本主义大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面对以中国等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时,开始陷入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一心理怪圈。(2)[美]罗伯特·库珀:《和平箴言:21世纪的秩序与混乱》,吴云、庞中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7页。面对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本能的维护自身全球利益以及相对来说正在没落的全球性主导地位的需要,不得不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对非西方世界的群体性崛起这一本质上符合世界历史发展大趋势的客观现实进行全方位围堵和外部干扰。(3)秦亚青:《全球治理:多元世界的秩序重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第35页;[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8年版,第9—17、77—90页。这种对中国等非西方国家进行围堵与干扰的最明显表现之一,就是试图以退群外交、退出地区一体化机制、撕毁限制核武器协议、违背甚至破坏全球气候治理框架协议等方式不断侵蚀本就脆弱且敏感的后冷战国际秩序。(4)A. Iriye,The Collapse of International Order,In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p.119-133.加之近些年来伊斯兰国(ISIS)的崛起与扩散、旧式地缘政治经济思潮的回流与泛起以及西方社会中民粹主义的回潮与蔓延等,再次将冷战后的国际秩序推向撕裂的边缘。(5)[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77—500页。面对西方各种思潮运动对现存国际秩序的冲击,中国等非西方国家,一方面有责任为维护一个良性且不断向善发展的国际秩序做出应有的贡献——对中国来讲,这是成长为一个新型负责任世界性大国的必备素质和必需的国际能力,而对于中国以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则是进一步维护自身合法合理国际关切和实现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一跨世纪目标的有益尝试;另一方面,中国等非西方国家也需要警惕这些由西方萌发并不断外溢的对当今国际秩序造成震荡的思潮运动给自身的外交布局以及自身所在区域一体化、区域合作以及区域秩序的构建与维持等造成的外部冲击。因此,本文尝试就区域秩序向度的周边关系进行学理探讨。
一、区域秩序建构的规范框架
国际秩序主要由区域秩序和全球秩序构成。区域秩序侧重从中观视角对由国家间的互动所遵循的规则程序等进行探讨,而全球秩序主要以一种宏观视角对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模式等进行探讨。不论是区域秩序还是全球秩序,均是观察、分析国际社会中各个国际行为体互动模式、互动规则的有效角度之一,缺乏其中任何一个视角,都无法掌握国际社会的全貌。因此,只有将区域和全球双重视角下的国际秩序研究路径进行结合,才有可能对动态发展的国际社会进行全景式描述与分析。
(一)区域秩序和全球秩序的概念特征
秩序兼具社会与政治内涵。(6)[美]彼得·盖伊:《启蒙时代:人的觉醒与现代秩序的诞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56页。秩序主要指的是社会中的各个行为体在一系列规则、原则、典章、习俗等约束和规范之下,相互之间所形成的一种有章可循、有规可矩的状态和动态性的建构过程。即社会中的各个行为体通过双边、多边的互动往来形成某种共识性的可靠预期,并在这种相互间可靠预期的基础上开展更为深度的互动。(7)[美]弗朗西斯·福山:《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唐磊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5—190页。但与此同时,行为体间的这些可靠预期辅以建立并被各个行为体内化到自身的外部行为、扩散到其他更广范围的行为体之后,便会对各个行为体的行为形成一种有效的外部制约。虽然有时候,这种外部的制约会面临失范、失效的困境,但并不能因此就彻底否定其应有的价值。另外,秩序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化、活动轨迹的持续明朗化,将整个人类社会囊括到一个更为封闭却又更为开放的人类聚合体开始出现。即,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逐渐由曾经原始状态下无政府社会过渡到一个由国家统一行使各种合法性垄断权的有政府社会,这是一个封闭与开放并存的人类集合体;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地理大发现的开始等,整个世界不断从一个相对隔绝封闭式地域性社会走向一个更具开放性、联动性的全球性社会。随之而来的,则是先前由各个行为体之间形成的共有预期和共有知识也开始呈辐射状向四周扩散,作为其中之一的社会秩序观念以及由秩序观念所带来的国家间秩序观便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8)[美]埃里克·沃格森:《求索秩序:秩序与历史》,徐志跃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77页。作为当前人类的最高集合体,国家以及由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中同样存在着相应的秩序。(9)E. Francis,“Sociological Concep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16,Issue 4,1954,pp.475-484.只不过国家间的这种秩序从大部分国际现实来看,主要呈现为一种无政府状态下的秩序模式。但不能因此就完全否定秩序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由国家等国际行为体所建构的国际社会中,存在着两个维度的秩序模式。一种是区域秩序,另一种是全球秩序。区域秩序主要是由在地理上临近的国家等行为体之间所形成的共识性安排,而全球秩序则更多是指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地理界限,在多个区域尤其是跨区域行为体之间所形成的共识性行事规则。即国际社会中的区域秩序是一种探究国际秩序的中观视角,因为其更为看重地理上的毗邻性,因此也可视为一种地缘性更强的秩序观;而国际社会中的全球秩序,则主要是一种研究国际秩序的宏观视角,这主要缘于其更为注重对整个国际社会所做的一种宏大叙事分析,其典型特征就是超越了简单纯粹的地理疆界划分,而是以一种大视角、广视域对国家等国际行为体间的共有预期进行分析,因此也可视为一种跨越地缘性的秩序观。(10)[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林华、曹爱菊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35页。不论是区域性秩序观,还是全球性秩序观,均是国际秩序观的有机构成部分。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视角的世界,都将是一个失真的世界,而在这样一个失真的国际社会中,秩序似乎就会被淹没在现实主义那种绝对抽象的无政府状态中而不易被人发觉。(11)[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第四版),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20页。
区域秩序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区域秩序具有地域性。区域秩序主要是由在地理上邻近的行为体按照一定规则构建起来的相互间共有预期,因而,地域性便成为区域秩序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如历史上欧洲地区曾经存在过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维也纳秩序以及东亚地区曾经存在过的朝贡秩序/封贡秩序等,从严格意义上讲,都是一种区域性国际秩序。第二,区域秩序具有封闭性或者半封闭性。既然区域秩序具有很强的地域构成性特征,其必然带有一定的封闭性。即使不是严格的封闭性,至少也是一种半封闭性。当然,这里所说的封闭性也好、半封闭性也罢,并不是说区域秩序是一个完全闭塞的回环型构成,而只是说,区域秩序因其地域性特征而具有的某种视角狭隘性。第三,区域秩序具有外溢性。区域国际秩序的封闭性/半封闭性并不影响其所具有的外溢性。特别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技水平的提高,人类的活动轨迹开始逐渐突破各种地理屏障,向本区域以外的地区扩展。(12)[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下)》(第七版),吴象婴、梁赤民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这就是区域秩序的外溢性或称外延性。也正是这种外溢性特征为区域秩序向全球秩序过渡提供了可能。第四,区域秩序具有动态性。区域秩序的建立、维持乃至重构均从不同侧面说明,这一中观视角的国际秩序模式具有动态发展性。即区域国际秩序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生着或进化或退化的演变。向善进化的区域秩序能够为全球秩序的形成提供有益借鉴,而退化的区域秩序往往会成为区域行为体之间相互征伐的理由。第五,区域秩序构建主体的有限性。虽然人类社会之间的通信手段、交通方式等均有空前的提高,但世界在政治地理上被划分为几大区域并存的现实依旧存在。这也进一步说明区域秩序是一个有限性的国际秩序。
而全球秩序的特点有:第一,全球秩序具有宏大性。全球秩序作为一种视角更为宏观、视域更为广阔的国际秩序模式,其最大的特征便是具有一种无所不包的全方位视角。这种宏大性视角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开启、加速以及其深化发展而逐渐受到更多重视。如一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秩序、二战后形成的雅尔塔秩序以及美苏冷战期间所形成的两极对立秩序,其所及范围均已超出某一大洲、某一地理区域的限制,而具有全球影响力。第二,全球秩序具有开放性。全球秩序的开放性是相对于区域秩序的封闭性/半封闭性而言的。这种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参与构建全球性国际秩序的行为体主体是多元的,既有国家行为体也有非国家行为体。与此同时,全球秩序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其多元的构成方式和构建路径。特别是现时代的后冷战全球秩序因为遭遇多重力量的冲击面临重建任务,给中国等非西方国家以自身思想资源重塑这一濒临破碎的全球性国际秩序提供了历史的可能。第三,全球秩序具有整合性。主要是指在政治世界仍旧存在人为疏离、撕裂的客观现实面前,需要从区域秩序的构建机制与运行机理中寻找可借鉴的资源,并将这些资源经过多次的磨合、调试后统一到一个新的秩序拼盘中,从而形成新的全球秩序。第四,全球秩序的参与主体具有多元多维性。(13)[美]彼得·卡赞斯坦:《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秦亚青、魏玲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7页。全球秩序的参与主体可以是国家行为体,也可以是非国家行为体。全球秩序还具有多维性。即全球秩序涉及全球经济秩序、全球政治秩序、全球安全秩序、全球文化秩序等维度。第五,全球秩序的变革具有迟滞性。现时代的全球秩序主要是从美苏冷战终结后的历史中形成的。面对这种全球秩序可能重塑的百年大变局,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既面临机遇亦面临挑战。而从当前的现实看,挑战大于机遇。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等非西方国家仍旧处在由美国等西方国家构建的全球秩序的非中心地带和非核心区域;另一方面,中国等仍在很多方面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差距。因此,即使历史提供了重塑全球秩序的窗口,在西方国家的干扰与本能的不信任感面前,中国等非西方国家仍然需要谨慎行事——将目光主要聚焦于区域秩序的构建与维持。综上,作为观察国际社会的两种不同视角,虽然区域秩序和全球秩序有着多重区别,但两者之间仍有密切的联系。
(二)区域秩序与全球秩序之间的关系
首先,二者存在着双向的互构关系和整体的联动关系。世界由区域构成。随着科学技术、远洋交通工具的发明与改进,曾经被地理屏障所隔绝开来的各个区域开始被人类的创造性活动联结在一起而逐渐形成一个全球一体化的世界。(14)[意]埃尼奥·诺尔福:《20世纪国际关系史:从军事帝国到科技帝国》,潘源文、宋承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9页。这个由各个“相互隔绝”却又“相互依赖“的区域所组合成的世界,其内部的秩序同样存在着相互建构的关系:一方面,区域在构成世界全景的同时,也将具有自身特色的秩序特征或多或少地带给了由其构成的全球性国际秩序;另一方面,全球性国际秩序一旦形成,并不是完全孤立地存在于区域秩序之外,相反,很多时候全球秩序的变动与摇摆往往会对区域秩序造成反冲击。(15)[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上)》(第七版),吴象婴、梁赤民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7页。同样,区域秩序的动荡也会对全球秩序的稳定造成一定冲击。(16)Tuckerb L M C & K,“Between Discipline and Dissent:Situated Resistance and Global Order”,Globalizations,Vol.8,No.4,2011,p.8.如中东地区的区域秩序。由于多重因素的复合性影响,中东地区的区域秩序至今仍处于建构过程中,并时而面临被各种力量解构的风险。(17)KAUSCH.Kristina,“Identity Politics and Regional Order in the Levant”,Uluslararas iliskiler,Vol.15,No.60,2018,pp.21-29;Jakub Sawek,“Yemen and the New Regional Order”,International Studies:Interdisciplinary Political and Cultural Journal,Vol.21,No.1,2018,p.34.这又会对全球秩序的稳定产生了不利影响。又如发生于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在对东南亚地区的区域金融秩序造成震荡之余,也对全球金融秩序造成了一定破坏。(18)Tran.Viet Thai,“The Evolving Regional Order in East Asia:A View from Vietnam”,Asia Policy,Vol.13,No.2,2018,p.67;Thitinan.Pongsudhirak,“Locating ASEAN in East Asia’s Regional Order”,Asia Policy,Vol.13,No.2,2018,p.53;Dewi Fortuna.Anwar,“Indonesia’s Vision of Regional Order in East Asia amid U.S.-China Rivalry:Continuity and Change”,Asia Policy,Vol.13,No.2,2018,p.59.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全球秩序对区域秩序的反冲击——如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大危机、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性金融海啸对世界多个区域的金融秩序均造成了破坏性影响。
其次,构建稳定良性的区域秩序是国家参与全球秩序重建进程的必经之路。任何一个国家,必先是其自身所在地区的区域性大国,然后才有可能走向全球性大国。这需具备多种主客观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将自身所在的区域搭建在一个有序、稳定、可靠的互动模式中。从世界历史的长河中看,至今还未发现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自身所在区域毫无秩序的混乱状态下登上世界舞台的中央。不论是传统的欧洲大国还是以山巅之城自居的美国,无一不是先拥有区域性大国身份继而迈向全球性大国身份的。而其背后最有力的支撑之一便是这些国家所在的区域被共识性或强制性地纳入到某种区域秩序中。反面的例子还是以欧洲地区的国家为例。如英法德等,虽然在历史上也曾问鼎全球性大国,但因这些国家间的纷争乃至相互征伐最终使其丧失了全球性大国的身份。再如历史上的东亚地区。曾经存在着以古代中国为核心的封贡秩序,但随着域内和域外力量地博弈,东亚地区的区域秩序至今仍处在新一轮的重建进程中。(19)Yong-Soo Eun,“Introduction:making sense of Korean discourses and the East Asian regional order”,The Pacific Review,Vol.31,No.2,2018,pp.240-242;Michael A. Glosny,“Re‐Examining China’s Charm Offensive Toward Asia:How Much Reshaping of Regional Order?”,Asian Politics & Policy,Vol.9,No.1,2017,p.37.由此可见,一个国家要想以周边区域为依托,由区域性大国成长为真正的全球性大国,稳定的区域秩序是关键。
最后,中观的区域秩序和宏观的全球秩序是审视国际秩序全貌的互补视角。如前所述,不断走向全球一体化的世界,首先是一个区域化的世界。(20)[美]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秦亚青,魏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这并不是要否定当今全球化深度发展与扩散的现实,而是说,全球化与区域化是一个并行不悖的历史进程。而且,更高阶的全球化是以区域一体化为前提的。否则,全球化只能是一个碎片化的全球化。而要对由多个国际行为体构成的国际社会做出较为全景式的描述与剖析,区域和全球视角缺一不可。区域视角为了解国际社会提供了细致入微的细节性内容,而全球视角则为观察国际社会提供了宏大且广延性的框架结构。舍弃其中一个角度,所观察到的世界都将失真。
(三)理解区域秩序的几个维度
国际社会中的秩序是随着多元国际行为体间的多维互动建构起来的。从纵向观之,区域秩序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现实的可变性;从横向观之,区域秩序按其聚焦内容的不同可大致划分为区域安全秩序、区域经贸秩序以及区域社会文化秩序等。(21)A. Phillips & J. Sharman,International Order in Diversity:War,Trade and Rule in the Indian Ocea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p.67-70.因此,全景式理解区域秩序,需要从这“一纵一横”两个维度进行剖析。
1.历史与现实维度
由国家等国际行为体所构成的无政府性质的国际社会是否存在着可以规范各个国际行为体外部行为的秩序?不同的理论范式对之有不同的解读。我们认为,即使国际社会处于一个无政府状态,也并不绝对地意味着国际社会中就不存在秩序。(22)H. Bull,“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Ord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26,No.3,1972,pp.583-588.倘如国际社会中真的不存在秩序,那么,各个国家在实施对外行为时为何仍旧会理性行事?即使包括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不例外。虽然有的时候,美国会抛弃于己不利的外部制约而施行单边主义,但这不能成为国际社会不存在秩序的充分理由。历史与现实维度的区域秩序可分别从历史的延续性和现实的变革性进行分析。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秩序一样,区域秩序和全球秩序也是历史的产物。(23)D. Ba. Alice,“Multilateralism and East Asian transitions:the English School,diplomacy,and a networking regional order”,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57,No. 2,2020,p.34.一方面,区域秩序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区域秩序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随着区域内各个行为体之间交往范围的扩大、互动频次的增加而逐渐形成的。这种随区域行为体间互动而被建构起来的秩序因而也就带有很强的历史惯性。即区域秩序一旦被区域行为体建构起来,便会获得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并会保持一定的发展惯性。直到这种惯性被另一个区域秩序取而代之;另一方面,区域秩序也具有现实的可变性。虽然区域秩序一经形成便会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历史惯性,但这不意味着区域秩序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区域行为体之间力量的消长变化、共有知识的错位、信息不对称的增加等,区域秩序也会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可能趋向于一个更为“善的秩序”,也可能退化为一个“恶的秩序”。关键在于区域行为体之间是否有一个更可靠的选择性预期。
2.政治与安全维度
虽然非国家行为体已经开始走进国际社会并已经对国际社会产生多领域、多方面的深度影响,但在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家仍旧是决定国际社会向何处去的关键驱动。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很大程度上仍要依托国家这一人类最高形式的集合体来对国际社会发挥影响。如日益兴盛的各种跨国公司、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等,仍旧无法完全摆脱主权国家对其构成的制约与管控。毕竟,国家才是合法拥有并行使垄断权力的唯一政治机器。因此,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具有政治性和安全性。(24)J. Mayall,Nationalism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50-69.同样,理解区域秩序也离不开政治与安全这一维度。从历史上看,不同地区的行为体在构建属于本地区的区域秩序时,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将政治与安全因素纳入其中。如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维也纳秩序、凡尔赛—华盛顿秩序等,均离不开政治与安全因素的考量。(25)Art. David,Continent by Default: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Demise of Regional Order Anne Marie Le Gloannec.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8,p.280.从现实看,区域秩序更是被注入了大量政治与安全因素。如南亚地区以印巴为主导构建的区域秩序(26)Ngaibiakching,Amba Pande,“India’s Act East Policy and ASEAN:Building a Regional Order Through Partnership in the Indo-Pacific”,International Studies,Vol.57,No.1,2020,pp.67-78.、美洲地区以美国为核心所构建的美洲秩序、欧洲以欧盟及其成员国中的传统大国为主推力量所构建的欧洲秩序,同样离不开政治与安全的关注。因此,要深入理解区域秩序,政治与安全就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
3.经济与贸易维度
在区域秩序的构建与维持实践中,经济因素的考量处于基础性地位,政治安全因素因属于上层建筑领域,而处于被决定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因素具有完全绝对的决定作用。政治安全这些上层因素也会对经济等基础性因素形成反作用。(27)The Secretariate,“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Summary of the Discussion on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Vol.25,No.2,1978,pp.225-233.区域秩序的构建,一方面,要对行为体间的互动方式有着政治和安全上的敏锐观察;另一方面,行为体间的经贸互动也不可忽视。而且,从现时代的国际现实看,区域一体化正在全球各个地区兴起。不论是区域合作还是次区域合作乃至微区域合作,驱动区域行为体开展合作的众多因素中,获得一定的经贸需求占有重要地位。如在欧洲地区的一体化起始阶段,经济考量就占据关键位置;又如非洲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共同发展、改善经济处境同样占据重要地位;再如东南亚地区一体化实践,共谋发展、占据东亚价值链的优势地位,同样是一个关键考虑因素。因此,区域秩序的构建与维持,是在经济等基础性因素驱动下,以谋求区域内的政治安全为目标的历史性活动。当然,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除了对政治与安全、经济与贸易等因素的考量,非政治经济性质的因素对构建于己有益的区域秩序往往更持久也更具韧性。
4.社会与文化维度
秩序本身就是人类文明不断提高的结果和自然人社会化的产物。作为规范、约束社会中各个行为体言行的原则、规则等安排,秩序一开始便被打上了文化的印记。(28)C. Reus-Smit,“Cultural Diversity and International Ord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71,No.4,2017,pp.851-885.虽然史前人类社会也存在某种秩序,但那更多是无意识、自发性的产物。(29)Clark.I,International and world order. In The Hierarchy of States: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p.31-48.随着人类社会步入文明时期,有意识、自觉性的秩序理念与实践才得以广泛生成并扩散。同理,由国家等国际行为体所构成的国际社会中的秩序,也是随着国家间文明意识的提高而逐渐被构建的。(30)E. Adler,International Social Orders. In World Ordering:A Social Theory of Cognitive 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9,pp.137-164.虽然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文明国家对国际秩序的撕裂与破坏,但这证明,一个良善的国际秩序仍旧处在一个不断社会化和文明化的转向中。(31)A. Phillips,What are international orders? In War,Religion and Empire: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p.15-33.据此,了解区域秩序,也需要对社会性因素进行分析。区域秩序是由某一地区内的行为体通过多维的互动构建起来,这些区域性行为体在互动进程中,也会存在对现存区域秩序的多重解读:一方面,当其认为现存的区域秩序能够普遍反映域内行为体的共有预期时,便会竭力而维持之;另一方面,当其认为现存的区域秩序已不具备普遍的公意性,特别是当域内行为体认为现存区域秩序安排不能满足自身扩大的利益诉求时,便会产生重塑乃至解构这种秩序的可能。而以上所有这一切,都可大致归结为:域内行为体之间的社会化程度仍有待提高。否则,区域秩序的重构便是迟早之事。
区域秩序的多重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用一种复合性思维、全方位视角对之进行解读。唯有此,方可对区域秩序的构建、维持、调试以及有序运转有一个较全面的理解。也正是由于区域以及区域秩序对国家发展和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及其与一国周边外交的联动性,接下来及至最后部分,将对区域秩序向度的中国周边外交进行探讨。
二、中国区域秩序建构的现实基础
世界认知中国,首要的途径就是看中国的外交理念与实践。而要认知中国的外交,周边关系则是基础性的一环。由此,中国的周边关系理念与实践便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这主要是因为:首先,中国当前仍是一个区域性大国或准全球性大国;其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再次,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由于存在着难以一时彻底化解的“历史情节”与“大国博弈”等,使得中国不得不对以东亚为代表的周边区域秩序的构建与维系持续关注。(32)郭延军:《东亚安全的区域治理之道——评〈国际关系理论与东亚安全〉》,《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08年第4期,第110—113页。因此,稳定的区域秩序应是中国经略周边的依托。
(一)区域秩序与中国周边外交:现实必要性
中国当前以及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首先是一个区域大国。不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任何一个国家在成长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性大国之前,无不需要首先拥有区域性大国的身份。历史上,中国曾经是东亚区域首屈一指的力量,并凭借文化的辐射力和感召力、经济体量的庞大性而具有全球性影响。但因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这种历史的荣光曾被新兴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多次蹂躏。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以及改革开放等政策的实施,现时代的中国正处在历史复兴进程中。不可否认,今日的中国已非昔日可比,尤其是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国际声望进一步提升。但仅有庞大的经济体量还不足以支撑真正的全球性大国身份。特别是在国际制度的创制、国际思想的凝练、国际话语的掌控等方面,中国已经付出颇多且早期收获成效显著。如在国际机制的创制方面,有上合组织;在动员型跨区域合作倡议方面,有“一带一路”;在国际金融多边合作方面有亚投行、金砖新开发银行等。但是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相比,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特别是在制度性、思想性国际公共产品方面,中国仍需要在充分挖掘自身古典文化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学习借鉴西方的有益之处并创造性同本土性资源进行融合,进而为国际社会提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智慧的公共产品。(33)王光厚:《从“睦邻”到“睦邻、安邻、富邻”——试析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转变》,《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第38—43页。总之,区域性大国的国际身份要求中国必须重视周边区域秩序的构建与维系,也要求中国重视对周边区域的治理做出创造性安排。
其次,现时代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决定周边区域才是中国外交的发力点。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推进,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着既微妙又显著的变化。一方面,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深度发展,中国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均无法回避这一历史进程。伴随全球一体化的是区域的一体化实践,对这一客观现实,中国仍然需要坦然面对,最好是主动出击,成为区域一体化的推动者。另一方面,面对全球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浪潮的冲击,特别是面临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各种思潮运动的冲击,中国则略显疲态。很多时候,面对外部于己不利的国际舆论和思潮运动,表现得往往是一种“应激反应”而且时常会陷入西方的话语陷阱。主要原因如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仅在经济上与西方发达的经济体存在显著差距,在非经济领域同样处于发展中地位。虽然十年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总体量的庞大并不能掩盖人均值过低这一事实。在非经济领域,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更为明显。如在国际话语表达上,当前的现实是西方国家仍旧占据着国际话语权的核心位置并时不时对非西方世界评头论足,甚至干涉他国内政,事后却还以救世主自居。因此,中国既然将自身定位成一个成长中的全球性大国,就不妨将自身的战略聚焦范围适当缩小:提升对周边区域的关注度。面对西方的话语陷阱时,也不妨坦然处之。当然坦然面对不是毫无原则的丧失底线,而是要在保持底线的前提下,有理有节地驳斥西方歪曲式的话语霸权。
再次,区域秩序的构建与维系应是未来中国周边外交部署的关键所在。区域性大国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双重国际身份要求中国外交必须重视周边外交的首要地位。(34)郭树勇:《区域治理理论与中国外交定位》,《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12期,第47—54页。而要使得周边外交成为中国历史复兴的坚硬基石,则离不开区域秩序的规范作用。毕竟,如果按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国家都是自私的行为体。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面前,每个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诉求,完全存在突破国际道义和国际伦理底线的可能性。然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并不绝对地意味着国际社会的混乱无序,而这背后就是由于存在着某种行为体间的共有预期——国际秩序对理性单一的国家行为体的外部行为产生的规范和制约作用。同样,在国际秩序的区域层级,也存在着这样的秩序并且也需要这种区域秩序发挥出规范与规则作用。同其他大国的周边区域比较起来,中国周边区域情况更为复杂,治理也更具难度:由于海陆邻国数量多,中国与部分邻国之间存在着领土、资源纷争;中国周边的中小国家对中国的庞大体量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崛起心存疑惧而不得不采取“大国平衡外交”以保障自身利益最大化;(35)丁工:《中等强国与中国周边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7期,第24—41页。中国所在的欧亚大陆大致处于麦金德笔下的“世界岛的心脏地带”(36)[英]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9页。,而这样的地理位置也确实给中国周边区域治理和周边区域秩序的构建造成多重困扰。由此,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对构建周边区域秩序的关注力度。而稳定的周边区域秩序又可为中国周边外交实践的推进营造一个规范性的区域环境,最终也可为中国“以周边为首要”成长为一个新型的具有东方特色的负责任大国提供借鉴与启发。
最后,重塑全球秩序是中国成长为真正的世界性大国后的选择。重视区域秩序的构建与维系,并不意味着对全球秩序的轻视甚至忽视。作为国际秩序的高阶层面,全球秩序与区域秩序是一个复合型联动体:区域秩序的稳定是全球秩序稳定的基础,反之,全球秩序也会对区域秩序产生反冲作用。只不过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需要将重塑国际秩序的战略重心更多倾向于周边区域秩序的构建与维持。至于全球秩序的重塑更多地是中国成长为真正的全球性大国之后的考虑。而且,区域秩序的构建、磨合、维系也会为之后全球秩序的重塑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二)区域秩序与中国周边外交:现实可行性
作为中国整体外交布局中的首要环节,周边外交的成效关系到中国能否借力周边实现历史复兴的百年中国梦。(37)卫灵:《周边外交是中国外交之“首要”》,《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年第5期,第70—73页。自中央高层提出以“亲诚惠容”理念指导周边外交实践以来,(38)邢丽菊:《从传统文化角度解析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以“亲、诚、惠、容”为中心》,《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3期,第9—20页。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关系逐渐朝着更为良性的轨道迈进。特别是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周边命运共同体意识也开始萌生并已获得良好的预期。(39)陈琪,管传靖:《中国周边外交的政策调整与新理念》,《当代亚太》2014年第3期,第4—26页。若从区域秩序的构建、维系及其与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取向来看,需要在开放的区域多边主义、共生型周边秩序观等基础上,继续深度推进区域次区域合作,为周边国家提供更多、更实在的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最终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奠定坚韧的基石。
1.开放的区域多边主义
区域在地理上的相对封闭性并不能因此就成为区域保守主义的借口。全球化深入发展、持续蔓延的今天,没有哪个国际行为体可以完全置身于这一历史进程之外。而作为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有效前提,区域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起了当前全球化未能涉及的领域和功能。可以说,区域一体化是作为全球一体化的前夜而存在的。即使存在着个别地区的“逆区域一体化”现象,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历史趋势。特别是对于中国而言,在逆全球化现象不断升温、旧式地缘政治思潮持续回流、文化民族主义时隐时现的国际大背景下,更需要重视周边区域秩序的构建与维持。并在相应区域秩序的规范之下,有效地进行区域治理。而不论是区域秩序的构建还是区域治理的实施,都需要在坚持开放的区域多边主义这一理念基础上进行。开放的区域多边主义包含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区域开放主义,一层是区域多边主义。区域开放主义主要是指在推动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要秉持一种包容与互鉴心态。一方面,对于区域内的文化多样性,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共存共荣;另一方面,对于区域外行为体要采取一种欢迎却限制的路径,即域外行为体可以参加本区域的一体化进程,但要对之采取一定的限制,以防止出现域外行为体“反客为主”的不利状况。(40)李开盛:《中国周边外交:70年来的演变及其逻辑》,《国际关系研究》2019年第4期,第26—39页。另一方面,对于区域内的经贸价值链,要坚持凭借各自的优势产业在相互之间实现互补效应。区域多边主义主要是指坚持在区域性多边对话平台上进行有效沟通、信息共享,以防出现因信息不对称、力量过度分散化等造成某种无效沟通。
2.共生型周边区域秩序观
良好稳定的区域秩序不仅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可靠保障,更是中国推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基础。但这里所说的区域秩序的构建已经不能是历史上那种“远交近攻”“朝贡—封赏”式的区域治理模式,而是一种新型的区域秩序观——共生型区域秩序观。共生型区域秩序观的最大特质就在于,各个行为体之间需要摒弃“强者即是真理”的零和思维,而是运用一种命运与共、各方共赢的理念进行互动往来。(41)魏玲:《新中国周边外交70年:继承与创新》,《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5期,第1—13页。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讲,虽然当前中国尚不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但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区域大国。这一国际身份要求中国以一种新的智慧对待周边的中等国家行为体。即用“以大事小曰仁”的理念来同周边国家搭建起一个稳定可靠可控的区域秩序。而要构建起共生型区域秩序,需要在各个行为体间协商的基础上展开。这就要求各个国家行为体之间拥有充分的信任感,对区域秩序的未来有可靠的共有预期。需要区域内的各个行为体在共商的基础上,共同为区域秩序的构建与后续的维护做出承诺。即是说,这一在共商前提下所共建起来的区域秩序不仅仅是为了利益的共享,还要做到责任的共担。否则,一旦出现大量的“搭便车”现象,区域秩序的解构则是早晚之事。作为准全球性大国,不论从哪个方面讲,中国都有责任为构建一个良好的区域秩序提供可行性的方案和路径选择。
3.深度扩展的区域次区域合作
在当前中国的周边外交实践中,收获最多且质量最高的莫过于各种形式的区域—次区域合作,也包括微区域合作。(42)吴剑明,刘寒雁,马啸:《“微区域合作”架构下的中缅跨境流动人口治理研究》,《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第48—54页。这已经在中国同周边邻国之间建立起了良好的双边或多边秩序。如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1992年,在亚洲开发银行的提议下,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六个国家共同发起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MS),其主要目的就在于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促进次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实现区域共同繁荣。中国云南省也参与其中。这为中国以次区域合作经略西南周边提供了多边对话的平台。当然,这一次区域合作最显著的成果还是在于,为中国周边外交的推进构建起来一个稳定健康的次区域秩序。又如澜湄合作。这是继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之后,中国同周边邻国之间化解纠纷、推进区域一体化实践的又一尝试。(43)李巍,罗仪馥:《中国周边外交中的澜湄合作机制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5期,第17—25页;卢光盛,熊鑫:《周边外交视野下的澜湄合作:战略关联与创新实践》,《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27—34页。自澜湄合作提出、实施至今,流域国家之间在经贸、人文交流等方面也已取得部分良好预期。再如中国同周边邻国之间共同实施的六大国际走廊建设,(44)这六大国际经济走廊分别是: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以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施载体,“六大经济走廊”主要是以中国同陆上邻国间的微型区域合作为推动,以期为中国的周边外交提供更多经验。因此,继续深化以次区域合作和经济走廊建设式的微区域合作,依然是中国在周边地区构建稳定的区域秩序的必要之举。
4.丰富多样的区域性公共产品
构建稳定的区域秩序,顺利推进周边外交实践,还离不开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保障性供给。(45)宋效峰:《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中国周边外交的新动力机制》,《广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第55—59页。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当前的国际现实看,中国需要在构建区域秩序方面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和非制度性公共产品。非制度性公共产品主要涉及经济贸易互动、产业产能合作、区域性公共资源的共同开发利用等领域。在这方面,以“一带一路”“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最具代表性。而制度性公共产品主要是指,建立相应的机制化、轨道化协商处理平台。(46)李益波:《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理念、内涵和实施路径》,《国际论坛》2019年第3期,第100—114页。这方面,中国也已同周边邻国之间建立起了部分的区域性国际合作组织,如上海合作组织。但从目前的现实看,制度性公共产品的供给相对于非制度性公共产品而言,仍旧处于一种“供应不足”甚至短缺状态。(47)卢光盛,别梦婕:《“成长的代价”:区域公共产品与中国周边外交》,《当代世界》2017年第3期,第16—19页;陈小鼎:《区域公共产品与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的战略内涵》,《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8期,第37—55页。这就进一步凸显了中国为周边区域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的紧迫性和必要性。(48)许涛:《新时代周边外交中的上海合作组织再定位思考》,《和平与发展》2018年第3期,第60—74页。对此,中国不妨将前述所提及的部分次区域合作机制和微区域合作实践进行有机的整合,形成功能更专业、定位更明晰的新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为区域秩序的构建与维系提供相应的制度化保证,也为周边外交的深入推进提供可靠的外部约束。
三、多层次构建中国周边区域秩序
历史经验与现实基础为中国周边区域秩序的构建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有益启发,也为新时代中国周边关系的构建与维系提出了新要求。面对多重考验的冲击,中国周边外交不妨在充分利用现实有利条件、吸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一种“大区域观”视域下的多层次区域秩序观来推动中国新型周边区域秩序的构建。(49)程大为:《全球贸易治理中多边主义、诸边主义和大区域主义的比较与选择》,《经济纵横》2014年第4期,第95—98页。即从“跨区域、区域—次区域以及微区域”等三个层次发力,在中国周边区域构建出一个多面向、联动性、整体性的区域秩序框架,为中国周边关系的持续改善提供一个有效且可行的路径,最终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营造一个有韧性的区域秩序。
首先是跨区域秩序的构建与维系。(50)这里的“跨区域”概念主要受到王伟进,陈勇:《跨区域发展与治理:欧盟经验及其启示》,《学习与实践》2020年第4期,第63—75页;袁伟平,闫晓燕,曹洪华:《跨区域合作下云南沟通“廊”“带”的区域战略研究》,《经济问题探索》2018年第2期,第130—134页等内容的启发。作为大区域观中的宏观层次,跨区域秩序的构建及维持在中国周边外交关系的动态发展中占据着关键位置。这主要是由中国辽阔的地理覆盖范围决定的。从历史看,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关系主要是在经济贸易诉求的基础上搭建起来的,如古丝绸之路等。这一方面将中国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以相互依赖的经济利益联结在一起;另一方面也给中国经略周边、治理周边提供了便利条件。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事实是,中华文化的感召力与辐射力在中国同周边地区国家关系维系中的隐形作用。但遗憾的是,这种历史上的跨区域秩序并未获得历史的延续。从现实看,中国同周边地区国家间的关系不仅体现在互补性的经济利益诉求上,也体现在共同面对的地区安全问题上。如现实所证明的那样,在周边地区不仅存在着传统安全问题,也存在着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而且很多时候,两类安全问题的相互交织给中国在跨区域地区秩序的构建制造着困扰。面对经济利益的相互依赖性、安全问题的复合交织性等多重困扰,中国在跨区域秩序的构建进程中,需要在区域安全复合体框架下(51)Derrick Frazier,Stewart-Ingersoll,“Regional Powers and Security: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Order within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e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6,No.4,2010,pp.731-753.继续发挥一种主导作用。如为了应对中亚地区的“三股势力”等安全问题,由中国同俄罗斯以及几个中亚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上海五国机制”并逐渐使之制度化——最终成立“上海合作组织”。随着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及运转,中国在欧亚地区的跨区域秩序构建中,逐渐发挥关键的影响力。随着上合组织首轮扩员的完成,跨区域经济秩序、文化秩序的重构也再次被提上中国周边治理的议程。总之,在跨区域地区秩序的构建进程中,中国在发挥关键影响力的同时,也需要同域内和域外大国在协商治理的基础上维系跨区域秩序的后续运转与适时的调整。(52)王磊,郑先武:《大国协调与跨区域安全治理》,《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1期,第118—135页。而要妥善处理同其他相关大国的关系,以形成构建跨区域秩序的共识,就离不开制度化的对话轨道。上海合作组织作为跨区域安全秩序构建与维系的重要平台,已经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也不可否认地成为中亚地区最重要的多边合作组织。(53)Rustam,Khuramov,“New Political Dynamism in Central Asia:Security Issues and Prospect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39,No.2,2019,pp.97-104.面对上合组织扩员后的新考验,中国要想使上合组织继续在跨区域秩序构建中发挥关键作用,需要明确上海合作组织的功能定位以及自身在该组织中的角色定位与成员国的权力分配比例。(54)李博一,黄德凯:《上海合作组织的困难和前景》,《战略决策研究》2020第3期,第85—104页。否则,扩员后的上合组织不仅不能为中国构建于己有利的跨区域秩序提供制度化的协商处理平台,反而会因组织内部成员国间差异的增大而使上合组织陷入停摆的困境。而一旦出现此种局面,中国以上合组织为发力点构建跨区域秩序便会遭遇新的困境。
其次是区域—次区域秩序的构建与维系。能否妥善经略周边、有效治理周边,不仅关系到中国是否能够实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复归,也关系到中国同周边地区和国家是否能够实现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愿景。区域—次区域秩序的构建主要是一种中观区域秩序的构建路径。就客观的地理位置而言,中国是一个东亚国家。若再从微观地理位置衡量,中国既是一个与东南亚地区有着共同边界线,又与东北亚地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东亚国家。面对这一双重地缘环境,中国在区域—次区域秩序的构建中更需要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在东南亚地区的区域秩序构建中,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辐射带动作用,中国发挥经济主观能动性,(55)Hsieh,Pasha L. Against,“Populist Isolationism:New Asian Regionalism and Global South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Vol.51,Issue 1,2020,pp.683-729.已同东盟及其成员国之间建立起多种层次的伙伴关系网络。这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构建良性、稳健的区域秩序提供了有利基础。但随着美国、俄罗斯等域外大国以及日本、印度等域内大国对东南亚地区深度介入,东南亚区域秩序构建进程面临着多种被解构的风险。至少从目前看,东南亚地区的区域秩序尤其是安全秩序主要是由美国及其盟友主导建立的。中国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是一个强大的经济力量存在,而不是所谓的政治力量。(56)E.V. Koldunova,“Regional Transform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Problem of just Regional (and World) Order”,Sravnitel’na Politika,Vol.10,No.4,2019,pp.52-64.另外,在东南亚地区的区域文化秩序构建过程中,由于中华文化的历史感召力与辐射力仍旧具有一定的影响,也为中国构建区域文化秩序奠定了有利根基。至于东北亚地区的区域秩序,则复杂得多,且更集中于区域安全秩序。中国在推动构建东北亚区域安全秩序进程中,时刻需要与域外大国——美国以及域内大国俄罗斯、日本等互动。而随着印日关系的改善以及“印日自由走廊”的提出,东北亚区域安全秩序的构建又增添了新的变量。对此,中国需要在东北亚区域安全秩序的构建中继续发挥“主场优势”,必要时可考虑与俄罗斯联合共同弱化美国等域外大国在该地区区域秩序构建中的影响因子。至于在东北亚区域经贸秩序中,既有的“图们江区域国际合作”与图们江自贸区建设可继续发挥纽带作用。(57)杜有,孙春日:《图们江区域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的文化视角研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70—74页;李国强:《“一带一路”倡议与图们江区域合作的新机遇》,《东疆学刊》2016年第4期,第93—99页;孙瑞杰,魏婷,杨潇:《图们江区域合作新格局的构建和策略》,《宏观经济管理》2016年第3期,第48—50页;郭文君:《关于将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纳入“一带一路”战略的思考》,《东疆学刊》2016年第2期,第85—93页;丁四保:《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面临的问题与推进战略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145—149页。在中国提出实施“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后,不妨将之整合纳入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进程中,为中国在东北亚区域经贸秩序的构建中发挥制度化的先导作用。在次区域秩序的构建中,目前来看,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以及新兴的澜湄合作(LMC)已收获良多。且中国在这两大次区域合作机制中均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次区域秩序的构建,不妨借鉴大湄合作与澜湄合作路径:中国作为主要发起国并在其中保持绝对话语权与影响力。当然这不是要排斥甚至否定其他国家的作用与价值,而是要防止这些次区域合作机制沦为域外大国平衡中国,甚至离间中国同次区域其他国家关系的工具。中国需要做的,就是充分利用这些既有的平台机制,适当时候进行有机整合,以防过度碎片化的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给中国构建稳定的区域—次区域秩序造成新的困扰。
最后是微区域或跨境区域秩序(58)郑先武,李峰:《东南亚微区域合作与跨境安全》,《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3期,第1—11页。的构建与维系。这里将微区域勘定为一种大区域观视域中的微观层次。在这一微观的历史地理单元中,参与国际实践——微区域秩序构建的主体仍主要由国家行为体构成。只不过参与微区域秩序构建的行为体主要限于地理上存在毗邻或接壤的国家。如中国当前已经开始推进实施的六大国际经济走廊建设项目,便是典型的微区域合作实践与微区域治理路径。在构建微区域秩序的进程中,中国不妨可从以下作为切口:首先是微区域秩序构建中的经济与贸易维度。中国已经开始以六大国际经济走廊建设项目与毗邻国家展开合作。在六大国际经济走廊项目中,中国的经济体量相对而言较为庞大,因此在为区域经贸秩序的构建中占据关键位置。这就为中国在微区域经贸秩序的建设进程中发挥负责任的新型大国意识提供了可能。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的深入推进,六大国际经济走廊建设项目与之实现有效对接便提上议程。在微区域经贸秩序的构建中,中国需要发挥引领与示范作用,但也要预防陷入纯粹工具理性的困境。其次是微区域安全秩序。从当前的客观现实看,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微区域安全秩序构建中仍旧存在一定短板。一方面,中国同周边地区和国家在应对各种安全议题时,往往会遭遇域外大国的介入与制衡;另一方面,中国同周边国家在微区域秩序的构建中缺乏制度化的对话轨道与协商平台。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的实施,中国同周边地区在应对威胁边境安全与稳定的安全性议题时,需要制度化的治理机制。如在澜湄流域推行的联合安全执法便可为区域安全秩序的构建与维系提供镜鉴。而在构建微区域安全秩序中,中国需要以一种共生安全观为指导,同微区域中的其他国家以共治的理念推动微区域安全困境的化解。最后是微区域文化秩序。随着世界部分地区旧式地缘政治思潮的泛起、恐怖主义的扩散与蔓延等,以文明冲突为论调的地缘文化碰撞开始撕裂本就脆弱的区域秩序。所幸的是,在中国周边的跨境区域范围内,尚未发生上述历史的回流。虽然也存在着异质文明的碰撞,但远未达到文明冲突的后果。但构建具有包容性、互鉴性的微区域文化秩序却不得不未雨绸缪。对于中国而言,构建一个包容互鉴的微区域文化秩序,既有有利基础也有不利因素。有利的是中国古典文化遗产至今仍具有感召力与辐射力,这为中国同周边地区国家间构建稳定的微区域文化秩序提供了基础;不利的则是周边部分国家担忧中国正在试图恢复历史上的“朝贡秩序”。特别是周边中小国家的这种心理更为明显。客观地讲,周边地区的中小国家有这种心理很正常,关键在于中国如何去化解这种不必要的疑惧。单凭“达则兼济天下”式的国际开发援助不足以弱化乃至消除之。从深层次来讲,还需要在中国同这些国家之间形成一种对微区域合作成效与微区域治理效果的可靠且共有的预期,而这又离不开一个兼收并蓄的微区域文化秩序和文化治理。对此,中国需要超越历史上的“朝贡思维”,以一种文化威望国或文化核心国的角色定位来推动构建一个兼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微区域文化秩序。
四、结语与思考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的区域性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共同决定着周边区域秩序的构建与维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周边区域治理,这是中国周边外交的有效发力点。而要利用好区域秩序和区域治理这一关键支点,就需要中国在“周边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目标的驱动下,同周边国家之间以共商的方式、共建的路径构建起共赢的区域秩序。从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看,要构建中国同周边国家之间的这种共生型区域秩序为中国的周边外交提供可靠的外部保证,离不开中国以开放的区域多边主义为指导,为周边区域合作提供更多的制度性公共产品。当然,以上分析只是对区域秩序和中国周边外交的未来取向和路径选择提供了一个更具学理性的思考。学理性的思考最终是需要由具体的实践活动来检验的。另外,从未来的发展愿景看,区域秩序向度的中国周边外交,需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尝试以一种大区域观视域下的多层次区域治理逻辑构建区域秩序,不断为中国同周边国家构建“命运与共、和谐共生”的“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动力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