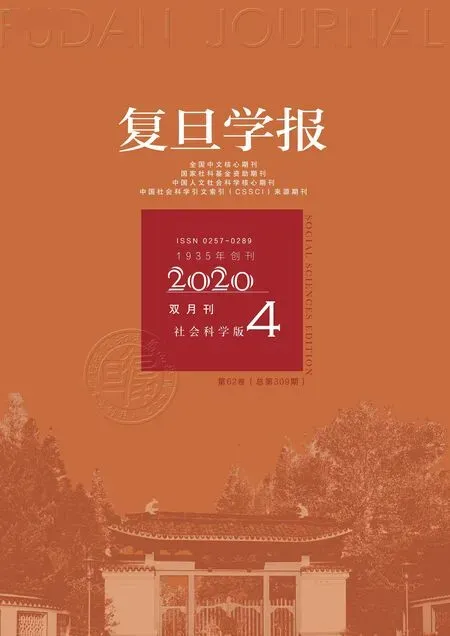康德论依附美:概念基础上的感性判断
王维嘉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 上海 200433)
根据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关于美的鉴赏判断是“感性(ästhetisch)”的,其规定根据只能是愉快或不愉快的主观情感,而非任何确定概念。(1)KU 5: 203-204. 严格来说,康德还区分了“关于美的、反思的鉴赏判断”与“关于快适的、感官的鉴赏判断”(KU 5: 214; cf. EEKU 20: 224);本文中的鉴赏判断特指前者。笔者对康德著作的引用按照普鲁士科学院版《康德文集》的书名缩写、卷数和页数(Immanuel Kants gesammelten Schriften, Ausgabe der königlich preuß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02)。缩写对照:Anthro = 《实用人类学》(Anthropologie in pragmatischer Hinsicht);EEKU=《判断力批判》第一“导言”(Erste Einleitung in die Kritik der Urteilskraft);GMS=《道德形而上学原理》(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JL=《耶施逻辑学》(Jäsche Logik);KrV=《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KU=《判断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对《纯粹理性批判》的引用按照对应第一、第二版的A、B 页码。笔者部分参考了以下中译本:《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判断力批判》(第一“导言”),载《冥河的摆渡者——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实用人类学》,载《康德人类学文集(注释版)》,李秋零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有别于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及其影响下的鲍姆加登美学,康德严格区分了感性的美与概念性的完善。鉴赏判断的感性特质不仅是康德美学的基本出发点,还深刻影响了以贝尔为首的形式主义者。然而,康德又在同一著作中区分了“自由美”与“依附美(anhängende Schönheit)”:前者不以“任何对象应当是什么的概念”为前提,后者则以“这样一个概念及按照这个概念的对象完善性”为前提。比如,花朵、鸟类和无词音乐具有自由美,其判断无需任何概念;而人体、建筑和马匹则具有依附美,其判断依赖于目的概念,并因此受到限制。(2)KU 5: 229-230.
但是,感性的鉴赏判断如何依赖于概念?康德的学说显得颇为可疑。洛伦德将依附美称为一个“错误”,因为它“不能既是一种美,又与美的定义相矛盾”。(3)Ruth Lorand, “Free and Dependent Beauty: A Puzzling Issue,”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29.1 (Winter, 1989): 32-40, at p. 33. 此外,雪普写道:“在依附美理论中,鉴赏判断与完善性判断似乎无法相容。” Eva Schaper, Studies in Kant’s Aesthetic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9) 80-81.蒋峦和余君则认为,康德在此发现了“辨证转化”的萌芽,却未能贯彻到底,因此无法走出“困境”。(4)蒋峦:《康德的徘徊——康德纯粹美与依存美关系探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余君:《论康德美学中的“纯粹美”和“依存美”》,《理论观察》第7卷,2007年,第77~78页。而在王德峰看来,康德“对付不了”一个关键问题,即依附美如何能通过想象力改变理念与感性、进而使之统一。(5)王德峰:《从康德的“想象力难题”看近代美学的根本困境》,《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那么,我们究竟该怎样理解依附美?笔者将既有思路大致分为“外在”与“内在”两大类:(1)斯卡尔、杰纳维、巴德、加蒙、埃利森、盖耶、鲁格、道林和曹俊峰等诸多学者将依附美视为完善事物所具有的自由美;在此,对完善性的概念判断与对自由美的鉴赏判断相互分离。(6)Geoffrey Scarre, “Kant on Free and Dependent Beauty,”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21 (1981): 351-362, at p. 358. Christopher Janaway, “Kant’s Aesthetics and the ‘Empty Cognitive Stock’,”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47.189 (October 1997): 459-476, at p. 473. Malcolm Budd, “Delight in the Natural World: Kant on th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Nature, Part I,”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38 (1998): 1-18, at p. 10. Martin Gammon, “Parerga and Pulchritudo adhaerens: A Reading of the Third Movement of the ‘Analytic of the Beautiful’,” Kant-Studien 90 (1999): 148-167. Henry E. Allison, Kant’s Theory of Taste, A Reading of the Critique of Aesthetic Judg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40-141. Paul Guyer, Values of Beauty: Historical Essays in Aesthe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29. Alexander Rueger, “Beautiful Surfaces: Kant on Free and Adherent Beauty in Nature and Art,”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16 (2008): 535-557. Christopher Dowling, “Zangwill, Moderate Formalism, and Another Look at Kant’s Aesthetic,” Kantian Review 15.2 (2010): 90-117, at p. 114. 曹俊峰:《康德美学引论》,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85~188页。(2)在贡布里希与沃尔顿等学者的理论基础上,麦勒班德、扎克特和图娜提出:依附美判断中,概念判断直接参与鉴赏判断。(7)Ernst Hans Josef Gombrich, Art and Illusion (London: Phaidon, 1959) 313. Kendall Walton, “Categories of Art,” Philosophical Review 79 (1970): 334-367, at p. 347. Philip Mallaband, “Understanding Kant’s Distinction Between Free and Dependent Beauty,”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52.206 (January 2002): 66-81, at p. 69. Rachael Zuckert, Kant on Beauty and B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05. Emine Hande Tuna, “Kant on Informed Pure Judgments of Tast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76.2 (2018): 163-174, at p. 165.笔者将指出,这两类思路各有其问题:“外在说”难以区分两种美,更无法解释美对完善性的依附关系;而“内在说”对概念性的强调则违背了鉴赏判断的感性特质。
本文研究康德的依附美学说,并通过阐发“感性鉴赏判断”与其“概念基础”间的张力,证明该学说的可信度。本文共有四节:第一节讨论康德对自由美与依附美的区分。第二和第三节分别考察“外在说”与“内在说”等既有诠释,并指出:当且仅当概念判断积极却又间接地影响鉴赏,我们才将对象判断为依附美;既有阐释却无法同时满足这些条件。在此基础上,第四节诉诸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图型论”,并提出:概念规定想象力用于表象事物完善性的图型,从而能积极地影响鉴赏判断。然而,这种影响仅仅是间接的:在对依附美的判断中,想象力仅仅借助图型(而非概念本身)与知性进行自由和谐的游戏;这就保证了鉴赏判断的纯粹感性。如此诠释下的“依附美”学说,可为形式主义艺术论提供新的反思框架。
一、 康德对自由美与依附美的区分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第十六节区分了自由美与依附美。自由美指独立存在、不以对象概念为前提的美。在康德的例子里,我们不考虑任何按照概念的完善性,就能直接地欣赏花朵、贝壳和许多鸟类的形式。有些郁金香具有教科书般的标准形态,堪称这类植物的范例;有些则发生变异,与一般的郁金香不甚相同。但是,两者与“郁金香”概念的一致或背离,并不影响其自由美。康德还认为:对于希腊式装饰线描和无词的音乐,我们不考虑它们本该是什么,而仅仅欣赏其自由美,因为这些艺术“不表示任何在某个确定概念之下的客体”。总之,我们对这些事物进行纯粹的鉴赏判断,而不预设任何概念。(8)KU 5: 229-230.
相比之下,依附美是有条件的,其前提为“有关对象应当是什么的概念”以及“按照这个概念的对象完善性”。在康德看来,人体、马匹和建筑的美都依附于它们的完善性。一座被装饰得五光十色的教堂,或许能就其自身而自由地取悦我们,却不符合“教堂”概念所要求的庄重性,因而不完善、不具有依附美。又比如,新西兰土著的纹身,其形式本身可能很美,却违背了人体该有的样子,所以称不上依附美。总之,鉴赏判断在此不再纯粹,而是“依赖”于概念判断中的确定目的。(9)KU 5: 229-231.
康德接着指出:“一个鉴赏对象就一个确定的内在目的之对象而言,只有当判断者要么关于这个目的毫无概念,要么在自己的判断中把这目的抽掉时,才会是纯粹的。”当一位判断者仅仅通过情感去判断对象,他就不考虑该对象的目的概念,最多将其视为自由美;而另一位考虑概念的判断者则可能将同一对象视为依附美,并与前者发生争执。康德举例说:一位植物学家认识到花是植物的受精器官,却可以抽掉这一目的,仅仅通过情感去判断一朵花,从而感受其自由美;不知这朵花“应当是什么”的普通人更是如此。于是,克劳福德提出:自由美与依附美的区别在于我们的判断方式,而非判断对象本身;我们总是能够抽掉概念,进行纯粹的鉴赏判断。(10)Donald W. Crawford, Kant’s Aesthetic Theor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4) 114.
但是,康德似乎又认为:我们的判断方式并不一定任意,而是可能取决于判断对象。维克斯、埃利森和图娜等学者指出:出于道德原因,我们在判断人体时必须考虑目的概念。(11)Robert Wicks, “Dependent Beauty as the Appreciation of Teleological Styl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55.4 (Fall 1997): 387-400, at p. 390. Allison, ibid., p. 142. Tuna, ibid., p. 165. 关于审美与道德的关系,详见:Weijia Wang, “Beauty as the Symbol of Morality: A Twofold Duty in Kant’s Theory of Taste,” Dialogue: Canadian Philosophical Review 57 (December 2018): 853-875.毕竟,根据康德哲学,我们不能仅仅将人视为工具或手段,而必须将其视为目的本身。(12)GMS 4: 429.此外,康德还写道:在艺术创作中,“某物必须被设想为目的”;因此,“在对艺术美的评判中同时也必须把事物的完善性考虑在内,而这是对自然美(作为它本身)的评判所完全不予问津的”。(13)KU 5: 310-311.艺术之不同于自然,就在于其生产“料想到一个目的”、其形式“应归功于这个目的”。(14)KU 5: 303.作为对比,蜂巢不是艺术,因为蜜蜂没有理性思虑,也没有目的,其生产仅仅出于本能。据此,我们判断艺术美时,必须考虑对应于艺术家意图的客观合目的性。
针对这段文本,道林与图娜等学者建议:我们或许能将艺术品作为自然物来欣赏,从而抽掉其目的概念,仅仅感受自由美。(15)Dowling, ibid., at p. 107. Tuna, ibid., at p. 166.笔者对此的看法有以下两点:
一方面,我们可以抽掉自然物的目的概念,欣赏其单纯形式。比如,植物学家也能欣赏花朵的自由美。根据康德的目的论,在判断某些自然现象(特别是有机体)时,我们无法解释它们与目的概念的偶然契合,因此设想按照某个概念创造它们的意志。这种表象仅仅是反思性的,并不构成关于对象的知识;归根到底,我们不可能洞见自然背后的目的原因性。
另一方面,康德明确指出:“在一个美的艺术作品上我们必须意识到,它是艺术而非自然。”(16)KU 5: 306. Cf. Diarmuid Costello, “Kant and the Problem of Strong Non-Perceptual Art,”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53.3 (July 2013): 277-298, at p. 297.我们不能抽掉艺术的概念,因为我们确知艺术家按照概念创造了它们。康德还谈到了“透露出某种合目的性的出土文物”:即使人们无法确知它们的目的,只要是将其看作艺术品,“已经足以使他们不得不承认它们的形状是与某种意图和一个确定的目的相关的了”。(17)KU 5: 236. 盖耶评论道:“只要我们认可一样东西有目的(这正是对所有人造物的看法),我们就必须设想其目的可能是什么,哪怕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Paul Guyer, “Beauty and Util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Aesthetics,”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35.3 (2002): 439-453, at p. 449.这进一步证明:我们必须将人造物(包括艺术)作为人造物来欣赏,而不能抽离掉它们的已知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讨论只解释了某些事物的判断必须通过目的概念,却未直接说明哪些事物的美必须是依附美。在康德笔下,“希腊式线描”、“卷叶饰”和“无词的音乐”等艺术恰恰是自由美的典型。它们固然没什么含义,不表示任何在某个确定概念之下的客体;但是,对这些艺术的判断必须考虑艺术家的目的以及相应的完善性。何况,正如朱俐俐所强调的:在把某种线描判断成“希腊式”时,我们已经规定了这个图样“应当怎样”。(18)朱俐俐:《“依附的美”:审美判断于目的论判断的交汇》,《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类似地,无词音乐也有种种体裁或规格,如舞曲、夜曲、练习曲、狂想曲等等;假设德彪西将《月光》作为舞曲发表,我们显然会将其判断为“不完善”的。那么,为什么康德不将这些较为抽象的艺术视为依附美呢?笔者将在第三节和第四节指出:只有当概念判断积极地影响鉴赏,我们才将对象判断为依附美;即使概念并不直接参与鉴赏,而是间接地、通过想象力之图型来影响后者。但是,我们必须先探究:在依附美判断中,感性的美与概念的完善性如何相容?
按照康德哲学,当我们只能通过“按照目的的原因性”理解一个对象的可能性时,我们就称该对象为“合目的”的。一方面,完善性指对象的内在、客观的合目的性,即杂多事物(或一个事物中的杂多部分)与其自身“应当是什么”的确定概念的一致性。比如,当我们在看似无人的沙滩上发现一个规则六边形时,我们必须假设某种按照“六边形”概念去安排这六条边的意志,从而表象这个六边形的完善性,即,其杂多部分与“六边形”概念的一致性。(19)KU 5: 220-226. Cf. EEKU 20: 226-228.
另一方面,康德将“美”称为“一个对象的合目的性形式,只要这形式是没有一个目的表象而在对象上被知觉到的”。(20)KU 5: 236.鉴赏力仅仅通过对美的愉悦情感而表象主观的合目的性。审美体验中,我们的想象力与知性进行自由而和谐的游戏,仿佛前者所表象的种种能够被后者在概念中统摄;为了解释这种心灵状态,我们必须假设对象与某个概念的一致性,却不表象任何确定的概念。正如亨利希所指出的:想象力与知性的自由和谐意味着“一般的可能概念化(a possible conceptualization in general)”。(21)Dieter Henrich, Aesthetic Judgment and the Moral Image of the World, Studies in Ka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49. 笔者加粗了“一般”两字。
总之,客观合目的性对应于确定概念,而主观合目的性指向不确定概念。在《判断力批判》的第十五节,康德特别强调“鉴赏判断完全不依赖于完善性”,还批评了“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对两者的混淆,以此与莱布尼茨、沃尔夫和鲍姆加登等人的美学划清界限。(22)KU 5: 226-227. 陈剑澜指出:康德美学的一大贡献在于“赋予审美自律论完整的哲学形式”。陈剑澜:《康德的审美自律论》,《文艺研究》2018年第11期。那么,他又如何能在紧接着的第十六节提出“依附于概念与完善性的美”?笔者将在下节考察一种对依附美的“外在性”诠释。
二、 依附美的“外在说”
斯卡尔写道:“康德似乎对事物之依附美提出以下条件,这些条件各自是必要条件,又一起构成充分条件:(a)该事物具有自由美;(b)它不违背合宜性(当它属于产生这合宜性的一类事物)。”(23)Scarre, ibid., at p. 358.所谓“合宜性(decorum)”,就是事物按照自身概念的客观合目的性。斯卡尔的阐述可被分为三层:
1. 自由美与完善性都是依附美的必要条件。不体现完善性的美,比如新西兰土著的纹身,仅仅是自由美;不体现自由美的完善性,比如一个标准的正圆,也称不上依附美。
2. 自由美与完善性各自是条件。在对依附美的判断中,纯粹鉴赏判断独立于概念判断,并不以后者为条件,反之亦然。
3. 自由美与完善性一起是充分条件。即使自由美与完善性彼此分离,两者在一个对象中的简单叠加也构成依附美。
巴德也认为,所谓“O作为K而具有依附美”即是“O在质上是完善的K”与“O具有自由美”的相合。杰纳维、加蒙、埃利森、盖耶、鲁格、道林以及曹俊峰等学者提出了类似的观点。(24)Geoffrey Scarre, “Kant on Free and Dependent Beauty,”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21 (1981): 351-362, at p. 358. Christopher Janaway, “Kant’s Aesthetics and the ‘Empty Cognitive Stock’,”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47.189 (October 1997): 459-476, at p. 473. Malcolm Budd, “Delight in the Natural World: Kant on the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Nature, Part I,”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38 (1998): 1-18, at p. 10. Martin Gammon, “Parerga and Pulchritudo Adhaerens: A Reading of the Third Movement of the ‘Analytic of the Beautiful’,” Kant-Studien 90 (1999): 148-167. Henry E. Allison, Kant’s Theory of Taste, A Reading of the Critique of Aesthetic Judg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40-141. Paul Guyer, Values of Beauty: Historical Essays in Aesthe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29. Alexander Rueger, “Beautiful Surfaces: Kant on Free and Adherent Beauty in Nature and Art,”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16 (2008): 535-557. Christopher Dowling, “Zangwill, Moderate Formalism, and Another Look at Kant’s Aesthetic,” Kantian Review 15.2 (2010): 90-117, at p. 114. 曹俊峰:《康德美学引论》,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85~188页。这些主张可被归纳为一种“外在说”:事物在质上的完善性与其自由美,就其本身而言相互外在;当且仅当两者都得到满足,我们就将这样的事物判断为依附美。
“外在说”的优点在于保持鉴赏判断的纯粹感性:一方面,我们规定性地判断对象的完善性,即它与其概念相符的那些部分;另一方面,我们反思性地、仅仅通过情感判断它的美,即它能引起我们想象力与知性之自由和谐的其余部分。换言之,在依附美判断中,我们表象同一个对象的客观合目的性与主观合目的性,而且概念判断与感性判断以互不干涉的方式并存。据此,巴黎圣母院就有依附美:一方面,以其尖圆拱券、飞扶壁、肋状拱顶与花窗玻璃,它符合哥特式教堂的基本标准;另一方面,它的许多建筑细节,如扶壁与主墙的具体角度、尖塔上的雕塑形象、花窗的特定图案,不为“哥特式教堂”概念所严格规定,从而能表现出自由美。其中,我们对自由美的鉴赏判断是纯粹感性的,并不出于完善性。与此同时,我们也不会因为不完善性而否定自由美:假设有人在教堂侧壁画上现代风格的彩绘,我们会认为它违背了教堂的概念、称不上依附美,但我们仍然可以肯定其本身的自由美。
总之,“外在说”主张:我们对完善性和自由美分别做出判断;这两种判断简单叠加,就构成不纯粹的、复合的依附美判断。笔者认为,此说面临两大难题:
第一,正如麦勒班德和扎克特所指出的:如果对依附美中的美的判断等于对自由美的判断,那么美就会只有一种,而非康德所区分的两种。(25)Mallaband, ibid., p. 69. Zuckert, ibid., p. 205.换言之,根据“外在说”,首先,通过一种关于美的、完全不依赖于概念的鉴赏判断,我们判断某个对象是美的;然后,再根据该事物的完善性与否,我们决定这种美是自由的还是依附的。但是,第二步中的概念判断并不干涉第一步中的鉴赏判断本身,这使得美本身只有一种,即不受完善性影响的自由美。因此,“外在说”下的依附美仍然属于自由美,而非与之相对的第二种美。这不符合康德本意。
第二,如果自由美判断与完善性判断相互外在,我们又为何要将事物的自由美“依附”于其完善性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判断“这事物是美的,尽管它不完善”?所谓“依附”应当是指:如果不判断事物的完善性,我们就无法判断它的美;或者,如果判断事物不完善,我们就会判断它不美。否则,即使我们考虑事物的完善性,它又何以成为该事物之美的“前提”?正如维克斯所指出的:概念以及按照概念的完善性应当对鉴赏判断有积极作用。教堂的依附美在于“它是一座美的教堂”,而非“它是美的、又恰好是座教堂”;前一个命题中的概念才起积极作用。(26)Robert Wicks, “Dependent Beauty as the Appreciation of Teleological Styl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55.4 (Fall 1997): 387-400, 389-390.固然,在日常经验中,我们可能出于道德原因而难以欣赏特定事物(比如汪精卫国画)的自由美,但这属于经验性范畴,并不是先验哲学的问题。康德已经强调:《判断力批判》“只是出于先验的意图来做的”。(27)KU 5: 170.
三、 依附美的“内在说”
为了克服“外在说”中鉴赏与概念的分离,有些学者提出了关于依附美的“内在说”,并主张概念对鉴赏有直接且积极的意义。麦勒班德认为,特定的概念内容能“建构”经验中的知觉要素,从而引发“适当”的审美反应。比如,以为鲸鲨是一种鲸鱼的人会将其判断为“灵活的”;但是,当他认识到这是一种鲨鱼,就会将其判断为“笨拙的”,因为它远不如其它鲨鱼般灵活。(28)Mallaband, ibid., p. 81. 此处的“灵活”与“笨拙”都是我们关于鲸鲨的客观感觉,而非审美情感。据此,我们对事物的审美体验不是纯粹感性的,而是部分取决于概念认识的。换言之,通过概念认识,我们能将对象与其规格理念比较,从而注意它与后者相背离的种种特点。只有意识到鲸鲨符合“鲨鱼”概念,我们才会将其对比于“鲨鱼”的规格理念,从而注意它相较于鲨鱼平均水准的笨拙。
类似地,扎克特指出:概念判断揭示了事物的标准属性,从而引导我们关注其可变属性,即,那些概念所未严格规定的特点。首先,在概念判断中,我们肯定一座教堂的完善性,并欣赏它作为“教堂”的简朴与端正;然后,在感性判断中,我们把上述标准属性当作“审美瑕疵”,转而注意教堂屋檐的特定角度、石头的特定灰度、廊柱的特定尺寸等等,以此感受其依附美。(29)Zuckert, ibid., p. 206.图娜则以亨利·摩尔的雕塑为例:如果我们把《斜倚的人》当作现代古典主义的作品,并要求它对人体的现实描绘,我们就会将其判断为“一堆乱七八糟的金属”、“像是一只濒死的螳螂或畸形的翼手龙”,总之“非常丑陋”;只有将其放入抽象雕塑的范畴,我们才会关注它与一般抽象雕塑不同的可变属性(比如它的流动外观与巨大尺寸),并感受它如何在柔弱不定中表现力量。(30)Tuna, ibid., p. 164-165. Cf. Jeremy Alex Liss, Randall, Daniel Stone, and Hallie Nell Swanson, “Statue of Limitations,” Columbia Spectator (July 2016).
以上对依附美的诠释强调了概念如何内在于鉴赏判断。这种“内在说”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贡布里希关于《百老汇爵士乐》(BroadwayBoogie-Woogie)的讨论:这幅画出自以严肃刻板画风闻名的蒙德里安之手,所以显得分外“欢脱(gay abandon)”;但是,如果我们以为它是塞维里尼的作品,就不会如此判断了,因为塞氏的未来主义风格一向强调“舞曲韵律”。(31)Gombrich, ibid., p. 313.沃尔顿也提出类似的看法,他写道:假设某个文明有种叫做“格尔尼卡”的浮雕式的艺术形式,俯视地看,“格尔尼卡”的色调、图案与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完全一致,但不同的“格尔尼卡”在高低或深浅方面有所差异。在那个文明看来,毕加索《格尔尼卡》(作为一种“格尔尼卡”)的特色是平面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冷静、肃穆与安宁等气质。相反,我们的文明习惯于绘画的平面性,从而注意到《格尔尼卡》的暴力、动感与活力等相较于普通绘画的特点。(32)Walton, ibid., p. 347.总之,观赏者对艺术的感性判断,取决于作者和作品范畴等概念性的背景知识。
按照“内在说”,概念规定了对象的标准属性,从而凸显其可变属性;于是,对后者的鉴赏判断,以对前者的完善性判断为前提。柯利甚至提出,哪怕最简单的感性反应(如“这幅画很美”)也不是纯然感性的。(33)Gregory Currie, An Ontology of Art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9) 40-41.与“外在说”相似,“内在说”也区分同一对象中的完善部分与优美部分;但是,“内在说”进一步指出完善性如何积极地参与审美本身,并使依附美判断“依赖”于概念。在笔者看来,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康德关于希腊式线描和无词音乐的例子:虽然我们带着概念去判断这些艺术,概念却不积极地参与鉴赏,所以它们的美仍然是自由美。相比之下,《加歇医生》表现一个确定概念下的客体(即医生本身的形象);其完善性勾勒出那些不受概念规定的、具有审美价值的可变属性,比如梵高的动态笔触、情绪化色彩,所以《加歇医生》的美是依附美。
尽管有以上优点,“内在说”却不符合鉴赏判断的感性特质。康德强调,鉴赏判断的规定根据仅仅是情感而非概念。鉴赏力(Geschmack)是判断力(Urteilskraft)的一种感性的、反思性的运用。根据《纯粹理性批判》,想象力是表象杂多事物(或一个事物中的杂多部分)的“直观能力”,知性是统摄杂多的“规则能力”,判断力则是“分辨某物是否从属于某个给定规则的能力”。(34)KrV B151 (cf. Anthro 7: 153); A128; A132/B171. 比如,想象力表象一棵柳树、一棵杉树与一棵菩提树,知性要将它们统摄在“树”的概念下;作为两者的中介,判断力分辨这些杂多是否从属于“树”的概念(参见JL 9: 94-95)。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进一步区分了判断力的两种运用:1.“规定性判断力”将特殊事物归摄于既有的普遍规则或概念,比如,判断“柳和杉都是树”。2.“反思性判断力”则为既有的特殊寻求普遍。为了形成一个普遍概念,我们必须“反思”诸多事物如何能是“一个意识”。(35)JL 9: 94. 根据《纯粹理性评判》,“概念”就是把杂多逐步结合在同一个表象中的“一个意识”(KrV A103)。当想象力的表象活动与知性的统摄要求达成协调,判断力会意识到这种心灵和谐;于是我们感到愉快,并形成概念。(36)KU 5: 187.然而,在反思某些对象时,我们仅仅感到心灵和谐,却不能找到与之对应的概念;这就将想象力与知性带入无概念的、自由和谐的游戏,判断力对此的意识则是感性的,即,仅仅通过愉悦情感、而非任何概念。(37)KU 5: 217-219.关于想象力与知性的和谐游戏,详见:Weijia Wang, “Three Necessities in Kant’s Theory of Taste: Necessary Universality, Necessary Judgment, and Necessary Free Harmony,” 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58.3 (September 2018): 255-273.这时我们说:鉴赏力,作为判断力的一种反思性运用,感性地将对象判断为美。(38)对美的鉴赏力并不等于反思性判断力,因为后者还被应用于崇高判断和目的论判断。
“内在说”认为我们通过完善性区分对象的标准属性与可变属性,这意味着想象力的活动必须受到概念约束。换言之,如果对可变属性的鉴赏判断包含对标准属性的完善性判断,判断力的运用就会既是规定性、概念性的,又是反思性、感性的。比如,我们一边认识到“这幅画较许多画作在色调上更活泼”或“鲸鲨较许多鲨鱼在动作上更笨拙”,一边感受这些特点的美。然而,严格来说,一个认识能力如何同时进行两种运用呢?固然,康德将依附美判断称为“不纯粹”的鉴赏判断,因为它“依赖”完善性判断中的目的;但是,依附美只是以概念和完善性为前提,并不包含后者。据此,概念即使对依附美判断有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也必须是间接的;毕竟,作为一种鉴赏判断,依附美判断必须是感性的,其规定根据仅仅是情感。我将在下一节指出,康德的“图型论(Schematismus)”可以调和感性判断与其概念基础间的张力。
四、 依附美的“图型说”
我们已经看到,“外在说”保持了鉴赏的纯粹感性,却无法解释其对概念的依赖;“内在说”解释了这种依赖,却又使依附美判断直接包含完善性判断,从而无法成为一种感性判断。那么,鉴赏判断如何能间接地依赖于概念,从而满足康德为依附美所设定的、看似矛盾的一对条件?笔者诉诸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图型论”。
康德将“图型”定义为“想象力为一个概念取得它的形象的某种普遍的处理方式的表象”。图型不同于任何特定形象,也不同于抽象的概念,而是描述了对应于概念的各种形象如何得到表现。比如,根据“狗”的图型,想象力描述一个四足动物的普遍形状,而不局限于任何单一形状(无论它来自经验,还是仅仅可能的、幻想中拼凑出的)。又如,一般的“量”的图型是数字,即,对一个又一个同质单位的逐次相加进行概括的表象。(39)KrV, A140/B179-A142/B182.数字“十”的图型并不指示任何特定的形象(纸上的十个点或屋里的十个人),而是描述将同质单位逐次相加十次这一方式。“十”的知性概念引导想象力去产生它的图型,无论它再用哪些形象去具现这十个单位。
虽然图型最初被概念规定,但它毕竟是想象力的产物,因此能脱离概念而持存。康德写道:“正是由于想象力的自由在于想象力没有概念而图型化,所以鉴赏判断必须只是建立在想象力以其自由而知性凭其合规律性相互激活的感觉上”。(40)KU 5: 287.在对自由美的欣赏中,想象力以任意方式表象或组合事物中的杂多部分;这种表象活动恰好与知性的统摄要求相协调,仿佛杂多符合某个图型,而这个图型又对应于某个概念。
据此,笔者提出:评判对象时,我们能够首先以事物概念判断其完善性,以此获得相应的图型;然后,想象力仅仅通过这个图型(而非概念)以一定方式组合对象中的一些部分,并以任意方式组合其余部分。于是,想象力的组合在整体上不受概念约束,而是与知性的一般合规律性自由游戏。如果这种游戏是和谐的、“相互激活”的,我们就通过纯粹反思性的判断力而感受到美。既然这种美既不直接被概念规定,又依赖于(规定了图型的)概念,它就是一种感性的、但不同于自由美判断的依附美判断;其中,概念的作用是间接而积极的。
固然,依附美判断中的想象力被图型所限制;但是,哪怕在自由美判断中,想象力也不是彻底自由的,而是被判断对象所限制的。康德指出:在鉴赏判断中,想象力“在领会一个给予的感官对象时被束缚于这个客体的某种确定的形式之上,并就此而言不具有任何自由活动(如在创作(im Dichten)时)”。(41)KU 5: 239.此时的想象力是“创作的(dichtend)”或曰“生产的”,即,“源始地展现(ex-hibitio originaria)对象”。(42)Anthro 7: 167-168.相对于创作:欣赏自由美时,我们的想象力被束缚于既有对象的确定形式;欣赏依附美时,想象力更是部分地被束缚于图型。但是,这两类审美体验中的想象力都不受概念束缚,并在此意义上自由。
比如,中国人能欣赏汉字书法的依附美:想象力在概念判断中获得组合这些笔画的图型;进而,在依附美判断中,它既要按照图型(而非概念)、以一定笔顺和字形去表象作品的部分特征,又要不按图型、任意表象作品中不对应于图型的另一些特征,如撇捺的特定粗细、折钩的特定角度。那些对应于图型的特征,本身只是完善的、而非美的;那些不对应于图型的特征,本身既不完善、往往也不美;但是,将两者一起表象时,想象力却可能与知性“相互激活”。作为对比,当美国人欣赏汉字书法、中国人欣赏阿拉伯书法,他们仅仅知觉到抽象形式,其想象力完全任意地表象那些笔划,最多感受自由美、甚或毫无美感。以上两类书法欣赏中,想象力都是自由、无概念的,却就图型而言有着不同的活动方式,从而与知性发生不同的和谐游戏——这意味着两种美本身的区别。于是,依附美并不等价于自由美加完善性,不是自由美的一种,而是与之相对的另一种美。
笔者的诠释符合康德对依附美的如下论述:
真正来说,完善性并不通过美而有所收获,美也并不通过完善性而有所收获;相反,既然当我们把一个对象(Gegenstand)借以被给予我们的那个表象通过一个概念而与客体(Objekte)(就它应当是什么而言)相比较时,不能避免同时也把这表象与主体中的感觉放在一起,那么,当这两种内心状态互相协调时,表象力的整体(gesamt)能力就会有收获。(43)KU 5: 231.
在康德术语中,“对象(Gegenstand)”通常指未受知性影响的直观杂多,而“客体(Objekt)”则已被知性概念规定。(44)KrV A190/B235; B137. Cf. Howard Caygill, A Kant Dictionar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5) 304-306.据此,文中的“对象”指我们所要判断的、被给予的一个具体对象。既然一个概念规定了“客体”应当是什么,这个客体就被表象为一个图型:它既是想象力的产物(而非概念),又具有普遍性(而不限定于任何单一形象)。比如,判断一座教堂的完善性:一方面,我们以想象力表象这座教堂,并通过“教堂”概念将这个表象与“教堂应该是怎样”的图型相比较;换言之,想象力按照图型去表象对象。另一方面,我们又将这座教堂的表象与主体中的感觉放在一起,即,感性地判断它的美。这两种内心状态的“互相协调”,意味着想象力在感性判断中也按照图型去表象,正如它在概念判断中那样。这种情况下,我们感受到这座教堂的依附美,并在概念性表象与感性表象上都有所收获。值得注意的是,依附美“并不通过完善性而有所收获”、不直接被概念规定;但是,它的基础是想象力仅仅按照图型的表象活动,而图型毕竟来自概念。于是,依附美判断既是感性的,又间接地依赖概念。
以上分析有助于我们考察艺术论中的形式主义思潮。贝尔主张艺术只在于“有意味的形式”,其欣赏完全无关于(1)对他物的表现;(2)有用性;(3)作者以及艺术史等背景知识。(45)这三点分别参见:Clive Bell, Art, Boston (Massachusetts), 1913, p. 12-13; p. 36; p. 44. 贝尔的形式主义艺术观也可追溯到康德“审美无利害”的讨论,详见:王维嘉:《康德论审美与利害》,《哲学研究》2018年第12期。赞格维尔则提出一种“折衷的形式主义”;他一方面肯定表象性艺术的非形式基础,一方面坚持道:不同范畴下的《格尔尼卡》有着相通的形式特征,并带给观众相同的感受,只是观众采取不同范畴尺度去判断这种感受的程度;总之,“具有程度和依赖范畴是两码事”。(46)Nick Zangwill, “In Defence of Moderate Aesthetic Formalism,”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50.201 (Oct. 2000): 476-493, at p. 487.赞格维尔似乎言之成理:一杯温水比沸水凉、比冰水热,但我们对这杯水的知觉本身不变;类比地,《格尔尼卡》作为“绘画”是动感、暴力的,作为“格尔尼卡”是平面、冷静的,但我们对其感受本身不变。
在笔者看来,形式主义正确指出了:我们只需要最基本的时空意识就能知觉事物;艺术范畴、作者风格,甚或所表现的对象,并不会改变我们对艺术的直观。话虽如此,问题恰恰在于:康德认为决定美感的并非被给予的直观本身,而是想象力对直观的表象活动;这种活动,又可能按照(对应于概念的)某种图型。康德举例道:当野蛮人和文明人看到同一幢房子,前者获得“单纯直观”,后者则获得“同时的直观与概念”。(47)JL 9: 33.换言之,两位判断者对相同直观作了不同表象。类似地,当美国人与中国人看到同一幅汉字书法,前者只有单纯直观,其想象力的表象是完全任意的;后者则有直观与图型,其想象力的表象按照一定方式。因此,两者的想象力虽然表象同一作品,却与知性进行不同的自由游戏。只有理解绘画平面性的观众,才能感受《格尔尼卡》如何在平面中传达动感,而“鸭-兔悖论”、达利的视错觉画等现象更有力揭示了形式主义的局限性。于是,正如沈语冰所观察到的:以形式批评闻名的弗莱,却在其晚年“越来越强烈地质疑作为现代主义基础的形式主义原理”。(48)沈语冰:《图像与意义:英美现代艺术史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80页。在他对弗莱著作的译文中,沈语冰还评论道:作品的意义并不存在于形式的固有必然性中,而是嵌入创作者与观赏者所构成的“相互游戏的整个语境中”。罗杰·弗莱著,沈语冰译:《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1页(第十章注1)。
五、 结 语
康德“依附美”理论的难点在于感性鉴赏判断与其概念基础之间的张力。“外在说”将依附美理解为依附于完善性的自由美,因此难以区分两种美,也无法证明这种依附的必要性。“内在说”认为概念判断直接参与依附美判断,因此违背了鉴赏判断的感性特质。我主张:想象力可在完善性认识中获得图型,并在审美鉴赏中仅仅按照图型与知性自由游戏,从而形成依附美判断:这种判断既运用反思性(而非规定性)的判断力,又通过图型依赖概念。于是,依附美既是感性的,又间接地以概念为基础;既有别于完善性,又有别于自由美,可谓一种特殊的美。如此诠释下的“依附美”学说,不但本身具有说服力,还能为形式主义艺术论提供新的反思框架。(49)感谢笔者的同事陈佳以及笔者讨论班上的学生们(特别有何婕、宋佳慧、吴一昊、谢玄玄、肖阳)对本文初稿的批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