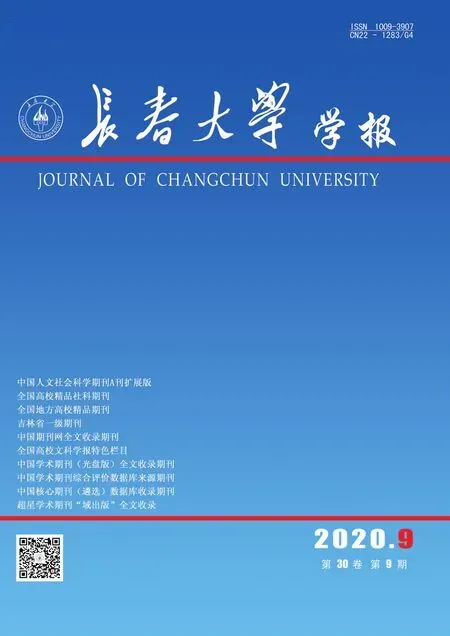从深层生态学视角看琳达·霍根的《太阳风暴》①
陈 征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外语系,福州 350108)
琳达·霍根(Linda Hogan, 1947—)是美国本土裔契卡索女作家,其作品曾获得美国图书奖、美国本土裔作家团终身成就奖等诸多奖项。其代表作品小说《太阳风暴》曾获得科罗拉多图书奖。无论是诗歌、小说、散文,还是戏剧、传记,霍根的作品都集中关注了环境主题,从本土裔族群传统文化的视角控诉美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和殖民暴力,揭示了本土裔遭受的苦难经历,透露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1973年,挪威哲学家阿尔内·纳斯在《浅层和深层孤独生态学运动:摘要》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深层生态学”一词。深层生态学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与自然地位平等,人类只是参与者不是操纵者,因而无权处置自然。深层生态学涉及多样性、复杂性、共生和平均主义的原则,“倡导重建人类文明的当前秩序,并使之成为自然和谐的组成部分”[1]。
霍根的小说《太阳风暴》(SolarStorm, 1995)讲述了17岁的印第安女孩安琪拉(Angela)从白人寄养家庭重回出生地的寻源归家之旅。小说描写了由于白人殖民者猎杀动物、修建大坝、砍伐森林等对环境的摧毁行为,部落自然环境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坏,继而导致印第安人民的身份迷失和精神创伤。小说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思想的同时,呼吁人类与自然的平等和谐共生,展示了作家深层生态思想,揭示了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融合的生命共同体的关系。
1 生物中心主义下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生物中心主义平等”是深层生态学的最高标准之一。深层生态学认为,在这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中,所有自然事物(生态系统,生命和景观)都具有同等价值,并享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
在白人社会入侵之前的亚当肋骨镇(Adam’s Rib)上,人与动物是和谐共生的。在印第安文化传统里,人对于自身的认识与对动物的认识密切相关,彼此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在动物的引导下,人类学会探寻水源、辨别方向、预测气象、躲避灾害,印第安人对动物心存敬畏和感激,并形成视其他物种存在为平等互惠的动物伦理。印第安人的许多神话传说和口述部落故事也是以动物为主题的,涉及宇宙的发源、部落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霍根在小说中也讲述了海狸创世的故事:海狸创造了人类,并与人类“订立盟约,承诺要彼此帮助。海狸提供鱼、水鸟和动物,人类则相应地要看顾好世界,并与神灵和万物对话”[2]239。深层生态学的代表人物阿尔多·利奥波德在其著作《沙乡年鉴》中也提到“大地伦理学”,认为山川河流、鸟兽虫鱼、花草树木等和人类共同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3]。因此,自然环境不是供人享用的资源,而应当是被保护的主体,与人类平等共生。印第安生态意识中,人类只是自然活动的参与者,而不是操纵者和支配者。正如小说中部落的长者们认为,“我们的生命被鸟儿、蜻蜓、树木和蜘蛛见证着。不仅动物和蜘蛛见证着我们,甚至深度空间里鲜活的银河系和北方吹来的冰雪也一同见证着我们”[2]80。印第安人崇敬自然,认为动物同样具有灵魂、主体意识以及神圣力量,体现了印第安人对动物的道德认同和伦理关怀,表达了人类与自然万物相互依存、平等和谐的理念。
印第安人把土地尊称为大地母亲,体现了人与大地和谐亲密的关系。印第安文化意识里,大地不但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更代表了无穷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具有神奇的治愈力量,因此,人类应对大地母亲的奉献和眷顾心怀感激和崇敬之情。“人们讲述土地的故事,因为这些地方自身具有能量,它们是有生命的,石头、泥土、云母、矿物或者其他种类的东西,它们都具备治愈的能力。”[4]印第安人认为,人和土地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没有土地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人类合理的社会和文化观念,也就不存在维持生命的土地”[5]。美国印第安评论家波拉·甘·艾伦也曾论及:“我们就是土地,这是渗透在美国印第安生活中最基本的概念,土地和人民是同一的。”[6]正如霍根所说,“这个世界在我们的血液和骨头里,我们的血液和骨头就是土地”[7]。对小说中亚当肋骨镇的印第安人来说,离开部落的土地无异于死亡,因为土地承载了部落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信仰,是印第安人获得自我身份认同以及构建自我与宇宙关系的根本。
印第安人的传统认知里,水即是大地母亲的血液,与土地共同构成人类生存的基本物质基础,具备无穷的精神力量。印第安人推崇水的神圣性,视其为孕育生命的灵性物质。他们保护淡水与海洋,坚守着人与自然互惠的原则,体现了平等和谐共存的宇宙整体观。霍根在小说中借用水的意象强调主人公安琪拉重建与“自然母亲”的联系。身心备受痛苦且迷失自我的安琪拉回到故土,在养祖母布什的帮助下,学会亲近“自然之水”,重拾游泳、划船和捕鱼等部落传统技能,并逐渐感受到自己在宇宙万物中的归属感。水成为她与自然万物之间密切相连的纽带:“我生活在水中。我们之间不可分离……我一生都在寻找我曾经迷失的古老世界,只有我的身体不曾遗忘它,在那一瞬间,我明白了我和鸟儿、雨水一样都是它的一部分。”[2]79通过回归部落故土的自然水域环境和印第安生态文化,安琪拉最终摆脱了白人文化的束缚和压制,跨越了人与自然的疆界,其自我意识得以唤醒,身心得以疗愈,自我身份得以重构。
2 人类中心主义下自然的灾难与人类的创伤和迷失
人类中心主义是西方文化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价值取向。居于中心地位的人类被赋予对自然界一切生命和非生命物质的绝对支配权力。人与自然是利用与被利用关系,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也不断地加剧。
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让人类背离了与自然的互相依存关系,造成环境的悲剧。在小说中,为了解决纽约居民的用电问题,白人政府强行要在印第安人生活了数千年的土地上修建大坝。大坝的修建导致了数千公里的土地被淹没,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驯鹿和鹅以及人们需要的用于治疗的植物都遭受到了影响”[2]36,印第安人民流离失所,印第安部落赖以生存的文化根基和精神信仰也被破坏殆尽。“挪威和瑞典的伐木工人砍伐了森林;加拿大人和美国人都渴望获得水力;法国的猎手捕捞海狸和狐狸,直到它们都消失了”[2]108。在人类中心主义文化下,为了所谓的文明进程和社会发展,自然成为仅具有物质价值的商品遭受盘剥,自然的巨大毁灭给人类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创伤。
在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引导下,白人对自然无节制的掠夺和破坏,不但让印第安人失去了家园,更让他们遭受了身份的迷失和精神的创伤。小说中,法国毛皮猎人在亚当肋骨镇上肆意捕杀动物,“海狸和狼消失到几乎灭绝时,男人们(白人贸易商)迁移到其他未被损毁的地方,把他们的女人和孩子留在身后,好像他们也是被耗尽了的动物”[2]28,沦为被抛弃的人,而原本是白人寻找毛皮和财富的“生意贸易之地”,最后成了“一片孤立的土地”[2]65。土地被掠夺和生态环境被破坏所导致的身份迷失和精神创伤,在安琪拉和她的母亲汉娜以及安琪拉的外祖母洛瑞塔三代印第安女性的经历中都有着深刻的体现。欧洲的皮货商和捕猎者通过毒饵猎捕动物的同时导致饥饿的印第安人在吃了下过毒的猎物后大量死亡。洛瑞塔虽然侥幸存活却遭受了精神上的伤害,汉娜从母亲洛瑞塔那里得到的只有她愤怒的情绪和仇恨的发泄,却没有丝毫的母爱。幼年的汉娜身上遍布戳伤、烫伤等各种伤痕,在承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汉娜的躯体里也仅有麻木、仇恨和暴力。因此,当汉娜成为母亲时,她将还是婴儿的安琪拉塞进木柴堆里差点冻死,用牙撕咬安琪拉致使她脸上留下永远的伤疤,最后又遗弃安琪拉使其辗转寄养在不同的白人家庭。这一切都是自然的悲惨命运在印第安女性身上的创伤书写,正如小说所说,“我们拥有相同的历程,生命被摧残,动物被虐杀,树林被毁坏,我们的命运同这片土地紧紧相连”[2]96。主人公安琪拉童年时期痛苦的遭遇以及成长的经历使她的心灵受到严重创伤,她缺乏安全感,与他人分离和疏远,深陷于生存危机和身份危机的困境中。
人类中心主义宰制下的印第安部落,不但被剥夺了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更深陷于丧失文化和传统的精神危机。面对土地被掠夺、资源被剥削、妇女被遗弃、种族将被灭绝、白人主流社会的文化渗透,印第安部落的文化传统和精神信仰逐步地分裂瓦解。印第安人幻想着能重新夺回土地和家园,回归原本的部落生活,却承受着现实和幻想撕裂的精神创伤,沉浸在绝望与麻木之中。小说中,安琪拉和祖母们回到故土小镇上,看到的是“部落的年轻人整日酗酒,跌跌撞撞,醉倒在街头巷尾……酒精似乎成为医治痛苦的唯一解药”,“没有酒的人们则更穷苦潦倒,不停地悲伤哭泣,并试图自残”[2]226。一方面,白人主流社会对自然的贪婪与物化的态度,导致“大地母亲袒露着伤疤”[2]224;另一方面,大地母亲满目疮痍的伤痛进一步印刻在部落人民身上。霍根借小说揭露白人主流社会对土地的暴行,更控诉其对印第安人民殖民式的宰制。正如她本人所说,“这里正发生的一切是对灵魂的谋杀,但凶手却无需承担任何后果”[8]。自然环境的破坏让印第安部落群体不但失去生命的延续性,同时失去了传统的信仰、身份的根基和精神内核,最终导致“集体性的经验消亡”[9]。
3 生态自我的重新实现
米切尔·托马斯豪指出,“生态自我”或生态身份描述的是个人与自然环境的联系和态度,“生态自我是指我们如何建立自我意识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而身份的建立是需要每一个人付出努力”[10]。马休斯在《生态自我》一书里指出,人类的自我实现应当与非人类自我乃至整个宇宙自我相关联,参与宇宙自我的自我实现,唯有如此,人的存在意义才能得到充分完美的实现,而生态的“大我”(Ecological Self)也只有建立了人主体与自然主体和谐共生的关系才可能实现[11]。小说的主人公安琪拉因被母亲遗弃并不断流离失所的经历,导致自我身份的迷失,在追寻自我身份的过程中,她努力实现自身与自然万物的融合依存,通过重建与自然的亲密联系,从“小我”成长为“大我”,最终实现了“生态自我”的回归。
部落故事帮助安琪拉加深了自我与土地和族群身份的认同。印第安人的口述故事讲述了美洲原住民的创世开源,与大自然的互惠共生的生活方式以及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历史与传统文化通过口述故事传统世代相传。安琪拉从部落长辈们的故事里了解自我与部落的关系,感知到自己的生命个体融入到部落群体的彼此关联之中。“我现在认为她(曾祖母朵拉鲁杰)是根,我们像是一棵树的家庭,在地下相互连接,老树滋养幼枝,让其发芽成长,正是在这个古老的世界里我开始绽放,她们的故事召唤我回家。”[2]48安琪拉在与部落文化和历史的重新连接中完成了生态自我的实现和身份的认同。印第安文化认为,人类的自我意识与物种起源的久远记忆以及所有生物的存在共享相互联系的记忆,失去生态记忆也就失去生态自我,因此,恢复生态记忆是人们恢复其生态自我的关键。
通过重建与自然的亲密联系,安琪拉重拾她的生态记忆并重建其生态自我。由于多年被寄养在白人家庭里,安琪拉受到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将自然界视为“他者”。回到家乡亚当肋骨镇后,她开始感受到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会闻到新鲜的空气,在我的皮肤上感觉凉爽的微风,听着隆隆声和水声。所有这些使我感到安慰”[2]43。有时她会想象着“我就像夜空的星星穿越时空时落下来,就像狼和鱼一样来到这里……我像狼一样美丽”[2]54。随着时间的流逝,她逐渐习惯了与自然融为一体。在养祖母布什的引导下,她开始在花园里工作,在水中划桨,砍柴,捕鱼,聆听动物和风雪的歌唱。随着安琪拉与自然的互动越来越多,她内心体会到更多的舒适与自在,对自然的偏见逐渐瓦解,她寻回了内心的宁静与平衡,重建与自然的联系,实现了生态自我,重新获得对世界的归属感。
梦境地图的重现预示了安琪拉重建与自然的联系,实现了生态自我。印第安的文化认知中,梦境根植于大地,记录了部落的历史、传统、文化,体现了人类与宇宙万物的动态联系,是人类与灵性世界沟通连接的路径。小说中,安琪拉的曾祖母朵拉鲁杰凭借“活地图”的本领,一种“以口语叙述的方式汇聚印第安人的自然地理知识、地方的历史与文化,融记忆图、体验图与梦境图为一体”[12]的印第安生态智慧,在从亚当肋骨镇到双城泛舟北上的旅行中,引领大家取道古老水路穿越荒野,安琪拉从中感受到万物灵性的智慧,认同了土地的记忆与意识。在朵拉鲁杰的帮助下,安琪拉逐渐恢复了梦境的能力,重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我遗失了生命的亮光,现在我再次找到它,梦境改变了我”[2]170。她意识到“在梦境里,人的内心可以与土地对话,找到自己的方向。人们梦见大地和水流,梦见食用的动物居住的地方,根据梦境地图便可找到猎物。这是动物和人类共同的语言,人类以同样的方式找到自我的疗愈”[2]170。同时,有关植物的梦境唤醒了安琪拉。她感到内心里对于自然的记忆被唤醒并像“野生固有的,等待萌发的”种子一样强劲生长。“也许梦的根源在日常的土壤中,或在心中,或在无法言说的地方,但是当它们聚在一起生长时,它们就像氢的种子和氧的种子,共同创造了海洋、湖泊和冰。这样,我和植物彼此融合了。它们把我缠在茎和藤上,那是一个美丽的交融。”[2]171植物梦境加深了安琪拉对自然万物的认知和敬畏,感受到自然丰富的灵性和无穷的生命力,自我与自然万物的界限消解并融合为一体。
4 结语
在小说《太阳风暴》中,琳达·霍根通过书写印第安部族的命运,表达其深层生态的理念,揭示了人类对自然环境与土地伦理的背离,不但造成了生态危机,更导致人类身份的迷失和精神的创伤。人类应摈弃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念,建立生物中心主义的平等生态观,重建与自然的亲密联系并恢复生态记忆,才能重建生态自我,建立文明持续发展的生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