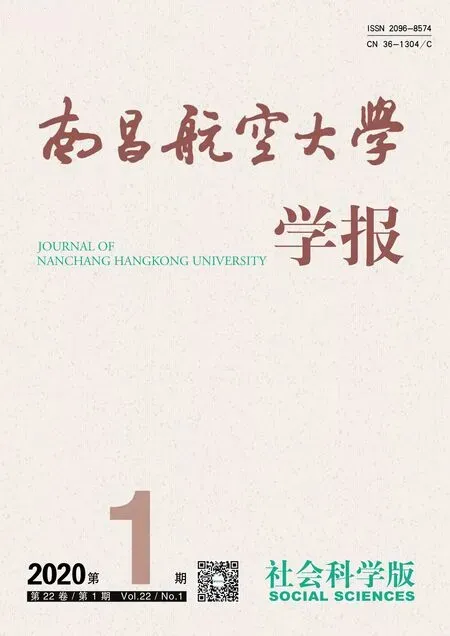放任、失衡、转向:苏联意识形态建设的嬗变
孙自胜
(淮南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淮南 232038)
意识形态建设是苏共开展社会动员、激发社会活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力量,也是对抗西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重要支撑。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共在意识形态建设上出现的诸多错误,成为改革失败的重要因素。对于苏共意识形态是如何一步步被消解的,学界经过长期的研究,亦见仁见智。在苏联解体三十年之际,本文对苏共意识形态建设嬗变的因缘进行深入反思,对推进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放松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意识形态幼稚病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的苏共中央掀起了一场著名的改革运动,试图改变这个超级大国社会主义模式僵化的状况,实现经济更加发达,人民更加民主,社会更加公正的目标。但在改革中,苏共无视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盲目自信,自由放任,出现了“去意识形态化”现象,失去了意识形态阵地。
(一)放松广大民众的社会主义教育
苏联民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可与认同,既取决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成就,也有赖于苏共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信念教育。从历史上看,经过斯大林集权主义、赫鲁晓夫自由化改革、勃列日涅夫的保守政治,苏联意识形态领域一直麻烦不断。到改革时期,由于经济增长乏力,物质匮乏,利益的重新调整,广大民众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存在的不满、冷漠,甚至怀疑愈发严重。而苏共领导层不仅没有正视民众的信仰危机,反而自我陶醉,盲目乐观。戈尔巴乔夫曾说过:“苏联的社会主义令人民引以为自豪,应该继续发展下去;神圣的社会主义信念会引导我们达到最终目标——建立共产主义社会。”[1]正是基于这样的自信,苏共领导层错误地判断应集中力量进行经济政治改革,完全无需在思想政治教育上消耗精力。
更为过激的是,苏共竟然片面地认为,只要通过改革能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至于他们信仰什么主义,理应完全由各人自己决定。戈尔巴乔夫说:“我们苏联人拥护社会主义,但是,我们并不强迫任何人接受我们的信念。”[2]这种让任何人自己选择信念的观点,完全背离了苏共长期坚持的自上而下的、对民众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列宁主义原则,陷入了列宁曾经批判过的“自发论”的错误。可见,改革后期民众信仰的崩塌,思想观念的失控,正是苏共自己自由放任造成的。
(二)放弃领导干部的党性教育
党章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纲领和行动指南,是党培养干部和选拔干部的思想组织原则。苏共历史上多次修改党章①从1903 年二大到1991 年二十八大,苏共通过了十四部党章,每一部党章都有部分修改。其中,修改比较大的是1925 年十四大党章、1952 年十九大党章、1961 年二十二大党章和1986 年二十七大党章。参见牛安生.苏共党章评述[J].苏联东欧问题,1988(2):41-47.,尽管修改后的党章仍不完善,但对规范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改革时期,苏共逐渐改变了按照党章培养和教育干部的方式,甚至抛开党章及其政治组织原则,放弃了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失去了党纪的约束,在苏共内部出现的是组织涣散、纪律松弛、行动乏力。一些政府官员、各级党的干部借着改革的名义大搞特权,生活腐化,滥用权力,大肆侵吞国家资产,严重损害了苏共的形象,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对于党内出现的问题,苏共中央不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反而推波助澜。戈尔巴乔夫公开宣称苏共党章是意识形态的“陈腐论调”,批评苏共二十二大颁布的党章是“伪马克思主义”,并武断地认为,党章“极其陈旧,连引用他都会感到难堪,只要提起他便会遭到嘲笑”[3](321)。在这样的新思维下,苏共二十七大通过的新党章,自然地成为形式上应景的工具。在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苏共把党员的评价标准界定为人们对改革所持的态度:谁支持改革谁就是合格党员,反之,则是不合格的党员。依据这个标准,苏共首先更换了领导核心,把一批所谓的改革“激进派”安排到主要领导岗位上。事实证明,正是这些人后来把苏联带入了深渊。
(三)取消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苏共通过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培养青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取得的效果是明显的。但由于长期的教条化教育,教学内容和方法的陈旧,单向的灌输,以及社会多种不良因素的影响,广大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带有一定的抵触和漠然情绪。针对思想政治教育出现的问题,本该理性对待、正确解决才是正途。但苏共却判断思想理论教育已经跟不上改革发展的需要,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课严重束缚青年人的思想,“对人用处不大”,培养不出知识化、年轻化和专业化的改革人才。主管思想理论教育工作的领导人雅科夫列夫,甚至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立场,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虚假意识”,不相信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生命力”[4]。他提出要把这些束缚青年学生思想的有害元素统统抛弃,转而鼓励高校要多元文化交流,开展自由的研究。
基于这种错误认识,苏共对高校思想理论课程进行了调换,从新开设的课程名称①苏共把高等院校的《苏共党史》改为《二十世纪社会政治史》,《科学共产主义》改为《现代社会主义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改为《哲学概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美学原理》改为《伦理学和美学原理》。参见陈先齐.八十年代苏联高等教育改革述评[J].苏联东欧问题,1991(10):26.看,基本上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功能。这种做法更加助长了高校师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漠视。在课堂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课不被重视,甚至还遭到一些学生的嘲笑。一些教师也随风转舵,不再坚持和研究马列主义,反而研修和追逐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并以这些西方理论为依据,来解释苏联的社会现象。1989 年12 月,苏联国家国民教育委员会又颁布命令,全面废除苏联高等院校统一的 “马列主义”课程。至此,苏共对青年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彻底走向了自由化。取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学,就等于放弃了长期坚持的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任务。
在改革中,苏共放任意识形态教育走非意识形态化的做法,实质上是自毁长城。苏联社会主义长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敌视和“围剿”,在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竞争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加上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不足,还有历届领导层主观意志化的困扰,致使苏联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着风险和危机。要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必须要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而苏共中央在改革中,面对各种不确定性,采取放任的态度,放松甚至取消对广大民众、党员干部和青年的意识形态教育,这种一手硬一手软的做法,迎合了西方国家对苏联“西化”的需要,犯了意识形态幼稚病的错误。
二、在“公开性”的民主化道路上失衡,失去意识形态话语权
在改革中,苏共高举“公开性”旗帜,此举也被世界舆论一度视为走民主化道路的亮点。我国一些学者也曾认为苏共的“公开性”“在苏联历史上,意识形态从未出现过如此民主、宽松、活跃的局面”[5]。今天来看,由于没有边界、没有底线的“公开性”,导致苏共在民主化的道路上逐渐失去平衡,走向极端民主化,最终丧失了意识形态话语权。
(一)倡导完全的“公开性”,社会舆论失序
“公开性”本质上是意识形态话语。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列宁曾在批判经济派错误时,提出过“完全的公开性”[6]问题。在改革中,戈尔巴乔夫积极倡导“公开性”,试图借助这一运动打开改革的局面。为了进一步推广所谓的“公开性”,苏共中央以1986 年4 月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露事件为契机,通过新闻媒体向国内外提供了与该事件有关的全面信息。至此,在“公开性”话语下,关乎苏共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潘多拉魔盒被正式打开。
首先把“公开性”作为推进民主化的武器。苏共逐渐把意识形态的一个个“窗口”打开。在公共事务领域,公开党和国家机关的一切信息。中央领导人面对国内外发表讲话不经过集体讨论,可以口无遮拦地自由言说;把国防、外贸、统计、生产等部门一切本属保密的信息公之于众;废止报刊检察机关,停止其监督检查的职能。在社会生活领域,开放一切社会舆论及场所。打破报刊杂志、广播电台的所有禁忌,鼓励人们对各种社会的丑陋现象、缺点和不足进行评论和批评;开放一切文学、艺术和创作领域,开禁所有书籍和影视作品。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是让广大民众不要仅仅只吃“一份单纯意识形态的可怜‘口粮’”,而让读者自己“亲自去比较、对照不同流派的哲学思想并作出自己选择的机会”[3](378)。
当苏共抱着良好愿望、毫无保留地把国内、党内发生的一切事件公之于众的时候,局势并没有按照预想的路径发展。民众积极参与政治民主生活的热烈局面并没有出现,反而,那些西方自由主义者、利益集团代言人、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心怀不满的敌对者,等等,借助“公开性”公开粉墨登场。一时间,各种对立的言论、恶意的攻击等不良情绪在社会上蔓延。正如莫斯科州前州长科诺托普在写给戈尔巴乔夫的信中所说:“世界主义者几乎是在利用所有信息媒体……,欺骗劳动群众,散步对党的不信任,千方百计让人们忘却苏联自古以来的爱国主义情感教育。”[7]而苏共迫于全面“公开性”的承诺,既没有对集体无意识现象进行正确地引领,也没有对宣传舆论进行有效地调控。在任何人都能罔顾事实、恣意妄言的氛围中,社会舆论场基本失去了控制。
(二)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评价失控
苏共在鼓动民众自由评判现实的基础上,继续以全面“公开性”为指导,推动民众反思历史。苏共领导层认为,要深入推进改革,必须要反思历史的错误,澄清历史问题。从平反冤假错案开始,逐步扩大到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重新认识和再评价。开始的一段时期,评价还比较客观,但逐渐地,一些个人和组织脱离了客观的立场,对苏联历史的反思和评价充斥着偏见和怨恨,也有一些人肆意编造苏联历史的谎言,对消极现象无限放大,故意抹黑历史。一些报刊杂志甚至刊登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文章,把布尔什维克革命运动的正当性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一笔抹杀①当时,苏联的《真理报》《消息报》和《共产党人》等一批报刊杂志,主动刊登“激进派”的文章,随意发文批评苏共与政府,同时还支持“民主派”和民族主义者。参见李慎明.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8 集DVD 教育参考片解说词(下) [J].科学社会主义,2007(2):142.。由于缺乏正确历史观的引导,逐渐造成局面失控,认识和评价出现严重的分裂。在民众无端的猜测和新闻传媒无原则的传播中,舆论生态继续恶化。从批判斯大林个人的“去斯大林化”,到否定整个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又延续到对“十月革命”的否定和对列宁主义的怀疑与批判。在无原则无底线的攻击和歪曲历史中,从大众的情绪化转为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否定和对苏共的信任危机。
这种状况的出现,正是苏共迷恋全面“公开性”神话、用虚无主义态度评判历史导致的恶果。从提出正视历史和纠正历史错误,到最终演变成否定和仇恨,恶毒攻击苏联历史的闹剧,完全出乎苏共的意料。诚如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弗·舍甫琴科在评说俄罗斯“去斯大林化”的危害时所反思的:“由于缺乏对新的历史时代的理论分析,苏联社会只能通过试错的办法实现发展,注定要付出惨痛的代价。”[8]反思历史,以史鉴今是世界各民族继续获得发展的重要手段。对苏共而言,长期处于“冷战”环境和特殊时期,确实存在着诸多模糊不明的历史问题,客观认知和正视其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澄清历史遗留的问题,是苏共迟早要面对的。但苏共放弃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原则,任由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结果把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抹得一团黑。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痛心地说过,对待苏联历史决不能用“黑色的油漆把过去全部抹黑”[9]。恰恰正是这“黑色的油漆”,不仅抹黑了苏共长期奋斗的历史,而且抹掉了民众的历史意识。
(三)自由化思潮泛滥,主流价值观失守
苏共倡导全面“公开性”还有一个明显的意图,就是要打击所谓的顽固保守派,让激进派上位,获得改革的主动权。但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在驱逐保守思想的同时,代表西方政治理念和价值取向等自由化思潮,却乘着“公开性”的风向,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长驱直入,与潜藏于国内的各种“不同政见”相互呼应。一时间,经济学界盖达尔的“经济私有化论”,历史学界阿法纳西耶夫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哲学界弗罗洛夫的“抽象人性论”,以及文艺界拉斯普京、拉克申的“揭露派”等思潮,在苏联政治思想舞台上大行其道,几乎波及到社会各个领域。按照戈尔巴乔夫事后总结的,从“地道的西方派”到乡土与帝制派,从人道主义与国际主义派到狂热的民族主义派,一应俱全。自由化思潮的泛滥,造成大量抨击甚至否定马列主义的“时髦”观点受到追捧,甚至一些正统的马列主义者也公开发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
严济慈果然不负众望,在法国以优异的成绩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成为中国现代物理研究奠基者之一。法国承认中国的大学文凭,就是从严济慈开始的。
在西方自由化思潮蜂拥进苏联政治思想舞台的时候,苏共并没有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反而推波助澜,一味地迎合自由化思潮,继续沉浸在“公开性”神话里。诸如,安排激进派掌管苏共宣传部、占据大众传媒的主编位置,夺取舆论领导权;默许知识界组成西化派,宣传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任由非法报刊,非法组织抢占舆论市场,宣传西方生活方式的优越,用自由化观点评价苏联改革;取消了BBC、美国之音、西方自由之声诸电台对苏广播的限制等①1990 年8 月1 日生效的《苏联新闻出版法》规定,舆论不受检查;苏联公民有权通过外国来源获得信息,其中包括通过直接的电视广播、电台广播和报刊。实际上,1988 年12 月苏联已经停止了对过去视为反动电台的多家西方电台的干扰。参见余敏.前苏联俄罗斯出版管理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59-74.。苏共无底线、无原则的结果是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和价值观的多元化。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党和政府公开国家和社会发生的真实情况,让广大民众了解事实真相,积极参与问题的讨论,理性发表自己的见解,是走向人民民主的必经之路。但苏共全面“公开性”下的民主化,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民主化,是没有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曾说过:“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0](193)在“冷战”环境下,苏共领导层却脱离国内国际现实的环境,大搞全面“公开性”,失去平衡,走向极端民主化,严重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结果搞乱的是苏联人的思想观念和改革的正常秩序。
三、从马克思主义转向“人道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末路
苏共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僵化体系,失去了生命力,已经没有必要花费精力坚守。他们试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熔断,开启一条所谓的人道主义新路。具体地说,就是用抽象人道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嫁接社会主义,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是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丢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必然会丧失,社会主义必然走向末路。
(一)以抽象“人道主义”原则处理国际关系,落入了西方“普世化”的陷阱
自20 世纪60 年代以后,人道主义思潮在苏联不断地集聚和扩张。苏共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的选择范围内使社会深刻民主化和人道化,使其成为自由的社会,为人民创造应有的生活条件。”[11]可见,人道主义思潮在改革年代已经呈现越演越烈的趋势。这种“人道主义”思维,首先危害到苏联与东欧各国关系的处理上,推动了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逐渐走向自由化道路,转而向资本主义的蜕变,最终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前所未有的分裂。
在国际交往中,“人道主义”是戈尔巴乔夫急于舒缓“冷战”造成的压力,为苏联扩展国际空间,提出的一种超越民族和国家意识的价值观,目的是取得西方国家对自己改革政策的认可和支持。为了取悦于西方国家,在苏共新党章中,取消了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看作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的基本观点,提出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新思维。按照这一思路,苏共把解决国际问题的出路定位于国际关系的“人道主义化”。这种用“抽象的人”来代替“现实的人”的观念,超越阶级利益看待国际关系,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也严重脱离了国际社会复杂的实际,落入了西方“普世化”的陷阱。戈尔巴乔夫后来在回顾苏共的外交政策时也多次承认,尽管苏联作出了巨大的让步,但西方并没有兑现承诺。足以见得,苏共用“人道主义”原则处理国际关系的失败。
(二)用抽象“人道主义”作为改革的旗帜,颠覆了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人道主义是以阶级斗争为前提,体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关怀和尊严的思想学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从人民群众现实的主体实践活动出发,理应重视人的权利和自由、尊重人的价值,但不应无视不同社会制度的差别,也要认清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对立的现实。苏共宣扬的抽象人道主义抹杀了阶级属性、民族属性等差别,混淆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界限。
同时,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下,以公开和隐蔽的方式鼓吹抽象人道主义。在苏共默许下,1986 年12 月苏联科学院成立“人的问题综合研究委员会”,多角度对“人”展开研究,为抽象人道主义摇旗呐喊;戈尔巴乔夫的亲信智囊弗洛罗夫出版的《论人和人道主义》(1989 年),公开为抽象人道主义做论证。同时,以人道主义为主线的新编高校教科书《哲学导论》①《哲学导论》是由弗罗洛夫等在20 世纪80 年代集体编写的哲学教科书,分为上下卷共十八章。该书上卷是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下卷是理论的方法论:问题、概念、原理。参见弗罗洛夫.哲学导论(上下卷) [M].贾泽林,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5.出版,取代了长期使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为避免引起民众的过激反应,“人道主义”的推行一直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表面话语下悄然进行的。就戈尔巴乔夫本人来看,他口头上一直打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幌子,但在实际行动上贯彻的是抽象人道主义。博尔金就这样评价过戈尔巴乔夫:“虽然他还在一本正经地大谈建设社会主义,大谈共产主义远景,但这些都是空话,如同一块遮羞布一样,在掩饰着见不得人的思想。”[13]可见,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主义”的目的,就是要替代马克思主义。
(三)用抽象“人道主义”改良社会主义,否定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在抽象人道主义指导下,苏联走上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强调的是“全人类的内容”。戈尔巴乔夫曾说过:“如果有人要问,对于我来说对社会主义的现代解释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那么这个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它的全人类的内容。”[14](1243)这里的“现代解释”具体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不是把某一个阶级的利益,而要把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利益放在首位。另一方面,要认可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个别国家的利益。在这种“社会主义”的解释中,抹杀了无产阶级解放和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国家学说,也混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制度上的本质差异。
这种“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表面上看还属于社会主义范畴,实质上与任何其他的社会主义思想都有差异,完全是戈氏杜撰出来的概念,是一种改良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具有本质的差异。从戈尔巴乔夫个人的心历路程看,他经历了从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到怀疑,最后逐渐对共产主义运动彻底失去信心的过程。正如他自己所说:“从兴高采烈地坚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定战无不胜到开始明白它已经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取代它的应该是某种新的由倡导社会正义者联合起来、相互协作的方式。”[14](1237)而这种“新的”方式,就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形成,已经宣告了科学社会主义在苏联的终结,标志着苏共已经改变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预示着苏联解体的必然。
苏共从完善社会主义逐渐转向颠覆社会主义,最后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当肢解苏联的“别洛韦日密林”事件①1991 年12 月18 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和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三人,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郊外的别洛韦日国家森林公园,共同签署关于“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定,又称“别洛韦日协议”,协定宣布放弃苏联的存在。参见弗拉季斯拉夫·施韦德.别洛韦日协议与戈尔巴乔夫 [J].马维先,译.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3):41-46.爆发,那些搞分裂的人开怀举杯;当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下,西方国家弹冠相庆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哀叹这是俄罗斯和苏维埃联盟历史上“黑暗的一页”,但为时已晚。正是戈尔巴乔夫张扬抽象人道主义,并衍生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造成苏共丧失执政地位,失掉国家政权的恶果。
四、揭示苏联意识形态嬗变的当代意义
苏共在意识形态建设上的错误做法,导致从高级干部到普通群众思想上的混乱、信仰上的危机,成为助推苏联解体的理论动因,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在新时代,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我们理应从苏共意识形态建设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对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有助于深刻认识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作为曾经的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与我国在意识形态建设上具有诸多的相似性,苏共很多成功的建设经验成为我国学习的榜样。但在改革中,苏共把改革和意识形态建设对立起来,不是与时俱进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而在改革中放弃了意识形态建设,后来又幻想用抽象“人道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其结果是苏共执政地位的丧失、人民陷入思想混乱和信仰迷惘。在我国经济、科技等“硬实力”不断增强的形势下,西方对我国的颠覆活动更加隐秘,更多地表现为文化上和制度模式上的意识形态渗透,国内由各种利益矛盾引发的思想冲突和“反意识形态”观念也有不断翻新的趋势。政治思想舞台上出现的一些我国“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论调,高校课堂上某些教师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等,都确证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
面对日益开放的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正确把握好意识形态的方向,守牢宣传思想舆论阵地,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话语权。西方国家利用其话语规则制定的主导权,以抽象的民主人权、绝对的平等自由等为幌子,向我国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其目的就是要占领我们的意识形态阵地,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民族国家的视域中,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普世价值”。我们要认真甄别,丝毫不能懈怠,以免落入“非意识形态化”的陷进。只要我们正确处理好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坚守主流价值观话语,讲好中国人自己的故事,就能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话语权。
(二)有助于坚定主流意识形态自信,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是独具特色的中国化理论。在西方的话语迷惑或诋毁面前,我们要有充分的意识形态自信,不要害怕也不要盲目崇拜来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东西,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邓小平说过,“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10](373)在苏联改革中,戈尔巴乔夫盲目打碎了一个僵化的传统社会主义体系,但他缺乏足够的意识形态自信,在理论建设上模棱两可,态度暧昧,听信西方政治家的蛊惑和别有用心者的教唆,逐渐丢掉科学社会主义立场,走上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歧途,其结果并没有给苏联民众带来民主和人道,反而导致亡党亡国,这样的教训值得警醒。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关乎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上,要理直气壮,不容丝毫的含糊和退缩。马克思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15]在新时代,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我们的行动指南。要坚决批判那些以“全民”的名义,高喊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全民党”的声音,实质上是企图否定党的先进性和无产阶级性质。认清“‘全民党’是反科学的虚假概念”[16]。同时,坚决抵制以否定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反对所谓“国家迷信”的叫嚣;以否定人民民主专政,推行所谓“宪政改革”的鼓噪。对这些容易扰乱我们视线的错误观点,都需要我们保持冷静的头脑,沉着应对。
(三)有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处理好与各种政治社会思潮的关系
在信息化时代,信息流错综复杂,线上线下的各种思想和理论相互碰撞,交锋交融,出现了多元文化共同服务于社会的现象。但一些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诸如崇尚西方民主和极端私有化的“西方自由主义”、对中国革命历史、建设事实和成就进行歪曲的“历史虚无主义”、主张取消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民主社会主义”等波涛汹涌,似有毁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后快之势。这就需要我们做好对各种政治社会思潮的引领工作,谋求正确应对的策略和方法,以免重蹈苏联改革年代出现的各种政治社会思潮泛滥的覆辙。
各种社会思潮的存在具有一定必然性,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干扰亦具有现实性。重点是我们如何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彻底揭示这些思潮的基本性质,暴露其真实面目,不断提高维护好意识形态安全的本领。这就需要我们正确“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17]。在政治原则层面的问题,我们要坚决抵制,坚决斗争;在思想认识层面的问题,可以通过批评教育、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来解决;在学术观点层面的问题,可以通过争鸣、对话,要勇于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合理成分进行吸纳。只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引领各种社会思潮,才能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有效性和引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