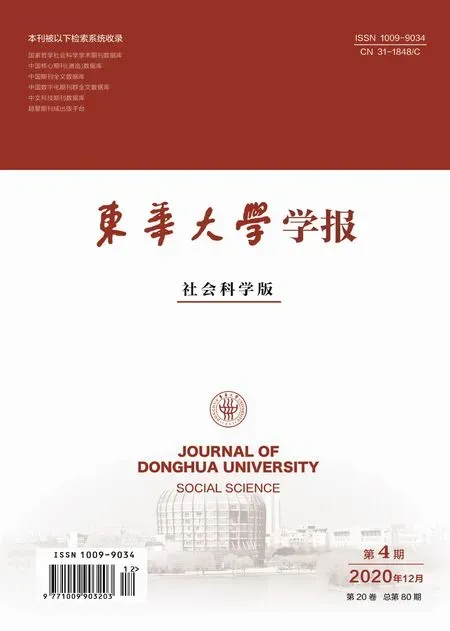反思信念的自主性
——对信念非自主论证的解释主义回应
|刘小涛 罗 涵|上海大学 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系,上海 200444
当代信念伦理学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应当相信什么”。许多研究者认为,理性认知者的信念应该遵循某些认知规范。比如,应当相信真的东西;在无法确定真假的时候,则应当悬置判断。不过,如何准确地表达信念应遵循的规范?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被广泛接受的答案。直觉上,真、合理、融贯、可靠等因素似乎都可以增加信念的“认知价值”(epistemic value)。然而,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也仍然缺乏清晰的阐明。
许多研究者注意到,信念伦理学的讨论和伦理学的探究有平行的结构。正如人的行动受伦理义务规范一样,信念受认知义务规范。因而,建立一种义务论式的认知规范就成为有指望的理论追求。当代的证据主义(evidentialism)就希望推进这样一种义务论式的认知规范主张,其中,一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来自费尔德曼(R. Feldman),他认为,人们应当相信那些有充分证据支持的命题[1]。
由于应用了义务论的概念,证据主义的信念伦理学也相应地面临义务论者的麻烦。“信念非自主论证”(the voluntarism argument)就是其中一个著名难题[2,3],它援引行动伦理学中的“应当蕴含能够”原则,以此为前提,通过论证信念不受自主控制,得到我们不能使用义务论概念谈论信念的结论。这一结论对于证据主义的认知规范论题而言是毁灭性的。为了回应信念非自主论证,当代的证据主义者作出了巨大让步——他们放弃了信念伦理学的规范性和信念的自主性[4]。
本文主张,证据主义可以在避免作出让步的情况下回应信念非自主论证。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将论证,存在一类人们能够自主控制的信念(1)尼克尔(P. J. Nickel)也曾论证,存在部分可自主控制的信念。按照他的主张,人们对那些证据尚不充分的命题可以有所选择。参见NICKEL, P J. Voluntary belief on a reasonable basis[J].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2010, 81(2): 312-334。——反思信念,而且,借助解释主义的证据主义(explanationist evidentialism),能够为这类信念提供可接受的信念伦理学规范。
一、 证据主义的信念伦理学
研究者大多将克里福德(W. K. Clifford)视为证据主义及信念伦理学研究的先驱,他因为主张一条强硬的原则而广为人知——任何人,在任何时候,相信任何证据不充分的东西,都是错误的[5]。该原则常被称作“克里福德原则”。这条原则的强硬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它以一条绝对命令的形式存在,无关背景,但凡是人类的一员,都要求有充分的证据才能相信某件事情;其二,原则中的“错误”一词有着较广的涵义,在克里福德看来,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相信一件事情不仅是一个认知错误,还是一个道德错误。
当代的证据主义者弱化(甚或取消)了信念评价的道德维度,同时缩小了证据主义原则的应用范围。研究者们通常会在有关信念的认知问题、实践问题和道德问题之间作出区分。按照通行的见解:信念是否为真、是否合理、是否来源可靠等属于认知问题,信念是否能够给人带来利益或好处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信念是否违反某种道德原则是一个道德问题。以这个区分为基础,当代证据主义的探究通常局限于认知问题,即主要考虑信念是否存在认知上的缺陷。根据费尔德曼的论述,证据主义的认知义务原则(简称EO原则)可表达如下:
EO原则:如果主体S在任意时间t对命题p持有任何信念态度,且S所拥有的证据支持p,那么S在t时认知上应当对p持有与证据相称的信念态度。(2)费尔德曼原文称其为“O2原则”。详参FELDMAN R. The ethics of belief[J].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2000, 60(3): 679。
如前文所言,EO原则不谈论认知义务的道德蕴含,它仅断言主体“认知上”应当采取特定信念态度。此处的“认知上”一词意义十分严格,简言之,它只能与信念相关,并且不能掺杂任何实践的或道德的因素。此外,EO原则加入了“S持有某信念态度”这一限制。这意味着,该原则不对主体未作考虑的信念作出评判,它只评估主体已有的某个信念态度是否恰当;而且,它还是一个共时性(synchronic)原则,简单来说,除了t这一时刻上主体的认知状态以外,其他任何时间点的任何认知状况都与评判无关。
这种认知义务概念起作用的范围颇为狭窄。一些哲学家曾对此提出过质疑。比如,德娄斯(K. Derose)提出,收集更多证据和让信念确实地基于恰当证据看上去也是认知上应当完成的事情[6];克鲁斯(M. C. Cloos)则认为,以负责任的方式获取证据也是信念义务的一部分[7]。面对此类质疑,费尔德曼坚持认为,EO原则以外的要求,要么涉及实践因素,要么涉及历时性因素,它们不同于EO原则所表述的这种特别的认知义务。
执着于刻画认知义务的共时性和“纯粹认知”特性,费尔德曼显然是出于一些重要考虑,而EO原则也确实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把握住了某些重要的直觉。不过,在我们看来,想要回答认知上应当相信什么,仅仅依靠EO原则是不够的。完全可以设想,两个持有相同证据的人,可能在其他方面存在认知差异,比如认知能力上的差异、信念所依据的证据集恰当与否的差异、证据清晰度的差异等。对此,我们的直觉是,证据之外的认知差异会影响认知义务;但EO原则没有空间为这些差异提供更进一步的解释(费尔德曼也未曾打算进行解释)。
证据之外的认知差异会对认知义务产生何种影响?这个议题仍未得到足够的研究。限于篇幅,本文不打算就此作进一步探讨。(3)通过一组对照思想实验,本文的作者之一曾希望表明,认知状况和伦理义务之间存在普遍性的一般联系。参见刘小涛. 为理智主义申言[J]. 哲学分析, 2019(6): 166-176。我们假定,它确实可以作为一个理由,用以表明为何不直接捍卫EO原则。接下来的讨论,我们希望以一个更朴素的观察作为讨论起点:认知上应当依据证据相信;不过,这一证据主义的基本精神并不要求严格的共时性,也未必如费尔德曼所希望的那么“纯粹认知”。
二、 信念非自主论证
在当代信念伦理学的讨论当中,信念非自主论证可谓最著名的论证之一。该论证受到广泛关注的原因在于,它对绝大多数信念伦理学理论构成破坏性的反驳。阿尔斯通(W. Alston)明确阐述的这一论证,可以简要重述如下:
(1) 可以对信念作义务论式判断,仅当,主体能够自主控制(voluntary control)信念;
(2) 信念不受主体的自主控制;
(3) 无法对信念作义务论式判断。[2]
该论证的可畏之处不仅在于其结论的破坏性,还在于其前提具有相当的吸引力。首先,前提(1)基于对一个行动伦理学原则——“应当蕴含能够”(ought implies can)——的类比。该原则可以有几种不同的解读,主要的分歧大概在于如何理解“能够”这个模糊的字眼。比如,该原则可以表达为“可以谈论某个行动的义务,仅当,主体可以自主控制该行动”,或者“某人对某行动具有义务,仅当,主体有能力执行该行动”。如果暂时排除这些细节上的争议,可以说,这条原则在总体上得到绝大多数伦理学研究者的支持。一个显著的理由在于,它表达了人们的一种道德直觉:如果张三不会游泳,说“张三应当跳下水救人”就是个十分不恰当的义务论要求;如果李四被挂在一个失控的机械臂上甩来甩去,中途撞飞了年迈的路人,此时若有人批评“李四不应当伤害那个老人”,就会显得十分悖理。
其实,上面的介绍已经暗示了一种捍卫信念伦理学的方案,那就是,在信念的领域当中重新划定“应当”和“能够”的概念边界,以此论证“应当蕴含能够”这一行动伦理学原则不适用于信念。费尔德曼采用的正是这个方案;他希望收窄“认知应当”的涵义,以此应对信念非自主论证。他声称,自己是在一种纯评价和纯认知的意义上谈论“认知义务”和“认知应当”,虽然这些语词在逻辑结构上与义务论判断相类似,但它们实质上并不具有类似的规范性。[4]
这个回应令人不满的第一个地方在于,它要获得成功所需付出的代价过大。要使这个回应有效,就必须接受前提(2),也就是要承认我们无法对信念有任何自主控制,事实上,费尔德曼甚至为前提(2)提供了一些辩护。但是,接受人类完全无法控制信念这一判断,就意味着承认,人类的一切信念和建基于其上的认知成就,都只是外部世界机械地在我们头脑中产生的东西;这对具有规范特征的知识论研究而言绝不是个好消息。
第二个令人难以接受的地方在于,该回应牺牲了信念伦理学的规范作用。事实上,当我们问“应当相信什么”的时候,显然不只是在传统知识论的意义上询问“知识的合理性条件是什么”,而是想知道,在特定的或某类普遍的场景当中,依据何种标准抉择相信与否;我们需要的是一套能够指导信念的规范性理论。为了保全一个适用范围极小的原则而舍弃信念伦理学真正的目标,这看起来不像是一种胜利,反倒更像是承认了整个信念伦理学的失败。
接下来的论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挽回当代证据主义作出的牺牲。我们将对信念非自主论证的第二个前提发起挑战,但并不打算论证人类有能力掌控自己所有的信念;这个观点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要为它提供辩护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想要捍卫一个相对温和,但也足够有力的观点——存在一些认知上重要的信念,人们对它拥有自主控制。如果这个论证足够成功,那么它将意味着,人们有权对那些认知上重要的信念作义务论式的判断,并且,通过一种恰当的信念伦理学,人们可以在这类信念上获得规范性指导。
三、 反思信念及其自主性
阿尔斯通和费尔德曼给出了许多有趣案例来说明信念不受自主控制。不妨回顾一下阿尔斯通提供的一个案例。(4)本文中所转述的案例均为适应中文表达习惯而略作修改。如果屋子里的灯开着,一个待在屋子里的人就会相信灯开着;他确实有能力即刻改变这个信念,只要马上把灯关掉就行了。但是,这明显不是对信念的自主控制,而是对环境的控制,或者说,主体通过自主地改变感觉经验的来源,迫使相应的信念产生改变。归根结底,信念仍然直接由感觉所决定。
费尔德曼给出了一类更加生动的例子。在一个大晴天,某人承诺,如果我相信外面正在下雪,他就给我500万元奖励。很显然,无论利益驱动有多大,也无论我想要去相信的意愿有多强烈,都无法促使我相信它。我至多口头上对金主说我相信,但令人难过的是,我从未如此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不可能相信一个错得如此明显的命题。[4]
上面的两个案例确实为信念的非自主性提供了很强的理由,只要在日常生活中稍加留意,任何人都能获得与案例主人公同样的感受。但是,信念非自主论的支持者所使用的信念案例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或者都是简单的知觉信念,或者是认知者有充足证据的信念。就这些信念而言,在通常情况下,认知者几乎都没有怀疑的空间,或者说,没有进一步反思的空间。根据大脑形成信念的运作机制(faculties),我们不得不如此相信;我们确实无法违抗大自然所设计的基础程序。
然而,不是所有的信念都完全确定无疑。有反思能力的人,总可能在某些条件下,通过进一步思考自己的信念内容或支持信念的理由,从而改变自己的信念态度。这些条件,可能是执拗的反对意见,可能是与经验的冲突,也可能是认知者持有的某个高阶信念规范。一种特别平常的情况,是人们通过不断地自我调适来让自己相信某个原本不相信的情况或某个理论;有个朋友,曾半开玩笑地讲,他可以让自己相信任何一个哲学理论,只要不断地深入研读单方面的文献,并且忽视所有的反对意见。
我们把这类认知者有反思空间的信念称为反思信念。它们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认知者可以对信念的原因或理由进行思考,并且有可能基于这些思考改变认知态度。这里的“反思信念”概念来自索萨的一个教导,广为人知。在区分信念的“适切”(apt)和“辩护”(justified)的基础上,索萨进一步提出了“动物知识”(animal knowledge)和“反思知识”(reflective knowledge)的区分。简言之,信念的适切在于它是理智德性的结果,信念的辩护则取决于信念之间的融贯。“对动物知识而言,只需要信念是适切的,并且是源自一种理智德性或机能。与之对照,反思知识则总是要求信念不仅是适切的,而且还有一种辩护,因为它必须与那些处在相信者的认知视角中的其他信念相融贯。”[8]以索萨的区分为基础,不妨说,就范围而言,我们讲的反思信念大体就指这一类信念,相信者可以从自己的认知视角来反思性地思考它的认知基础,特别是,它是否与自己的其他信念相融贯。
索萨本人并未将这对区分与信念自主性的讨论联系起来,他更多地是想要表明,仅依靠客观可靠的外部程序,并不足以解释人类的全部知识;人类有许多特有的知识,它们必定要经过某些内部的处理才有可能形成,而正是这些认知上特别重要的知识,为信念辩护的讨论提供了意义。
尽管如此,这对区分却可以为当前讨论提供有益的指导。如果沿着索萨提供的思路,将动物知识视作适切信念(apt belief),也就是那些仅凭认知能力或德性产生的信念[9],就会发现,信念非自主论者所提供的信念案例,大多可以归为单纯的适切信念。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那些对人类而言真正重要的知识,尤其是哲学或科学知识,显然不仅仅是适切信念;相反,它们常常是不断权衡反思的结果。对哲学家和科学家而言,通过不断权衡证据或论证的力量,以及证据和竞争假说或理论之间关系而形成特定信念的过程,根据我们的判断,正是反思信念具有自主性的最好体现。
在这个意义上,从反思信念和反思知识的角度考虑人们的科学知识或许更为合适。以此为基础,如果能够说明反思信念的形成具有自主性,就可以保住人们对相当一部分信念作义务论式判断的权利。而这看上去也并不难实现,理由在于,按照通常的理解,反思自身便蕴含有一定的自主性。并且,这种自主性相对独立于主体的认知能力:头脑正常但认知懒惰的人总是拒绝深思;充满好奇心但认知能力欠佳的人,通过思考和练习也能合理地产生复杂的信念。只要不是极端的机械决定论的拥护者,大概都会接受,人们能够自主地选择是否对头脑中的认知素材进行反思。不仅如此,人们还能够自主地采用不同的方式,或选择不同的认知素材进行反思,若非如此,就很难想象艺术创作和科学创新何以可能。
如果反思信念确实具有这种自主性,那么它就能够为认知义务提供支持。因为,通常来说,一个人可以主动地拒绝反思,或者通过不合理的反思得出结论,但这显然犯了认知上的错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对信念作出义务论式的判断:一个人在认知上不应该拒绝反思,并且,如果进行反思,他就应该合理地反思。
四、 解释性作为反思信念的标志
反思信念显然不同于动物信念或简单的知觉信念,这一点或许比较容易让人接受;但是,二者之间的差异具体体现于何处?显然,这种差异并非源于信念的命题内容。从原则上讲,最简单的经验陈述也可以成为反思信念的内容;对笛卡尔而言,“面前有一根燃烧的蜡烛”就是一个经过了复杂反思而确定下来的信念。
或许,索萨后来提出的观点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依索萨之见,反思知识(K+)与动物知识(K)之间的关系满足等价式:K+p⟺KKp。因为索萨将动物知识等同于适切信念,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地将这一关系理解为反思知识等同于二阶适切信念。[9]
但是,如果接受这种观点,前面所获得的有关反思信念自主性的结论将有可能遭到破坏。因为,我们可以认为,一阶和二阶的适切信念之间仅有程度上的差异,但本质上是相近的。这就意味着,如果适切信念只是认知机能非自主地产生的东西,那么二阶(或更高阶)的适切信念也同样如此,它们只是在加工精细度上有所不同而已。或许,通过断定一阶和二阶适切信念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差异,我们可以为信念的自主性保留一些空间;但这种想法将会产生不必要的形而上学负担——在理论上存在无穷多级且本质上各不相同的信念类型。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方案可以容纳信念的自主性,那就是声称作为二阶适切信念的反思信念产生自不同的理智德性。实际上,这种思路与索萨的观点有些相似,他认为,相比动物信念,反思信念不只是对外部刺激作出直接反应,还含有对信念或知识之间的融贯性的理解[8]。延续这一思路,我们可以断定,与动物信念相比,反思信念包含更多的理智德性的贡献,后者与主体信念的融贯性有关。但是,若要沿着这一思路回应信念非自主论,至少还需要说明,产生反思信念的这种理智德性具体以何种方式运作,以及为何这种理智德性蕴含信念的自主性。
对此,我们的建议是,从解释的角度去理解这种特殊的理智德性。请注意,上文所提及的诸多反思信念案例似乎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共同特征:它们都为各种现象之所以如此给出一个原因或者统一的说明;也就是说,反思信念与外部世界的现象(或人们对这些现象的认知状态)之间存在解释关联(5)本文在一种相对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解释概念。科学哲学关于“解释”的基本涵义的长期争论与两种基本的解释观念——因果论和统一论之间的差异有关,斯特雷文斯的论文提供了一个简明的导论。详参STREVENS M. The causal and unification approaches to explanation unified—causally[J]. Nos, 38(1): 154-176。——人们用光学原理解释水中弯折的筷子,用数学模型解释世界上各种现象间的相关关系,用犯罪事实解释犯罪证据的融贯性;笛卡尔用上帝的全善全能解释知觉信念的真和外部世界的存在。与之相对,动物信念通常只是单纯地描述或表征一些外部事实或现象。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尝试断定,拥有解释关联是反思信念的一个标志。为便于讨论,不妨作更形式化的表述:
解释—反思原则(简称ER原则):如果主体S的信念D与主体的其他信念之间存在解释关联,且S意识到该解释关联,那么D是S的一个反思信念。
ER原则的特别之处可通过一个案例来说明:张三是一个强迫症患者,他出门时总觉得自己的门没有关上,因而总是反复检查门锁后才相信“门关好了”。对于该情景,如果遵循索萨的原则(K+p⟺KKp),或许张三的信念会被判定为反思信念,因为它经过了多层认知处理。但事实上,张三的反复犹豫和检查确定看起来并未改变这一信念的地位,它仍然只是对知觉的简单描述,这与笛卡尔关于蜡烛的信念明显不同。从信念伦理学的角度讲,张三的这种“反思”没有带来任何附加的认知价值,而只是在无谓地消耗认知资源。从这两个方面来说,ER原则作出的判断都显得更加恰当。依据ER原则,张三的信念并未对解释世界作出任何贡献,所以它不能算作反思信念。这一判断能够更好地说明上述案例,同时也与信念伦理学更为亲近。
更加重要的是,ER原则所刻画的反思信念观念能够充分地体现信念的自主性,因为解释活动自身蕴含相当程度的自主性。举例来说,假定“空屋里亮着灯”是一个未经反思的简单描述,“灯亮着是因为李四开了灯”则是一个解释。任何主体都可以自主地质疑后者,只要他愿意,他总可以相信一些由其他理由或证据支撑的竞争解释。比如,“其实灯是张三开的,因为张三刚才也去过那间屋子”,或者“灯是自己亮的,因为那间房线路有问题”。
一些科学实践的情景或许更加能够体现这一点。比如,考虑一种常见的学术研究情景:两个认知能力相近的研究者,都掌握相同的实验数据,但仍然可以基于这些数据提供不同的解释。(6)这也是知识论讨论中十分著名的“同侪分歧”(peer disagreement)案例。比如,可参见Rogier De Langhe. Peer disagreement under multiple epistemic systems[J]. Synthese, 2012, 190(13): 2547-2556。该情景可以说明,具有解释特征的反思信念不是某种机械的认知机制的产物:即便输入相同的认知素材作为证据,不同的主体仍可以产生不同的信念。
对于这个案例,坚定的信念非自主论者或许会如此回应:信念不是感觉材料的机械产物,而是头脑中总体认知材料的结果,并且,现实中不可能存在两个认知状态完全一样的主体。因此,即便给定一簇相同的认知材料,两个主体也可能因为其他认知材料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信念,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断定信念的非自主性。
确实,信念似乎总会受到认知者总体认知材料的影响,并且,正常的认知者在大多数时候都会对恰当的认知材料作出恰当的反应(7)这种想法或许可以理解为信念倾向于对真理展现特征表现。参见刘小涛. 信念何以瞄准真理?[J]. 现代哲学, 2019(6): 104-112。;但这并不意味着信念完全与人们的意愿无关。为了说明这一点,请考虑下述案例:一位母亲掌握了儿子的犯罪证据,但仍然不愿相信她的儿子是罪犯。经过多次自我说服,她最终成功地让自己相信罪犯另有其人。可以认为,对这位可怜的母亲而言,“儿子是罪犯”这一命题得到了充分的证据支持,然而,“信念机制”这次没能成功地强迫她产生相应的信念。事实是,她出于强烈的情感和意愿,对自己眼前的证据作出了另一种解释。
类似的情况还有许多,著名的克里福德案例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利欲熏心的船主成功说服自己相信船没有问题[5]。考虑到诸如此类的情况,似乎没有理由认为,人们对所有信念都不具备自主控制能力;正相反,人们都能够自主地选择是否解释现象,以及如何进行解释。
至此,对信念非自主论证的一个简单且有效的回应已经成型:存在一类反思信念,人们对其拥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控制。因此,信念非自主论证的前提(2)有误,我们可以对反思信念作出义务论式判断。如若上面的论证成立,那么就可以转向下一个任务:论证一种证据主义观点,使之能够为反思信念提供恰当的信念伦理学规范。
五、 解释主义方案
依据前文的论证,人们对反思信念拥有相当的自主性,而解释性或解释关联是反思信念的主要特征。针对这一类信念,证据主义内部有一种现成的思路非常适合用来为其提供规范,这种观点被称作“解释主义的证据主义”,也可简称为“解释主义”(explanationism)。费尔德曼和柯尼(E. Conee)共同开辟了这条进路,但是,费尔德曼却在信念伦理学问题上放弃了这种思路。
简单来说,证据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认知上应当依据证据相信”,而柯尼和费尔德曼为了说明证据与命题之间的支持关系,引入了解释主义原则——命题与证据之间存在契合关系,仅当,命题属于对证据的最佳解释的一部分[10]。将该原则与证据主义的基本原则相结合,就可以得到一条信念伦理学要求:“应当相信那些最好地解释自己所持证据的命题”,或者,可对其作如下半形式化的表达:
解释主义的认知义务原则(简称ExO原则):主体S应当持有反思信念D,仅当,D的命题内容p是对S所拥有的总体证据e的最佳解释的一部分。
之所以选择解释主义作为补充,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理由:我们希望为反思信念提供规范,而反思信念具有解释特征,那么,解释力无疑是一个方便的评判标准。当然,方便并不是接受这个原则的主要理由;更主要的考虑在于,许多认知上重要的信念都旨在解释世界,而许多命题之所以成为人类知识的一部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拥有,或曾经拥有过当时最好的解释力:相对论的解释范围比牛顿力学广阔得多,而牛顿力学的解释力远强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在这个意义上,为自己所能掌握的全部证据提供一个尽可能好的解释,无疑体现了一种认知上的高尚;与之相较,那些无视新证据,固守成见的人则表现出了某种认知上的懒惰或不负责。好的解释总是比坏的解释具有更多认知价值,因此,我们应该追求好的解释。看起来,这个判断可以为解释主义的信念伦理学提供恰当的价值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证据主义的传统,某个命题的义务状态取决于主体所拥有的总体证据。可是,总体证据必定是一个十分庞大的集合,要求主体在形成任何一个命题之前,都通盘检查自己拥有的全部证据,这显然是个过分强硬的要求。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建议将ExO理解为一个理想原则,就好比人们常说“应当相信所有真理”或者“应当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一样,这类理想原则具有两个特征:其一,理想原则所提出的要求通常十分苛刻,现实世界中的人几乎不可能完全满足这些原则;其二,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这类原则通常蕴含程度判断,通俗地讲,它们并不是给出好与坏之间的明确分界线,而是给出坐标的原点和顶点——完全满足原则就使相应的价值最大化,反之,完全违背原则意味着获得最小价值,在此之间,越接近顶点意味着越高的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ExO原则断定,最佳的解释意味着一个主体的认知最大合理性。同时,如果接受最佳解释推理[11],则最佳解释也使信念为真的可能性最大化。在这两重意义上,都可以认为,ExO原则提出了一个可以作为理想标杆,并且值得现实中的认知者遵循的信念伦理学要求。
原则上,也可以效法EO,为ExO原则添加共时性限制。但是,在我们看来,解除共时性限制对一个规范性原则是有益的:对信念伦理学而言,重要的不是在理想变量控制的情况下,判定某一时刻某人的某个信念是否正确,而是为人们实际求知的过程提供方向。虽然我们并不反对任何共时性的讨论(在一些精细的情景当中,为原则添加时间限制是必要的),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拥有一个共时性原则。此外,ExO原则并不会像费尔德曼一样追求某种“纯粹认知”,或者说,将讨论严格限制于“以内部认知流程追求认知价值”。收集证据当然是一件认知的事情,尽管它属于行动,也可能涉及某些实践目的或限制,但并不妨碍收集证据能够提高信念的认知价值。虽然,放开这些限制可能会带来很多额外的问题,尤其是在信念伦理和行动伦理交叉的地方很可能产生各种难题,在这些问题面前,ExO原则所表达的观点或许会显得特别稚嫩,但是,这些问题正是一个规范理论应该讨论和想要回答的问题,传统知识论学者不应为了避免难题而限制对这些问题的讨论。
或许,ExO原则作为一个信念伦理学立场仍存许多讨论余地;但无论如何,上述讨论足以说明,相对于既有的证据主义信念伦理学而言,它可以更好地应对信念非自主论证的威胁,与此同时,它能够满足信念伦理学的基本诉求——为信念提供规范性指导。虽然,必须承认,ExO原则在一个方面不及EO原则——它缩小了证据主义信念伦理学的适用范围,从适用于全部信念,缩小到仅适用于反思信念。但是,一方面,这个牺牲在某种意义上是必要的,诚如阿尔斯通等人所论证的,对于那些直接由感官刺激产生的信念,我们确实无法强加自主性;另一方面,从理论好处的角度来看,以缩小理论的适用范围为代价,不仅可以换回信念伦理学的规范性特征,还能够换取对人类知识成就的更好解释,这显然是有利的交换。
六、 结语
不难发现,支持信念非自主论证的案例,通常只会谈论那些感觉直接刺激产生的信念(它们往往只是索萨意义上的动物知识),这正是因为,与其相对的反思信念很难被用以支撑信念的非自主性论证,而恰恰是这一类信念在人类的知识进步中占据了首要地位。基于这一判断,我们尝试在解释主义的立场上,提供一个区别于当前主流证据主义信念伦理学的主张,以此来为反思信念提供有实际指导价值的规范。论证表明,这种解释主义的认知义务原则在多种意义上比现有的证据主义观点更成功:它能在保持证据主义精神的基础之上,避免自主性论证的破坏性结论,并更好地契合人类关于信念和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的一般性直觉;同时,它比起当前主流的证据主义信念伦理学观点来说更接近一个真正的伦理学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