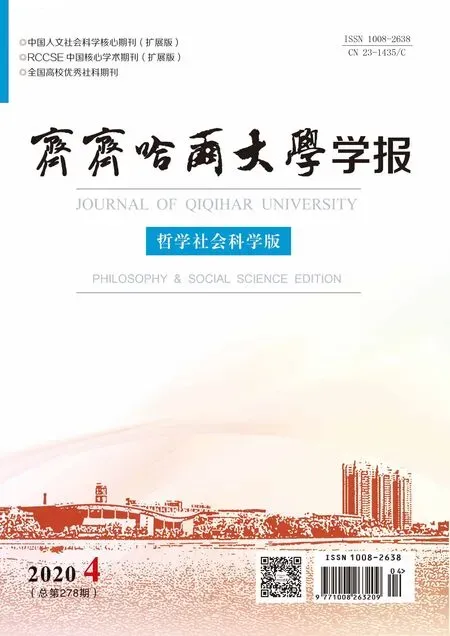愤书与神思:中国古代文艺创作论的两元
沈 旭,李 平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愤书”是一类艺术创作方式的统称,其特征是以愤懑郁结为创作动力。胡经之先生在《古典美学丛编》和《古典文艺学丛编》中都使用了这一范畴,并解释道:“所谓‘不平则鸣’,即主体和客体的‘不平’关系使主体内心产生‘愤懑’,引起艺术创造的愿望。‘愤书’说认为,‘不平’是艺术创造的源泉之一,是艺术创造的一种动力。”屈原所言“发愤以抒情”,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刘勰的“蚌病成珠”说、钟嵘的“托诗以怨”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以及李贽的“夺他人酒杯,浇自己垒块”等命题皆可归于此范畴之下。“神思”这一范畴的内涵以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为重要依托。“龙学”界对“神思”的认识历来存在分歧。如王元化、叶朗、李泽厚等支持艺术想象活动说;张文勋、牟世金、缪俊杰等声称艺术构思说。本文无意对其概念做详细辩证,而借鉴了张少康、周振甫、李平等学者的观点,认为神思是综合了情感、想象、思维等诸方面因素,以灵感为核心的艺术创作方式,尤其强调发源于天机的审美感兴,追求一种看似与人力无关的、超理性思维的心灵体悟。
“愤书”与“神思”作为中国古代艺术创作论的重要范畴,学界研究的成果颇为丰硕。但研究者多孤立地探讨二者各自的内涵特点和历史流变。其实,它们在大不相同的表象下还有着对应性的联系。朱良志说:“中国艺术有两种不同的群体观念:一是表现民间疾苦、反映社会情况的群体意识,如白居易等所强调的;一是通过归复本心所体现的群体意识。前者孕育着现实主义的力作,后者促使了中国精澄玲珑的抽象艺术之产生。”愤书与神思作为两种群体观念的集中体现,可谓中国艺术创作论的“双璧”。二者相反相成,共同成为中国艺术创作论的基石。
一
神思的构思前提在于心灵的虚静。《文心雕龙·神思》篇直言:“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所谓虚静,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虚静指的是宁静空灵的心理状态;其二,虚静涵盖了心灵的修养方式。个体通过“心斋”、“坐忘”的自我净化,使内心如寒潭古井般波澜不惊,进而摆脱现实因素的种种束缚,最大程度地享受心灵的自由。而愤书的构思前提则为心灵的愤懑,其内涵亦可分为两层。一层是因个人困顿穷愁的遭遇而产生的一己之愤;另一层是因天下动荡、社会黑暗而产生的家国之愤。个体因心灵与现实的对立,产生难以解开的郁结,并陷入痛苦、挣扎之中。
《毛诗序》有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之”、“发言”均表明心志与作品之间仍有着明晰的界限。也就是说,即使是已经进入审美活动的人,要实现向创作主体的转变,仍需要另一种动力的牵引。对于愤书而言,人与社会、人与命运的矛盾冲突导致个体的心理性失衡,并形成“情结”张力。而张力需要导泄、释放,这样才能使心理回归平衡的状态。“在实际生命里不能满足欲望的人,死了心作退一步想,创造出文艺来。”为使郁结的情感得以净化、生命的需求获得替代性满足,个体的内心便燃起创作的冲动。诚然,排遣烦恼的方式还有很多,然而,中国自古就有“长歌当哭”的传统。钟嵘说:“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这正概括了艺术创作与情绪宣泄之间的关系。此外,中国文士把“立功、立德、立言”看作超越自我有限生命的精神目标,也使中国人自觉地将艺术创作视为实现自我生命要求的出路。至于神思,虚静的心灵状态既然要摒弃与外界的感应,在神光内莹中进入水镜渊伫的杳冥寂寞之境,那么,“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这时,创作冲动应是源自于“物感”的引发。杨万里说:“我初无意于作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乎我,我之意亦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先焉,感随焉,而诗出焉。我何与哉?天也。斯之谓兴。”神思者用心若镜,在“玄览”式的审美静观中因外界触动而与之交感呼应。创作动力显然是人在“虚以待物”的审美心胸中造就了“有斯来应,每不能已”的情感勃发。
因此,二者在情感与形象的关系上也有所不同。愤书者关注于精神的重铸,是要将郁结于心中的愤懑抒发出来,将“大写”的人格精神熔铸后铺展于作品之上。“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惜诵》)创作者欲向天地明其志,要请日月鉴其心,其创作目的和核心情感从一开始即是十分明确的。作品中写山不是山,写水不是水,而皆是写“我”之血肉与情灵。这种精神意念的集中喷发,大有“万物皆备于我”之势,使形象成为寄托创作主体情感的载体。而在虚静的前提下,神思是触物起情、静极而动的。神思者有一颗“无己顺物”之心,其精神思维是“随物以宛转”,其创作过程是在“神与物游”的基础上营造意象,其作品形象是自由心灵和大化流衍交融的产物。此时,自然万物不仅仅是被观赏的审美客体,还具有唤醒个体魂灵深处之本质力量的主动性。于是,创作者登山则赞山,观海则颂海,一任才情与风云并驱。也就是说,神思者的创作意图和心灵体悟是在脑海中的意象诞生之后,才逐渐由朦胧变得清晰起来。从感发层次上看,愤书是“由心及物”的,神思是“由物及心”的;从感发性质上看,愤书具有理性的指引,神思则纯任感性的体悟。而上述两点恰恰是判断“比”、“兴”两种艺术思维的核心依据。“比、兴”属于上古流传的“六义”,《周礼·大师》曰:“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千百年来,人们对它们的理解不一。关于“赋、比、兴”的认识,约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从修辞手段的角度对其加以认识;另一派则是以心物关系的角度来进行阐释。后一派经由叶嘉莹得以明确建立。对于心物关系先后的感发层次,她说:“‘兴’的作用大多是‘物’的触引在先,而‘心’的情意之感发在后,而‘比’的作用,则大多是已有‘心’的情意在先,而借比为‘物’来表达则在后。”关于感发性质的判断,叶嘉莹说:“‘兴’的感发大多由于感性的直觉的触引,而不必有理性的思索安排,而‘比’的感发则大多含有理性的思索安排。前者的感发多是自然的,无意的,后者的感发则多是人为的,有意的。”而后,黄霖在心物交互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赋、比、兴”明确为针对整个创作过程而言的三种艺术思维,并声称“比”是“心在物先”、“索物以托情”的;“兴”是“物在心先”、“触物以起情”的。
愤书与“比”,神思与“兴”,它们是艺术创作论的两组重要范畴。虽然它们着眼于不同的阐释维度,但却有着相同的艺术思维。并且我们完全可以预测愤书与神思创作的作品将分别归属于“比”与“兴”的类别之中。因此,先贤在介绍“比”时,往往会涉及“愤”的内涵,如《文心雕龙·比兴》所言:“‘比’则畜愤以斥言”;古人在论述“神思”时,也总是与“兴”相联系。其例证除了前引杨万里所言之外,还如葛洪《西京杂记》说:“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如兴。”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对应联系,是因为中国古代智慧总是围绕着天人合一的精神,以内在的心灵为起点,以外在的天地为参照。另外,叶嘉莹在《中西文论视域中的“赋、比、兴”》一文中还指出:西方的文艺理论关于“形象”的八种阐释都可归于中国的“比”,而“兴”在西方文论中却没有相当的表达。由此,若将愤书与神思放入国际化视角中比较,则神思更能凸显中国艺术论的独特思维。
二
人进入审美状态并在脑海中诞生意象是作品诞生的先决条件,而作品成就的高低却与此前更早的因素息息相关——这便是个体平日里的修养。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首倡“文以气为主”。此后,中国艺术论明确地将“养气”视为艺术创作的前提和基础。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特设《养气》篇,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云:“此篇之作,所以补《神思》篇之未备,而求文思常利之术也。”这点明神思与养气之间的密切关系。而唐朝强调“不平则鸣”的韩愈也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答李翊书》)可见对于愤书而言,创作者也需要日有所养方可“气盛言宜”。
“养气”本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功夫,其与艺术创作论相契合后主要指向三个方面:生命能量之气、道德修养之气、才学见识之气。愤书与神思中的“养气”,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这三个方面。其中,“才学见识之气”是所有创作者必备的基础,也是人类艺术实践发展和审美经验丰富所带来的必然要求。除此之外,愤书则强调道德修养之气的培育;神思更侧重生命能量之气的涵养。这是因为对于愤书而言,道德修养为其提供了三个方面的保证。第一,道德修养所带来的正义感和社会关怀,使个体能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不合理的现象所在,并为之进行深刻思考。换言之,道德仁义的修养是人感受到“不平”的基础,是愤懑郁结心理的形成条件之一。面对社会的黑暗和人生的苦闷,小人与乡愿则难以有此“郁结”。创作主体具有是非分明、追求公正、勇于担当的品质是愤书潜在的必要条件。第二,道德修养的充实能为“愤”的情绪提供价值支撑。按照心理学的观点,“动机不过是生理的不平衡”,也由此引发心理上的不平衡。愤懑的情感源自于人所处的矛盾关系,而矛盾冲突的根源在于人之有欲。并非所有的欲望都值得赞同,而道德修养在调控个体欲望的同时,也保证了由此而来的愤懑情绪的合理性。第三,创作主体的人格修养有助于加强愤书的表达效果。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涵养“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而后进入愤书的创作状态时便可达到韩愈所言“气盛言宜”、“气醇而后肆”的境界。创作者的浩然之气越充实,其郁结于心中的苦闷越能够转化为创作时强烈的心理势能。这是愤书者创作的内在力量,有助于其写出震撼人心、带有普遍价值情感的深刻作品。也因此,韩愈提出养气的方式在于“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以仁义修身之为正途,这正说明养气要与德行相配。对于神思而言,生命能量的涵养有助于促进艺术想象的迸发,提升精神生命的境界,实现心灵体悟的获得。先述其一。日本文艺理论家浜田正秀说:“文学燃起了生命新的火焰……然而,这种燃烧也是需要引爆剂的。这就是旺盛的生命力。为了使想象力超脱现实而展翅高翔,也需要生命的高电压,以及为此而进行的激烈冲击。”主体在精神振奋、心情愉悦时,其大脑皮层会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这有助于使注意力全部转移到思维活动的对象上来,充分调动头脑中已储备的知识,提升思维的敏锐度并强化信息处理能力,从而创作出充满想象力的作品。其二,自然生命是精神生命的基础,精神生命是自然生命的提升。《淮南子·精神训》云:“夫血气能专于五藏而不外越,则胸腹充而嗜欲省矣……则精神盛而气不散矣。精神盛而气不散则理,理则均,均则通,通则神,神则以视无不见,以听无不闻,以为无不成也。”这段话详细论证了由血气既定到精神自明的过程。精神的听无不闻、视无不见、为无不成,是由生理的净化和升华得来的。其三,不论是以钱钟书先生的“体异性通”,或是以格式塔心理学的“异质同构”为依据,神思的审美感兴都是人在“虚以待物”、“物之感人”的基础上,与物象在无间的默契中以彼此自在性的存在契合对方而实现的。《庄子·达生》有言:“壹其性,养其气,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个体的生命能量越是旺盛,则越能感应到充盈于宇宙间的大化流衍、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气,实现物我之间的生命互通,以致“相值而相取,一俯一仰之间,几与为通,而勃然兴矣”。故刘勰强调创作者应注重生理精气的调养,在审美活动中以生命之光观照从而使文思常利。其在《文心雕龙·养气》中说:“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以神清气爽之姿创作,这正说明调畅生理对于艺术家创作的重要性。
王钟陵曾总结道:“刘勰的‘养气’说侧重在文与思的结合上,与养生论密切相关。古文家的‘养气’说则侧重在文词的结合上,与道德修养说相互交融。”在此,笔者想接过话头来补充:中国古代文论之所以有两种“养气”说,是因为中国古代智慧有“儒”、“道”两种哲学体系。而加入创作论的视野会发现,与两种养气说各自对应的愤书与神思,也有着儒道不同的理论背景。孟子曰:“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人的心志对于生命运动起统帅作用,同时也引导着艺术创作的方向。愤书与神思对“养气”的不同倾向是由创作者迥异的志向所导致的。愤书者尚实重用,关注于社会人事,强调创作不可“无病呻吟”。元人刘壎说:“然亦必有为而作,有关涉而作,若无病而呻吟,虽奔涛走石,冶叶倡条,动可人心,於道何补”(《隐居通议》)。愤书的作品蕴含着创作者丰富的价值诉求,创作预期也更多地看重社会影响。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种“立言”以传之后世的精神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处于悲苦之境的知识分子,并成为他们共同的心路历程和人生选择。神思者体玄重虚,着眼于心灵体悟,以虚静恬淡为基调。在审美观照上,其强调“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回归生命的本真状态而后把握对象的整体存在;在审美境界上追求“顿失天地,粉碎形骸”的“身与物化”之境,从而突破一己之躯的局限,与自然万物合为一体。艺术作品是生命高度和谐的产物,是一种生命力“充实不可以已”的整体、直接释放。创作者在艺术创造活动中体验无时无空、非生非死、妙合宇宙的生命畅达之感。由此可见,愤书者的心灵具有浓烈的入世情怀。艺术主体观社会人生之事,为哀者抒其志,替苍生鸣其悲,其欲对现世做到针砭时弊,从而“以尽君子之责,以致社会之用”。这种“愤”的情绪为社会现实而服务,是“补天”思想的另一种表现。并且,艺术主体那没有得到满足的自我需求实际上已经是内化了的儒家的社会伦理纲常和正统观念。神思的心灵则有着明显的出世倾向。艺术主体以“无己”、“无待”之心进入审美之境,将自我生命引入大化氤氲之中,同宇宙生命息息相通。此主体清静无为,超然孑立,挣脱概念、因果、欲望的束缚进而“澄怀味象”。这种强调“以天合人”的自我洗礼、“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与万物”的对象化思维、“游心物外”的逍遥自得的精神追求,无不是道家思想的传承。
值得注意的是,愤书与神思中的儒道精神并非是“进”、“退”二字可以简单概括的。愤书潜藏着儒家的进取精神,但当其创作的指向不是批判扭曲生命的外在力量而是转向内心苦闷的抒发时,骨子里就有一种明哲保身的逃避;神思有着道家的无为思想,但人在困境时依然涵养不惊不喜、无忧无惧的心灵便可谓生命的不屈。二者共同展现了中国人生存的智慧及中国艺术论中生生不息的精神。
三
中国文化擅长在事物的两极之间实现超越,并于更高的维度找到它们的统一点。就愤书与神思而言,虽然它们呈现出二元对立的表征,但无不合于古代艺术思想中“神道”的本质特征。《周易·观卦》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神道”既非儒家仁义之道,亦不是道家自然之道,而是包涵各家思想,或者说中国人心灵所共有的终极指向,是至高无上的本原。中国艺术创作论也自然是以“神道”为重要依托,表现出中国艺术对于形而上之“道”的向往。
中国艺术论认为:“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虽然愤书与神思之“道”不尽相同,但因此都有着“超越”的理念。这种理念具体体现在个体意识、观照对象和创作目标等三个方面。其一,愤书与神思皆发于“诚”之真实无妄之心,其作品都是艺术主体心灵与外界的交媾和合下的产物。《中庸》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人复归于“诚”,便是体悟本心,其所要传达的“真于性情”、“不得不发”的个体情感也净化、升华至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共感。此时,艺术主体不再是自然的存在,而是一种自为、自由的存在;不再是现实性的存在,而成为一种理想性的存在。创作者内缘己心,外参群意,最终将个体意识融于群体、天地、时空之中。其二,愤书与神思观照的对象皆非物象本身而是其背后所蕴含的本质属性。这种观照体现在面对物象和营造意象两个阶段。愤书者面对现实处境时,会引起痛苦地理性思辨从而深刻剖析人生苦难的本质和社会黑暗的根源;而神思者观照自然时,则通过感性思维整体直观地把握对象的本质从而获得“美”的感召。二者都将自身抽离出来在审美距离中对外物进行审美观照,从而将物象内在的意指与外在的形态相剥离。另外,《文心雕龙·比兴》说:“诗人比兴,拟容取心。”愤书与神思的艺术主体通过心灵感悟的方式赋予现实表象以深层意蕴。艺术形象是情志与“物容”的结合体,有着以具体显示概念的特性,进而实现刘勰所言“称名也小,取类也大”的深刻思想内涵。其三,愤书与神思的创作目标都是从“有限”向“无限”追寻。《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解释道:“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愤书多有儒家三不朽之“立言”的意味,欲使其自身有限的生命体验凝练成超越时空限制的永恒美感与内蕴,传之后世以留待人知。苏轼说:“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神思的艺术主体希冀自身与大化相融,进而“混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乎自然”。其在俯仰流连之际,契合天地的神妙变化,最终在精神王国中体验无限的自由。
《庄子·渔父》篇曰:“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中国艺术论先在地有“神道”的终极关怀,其强调创作应是性情的自然流露。在愤书与神思的创作心理机制中,都有着“充实而不可以已”的不得不发的意味。一是在现实矛盾的刺激下,一是在审美静观的体悟中,这两种创作皆非主体刻意为之。因此二者都更加注重内容的方面,共同赞赏着“质朴”的审美形式。“质”强调“真于性情”的思想内涵。《文心雕龙·情采》篇说:“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中国艺术论并非不注重文辞,如孔子曰:“质胜文则野”。但相较而言,内容绝对是占据第一性的。不论是从儒家道德规范与礼仪制度的关系出发,还是着眼于道家“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的角度,文论家肯定“质”便是要首先确保艺术作品的精神所在。中国艺术论历来反对虚有文辞之美的作品,也正是因为脱离了“质”,人的性灵便无处安放,“神道”的真精神也无以传达。作品只是死的文字,失去了超越现实的可能。“朴”则强调个体情志自然而然的流露。《毛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中国艺术论将艺术作品看作情志的外化显现,也因此力求还原内心情感的本然、完整面貌。钟嵘在《诗品序》中说:“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与“质”的第一性相对应,这种生命本真的自然表达因不掺杂人为造作的因素而有利于保证情感的纯粹性和表达的自然性,最终达到在不自觉中已与“道”合的境地。与之类似,中国艺术论在“神道”的高卓视野下更加注重情景交融之情、形神兼备之神、有无相生之无、虚实相映之虚、显隐交至之隐,并追求气韵生动、余味无穷的艺术境界。
这种通天尽人的人文追求背后是中国“天人合一”思维的凸显。神思的虚静心灵讲究“无己”、“无待”,显然与“天人合一”的观念相合。而即便愤书的愤懑状态是“有我”、“有待”的,其亦不存在“我”与“非我”的关系。张载在《正蒙·大心》中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古人以人为天地之心,又以心为体道之本,所有的哲学智慧都建立在“心化”的基础上。因此,古人眼中的世界实际上是心的扩大化,主客之间的区别也在此泯灭混融。这种民族深层意识中的至高理念必然对创作论有所影响,其结果便是创作者“既不是有意识模仿自然,也不是以纯粹无意识的方式反映‘道’……而是在力所能及的、主体与客体的区别已经消失的意识的‘化境’中,本能地显现出‘道’。”
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中的诸多范畴实际上是综合通观、相互联系着的,因此其必然构成一个互为指涉、彼此渗透的动态体系。有论者指出“范畴是理论的筋骨”,中国“美学体系仅需范畴的勾勒就足以完成。”此言或许不完全正确,但确实明示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构建中国特色学术体系研究的方法之一。而神思与愤书作为艺术创作论的两大范畴,其对应性联系也显示出中国文化的内在规律和中华民族的思维习惯。虽然由于道家的思想与艺术精神具有高度契合性,神思往往被单拈出来作为中国艺术创作论的代表,但在中国古人的心灵之中,愤书与神思是缺一不可的组合体系。这不仅对应着中国人在不同境遇下安放灵魂的方式,还是中国文化阴阳和合、相反相顺、相偶相成的思维结晶。钱穆说中国文化相较于西方的“科学文化”、印度的“宗教文化”而言,可谓是“艺术文化”。这种文化的特质决定了我们对于自然科学和宗教神学的忽视。而就愤书与神思而言,二者作为艺术创作论相反相成的两极,涵盖了虚静与愤懑这两种创作心境从而使士人们无论在穷达之际都可以找到心灵满足的途径,可谓在不自觉中已经进行以自我艺术修养为内涵的“美育”代替“宗教”皈依的实践。这也使得中国文艺创作无论在顺世还是在厄世皆散发出生生不息的熠熠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