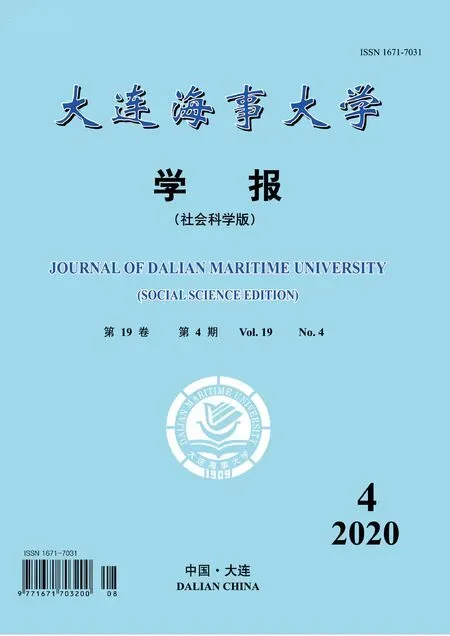争议海域划界前的临时安排与中国实践
欧水全
(清华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4)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世界上存在着多种海洋划界争议,涉及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方面,但在各种划界争议中,最常见、涉及海域面积最广同时最为复杂的是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争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海洋法公约》)对这两类划界做了相关规定。(1)参见《海洋法公约》第74条、第83条。尽管存在相关的法律制度以及相关的习惯国际法,目前世界上依然有诸多的海域划界未能完成。
面对争议海域划界悬而未决的状态,应理性思考争议海域在划界前的安全、秩序以及开发利用等问题。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中已经有了这样的共识,就是在未来制定的公约中应该包含适用于争议海域而不影响最终划界的临时措施。[1]117最终,《海洋法公约》第74条和第83条的共同第3款(以下简称“共同第3款”)分别规定了争议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前的临时安排,(2)之所以将《海洋法公约》第74条第3款和第83条第3款合称为“共同第3款”,是因为两个条款分别规定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前当事国的义务,且两个条款的内容一致:“在达成第1款规定的协议以前,有关各国应基于谅解和合作精神,尽一切努力作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并在此过渡期间内,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这种安排应不妨害最后界限的划定。”这为相关处理争议海域问题提供了国际法上的依据。但是,如何认识这样的规定并将其适用于实践中是目前需要面对的问题之一。因而,本文的目标是立足于共同第3款的规定对临时安排进行专门探讨。除特别说明外,本文讨论的争议海域指的是争议性的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
值得注意的是,共同第3款的起草历史表明,关于临时安排没有形成习惯国际法,而是“表明国际法治逐渐发展的一个例子”[2]354。共同第3款中亦未对临时安排的含义、类型、法律效力等方面做具体规定。因此,该条款文本的具体含义难以准确地把握。[3]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虽然共同第3款有利于促进相关争议国的合作,但是缔约的历史表明此条款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4]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在诸多海域划界争议难以最终解决的情况下,研究作为划界前法律制度的临时安排,对于维护争议海域的秩序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二、临时安排之含义
(一)临时安排的传统国际法依据
尽管《海洋法公约》在共同第3款中规定了临时安排,但作为一种临时性措施的临时安排并非《海洋法公约》独创,在一般国际法中依然可以找到相关的理论与实践依据。这就为研究《海洋法公约》共同第3款中的临时安排提供了一般国际法上的来源和基础。(3)在实践中,临时安排(措施)在英文中有不同的表述:temporary measure, interim arrangement, interim measure, provisional arrangement等。参见文献[5]一书中的表述,该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实践中的各种临时安排。
《联合国宪章》第40条规定了“临时措施”(provisional measures),这被认为是临时性措施(安排)的一般性规则,[6]815其规定了此种措施“不妨碍关系当事国之权利、要求或立场”。(4)《联合国宪章》第40条规定:“为防止情势之恶化,安全理事会在依第三十九条规定作成建议或决定办法以前,得促请关系当事国遵行安全理事会所认为必要或合宜之临时办法。此项临时办法并不妨碍关系当事国之权利、要求或立场。安全理事会对于不遵行此项临时办法之情形,应予适当注意。”从该条的文本规定出发,可以初步得出,作为一般性的临时性措施包括以下几个要素:一是临时性。顾名思义,这种临时性的措施不是最终协议,当然也不能提供最终的解决方案,这只是在最终的解决方案达成之前的一种临时做法。因此,这种临时性的措施不能“有损将来任何法律效果的实现”[7]733。二是避免形势之恶化。[7]732临时安排之所以出现,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立刻或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达成最终的解决方案。三是不妨碍当事国的相关权利和利益。临时措施的目的主要是在争议最终解决之前维持一种和平的状态。
(二)《海洋法公约》中的临时安排
如前文所述,临时措施通常指的是在某事项达成之前的某种临时性做法,因此争议海域划界前的临时安排也是一种临时性措施。[5]38共同第3款的临时安排既属于一般意义上的临时措施中的一类,同时在海洋法的语境下也有其具体的含义。当然,临时安排也需要“在更为广阔的一般国际法语境下进行探讨”[2]349。
从共同第3款的文本中可以看出,作为《海洋法公约》中的一种特殊的规定,临时安排与上文所讨论的一般国际法上的临时措施有着共同之处。也就是说,共同第3款的临时安排满足了临时措施的三个要素。因而可以说共同第3款中的临时安排是一般意义上的临时措施在《海洋法公约》中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所以也应该从共同第3款的规定出发解读争议海域划界前的临时安排的含义。
首先,争议海域的相关争议国应基于合作精神达成临时安排。《海洋法公约》中基于争议海域划界的复杂性和长期性的现实考虑设立了临时安排制度,笔者认为这是为了维持争议海域的和平稳定。同样,临时安排必须充分尊重相关争议国的意愿,各争议国应该基于合作精神来达成临时安排,以维持最终划界前的和平秩序或者对争议海域进行和平的开发利用。
其次,临时安排必须是实质性的(practical nature)。共同第3款规定了临时安排应该是实质性的,这从文义上来看至少说明临时安排不管采用什么形式,都是能够作用于相关争议国的。实质性的临时安排被认为是实现《海洋法公约》目的的重要手段,因而在公约中规定了相关争议国有达成此种安排的义务。(5)See Arbitration between Guyana v.Suriname, Award,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2007, p.131, para.464.但是,在《海洋法公约》中并没有对“实质性”进行进一步的细化,这难免在具体的法律解释和适用中遇到操作上的困难。同时,“实质性”是否要求临时安排应当具有法律效力也是目前遇到的问题之一。
第三,临时安排具有过渡性。由于临时安排是争议国达成最终协议或划界之前基于合作精神达成的一种安排,因此具有过渡的性质,是暂时性的。[5]48这符合上文说到的一般国际法上的临时措施(安排)的要素。通过对共同第3款的文本进行解读可以看出,临时安排的主要目的是更好地在争议海域划界前进行良好的过渡。尽管这种过渡时间的长短难以确定,但毕竟不是永久性的。可以说,临时性也即表明过渡性。
第四,临时安排不影响最后的协议以及海洋划界。最后的协议以及海洋划界应该由争议国重新独立地解决,临时安排不应该对此有影响。也正是由于争议国无法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完成最后的海洋划界,才会采取临时安排这样一种过渡性方法。如果临时安排应对最终的划界产生影响,无疑会增加达成临时安排的难度,以及加剧本已存在的争议。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共同第3款中的临时安排不仅仅如《联合国宪章》中的临时措施那样旨在避免情势的恶化,而且旨在促进相关争议国在争议海域的某种合作或者是规范争议国的行为,[5]42,46例如,常见的是对争议海域内自然资源的共同开发。
总之,临时安排在本质上是在相关争议国不能在短时间内达成划界协议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利用争议海域或者维持争议海域的稳定秩序而达成的一种折中的且具有一定现实可操作性的临时性方案。显然,这有利于维护争议国之间关系的稳定。[8]443尽管《海洋法公约》中的共同第3款未对临时安排做出更加具体的规定,但目前这样的规定能够为相关争议国在暂时缓解争议海域的矛盾以及加强合作方面提供国际法基础和一个现实的思路。临时安排不仅能够促进资源的开发,而且能限制和规范争议海域的活动,这对于海上资源的有效利用、缓解争议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发挥着实际的作用。[9]
三、临时安排的类型和形式:从文本到实践
共同第3款并没有对临时安排的类型和形式做出具体的规定,但是对该条款本身的解读是分析临时安排类型的起点。通过对各国的临时安排进行实证考察,可以从整体上做出类型上的划分。临时安排的类型与形式应该基于不同争议海域的不同情况留给相关当事国来确定。[10]206由于临时安排尚未发展成为习惯国际法,因此很难仅仅基于共同第3款的文本规定就完全确定其类型和形式。所以,目前各国在这方面的实践是对临时安排的发展,至少可能为未来习惯国际法的形成提供实践的支持。
(一)国际实践中临时安排的类型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共同第3款并没有直接规定临时安排的类型和形式,但这给相关国家在达成临时安排时留下了很大的灵活性。通过对国际实践的考察发现,各国在争议海域的临时安排上有着不同的做法,因而“这种安排的内容由相关当事方来确定,同时也取决于个案的具体情形”[2]359。
1.共同开发型临时安排
共同开发是目前最为普遍的临时安排类型。共同开发较早地出现在国际实践中,这也是伴随着各国扩大海域的主张而出现的。在“北海大陆架案”中,国际法院在判决意见中认为,争议国之间如不能达成划界协议,可以订立共同开发协议来处理海域争议。(6)See North Sea Continental Shelf Cases(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Denmark;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Netherlands), Judgement, I.C.J.Reports(1969), p.53, para.101.在“厄立特里亚/也门案”(第2阶段)中,仲裁庭在裁决中指出,已经出现了相当多的存在着海洋划界争议的国家合作开发自然资源的实践。(7)See Eritrea/Yemen-Sovereignty and 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Red Sea(Second Stage), Award,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1999), p.28, para.86.这主要表现为诸多的共同开发协议。(8)关于目前世界各国共同开发的实践,可参见文献[11]。例如,1993年牙买加与哥伦比亚通过在临时安排中设立一个“共同机制区域”(the joint regime area)来进行两国在争议海域的共同开发活动。(9)Maritime Delimitation Treaty between Jamaica and the Republic of Colombia, November 12, 1993, Article 3.参见文献[12]。苏里南和巴巴多斯在2003年签订了关于共同合作开发分享两国重叠专属经济区内的生物与非生物资源的合作条约。(10)Se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Co-operation Treaty between the State of Barbados and the Republic of Guyana concerning the exercise of jurisdiction in their exclusive economic zones in the area of bilateral overlap within each of their outer limits and beyond the outer limits of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s of other States, United Nations Treaties Series, volume 2277, no.40555, pp.201-209.尽管共同开发也是临时安排的一种类型,同样具有临时性、过渡性,但是共同开发的意义体现在相关争议国之间不仅仅是搁置了争议,而且积极地推进了争议海域的开发利用。这使得争议海域能够发挥出积极的作用,而不是在争议国之间的僵持中阻碍海洋的和平利用。
2.临时划界型临时安排
在实践中,争议国之间可以通过临时安排的方式来划出临时的海上界线。例如,2002年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双方共同确立了一条单一的海上临时界线。(11)See Agreement on Provisional Arrangements for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ies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Tunisia and the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Algeria(11 February 2002), 2238 UNTS 197.按照共同第3款的规定,临时界限不能影响两国之间的最终划界,但是这种临时划界型的临时安排暂时性地划分了争议国在争议海域的活动范围,减少了直接的冲突和对抗。
这说明,在实践中已经逐步形成了临时划界(或包含着临时性界线)这种类型的临时安排。这种类型的临时安排反映了争议国之间务实进取的精神,而不是消极地面对争议。但是同时也应看到,临时界线型的临时安排的主要目的也是使得争议国暂时搁置争议而开发利用海上资源,这在目的上与共同开发型的临时安排有相似之处。
3.维持秩序型临时安排
顾名思义,维持秩序型的临时安排的主要目的不是对争议海域进行开发利用,而是维持该海域的和平秩序,以避免矛盾的激化。共同第3款规定了争议国之间基于谅解与合作的精神尽一切努力达成实质性的临时安排,从这样的规定中可以解读出该条款的精神包含了要求争议国在争议海域上维持和平秩序的义务。
实践中,维持秩序型的临时安排有不同的形式。例如,泰国和马来西亚通过临时安排的形式在争议海域分配两国的刑事和民事管辖权。(12)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and the Government of Malaysia on the Constitution and Other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laysia-Thailand Joint Authority.参见文献[1]第118页。又如,通过临时安排的方式来保护争议海域的环境。[10]56尽管这样的安排没有对争议海域进行开发利用,但是通过暂停争议海域中两国的活动可以维持该海域的和平秩序。因为临时安排不仅仅是“积极利用争议海域,也可以暂停争议海域内某些领域的活动”[13]。
另外,也有学者以争议国之间进行海洋划界的不同阶段为标准来对临时安排进行归类,分为划界协商阶段达成的临时安排和进入仲裁或司法阶段后达成的临时安排。[8]432-438
(二)临时安排的形式问题
不同类型的临时安排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与实体内容互为表里。《海洋法公约》中的共同第3款并没有进一步规定临时安排的形式或者对其类型进行界定。在实践中,临时安排可以表现为条约和非条约两种形式。临时安排具有过渡性,因而可以有灵活的表现形式。
首先是条约形式的临时安排。有学者提出,尽管在共同第3款中同时出现了“协议(agreement)”和“安排(arrangement)”两种不同的表述,但是临时安排也可以采取协议(或者是条约)的形式。[5]46-47在实践当中也出现了条约形式的临时安排,这表明相关的国家实践客观地反映了其对共同第3款中的临时安排的理解与适用。在“渔业管辖权案”(英国/爱尔兰)中,英国与爱尔兰达成的临时安排就以条约的形式出现。(13)See Fisheries Jurisdiction(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v.Iceland), Judgement, I.C.J.Reports(1974), pp.15-19, paras.30-39.因此,尽管临时安排顾名思义有着“临时性”的特点,但是这并不排斥这种安排以条约的形式出现。以条约形式出现的临时安排对当事方有着更强的法律上的拘束力,同时更加明确地规定了当事国在争议海域范围内的权利和义务,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其次是非条约形式的临时安排。与条约形式的临时安排类似的是,非条约形式的临时安排也可能有书面的形式。这类书面文件不是条约,但是其法律效力需要根据其内容(是否实质性地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或者是否具有共同第3款中的“实质性”特征来确定。在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在两个当事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中规定争议海域的临时安排。泰国与马来西亚两国于1979年10月24签订的《泰王国与马来西亚关于两国在泰国湾大陆架划界的谅解备忘录》的附件一规定了两国在泰国湾大陆架的确定区域内成立共同管理机构(joint authority)对其海底资源进行开发。(14)Annex I to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and Malaysia on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Boundary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 Gulf of Thailand, 参见文献[14]。也有观点认为,临时安排可以是非正式的,例如相互间的照会。[2]358另外,还有观点认为,临时安排也可以以口头的形式做出,因为共同第3款对临时安排的形式没有做具体的要求。[5]47但是,该观点并没有得到具体实践的支持。
综上,通过对共同第3款的文本分析和实践考察可知,临时安排在类型和表现形式上有着很大的灵活性。目前世界上存在着大量的海洋划界争议,这些争议也都有着各自的特殊情形。如果对临时安排在内容和形式上做整齐划一的规定,不仅不利于实现共同第3款的目的,而且更有可能导致不必要的争议。内容和形式上的灵活性其实恰恰能够促进临时安排的达成,维持争议海域的和平秩序,促进资源的共同开发利用。
四、临时安排之法律效力:对“实质性”标准的考察
共同第3款规定了争议国“尽一切努力做出实质性的临时安排”。这里的“实质性”标准的法律效力应当如何把握?有观点认为,根据共同第3款的规定,相关的争议国并没有达成临时安排之义务,而仅仅是要求争议国“尽一切努力”达成此种安排。[8]444但是,“尽一切努力”是否构成一项公约义务?其与“实质性”标准的关系如何?
(一)“实质性”与法律效力之关系
共同第3款并没有直接规定临时安排的法律效力,但是规定了争议国之间“尽一切努力达成实质性的临时安排”。相关的国际裁判实践已经触及了这点。在“圭亚那/苏里南仲裁案”中,仲裁庭指出,“实质性的临时安排已然被认为是达成公约目的之重要工具,也正因为如此,公约规定了当事方‘尽一切努力’达成这样的安排”。(15)Arbitration between Guyana and Suriname(Guyana/Suriname),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Award, p.154, para.464.所以,这里产生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评判“实质性”与法律效力的关系。
首先,从共同第3款的缔结历史过程来看,缔约国并不是一致地要求临时安排具有法律效力。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中,各国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上存在很大的争议。[6]948-985作为妥协的结果,在最终达成的《海洋法公约》的第74条和第83条中并没有对划界方法做出具体且具有操作性的规定,而只是要求相关国家在划界问题上基于国际法达成公平的结果。相应地,在争议海域划界前的临时安排上也出现了同样的妥协,在最终的共同第3款中并没有规定临时安排的法律效力,而只是规定了“尽一切努力达成实质性的临时安排”。因此,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实质性”和法律效力的关系?或许可以从相反的角度去理解这个问题,如果各国的立场在临时安排的法律效力问题上能够完全一致,就可以直接规定在争议海域划界前相关争议国有义务达成有法律效力的临时安排,而不是使用“实质性”标准。采用“实质性”这一标准表明其法律效力并不是绝对的。
其次,从共同第3款的目的上看,共同第3款主要是为了促进争议海域的和平利用,维护海洋秩序与安全。从这个角度说,只要临时安排达到了上述目的,就可以满足“实质性”的标准,而不是绝对地要求其具有法律效力。“实质性”标准的设置是为了解决在实践中各国难以解决的划界问题,因为临时安排就是针对沿海国难以达成最终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或者划界的复杂现实情况而设置的一种机制。如果严格要求临时安排也必须具备法律效力,就很难发挥其缓和争议的作用。当然,如果争议国之间能够达成有法律效力的临时安排,那将在更高的程度上体现出“实质性”。进一步说,临时安排的“实质性”标准应该根据不同的个案进行评判。[6]815,984[15]577
另外,“尽一切努力”对于达成“实质性”标准有何影响?在共同第3款的语境下,“尽一切努力”体现的是国际法上的善意原则(good faith),[15]576这也是贯穿于《海洋法公约》中的重要原则。(16)《海洋法公约》第300条。因此,争议双方应该基于善意原则尽力达成临时安排,无论是通过外交途径还是直接协商。[2]354
综上,临时安排的“实质性”标准并不当然地等同于具有法律效力。
(二)临时安排的法律效力对整体适用共同第3款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临时安排其法律效力也有所不同,但决定临时安排法律效力的不是其类型或者表现形式,而是当事国的意图。[5]48但是,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共同第3款并没有明确规定临时安排需要有法律效力,而是要求其具有“实质性”。那么,正如前文所述,在对临时安排的法律进行考察时,就不得不处理好法律效力与“实质性”的关系,这对于正确理解与适用共同第3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对于具有法律效力的临时安排,例如条约以及其他表明其具有法律效力的临时安排,根据共同第3款的精神应当是“实质性”的。因为那些具有法律效力的临时安排,无论其是否以条约的形式出现,其在实际上在当事国之间产生了法律拘束力。临时安排在这种情况下指明了当事国在争议海域中的权利和义务,使得争议的行为在法律上得到一定程度的规范,这很明显地体现了临时安排的“实质性”。
其次,对于没有明确的国际法效力的临时安排如何体现其“实质性”的问题,应该从维持争议海域的和平秩序出发来全面考虑。相关争议国基于谅解与合作的精神达成的临时安排尽管没有法律效力,但对于维持争议海域的和平秩序以及稳定繁荣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16]从这个角度上看,临时安排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达到“实质性”的效果。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实质性的临时安排不一定需要有法律效力并不影响共同第3款作为公约条款的法律效力,“尽一切努力达成实质性的临时安排”并不简单地意味着这仅仅是“一个没有法律拘束力的建议或意向,而是一个有强制力的规则,对这样的规则违反也即是对国际法的违反”[2]354。
总之,临时安排对于整体适用共同第3款来说不应仅仅限于其直接的法律效力上,而是要立足于争议海域的划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以及目前维持争议海域的和平秩序的现实性和必要性。尽管临时安排不影响最后的海洋划界,但其为划界前的争议海域的秩序提供了基本的法律基础。笔者认为,应该从临时安排达到的实际效果来衡量其“实质性”。临时安排的“实质性”标准不单单是具有法律效力性,同时也包括这种临时安排是否在实际上维持了争议海域的和平秩序或促进了共同开发利用。
五、中国关于临时安排的实践
目前,中国与周边的海上邻国依然存在着在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的海域划界争议。针对这样的现实,中国较早地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倡议,其实这也反映了中国在临时安排上的基本立场。《海洋法公约》共同第3款中临时安排的前提实际上就是争议国之间搁置划界争议。中国与海上邻国也已经做出了一些临时安排,不过这些临时安排在实际上发挥着何种作用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共同第3款乃至《海洋法公约》的整体目的,需要进一步审视。
(一)中国在临时安排上的实践
目前,中国与海上邻国做出了一系列临时安排。在东海争议海域,中国与韩国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渔业协定》,划定了暂定措施水域与过渡水域。[17]这实际上就是两国针对争议海域的渔业做出的临时安排。该协定以条约的形式出现,规定了双方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具有实质性。但是,该协定的在何种程度上和平有效解决中韩渔业冲突却有待进一步考察。在南海,中国与周边国家做出的临时安排主要有2011年《关于指导解决中国和越南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18]、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海上合作谅解备忘录》[19]、2007年《中国国家海洋局与印尼海洋渔业部关于海洋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等。另外,中国与南海各国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也被认为是一种多边性的临时安排。[1]118-119
但同时应当看到,这些临时安排大多缺乏可操作性以及约束力不强,在实际上发挥的效果较为有限。[21]不过这也说明中国与海上邻国在未来有更大的空间达成程度更高、覆盖面更广的临时安排。当然,达成临时安排的障碍不单是体现在解释和适用法律上,同时争议海域本身的特殊性以及国家关系的复杂性与法律问题的交织使得在这个问题上有时会举步维艰。
(二)临时安排的中国路径选择
中国长期以来坚持的关于处理与周边邻国的海洋争议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倡议面向的是争议海域,包括东海和南海。其中,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主张以“双轨思路”来处理目前的争议。(17)“‘双轨思路’,即有关具体争议由直接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基础上,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南海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加以维护。”参见文献[22]。笔者认为,以上两个方面是中国在争议海域中适用临时安排的指导原则,也是探讨中国临时安排的路径选择的基础。总体来说,中国在周边争议海域的临时安排的路径选择上,一方面应立足于《海洋法公约》共同第3款以及其他的国际法规则,另一方面要针对不同海域的特殊情形达成实质性的临时安排。
1.临时安排以维持海洋和平秩序为原则
维持海洋的和平秩序原则始终贯穿于《海洋法公约》之中,针对争议海域设计的临时安排也体现了该原则。争议海域的和平秩序需要争议国共同维持。争议海域的产生缘于国家之间海洋权利主张的重叠,这种主张的重叠直接导致了权利的对抗。所以,争议国之间应该在和平的原则下务实地面对海洋权利的对抗。
共同第3款中规定了争议国在达成临时安排的“过渡期间内,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的克制义务。争议国之间海洋权利对抗的特殊情形更加要求其保持克制。为了维护秩序或共同利用资源达成临时安排有利于防止争议国之间权利的无限制扩张,在克制的基础上达成合作,并适当顾及对方在临时安排下的合理利益。这同时也表明,临时安排规范争议海域在划界前的秩序以及促进争议国之间的合作,实际上就是对分歧进行管控。同样,中国可以基于这样的思路,促进临时安排作为一种面向争议海域的管控分歧机制。
2.继续探索多边性临时安排
通过前文的梳理可知,实践中存在着多种类型的临时安排。不同类型的临时安排适应了不同争议海域的特殊情况,这也体现了国际实践对共同第3款的发展。中国目前与周边海上邻国存在着不同的争议海域,在临时安排的类型选择上也应根据不同争议海域的特殊情形进行选择。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南海争议海域问题上,由于涉及的争议方较多,这就要求在临时安排的设计上考虑这样的特殊性。因此,针对南海的争议海域的临时安排,可以积极探索包括多方的、具有实质性的临时安排。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该在这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2002年,中国与东盟各国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意味着南海争议各方在南海临时安排上的初步努力。从其内容可以看出,宣言是一种包括多方争议国的、旨在维持南海和平秩序的临时安排,但同时只具有“软法”的性质。[1]118笔者认为,一方面,面向南海的临时安排要体现维持南海和平秩序的精神,并将这样的精神落实到实际中去。目前正在进行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正体现了这样的精神,同时也是对《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效力的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在南海维持和平秩序的前提下,中国与南海各国之间应该理性地面对分歧,积极地推动共同开发,这也体现了中国一直坚持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
3.临时安排与争议解决机制
临时安排实际上可以作为一种临时的争议解决机制,这主要体现在:一是从一般意义上看,共同第3款规定的临时安排实际上就是一种针对争议海域的临时争议解决机制,旨在暂时性地处理在最终划界达成之前的过渡期间争议国之间在未划界海域的矛盾。二是从临时安排的内容设置上看,争议国之间达成的临时安排文件中可以包括争议解决条款。例如,在共同开发协议中设置争议解决机制来处理共同开发过程中出现的争议。(18)See Article 10,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Co-operation Treaty between the State of Barbados and the Republic of Guyana concerning the exercise of jurisdiction in their exclusive economic zones in the area of bilateral overlap within each of their outer limits and beyond the outer limits of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s of other States, United Nations Treaties Series, volume 2277, no.40555, pp.201-209.需要指出的是,临时安排作为一种争议解决机制不是狭义的司法上的争议解决机制,而指的是临时安排在争议海域最终划界之前的过渡期内发挥争议解决的临时性作用。
针对目前周边争议海域难以达成最终的划界协议的现实情况,中国在临时安排上可以从实际出发,与争议国达成相关的争议解决机制,解决机制可以涵盖渔业、资源开发、海上航行、海上执法等方面。在临时安排中针对海上执法设置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一方面可以使执法冲突解决进入稳定的状态,另一方面可以将争议控制在法律的范围之内,避免进一步的政治和外交纠纷。
六、结 语
临时安排始终贯穿着缓解争议海域的紧张局势、维持海洋和平秩序以及促进海洋和平有效开发的精神。尽管可以看到,共同第3款的规定较为简单,但该条款设置的临时安排为争议海域划界前的秩序维护乃至开发利用提供了国际法上的直接依据。对共同第3款中临时安排的把握,一方面要着眼于《海洋法公约》的整体以及海洋秩序的维护,另一方面要看到不同地区的争议海域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应立足于这种特殊性灵活地做出体现务实进取精神的临时安排。
中国作为海洋大国,与周边沿海国家存在诸多的海域划界争议。“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中国的一向态度,同时也一直坚持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来解决海上争议问题。这完全符合《海洋法公约》中临时安排的精神。临时安排的主要目的是在争议存在的情况下促进争议国之间的合作,从更广的视角来看,这关系到维护海洋秩序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合作与发展。这也是中国携手各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