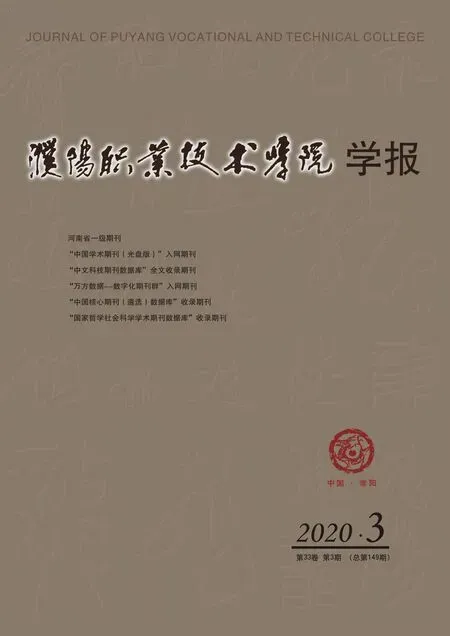时代镜像下的双重身份书写
——重读《人生》
呼丹丹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人生》的发表处于中国的社会转型期,路遥这一时间转折点上,描写“交叉地带”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的出路问题无疑是对时代的回应。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强调:“我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充满了焦灼的关切之情。我更多地关注他们在走向新生活过程中的艰辛与痛革,而不仅仅是到达彼岸后的大欢乐。”[1](112)路遥的这种创作倾向也使其作品常选取农村知识青年这一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群体作为自己的描述对象。不论是《人生》中的高家林,还是《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都是这一群体的代表。但他们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村人,而是“知识青年+农民”的混合体。李陀曾说:“在某种意义上,农村中的知识青年是社会主义中成功的部分……而恰恰是这部分农村青年在改革中遇到的问题是最严重的。”这些问题凸显了 “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刻矛盾”[2](272)。路遥选取这一群体作为描写对象来表现社会转型期“交叉地带”的风云变幻以及农村知识青年的人生困境,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
然而,路遥在《人生》中塑造的高家林形象是否具有典型性?陈骏涛认为,“高家林是处于人生岔道口的农村知识青年的典型形象。在高家林身上集聚了种种矛盾的性格……种种矛盾汇聚于一身,可能使习惯欣赏简单化人物的读者感到不可理解,但我们却通过这个人物的复杂的性格,看到了像万花筒般的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3](90)。阎纲认为高家林是“具有自觉和盲动、英雄和懦夫、强者和弱者的两重性的人物形象。性格的复杂性、两重性,是人生社会复杂性、流动性的生动反映和深刻表现”[4](404)。 由此可见,对于高家林这一人物形象不能简单视之,他的身上充满了矛盾和复杂。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在爱情上,高家林都不可避免地陷入生抉择中。高家林的人生难题既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也是他双重身份摩擦碰撞的表现,知识的冲击使他执着于个人价值的实现,农民的身份又使他受困于土地,这种人生僵局必然造成他精神上的创伤,使其挣扎在理想与现实之中。
一、时代变革下的认知重组
高家林所处的年代是社会主义的大变革时期,国家的政策和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变。在这一历史语境中青年们的精神追求和价值理想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发生转变。在高加林看来,十几年的刻苦学习就是为了能够通过知识,摆脱农民一辈子在土地上劳作的命运。高考制度的恢复,使“知识改变命运”这一名言更具说服力,更激励着无数农村青年奔赴在高考的道路上。这一现象在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如刘震云的《塔铺》中就描写了一群农村青年为梦想而奋斗高考的故事。时代的变革和现代知识为高家林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在这里他看到了自身的价值和人生的追求。现代知识的冲击已使他不安做一个农民,农村这一闭塞的环境也无法盛放他躁动的灵魂。
20世纪80年代初,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的“潘晓讨论”反映了知识青年对于人生出路的困顿。青年们对于自身理想的追求,对于人生价值的实现都有着不可阻挡的热情,然而现实的社会环境对于青年来说确实残酷,他们的理想和追求在现实中处处碰壁。农民出身的知识青年对此更深有体会,因为在理想追求中不仅有现实的阻碍,更有自身难以摆脱的身份束缚。身为农民的高家林深感农村社会的落后和闭塞,急于通过知识使自己摆脱土地的束缚,他对于自身价值的确认也是以远离土地为标准的,正如李劼所评论的那样:“他似乎只有把自己的身份变换成记者、作家、局长、书记等等才能体现他的自身价值。 ”[5](71)《人生》的开头就描写了高家林的民办教师资格被挤掉,面临着重回土地的残酷打击。当高家林在家颓废数日,由于生活的窘况逼得他不得不扛起锄头上地劳作时,他出乎众人意料地把自己打扮的破破烂烂,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他是一个农民。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是生活的希望,生存与土地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个人价值也是通过在土地上劳作实现的。正如作者对刘巧珍勤劳能干的夸赞也是通过对她劳动能力的确认,她劳作的能力比他爹——高家村的“二能”人刘立本还强。
在高加林看来,土地并不是他人生奋斗的舞台,在土地上的劳作也是迫于现实的无奈之举。在劳动中,他从不讲究耕作的技巧技法,只是一味地蛮打蛮干。他从没有思考过如何在土地上创造价值,在土地上没命地干活也是为了通过肉体上的折磨摆脱精神上的痛苦。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我现在思想上麻乱的很,劳动苦一点,皮肉疼一点,我就把这些不痛快事都忘了……手烂,叫它烂吧!”[6](46)反观后来他在县城做通讯干事时的精力充沛,干劲十足,愿为工作奉献一切的热情便能看出他对于人生价值的定义。
在精神上,高家林从来没有做农民的准备,对于土地的回归也只是暂时的休养生息。他对于农村集体的感情已不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作品中描述的那样热切,他更加注重对于个人理想的追求。比如同样是学业上遭遇失败回村务农的青年,马烽小说《韩梅梅》中的韩梅梅却与《人生》中的高家林有着截然相反的人生选择。中考失败的韩梅梅回到农村后并没有气馁,而是努力将自身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农业生产上,将人生的价值放置于集体利益上。而《人生》中高家林所学的知识有意地规避与农村社会的联系。他喜欢阅览报刊杂志,关注时政热点,关心国际问题,然而对于农村的改革或建设信息都被他有意忽略了。在这里,他所学的知识不再与土地发生联系,知识的获取是身份转换的垫脚石。
纵观《人生》全文,高家林对于个人理想的追求从未切断过,只不过路遥将其作为暗线贯穿于文中。高家林有着高远的理想,他对于人生的追求也是放置于广阔的天地中。做民办教师时,高家林就为自身的前途做准备,继续学习,钻研他喜爱的文科,并在地区的报纸上发表文章。他并且希望通过考试成为国家的正式教师,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事更好的工作。虽然这些幻想被“走后门”的三星打破,但他也不安做一个农民。这在他亲吻巧珍后懊悔的情绪中得到鲜明的表现,“他后悔自己感情太冲动,似乎匆忙地犯了一个错误。他感到这样一来,自己大概就要当农民了”[6](39)。在家劳作的时间高家林也不忘为自己的未来做规划,给远在新疆的叔叔写信为自己谋求工作。虽然后因叔叔归乡工作而被搁置,但他终究通过“走后门”的形式实现了自己的“城市梦”。在县城做通讯干事的高家林风光无限,可他对于个人理想的追求不止局限于这个小县城中,而是在更大的城市里开展自己的宏图大业,所以才有了后来爱情中的艰难抉择。高家林对于个人理想的追求使其在爱情和事业上两手空空,最后,路遥虽然设置让其回归土地,然而对于受过教育的高家林来说是不现实的,土地只是他躁动灵魂的休憩地,一旦时机成熟他会再度离乡,追寻自己的人生理想。或许路遥也意识到高家林的“回归”只是暂时的休养生息,因此才将结局设置为“并非结局”。
二、双重身份下的矛盾性
在《人生》中,不管是高家林对于爱情或事业的选择,还是他自身的性格都充满了矛盾性。作为农民出身的高家林,有着知识青年的精神追求,身份的矛盾性决定了他人生道路的复杂性。高家林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但在城里几年的学校生活已经将他从里到外都变成了一个“城里人”,农村气息已经在他身上消失殆尽。作为农民的高家林对于农业劳动一窍不通,对于各种体育和文艺技能却是样样精通。他的生活理念也与高家村人不一样,他爱干净,有刷牙的习惯,穿衣服也讲究,抽烟也是纸烟。他的身体虽然健壮有力,但那是体育锻炼的效果,而不是农业劳作出来的。路遥对此有过详细的描述:“他的裸体是很健美的。修长的身材,没有体力劳动留下的任何印记,但又很壮实,看出他进行过规范的体育锻炼。”[6](14)高家林健美的身躯显然与他农民的身份不相符合,作为地地道道的农民,虽然因为他十几年的读书生涯和三年的教书生活可能从事农业劳动的时间较少,但最基本的农业活动锄地对他来说都较为陌生,由此可以看出,高家林无意识中对于农业活动的逃避。高家林“从来都没有当农民的精神准备!不必隐瞒,他十几年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或者按他的另一种说法是奴隶)”[6](5)。
精神上对于土地的远离使高家林潜意识中内化了对于农民的歧视感。作为农民,高家林之所以对各种歧视过于敏感,就在于他文化程度的提高。接受过学校教育的高家林,农民身上的泥土气息在他身上几乎消失殆尽,他已经有了知识分子的“清高”。在《人生》中,路遥对高加林进城有过三次描写,第一次是进城卖馒头,第二次是进城拉粪,第三次是进城做通讯干事。前两次是高家林以农民的身份进城,第三次是作为知识分子进城。对于高家林来说,前后两种不同身份的进城有着完全不同的心理感受,这种差异性是其自尊自卑矛盾性格的相互较量。当他作为农民进城时,他是窘迫的,不安的,羞于见人的,他害怕碰见熟人和老同学。卖馍时即使是家里的生存窘境也不能迫使他放下自己的脸面去吆喝,如果不是巧珍过来“救场”,他将如何面对家中油盐即将用完的困境?当高家林在副食品公司挑粪被院子里的一位中年妇女骂为“乡巴佬”时。他第一反应是如何反驳他,而当他发现这位妇女是张克南的母亲时,他的反应是不能与她吵架。在高加林看来,他在克南母亲眼中是有文化的知识青年,所以他的举止应与知识分子的行为相符合。而当他确定克南母亲没认出他后,就大胆地进行反驳,并讽刺张克南的母亲身上也有臭味。但这种反驳也是底气不足的,连他自己都难以说服,甚至于粪桶没拉满就去河里洗澡。虽然高家林一再强调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自己从不鄙视任何一个农民”[6](5),但他自身对于农民身份的逃离,便是他对农民歧视感内化的确认。当第三次作为通讯干事进城时,高家林一反前两次的农民自卑感,“抬头挺胸,朝气蓬勃”地走进县城。这一次他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进城,将在通讯干事这一岗位实现个人价值。在这里,他热血沸腾,斗志昂扬,而且走到哪里都是引人注目的焦点。高家林这种反差表现了他对于自我价值的确认。
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将劳动划分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从字面上看是劳动性质的不同,而它背后隐藏的是对于劳动等级的划分。高家林之所以迫切地想要来到城市做脑力工作者,便是他对劳动分工的清醒认知。然而横亘在他面前的却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他有知识,有文化,却有着难以转换的农民身份,这也是城乡二元结构无法调和的矛盾。
三、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人生困境
在当代中国社会里,城市和乡村不仅存在地理空间上的中心和边缘,还有户籍之间的壁垒。城市和农村因为户籍制度、资源分配、社会保障上存在着结构上的差别,因此城里人与乡下人之间也有着鲜明的社会等级差异。《人生》中的高家林是生活在时代变革下城乡交叉地带的农村知识青年,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农民,他有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不安于农民身份的束缚,企图在城市中谋求自我的人生价值。然而,现实的身份差异也使他无法跨越鸿沟,在人生道路上陷入困局,难以自拔。就如姜岚所评论的,“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横着一条城与乡的界线,但进城读书,已经使他们从精神上突破了这个界限,他们断然拒绝对农民身份的自我认同。可是,在不同于父辈的全新生存理想和无法改变的农民血统之间,那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始终存在,不断刺激着他们奋越的欲望,也不时勾起他们对农民血统的自卑和沮丧”[7](93)。
在《人生》中,不管是读书、教书,还是务农,高家林始终没有改掉他知识青年的特质,刷牙、爱干净以及对知识的渴望。这是他自我意识的体现,也是他不甘于农民身份的自我挣扎。在“卫生革命”这一事件中,高家林作为这一事件的提出者和实施者,本应发挥自己知识者的主体地位,然而他却在知识的解释上缺席了,倒是高家村的“大能人”高明楼通过自身的权威以及“以身试水”的行为说服众人,为“卫生革命”画上句号。农村闭塞的环境使村民一直保持着古老的生活方式,对于高家林撒“漂白粉”这一“荒唐”的行为,他们是难以接受的。他们一直秉持的理念是“眼见为真,耳听为实”,因此对于刘巧玲讲解的知识原理他们也是置之不理的。现代的理论知识在这里成了“空口白话”,而高明楼的个人权威和实践行动在这里更具说服力。由此可见,高家林发起的“卫生革命”注定是失败的,因为他面对的不是一群受过知识教育的群体,而是保守着传统生活经验的农民。他们安于本分,固守土地,对于生活中的变故和无常也都“欣然接受”。作为自我意识的觉醒者,高家林是不会允许自己的人生消磨在闭塞的山村中的,农村社会的落后与封闭更激发了他对于城市的向往。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中,他看到城市与农村的现实差距,以及城里人与乡下人的等级差别。当他被张克南母亲骂为“乡巴佬”时,更加激发了他知识分子敏感的自尊心,刺激了他对于个人奋斗的追求。正如高家林所愤恨的“我有知识,有文化,哪里比他们差?”[6](93)然而现实中他确实难以跨过身份的鸿沟,将自己的理想置于现实之上。
在城乡二元结构中,高家林与刘巧珍感情注定是以悲剧结尾。在这段感情中有着鲜明的身份对立,这种不平等的爱情关系注定是以失败告终。在高与刘之间一直存在着知识青年与农村少女、躁动不安与安于现状、理想与现实、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矛盾冲突,两人的感情一直处于不对等的状态。在这段感情中,高家林凭借他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一直属于强势地位,巧珍虽一心恋慕于他,但始终处于依附地位。在恋情的一开始,高家林就以恋爱为由要求巧珍刷牙,在这里刷牙已不仅仅是一种爱干净的个人习惯,“更是一种身份、道德的标识”。当他们的恋情被村人传得沸沸扬扬时,高家林带着“报复性”的心理将二人的恋情公布于众,而且巧珍对于“卫生革命”也是在高家林的鼓动下参加的。对于高家林的要求,巧珍是毫不犹豫的践行,即使与父亲作对也在所不惜,然而巧珍的一味付出换来的是高家林的无情抛弃。在这段感情中,高家林眼中的巧珍是悬浮在空中的画像,他脑海里的巧珍总是与俄罗斯画像中的女孩相对应,可是巧珍没有画像女孩的红头巾,她与画像中的女孩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即使后来高家林送给巧珍一条一样的红头巾,但依旧改变不了巧珍农村少女的身份,她与画像中的女孩是不能等同的。这就像高家林文化程度再高,工作能力再强,衣食住行再像“华侨”也不能改变他的农民血统一样。高家林的人生困局在于他个人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冲突,就如他自我身份之间的矛盾冲突,想做知识工作者的不得与难以摆脱农民身份的无奈。
王愚认为高家林的人生困局“展现了转折时期城乡交叉的社会矛盾”,同时也暴露了“新一代农村知识青年”“‘先天不足’的弱点和‘后天失调’的缺陷”[8](38)。高家林对于个人理想的热烈追求使他忽略了现实的束缚,忽视了自己的农民身份,从而导致了个人出路的困境。因此,在《人生》的结尾中,路遥安排高家林回归土地。同时,作为知识分子的高家林不可能完全放弃对于个人理想的追求,扎根农村。当情况有所改变,他极有可能“卷土重来”,这便是路遥所标注的“并非结局”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