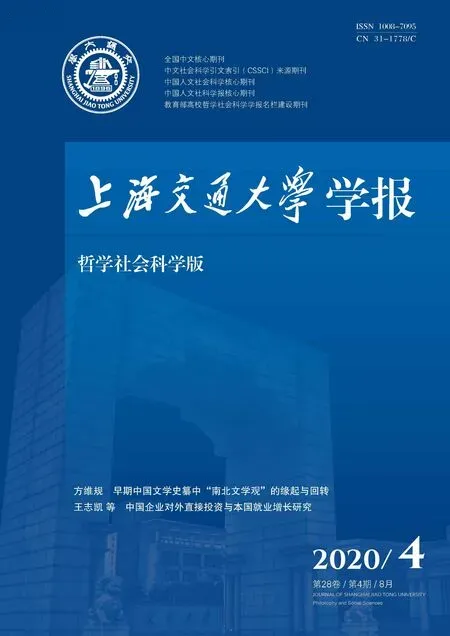当代德国汉学关于中国认知的元方法论之争
范 劲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 200241)
一、 问题的提出: 接近东亚的可能性
对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西德汉学界来说,中国早不再是唐诗中田园牧歌般的永恒胜境,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自身的社会政治进程,也否定了一度流行于西方的中国政治神话。中国并不神秘,有自身的演化规律和运作法则,有自身的困难和曲折,也有改革和突围的勇气,这对她的外部观察者提出了新要求。思考如何重新接近中国的路径,如何实现和一个活生生的中国对象的交流,是摆在汉学家面前的急迫问题。
《波鸿东亚研究年鉴》于1978年由波鸿大学东亚系创办,虽然刊名以“东亚”为对象,内容上却以中国为侧重点,成为西德方兴未艾的中国学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平台。《年鉴》把具体研究的框架条件作为优先考虑的话题。1978年第一辑主题为“东亚现代化过程中的西方和东方因素”,1979年第二辑主题为“科学在东亚: 历史、意识形态和方法论”,1980年第三辑主题为“东亚研究: 历史、意识形态和方法论”,都涉及东西方文化和知识系统间关系,以及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问题。
1979年《波鸿东亚研究年鉴》“编者前言”反思了东西方学术体系的区别,颇具元理论探讨意味。系统独立是系统论的基本前提,但前言执笔者克拉赫特(Klaus Kracht)认识到,在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形势下,一个完全自治而独立于东亚自身研究程序的西方的东亚研究已不再可能,东西方的研究必然会相互渗透和影响。但实情为何: 东西方研究者是否使用同一种语言?相同术语下是否隐藏了不同含义?何种程度上可以说,东西方学者遵循相同的科学话语形式?要确立西方的东亚研究者的自身身份,这些问题是必须要提出来的。
要实现自我认同,就要清楚东西方研究方式的差异何在。但克拉赫特言外之意是,西方学者相比于其东方同行,有何优势。他给出几个临时“坐标”,以概括东亚现代学术的特征。第一个坐标是学术服务于“民族国家的重新定位”(nationale Neuorientierung)。将学术用作“民族国家的定位学术”(nationale Orientierungswissenschaft),无论在中、韩或日本都成了新传统,以“内/外”二元对立为基本结构。学术实际上成了寻找民族身份的工具,这一倾向远远胜过西方学术界,而这是和一个世纪以来的民族身份危机相关联的。第二个坐标是实践对于理论的优先性。克拉赫特说,谁读过顾彬对于中国在文学研究上“非辩证方面”的批评,就会质疑,中国自身的文学研究在严格意义上可否称为“学术”。学术和社会实践乃至政治密切关联,从西方市民阶级传统的角度来说无疑是落后的,因为它妨碍了科学研究主体创造性的自由展开。究其原因,克拉赫特认为这和儒家传统相关,中日韩的现代学术都受到儒家深刻影响,而儒家学术——“学问”——从根本上说立足于实践,学术和伦理须臾不离,学术的目标是实现“仁”的理想。故不难理解,为何意识形态和实践在中国当代学术中占据统治地位,因为“当代中国对于科学的态度”实为“一种儒家科学观念的遗产”,而文学批评仍要起到历史上曾有过的那种“劝善惩恶”之用。(1)Klaus Kracht. Redaktionelle Vorbemerkung [J]. 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 1979,2: X.第三个坐标是语言和现实的关系。在过去西方人眼里,亚洲语言的含混性特征导致了概念的模糊性,不利于科学研究。克拉赫特这一辈学者自然已摆脱了老旧观念,同时也意识到,现实本身就是含混的,清晰的科学语言不啻对于现实的人为干预,是要赋予“无框架”的生活本身一个框架,这一导向常常遭到东亚学者质疑。但克拉赫特也渴望知道,经过数十年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的概念语言系统是否已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认知方式,使其人文科学和韩日两国产生了重大区别。
既然东亚有自己的学术认知方式,西方的东亚研究就面临两难: 如果不和东亚的学术系统保持批判性关系,可能沦为对方意识的简单反映;但如果将自身学术传统的标准绝对化,又无法为自身意识赢得新经验。这是自我指涉和外来指涉的矛盾,合适的道路是保持两种导向的辩证张力,在更高层面反思东西方学术各自的优缺点,同时要意识到,“学术”的涵义比人们通常理解的更为深刻。
1980年《波鸿东亚研究年鉴》“编者前言”又是一篇深入的元理论反思,副标题为“言说‘东亚’: 缺失的语言、此在的语言”。为了打破独语格局,克拉赫特特别采取了A和B虚拟对话的形式,不过他提醒读者,不要把对话双方A和B当作真实人物,去猜测各自代表了谁的立场,可见前言力图达到德国东亚学的集体意识层面,探讨研究本身的条件和可能性。克拉赫特指出,有三种西方语言在言说东亚:“缺失的语言”(Sprache des Mangels)、“启示的语言”(Sprache der Offenbarung)和“此在的语言”(Sprache des Daseins)。
“缺失的语言”从求同角度出发,寻找欧洲的对应物,却在东亚之旅中发现了令西方市民阶级不安的众多“缺失”。马克思主义者要做的,是在东亚市民阶级中寻找“资本主义的萌芽”。韦伯的拥趸想在东亚见到现代经济伦理的萌芽,然而《儒教和道教》中出现最多的就是“缺失”一词。弗洛伊德的信徒试图寻找儒家象征体系中的父亲形象,故而为“东亚自我”中俄狄浦斯冲突的缺失深表惋惜。《爱弥儿》和《威廉·麦斯特》的读者指责说,东亚小说中缺少早期市民阶级对自我发展的描述。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的同道在早年鲁迅的“希望”概念中搜寻“到何处去”的问题(影射汉学家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的论文《鲁迅和“希望原则”》)。这就是所谓欧洲中心主义,从古典时期到新殖民主义时代,它一直在为政治上的压迫话语提供辩护策略,也对西方的东亚研究产生了负面影响。但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后果,即可能导致东亚的东亚研究也欧洲化,从而使西方中心主义失去了可与之抗衡的东方中心主义。克拉赫特担心,东亚的研究者在马克思、韦伯、弗洛伊德或帕森斯等影响下,可能全盘接受欧美中心主义的论述前提,将“缺失的语言”内化。自身传统中不符合西方市民阶级的情感、思维结构和内容的东西,要么被忽略,要么作为落后之物遭到批判。不过,他心目中欧化的东亚主要还是马克思主义化的中国。语言批评因此不可或缺,必须在“同”中发现微妙差异,在东亚语境中重新审视“市民阶级”“科学”“传统”等概念,比方说,欧洲中心主义的概念Tradition就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中文的“传统”或日语的dentō。
相比对“缺失的语言”的详细描述,“启示的语言”只是一笔带过。后者意味着,东亚被视为西方生活和思想方式的有益对立面,它作为“替代性合理性”,(2)Klaus Kracht. Redaktionelle Vorbemerkung. Über, Ostasien sprechen: Sprache des Mangels, Sprache des Da-seins [J]. 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 1980,3: XII.将给灵明枯竭、精神窒息的西方人带来启示之光。但无论是“缺失的语言”还是“启示的语言”,都是由自身利益出发对于对象的工具化使用,它们孤立地处理现象,缺少一种对于异者之整体性的意识,而只有在整体性中才能说明作为类比或是对照的个别物的具体存在价值。可是整体性又是一个悖论,卡尔·波普(Karl Popper)已经指出,整体性无法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替代性方案显然不应是单纯整体主义的接近方式,而只能谨慎地将整体性纳入认知过程,在意识到自身认识局限的认知主体和日益清楚地表达自身诉求的对象之间维持辩证张力。
“此在的语言”则代表这样一种态度,即任由东亚现象保持在自身矛盾性之中,以此矛盾性为真,这种“真”又不是历史性的、已被全球性“发展”所超越的过去现象。这就要求彻底抛弃西方市民阶级的陈套思维,以一种开放方式去获取新经验。用克拉赫特的话说,“我们所要关心的不是自以为(对方)‘缺失’的东西,而应该去描述、分析,在其自身的可能性中去展示所‘存在于此’的一切。”(3)Klaus Kracht. Redaktionelle Vorbemerkung. Über, Ostasien sprechen: Sprache des Mangels, Sprache des Da-seins [J]. 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 1980,3: XV.具体地说,在理论语言之前,要先学会对象的语言,要学会用中文、韩文和日语去说和写,也就是说,要具备语文学的扎实工夫。
鉴于整体性经验对于理解和阐释个别现象的重要性,跨系统学习变得微妙而棘手,但是克拉赫特认为,东亚经验已经历史性地说明了这种学习的可能性。事实上,东亚在过去一个多世纪有效地融合了大量西方知识,将其变成自身现代身份的一部分,反之,现代西方却显得固步自封。B最后向A提问说,基督教背景是否阻碍了西方对异文化“新经验”的接受。然而这个命题似新实旧,上世纪20年代,在法兰克福大学的汉学家卫礼贤组织的一次讨论中,非洲学家弗罗贝纽斯也提出了西方是静止思维、不易领会变化的观点:“我们更多地立足于真理,更多地立足于僵化,立足于被坚实打造的概念和词汇……”(4)Leo Frobénius. Diskussionsreden anläßlich des Vortrags von Prof. Lederer im China-Institut [J]. Sinica, 1928,3: 162.A在此处给出了一个类似的有趣答案,认为在接受新经验方面,欧洲社会作为一神教社会相比于多神教社会具有天然劣势,一神教只相信一种真理,故思维容易变得教条化。
二、 论争的展开
显然,跨系统交流的可能性始终困扰德国汉学界。波鸿大学政治学和汉学家韦伯-谢菲尔1995年在《波鸿东亚研究年鉴》发表《理解东亚: 可能性和界限》一文,再次触及敏感问题。他把“科学”界定为西方文化特有的语言游戏,科学思维的规则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他指出,无论汉学、日本学或朝鲜学的研究对象,其实都不属于东亚,而是不折不扣的欧洲范畴:“我们活动于其中的话语系统,我们所采用的方法,我们表述自己研究结果的术语,都产生于欧洲近代,并不属于任何独立的东亚传统。”(5)Peter Weber-Schäfer. Ostasien verstehen: Möglichkeiten und Grenzen [J]. 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 1995,19: 4-5.认为科学思维反映了人类思维的普遍结构,不过是一种幼稚想法。如此一来,欧洲学者就面临尖锐问题: 东亚研究能摆脱科学话语固有的欧洲特性,获得真正符合对象之实在的观点吗?执著于差异,必然再遭遇克拉赫特16年前已触及的窘境,作为跨文化比较研究的“东亚科学”(Ostasienwissenschaft)呈现为悖论: 如果采用异文化自身的思想范畴,会失去在科学层面进行文化比较的可能,因为这种操作必然采用一种“前分析的术语”;如果采用欧洲思维模式,则不是在阐释异文化,最多算是阐释异文化在欧洲意识中的影像。
这一悖论源自认识本身的特性。韦伯-谢菲尔说,客观的观察有一前提,即观察对象不会因为观察者的存在发生改变。理想情况是,我在进行观察时,就好像世界上没有作为观察者的我存在。可这种情况已被现代的认识论否定,甚至在最讲究精确性的物理学中,也不承认有一位超然的“超级观察者”,我和我的对象在任何时候都是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韦伯-谢菲尔从两方面来展示新的认识论框架对于东亚研究的影响: 一是对于研究对象的界定;二是研究者对这个对象的认知。就第一个方面来说,他认为并没有一个真实东亚,只有一个存在于认识者头脑中的被建构的“东亚”,其疆界随西方人的视域变化不断延展。可东亚的居民从未将自己生活的地域当成“东亚”,而只有“中央帝国”“日出之国”“朝霞之国”的概念。就第二个方面来说,他认为认知的客观性相关于预期,向世界提问的形式已预设了答案。他举历史学家德默尔(Walter Demel)的就职演讲《中国人怎样变黄的》(1992)为例。后者这篇报告提到,在葡萄牙人的早期游记中,中国人是“有点类似于我们德国人”的“白皮肤的民族”。直到18世纪中期以后,中国人才由白种人变成了黄种人,从而不但在精神上,也在外表上和欧洲民族相区分。而在欧洲人对中国的政治形势认知上,18世纪中期也恰好是个转折点,启蒙时代塑造的中华理性帝国形象逐渐褪去了光环,取而代之的是卢梭、孟德斯鸠眼中的暴政、专制帝国。看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在人种形态学认知上的突变了。
对于文化比较科学而言,欧洲性既是界限,也意味着可能性。可能性乃是界限内实现的可能性,彻底回返自身,等于将东西差异绝对化。韦伯-谢菲尔进一步说,将自身特性投射到异文化身上的冲动,是欧洲现代性机制的一部分,目的是在异者身上发现、确认自身。顾彬1995年出版的一部论文集标题为“我的形象在你眼中”(Mein Bild in deinem Auge),韦伯-谢菲尔认为再精确不过地概括了东亚学研究的实质。为何如此?因为由笛卡儿“我思故我在”这一现代性元话语,无法导出外界的实在性和自我的实存感,“如果我确实存在,我是谁?”的关键问题仍未被回答。为了获得自我的图像,现代性意识在对异者的意识中反映自身。由焦虑的现代性自我意识,产生了对于异者的兴趣,也奠定了跨文化比较的形式和内容——配备了科学分析手段的文化比较不过是“欧洲思想的求生策略(Überlebensstrategie)”。(6)Peter Weber-Schäfer. Ostasien verstehen: Möglichkeiten und Grenzen [J]. 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 1995,19: 12.不仅如此,这还构成了东西方区分,东亚文化就从来没有这种好奇心和通过异者认识自身的需要。但正因此,就无需用诸如“此在的语言”等手段来克服自身视角,因为对于“欧洲中心主义”的畏惧本就是欧洲特有的、即“欧洲中心主义”的现象。也因此,长期困扰西方研究者的“欧洲中心主义”原罪实为错误提问。欧洲的科学范畴不但是西方人特有的认识工具,且正因为东亚是西方科学话语的建构物,才能保证其客观性和可认识性——言下之意,客观性和可认识性也是科学系统特有的概念工具。
波鸿大学中国思想史家罗哲海在2002年《波鸿东亚研究年鉴》上发表了题为《语文学与公共性: 汉学阐释学之思》的方法论文章,立场与韦伯-谢菲尔相左。他认为,语文学是传统汉学的核心,也是科学性的基本保证,公共性则是政治性的代名词,语文学和公共性的结合,应服务于人类普遍价值和伦理的实现而非现实政治。汉学家不应满足于相对主义,消极地坐视异者逍遥于界限之外,而应该履行理性使命,在积极的阐释活动中将异者纳入以理性为核心的普遍价值框架。为此就首先要承认,中国作者是合格、理性的对话者,尽管使用另一种语言、修辞和思维方式,却同样关心普遍真理,可以在和西方对话伙伴的交流协商中达成共识,构建“科学的共同体”。反过来说,既然中国文本有公共性诉求,汉学就应具备相应的公共性诉求,在诸如人权问题上表达政治立场,同样以“伦理文化”(史怀策[Albert Schweitzer]20世纪30年代对于中国文化下的定义)理念来衡量中国文本的言说,等等。但这就意味着干预的合法性。他正确地认识到,西方汉学本身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即便是对儒家美学和中文句法的探讨,也没有脱离政治: 中文句法的特殊性往往成为中国人缺乏个体性的论据,中国人缺乏乌托邦构想被归咎于中文中虚拟式的缺失,等等。
罗哲海另一预设是,汉学研究的“材料来源”(Quelle)不是无生命的、任由操纵的“对象”。根据阿佩尔(Karl-Otto Apel)的话语伦理学,理解者和理解对象的关系乃是平等的主体间关系,“材料来源”是一个“招呼”(Ansprache),背后是作为主体的作者,和一个“作者”打交道就应该遵循日常交流情境中通行的“平视原则”(Prinzip Augenhöhe)。这就如作者要让文本产生意义,就必须设定一个和读者平视的场景,读者可以承认或拒绝这个意义,可以而且必须进行评判,这是所有非独语性哲学文本和普通日常对话的共同之处。
罗哲海和韦伯-谢菲尔在阐释立场上的分歧一目了然。前者反对过多强调阐释者的地域联系,认为后者在激进的视角主义上走得过远。这种阐释学的问题在于,它始终是独语的,将“欧洲范畴”和异域“素材”的差异绝对化,但在真实或虚拟的对话中,“范畴”也可以在相互协商中得到改变。韦伯-谢菲尔尽管正确地揭示了欧洲研究者历史和心理上的结构性偏见,却没有在此基础上去纠正扭曲认知,开启“学习过程”,而是画地为牢,让经验性的理解障碍变得理所当然。(7)Heiner Roetz. Philologie und Öffentlichkeit: Überlegungen zur sinologischen Hermeneutik [J]. 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 2002,26: 93-94.韦伯-谢菲尔将东亚学理解为“比较的文化科学”也不妥当,因为这一定义仅强调对照,而不求在相互理解中达成共识。(8)Heiner Roetz. Philologie und Öffentlichkeit: Überlegungen zur sinologischen Hermeneutik [J]. 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 2002,26: 102.
他认为,法国汉学大师葛兰言(Marcel Granet)开启了一个错误的认知传统,认为中国文本的主旨并非思想的把握贯通,也不是要通过理性论证达成理解,而仅注重实际效果,以塑造语言共同体成员的行为为鹄的。受此观点影响,美国汉学家陈汉生(Chad Hansen)视中国文本为无反思的“表演”。德国的“波恩学派”则拼命强调“中国哲学家和语言的含混、非反思性的关系”,在默勒(Hans-Georg Möller)眼中,中国语言只有“实用的-宗教仪式的”而没有“阐释学功能”;对于陶德文(Rolf Trauzettel)(公认的波恩学派的灵魂人物)来说,中国语言的特征在于“规定性”而非“描述性”功能,语言不是表意媒介,而是“众多物中的物”(Ding unter Dingen)。(9)Heiner Roetz. Philologie und Öffentlichkeit: Überlegungen zur sinologischen Hermeneutik [J]. 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 2002,26: 100.他相信,“波恩学派”代表“差异原则”或“落差原则”,和他坚持的“平视原则”正好相反。“差异”是后结构主义时代的理论时尚,受到汉学家的普遍推崇,罗哲海凭什么逆潮而动呢?他从正反两面给出理由。首先,差异模式同样是主观投射,是“有意的片面”(gewollteinseitig)。他提醒说,对照解释的鼻祖马克斯·韦伯在撰写《儒教和道教》时就已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有意排除了中西方的共同点,以呈现一个作为西方的对立面的中国图像。(10)Heiner Roetz. Philologie und Öffentlichkeit: Überlegungen zur sinologischen Hermeneutik [J]. 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 2002,26: 103.其次,他认为中国文本和西方文本一样基于普遍真理的观念,中国作者也追求观点普遍有效。孟子要在他那个时代实现其伦理主张,也必须尊重一般论述原则,展示“对于每个人都可以在理性上接受的事实真理”。故孟子文章绝非葛兰言那一路汉学家所声称的纯规定性的,而是“一种描述性-规定性(deskriptiv-präskriptive)的,或不如说,断言-调节(konstativ-regulative)的双重结构,这一结构将这些句子和所有人都熟知的,以及——从信念上说——对所有人都同样客观的世界相联系。”(11)Heiner Roetz. Philologie und Öffentlichkeit: Überlegungen zur sinologischen Hermeneutik [J]. 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 2002,26: 106.
也是由强调共识的理性立场,他明确地反对解构主义的中国文学研究。何致瀚是德国汉学界这方面的代表,继两卷本《顾城——一个朦胧诗的解构研究》之后,他又将庄子置于解剖刀下,在2001年出版了《世界作为言辞——对于庄子南华真经的文学解读》。他试图以解构主义操作敞开这部难解的中国经典的言外之意,其中一个要点是将言辞(Wendung)分为“寓言”“重言”“卮言”三类,而突出“卮言”的重要性。所谓“卮言”,何致瀚理解为最完善的言辞,在自身中包含并扬弃了此和彼、是和非的语言,能真正呈现宇宙的整体性。他举《庄子》第17章中“鱼之乐”故事为例,认为庄子是有意玩弄语言的双重语义:“鱼之乐”既指代鱼之乐,也表示渔(捕鱼)之乐。《庄子·外物》又有“荃”之喻,足可证明鱼也代表思想,同时也代表语言媒介,这就生成了一个多重转折(德文“言辞”的本义即“转折”),故“鱼之乐”的故事主题实为“语言之乐”,指涉“关于言说的言说”,(12)Hans Peter Hoffmann. Die Welt als Wendung. Zu einer literarischen Lektüre des Wahren Buchs vom südlichen Blütenland (Zhuangzi) [M].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1: 321-322.“鱼之乐”成了一个将读者卷入宇宙事件之漩涡的卮言。尽管如此,罗哲海意识到解构中的建构,艺术表演中的语文学阐释学。他说,何致瀚的实验仍仰赖传统语文学,解构主义者口头上不承认科学语言和文学艺术的界限,实际上还是要遵循一般论说标准,如避免逻辑上的自相矛盾等等,才能维持特定阐释。何致瀚阐释的初衷本就是要赋予“鱼之乐”故事“更多智性”,实现一个“对于文本(重)建构的贡献”(Beitrag zur Textre(!)konstruktion)。(13)Hans Peter Hoffmann. Die Welt als Wendung. Zu einer literarischen Lektüre des Wahren Buchs vom südlichen Blütenland (Zhuangzi) [M].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1: 62.如果鱼在《外物》篇中代表了思想乃至语言,岂不又证明,这里涉及“媒介的替补作用(Supplementierung)”,而这正是何致瀚一开始就明确反对的孤立的“哲学性解读”的特征。这些段落恰好说明,何致瀚并未像他所主张的那样卷入庄子的语言漩涡中以致“忘言”,(14)Heiner Roetz. Rez.: Peter Hoffmann 2001 [J]. 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 2005,29: 293.因为“一种和存在相融合的语言如何获得和对象的必要距离,从而能对它进行表述呢?”(15)Heiner Roetz. Rez.: Peter Hoffmann 2001 [J]. 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 2005,29: 294.这一批评,对于克拉赫特“此在的语言”同样有效。罗哲海也对法国汉学家于连的后现代主义滥调表达了质疑,认为后者关于中国古代语言“没有语法”,只有纯粹“关系性”之类说法,(16)Heiner Roetz. Rez.: Peter Hoffmann 2001 [J]. 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 2005,29: 294.不啻将西方后结构主义时代的语言学范式强加于先秦时代中国。
罗哲海反对以语言替代生活世界,反对“语言学转向”导致的对于语言的夸张看法,点名批评于连、陈汉生和默勒,同样也招致对方回击。汉学家和哲学家默勒是陶德文的学生,他针对罗哲海《语文学和公共性》发表了题为《盲目的理解》的评论。他嘲讽说,谁如果长时间浸淫在话语伦理学中,自然能够把孟子认作话语伦理家,过去的汉学家大都如此,卫礼贤能在中国古人身上看到基督教萌芽,李约瑟把中国古人视为现代科学家,将来马克思主义者大概要谈论中国古代的阶级斗争了。(17)Hans-Georg Möller. Blindes Verständnis: Überlegungen zum Beitrag von Heiner Roetz [J]. 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 2002,26: 113.他看到了罗哲海和哈贝马斯的思想关联,故援引后现代理论家史路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来回击他们的普遍理性观点。史路特戴克认为,如果按照哈贝马斯的游戏规则进行交流行动,可以肯定的是,“在最终淘汰之后,不会再有求异理论家,或多元主义者,或建构主义者,而尤其不会再有艺术家留在真正理性的交流者圈子内”。史路特戴克又援引哈贝马斯的老对手卢曼说,“批判理论的结构性不宽容”可回溯至“它对于老欧洲的本体论前提的固守”,由此导致了“强制求同”(Zwangskonsensualismus)。言下之意,他和罗哲海的分歧是小号的史路特戴克(卢曼)和哈贝马斯之争,而罗哲海错在“结构性不宽容”和“强制求同”。(18)Hans-Georg Möller. Blindes Verständnis: Überlegungen zum Beitrag von Heiner Roetz [J]. 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 2002,26: 114.他认为理解不是公共的,而恰是盲目的。理解的对象事先已经设定,它要寻找的对话“主体”怀有“无限的公共性诉求”,可以就它们的“伦理”达成理解。一旦预设了主体,即便是《论语》文本“含混的生成情形”也可以忽略不计。可不论怎样一厢情愿,话语伦理学家也无法在无作者的文本集合《论语》中找到主体,既没有明确作者,又何来“作者意图达到的意义”?(19)Hans-Georg Möller. Blindes Verständnis: Überlegungen zum Beitrag von Heiner Roetz [J]. 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 2002,26: 116.所以话语伦理学不啻为党同伐异的政治学和伦理学,悖论性地用一种普遍主义来抵制其他普遍主义。
三、 论争的外在化: 制造“学派”
德国汉学的发展离不开争论,魏玛共和国时代就有围绕胡适接受展开的争论、柏林的正统派和莱比锡学派的争论、对于卫礼贤中国话语的批评,等等,当代德国汉学界同样不乏论辩和冲突。在这些争论中,一个“波恩学派”概念逐渐浮出水面,围绕“波恩学派”制造的纠纷也有方法论立场的站队意味。罗哲海已经不客气地提到了“波恩学派”,一般人也认为这是他的发明。但顾彬认为是他更早提出了这个概念,(20)[德]顾彬.略谈波恩学派[J].张穗子,译.读书,2006(12): 115.而且针对范围超出了德国内部。波恩学派在罗哲海那里是个贬义词,对顾彬来说却担负了和所谓“美国学派”相对抗、挽救欧洲学术正统的英雄使命。何为美国学派?按顾彬的说法,那就是一种教科书式学术,总是迎合时尚,发明浮华的新概念,而最关键的是,它因为严重缺乏历史意识而忽视中西文化间的根本差异,误认为现代性可以由中国传统文化内部产生。相反,波恩学派认为所有话语和思想都是特定时代的建构,故反对“那种在一切文化中寻找同样东西的普遍主义思想”;(21)[德]顾彬.略谈波恩学派[J].张穗子,译.读书,2006(12): 118.波恩学派坦率承认中国就是他者,且只有真正的他者对欧洲人才有价值,相反欧洲人也不应妄自菲薄“自己的”理性传统。作为波恩学派的哲学家同盟,顾彬援引西蒙(Josef Simon)、卢曼、史路特戴克、黑格尔,但拒绝“落伍”的哈贝马斯。(22)[德]顾彬.略谈波恩学派[J].张穗子,译.读书,2006(12): 119.
问题焦点是跨系统交流的可能,更确切地说,如何理解交流的涵义。交流若基于双方的符合,则在韦伯-谢菲尔这派人看来,文化系统间不存在符合。这又进一步涉及认识论问题,跨系统观察其实是一个文化系统在观察另一个文化系统,按照传统的哲学表述,则一个系统相当于主体,另一系统相当于客体,然而,即便主客体符合的可能也被现代人质疑。但如果交流基于差异,则交流就是差异两边的交替互换,不需要找到一个共同标准。
在客观性是否可能的问题上,韦伯-谢菲尔非常接近卢曼的立场。卢曼的“新”认识论有三个要点: 首先,他认为传统认识论框架设定了静止的主客体,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不但主客体各自的位置会随时变动,连主客体都可能相互换位,自然不存在主客符合意义上的客观;其次,观察者无法观察自身的观察,其自身成为认识过程中被排除的第三者,而这意味着,世界整体也是被排除的第三者,观察者和世界整体成为最后的观察盲区;其三,卢曼把认识者和对象的关系理解为相互观察,把人类认识理解为观察的接力,认识的客观性仅存在于观察的连续互补。如果主客符合做不到,文化间符合就更是空谈,但是按照卢曼的思路,持续不断的文化差异性比较反而实现了观察的接力。默勒更是汉学界的卢曼信徒,用英语撰写过《卢曼解释》《激进者卢曼》等书,向德语区之外的世界介绍卢曼系统论。他的《卢曼解释》旨在捍卫卢曼受人诟病的“反人本主义”,认为卢曼的理论并不是要否定人类经验,而是要维护其多元性和差异性,卢曼才是“彻底的历史性思考者”。(23)Hans-Georg Möller. Luhmann Explained: From Souls to Systems [M]. Chicago: Open Court, 2006: ix-x.相反,罗哲海遵循哈贝马斯的逻辑,将日常交流中的交往理性视为超越历史、文化差异的本体论层面。尽管交往充满误会和风险,跨文化沟通更是困难重重,他还是像哈贝马斯那样乐观地相信理解的可能,而理解之所以可能,自然不是因为功能系统的操作需要,而是因为论述本身符合真理。汉学争论的背后,逐渐浮现出卢曼和哈贝马斯之争的影子。
德国汉学家争相援引哲学权威以获得和知识大系统的联系,但他们的指向通常模糊而游移,美国学派时而被推到现代一方,时而被划入后现代一方,而顾彬尽管曾拥戴史路特戴克这位德国的后现代代表,反对哈贝马斯,而实际上他的总体立场更近于黑格尔式的坚持理性、主体性的现代派。汉学家喜欢附会最新、最激进的哲学家,自身观念却不像所声称的那样激进,德国汉学界主导标准还是19世纪精神哲学。立场的含混决定于汉学在知识系统内的边缘位置,作为中西知识系统的界限本身,汉学本身就是西方/中国的悖论统一,注定有时拥抱差异,有时偏向共性。无论面对西方或中国,汉学家都要根据求同或求异的需要,交替扮演西方或中国。为了在西方知识界标新立异,他们接纳史路特戴克这样的争议人物,面向中国知识界时,又会以西方正统的维护者自居,或者将中国排除在理性之外,又或者将理性标准强加给中国。汉学交流的边缘性造成了不确定性,但也正是其活力所在,主流话语借助边缘话语获得自我修正的可能性。
同时处理建构和解构、同一性和差异性的两方面需求,是德国汉学的方法论难题。克拉赫特1979年的结论是,距离不是真正障碍,关键是要在情和理、感性的接受意愿和批判性认识之间建立一种能动的“辩证的张力”,从而走上一条“和谐的道路”:“这就意味着,回到感觉、不作反思、不实行个别化,因为民族志学也是个别化,它将作为我经验对象的语境分割为各部分……”(24)Klaus Kracht. Redaktionelle Vorbemerkung [J]. 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 1979,2: XIII.放弃反思和个别化当然不可能,但“辩证的张力”是朴素而睿智的说法,暗示了一种能够包容悖论的弹性框架的可能性。科学系统的理想是,在一个超越情和理、感性接受和批判认识的更大框架中,不同学者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但也不会消灭具体操作上的分歧: 交流的目的是指向真理的终极目的,还是作为交替确证的交流本身;是通过交流消除差异,还是借助差异创造新的差异。能做到这一点,罗哲海和波恩学派的对立诉求也就成了良性的互补关系。
四、 余论: 论争作为交流形式与中国的实在性
如上论争透露了两点: 首先,中国在当代德国知识界逐渐成为东亚的象征,克拉赫特、韦伯-谢菲尔的论述对象虽然是东亚整体,实际上主要针对中国;其次,有关中国的方法论争发生于德国汉学系统内部,并无中国对话者参与。尽管中国系统一直存在于环境中,中国在德国知识界新近唤起的兴趣又构成了外在刺激,但无论哪一种中国想象都是系统内交流的产物,其原因正如韦伯-谢菲尔所说:“欧洲的东亚科学被迫以欧洲范畴来开展工作,因为它并非要向东亚人、而是要向自身解释东亚。”(25)Peter Weber-Schäfer. Ostasien verstehen: Möglichkeiten und Grenzen [J]. 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 1995,19: 11.从系统内交流来说,不难理解论争的对峙态势。首先,“中国”既然是科学系统的产物,就得服从理性逻辑,否则无法实现知识的交流、评估和再生产。其次,“中国”又是系统内定制的他者,必须拥有自身结构(另一种理性),否则无法实现和西方的区分。同一性和差异性都是系统存续的必需条件,系统编码同一,才成为自主的功能系统;但系统运作基于差异,以自我指涉和外来指涉交替引导系统操作,因此他者必不可少,不管它被称为“东方”“东亚”“中国”还是“印度”,但这是悖论性的“内部的他者”。
汉学元方法论争背后的现代和后现代之争,反映的也是同一性和差异性的系统内交替。上世纪80年代哈贝马斯介入了西方知识界关于后现代的讨论,也成为利奥塔等后现代理论家的直接对手。哈贝马斯坚持现代性尚未终结,现代性元话语仍然有效。面对后结构主义和系统理论的前后夹击,他既捍卫作为现代性核心的理性原则,也竭力避免重蹈主体中心思维的覆辙。他开出的药方是交往理性概念,交往行动理论以新的方式寻找话语背后的理性基础,重构让一切话语具有合理性的元话语。利奥塔认为这仍属于思辨哲学的旧模式,在《后现代状态》中批评哈贝马斯说,后者将合法化问题的答案限制在普遍性上,一方面将认知主体合法化和行动主体合法化同一,另一方面把共识当成话语的目的。然而对于利奥塔来说,认知和社会行动属于不同语言游戏,拥有不同的语用学,语言游戏的同态性会造成“恐怖”,而理想的交往共同体寓含专制性要求。另外,利奥塔认为共识原则违背了科学语用学,因为共识只是科学讨论的一个环节,当代知识生产的目的是求新,创新通过分歧实现。(26)[法]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 关于知识的报告[M].车槿山,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23-225.利奥塔主张以不可通约的多元化语言游戏来代替普遍理性,将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27)[法]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 关于知识的报告[M].车槿山,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而元叙事的基本形式是思辨理性和解放叙事——宣称理性不但在知识论场合普遍有效,且能实现人的集体自由。卢曼一方面承认利奥塔反对元叙事的合理性,一方面否定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和共识导向,因此让汉学家误认为他是和史路特戴克一样的后现代主义者(默勒把卢曼明确归入后现代阵营(28)Hans-Georg Möller. Luhmann Explained: From Souls to Systems [M]. Chicago: Open Court, 2006: 194.)。汉学家不了解的是,卢曼并非后现代主义者,而要求在差异共在场(而非主体间性原则)的基础上重新思考整体性框架,因为他很清楚,反对元叙事的口号本身就是元叙事。在他看来,现代/后现代作为现代社会的“自我描述”都服务于系统运作,都并非“唯一正确”。(29)Niklas Luhmann. 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 [M].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98: 1144.因此,这里对垒的实际上是三方立场: 后现代、现代、系统论,各执一词,后现代一方虽然声势逼人,但哈贝马斯对于福柯和卢曼等人的批判,也不乏合理性。
如果“中国”是内部交流中的建构,如何理解其实在性?关于中国为何的问题,一般答案有三种: 1、中国是对象信息(实体属性);2、中国是相同者(共识);3、中国是他者(分歧)。第一个意义上的中国虽然必不可少,但并非理论关注的焦点,因为对象信息属于一阶观察,而理论属于二阶观察,即对观察的观察,相同者意味着相同的观察方式,他者意味着另外的观察方式。观察用的区分标准决定了理论导向,而汉学家共同的引导区分是自我/中国(系统/环境)。从自我(系统)一面看问题,必然求同,中国成为理性自我的投射;从中国(环境)一面看问题,必然求异,强调他者的自主。由自我指涉/外来指涉的交替,生出东西二元对立、东方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意识形态性命题,也正是自我、外来指涉本身在支撑实在性问题,然而由德国汉学的方法论之争可见,无论求同或求异、自我指涉或外来指涉都是片面观点。哈贝马斯式求同的缺陷在于忽略具体历史性(昨日的《诗经》不等于今日作为文学文本的《诗经》),后现代求异的缺陷在于否定了理性交流的可能,等于取消了中国的实在性,对此可以有一种简单反驳: 既然中国是绝对他者,则关于它的任何谈论,包括中国他者论都变得毫无意义。
差异论在当代西方汉学界占据主流,从上世纪美国汉学家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以来,学者们又提出了“亚洲作为方法”(陈光兴)、“中国作为方法”(沟口雄三)等新命题。这类提法看似摆脱了二元区分造成的方法论困境,却仍是悖论性的,它们不过是差异论的变种。很显然,作为方法的中国是一种意识形态性征用,旨在从他者角度强化中国对象的自主性。中国自身就是方法,意味着有一种他者的方法,一方面应用于中国观察,促成一种不受西方概念污染的自我观察;一方面应用于反观西方,挑战传统思维。总合起来就是,由中国发现超越主体窠臼的本真世界,由中国他者性理解世界他者性,此即为“以中国为方法,就是以世界为目的”。(30)[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M].孙军悦,译.北京: 三联书店,2011: 130.另可参见曾军.“作为方法”的理论源流及其方法论启示[J].电影艺术,2019(2): 3-8;吴攸.中国作为“方法”——论弗朗索瓦·于连的对话主义汉学研究路径[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9(4): 77-87.不过中国作为方法其实意味着中/西方区分作为方法,因为只有在和西方的区分中才存在中国他者。沟口雄三等人希望通过回到作为他者的世界,超越东西方对立,忽略了一点: 他者/自我的区分也是内部生产的区分,而这一点倒是被韦伯-谢菲尔注意到了。方法作为连接主客体的认识论关系本身虽然超出了作为实体的主体或客体,但并未造成中国自主: 方法受制于一整套框架条件,作为方法的中国不过是作为中国的(西方)方法。从德国这场元方法论之争,可清楚地看到他者中国的位置——理性中国的对立面。汉学系统既生产作为自我的中国,也生产作为他者的中国,他者论也是汉学史上可追溯到葛兰言一辈的老话题。但不管是作为自我还是他者的中国,都可以根据理论政治需要带上正面或负面意义,也就给了论争双方相互攻击的理由。
从系统论角度来理解中国的实在性,则三个答案都可以接受,“中国”既是对象信息,又是相同者,还是他者。那“中国”是什么?系统论借自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海德尔(Fritz Heider)的媒介和形式概念或许能给人以启迪。海德尔注意到,对那些和身体无直接接触的客体的知觉(如视觉或听觉)需要借助专门媒介(光或空气)而实现,但媒介本身不会被知觉到。媒介的特征是要素间松散的关联,而形式将松散关联压缩成可供知觉的紧凑耦合。卢曼将这对概念引入系统论,用来描述社会系统中的交流媒介。交流媒介连接交流,让交流进入耦合/脱钩的交替,从而实现形式的生产。媒介作为交流的松散连接,经过压缩会变为形式,如同声音媒介可以压缩为语言。媒介和形式的关系又是相对而言的,一种媒介的形式可以充当另一种形式的媒介,譬如语言是声音媒介的形式,但又可以充当交流内容的媒介。(31)Claudio Baraldi, Giancarlo Corsi, Elena Esposito. GLU: Glossar zu Niklas Luhmanns Theorie sozialer Systeme [M].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88,2. Aufl.: 58-60.循此思路,如何接近中国的问题可转换为如何使用“中国”这一交流媒介,以何种路径——参照自我还是参照外部环境——将松散连接的中国信息压缩成紧凑形式的问题,而作为自我或他者的中国,都是由媒介生成的具体形式。中国文化“走出去”命题并未被证伪,只是需要从另一视角来看待西方语境中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并非实体,而是符号性的一般化交流媒介,是来自不同渠道的种种中国信息的松散、无形式连接,从系统需要出发,可以被形式化为客观实体、主观心像,或一种特有的认识论范畴。当全世界的人们都在使用中国文化媒介以实现自身的交流目的,创设局部交流场景时,中国文化就算是真正走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