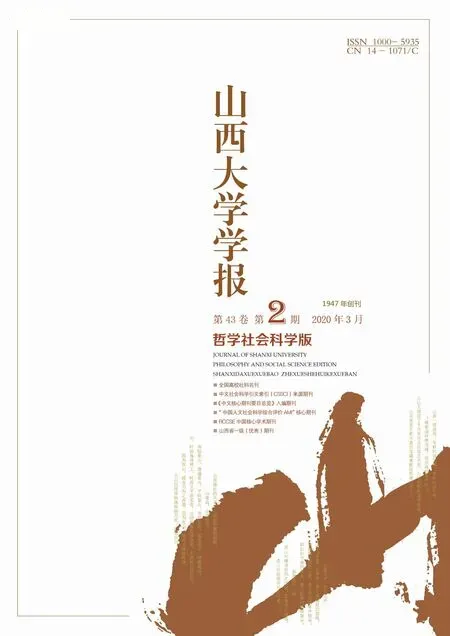朱熹与伊藤仁斋关于孟子仁说之异同及其意义
刘毓庆,王 岩,2
(1.山西大学 国学研究院,山西 太原 030006;2.山西财经大学 新闻与艺术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作为《四书》之一,《孟子》一书在中国和日本都有重要影响,尤以朱熹《孟子集注》和伊藤仁斋《孟子古义》影响最大。
朱熹(1130—1200)其学上承周濂溪、张载、邵雍、二程,下启元明清三代,是孔孟之后最大的儒学宗师。《宋史·道学传》引黄榦之言盛赞朱熹继孔孟绝学的历史功绩:“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1]其《四书章句集注》代表了理学乃至中国传统经学的最高成就,故钱穆云:“朱子乃集宋儒理学与自汉以下经学之大成而绾于一身,而《集注》则是其最高之结晶品也。”[2]214而《孟子集注》全面阐说了性善、心、理气、命、诚等理学思想,是朱熹理学思想的重要载体。
伊藤仁斋(1627—1705,即明天启七年至清康熙四十四年),是日本江户时代古学派创始人。北村可昌盛称其云:“洙泗正统,本邦主盟,无一时用,有千载荣,学耶德耶,日月双明。”[3]古学先生伊藤君碣铭可见其在日本近世学术史上的地位。其代表著作是《论语古义》《孟子古义》《语孟字义》《童子问》等。仁斋早年浸淫朱子之学,而后则力反朱子。其晚年所撰《孟子古义》,与朱熹《孟子集注》展开隔空对话,表现了仁斋古学与朱子宋学在具体观点、思维方式乃至文化传统之间的巨大差异。
“仁学”是孟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故伊藤仁斋说:“仁者,人道之大本,众善之总要。……若欲明其义者,当自《孟子》入。”[4]216仁斋又认为对“仁”的不同理解形成了日本古学与宋代理学的分水岭:“佛老之所以与吾儒异者,多在于义,而后儒之所以与圣人殊者,专在于仁。”[4]215所谓“后儒”,即指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其实对孟子“仁学”的不同理解,不仅反映了中日古代两个学术流派之间的分歧,更主要体现了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下,对同一部经典的不同理解和阐释。朱熹以中国传统的“天人一体”观念为背景,视仁为“天地生物之心”。而仁斋则接受日本本土神道的影响,以天人分立的思想为背景,重在阐发仁的现实功用。通过对二者之比较,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儒学和日本儒学在世界观和学术精神上的显著差异,进而增进对中日两个民族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差异性的认识。
一 朱熹对孟子仁说的阐释及其意义
《孟子》首章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仁”既是《孟子》首章的大旨,也是《孟子》全书的大旨。朱熹注:“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5]201“心之德,爱之理”蕴含着天理、人心、性、情的关系,使“仁”成为上通天理、下达人心,又从爱中流出的儒学思想核心。朱熹特在此揭示出这六个字,是要在《孟子》开篇即揭示出理学精髓。
析言之,“心之德,爱之理”实际上是从宇宙界与人生界两个层次来说仁。“爱之理”主从宇宙界来说仁,又注重从宇宙界贯通于人生界。朱熹又云:“要识仁之意思,是一个浑然温和之气,其气则天地阳春之气,其理则天地生物之心。”[6]111一“仁”字实际上绾合了理与气,接通了宇宙界与人生界。而“心之德”则从人生界来说仁,又注重从人生界上溯到宇宙界。仁具于人心,是一种对天地万物的痛疴保持高度敏感的大爱,而此温和之爱的生发源于天地阴阳之气的内外交通。
所谓仁是“爱之理”,即言所以能爱的道理,“理”指天理。仁之所以为天理,根本原因在于它是“天地生物之心”。朱熹说:“‘天地以生物为心’,天包着地,别无所作为,只是生物而已。亘古亘今,生生不穷,人物则得此生物之心以为心。”[6]1280古往今来之间,天地六合之内,四季寒暑往来不已,草木春荣冬枯不息,人与禽兽繁衍孳育不止,天地之间虽然有生气几尽的萧瑟之时,但归根到底只是生生之理运转不息,阴阳二气流转不已,生生之意发畅不已。所以说,仁即生也,天地之仁即天地生生之理;人得此天地生生之心以为心,所以仁为性。
既然仁是“天地生物之心”,自然就是天理,故朱熹以“仁”为“爱之理”。“爱”是情,“仁”则是支配情的理,也是性,不管人心是否能爱,仁性都在那里。换言之,人心有恻隐羞恶之时,也有刻薄残忍之时,但不论人心如何表现,爱之理只在那里。所以说:“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为心。人未得之,此理亦未尝不在天地之间。”[6]2440“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7]1511
所以,朱熹虽从爱上说仁,但不能说仁就是爱,朱熹时时留意提醒仁不是爱,仁是“爱之理”。“信不足以尽诚,犹爱不足以尽仁。”[6]103“仁是根,恻隐是萌芽。亲亲、仁民、爱物,便是推广到枝叶处。”[6]118仁不离爱,但爱不足以尽仁;仁是根,爱是苗,苗从根上发出,没有苗便不容易感知到根,但不能说苗就是根;仁是体,爱是用,爱从仁里发出,但不能说爱就是仁。
在朱熹看来,“仁”虽说是“理”,却不能只以“理”说“仁”,否则会流于呆板。“仁”也是天地浑然温和之气,是“心之德”。这又是从宇宙界下而降接于人心。天地阴阳之气流转不已,春夏秋冬,虽分为四截,但究其实只是一气之流转。正如“仁”为心之德,虽分为仁义礼智四个名目,但究其实只是仁一德之流转。故其云:“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7]1511“仁字如人酿酒,酒方微发时,带些温气,便是仁;到发到极热时,便是礼;到得熟时,便是义;到得成酒后,却只与水一般,便是智。”[6]111简言之,人心之德与天地之气、自然之序皆是有联系的。仁与天地之理贯通,义礼智与仁贯通,人心与自然只是一体。
朱熹说:“‘见孺子匍匐将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处见得亲切。圣贤言仁,皆从这处说。”[6]119赤子匍匐入井,人心有怵惕恻隐之动,惟在此人心一动之间,人才能深刻感受到内在的仁性。所以,仁虽为理、为情,但就人身来说,心才是最直接感受仁、领悟仁的地方。仁无形体,情有善恶,只有人心最初的萌动,才能使人深刻而真切地感受到仁性,所以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公孙丑上》)。因此,朱熹既说仁是“爱之理”,又补之以“心之德”。“心之德”即指人心不为物欲、利害所蔽锢,能时时刻刻保持醒着、能知觉的状态。
朱熹注解“四端之心”时,引程明道之说:“满腔子是恻隐之心”[5]239。朱熹解释说:“精气周流,充满于一身之中,嘘吸聪明,乃其发而易见者耳。”[6]42人之一身之内,只是精气周流;精气周流充满于一身之中,所以鼻能知臭,口能知味,耳能知声,目能知色。人之知觉运动,皆是精气使然。然此精气并非人所独有,或人所自创,而是内在于人身的天地之气。“看得到这里,见一身只是个躯壳在这里,内外无非天地阴阳之气。……如鱼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里面水。鳜鱼肚里水与鲤鱼肚里水,只一般。”[6]40正因如此,人才能敏锐地感知天地万物的痛痒,即“知觉”。“只是满这个躯壳,都是恻隐之心。才触着,便是这个物事出来,大感则大应,小感则小应。恰似大段痛伤固是痛,只如针子略挑些血出,也便痛。”[6]1283达到此状态,必是割除了任何私意,达到“心即理”的境界,只有圣人能保持这种高度敏感的心理状态,而这也就是儒家的最高境界——“仁”。
总之,朱熹在对《孟子》的阐释中,以“仁”字绾合宇宙界与人生界,贯通天人。钱穆称其为“理气一体之宇宙观”[2]38,丸山真男称为“连续性宇宙观”[8]33,子安宣邦称“‘天人关系’之思维系统”[9]91,三宅正彦称“社会与自然相统一的世界观”[10]9,这都体现了中国儒学特有的精神传统和认识世界的方式。
二 伊藤仁斋对朱熹的反驳及其意义
仁斋认为“仁”是《孟子》的主旨:“孟子之学,……以仁义为宗,以王道为主。而所谓王道者,亦由仁义而行。”[11]孟子古义总论仁也是传统儒学的核心:“圣门学问第一字是仁。”[4]213但他不认为仁是“爱之理”,而是实实在在的爱。他说:“慈爱之心,浑沦透彻,从内及外,无所不至,无所不达,而无一毫残忍刻薄之心,正谓之仁。存于此,而不行于彼,非仁也。施于一人,而不及于十人,非仁也。”[4]216又说:“仁之为德大矣,然一言以蔽之,曰:爱而已矣。在君臣谓之义,父子谓之亲,夫妇谓之别,兄弟谓之叙,朋友谓之信,皆自爱而出。”[4]215朱熹不得“仁”之真义的症结在于持“理”求仁。“后人之学,先以穷理为主,是仁之所以难识也。”[4]21
仁斋认为宋儒之所以体贴出“理”,是接受了佛学追问本体思维方式的影响。“夫万物本乎五行,五行本乎阴阳,而再求夫所以为阴阳之本焉,则不能不必归之于理。此常识之所以必至于此不能不生意见,而宋儒之所以有无极太极之论也。”[12]3因此,仁斋断定宋儒为“禅儒”[4]233,其“理”说杂合了佛学教义:“朱子之学,本自禅庄来,故以理为本,而以气为粗,为善恶杂。”[13]实际上,正是宋儒体贴出“理”,才使“仁”会通宇宙界与人生界(1)钱穆先生认为,朱熹论理气、心性等都分为宇宙界与人生界两部分,如理气论,“从宇宙界说,是理在气先;从人生界说,则又气在理先。”(钱穆.朱子新学案[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40)。“宋明儒对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正在于这一点,在其能把佛学全部融化了。”[14]168因此,仁斋对“理”的否定实际上取消了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联系,进而把天道与人道分开,“爱之理”与“心之德”分开,从而使得仁只成为人世间的道德法则和情感表现。
进一步,仁斋认为“仁”与宇宙、禽兽、草木等关涉不大,只是日常生活之间真实无伪的人伦情感,即只能在人道的基础上说仁。而其理论基础则是分离天道与人道。他否认“理”,宣称要恢复孔孟古义,实际上所追寻的是符合日本人文化心理和制度传统,以人伦日用为特色的儒学新解。仁斋认为“道”有大道、常道之分。大道为三皇五帝之道,讲天理、天道。常道为尧舜之道,只讲人伦。后世人之所以只知常道,不知大道,就在于孔子黜大道、明常道的不世之功。“然而夫子定特断自尧舜,而虽上三皇五帝之书,犹在所黜焉,……于是天地之道明,人伦之法定,民无所惑焉。”[15]所以,孔孟所说的道,只是“常道”,即日常生活中不可须臾离开的人伦之道,“故人伦之外无道,仁义之外无学。”[12]87仁斋虽否定大道,但并非不言天道,与宋儒不同的是,仁斋认为天道与人道彼此独立。“《说卦》明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不可混而一之。其不可以阴阳为人之道,犹不可以仁义为天之道也。”[12]13天道为阴阳之气运转不已,人道为仁义之德行于天下,人道之仁义与天道之阴阳,在语义上不存在相互对应的关系,在义理上也不存在相关贯通的关系,二者互不相干。
所以,仁斋嗣子东涯说:“仁者人之道也,然仁不自仁,非人则无以见仁。人不自人,非仁则无以为人。以人而行仁,是之谓道。”[16]人与仁不可分离,仁只是人世间的道。仁不是所谓的“爱之理”,只是人与人相亲相爱的朴素亲切的情感,这就是仁斋“慈爱之德”的确义。扩展来说,以爱释仁是德川时代儒者的共同特点,“德川儒者之重‘情’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现象,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仁斋之‘仁说’何以突出强调一个‘爱’字的缘由。”[17]
质言之,仁斋古义学在分立天道与人道的基础上,舍弃了中国儒学中对于天人关系的思考,只采取了其中有关人伦情感和伦理关系的部分。这可以透露出仁斋及德川儒学在吸收中国儒学时所持有的标准:即以是否具有指导社会生活和制度建设的实用性为标尺。“仁斋用来甄别圣人是否绝对伟大的标准,是看他们的思想是否切合人伦日用,是否有益于天下国家之治。”[18]1229事实上,德川儒者以实用性态度取舍儒学的作法,在日本历史上并非孤例,日本儒学发展史上著名的圣德太子《十七条宪法》和大化革新亦是如此。“从历史进程来看,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604年)和大化革新,主要是搬入当时在世界上颇为先进的唐代的政治社会制度,亦即儒家礼制体系和与之相关的儒家的政治、伦理、道德观念。……在这里,儒学主要作用在于‘维持’社会‘秩序’的外在‘执行’性(如士、农、工、商的等级制)。”[19]291这种不究其精神实质、以实用性选择文化的态度,是日本民族面对外来文化时的典型态度,因此,它不仅在江户时代迅速将儒学转化为推动社会兴盛的工具,从而助推了江户时代的繁盛,也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民族能够迅速从传统中转型,吸取西方文化中的有用部分,从而实现经济腾飞和社会转型的文化心理基础。正如李泽厚所言:“这种否定阴阳五行的理性框架,只肯定感受经验的态度,正是日后比中国更无阻碍接受西方自然科学的张本。”[19]300
进一步来说,仁斋虽以爱释仁,但认为“仁”不是个人的私情小爱,更是推己及人,将一己好恶推达于天下的公共之爱:“王天下,则及天下。君一国,则及于一国。主一家,则及于一家。为父,则及于其子。为夫,则及于其妻。为兄,则及于其弟。”[4]216从这个意义来说,仁斋之仁是现实社会中的博爱,是遍及天下的公共之爱。正因如此,仁斋非常赞同韩愈“博爱之谓仁”的说法:“问:韩子《原道》曰:博爱之谓仁,宋儒深非之,如何?曰:……夫博爱之未足为仁者,正在于生熟大小之间,而非性情之别。”[4]218
朱熹与仁斋之“仁”都包含有将爱推己及人的公共性,但其间含义差异巨大。朱熹之“仁”是对天地万物保持高度敏感的大爱,是具有公共性的,这一点被仁斋所继承。但不同的是,朱熹“心之德”内有理存在,仁不止是对人世间伦理秩序、祸福兴灾之爱,更是对草木虫鱼、风云雷电,乃至六合之内、六合之外天地万物的大爱;其背后的思维模式正是将人之德行、情感(仁之爱)视为对天地德行(仁之理)的模仿和继承的理气一体的世界观;更深一层,其思想背景是中国人视天地万物与人为一体的传统天人一体思想。而仁斋之爱只局限在人世间,与宇宙、草木、禽兽没有任何关联,并且,人心与事功之间的关系开始松弛,即事功大小不再取决于人心是否公而无私,只要能够取得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实际效应,都是“仁”。这反映了宋儒将“理”、心与事功联系起来的整体性思维方式的解体。“这是把圣人之仁与管仲之仁‘等量’齐观。与作为仁的必要条件无私心这种个人的动机相比,仁斋更重视的是民众受到福利的社会成果。……由此,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朱子学连续性思维结构的解体,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勇往直前。”[8]38
可以说,仁斋及德川儒者只重取儒学的实用性的态度,一方面使儒学能够迅速转型为伦理工具,快速而有效地作用于社会治道;另一方面也说明,与中国儒学浸润了中国人的思想情感、行为方式不同,日本儒学对塑造日本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的作用是有限的,即它只在实用制度和社会礼法规范的领域发挥了作用,而并未成为日本民族深层的集体意识形态组成部分,并未真正支配日本民族对人、社会、自然及其关系的认识。例如,德川儒学的适用范围被严格设定在幕府文化统治手段以及改造日本社会的伦理工具上。“日本儒学则仍只是一套只有特定功能的文化学说,它从未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意识和正统的信仰体系。即使在它被幕府采纳为必须在国立学校里讲授的国教并成为江户朝廷的国学时,它仍然也只是有助于达到江户的政治目的的一套文化学说。”[20]457更深一层来说,日本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其实是本土源远流长的神道,即以天皇神崇拜为核心的“大和魂”。以天皇神崇拜为特征的人格神信仰既是日本天人分立思想产生的根源,也是日本儒学舍弃天人一体思想的根源。“神道主要‘教义’既在对众多神灵、特别是天皇(现御神)的宗教性的敬畏崇拜,因之中国儒学中非人格神的天道论包括阴阳五行说(汉儒),和非人格神的本体论如天理人欲论(宋明理学),就并没有为日本儒学所真正重视和接受。”[19]295李泽厚认为神道影响下的日本民族文化心理有两大特征,即“神秘主义与经验论(亦即非理性与重实用)”[19]292,因此,仁斋以实用态度阐说仁,正是神道重视“经验论”的体现。朱熹与仁斋对仁的不同理解、阐释,既透视出儒学对中日民族的不同影响,也看出两个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文化传统和对于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把握,从而理解其在历史道路、中西文化、社会制度上作出不同选择的思想端倪。
三 结语
子安宣邦认为,以儒家经书的重新解释为基础的儒学学问再生产方式是东亚儒者的共同特点。“儒学的学问再生产方式,大都是通过将读解限定于经书文本及其注释者的解释文本的‘内部’,从而不断对儒学进行重构的作业。”[9]85如朱熹通过重新阐发《四书》来构建理学思想体系,伊藤仁斋通过重新解释《论语》《孟子》来构建古学。这种经典的学问生产方法诞生于中国儒学,德川儒者不能不受其影响,进而成为东亚范围内共同的学问生产方法,从而奠定了以经书为核心的东亚精神传统、思想传统,维护了儒家精神在东亚文化圈内的主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对东亚思想传统、精神传统乃至民族性格形成的意义是重大的。
但仁斋及德川儒学特殊性在于,他们一方面接受了儒学的方法,以注释经典的方式阐发新思想;另一方面,在恢复孔孟原意的旗帜之下,跳出了天人一体的思维模式,以日本神道支配下的实用性思维来思考问题,从而产生了异于中国儒学的异质因素。尽管如此,仁斋不能不流露出朱子学的影响,即这种解经方式实际上并非汉唐儒学字义训诂的方法,而是以字义解释和经典注疏为桥梁,对儒学经典作思想史意义上的新解,从而建立古义学基本框架的学术操作。因此,仁斋突破汉唐儒学字义训诂方法、寻求儒学义理的古义学策略正是对宋学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儒学创新发展的趋势与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