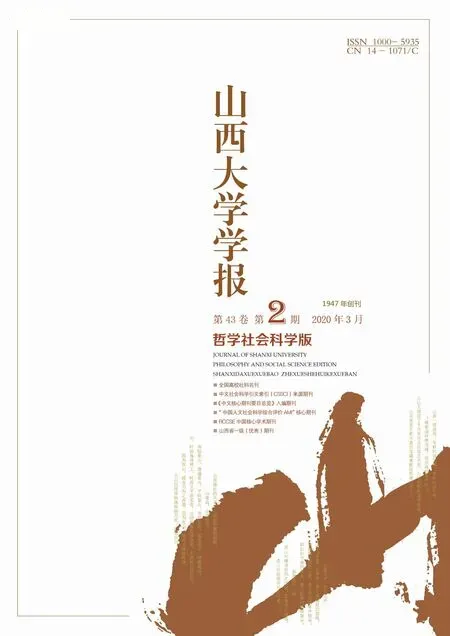山西方言研究70年
王晓婷,乔全生
(1.山西大学 语言科学研究所,山西 太原 030006;2.华中师范大学 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9)
山西地处华北黄土高原、黄河流域中游,因居太行山之西而名,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山西方言作为黄土高原、黄河流域的一支古老方言,无论就其形成的历史,还是所保留的古代语言、古代文化成分,在汉语发展史、中国文明史上均占有突出的地位。山西境内的主要语言类型晋方言是全国汉语十大方言之一,特色鲜明、独具魅力,一直吸引着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和调查。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代山西方言学人致力于山西方言研究,殚精竭虑,薪火相传,其影响力和辐射力不断扩大。由初创、探索走向兴盛、辉煌,具体表现为研究成果数量多、质量高,研究团队力量强、设备全,研究课题内容广、视野新。据统计,70年共出版方言著作199部、发表论文1 952篇。及时、全面地总结70年来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必将有利于山西方言研究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更高质量迈进。
本文将70年来山西方言研究划分为四个时期,分别为:初创与探索期(1949—1965),萧条与停滞期(1966—1977),恢复与提升期(1978—1998),兴盛与辉煌期(1999—2019)。
一 初创与探索期(1949—1965)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迅速实现各领域的现代化,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大力普及文化教育,推广普通话是大力普及文化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为配合推广普通话,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规模空前的方言普查工作,在这个大潮的推动下,山西方言普查工作也随之展开。此次普查是山西历史上第一次全省范围内大规模的方言调查,以田希诚、杨述祖为主要负责人,1958年底共完成97个方言点调查工作。1960年,由田希诚执笔,开始编写《山西方言概况》(以下简称《概况》),语音部分于1961年10月完成初稿并油印交流。《概况》将山西方言划分为四个方言区,归纳总结了山西方言11条语音特点,分区列出所属各点的声韵调对照表,绘制了山西方言地图22幅。[1]《概况》第一次大面积反映了山西方言语音的主要特点,是对山西方言全貌的初步调查和研究,为后来大规模调查和描写山西方言奠定了基础。北京大学中文系师生分别于1959年、1964年两次来山西进行方言调查实习,其调查材料已成为山西方言研究的重要成果。
本时期的山西方言研究主要为配合推广普通话服务,内容上多为山西方言与普通话的比较。相关论文有9篇,如:王立达《太原人学习普通话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956)、《山西方言中的声调与普通话的对应关系》(1958),田希诚《晋东南语音和北京语音的差别》(1956),赵秉璇《晋中、太原、榆次、清徐等地的方音与北京语音的比较》(1958),胡双宝《山西文水话和普通话语音、词汇的比较》(1959)等。
通过与普通话比较,山西方言的独特性越发突显,这一时期也发表了10余篇以山西方言为主体的研究成果,由于正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成果多为单点方言的零散调查研究。涉及语音的有:SiuLin《晋南方音的几个例子》(1955)、王立达《太原方言中的“文白异读”》(1958)、赵秉璇《太原话中的促音韵尾和入声》(1963)等;涉及词汇、语法的有:王迅《晋南方音中的“疙k”》(1959)、王立达《太原方言词汇的几个特点和若干虚词的用法》(1961)、田希诚《运城话的人称代词》(1962)等。另有日本野村正良《山西诸方言“明”、“泥”、“娘”、“疑”母の头音》(1951)、仓石武四郎《晋南的方言资料》(1953)等。
二 萧条与停滞期(1966—1977)
从1966年开始,受政治因素影响,山西方言研究一度陷入萧条期,研究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本时期国内未见山西方言研究的论著。国外有日本桥本万太郎的《晋语诸方言の比较研究》,该书是作者50年代在日本找人调查,1976—1977年陆续发表在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亚非文化研究》12—14别册上。全书共分三部分,前两部分为语音描写和分析,后一部分为词汇、语法比较。语音部分列有山西朔县、五台、汾阳、安邑(今运城)4个方言点方言的音系和声韵调配合表,并对其声韵特征进行了历时对应,对鼻音声母后带有同部位塞音、安邑话与关中方言相近等特点进行了分析解释。[2]
三 恢复与提升期(1978—1998)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各领域进入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山西方言研究也迅即恢复,出版了多本县域方言志。根据山西方言已有调查研究成果,李荣先生在《官话方言的分区》(1985)中将“晋语”从北方官话中分立出来,列为全国汉语十大方言之一。晋语的分立,大大促进了山西方言研究。这个时期山西方言研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以详尽的共时研究为主,注重单点方言的专题研究,揭示山西方言的重要特点。据统计,这20年共出版方言志41种(每种10万字)、词典3部、著作15部、论文集3部,共发表论文367篇;先后成立了山西省语言学会、山西省方言学会,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交流山西方言研究成果;创办了山西省语言学会会刊《语文研究》(现已成为山西省社科院主办的语言学重要学术期刊);举办了首届晋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现已举办到第六届),为国内外山西方言研究学者提供学术交流平台;培养了一支方言研究队伍。下面在概要介绍几种重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从方言语音研究、方言词汇研究、方言语法研究、晋方言的分立、方言与民俗研究五个方面对本时期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
温端政主编的《山西省方言志丛书》(1982—1996)是配合山西省各县市地方志的编纂工作而完成的各县市方言调查报告,共出版41种,每种10万字。内容包括:导言、语音分析、同音字表、方言语音与北京话语音的对应关系、分类词表、语法特点、语法例句、标音举例8个部分。[3]该丛书以记录和分析某个方言点的方言事实为主,采用统一体例,集中反映某方言的重要特点,对山西方言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奠基作用,为其后晋方言的分立提供了比较充分的依据。
侯精一、温端政主编的《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1993)是“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山西方言通志”的结项成果,全书约122万字,分上、下两卷,共22章。上卷是对山西方言整体情况的描写,介绍了山西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特点,用方言地图展现出山西方言内部差异。下卷将全省方言分为中区、西区、东南区、北区、南区、东北区6个区。先说明各区方言的总体特点,再分别列出各区中各点方言的语音系统,附山西方言地图31幅。[4]该书的出版标志着山西方言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方言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侯精一主编《现代汉语方言音库》(1994—1998)是“九五”期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结项成果,选取了全国具有代表性的方言40种,其中包括山西方言两种,分别为乔全生、程丽《平遥话音档》(1997),沈明《太原话音档》(1997)。每种音档编写体例基本一致,包括语音、常用词汇、构词法举要、语法例句、长篇语料5项内容。[5]该成果附录音光盘,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有声语料,也“结束了我国汉语方言的出版物仅停留于书面描写各地方言现象的历史”[6]。
(一)方言语音研究
这个时期山西方言语音研究主要集中在入声(包括入声调及入声韵)、文白异读、变调等方面。
1.入声研究
晋方言的主要特点是保留入声,晋方言从官话中分立出来的最主要的依据就是因为保留了入声,因此,这一时期山西方言入声研究成果比较集中。根据研究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1)山西方言入声的整体特点和发展趋势。杨述祖概括山西方言入声有三个特点,即:声调大都短促、有[-]尾、入声韵自成系统。入声的发展趋势是逐渐向普通话靠拢。[7]温端政认为山西方言的入声“多数读得短促”,“也有的拉长”;“有喉塞尾”,但也有“舒促相互转化”的现象;“入声韵自成系统”,但“入声韵母的数量不等”,“有的分阴阳,有的不分阴阳”。[8]山西方言入声的发展趋势,除“向北京话的方向合并”外,还有另外两种变化路径:一是阴入、阳入先行合并,再并入调值相近的舒声;二是阴入、阳入分别向调值接近的舒声合并。这些观察丰富了山西方言入声的特点及发展趋势的内涵。
(2)山西方言入声的历时演变。马文忠《中古入声字在大同方言的变化》(1984)、张益梅《介休方言的入声字和古入声字的比较》(1986)、王洪君《入声韵在山西方言中的演变》(1990)等,从历时角度描写分析了中古入声字在今山西方言中的变化。
(3)利用山西方言入声探求汉语入声的历时演变。潘家懿《从交城方言看汉语入声演变的历史》(1982),根据交城方言入声的四个特点:喉塞尾不明显,入声字数量正在不断减少,入声调出现调值变体,阴入、阳入混读、界限不清,得出汉语入声消失是必然的结论。[9]金有景《山西襄垣方言和〈中原音韵〉的入声问题》(1989),利用山西襄垣方言的入声,探求早期北京官话是否存在入声及入声的变化情况。[10]
(4)舒声促化。保留入声是晋方言的重要特征之一,山西方言中还有舒声促化后读同入声的现象,这也是这一时期山西方言研究所关注的焦点。如:马文忠《大同方言舒声字的促变》(1985)、《大同方言入声字两读详例》(1994),王希哲《左权方言古入声字今舒声化现象》(1996),曹瑞芳《山西阳泉方言入声舒化的初步分析》(1996),李小平《山西临县方言舒声促化现象分析》(1998)等,对山西方言中的舒声促化现象均作了细致描述,并对其成因进行了探析。
2.文白异读研究
徐通锵说过“文白异读是方言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产物,文白之间的竞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音类替代是语言演变的一种重要机制”[11],因此,文白异读对于深入研究方言的历史层次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山西方言中存在着大量的文白异读,“《切韵》音系的音类,绝大多数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文白异读,除闽方言以及与它接壤的一些地区的方言外,汉语方言中的文白异读恐怕就数山西方言最丰富、最复杂了”[11]。本时期的研究已经意识到山西方言文白异读的重要意义,发表了多篇论文,根据内容可将其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对单点方言文白异读现象进行共时研究。李守秀《榆次方言的文白异读》(1980),田希诚、吕枕甲《临猗方言的文白异读》(1983),张益梅《介休方言文白异读初析》(1983),侯精一《平遥方言的文白异读》(1988)等,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分别描写了榆次、临猗、介休、平遥方言中声母、韵母的文白异读现象。侯精一、杨平《山西方言的文白异读》(1993),对整个山西方言的文白异读进行了综合描写[12]。王临惠《临猗方言的文白异读》(1997),不仅记录了临猗城关话中的文白异读现象,还对其分布条件和特点作了概括性描写[13]。
(2)通过分析文白异读读音,反映语音层次、判定层次时间。王洪君《山西闻喜方言的白读层与宋西北方音》(1987),利用历史层次分析法,离析闻喜方言的白读层和文读层,通过对白读层与宋西北方音的比较,认为闻喜方言的白读层反映了宋西北方音的特点,“宋代西北地区和山西南部的方音同属一个系统”[14]。
3.变调研究
本时期山西方言的变调研究主要集中在连读变调上,也有对子尾变调、变韵及其他变调的描写。
首开连读变调研究先河的是侯精一在1980—1982年间连续发表的《平遥方言的连读变调》(1980)[15]、《平遥方言三字组连读变调》(1982)[16]、《平遥方言广用式三字组连读变调》(1982)[17]系列论文。这些论文对研究山西方言的连读变调起到了示范作用。其后陆续有吕枕甲《运城方言连读变调的若干规律》(1989)、孟庆海《阳曲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1991)、江荫褆《朔州市朔城区方言的连读变调》(1991)等论文发表。这样,山西南、中、北部的方言均有连读变调的论文问世,掀起一个讨论连读变调小高潮。
沈慧云《晋城方言的“子尾”变调》(1983)[18]、米青《垣曲方言用变调表示子尾》(1988)[19]194-195,描写了晋城、垣曲方言中一种特殊的子尾变调现象,即普通话中的子尾词在这些方言中不用后缀“子”表示,而是采用词根变调方式来表示。
马文忠《大同方言的重读变调》(1995),描写了一种非因语流产生的变调现象,即在强调、反语或独字用于答句等情况下需要重读这个音节而产生的变调现象,[20]丰富了山西方言的变调类型。
这一时期,除了对山西方言语音事实进行全面共时研究外,徐通锵、王洪君致力于山西方言语音与普通语言学理论相结合的研究,不仅为普通语言学理论提供了鲜活的方言例证,也为山西方言研究注入了新的理论血液。如:徐通锵、王洪君《说“变异”——山西祁县方言音系的特点及其对音变理论研究的启示》(1986)、《山西闻喜方言的声调——附论“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1986)等。还有的论文对山西方言语音史进行了初步探讨,如:陈庆延《晋语的源与流》(1996)、徐通锵《山西方言古浊塞音、塞擦音今音的三种类型和语言史的研究》(1990)、王洪君《阳声韵在山西方言中的演变(上、下)》(1991、1992)等。
(二)方言词汇研究
这个时期山西方言词汇研究成果非常丰富。综合研究的论文有:温端政《太原方言的词汇》(1981)、陈庆延《山西方言几个点的词汇特点》(1985)、侯精一《平遥方言词语研究》(1989)、田希诚《山西方言词汇调查笔记》(1990)、吴建生《山西方言词汇异同例说》(1992)等,综合描写了单点或整个山西方言的词汇特点。著作有:王雪樵《河东方言语词辑考》(1992),记录、考证了河东地区的方言词汇,每个词目下列出方言的拼音、再释义并指出这个词的来源、变化及在河东各县市的异同。释义引用《尔雅》《方言》《说文解字》和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唐宋笔记、小说直至元明清戏曲、传奇、平话等文献[21],考证细致,多数是可信的,但也有部分欠妥。
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994)分卷本中有3本是山西方言点的词典,分别为:沈明《太原方言词典》,温端政、张光明《忻州方言词典》,吴建生、赵宏因《万荣方言词典》。三种方言词典内容和体例统一,包括三部分:引论、主体、索引,主体部分收录本方言特色词汇8 000余条,每个词目后加注国际音标、义项释义和例句。[22]这三本方言词典的出版为山西方言词典编写提供了范例,标志着山西方言词汇调查的新进展。
专题研究主要集中在词头、词尾、分音词、合音词、逆序词、古语词、四字格等方面。
1.词头和词尾研究
词头研究以对“圪”的性质及“圪”头词的词性研究最为突出,成果也最多。如:宋秀令《汾阳方言中带“圪”音的词》(1983)、韩振玉《文水方言“圪”字词例释》(1987),将方言中丰富的“圪”头词,按成词后的词性进行分类汇释。韩文认为有的“圪”与词义有关,有的与词义无关,只是同音字[23]。白平《“圪”非词头辨》(1988)认为,“圪”非词头,实则为前字的音转。[24]赵宏因《夏县话里“圪”的用法》(1991),指出“圪”的基本用法是作词头或词嵌,可构成名词、动词、形容词、量词和象声词等,“圪”仅仅起表音作用,本身并无具体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25]。任林深《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1991),注意到了闻喜方言中除有与晋中方言相同的“圪”外,还有“古”,通过对其构成词汇进行考察,发现选择哪个词头成词受后字声母的影响,二者是互补关系[26]。马文忠《晋方言里的“圪”》(1995),在综合各单点方言“圪”头词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将山西晋方言中的“圪”分为“实语素”“虚语素”和“非语素”三类,其次对“圪”头词的构成形式及语法意义进行细致分析,最后还对虚语素的“圪”字进行了简单探源,认为是古晋地随着民族融合而进行的语言融合的产物[27]。
少数论文涉及“圪”的历时研究,如:邢向东《晋语圪头词流变论》(1987),认为晋方言中的派生圪头词是由单纯圪头词产生,而单纯圪头词则是上古复辅音析音化的结果[28]。乔全生《晋语附加式构词的形态特征》(1996),详细描写了“圪”的构词形式、表义作用和语法功能,从语言接触的角度对“圪”字探源,认为“圪”可能来源于山西历史上某个少数民族语言的底层词[29]。
词尾研究主要集中在“子”“儿”等上,如:侯精一《晋东南地区的子变韵母》(1985)、田希诚《山西和顺方言的子变韵母》(1986)、徐通锵《山西平定方言的儿化和所谓的“嵌l词”》(1986)、杨述祖《太谷方言的儿韵、儿尾和儿化》(1991)、王临惠《临猗方言的子尾与子变韵母》(1993)等。乔全生《山西方言子尾研究》(1995),描写了山西方言子尾丰富的读音形式(包括子变韵)及富有特色的语法结构、语法意义,并与北京话进行比较,得出山西方言子尾具有“对内一致性和对外排斥性”[30]的特点,是对山西方言子尾进行全面描写、综合研究的佳作。
关于词缀研究的还有:吕枕甲《垣峪话里的语素“头”》(1982)、赵宏因《稷山话中的词缀“日”和“人”》(1989)、马文忠《晋北方言的“灰”》(1991)、乔全生《山西方言的几个詈词后缀》(1996)等,通过对山西方言中特殊词缀进行描写分析,丰富了山西方言词缀研究。
2.分音词、合音词和逆序词研究
山西方言存有大量的分音词、合音词和逆序词,如:“杆”说成“圪榄”,“这个”说成“宰=”,“气味”说成“味气”,这些特色词汇也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之一。相关论文有:赵秉璇《晋中话“嵌l词”汇释》(1979)、吴静《万荣方言的合音词》(1995)、张光明《忻州方言的逆序词》(1994)。这些论文将山西方言的分音词、合音词及逆序词进行汇释,用国际音标注音、普通话注释,给出了方言用例。赵秉璇《切脚词、嵌l词、反语骈词——兼与徐通锵先生商榷》(1983)、董树文《晋中话“嵌l词”与北京话对应词的比较》(1983),通过将山西方言的“嵌l词”与福州方言的切脚词、北京话的对应词进行比较,展现了山西方言词汇的独特性。
3.古语词研究
山西方言作为一支古老方言,保留了大量的古语词,有的至今还保留着古义,有的虽然词形相同,但意义已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了变化。这个时期山西方言古语词研究多是汇释性的,如:李守业《山西文水话所见元曲词语释例》(1983)、陈庆延《山西稷山话所见宋元明白话词语选释》(1984)、潘家懿《临汾方言里几个保留古义的口语词》(1985)、潘耀武《清徐方言中所见早期白话词语选释》(1992)等,摘录了方言中保留的古语词,并给出释义、列出方言例句,对研究方言词义演变很有参考价值。
4.四字格研究
本时期共有5篇汇释山西方言四字格的论文,如:侯精一《平遥方言四字格释例》(1980),收录平遥方言的特殊四字格词语,先做简要注释,然后列出方言例句[31]。
(三)方言语法研究
山西方言语法研究在这一时期起步,多以共时研究为主。根据研究内容,可分为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
综合研究的成果有:潘家懿《交城方言语法特点》(1981),郭正彦《晋中方言的特殊语法现象》(1981),胡双宝《文水方言的若干语法现象》(1981),田希诚《临汾方言语法的几个特点》(1981)、《和顺方言语法的几个特点》(1985),侯精一《平遥方言语法研究》(1989),李小平《临县方言的语法特点》(1990),吴建生《万荣方言语法的两个特点》(1991)等。
专题研究主要集中在代词、重叠、句法结构、助词、形容词、量词等方面。
(1)代词研究。综合研究的成果有:乔全生《洪洞话的代词》(1986)。对代词再分类进行研究的有10余篇之多,如:杨增武《山阴方言的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1982)、米青《指示代词三分说法补例》(1986)、沈慧云《晋城方言的指示代词》(1986)、宋秀令《汾阳方言的指示代词与疑问代词》(1994)、乔全生《山西方言人称代词的几个特点》(1996)等,分别对单点方言中的一类或两类代词做了详细描述与分析。
(2)重叠研究。综合论述的有:吕枕甲《运城方言重叠式的韵律特征》(1988),从韵律的角度研究运城方言重叠式的构成形式与语义语法功能的关系[32]。侯精一《平遥方言的重叠式》(1988),从构成形式和语法意义上描写了平遥方言的名词、量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象声词及数词的重叠式[33]。分类论述的有:宋秀令《汾阳方言的叠音名词》(1996)、李小平《山西临县方言AA式名词的构词特点》(1997)等,分别对重叠式的读音、构词特点及语法功能进行了描写。
(3)句法结构研究。这一时期的句法结构研究主要为由动词构成的句法结构,如:侯精一《平遥方言的动补式》(1981),马文忠《大同方言的动趋式》(1986)、《大同方言的“动词+顿儿”》(1987)等。还有一些论文涉及对句法结构来源的分析,如:乔全生《洪洞话的“VX着”结构》(1989)、《山西方言的“V+将+来/去”结构》(1992)等。
(4)助词研究。以单点方言助词研究居多。综合研究的有:李守秀《榆次方言的助词》(1982)等;专题研究的有:宋秀令《汾阳方言中的“的”》(1988)、吕枕甲《运城方言两个表时间的助词》(1993)、马文忠《大同方言语助词“着”》(1992)等。乔全生《从洪洞方言看唐宋以来助词“着”的性质》(1998),从山西洪洞方言及其他语言材料出发,着重对唐宋以来“着”的动态助词性质做出界定[34]。
(5)形容词研究。李鼎龙《万荣县西话形容词表程度的三种形式》(1983)、李守业《文水话形容词的复杂形式》(1983)、任林深《山西闻喜话形容词的生动形式》(1986)、侯精一《山西平遥方言的状态形容词》(1992)等,分别对各单点方言中形容词表示性质或状态的程度加以描述。
(6)量词研究。陈庆延《稷山方言的量词》(1981)、胡双宝《文水话的量词、代词和名词》(1981)、宋秀令《汾阳方言的量词和特殊的数量词》(1996),描写和分析了稷山、文水、汾阳方言量词的特点。
其他词类研究。介词研究,如:任林深《山西闻喜话常用介词例释》(1988)等;语气词研究,如:宋秀令《汾阳方言的语气词》(1994)、崔淑慧《代县方言的几个语气词》(1998)等。其他特殊词研究,如:乔全生《洪洞话的“去”“来”》(1983)、《河东方言片的独立词“可”》(1995),田希诚《临猗方言中“走”的语法特点》(1998)等。
(四)晋方言的分立
1985年,李荣先生在《官话方言的分区》中首次将“山西省及其毗连地区有入声的方言”[35]从官话中分立出来。1987年,《中国语言地图集》将汉语方言分为十大区,晋方言成为与官话等其他九大方言平行的大方言。对于晋方言分立观点的大讨论,大大推动了山西方言的整体研究。
晋方言分立问题讨论的热点有二:一是晋方言立区的依据和标准,二是立区后的“级别”问题。不同意将晋方言作为与官话平行的方言之一、同意作为官话一支次方言的有丁邦新、王福堂等,赞同晋方言分立观点的有侯精一、温端政、张振兴等。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和新编教材词典看,晋方言分立已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我们认为,只要深入挖掘山西方言的特点,对晋方言的现实和历史均搞清楚,层次的安排就会迎刃而解。
晋方言的范围同样也是立区后讨论的重点,根据晋方言是“山西省及毗邻地区有入声的方言”,由此,晋南地区20多个无入声的县市划归中原官话。学界基本赞同这一说法。提出不同观点的有侯精一、王福堂、李蓝等,他们认为除入声外,划归中原官话的晋南方言还保留着晋方言的很多重要特征,如文白异读等,将这些方言划归晋方言才不失晋方言本身的完整性。同样,在晋方言内部,划归吕梁片的永和、大宁、隰县、蒲县、汾西方言因其多数特征与晋南方言相同,其归属也是讨论的重点,如:乔全生《汾西方言的归属》(1990)等(1)吴建生《蒲县方言的归属》(2003)、王晓婷《山西西南部地区方言语音研究》(2017)发表时间虽不在此时期,但与此处讨论内容密切相关。。
(五)方言与民俗研究
方言与民俗相伴相生,民俗方言词不仅是语言符号,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民俗符号。山西方言与民俗研究由来已久,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们在生活习俗、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差异,都会在语言中找到印证。相关论文有:潘家懿、赵宏因《一个特殊的隐语区——夏县东浒“延话”(隐语)调查纪实》(1986),乔全生《山西方言人名里的原始崇拜遗迹》(1989),潘家懿、李小平《山西的羊文化》(1993),潘家懿、辛菊《山西晋南的馍文化词语》(1996)等。
侯精一《平遥方言民俗语汇》(1995),是研究平遥方言(县城音)民俗语汇的专著。全书收录了平遥方言婚丧、游艺、饮食、交际、自然现象等29类约4 000条民俗词汇。[36]该书不仅为汉语方言词汇研究提供了丰富材料,对人类文化学、社会学、民俗学的研究也颇具参考价值。
四 兴盛与辉煌期(1999—2019)
跨入21世纪,山西方言研究也迈进了新时代的兴盛与辉煌期。20年间,研究成果数量快速增长,质量不断提升;研究团队的专业化水平显著提高,研究内容不断创新,研究方法日益多样。本时期山西方言研究的主要特点有三个:一是对有特色的单点方言进行重点深入研究;二是研究范围由单点方言转向了整个山西方言或晋方言;三是在共时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了以历史文献为基础的山西方言以及山西方言某片区的历史研究,其中语音史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此外还进行了山西方言的应用研究。这20年共出版《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9辑60部、著作52部(专业性的27部、非专业性的25部)、词典6部,发表论文1 575篇(包含硕、博士论文373篇),举办了5届“晋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以下在概要介绍几种重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从方言语音研究、方言词汇研究、方言语法研究、区域方言研究、诗词用韵研究、学科交叉研究、方言与文化研究等七个方面对本时期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
侯精一《现代晋语的研究》(2008),共收录作者论文38篇。其中,大部分论文是对山西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的研究成果,该书是对作者晋方言研究成果的一次总结。[37]
乔全生主编的《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是对山西省内单点方言进行较大规模集成研究的一套丛书。目前已正式出版9辑60部,每部20余万字,走在全国最前列。该丛书以《洪洞方言研究》(乔全生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为蓝本,本着“细致描写,科学分析,突出重点,不拘一格”的原则进行编写,内容包括:方言概说、语音描写、历史音韵、词汇研究、语法专题等方面。[38]张振兴教授(2003)在该套丛书总序中说:“《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的规划,是非常适时的,是很有远见的一个重大举措。”[38]该丛书的出版不仅对山西方言的保存保护起到抢救作用,更重要的是对山西方言的共时、历时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015—2018年,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连续四年承担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山西汉语方言调查”重大语言文化工程专项项目。四年来,首席专家乔全生教授带领团队高质量完成了57个调查点及3个“语言方言文化调查”点的调查和摄录任务,每个点包括1 000个单字、1 200个词汇、50条语法例句及若干歌谣、故事、谚语、戏曲等口头文化条目的音频、视频。结项成果得到了教育部、国家语委、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语委领导的充分肯定。山西语保工程实现了山西方言的有声数字化,对山西方言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作用,也为保护和传承山西方言和山西文化、推动山西省生态旅游事业的发展、促进山西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服务。
(一)方言语音研究
这个时期山西方言语音研究最大的亮点是在共时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了山西方言语音史的研究,其中以文献为基础的山西方言语音史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
陈庆延的《晋语的源与流》(1996)、《晋南方言疑为晋语祖源方言说》(1999)提出构建“晋方言史”;李如龙、辛世彪《晋南、关中的“全浊送气”与唐宋西北方音》(1999)认为晋南、关中方言与唐宋西北方言在送气音特征上是一脉相承的。但他们只是提出了一个构想,罗列了晋南、关中方言与唐宋西北方言“全浊送气”的一致性,并没有真正系统地开展山西方言语音史研究。
2002年,乔全生成功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晋语史研究”,运用鲁国尧先生提出的“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相结合的新的二重证据法”研究晋方言语音史,发表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内容涉及晋方言的声母、韵母、声调以及晋方言与官话方言的比较等诸多方面。结项成果《晋方言语音史研究》(2009),根据唐五代以来的历史文献和多种对音资料,提出“晋方言是唐五代西北方言的直系后裔”“汾河片方言是宋西北方言的延续”“晋方言与官话非同步发展”等重要观点[39]350,是第一项全面、系统地研究晋方言语音史的标志性成果,也是第一部以一个大区方言语音史为研究对象的专著。
2007年,乔全生又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晋方言语音百年来的演变”,以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方音字汇》中所记录7个晋方言点太原、文水、太谷、兴县、晋城、大同、呼和浩特材料为参照,与20世纪中后期的语音现象进行纵向比较,考察晋方言声韵调发展演变过程。阶段性成果有:乔全生、余跃龙《文水方言百年来的元音高化》(2009),余跃龙、乔全生《文水方言声母百年来的演变》(2009),原慧艳《晋城方言百年来入声的演变》(2010),张楚、王为民《百年来兴县方言声母的演变》(2011),乔全生、张洁《太原方言阴声韵百年来的演变》(2011),王为民、乔全生《百年来山西太谷方言入声韵的演变》(2012),蒋文华《呼和浩特方言韵母百年来的变化》(2014)等。结项成果《晋方言语音百年来的演变》(2019)[40],被鲁国尧先生评价为“迄今为止,体量大的方言,出版‘百年演变史’的,独此一家!”“在汉语诸方言的研究中,晋方言史的研究处于‘一流’地位,《晋方言语音百年来的演变》一书的出版是重要‘地标’”。[41]
研究山西方言语音历史演变的论文还有:乔全生、刘洋《三十年来山西长治方言语音的三点显著变化》(2018),蒋文华《三十年来山西忻州方言语音的变化》(2019)等。其中乔全生《语言接触视域下晋方言语音的几点变化》(2019),立足晋方言语音事实,从与历史上阿尔泰诸民族语言接触视域,对晋方言语音调类减少、舌尖塞擦音和擦音声母只有一套、咸山摄舒声字鼻音韵尾脱落三个方面进行了考察,说明这些现象是晋方言与历史上阿尔泰诸民族语言深度接触所引起的语音变化[42]。
语音史的研究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支撑,历史文献是方言语音史研究的坚实基石,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山西方言语音史研究的深入,历史文献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
2010年,以乔全生为首席专家,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近代汉语方言文献集成”。该项目已于2019年1月顺利结项。八年来,首席专家及14个子课题负责人收集到了从晚唐五代至1949年全国汉语十大方言区的原始汉语方言文献1000余种,实现并达到了“使散见的文献集中起来,使罕见的文献常用起来,使孤本的文献共享起来,使隐性的文献彰显起来”的总体目标,真正体现出“集全国之力,尽地利之便,成文献之全,显学术之威”的实际效果。其中包括的山西方言历史文献12种(含域外方言文献1种),为山西方言语音史的研究提供了文献支撑。相关论文有:韩沛玲《山西方言音韵研究》(2012),赵祎缺《〈乡音正误〉所载山西方音研究》(2015),乔全生、王晓婷《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方言字汇〉在晋语史研究中的价值》(2016),郭慧《敦煌变文中“可”的特殊用法与晋方言的契合》(2018),朱光鑫《〈算学宝鉴〉用韵与16世纪山西汾阳方言》(2019)等。
历史文献为山西方言语音史研究提供了重要佐证,丰硕的山西方言语音研究成果又为汉语音韵学研究提供了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材料,为汉语语音史研究做出重要贡献。如:王为民《山西方言与汉语语音史上的tsi(-)类音节》(2011)、《晋语蟹效摄一等开口字锐钝分韵现象及其意义》(2016),乔全生系列论文《论晋语语音研究在汉语音韵学史中的重要价值》(2017—2019)等,展示了山西方言独特的语音特征,为中国音韵学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音变线索及可贵的方法论依据。
通过方言间的比较,利用历史层次分析法离析方言语音历史层次的相关论著有:沈明《山西晋语古清平字的演变》(1999),王临惠《山西方言声调的类型》(2003),孙小花《山西方言果摄字读音历史层次之推测》(2006)、《山西方言梗摄开口二等字白读音分析》(2009),王利《晋东南晋语知庄章组声母的读音类型及其演变层次》(2014)等。
山西方言语音特点仍是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在扎实的共时研究基础之上,以各点、各片、各区翔实、准确的描写、记录为前提,山西方言语音共时研究更加细致深入。如:王临惠《山西方言声调的类型》(2003),沈明《山西省的汉语方言》(2008),王利《晋东南晋语的阳声韵》(2012),薛志霞《从几个常用词白读音看山西方言山摄白读》(2017),沈明、秋谷裕幸《晋语吕梁片的过渡性特征》(2018),白静茹《从吕梁方言的一二等韵看晋语的保守与创新》(2019)等。沈明《山西省的汉语方言》(2008),概括了山西省内汉语方言的分布、使用人口及各片的语音特点,从历史行政区划角度分析了晋南中原官话汾河片与关中片、晋方言的关系,最后简要归纳了关于晋方言归属问题的讨论[43]。
(二)方言词汇研究
山西方言词汇仍以详尽的共时研究为主,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词汇比较研究及词汇史研究成果,但总体上看,后者研究相对薄弱。
词汇共时研究的重点仍在词头、词尾、古语词、核心词、方言语汇上,但与上时期相比,本时期更注重对词汇特点的宏观把握。
1.词头和词尾研究
词头仍以“圪”字研究为主,但研究范围由单点方言转向了整个晋方言或山西境内方言,有的论文还涉及“圪”的历时变化研究。如:刘育林《晋语词汇双音化的一种方式:加“圪”》(2001),认为加“圪”是汉语词汇在一定时期的一种双音化方式[44]。王临惠《山西方言“圪”头词的结构类型》(2001)等,分析了山西方言“圪”头词的结构类型,认为“圪”头词的性质是“构成合成词的词缀”。[45]白云《晋语“圪”字研究》(2005),考察了晋方言中“圪”从产生之初到近代的历时发展及在现代方言中的分布情况,认为“圪”是晋方言词汇复音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构词手段。[46]刘育林《现代晋语圪字新探》(2012),认为现代晋方言“圪”字带有明显的黏着性,很像阿尔泰语的黏着成分,其与汉语并用,构成了独特的“圪”字混合语,将“圪”字与阿尔泰语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47]。
其他词头研究主要涉及“日”,如:陈庆延《说前缀“日”——晋语构词特点研究之一》(1999),认为晋方言前缀“日”有定位性特征,其构词功能、分布范围有地域特征,构成的词具有代表性,所以晋方言是个“日字岛”,并从语源上讨论了前缀“日”源于元明白话[48]。
关于词尾研究的有:蒋平、沈明《晋语的儿尾变调和儿化变调》(2002),沈明《晋语里残存的“儿[n]”缀》(2019)。后者分析了山西方言中少数常用的、老的土词里残存着的“儿[n]”缀与前字合音成一个音节的现象[49]。
2.古语词、核心词研究
姚勤智《晋中方言古语词拾零》(2007),乔全生、张楠《晋方言所见近代汉语词汇选释》(2010),选释一些在今山西方言中仍保留的古词语,分析它们在普通话和方言区的使用情况,并探寻其历史发展线索。
陈庆延《晋语的核心词汇研究》(2001),围绕山西晋方言核心词汇的同义语素与非同义语素的取舍、附加成分构词方式以及使感词、分音词的构造等展开讨论,以展示晋方言核心词汇的特征,提出了晋方言核心词汇的特征最终取决于操本方言的居民在长达几千年里形成的遣词意识和取料规则的观点[50]。
3.方言语汇研究
杨增武主编,张光明、温端政编纂的《忻州方言俗语大词典》(2002)是忻州方言词汇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该词典共收语词22 000多条,近150万字,比较系统全面地反映了忻州方言的词汇面貌,为深入研究忻州方言乃至山西方言词汇提供了翔实的语料[51]。此外,还陆续出版了忻州方言的成语等系列词典。邢向东《以构式为视角论晋语方言四字格》(2019),以构式语法理论为背景,讨论了填加成分在四字格构成中的作用,认为:方言四字格的核心意义是描绘人、物、场景的形貌、声音、行为、心理、环境等,因此具有描绘性、述谓性等多种意义[52]。
4.本字考释研究
乔全生《山西南部方言称“树”为[po]考》(2002),利用历史文献及现代方言中的读法,考证得出山西南部20余个县市称“树”为“po”,“po”的本字实则为“木”[53]。李小萍《山西北部、中部方言植株个体量词“[pu]”考》(2013),考察山西北部、中部方言中植株类个体量词“[pu]”的读音及用法,其本字当为“木”。[54]冯蒸、马冬梅《考晋语thia(ɑ/Α)本字为“生”》(2018),通过考察山西方言“生”的读音,认为表“生(孩子)、抱(孩子)、收养”之义的thia(ɑ/Α)本字为“生”。[55]
5.词汇史研究
虽然学者们已经开始关注山西方言词汇史的研究,但成果依然较少。如:孙玉卿《山西方言亲属称谓研究》(2005),对山西106个方言点方言的亲属称谓词进行了横向比较与历时考察[56]。秋谷裕幸、邢向东《晋语、中原官话汾河片中与南方方言同源的古词语》(2010),讨论了晋方言与中原官话汾河片中7个基本的古语词,证明它们与南方方言词同源,是早期词语的保留[57]。白云、董娉君《语言横向传递与晋方言词汇历史层次的形成》(2019),以山西方言“父亲”称谓词的不同说法为例,探讨晋方言词汇历史层次形成的原因[58]。此外,白云主持并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晋方言词汇史研究”。
(三)方言语法研究
本时期的山西方言语法研究除共时研究之外,还积极引入语言学理论或开展语法史的研究,取得了明显成效。
综合研究的著作有:乔全生《晋方言语法研究》(2000),是作者20年来研究山西方言语法的结晶,全书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山西方言语法的突出特点,归纳了山西方言语法演变的有关规律[59],是第一部研究山西方言语法的专著。郭校珍《山西晋语语法专题研究》(2008),主要讨论山西晋方言的一些特殊句法现象[60],是一部翔实的山西晋方言语法专题研究著作。单点方言综合研究的著作有:范慧琴《定襄方言语法研究》(2007)、吴云霞《万荣方言语法研究》(2009)、李卫锋《山西汾阳方言语法研究》(2019),较全面、客观地展现了各单点方言的语法面貌,为山西方言语法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专题研究的论文主要集中在代词、疑问句研究等方面。
(1)代词研究。综合研究的有:杨文娟《大同方言的代词》(2004)、蒋文华《应县方言的代词》(2011),分别分析了山西单点方言代词的语法特征及语法意义。对代词进行再分类研究的有:史秀菊《山西临猗人称代词的音变》(2003),赵变亲《襄汾汾城方言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2009),白云、石琦《山西左权方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X都、X都们”》(2014)等;霍晓芳《蒲县方言的指示代词》(2004)、吕美红《山西翼城方言的指示代词》(2005)、史秀菊《晋语盂县方言指示代词四分现象的考察》(2010)等。除单点方言外,还对某一片区或大区的代词进行了研究。如:史秀菊《山西人称代词复数的表现形式》(2010)、《山西晋语区与官话区人称代词之比较》(2010),范晓林《晋北方言领属代词的重叠》(2012),赵变亲《晋南中原官话的人称代词》(2012),武玉芳《山西方言“人家”义代词的形成及其连用》(2014)等;张维佳《山西晋语指示代词三分系统的来源》(2005)等。
(2)疑问句研究。这一时期山西方言疑问句的研究成果也比较集中。如:郭校珍《山西晋语的疑问系统及其反复问句》(2005)、郭利霞《山西山阴方言“A一A?”式选择问句》(2009)、史秀菊《山西方言特指疑问句(一)、(二)》(2011)等。山西方言疑问句研究的角度日益丰富、多样化,如:郭利霞《山西方言的语调问句》(2014),分析了山西方言的语调问句,并将其分为低平语调问句和高升语调问句[61]。乔全生《洪洞方言用于答语的反诘问句“咋呢不行的”研究》(2015),分析了洪洞方言中反诘疑问句做答语的现象[62]。
此外,还有对助词进行研究的成果,如:史秀菊《山西晋语区事态助词“来”“来了”“来来”“来嘅”》(2011)、赵变亲《山西汾城方言中的助词“价[ti0]”》(2011)等;还有对句法结构进行研究的成果,如:宗守云、张素玲《晋语中的“往CV”结构》(2013)等。
引入语法化研究山西方言的相关论文有:史秀菊、郝晶晶《山西平遥方言复句关联标记“门”的演变——从后置到前置》(2018),李仙娟《晋南方言“到”的用法及其语法化》(2019)等。
史秀菊主持并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晋方言语法史研究”,发表的相关论文有:《山西南部方言的“X去”及其来源》(2010)等。
(四)区域方言研究
山西境内根据地形地貌可分为7个区域:5个盆地,2个高原,由北向南依次为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原盆地、临汾盆地、运城盆地、沁潞高原、晋西高原。除临汾、运城两个盆地之间没有太大的自然屏障外,其他5个区域均有明显的自然界限,因此每个区域内的方言对外具有排斥性,对内具有一致性,区域方言的共性特点构成了整个山西方言的共性特点。
区域方言研究主要集中在语音上。如:崔淑慧《山西北区方言语音研究》(2004)、王利《晋东南晋语语音研究》(2007)、崔容《太原盆地方言语音研究》(2014)、郭贞彦《山西中北部晋语声调研究》(2016)、王晓婷《山西西南部地区方言语音研究》(2017)等。这些博士学位论文分别对山西北区、东南部、太原盆地、中北部、西南部方言的声韵调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分析了其方言语音的共时类型,探寻了其历时发展脉络,总结了其区域方言语音特征及形成原因。
(五)诗词用韵研究
诗文用韵一直是汉语语音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研究山西地区诗人诗词的用韵可为山西方音史研究提供依据。重要论文有:丁治民《金末道士侯善渊诗词用韵与晋南方言》(2002),穷尽考察了金末道士侯善渊的诗词用韵,将其归纳为18部韵系,经过与金代晋南籍作家的诗词用韵中的特殊通叶现象和现代晋南方言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侯善渊诗词用韵的语音基础是晋南方言[63]。张洁《唐代山西诗人诗歌用韵研究》(2017),选择唐代山西诗人诗歌用韵作为研究对象,运用韵部分析、算术统计和比较等方法,对唐代山西籍127位诗人的3 556首诗歌、4 208个韵段进行了穷尽性的分析研究,探讨了唐代山西地区的实际语音与西北方音的密切联系[64]。
(六)交叉学科研究
1.地理语言学研究
地理语言学利用语言地图的方式描述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进而用社会文化等因素解释分布的原因,探索语言现象的历时演变。山西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是地理语言学研究最理想的场所之一。最早利用地理语言学研究山西方言的著作是贺登崧《汉语方言地理学》(2003),从地理语言学的角度划分方言边界线及同言线,从地理、文化角度考察语音及词汇的异同,[65]开创了山西方言地理语言学研究的先河。其他重要论著有:王临惠《汾河流域方言的语音特点及其流变》(2003),武玉芳《山西大同县东南部方言及其变异研究》(2010),邢向东等《秦晋两省黄河沿岸方言比较研究》(2012)及系列论文,李小平《入声调在秦晋黄河沿岸方言中的演变》(2006),侯精一《山西、陕西沿黄河地区汉语方言第三人称代词类型特征的地理分布与历史层次》(2012),王利《晋豫两省太行山沿麓方言“儿”系字的演变》(2014),余跃龙《山西晋语“个/块”的地理分布特征》(2014)、《从晋方言常用词汇看山西中部交界方言的归属》(2019)等。
近年来,以GIS地理信息系统为手段研究山西方言,取得了系列成果。如:沈力等《用GIS手段解读混合方言的成因——以灵石高地为例》(2011),冯良珍、赵雪伶《用GIS考察方言过渡区词汇的传播路径》(2019)等。
2.实验语音学研究
实验语音学在山西方言研究的运用主要集中在声调和韵母上。研究声调的有:王红斌《长治市城东桃园村方言点声调格局的实验报告》(2003)等。研究韵母的有:王晓婷、杨俊杰《语音同一性鉴定中口音韵母、鼻化韵母、鼻韵母的语图判别法探究》(2016),利用语音工作站对山西方言与普通话鼻音韵母对应的口元音韵母、鼻化韵母、鼻音韵母的语图差异进行研究,通过识别语图可准确地判别相近的韵母,弥补了“听官之缺”。[66]
3.刑侦语言学研究
通过犯罪分子无意间留下的“语言痕迹”进行科学识别和分析,揭露、确定犯罪分子,成为一门新兴的刑侦语言学科。将方言调查研究成果应用到公安刑侦领域,已取得系列成果。如:杨俊杰《山西方言与普通话进行司法话者识别可用特征音段研究》(2013)、常乐《榆次人普通话中方言特征研究——以人身分析为视角》(2018)等。
(七)方言与文化研究
具有地域性的方言往往承载着当地独特的文化信息。深入挖掘山西方言与山西文化之间的关系,从山西方言中感受山西文化的独特魅力,是方言工作者的又一使命。如:乔全生于2008—2009年与《太原日报》合作,开辟专栏发表“山西方言与山西文化”系列小论文55篇,其中包括《晋方言与醋文化》《山西方言与窑洞文化》等,全方位展现了山西方言所承载的丰富的地方文化。其他相关论文有:张晓瑜、李小平《山西方言与文化综合研究的宏观思考》(2005),余跃龙、刘芳《山西东南部地域文化方言解析》(2013)等。著作有:冯良珍等《平遥方言民俗图典》(2014),采用方言词语加注国际音标并配以图片的方式,反映平遥方言与民俗文化[67]。
建设中国方言文化典藏多媒体资料库,编写出版中国方言文化典藏图册,是这个时期山西方言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山西省获批4项“语言方言文化调查”项目,分别为清徐、洪洞、夏县、大同,除大同在研外已全部结项,结项成果《清徐典藏图册》已出版。每部图册都可谓当地语言文化图、文、声、像并茂的博物馆。
山西流传着许多方言说唱艺术形式,通过对这些说唱形式进行整理、研究,可为山西方言研究提供实态语料。相关论文有:赵海英《民间俗信仪式中的说唱艺术——山西霍州书的形态研究》(2011)、《方言学视野下的山西民间音乐》(2013),刘芳等《平遥弦子书“声韵”与“音色”关系之解读——以经典剧目〈骂鸡〉为例》(2014),蒋文华、乔全生《方言研究在文化生态保护中的重要意义——以山西民歌、山曲、说唱等为例》(2019)等。
五 结语
纵观山西方言70年来的研究历程,从新中国成立伊始的初创与探索,历经“文革”时期的萧条与停滞,迎来新时期的恢复与提升,走向新时代的兴盛与辉煌。70年来,山西方言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在汉语方言学界令人瞩目。作为汉语方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方言研究成果不仅为汉语方言研究提供了鲜活的语言事实,也为其他学科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山西方言研究任重而道远,还有很多重要课题有待攻克,如:山西方言“北杂夷虏”的阿尔泰化与“底层词”的研究,核心方言、权威方言以及各片方言地位的研究,山西方言口传文化典藏的整理与研究,山西方言大词典的编写等。只要山西方言学人付出更为艰苦的努力,就能实现全方位展示山西方言无穷无尽的宝藏这一宏伟目标。
说明:本文以上所论,多以中国大陆学者的山西方言研究成果为主。限于篇幅,可能有的重要作者和论著未能一一列举、评述,难免挂一漏万,以后择机增补,敬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