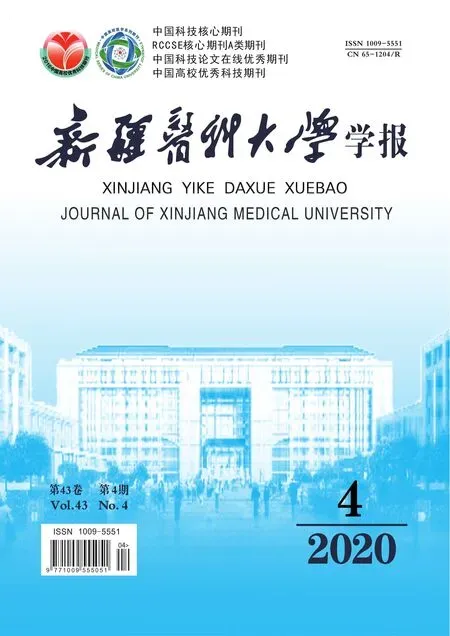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最新研究进展
鲁晓擘, 唐 莉,沙尼亚·尼亚孜,孙晓风,刘 浩,曾斌芳,张跃新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性疾病中心,乌鲁木齐 830011)
自2019年12月起,在我国湖北武汉发现一些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2019年12月1日最早的1例发病[1],随后病例数迅速增加,传播速度极快。武汉市华南海鲜批发市场被怀疑可能与发病相关。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些不明原因肺炎是由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引起。2020年1月12日,这种冠状病毒被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命名为“2019-n Co V”。2020年2月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通知,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统一称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NCP)”,简称“新冠肺炎”;2 月11 日,又将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命名为“COVID-19”[2]。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又根据这种病毒与SARS-Co V(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遗传相似性,将其命名为“SARS-Co V-2”。截止到3月10日,2019-n Co V已导致我国感染 80 955例,而国外感染人数已达 36 900人,该病已席卷全球,严重威胁了全球公共卫生,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因此,本文就COVID-19的病原学、治疗、预后及重症化预测因子及目前亟待阐明的若干关键科学问题等方面进行综述,为进一步研究及防治提供参考。
1 新型冠状病毒的病原学研究
在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发生后,我国病毒学家立刻对该病毒进行相关研究。作为COVID-19病原体的SARS-Co V-2于2020年1月 7 日由我国国家疾控中心成功的自武汉的患者血清中分离,随后浙江省、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分离出该病毒毒株。由于到目前为止,SARS-Co V-2发现仅2个月余,后续动物模型相关验证实验尚未进行,因此还需要研究者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迄今为止,我国武汉发现的SARS-Co V-2是目前已发现的第 7 种可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与SARS-Co V、MERS-Co V(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同属于β-Co V[3-4],其基因组与SARS-Co V基因组表现出高度的序列同源性,Lu等[3]的研究提示为79%,Chan等[5]的研究提示为82%。
研究表明,SARS-CoV-2 基因组有2个具有高度变异性的核心位置。一个是开放阅读框(ORF)1ab基因中的沉默变异[6],另一个是氨基酸 ORF8 的多态性[3,6]。预测显示,ORF8 中的突变可以导致2个变异体(即 ORF8-L 和 ORF8-S)[6],这2个变异体可导致蛋白质的结构发生变化。SARS-CoV-2的核衣壳蛋白与刺突糖蛋白也可以发生突变[7]。这些研究均表明 SARS-CoV-2 基因组结构具有独特的特征,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明确这些变异在发病机制中起到什么作用。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指出[8],患者病理结果显示,各脏器呈现不同程度变性,坏死,淋巴细胞和(或)中性粒细胞浸润。其中肺泡腔内见浆液、纤维蛋白性渗出物及透明膜形成。患者体内T细胞明显被激活,说明免疫损伤非常严重。
2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
目前尚无针对SARS-CoV-2感染的特效药物,现有的治疗方法多来自于治疗SARS、MERS及流感的经验。因此对SARS-CoV-2特效药的研究与开发成为了目前的热点之一。首先,SARS-Co V-2 可通过刺突糖蛋白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2(Spike-ACE2)途径感染人体,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2(ACE2 )可作为治疗药物的靶点起到一定疗效。其次,抑制SARS-CoV-2复制的药物,尤其是已经证实对治疗SARS-Co V和MERS-Co V有效的药物,到目前为止这些药物已经进行了相应的临床药物试验研究。
2.1 抗病毒治疗药物
2.1.1 干扰素α 干扰素α是一种低分子蛋白,由白细胞产生,具有广谱的抗病毒作用。它作用于病毒复制的不同阶段发挥抗病毒作用。自2003年截止到目前,多篇文献报道对SARS-CoV 、MERS-CoV 等病毒,干扰素α具有广谱抗病毒作用[9-13]。在目前的COVID-19治疗指南中,也采用干扰素α雾化吸入抗病毒治疗,但属于低级别推荐[14]。
2.1.2 洛匹那韦/利托那韦 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是治疗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一种药物,研究发现洛匹那韦对SARS-CoV有抑制作用。2003年治疗SARS期间,中国香港学者发现,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合剂能抑制 SARS-CoV 主蛋白酶 Mpro,降低ARDS发生率及病死率[15]。另一项研究表明洛匹那韦/利托那韦还可以抑制MERS-CoV 活性,降低感染 MERS-CoV 绒猴的病死率[16]。基于以上研究,提出经验性使用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治疗 COVID-19。并且该药也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列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
2.1.3 阿比多尔 阿比多尔是一种广谱的非核苷类抗病毒药物,用于甲型、乙型流感病毒导致的流行性感冒。曹瑜[17]的一项阿比多尔片治疗急性呼吸道病毒感染有效性的研究证实,阿比多尔可以有效抑制甲型、乙型流感病毒。 2018 年关文达等[18]的另一项研究表明,在体外阿比多尔可有效抑制 MERS-CoV。2020 年 2 月,我国李兰娟院士团队公布,体外细胞实验中阿比多尔可以有效抑制冠状病毒,并被纳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中。
2.1.4 氯哇 氯哇既往用于抗疟疾及阿米巴原虫的药物。在COVID-19流行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体外试验研究证实氯哇不仅有抗病毒作用,还具有免疫调节活性,具有抗2019-nCoV的作用[19]。因此在中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第六版)中新增磷酸氯哇作为抗病毒药物。
2.1.5 利巴韦林 利巴韦林能抑制多种病毒,在2003 年SARS流行期间,利巴韦林的使用显著得降低了病死率和气管插管比例[20-22]。针对MERS-CoV感染,Almekhlafi 等[23]及Omrani 等[24]的研究均表明利巴韦林能明显抑制MERS-CoV,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在体外实验中,我国学者研究发现,利巴韦林可以抑制人体细胞株感染2019-nCoV 。基于以上研究,利巴韦林被推荐运用于COVID-19的治疗。
2.1.6 瑞德西韦( remdeivir) 瑞德西韦也是一种广谱核苷类似物抗病毒药物。它通过抑制 RNA依赖性的 RNA 聚合酶抑制病毒复制。针对埃博拉病毒该药只进行了II期临床试验[25],多项体内外试验均研究表明,瑞德西韦对冠状病毒有抑制作用[26-30]。而2019-nCoV 的基因组结构,被感染患者的临床表现与 SARS-CoV、MERS-CoV 极其相似,因此推测瑞德西韦针对 2019-nCoV 可能有效。2020年1月31日,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在线发表美国对来自武汉的首例COVID-19 患者使用了瑞德西韦,该患者很快得到控制[31]。2020年2月5日,中日友好医院王辰、曹彬团队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宣布启动瑞德西韦治疗COVID-19 的III期临床试验。
2.2 恢复期血清理论上恢复期血清应对感染者有一定治疗效果。但在 SARS 治疗中,疗效并不稳定[32],因此其治疗SARS-Co V-2的作用还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2.3 激素在SARS流行期间,大量运用激素能明显减轻患者肺部感染中毒症状,但激素的副作用及股骨头坏死发生率明显增加。研究表明,SARS和MERS患者接受激素治疗不会降低死亡率,反而会延迟病毒清除[32-34],因此,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中都提到要谨慎使用激素。
2.4 传统中医药治疗中医药在新冠肺炎的防治中也取得很好的疗效。2020 年2月3日,在科技部大力支持下紧急立项的《国家科技应急攻关项目中西医结合防治新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临床研究》正式启动。截止目前,已有超过 6万例的确诊病例接受中医药治疗,结合西医治疗,已经取得显著得效果。因此中医药被纳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中。
3 预后与重症化预测指标
病毒本身引起的过度免疫反应可以导致炎症因子风暴,从而引起器官组织损伤,引起多脏器功能损伤[35]。重型COVID-19会出现细胞因子风暴综合征(Cytokine storm syndrome,CSS),多种炎性因子,如白细胞介素-1(IL-1)、IL-6、IL-8、IL-12、干扰素-γ(IFN-γ)、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等在体液当中大量生成,是导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和多器官衰竭的重要原因[36]。淋巴细胞的异常激活是产生CSS及ARDS的重要原因。对于COVID-19是否是预测病情进展的主要因素还需要进一步验证,但毫无疑问,失控的细胞因子风暴进一步造成炎症弥漫,导致肺泡结构受损,最终发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危及患者生命。
国内研究团队研究发现IL-6和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是导致新冠肺炎患者炎症风暴中的2个关键炎症因子。在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2020年2月14 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型、危重型病例诊疗方案(试行第二版)的通知》已经明确将IL-6 进行性上升作为病情恶化的临床警示指标[37]。
国内学者研究发现[38],COVID-19患者存在淋巴细胞亚群水平的异常,其中自然杀伤细胞下降明显,提示淋巴细胞亚群在COVID-19 的诊断、病情评估中可能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对预后的判断具有一定价值。
4 亟待阐明的若干关键科学问题
在国内外研究人员和大量医务人员的不断努力下,逐渐对 SARS-CoV-2 及COVID-19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但仍有很多未知领域。
4.1 病毒的最初来源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分析发现2019-n Co V在整个基因组水平上与一种蝙蝠中的冠状病毒的序列一致性高达96% ,提示2019-n Co V可能来自蝙蝠[39]。在武汉COVID-19 暴发初期,确诊病人大多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但是,随后陆续出现许多与华南海鲜市场无关的病例、家庭聚集性发病病例及医护人员感染的情况[40],这些都表明野生动物跨物种传播给人类后,又出现人与人之间的传播,除野生动物之外受感染的人类成为又一传染源。COVID-19 患者是SARS-CoV-2 主要传染源,处于潜伏期的 SARS-CoV-2 感染者是否具有传染性还存在争论。
4.2 宿主之谜石正丽团队报道了SARS-Co V-2 与一种蝙蝠(中华菊头蝠)中的冠状病毒序列高度一致达96%,故推测SARS-Co V-2的自然宿主很可能是蝙蝠[39]。但是 SARS-Co V-2 只有在中间宿主内进行连续进化,最终才能有感染人的能力。因此查找中间宿主非常关键。北京大学、广西中医药大学、宁波大学、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的研究人员联合完成并在线发表了SARS-CoV-2 中间宿主的研究结果[41]。研究结果显示,与其他动物相比,蛇最有可能是携带SARS-CoV-2的动物。除上述研究外,广东省动物保护中心陈金平团队[42]在Viruses杂志上发表文章,通过宏基因组测序分析发现,穿山甲中携带有仙台病毒和冠状病毒,提醒穿山甲可能是一病毒传播者。今年2月7日,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结果表明,穿山甲可能为新型冠状病毒潜在中间宿主。目前国外多个国家亦有大量患者,可收集更多资料进行进一步研究。
4.3 零号病人2020年1月 24 日,金银潭医院副院长等在Lancet刊载的文章里提到[1],新型冠状病毒第1例患者症状开始日期推定在12月1日。但是第1例病人和后来的病例之间没有发现流行病学联系。由于缺乏信息,至今仍不能完全判定该患者即为零号病人,如果按照12月1日发病推算,至少在11月中旬这个人就被感染了。该篇论文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在前 4 位发病的病人里,有3位都跟海鲜市场没有关系。在必要时如何寻找零号病人仍是值得研究的科学问题。
4.4 未来发展随着国内疫情的陆续解除,该病毒可能变异为与普通流感类似的冠状病毒,长期在人际间传播,但目前仍缺乏证据。因此要加强针对病毒流行病学特性的研究和动态监测,特别是对病毒的传染力、传染率以及变异性检测。同时做好新冠病毒在人群中长期存在的准备,加紧新冠病毒疫苗研发。
作为新发传染病,COVID-19疫情暴发与流行,给中国乃至全球造成极大威胁和影响。经过中国政府和全体人民的坚持不懈,中国的疫情得到了明显的控制,中国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是目前除中国外其他国家病例数迅速攀升,因此接下来的还有许多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需要全世界人民共同努力才能渡过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