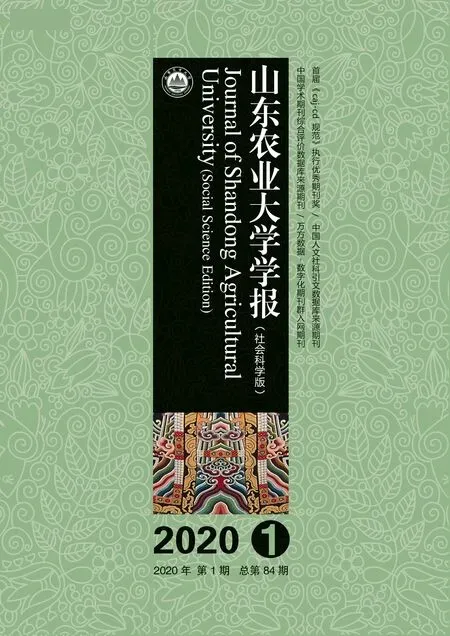英语会话含义解读的四维透视
□庄淑霞
[内容提要]英语会话是交际主体借助英语语言符号表达变化中的社会存在。英语会话双方能否理解彼此会话的本义直接影响交际目的的成败。只有从英语会话的社会性、主体性、整体性、动态性来分析英语会话,才能准确解读英语会话含义。
会话是人与人之间表达情感、交流思想的重要途经。英语作为一门国际语言,无论英语使用者将其作为外语还是第二语言,在交际过程中都力求准确解读对方话语的真实内涵,交际活动才能有效进行。但在实际英语会话中,往往出现不能透彻解读会话含义的现象,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源有很多,但会话的社会性、主体性、整体性、动态性四维属性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只有四维透视英语会话,才能正确解读英语会话含义。
一、英语会话的社会性
语言是浓缩的社会历史。会话的产生以及会话的内容、形式等方面都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演变,都承载着社会历史的痕迹,这是语言会话的根基。只有认识到语言会话的社会性,会话解读才有基础。会话是社会交往的手段,会话表达的观点和情感等要素都是对社会存在的主观反映,这是解读会话的当代价值。只有认识到会话的当代价值,解读会话才有动力。任何会话主体都是处在一定的社会阶级关系中,语言的表达必定会折射这一社会阶级的思想和心态,而且表达的方式都具有自己族群的文化特色,不论是正式会话还是非正式会话,不论是官方会话还是非官方会话,都是为了达成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社会生活目的而进行的语言交流,能否站在社会的高度审视英语会话直接影响交际语言的阐释及交际目的的成败。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把“社会”划分为“生活世界”和“制度”两部分。他认为,生活世界乃是积淀在语言中的各种“背景知识”和行为规范的综合要素,它代表了社会共同体的集体行为期待,个体的经验和行为准则、社会文化都是这种知识的产物。交往行为理论正是通过对生活世界和以语言为媒介的人际交往行为的语用学分析,提出了语言交往行为的三大有效性标准,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即符合理性的要求。[1]
A.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45th president?
B. That destroyer-in-chief!
我们知道,商人出身的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自上台以来就奉行“美国优先/美国利益至上”的对外政策并对它的贸易竞争对手加大贸易增税、实施经济制裁或军事打压,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搅局、到处树敌,甚至连它的盟国都不放过,所以他的批评者或反对派针对特朗普的疯狂行为借由the commander-in-chief一词衍生出the destroyer-in-chief(终结者/掘墓人)的说法。另外,针对特朗普以往的诸多表现,对他的外号还有 the liar-in-chief, the groper-in-chief, the dotard-in-chief, the racist-in-chief, the misogynist-in-chief, the divider-in-chief。这些短语都是美国公众对特朗普过去的所作所为和2017年执政以来导致的社会乱象的真实写照。显而易见,社会存在是会话内容的基础,是话语行为实施的前提条件,离开了会话的社会性就根本无法解读会话的内涵。在会话解读中,必须审视其社会性。
二、英语会话的主体性
任何英语会话都是交际主体之间的言语行为,展现会话人的语言风格、个性等主体性特征。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往往通过某种方式间接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图,听者必须透过字面信息来推导说者隐含的话语含义,所以脱离主体性的解读往往会出现严重偏差。言语交际是一种主体之间的合作性游戏,说者何以在没有明说的情况下被理解表明不仅要理解他的话语内容而且还要明确他的交际意图。因此应该区分言语交际行为中的每个主体话语的两种意图和两种意义:信息意图和句子意义与交际意图和说者意义。语用学将语言的交际功能作为研究的主要领域并试图将语言形式看成是表达主体性意图的动态手段而非静止不变的事物。
在英语会话实践中,语言使用者是言语交际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只有听者准确破译说者的交际意图,当下的交际行为才会有效。因此,对会话含义的解读要考虑会话者的主体性要素。首先,会话是主体之间的言语行为。会话内容通过主体的语言选择来呈现,说者通过不同的语言音符、音调等来传递主体的思想和情感,由此彰显主体双方的个体特征。其次,会话是人创造的对象。会话不仅是会话主体沟通自我与客观世界的桥梁,更重要的是会话主体创造的高超的会话艺术能够充分展示说者的语言智慧。会话主体语言素养的高低直接决定英语会话的表达效果。
A: Donald Trump again?!!
B: Yes! DT!
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无论是总统大选期间还是任现职期间,口无遮拦、出尔反尔,动辄在推特暴粗口的行事风格有目共睹,一直成为众多美国媒体及大众嘲笑的热门话题。
秦明月摸出一包烟来,抽出一支点上,又把余下的丢在赵大刚的面前,长吐一口烟雾说:“我也感觉这案子不简单。志武的意见也很有道理,如果凶手是器官偷盗者,完全可以有无数种方式处理尸体,而不必这么费事。另外,从凶手缝合死者的伤口来看,他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他绝无可能不小心把这玩艺留在死者伤口中。所以有两种可能,一是大刚说的凶手故布迷阵,引我们走弯路,另一种就是如志武所说,这是凶手的标志。”
从A和B的对话可以看出,二者先前谈论过特朗普并再次提及。DT不仅是Donald Trump的首字母缩写,还是Delirium Tremens (震颤性精神错乱)的首字母缩写,根据现实语境,B有意整合两种语义,对DT的原有语义进行了拓展、丰富和强化,借助DT一语双关地对特朗普进行了尖锐犀利的嘲讽。
因此,在解读英语会话的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到主体性因素,只有全面了解会话主体的认知、情感和态度,才能有效解读会话意图。
三、英语会话的整体性
“整体”(holism源于希腊词holo)意指“一切”“整个”“全部”。亚里斯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精确地总结了整体论的指导原则: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整体论囊括有关局部的本质、功能、特性的知识以及局部与整体的互动关系。整体论强调整体的重要性和局部之间的依存性。整体论反对将局部的功能与整体割裂开来。
英语会话的整体性是指任何英语会话都是在一定的时空、社会条件下进行的,不论是会话的形式还是内容都渗透着主客观因子,是历史与未来在当下的呈现,通过会话展示出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语义整体论强调单个的语词或句子的意义只有在与其更大的语体关系中才能确立,一个表达式只有作为整体语言的一部分时才有内容。无疑,这个论述突出地强调了会话的整体性。语言哲学家弗雷格、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也非常深刻提出语义整体性的问题。弗雷格主张对逻辑的探讨首先就是对语言意义的探讨,而对语言意义的分析是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在他的《算术的基础》中为自己的逻辑研究规定的原则就是“在句子的关系中研究,而不是孤立地研究语词的意义”。[2]这条原则后来被成为“语境原则”。在弗雷格的语境下,逻辑、语言、哲学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在内容上,都是整体把握世界的方式,只是形式、切入点不同而已。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解释“意义”的用法时引用了弗雷格的这一原则:“一个词的意义就在它在语言中的使用”。会话如果离开了会话的整体架构就会导致误读或迷茫。维特根斯坦在其《逻辑哲学论》中指出“除了简单地‘描画’对象外,语言还有许多功能。语言总是在某个语境里发挥功用,因而,如同存在着众多语境那样,语言有许多效用。”[3]维特根斯坦通过语言的效用与价值阐明了内在的相互联系的话语世界。弗雷格的语境原则经由维特根斯坦的发展成为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研究的一条基本原则,并形成了当代分析哲学中具有重要作用的整体论思想。分析哲学的整体论思想体现了会话行为的整体性特征,揭示了整体论视域下的话语含义:它超越了传统孤立、静态的语义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并代之以整体的、动态的研究方法,从而极大地拓宽了语言的研究手段和领域。
语言学家Howard Jackson 和Peter Stockwell着重强调整体关联的重要性,并将关联视为超级准则(supermaxim)。关联假设是人们在语言交流中解读语言形式上没有任何联系的言语信息时所依循的一条重要原则。我们总是填补所需要的连接.[4]
A: Donald Trump Jr's former Fox News host girlfriend joins President Trump's 2020 campaign — 1 year after they started dating.
B: I quit watching cartoons a very long time ago.
从语言形式上看,A和B的对话没有任何连接,但依据关联假设,B生动形象、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美国现任总统的强烈态度:和特朗普有关的一切事情像动画片一样幼稚至极,自己对他早已不感兴趣。可见,用整体关联的语义分析方法能避免语义解读产生偏离。
四、英语会话的动态性
英语会话是交际双方通过语言表达彼此的意图,具有动态性特征,而动态性促成了由静态语义的单一性、确定性到动态意义的可增生性的本质性跳跃,凸显了语言多侧面、多层次内涵不断生成的特性,充分映射出人类丰富多彩的意识活动的可变性。而语言的歧义性、多义性是语义的可增生性的体现,是语言的魅力所在。语言使用者表达的意义要比实际所言丰富得多。词语的多义性与语境的敏感性是日常语言发生作用的永久的富有成效的条件。语用学研究的核心就是超出所言的话语意义和交际意图,即所言隐含的信息所实施的动态的言语行为。
Levinson提出与语境的动态性相近的概念——语境相对性,即同一个句子在不同的语境中表达不同的命题。任何概念的意义都不是固定的——取决于它所处的语体关系。要想赋予意义就必须搭建参照点——特定的语境。同一个表达式语境不同,则意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语境的相对性、语义的不确定性表明会话解读的动态性。Recanati认为语用解读具有三个特征:第一是顾它性,也就是交际双方只有在理性合作的条件下,语用推理才有可能;第二是非单一性,这意味着语用解读是可撤销的;第三是整体性。鉴于语用解读具有可撤销性和可废弃性以及语境信息的可变性,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必将影响会话解读的动态性。这三种特征的结合构成了语用解读的阐释学特征。语用推理的这种阐释学特征和逻辑数理的、机械的语义学解读形成显著差异。[5]
Verschueren将语用学定义为语言的纵观论,并认为语用学的核心是语言的顺应性——语言的基本特性,要求我们从事语言活动时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不断选择以便符合人们的要求、信仰、情感、欲望、意图及交流的真实世界。[6]Verschueren呼吁重返Charles Morris的语用观:语用学是关于人在交际过程中心理的、生物的和社会的一切。语用学致力于将语义研究由静态到动态、由语义单一性到语义多样性的回归本真的生活世界。
Grice的语言研究从分析意义着手,把意义分为“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Grice运用“非自然意义理论”全面深入地分析言语交际中的话语意义,即在特定的语境中的语言意义——语用意义,而不是抽象的、静止的语义内容。Grice的“非自然意义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动态化的交际理论。任何交际过程都涉及动态化的交际意图,对会话含义的推理过程就是对说者意图的剖析过程。在言语交际中,说者的话语的真实含义是由说者的意图所决定的。任何成功的交际都取决于听者对说者所要表达的真实意义或真正意图的准确解读,而这个过程受多种因素制约,这就决定了会话的易变性、动态性。
解读会话含义必须考虑会话语境的动态性,避免以“静止的、孤立的”观点考察会话系统诸要素,因此对语言意义的研究不能将语言与其表达式、语义理解、交际意图割裂开来。意义来自社会交往,意义的生成是一种社会行为。交际双方在动态的语言交往过程中不断对意义进行协商、推理和建构,因此意义不是词语固有的或预设的,而是由交际双方在互动过程中共同建构或动态生成的,是对话语的语境(物理的、社会的、语言的)和话语的潜在意义协商的过程。语义的产生和解读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它深深地植根于认知、社会和文化的世界中。
A: Our president has again slammed trade tariffs on Chinese imports.
B: You know our president is a stable genius!
特朗普对贸易战情有独钟。我们知道,2019年5月美方对2000亿美元中国出口商品加征的关税从10%飙升至25%,计划2019年8月对5500亿美元中国商品进一步追加关税。
在这个对话中,A陈述事实,但B的回应具有不确定性。如果B是特朗普的追随者,这无疑是对特朗普打压中国经济的高度认可;如果B是特朗普的反对者并深知美国政府对中国商品增加关税实则是由美国消费者买单,最终伤害的是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在此B则用特朗普本人在2018年的自封(稳定可靠的天才)对特朗普的拙劣的执政能力进行了形象有力的贬斥。
英语会话含义的解读必须考虑语境的动态性,区分说者意义和语言意义,因为语言形式和表达功能往往呈现不对称性,听者必须明辨说者交际意图、领会会话含义、消解潜在歧义。
四、结语
会话具有社会性、主体性、整体性和动态性。在特定的交际语境中解读英语会话,凸显人作为主体为达到特定的交际目的而进行的语言符号的创造行为。德国人类文化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说“人是符号的动物”。人们使用语言符号分享彼此的内心世界,或有目的向他人传递信息以改变或影响他人的认知行为,从而创造一个意向性的语言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