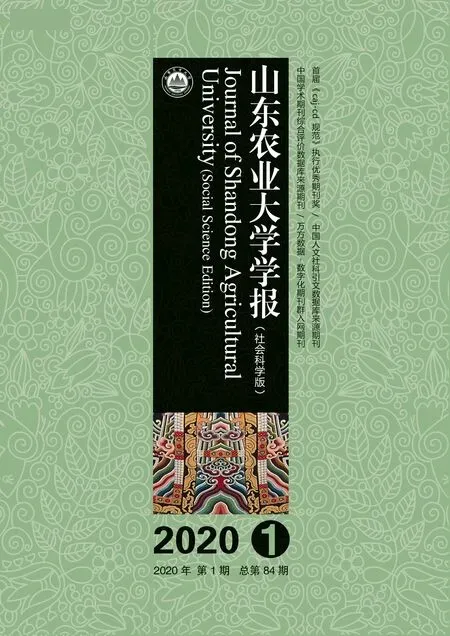孔“乐”之我见
□韦正春
[内容提要]孔子对于“乐”的论述是中国一个美学思想的源流,乐是音乐,乐是由艺术而产生的快感。孔子提出礼乐并举的思想,将“乐”之作用提升到教化人心、调节社会次序的高度。其希望通过乐教来恢复礼治,从而沟通审美和道德之路,形成伦理规范,从而恢复到周礼制度。因此,“乐”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或审美活动,而是其伦理道德的载体或实现方式。
春秋之末,诸侯“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道德沦丧,上下失序,大夫弑其君,八佾舞于庭。父子不相亲,兄弟残手足,夫妇重其利。故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1]由于周代的“乐崩礼坏”,孔子心痛不已,进而感叹说:“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1]面对这种无序的社会状态,孔子极力希望通过言传身教,借礼乐来恢复周朝的礼乐文明。为此,孔子“将他的政治理想寄予礼乐之中,赋予音乐更多的内容和含义,又将音乐与政教、礼制相通,使礼成为其实现和谐社会抱负的重要手段,希望恢复西周的礼乐等级名分制度、维护礼乐的整合性、坚持礼乐的政治性规定。”[2]孔子所提倡的礼乐文化虽然没有实现其政治理想,但是却成了中国几千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流。
一、乐道之观
孔子之道,即仁道。其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教。礼之居前,乐紧居后,说明礼乐的重要性。孔子希望通过艺术和仪式的结合来达到成“仁”的高度。
(一)乐与礼
《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3]可见在商代,神先于礼。殷人因鬼神而制礼,所以“礼”最初只是一种祭神用的仪式。《说文解字·示部》:“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声。”又 《说文·豊部》:“豊,行礼之器也。从豆象形。凡豊之属,皆从豊,读与禮同。”王国维先生通过对甲骨文 “豊/禮”的解读,认为 “豊”最初是指以器皿(即豆)盛两串玉祭献神灵,后来兼指以酒祭献神灵(分化为醴),最后发展为一切祭神之统称(分化为礼)。[4]由此可见,“礼”的最初仪式是祭神,它不仅仅祭祀鬼神或人类始祖,更多的是祭祀自然之神。如:山川、河流、树木等一切自然化、观念化的东西。这就形成了人与自然的一种关系——“礼”,这种“礼”更多的是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如人们在祭“礼”中,所寻求的便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显然,这种礼的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最终可达到一种中“和”的境界。礼从原来单纯的祭神仪式推广到社会生活,成为了人们的行为准则和人伦规范。周与商不同,“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3]周人重礼乐而轻鬼神,更多的是强调人的因素,在客观上有意识的淡化殷商“神权”宗教崇拜。周人尚礼,由“礼治”演变而成一种“德治”。诚如《易》中所云:“‘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错(措)’而帝王质文也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5]可见,礼所解决的问题已演化为人伦至理,夫妇的本质是“敬”,父子是“孝”,君臣是“忠”,上下是“信”,由敬、孝、忠、信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类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由于人口不断的增多,在有限的社会资源承载力下难以满足个体的生存需求。因此,需要集体的力量去生存。在这过程中,就会产生诸多问题,如在集体劳作中如何激发群体的力量,以及保护好个体的利益。所以契约由此产生,契约成为保护个体与群体生存与发展的纽带,以及把个体的力量发挥到极致的一种“礼”,礼成为了一种节制,一种节律,一种礼节,一种仪式、隐喻和象征。它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和处事准则,还维系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而且还形成尊卑有别。“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1]为了弥合这种等级鸿沟,周人作“乐”统同,使情感与理智的谐和。《礼记》云:“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和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乐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3]礼别异,乐和同,礼所别的是“个体意识”,乐所和的是“群体意识。”只有把个体与群体联系起来,才能维护好整个社会的稳定。
《文心雕龙》曰“夫乐本心术,故响浃心肌髓。故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6]故乐本心生,由情牵引,随物而动。“风”在大气的流动中会产生声音,而声音会在人内心里形成一个内在的节律,古人通过“管”来测律所得到的每一个节点,再把每一个节点串联起来就形成了音律。因四季风速不同,所测到的节点各有不一,故古人通过时间的变化形成内在的节律去做事,通过节点来对人事的管理。人类通过节点和事物的规律,对自然的观察和思考而形成了一套法则。音乐表达人与自然的关系,又通过自然界的规律与人类约定俗成的规范结合形成了礼。“乐者和也,和则通天地万物,是一团生意,无彼此之隔。礼者序也,序则因彼此之公情而为之序。使彼此各尽其所应尽,各得其所应得,人皆自由而皆以对方之自由为界。”[7]礼别异,故刚,过刚则易折;乐和同,故柔,过柔则易堕。因此需要礼乐结合,刚柔相济,才能水乳交融,社会才会稳定,群体才能更好地发展,个体才会获得更多的自由。
孔子因人性而释礼,亦因人性而正乐。所以,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1]礼乐同源,但作用各异,礼主敬而检于外,乐主和而诚于中。“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3]《毛诗正义》曰“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仪。发乎情,民之性也;志乎礼仪,先王之泽也。”正好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1]一脉相承,形成了中国儒家的伦理美学:温柔敦厚、中正和平、以礼节情。乐以畅其性,乐者和,既是仁;礼以辨人伦,礼者序,既是义。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1]故“礼”主“敬”,即维护整个社会的秩序,是个体意识服从群体意识,克己复礼即如此;“乐”主“和”,即通过音乐的功效让整个群体不同阶层的意识消融,让社会起到稳定的作用。
礼乐的功用大则维护社会的稳定,小则培养人格的形成。“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1]孔子把外在音乐的“乐”和内心的“乐”联系起来,把礼乐提到“可以成为人”的高度,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锺鼓云乎哉?”[1]“他认为礼乐绝不只是玉帛之式和钟鼓之声,而是包含有个体在处于和群体的和谐完美的关系中时所感受到的欢乐和愉悦;内在的乐一旦由外在的乐形成,就达到了仁的最高境界,外在的乐通过内在的乐作用于人的道德修养,就是人‘成于乐’,这就是礼乐的巨大的政教作用。”[8]乐不仅仅是单纯之“音乐”,于此同时,它也是一种身份和地位之象征,它必须同“礼”相结合起来,从而形成等级次序的对立,从而对社会起到“调”与“节”的功用。
(二)乐与仁
《论语》中,仁字出现190次,孔子在不同场合的教学或对话中对仁的多重涵义作出了阐释。但是“仁”字在孔子之前,各种文献就已有记载。据《孔子与中国文化》统计“《尚书》里有一个‘仁’字;《诗经》里有两个‘仁’字。在孔子所处在的春秋时代,‘仁’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提及:《国语》中,‘仁’,凡二十四见;《左转》中,‘仁’凡三十三见。”[8]不过,唯独孔子对“仁”作出多种解释,把“仁”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核心,并将“仁”抬高到礼乐并举的高度。“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出门,门人问:‘何谓也?’曾子曰:‘父子之道,忠恕而已矣。’”[1]忠,尽力为人谋,忠人于心,故为忠;恕,推己及人,如人之心,故为恕。孔子所谓的“一以贯之”此“一”即“仁”。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儒家的“道”的含义是人道即仁义之道,其的文化里是表达社会人伦秩序的范畴。
孔子认为仁、乐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仁与乐统一,实际上就意味着理想人格是内在的品格和外在的表现统一。“仁”是看不见的,是一种存在于人思维观念上的东西,其必须要有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乐”来引导。“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1]孔子把仁、礼、乐结合起来,仁居礼乐之间,由艺术审美活动把礼与乐结合起来。如果不仁,艺术审美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以“仁”来诠释艺术审美必须符合礼才能达到乐。仁之以义,以义学礼,乐以节和,以和达顺,也就是儒家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1]这里的“仁”纳入大爱之中。“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1]由“亲亲”孝悌到“泛爱众”,把亲子手足之爱从血缘关系延伸出去;从“仁者爱人”达到大爱,引申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来。“正因为这里的‘人’是宗法群体的人,于是‘际’也就成了儒家美学的第一要义。孔子正是把人际关系看作人的本质,从而把‘仁’作为他全部学说的基石。‘仁’就是‘爱人’,也就是每个人自己都去爱别人。”[8]所以,孔子说:“夫仁者,子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可谓仁之方也已”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其不仅仅阐述了“仁”的定义,而且还具体给出“仁”的实践方法。
二、乐德之观
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从道、德、仁、艺的排列次序来看,它们是有先后顺序的,是有层次的。孔子的“游于艺”正是在伦理道德的前提下进行艺术创作和审美活动,而“艺”的本身就包含有礼乐文化道德精神,不管是对这种艺术创作还是艺术审美都可以丰富、充实、完善自我的道德修养和人格提高。孔子之道即“仁”道,道是原则,“德”是践行道的尺度。许慎《说文》曰“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由此看来,“德”作为一种内外兼修的品质,它不仅仅需要别人对自我的认可,还需要自身素养的提高。不管是人生面对顺境还是逆境,都需要维护好自身的底线,守住自己的节操,这就是孔子强调“德”对人格修养的重要性。
(一)乐与贫
乐与贫的抉择是《论语》里常提到的话题,在孔子看来“乐”与“贫”只是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选择,人生的意义在于实现个人理想和社会意愿,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孔子在面对“利”与“义”的坚守上,不以利害义,也不居利为耻,其认为只要在符合道义即可。义作为一种道德原则,所表达的是人的理性品质,展现的是对于一种“仁”的观念;而利,首先它是物欲需求相联系的,而物欲所展现的是人与动物很少有本质区别的生物学特征。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1]孔子这里所指的“利”非世俗的“利”,这里的“利”是在道德标准下的利,即不妨碍其“道”之行,在“道”的准则下逐利。孔子说:“邦有道,贫且贼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1]这里就涉及到人生价值的实现与自我道德修养的问题:邦有道,如若居贫、且贱,孔子认为这是耻辱的,因为没有积极去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邦无道,如若居富、且贵,孔子也认为这是耻辱的,没有维护好自己人格底线的操守。 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1]当涉及到“利”与“义”两度抉择时,孔子以“道”作为衡量的标准。“重义轻利在这里显然体现了安贫乐道的个人理想:即处于穷困之中,却以锲而不舍地坚持合乎道德原则的理想追求为最大的快乐。”[9]孔子说:“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1]在面对“贫”与“富”的态度上,孔子认为物质的丰足对于人格道德的修养有很重要关系。“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如何?’子曰:‘可以,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1]居贫以乐道,据富而好礼。梁漱溟先生说人生有三种乐:“一、与苦对待之乐;二、系于环境的相对之乐;三、不系于环境的绝对之乐”[10]孔子之乐是不系于环境的绝对之乐,亦是回归本心之乐,回归孩童之乐,其之乐返璞归真,超脱于人世。孔子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孔子回归自然,亦回归人初之本性,虽“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但,其心不违“仁”,居“道”乐贫,其胸中始终萦绕着一股浩然正气,在面对富与贵的抉择时,视为浮云。
颜渊是孔子最得意且最喜爱的弟子,其深受孔子言传身教的影响。因此,孔子常在弟子面前夸赞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1]这就是著名的“孔颜之乐”,超越环境,回归于生命之本身,不以物欲违“仁”,从而所得到的一种精神的自由和愉悦。 “孔子‘乐’的人生境界思想,正是提倡人要有精神信仰和道德修炼,一个人的快乐除了财富等带来的感性快乐,还应该超越他们,通过个人修炼和信仰获得超越物质需要、利害得失从而更加根本和持久道德快乐。”[11]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更因该注重自己精神信仰和追求,不要让一味地追求物质而丧失掉人心最简单的快乐。
(二)乐与忧
《论语》之“乐”,据有心人统计达46个字,而纵观《论语》全书,全无一个“苦”字。故《论语》言忧不言苦,乐忧不乐苦。此谓何故?《论语》是其与弟子在学习及相互探讨中所辑拾而成,是最切近还原孔子习性以及与诸弟子相互交流的情景。但《论语》何无一“苦”字,难道孔子与弟子一生都一帆风顺,大吉大利,没有挫折受难?非也,孔子一生困顿受厄,颠沛流离,中年丧妻,老来丧子,四处碰壁,郁郁不得志。但颜回落魄时,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1]孟子说:“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12]颜渊身居陋室,箪食瓢饮,不以为耻,安然处之,怡然自乐。然,颜渊受困,为何孟子却说“人不堪其忧”,而不是“人不堪其苦”。孟子也曾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12]故颜渊居陋巷,不苦其心志?箪食而瓢饮,不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1]鲁衰公六年,孔子已年六十有三,已达“耳顺之年”,而其仅曰“老之将至”,又曰“不知老之将至”,此正值孔子在外游学,居无定所、去卫过宋、在陈绝粮、困于恒魁、饥困交迫。但是孔子始终怀着一种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心态去激励自己和鼓励弟子们用乐观的心态去面对人生。颜渊英年早逝,其号啕大哭,子路以身殉道,其抹泪预言,老年又丧子丧妻,身边一个又一个亲人或弟子逝去,却只言“忧”,却不言苦。这正是儒家所追求的一种内在的至大至刚之气,以一往无前的勇气超脱自身困境,在“小我”与“大我”做出选择,孔子择“大我”,始终不以自我境况如何坎坷、困顿、缺衣或少食等而改变气节,故其胸中常若有一腔乐气盘旋,不觉有所谓忧者。在孔子的内心里,与“乐”相对的是“忧”而不是“苦”。“苦”多指单一的,个体的经历或感受。“忧”多指群体的,社会所虑,与之相对应的“苦”更指的是“个体意识”。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孔子之道即“仁”道,仁者爱人,此“人”不仅仅是单指一人,而是大众。如道家庄子之乐,是以乐“逍遥 ”,是个体避世之乐,其之乐流于自私、颓废,不能与民众同忧患,这是乐其“苦”之乐,而不是乐其“忧”之乐。佛家亦自西来,自汉后与儒、道交汇,倡导众生平等,盛行于士大夫于庶民之间,然其既不能出世,亦无所谓入世,流于“寂”,归于苦,所谓众生苦,倡导渡苦海以达彼岸,故佛家亦是乐其“苦”之乐,而不是乐其“忧”之乐。只有儒家乐以忧对,以“仁”道贯之,形成两个不同的境界。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1]忧道是圣人之忧,忧贫是小人之忧,仁与忧是人生不同的两种境界,有仁之忧,才会有仁之乐,孔子之乐是与忧相对的,故其称“乐以忘忧”并非所忘,而是乐疏忧。
“孔子以为人生最大之义务,在努力增进其人格,而不在外来之富贵利禄,即使境遇极穷,人莫知,然我胸中浩然,自有坦坦荡荡之乐。无所歆羡,自亦无所怨尤,而坚强不屈之精神,乃足历代万古而不可磨灭。”[13]乐与忧的存在正好从两个方面去描述孔子超越性和现实性的人生境界。孔子说:“周监于殷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周人“轻神重礼”,这是一种封建文化和氏族文化的产物。这种文化饱含着冷静深沉的“忧患意识”,如重人事,重伦理,重礼教,重乐感,因而较之夏的“尊命”,更具有“人文”色彩。这种忧患意识一直贯穿着中国文人士大夫体性修身,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群体意识),而且是忧先于乐的(忧患意识)”。[8]正是这种忧患意识的体现。
三、乐美之观
孔子非常重视艺术对于人格的影响作用。孔子认为“善”即美,艺术的功用首先为政治服务,这也深深地影响到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在面对人生的困惑和现实的窘境时,他采取“中庸”的态度,在对于艺术欣赏和评价时,他采用“中和”的方法。
(一)乐与教
教,模也,学,觉也。教与学之间有间距,故需乐来弥合,即发从心底,身心愉悦地学,才会有所觉。“《说文》:‘儒,术士之称。’是故谓术士为儒,凡有一术可称,皆名之曰儒,故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别。”[13]由此可知,孔子之前,儒已有之,及孔子后儒业始兴,儒家变成了一门学派的代名词。“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1],这是整部《论语》中唯一一次出现的“儒”字。俞樾说:“师者,其人有贤德者也;儒者,其人有技术者也”。“哀公曰:‘敢问儒行?’孔子对曰:‘儒有不损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慁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诟病。’”[3]故孔子也曾耳提面命地告诫曾子“君子儒”与“小人儒”之别,孔子把传到授业与德行培养结合起来,以成“君子”为己任,故后世以“儒圣”来尊称孔子。
孔子教者,范围虽广,以心性的修养和人格的完成为宗旨。子贡说:“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1],“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1],“子以四教,文、行、忠、信。”[1]孔子在与诸弟子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常言道,言传者易,身教者难,诸弟子如此评价孔子,足以见其人格魅力。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1]钱穆先生说:“乐:悦在心,乐则见于外。孟子曰:‘乐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慕我者自远方来,教学相长,故可乐也。”[14]孔子以乐导其心,心愉而婉容,乐以教其诚。在孔子之前教育是贵族子弟的特权,平民阶层是没有资格接受教育,孔子是首个提出教育平等的第一人,孔子说“有教无类”[1]故其门下弟子无高低、贵贱、长幼、职业、种族及国界之歧视,足以见其乐教之心,并育万物。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孔安国注云“乐所以成性”,可见“乐教”是“诗教”的完成,“乐”在陶冶性情,完善人格方面比诗更具重大的作用。孔子说:“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遊,乐宴乐,损矣。”[1]乐骄,则戒奢以明节;乐佚,则戒惰而闻善;乐宴,则戒勿淫而亲小人。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弥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孔子善以《诗》教,故其提出兴、观、群、怨说。“诗可以群,就意味着个体通过诗(艺术)的激发,宣泄自己的感情(兴、怨),或体验他人的,社会的感情,而实现本人或他人、个人于社会之间的情感交流,并体验到个体作为群体的存在;通过客服个体的孤独感和卑微感,以高度的自觉和热情回到群体中,在群体的存在中得到协调的情绪感受,于是就从心理上确证了自己的群体性。”[8]故不学诗,难于与人言,人与人相处,心与心相通之道,应于诗中求。知于心与心相通之道,乃始知人与人相接之礼,由此心与心相通,人与人相接之诗与礼,而最后达于人群之和敬相乐。
春秋末年,周室衰微,周师解体,学术分裂,即上层贵族之解体(原来的贵族已经失去贵族的身份),但原属贵族掌握的知识并没有因其政体地破坏而遗失。孔子是没落贵族的后裔,其掌握着上层贵族的礼教知识。“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悔焉”[1]脩即干肉,又称脯,每条脯即一脡,十脡为一束,因此束脩就是十条的干肉。孔子招收弟子,弟子只要象征性的送些薄礼,以表示尊师重道。故其首开私学门风,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使得平民阶层也有机会获得知识。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远。”[1]孟子抓住前半句“性相近”,因此提出性善论,人天生就被赋予了性善的基因在里面,后天的习只不过是将善性的因子唤醒,一旦善性被唤醒,就变成德性。这种性善论是最初的“复性之说”,即以天性为德性。而荀子抓住后半句“习相远”,因此提出了“性恶论”,其认为人的本性就是恶,并没有善之存在,因而只有通过后天的习才能,故有“积善成德”说。
(二)乐与乐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不知乐者,众庶式也,唯君子为能知乐。”[3]乐者,乐也,指音乐给人带来一种精神形体上的享受。但音乐不仅仅是给人以感官上的享受,音乐演奏本身就有仪式感,而这种仪式是符合儒家传统的人伦至理,对人的道德和人格上起到熏陶作用。“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3]乐是诗、歌、舞的结合体,诗以述其志,歌以传其声,舞以蹈其容。从诗、歌、舞来表达乐才不失礼,而此乐才是伦理之乐。孔子说:“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1]音乐的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音律有着高低起伏的变化,情感如同音乐一样有着起始与高潮。“子谓《韶》,尽善矣,又尽美矣;谓《武》,尽美亦,未尽善也。”[1]孔子在这里对舜乐《韶》与武王乐《武》进行了比较,从思想性、艺术性上作出全面的评价,他认为《武》未达到尽善尽美的原因在于,武王伐纣,是臣弑君,《武》乐带有以下逆上之意,与他的仁爱思想相悖。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乐之至于斯也’”[1]三个月是象征性的语言,形容时间之长;肉味是与人体物欲相对,表示是人的味觉。三个月连对肉的味觉都忘掉了,说明其的精神已经超脱了形体的世界,从肉体解放出来,而其精神却停留在对《韶》的世界里,形体仍然受到束缚,被人间烟火所笼罩着,但是却不影响其心地飞驰,心离形外,形坐心驰。孔子深深的沉醉于这种美的意境之中,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3]儒家的这种审美意识是以静观为审美的最高境界。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1]朱熹解释说:“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滯,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1]孔子以“乐”作为媒介,而“仁”才是它最终的目的,“仁”这种最高的道德品质正体现了对山水的审美观中。“移情”即把人的情感赋予物,使物拟人化,也具有一样的情感,故作为一种审美理论,虽在中国没有得到过抽象的研究,但作为一种审美态度,却早已有之。孔子所谓的“智者乐山,仁者乐水”与“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无不体现了这种“移情于物”审美姿态。孔子的这种审美观念是有前提条件的,这种境界必须是于政教融合一,它不可能单纯的就只是欣赏音乐,作为审美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乐”的概念成为通向道德境界的天梯。孔子说:“乐则《韶》舞,放郑声,愿佞人。郑声淫,佞人殆。”[1]音乐,如果失与礼的节制,也就失去其审美的意义。艺术审美的手段是为了提高个人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孔子认为审美体验应该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道德情感的阀限和审美静观的尺度正相吻合,达到了一个中和——即“中庸”的美。故这种美学思想的宗旨是为政教服务的,不是因为美而单纯的欣赏美,所以这种境界是立足在社会理论观上的“温静”,这种温静恰好是沟通政教态度与静观态度的中介。“这个基本思想使得中国艺术对情感的表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保持着一种理性的人道的控制性质。极少堕入卑下粗野的情欲发泄或神秘、狂热的情绪冲动。”[15]政教态度与静观态度刚刚好形成互补,在这一静一动之间,形成了中国古人审美理想的人格——温柔敦厚。
四、结语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即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父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卒相与辑而论篹,故谓论语。”[4]又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论语》是描述或记录孔子与诸弟子在日常生活中的教学活动或对话,孔子卒,众弟子辑而论篹,故谓《论语》。“周人创立、孔子高扬‘礼乐文化’,试图以伦理代宗教、以美感代信仰、以教化代刑律、以艺术代政治,结果反到是伦理代替了宗教色彩(所谓的儒教),美感具有了信仰作用(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教化变成了刑律(礼治与孝治),艺术变成了政治。”[8]不可否认的是,孔子在保护先秦典籍,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又汲汲入世,倡导“学而优则仕”以天下为己任,作士大夫入世精神的楷模。但是其思想仍然受到时代的局限,孔子曾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1]孔子提倡“有教无类”却把女子排除在外在教育对象之外。《论语》是记录孔子与诸弟子教学交流的话语,却没有一个女子,或是受到男权主义的影响,还是身处时代的局限,孔子对女子教育明显带有带有歧视。“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对此,孔子说:“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1]由此看出,孔子反对女性参加政治,“孔子在这里将武王的十位辅臣中除掉了武王之妻邑姜这一女性。妇人不得参与政治,因而不配位列辅臣。”[16]从《论语》上看,孔子对学生的教学内容,偏重于道德的修养和人格的塑造,很少反映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知识。樊迟向孔子请教庄稼和种菜的事,被孔子训斥为没有出息。“学而优则仕”一直是孔子的执教理念,孔子希望通过提高道德与人格来培养德才兼备的弟子从政,也正因如此的缺陷,对中国后来的两千年的传统教育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中国的智识分子把读书变成一种求取功名的工具,而忽视知识可以转变成为一种生产力,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
但是,我们不可忽视音乐的娱乐功效和以及对人的审美情感的重要作用。孔子以“仁”为轴心来调和礼乐之治,从而形成了儒家的伦理美学,孔子希望这种伦理精神能够调和社会矛盾,恢复到周礼制度,用“礼”来实现其政治思想的载体,然而其思想终落空。但是其所创造的音乐伦理精神对于当下发挥音乐的德育功能有重要启示。这也是我们所提倡的“文化自信”,进一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国所特有的和谐社会价值观的一条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