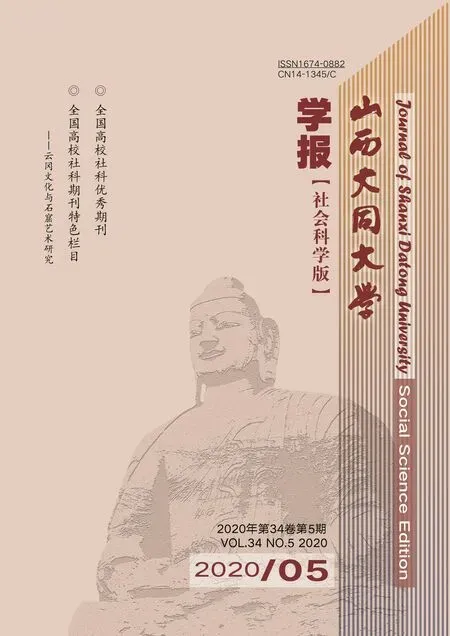论《宋书》《魏书》佛事记载的差异
卢鹏程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政治与公共关系管理学院,山东济南 250103)
东晋、十六国以后,佛教传播迅速,出现了一批专门记载佛教历史的著述,如《高僧传》、《出三藏记集》等,官方史著中也有佛教事迹的记载,如《宋书》于《天竺迦毗黎国传》后附记,《魏书》则有《释老志》专述。南北正史虽都有相关记载,但又表现出各具特色的一面。《魏书》对佛教传入中国的历程记载更为明晰,《宋书》则概述大略,而且是在记录与他国交往之后,因其诸国皆事佛道,才用带叙的形式简要介绍了佛教在本土的情况。因两篇记载一为志,一为传,文体不同,在佛事记载的裁剪取舍上差别很大。《宋书》专记当朝之事,虽然涉及到部分人、事,但前后看不出有何关联,使人仅能模糊感知刘宋佛教的片段,难以形成系统认识。反观《魏书·释老志》,对佛教的记载基本符合“志”体要求,“以精炼通俗的文字,对佛教的基本经旨教义以及教徒的习俗等,从文化的角度作了简明的介绍。”[1]可以说,《宋书》是将佛事简单视为历史事件,而《魏书》则是将佛教相关事项列为重大社会问题。对南北朝佛教入史差异考察已有学者作过比较研究,本文拟从佛教传播面貌与南北朝不同政治现状角度,对佛教事迹载入正史现象作一补充辨析。[2]
佛教在南北朝均有发展,但付诸文字笔端却呈现详略差异,甚至在处理态度上有强烈反差,早为学者觉察。北魏佛教兴盛,史官魏收以其自觉意识专志记载,与前后史家相比更可称其“尤为卓见”。[3](P223)而东晋以降,南朝宋、齐、梁世佛教蓬勃发展,但如钱大昕所言,“晋南渡后,释氏始盛。宋文、梁武之世,缁流有蒙宠幸者,然沈约、姚思廉之史,不为此辈立传。”[4](P136)面对客观历史而不加撰述,倘若不是因为狭隘观念的针对,则必有其他难以言明的障碍。更何况沈约出身天师道世家,又是与佛教有密切关系的竟陵八友之一,其佛教信仰早已为人所知。但为何《宋书》中没有给佛教留出起码的位置,值得进一步思考。或称可能因时间有限不能将《宋书》从头到尾仔细修订,首撰者何承天的反佛态度保留下来,[5]或是径称沈约继承何承天的抑佛思想,[2]都略显草率。沈约于《宋书·自序》中称前人之作“立传之方,取舍乖衷,进由时旨,退傍世情,垂之方来,难以取信”,因此他要“谨更创立,制成新史”,[6](P2467)从这点来讲,即使编集《宋书》时间较短,沿用何承天、徐爰等人旧本,沈约仍有强烈创新意愿。抛开沈约与何承天对佛教的正反态度,《宋书》的传记中尚可见其他受佛教感应思想影响的记载,如刘义庆因太白星犯右执法惧有灾祸请求外调,但宋文帝诏称:“天道辅仁福善,谓不足横生忧惧。兄与后军,各受内外之任,本以维城,表里经之,盛衰此怀,实有由来之事。”[6](P1476)这里掺杂着传统天命观与佛教的因果感应,在刘宋开国僧徒献瑞事件记载中也有反映。再如王玄谟因梦中被告知诵观音经千遍能免死,“既觉,诵之得千遍,明日将刑,诵之不辍,忽传呼停刑”,[6](P1974)这是典型的观音救难应验。由此说明《宋书》并非简单的抑佛排佛就能概括。也有学者以传统史学中儒家文化本位立场解释《宋书》对于佛教内容的安排,认为“对于传统史学来说,从感情上对佛、道等非儒家的异端意识形态,必在排斥之列;从内容上,亦因其无补于治而不取”。[1]就当时文士的观点来看,后句应该是成立的。如依范泰、谢灵运等言,佛家学说在于解决心灵上的问题,儒家学说则侧重现实政治。袁粲亦言:“孔、老、释迦,其人或同,观方设教,其道必异。孔、老治世为本,释氏出世为宗。”[7](P931-932)这些都是信仰、研究佛教思想的文士所言,既是为佛教超脱俗世推广,又可说明佛教于传统史书的资政功能无用。但就感情排斥一说,似是忽略了《宋书》、《魏书》均有佛教事迹记载这一相同之处,当有史学自身以外更现实的背景原因。笔者认为,在比较南北朝佛事入正史的差异之前,应先解答何以两部史书中均有佛教事迹记载。
一、北朝佛事入史背景
北魏承继十六国而来,十六国政权统治者多为少数民族,与被称为“胡神”的佛教有天然亲和力。典型者如后赵,西域僧人佛图澄极受石勒、石虎崇信,“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著作郎王度以旧制汉人不得出家求禁,石虎则自称“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8](P2487-2488)后秦姚兴托意佛道后,“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8](P2985)可以说,从河西到河北,从凉州到长安,都有佛教的身影。拓跋鲜卑兴起以后,逐步平定统一北方地区,迁徙的各政权旧属就包括大量佛教僧徒,“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9](P3032)北魏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自然继承其他少数民族政权。
北魏建国初期,便将佛教作为稳定统治的手段,对那些信仰佛教的被征服地区实行安抚政策。到明元帝拓跋嗣时,“遵太祖之业”,“仍令沙门敷导民俗”。[9](P3030)不过在统治者看来,佛教并非唯一的统治手段,道武帝拓跋珪“好黄老,颇览佛经”,[9](P3030)佛、道并无区别对待。太武帝拓跋焘“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9](P3033)其后又因有沙门私藏弓矢,于太平真君七年下诏灭佛,“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9](P100)不过需要注意,北魏实施灭佛还俗一事,某种程度上可能会促使佛教渗入底层民间社会,信众传播更广。而文成帝即位后下诏称:“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等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妙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9](P3035-3036)有学者早已指出,“就北魏对佛教的政策来说,和其实际的利益有关”。[10](P35)北魏对佛教的态度完全是从维护统治角度出发,前后兴佛,因其能安抚治民。至于灭佛,则因“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9](P3034)有损王朝安稳。
针对统治区域内佛教信徒众多的现实,北魏统治者在巩固权威方面有诸多举措。首先是设置道人统、沙门统等僧官制度。道人统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9](P3031)僧官制度将僧众与统治阶层绑为一体,僧徒受宗教戒律与世俗政权双重管辖。其次是大兴佛事。自文成帝始,先“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后又“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9](P3036)从保留至今的云冈石窟诸佛像便可想知北魏兴佛之规模耗费。这种将宗教信仰与政治统治融为一体的方式,应对维护拓跋政权在北方地区的稳定有重要作用。再次是自上而下的推崇佛教义理。“陇西王源贺采佛经幽旨,作《祗洹精舍图偈》六卷,(赵)柔为之注解,咸得理衷,为当时俊僧所钦味焉。又凭立铭赞,颇行于世。”[9](P1162)宣武帝元恪本人“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沙门条录,为《内起居》焉。上既崇之,下弥企尚。”[9](P3042)“上崇下尚”反映了整个北魏的崇佛氛围。北魏分裂后,北齐、北周承继北魏的统治范围,北齐佛教兴盛不减,北周则有周武灭佛,两方差别均与维护统治需要有关。[11](P44-58)
北朝佛教风气渐浓,对当时的学术文化有所影响。如儒宗刘献之“注《涅槃经》未就而卒”,[9](P1850)孙惠蔚之“惠”字亦因论佛而得。[9](P1854)可见,北朝文士对佛学有所涉及,文士的知识构成必然会受佛经所体现的思想影响。不过北方佛教义理尚未显达,这种影响又不十分显著。并且中原士人中不时有抑佛之论,如崔浩视佛教为“胡神”,[9](P827)李瑒认为沙门绝户有违孝礼,“三千之罪,莫大不孝,不孝之大,无过于绝祀。……正使佛道,亦不应然,假令听然,犹须裁之以礼。”[9](P1177)李崇奏请复兴国子学时认为经国治要应先于兴佛之事。[9](P1472)这些言论均有针对,虽是个别,却与更广泛的兴佛言论形成对比,说明北朝文士尤其是部分中原文士,对佛教持有谨慎态度。
北魏社会存在重史风气,关注佛教在北地传播扩散这类影响重大的社会事件,正是北朝佛事入史的社会背景。不过相对南方,佛教与史学的互动联系在北方主要停留在表层,即北朝史家撰述时关照社会问题,将佛事纳入史籍之中。有学者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史学的关系时已有发觉。[12](P85-104)与李彪齐名的阳尼“少好学,博通群籍”,任秘书著作郎时“奏佛道宜在史录”。[9](P1601)阳尼虽未有相关文字传世,其原意不可确知,但以史官身份上奏此论,应是史家撰史自觉选材的体现,将宗教与政权统治下的著史活动联系,留存史事之心可见。由此推之,魏收撰《魏书》时列《释老志》详记佛教传入之后的历史,应与阳尼一脉相承。而其典型,则是杨衒之作《洛阳伽蓝记》。杨衒之生于北魏,仕于东魏,武定五年(547),杨衒之因事重览洛阳,却见故地“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刺”,“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寮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13](P2)杨衒之感慨所撰,不仅是记“伽蓝”,更是记国之盛衰,从佛事兴衰角度总结北魏衰亡的经验教训。
二、南朝佛事入史背景
南朝佛教传播与北朝不同,区别在于玄谈义理的程度。这与当时北方战乱,文士僧徒南迁有关,“南北佛学,风气益形殊异。南方专精义理,北方偏重行业,此其原因,亦在乎叠次玄风之南趋也。”[14](P340)两晋玄谈之风大兴,佛学与玄学在超越现实、经验层面存在一定的契合,特别是一些佛教徒,除了译注佛经之外,还注老、庄,正如汤用彤所论:“《般若》大行于世,而僧人立身行事又在在与清谈者契合。夫《般若》理趣,同符《老》、《庄》,而名僧风格,酷肖清流,宜佛教玄风,大振于华夏也。”[14](P153)对中原文士而言,佛教学说乃“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道书之流也。且好仁恶杀,蠲敝崇善,所以贤达君子多爱其法焉。”[15](P2932)《世说新语·文学篇》中有多处东晋文士与僧徒交流的记录,儒、释、道三教相通,是晋室南迁之后佛教被中上层文士接受的主要原因,有别于北朝的“胡”族统治因素。而在接受之后,佛教思想悄然内化到文士的知识结构之中,进而影响行事风格,则更甚于北方。南朝史家多受佛教思想影响,或是认可,或是笃信。如刘宋文帝曾说:“范泰、谢灵运每云: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灵性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16](P576)梁裴子野,“末年深信释氏,持其教戒,终身饭麦食蔬。”[17](P444)《宋书》著者沈约更有多篇维护佛教文论。
南朝玄谈渐稀,而佛教已获得较稳定的发展,晋宋之际,道生立顿悟义,谢灵运著《辨宗论》为其与佛教旧势力辩论,称“去释氏之渐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极。一极异渐悟,能至非殆庶。故理之所去,虽合各取,然其离孔、释远矣。”答法勖问曰:“华民易于见理,难于受教,故闭其累学,而开其一极;夷人易于受教,难于见理,故闭其顿了,而开其渐悟。”[18](卷十八)僧徒与文士合作为佛教扎根华夏努力,既是佛教中国化的表现,又反映了社会对佛教的认可程度。南朝包括世族在内的统治阶层,对佛教的崇敬比北朝更甚,学界已多有论述。[14](P415-486)[19](P82-88)而佛教与政治互动典型者,如《宋书·符瑞志》载法义嵩山寻瑞,借佛教徒之口应验刘宋代晋的天命,刘裕承佛教相助之情,对佛教倍加崇重。[20]梁武帝从信道到信佛,是东晋南朝由天师道世家改宗佛教的代表,而其作为统治者,“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采取宽容态度,兼容并包,更易争取民心,往往比专崇一种信仰而打击其他宗教更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安定巩固”。[3](P321)在利用宗教维护统治层面,南北是一致的。
南朝同样设有僧官制度,分中央、地方、基层三重建置。中央僧署设僧正或僧主,地方有区域僧官、郡僧正及基层寺主,在整个系统中,区域性僧官握有实权,而中央僧官只是在形式上被赋予监督全国僧团的名义。南朝僧官更替有较明显的法系传承倾向。南朝还有刘宋设置的尼僧僧官以及梁武帝时设想的白衣僧正两类有时代地域特色的僧官制度。[21](P18-37)与北朝相比,南朝僧官制度反映了南朝佛教发展过程中适应政治区域性发展的特征,如成实学、三论宗、天台宗等学宗派别的传承,使地方教团发挥了更大作用,这与北朝统一控制下的佛教发展面貌不同。
相对应的,南朝的佛教史籍中有一类独特的佛事记载文本,僧史传记。汤用彤称中国僧传为两晋南北朝最发达之史书,详列了一人之传记、一类僧人之传记、一时一地僧人之传记、尼传、感应传、通撰僧传者等诸多门类的书目。[14](P574-587)从陈垣对《高僧传》、《出三藏记集》等书史学价值的评价,亦可知这类书籍于六朝史学的特殊地位。[22]然而这类书多是佛教僧徒所著,出于宣扬佛教的现实需要,或是记录世系传承,或是树立高僧楷模,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的夸张成分,又因其立场所限,很难从其中辨别出斥佛非佛的内容。有学者将这类史著归入狭义的佛教史学,称其特殊性在于“具备了历史学与佛学的双重性”,[23]表明僧史传记与正史佛事记载有所区别。而在南朝《宋书》、《南齐书》两部正史中,除了传主信仰佛教的相关记载外,仅有《宋书·天竺迦毗黎国传》中附记的零散佛教事迹与人物,与《魏书·释老志》单列专志记载反差明显。
佛教事迹入史著的南北差异,源于南北佛教发展的背景差异。这种差异呈现为史著体例中侧重不同,北方偏重事迹记载,南方则有佛教自身史籍。魏收所言“释老当今之重”不难理解,但沈约《宋书》中对佛教记载的处理方式,仅从南北佛教发展状况角度尚不能完全解释,还须从史官所处境地角度进一步考察。
三、夷夏之辨的视野
崇佛与反佛往往成对出现,面对一种宗教信仰,甚至是可能危及社会统治稳定的信仰,总会出现不同声音。佛教宣扬的因果报应、转世轮回之说与中国传统有神论相适应,范缜则针锋相对地提出神灭论。《魏书》中佛家感应、报应之说的明确事例多处,同时也有李瑒因佛教有违孝礼而反对的记载。南北朝时期的崇佛反佛之争,多与礼仪规制、社会利害甚至统治根基有关。在南朝,事关礼仪争辩典型者有踞食之争,[24](P115-127)在面对伴随佛教传入带来的印度式风俗时,范泰不再是捐资修建祗洹寺的信众,相反以中国礼教的捍卫者身份与之论争,这就从佛教经义虚的层面跨越到了行止这一实的层面。即便是被认为通晓佛教教义的范泰,在涉及到中原固有的礼仪、历史时,与佛教的疏离也可见一斑。
北朝对兴佛持反对意见的人,多是从危及社会发展立论。北魏孝文帝时,“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9](P3039)宣武帝延昌年间,“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9](P3042)北魏大兴佛事加剧了社会负担,宣武帝时宗室元鸾“爱乐佛道,修持五戒,不饮酒食肉,积岁长斋。缮起佛寺,劝率百姓,共为土木之劳,公私费扰,颇为民患。”[9](P510)孝明帝崇信佛法,张普惠上表称:“殖不思之冥业,损巨费于生民。……愚谓从朝夕之因,求秖劫之果,未若先万国之忻心,以事其亲,使天下和平,灾害不生者也。”[9](P1737)兴佛之害于北魏末年已现端倪,《洛阳伽蓝记》与《魏书·释老志》的记载都是因此而发,“流弊不归,一至于此,识者所以叹息也”。[9](P3048)南朝亦有因佛教影响社会稳定而排斥的立论,即便是兴佛最盛的梁武帝时也不例外,郭祖深认为“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养女皆服罗纨,其蠹俗伤法,抑由于此。”[25](P1721-1722)虽然南朝在学理上对佛教的认可程度较北朝高,但当佛教触及到世俗统治的底线时,必然要承担风险,裁汰沙门、强制还俗之类举措在南北诸朝均不少见。
北朝从辨明夷夏的角度排斥佛教,可能仅为崔浩一人所论,崔浩因国史案被诛后,北方史家对此类问题处理较为敏感,未见再有。而在南朝,因为面临北方外族政权的对峙局面,对佛教的认知极有可能与现实层面的夷夏之辨产生联想,由此产生的抑佛立场就更为强烈。前引谢灵运著《辨宗论》,其实已经涉及到佛教传播时的华夷之别,虽然谢论主要是为了说明顿了与渐悟的区别,为顿悟说造势,但是潜意识中对华夷做了区分。对北朝而言,胡(教)与胡(政权)通不是问题,“作为‘夷教’的佛教则受到少数民族统治者的特别崇重,有意识地使之成为辅助教化、统治民众的手段。这就使得北方佛教显示出更突出地与国家专制政权相结合的性质。”[26]对南朝而言,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出身渊源使得有关佛教问题的争论都与夷夏之别扯上关系,“胡汉分别不在种族而在文化”,“拜不拜王室,现象上是僧俗的区别,实质上是夷夏的区别”。[27](P291-296)
就佛教自身来说,为了更好的在华夏发展,必然要适应甚至用传统文化资源改造完善自己的理论,这是佛教一方的应对方式。作为佛教以外的世俗世界,统治者利用甚至崇信佛教维护统治,在其影响稳定时又加以控制的决策不必多言。此外文士之中又有信佛与排佛两类,反对佛教最著名者,莫过于顾欢著《夷夏论》。顾欢崇道抑佛,称“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异。”“舍华效夷,义将安取?”认为佛教只适合外国而不适合中夏,“虽舟车均于致远,而有川陆之节,佛道齐乎达化,而有夷夏之别,若谓其致既均,其法可换者,而车可涉川,舟可行陆乎?”[7](P931-932)针对顾欢的言论,佛教徒进行了多次反驳,甚至发展出佛教发源地天竺才是中土的理论。[16](P396)梁时僧祐归纳对佛教质疑有“教在戎方,化非华俗”一项,在其后的应答中提及一句:“伊洛本夏,而鞠为戎墟,吴楚本夷,而翻成华邑……故知天竺居中,今以区分中土称华,以距正法,虽欲距塞,而神化常通。”[16](P800-801)可以说,华戎夷夏的区别,在佛教神通普化之下是不存在的。这种文化层面上的论争给佛教创造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使得南朝不曾发生剧烈的灭佛动荡,但也潜伏着佛教中国化的暗涌。
有意思的是,北朝主持灭佛的北周武帝称:“佛生西域,寄传东夏。原其风教,殊乖中国。汉魏晋世,似有若无。五胡乱治,风化方盛。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而僧任道林回答:“佛教东传,时过七代,刘渊篡晋,元非中夏,以非正朔,称为五胡。其汉魏晋世,佛化已弘,宋赵苻燕,久习崇盛。陛下耻同五胡盛修佛法,请如汉魏不绝其宗。”[18](卷十)前者以非胡族故不信胡教,与后赵石虎处境虽同,但以华夏自居,态度截然相反。而后者回答称若非胡族、不与五胡同列,则沿袭汉魏正是恰当。这场覆灭北齐之后谈话,实际上是以辨明夷夏之名,行收拢新占区域财力之实。但对比当时南朝对佛教的崇信程度,北朝后期统治者反而提出非胡身份不宜信仰胡教的理由,极为微妙。
佛教徒用来解决佛教并非不能普及华夏的辩证说辞,可能正是南朝官方史著对佛教态度纠结的根源。夷夏之辨,辨在政权正统与文化正统。官方编撰史籍,根本在于宣扬天命赞颂当朝,但南朝偏据一隅难控中原的现实使得著史者无法避开名实难副的尴尬。南北对峙、夷夏之别在南朝是不可忽略的政治现实,也是正史书写面临的首要问题。将佛教入正史置于夷夏之辨的视野下考察,会发现南朝史官处理佛事确有难题。北朝记载佛事,基本不存在身份认同的困难,当然随着对华夏文化认可度的增高,会出现反复,但在魏收编撰《魏书》时只需考虑用何种文体记载当时较为重大的社会问题,没有其他阻碍。而南朝记载佛事,则需多重考量。首先,佛教通传中外南北的现状不会抹杀区域政权的差异,相反,因其传播的范围已超越南朝政权统辖范围,又因佛教本外来宗教,顾欢所论:“佛非东华之道,道非西戎之法,鱼鸟异渊,永不相关”,[7](P934)佛教传播也就难以被单纯当做社会现象记录。其次,儒释道三家主次排序问题,道家作为本土宗教暂且不论,反佛言论多是从华夷有别角度阐发,实是由佛教理念冲击传统仪礼而起。佛教宣扬出世思想,僧属常又不受俗世制约,危及政权统治,偏偏统治者大多崇信佛教,甚至有梁武帝舍身之举,这对怎样用传统观念评判佛教造成困扰。再次,佛教传入已历数代,随着对其认知增加,从感应、报应、轮回之类佛教概念到抽象、思辨的思维方式都已与传统天命观、谣谶说结合,甚至一些佛教应验故事模版也成为史家笔下套用的材料,即使是排佛者也难以一一甄别。以上都会是《宋书》记录、裁剪、处理佛事记载过程中避不开的因素。
晋世官方史著中有无佛事记载已难考辨,《宋书》编撰早于《魏书》,似乎之前并无可以参照的处理方式,带叙法成为可行的尝试。赵翼言“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而不为立传则其人又有事可传,有此带叙法,则既省多立传,又不没其人,此诚作史良法。但他史于附传者,多在本传后方缀附传者之履历,此则正在叙事中,而忽以附传者履历入之,此例乃《宋书》所独创耳。”[28](P194)若将有关佛教事迹视为一个整体,则《宋书·天竺迦毗黎国传》符合带叙法的界定。依政权统治下的正史撰述活动而论,不同于北朝《魏书》单纯只需考虑如何写,由于南北对峙局面下华夷有别、正统之争的现实困扰,南朝官方史学需要完成能否写、如何论以及度的把握三重推敲。就史官自身自觉意识而言,不得不写的佛教事迹如此处理不失为一种取巧的做法。《宋书》、《魏书》佛事记载差异,作为南北史学差异的一端,亦可见对峙局面下史学与政治之纠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