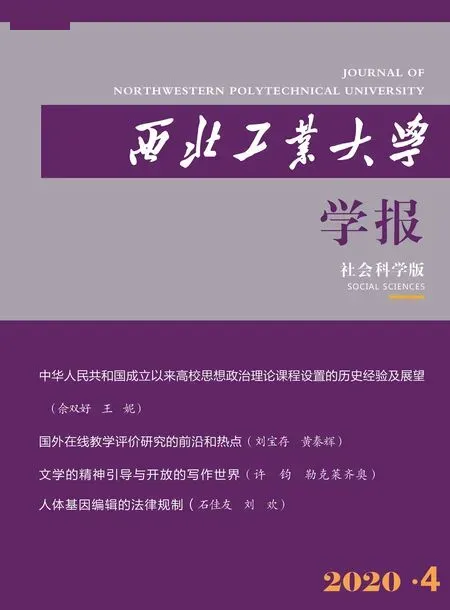从多元主义到跨文化相联
此次全球疫情,以令人无法预料的方式影响并持续影响着每一个人。8月,我一边在线上为2020年毕业生作毕业致辞,①一边牵挂着2019年毕业学生的境况;他们中很多人正在各地求学,一波波疫情直抵他们所在地,包括欧洲和美国。一位学生问我是否开个班会,我马上答应。于是,8月1日按他们的安排上线,在不同国家地区、不同语种环境中进行学习的青年们一起出现在屏幕上,其中有一位完成援藏支教实习,刚回到老家。一瞬间,仿佛时空世界一统。但这一统时空很快示意出其中时间地域差和语言文化差的巨大张力。交谈变得简洁,简洁程度和跨越差异的程度成正比,每一句话之后的停顿,是时间也是空间,是句号也是省略号;是转瞬间个体生命的回音,也是流动中多重历史的呼应。我看着听着他们每个人,如何在每次“跨越”中传递各自的异地生活,每次“相联”中感知对方的语境差异,这里有一种相互辨认的探索、相互牵手的尝试。而那天的话题,是“跨文化能力”。之后,其中一位学生发邮件给我,这样说:
之前表述的跨文化过程,常用的一个意象是“回音”或“呼应”(echo),指不同历史文化信息在流动中互相应和,在听者心里留下些许波澜印痕。这其中其实还包含抵达心智的触动,并让人联想到一种更积极的过程,听者由此不仅产生安全距离外的思辨认知,而且带来内心的感悟,和由此产生的跨文化相联相通。
学生是指线上班会里讨论的不同民族文化养成的人们,如何在交流中相联,以获得相通的不同方式;这也是拥有共同的中华民族文化养成的他们,在国内外世界各地展开人生的过程中,从各自经历的语境差、时空差里吸纳精华,相互之间如何再交流、再发现的命题。英国作家福斯特曾说过“只有相联相通,美才会诞生”。这似乎是一种事实表述,更似乎是一种愿望期待,触及某种现代人安身立命的心智支点。自从人们的相互关联不再由神祇(以及帝王)给定的秩序来界定和固化,如何相联作为现代生活的母题之一就应运而生;而相联的方式和内涵千差万别,多种多样。②当下关于世界文学的研讨,是较有影响的一个案例。本文通过对其中一些跨文化文本的分析,对此稍做展开。这里需要简要说明的是“跨文化”一词的定义和运用。当代中外学界“跨文化”研讨已有数十年历史;其前提,是近代以来以“民族国家”(nation-state)来界定的“民族文化”;其重心,是超越“民族文化”这一欧洲范式所示意的“同质性、稳定性、界限性”③,从而指向不同文化传承之间的交汇、交叠、交融和延展④。在此前提下,笔者这里所称的“文化”更为具体,主要指以母语为载体的心智传承、精神谱系和互相关联的生活方式。由此,“跨文化”是指某个个体或群体跨越各自的母语及其心智、生活、精神传承的轨迹,进入包含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流动相遇、对话延伸的过程,乃至在过程中发生的思辨形态和更新活力。⑤
当代数十年科技和经济巨变中产生的跨文化流动,剧烈浩瀚;学界对此现象及其持续变奏,各有理解。持乐观态度的哈佛大学“世界文学”学派有一定的影响。⑥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提出的理论阐释,既是学理层面的专述,也是落实在课程设置方式中的实践。马丁·普赫纳(Martin Puchner)作为其成员和某种意义上的普及者,近期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他原版英文《文字的力量》 (TheWrittenWorld),是一门“世界文学”网络通识课程的文字形式,中文版2019年7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⑦普赫纳协同数位学者于2012年出版了《诺顿世界文学选》(TheNortonAnthologyof WorldLiterature),由来自不同国别语种文学领域的上百位学者合作,力求做到文体和题材上的全面和多样。诺顿文集编撰的雄心,当然不是提供简单按照国别顺序的各国文本罗列,而是致力于将各国文学的文本“带入一个相互关联、相互呼应的宏观图景,着重突出各国文学在历史上(特别是中世纪时期)的交往和历史性的关联,以及一些重要的文本和母题在不同作家那里的回音和变奏,在其中贯穿了一种世界地图、世界文学和世界史的意识。”由不同语种文学专业人员构成的编撰共同体,明显超过前两版的覆盖度、更新度,使得这一“世界文学选”的第三版显得比之前的版本更有理由如此命名。⑧
与他的同事大卫·达姆罗什相呼应,普赫纳将“世界文学”的理念追溯至歌德。在2019年9月做客清华大学世文院外文系国际人文研讨课暨清华论坛世文讲演时,普赫纳回顾,作为一种心智实践,文学如何在四五千年前出现在世界各地;而世界文学的观念,则是1827年1月31日歌德在阅读17世纪中国小说时产生的灵感,被他的助手爱克曼记录在两人的谈话录中。普赫纳强调,世界文学的宏大理念并非诞生在巴黎或法兰克福这些大都市,而是在年岁已高的歌德寓居的乡间城镇,这正是因为歌德在试图超越小城镇的空间限制。19世纪德国国家主义兴盛,此时诞生的世界文学理念中蕴含着国家与世界的矛盾。从歌德憧憬的世界文学和现存强势的国族文学之间的差异性中,普赫纳看到的是世界文学的包容愿望或者说进步意义。他没有回避这一观念的大背景,即19世纪的欧洲殖民扩张及其文明“世界传播”的历史条件:“多数殖民国家觉得有必要通过主张一种观点来证明他们行为的正当性,即欧洲殖民者是在将文明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这意味着那些研究被殖民者的东方通常带着优越感看待这些文化。”⑨但德国在欧洲宗主国殖民竞争中相对滞后,成为普赫纳将歌德与之完全区别的根据:“于是,歌德身在魏玛这个远离都市的地方,这变成了一个优势。他的魏玛公国与帝国主义毫无关联:许许多多的中小型德意志帝国,没有一个拥有殖民地。这意味着歌德可以间接地获益于他国的帝国主义,同时避免征服外国文化(的欧洲行为)以及它常常导致的错误的优越感。”并特别提出歌德重视翻译,“认为世界文学建基于一个由翻译推进的全球文学市场”的远见性。⑩普赫纳是在谈历史,也是在对人们如何处理当下的巨变做建议:就当下而言,数十年的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又一轮多语种翻译的新浪潮,国别之间联系越来越紧密;这相联不仅存在于实业界,也存在于不同文化的文学之中,其中多变的张力具有的生产性,日显重要。
听着远道而来的同行面对中国师生讲着“世界”和“文学”,一种“回音”(echo)唤起多年前的记忆。我20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高校开始任教,面对主要是欧美裔的学生开设比较文学导论,起篇即是对歌德“世界文学”主张的阅读和研讨。⑪我与学生们讨论1827年那场著名的谈话,歌德如何宣告“世界文学”(Weltliterartur)时代的来临,如何认为民族国家文学将变得不合时宜。⑫歌德的这种宣告,一方面与当时的技术发展、世界市场的逐步成形,翻译文学的兴盛与报刊杂志、旅行文学等跨越国界的提速流通相呼应,⑬另一方面,是对这一流通所携带的特定欧洲语境中,所谓“拿破仑遗产”的回应。歌德看到,“对于被巨大的战争抛入混乱交织、然后又回复到互相分立状态的所有民族而言,人们意识到他们观察和吸纳了极为多面的不熟悉的事物”,开始感到“某种之前从未知晓的精神需求”。不同的民族,或者更准确地说,居住在不同欧洲民族国家的作者们应当“相互关注和理解。如果他们不想互爱,至少他们要相互容忍”。1827年10月,歌德给友人泊瑟瑞(Sulpiz Boisseree)写信:“我所说的世界文学最有可能发生在这样的情景中:一个民族内部占主导的差异和矛盾,通过其他民族的见解和判断来得到和解。”⑭这里的重心是文化欧洲,和欧洲民族国家及其方言化的(vernacularized)语言文学。倡导世界文学的歌德本人,是以德语民族语言写作的驱动性人物,而民族语言正是创制民族文学的界定性载体。并不奇怪,从中国小说发现灵感的歌德,同时认为世界文学的范本不能交由古希腊以外的任何地区。事实上,对歌德而言,整个世界将会是一个立足于希腊文明的德意志祖国的延展(expanded fatherland)。⑮这并不否定歌德世界文学观的巨大想象力,其中凝练着人类历史上重复出现的社会情形和心智状态:大迁徙时代驱动着人们超越既定的社会与文化关系,也引发着人们与他者构建和扩展关联的渴望。同时,近现代世界历史,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经验,使得我们认识到人的“渴望”脱离不了具体的历史条件及其作用,其深度的多面性始终需要反思,要求我们更为具体而历史地探讨与他人建立“相联”的方式。二战期间,德国士兵或军官背包里携带着歌德的作品,是一个难以轻易一笔带过的世界性文学文化现象,迄今学界仍在探讨这一现象,以求化为拓展人类认知的经验。如果选择将“世界文学”作为一种方法和愿景,如何对展开愿景和践行方法的具体过程同步反思、有所自觉,可能是关键;我们需要关注多种力量交互影响、共同作用的交织或结果;有意识设立的历史目标和具体发生的历史后果之间可能出现的偏离,甚至断裂。特别是在当下文学观念显性变更和文学生产结构性移动的时空里,以往的多重经验要求我们去思考,如何开启更具包容性、差异性、生产性的心智行为和相联路径,从而有别于近代以来以同质化世界市场为单一驱动、以其化约规定的“西方文学”为思辨中心和观念定势。⑯我与普赫纳在交流中,做了一个具体说明:清华大学世文院外文系近年来“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提法,是描述性而非观念性的;旨在根据中国外文人文学科的需求,拓宽教研范畴和实践空间⑰,以助师生在深化自身作为“外文专家、中国学者”的专业辩证自觉中,克服“中外文化”二元对立的划分,在对千差万别各种语言文学的探讨中,将世界上不同民族和地区的语言文学,与更新绵延的中华传承相互关联起来,催生在语言文学、人文认知的领域里,具体多样的对话和互为更新的开放版图。这一描述与哈佛学派的提法相关联、有“回音”(echo),但其内在的基本逻辑,不指向典籍化、机制化、统领性的“世界文学”。⑱
普赫纳对这种描述性而非观念性的“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表示理解。他提到修纂诺顿文集第三版的主要目的,正是增扩开放性。首先,选集旨在为开授世界文学导论课程的中学和高校老师提供教学上的参考材料。在此过程中,编撰者们声称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对世界文学的渴望往往来自偏远闭塞的地方,越是在地方偏远、排名一般的地方高校,对于世界文学导论课程的需求就越强烈,世界文学给那些很少有机会去海外旅行的学生们提供了一个认知世界、开阔眼界的机会。因此,文集编纂的精神是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鼓励人们向更为多元的文本开放。就美国而言,时代变迁带来了文学类课程的兴衰和转型。二战之后,美国社会以欧洲移民为主,“文学经典”仍以西方文学为主。1965年后,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增多,对于文学课程的范围和题材提出了更为多样化的要求,阿拉伯、墨西哥、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学文本进入了视野,也重新塑造了对经典的定义。同时,“选集”还示意着读者和使用者对自己选择阅读方式的更新路径。当下的互联网时代,许多方面呈现出一种类似“编辑文选”的“再创造”行为,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和喜好,对网上的文本进行筛选、剪切、拼贴、重新排列组合并加以收藏,打开丰富多样的个性化可能。⑲
对普赫纳所属哈佛学派蕴含的文化多元主义的驱动,中文书评反馈基本积极;人们从中看到了文学史书写编撰方式的变化,有助于中国文学进入欧美图书和教学渠道、获得某种经典化即主流化的正面契机。⑳部分英文学界的书评,从文学是历史和日常生活构成部分的角度入手,强调了科技变革时代人文学的不可或缺性;分析普赫纳揭示了在科技变革书写更新的湍流中所出现的“奠基性文本”如何“在历史长时段中积聚力量和重要意义,直到他们成为整个文化的语源,告知人们,他们从哪里来、他们该如何生活”。文字文本是在与人群、文化、文明、历史的兴亡的关联中撰就;是对人间兴亡形态建构的一种力量。㉑这些多角度积极见解,与普赫纳意在建立的“一个全新的人文视野角度”互有回音呼应(echo),各有洞见。㉒但这些呼应,没有面对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即作者编者付出深切关注和思辨劳动的“多元文本”,是以英文来承载、流通、再现其存在的。作为欧美数十年来文化多元主义流变中一个成功案例,这一具体但不简单的细节提醒我们,哈佛世界文学学派是如何既凝聚和体现了多元实践中的精华愿景,又始终无法处理其中 “anglo-centric”(盎格鲁中心主义)或“euro-centric”(欧洲中心主义)的在场及其局限。过去数十年为所谓“语言学转向”影响的人文学主要成果使我们了解,这是语言话语,也是文化秩序、地缘政治和流通机制的在场和局限。㉓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开始在美国执教,作为青年代表受邀参加教研改革委员会,经历了以这样的多元主义为基调所进行的人文学科岗位设置修订;这样的岗位修订当时发生在全美各大主要高校,形成了自二战结束以来对传统意义上英美和欧美研究领域建制的再一次历史性扩展、学科和教授专业布局的一次重组和岗位所要求的学术成果类别的一次更新。当时英文系的主要增量是前英法属殖民地浩瀚的作家作品和学者(另一种命名是后殖民研究与批评);而比较文学系开始吸纳英法德之外的语种和传承。同样,这一重要的变革无法处理欧美中心的基本逻辑及其局限。如当时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同事文森特·皮科拉对一个“开放性”比较文学专业招聘文本分析之后所指出:“(由此可见)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位广泛掌握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主要源自法国的研究传统,代表性人物包括从阿尔都塞至齐泽克等。这些人可以说是从西方学科自身内部对其进行理论上的解构”;(我们同时要求这一位新人拥有)“对一种或多种非西方传统的深入学识”,从而能够“用非西方的观点看待西方的哲学”,以“反思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和边界、挑战比较文学的欧洲中心特征”,以双倍乃至多倍于同行的知识积累和传承资源,对“欧洲中心特征”进行批评——换言之,以“欧洲中心特征”为中心展开职业和思辨的人生,尽管是批评性的。这里的文化多元主义,离不开由语言话语、文化秩序、地缘政治和流通机制构成的“中心特征”。㉔
这样一种一个中心的多元主义,也存在于普赫纳期待“选集”在网络时代的多元性设计中。一方面,人们将以自己的“个性喜好编辑文选”,由此抵达“无限个性化”的文化多元主义境界。另一方面,抵达这一多元主义境界的结构支撑——或曰中心设施——是网络经济的世界一统。这里,作为乐观愿景的“多元主义”含有一个预设判断和具体后果:不同语言传承的文学、文化文明可以或平行自在、或叠加流转;不构成处理差异如何相互关联的问题;而“异质文化”如何相遇、相联、相通,作为跨文化流变中的命题基本消解。㉕不热衷聚焦“异质文化”的德国学者如伊利亚斯,在对文明和文化的区分中,留有对“差异文化”和“异质文化”的认知范畴,并提出处理方案。按照伊利亚斯的说法,文化是与生俱来的习惯,使各个民族彼此存在差异。文明是习得的行为,是社会群体交往的规则,使不同人群差异逐减并趋向同一。这样对文化与文明的区分,使得人们思考能够拥抱文明又能够保护文化的路径。㉖沿着这一思路延伸,我们接着面对的,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具体习惯(文化),在人们习得更具有普遍性的文明规则的过程中发生变化和如何变化的问题。换言之,就具体文化生活中的人和人群而言,文明规则习得的过程,也是文化习惯发生移位变化的过程。文化习惯的移动变化过程,亦关联着具有普遍性的文明规则在被习得过程中的特点构成。㉗普赫纳“开放性多元”话语中,文学、文化和文明的区分和差异不是重心;他的主旨指向或就是对这些区分本身的跨越,以抵达“大文学”的观念和多元主义的图景。㉘但正因为如此,其多元主义逻辑所携带的“多元个体无限化”,在无限个体化的意义上趋向同质,与多元主张本身成为悖论。网络数字时代的全方位信息流通驱动中,差异成为同质化的商标效应或消费驱动本身,是一个需要面对的命题。㉙当我们聚焦于其中的产能,以寻求文学新的生产性的同时,我们需要关注深刻多样的具体个人和社会群体,在这样“无限多元”的“无限个体化”过程中是否被悬置,日常生活中人类社会性的存在和价值是否被挤压或消散,由此而起的迷思是否在弥散和尖锐化。《文字的力量》 和诺顿文选为中国出版界引进介绍的同时,在书籍原产地美国发生的社会撕裂的状况,成为文化多元主义“无限个体”乐观逻辑的镜像。
在人文学界反馈缓慢的同时,诚恳的反思也正在酝酿发生。普利策奖获得者伊莎贝·维克森(Isabel Wilkerson)的文章,对美国历史中文化多样性的积极进步意义,做了重新历史化的叙述;不同于碎片化的多元主义,她追溯了20世纪马丁·路德·金民权运动与第三世界民族独立的精神谱系如何互为相联,在正视严酷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寻找跨语言、跨文化、跨文明的人间友谊和价值桥梁。㉚近期美国哈珀杂志发表拉瑞·德波利埃(Laurent Deburiel)的文章从另一个维度做出同样的溯源,即重访美国本土文化史中的著名案例——印第安妇女在变革社会偏见的奋争中撰写的文本《1977年康巴河团体宣言》。这份历史性文本记载了被称为“身份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当代源头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撰写人在其中提出,在面对和变革被偏见规定的身份的同时,要对“分隔主义”做出预警,更要在克服偏见寻求变革中,提出社会建设的共同愿景。今年,这一团体的成员之一芭芭拉·史密斯再次重述:“(康巴河团体一文)绝不是说我们将只与‘和自己同样’的人相联”,相反,“(我们)不仅必须面对自己被那些被偏见所规定的身份问题,我们更着力于将社会变革的努力,作为(来自不同文化传承的人们)共同生活的艺术来珍视”。瑞拉·德波里艾以此示意出文化多样的历史在当下身份政治中被援引置换而发生的“分隔主义”变异,并揭示出其中多元主义的逻辑及其终点,是与“康巴河团体”等一系列进步的理论实践的分水岭。德波里艾分析了这一变异与网络经济资本市场同质化倾向的关系,尤其是不断复制“多元身份产品”的市场获利新法则,是如何将其扩张的控制力从线上延伸到了线下,使得关于“具体的生活、思考、触动、梦想、相联和相通”的社会时空被压缩,甚或消散。“而生活、思考、触动、梦想、相联和相通,则与我们是什么、可能成为什么、未来变成是什么有关。”㉛这原本也是《文字的力量》和诺顿文选编撰者的初衷,即通过重温各种语言的“奠基性文本”如何“在历史长时段中积聚力量和重要意义,直到他们成为整个文化的语源,告知人们他们从哪里来、他们该如何生活”,帮助我们想象和找到跨文化的方法,在阅读和体认世界上多种多样的文字文本过程中,相遇、相联、相通。
回到我与普赫纳在交流中的具体说明。清华大学世文院外文系近年来提出的“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旨在拓宽中国外文人文学科的教研范畴和实践空间,以助师生滋养和深化自身作为“外文专家、中国学者”的专业辩证自觉,致力于将世界上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学和更新绵延中的中华传承关联。如何深化对母语的自觉、母语和外文能力如何互为提升的实践,是这一描述性提法的重心。“在外文的研习中获得对母语的自觉和理解,在深化母语自觉和理解的过程中强化提升外文能力,两者相辅相成”㉜。当我们对自己的母语自觉日益加深,意识到母语的复杂精邃和包容,与外文如何互为推动互为延伸,“相联相通”就能发生。比较起欧美一流高校多语种、跨语种人文学科和人才培养的语境资源,我们还有距离;而考虑到中文和英文并驾齐驱的发展,这一距离又有另外一面:不仅熟练而且深入掌握属于不同语系语言的中国学人,与以印欧语系中几大语言能力为主要构成的欧美学人相比,跨文化的尺度甚或还稍大一些。我们能否想象印欧语系的歌德生活在今天,在不同语系语源互换的谈话中,推崇或批评(中文或其他语种)小说文本、以倡导“世界文学”是怎样的情景?或者诺顿世界文学选集采用多语种丛书《TRACES/印迹》的形式㉝,又会是怎样的存在?主要起源于西方的诠释学的核心,如何把握人与神的语言世界转换的方法?㉞如果将其重心人间在地化、成为把握具体的跨语系、文化、文明的转换方法之一,能够孕育的将是什么样的心智状态和想象力量?㉟跨语种语系、跨文化文明的相联相通,近代以来被中国和世界一代代学人呼唤和经历;与文学一样,这似乎是人间一个不可或缺的想象愿景。延续愿景无法只靠个人之力,即便这个人伟大如歌德;愿景延续同时离不开不同文化养成的个人,在具体的跨文化交流对话中相互辨认、尝试牵手,由相联求相通。由此,清华大学2016年提出并与中英11所高校机构一起建立中英高等教育人文联盟时,发起文本如下:
当下的经济全球化,作为现代长时段历史中的又一个阶段,改变并且将继续改变着横跨所有国家和地区、为人类所共有的世界的面貌,它包含着人类历史上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的人类和社会生活的再生产。经常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生活在一个超高速发展、超高速转型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使人的生存历史和心智记忆变得无关紧要。而与此同时,越来越不确定的社会归属感以及各种形式的文化狭隘主义的抬头或推进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现象,这一现象对于给世界带来巨大幅度的财富增长和发展机遇的科技发展和经济成果的使用与含义,带来了思考。在这样的巨变中,以跨文化的知识生产和交流交融能力为重心的人文教育具有了更为清晰的历史功能和重要意义。无论全球化的科技如何创新、经济财富如何强大,最为重要的是它们与所有人类个体、社群、民族和不同类型的国家相互关联的方式,这对于现在和将来,犹如在过去的世界历史上一样,具有重大而全面的后效与影响。
本着这样的认识,清华大学提议成立“中英高等教育人文联盟”,作为不同高校之间在人文学术和人文教育的领域里进行跨文化、跨民族、全球性的对话、探讨和合作的长期机制。㊱
“只有相联相通,美才会诞生”,这是一种愿景想象,也是一种事实陈述,这关乎现代人安身立命的心智支点;关乎于从历史走来的人间福祉,她的过去、当下和未来。
注释
① 这是笔者作为系主任送别的第6届毕业生。师生共同度过的线上毕业季,记忆永存。
② 这个命题贯穿了整个西方文化的世俗化过程和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社会的研讨。参见乐黛云:《涅槃与再生》,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文森特·皮科拉 (Vincent P.Pecora):《世俗化与文化批评》(Secularization and Cultural Criticism),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6。
③ 方维规:《“跨文化”述解》,文艺研究2015年第9期,第5-13页。“社会同质性、种族稳定性、文化界限性”源于欧洲,与现代民族国家互为建构。赫德提出民族(people)和语言之间有机联系的理念,呼吁使用“民族语言”,推动民族文学的发展。而后洪堡提出人和人性的多元性,认为语言不只是表达思想的载体,而是本身即代表了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所具有的意识和认知模式;语言决定了一个民族、国家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由此将不同的种族、民族、社会、国家区分开来,并将语言文学和民族国家的互为构建自然化。
④ 跨文化实践和创新包含于近代以来中国人文学的发展历史。参见乐黛云、陈越光主编《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化本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第274-298页;高瑞泉、颜海平编著《全球化与人文学术的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葛兆光:《中国文化研究中的三个难题》,王博:《善意与留白》,中英高等教育人文联盟第三届峰会主旨论坛,香港中文大学,2018年12月6-7日。
⑤ 限于篇幅,本文使用的具体材料,是英文为主的人文学文本。中文文献同样是跨文化研讨的重心范畴。笔者目前执教的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遵循外文学科建设中重视中文、“由阐释世界以叙述中国、以叙述中国而影响世界”的学理定位,自2015年起从单一语种(英、日)公外教学为主的建制转型为以多语种跨学科专业方向为主的学科群建制,至2020年完成了第一阶段稳态运行。2014年筹备、2016年揭牌的清华大学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院(简称世文院)及其与外文系合办的世界文学与文化实验班,秉承清华人文中西融会的学术传统和育人理念,与中文学科协同发展,为清华大学基础学科拔尖人才计划“学堂计划”首个文科班,简称学堂世文班。
⑥ 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3;《如何阅读世界文学》(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布莱克威尔出版社,2008。
⑦ 马丁·普克纳:《文字的力量:文学如何塑造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陈芳代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英版Random House出版社,2017。
⑧ 见《清华大学世文院世界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暨“清华论坛-世文系列”马丁·普赫纳教授讲座举行》,2019年9月11日;《哈佛大学马丁·普赫纳做客世文研讨课》,2019年9月23日。
⑨ 普赫纳,《文字的力量》,第318页。
⑩ 同上。
⑪ 1991年在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首次开设比较文学导论。
⑫ 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第113页。
⑬ 一个世纪后,世界文学的乐观者持有基本相同的起点。大卫·达姆罗什主要注重的是市场流通的力量,对流通中社会内涵差异性的探讨注意相对较少。
⑭ 维斯斯坦(Ulrich Weisstein):《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瑞根(William Riggan)译,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Bloomington/London: Indiana UP),1968,第18-19页。
⑮ 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第114页。
⑯ 这里“西方文学”不是统指所有发生在欧美民族国家的文学文本,而是指“西方中心主义”在文学领域的有限的固化谱系,其内核是“自我”和“他者”二元对立的逻辑及其认知后果。学界对此数十年的丰富研讨富有成效的部分值得继续汲取。参见文森特·皮科拉:《全球化与人文主义》,载《全球化与人文学术的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1-20页。
⑰ 按美国高校语境中人文学科的常规划分,英语文学被称为“英语文学”,英文之外的文学均称为“世界文学”。而英语语境中的中文文学,长期以来被纳入区域研究。
⑱ 见相关报道。2016年,清华大学外文系90周年系庆,延续全年的国际论坛系列“世界地图与世界文学”(World Maps and World Literatures)是这一描述性提法的实践尝试之一。
⑲ 见上注释8,《哈佛大学马丁·普赫纳做客世文研讨课》,2019年9月23日。
⑳ 方汉文:《走入世界经典的中国文学》,光明日报2013年1月28日;沈祖新:《马丁·普克纳〈文字的力量〉:勾勒幽径与探寻边界》,文汇报2019年11月4日;李钧鹏:《文字的胜利》,澎湃新闻2020年8月11日。
㉑ 陈芳代:书评,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2 NO.4 (2019):808-810。
㉒ 通过对技术革命的积极把握,普赫纳着重揭示新技术革命与文学演进的共振,文字书写与社会生活方式变迁互为展开的相互关联。见上注释20-21。
㉓ 康奈尔大学酒井直树教授和同事们数十年的英中日韩多语种出版《Traces/印迹》,是对这一局限极限尝试克服的案例之一。对“何为语言”的研讨,参见包括萨特“存在于世界即存在于语言”立论在内的前后数十年各种理论流派,如巴特斯、福柯、德里达、詹姆士、萨伊德等。
㉔ 文森特·皮科拉:《全球化与人文主义》,载《全球化与人文学术的发展》,高瑞全、颜海平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17-19页。
㉕ 中外学者对“异质文化”的研讨,参见乐黛云、陈越光主编《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化本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㉖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㉗ 这里的互动变化过程,并不必然导致文化的同质化;笔者认为在两个互为关联的变化中,存在着一个枢纽之域,即最为多元、最具差异、最具变化,也最有包容性和普遍性的文学之域。限于篇幅此处不展开。早期对此研讨的著述包括莫里斯·布朗肖:《文学空间》,顾嘉琛译,商务印书馆,2003。近期参见多米尼克·拉科普兰(Dominick LaCapra):《什么是历史,什么是文学》(What is History? What is Literature),载《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2017年第1期。
㉘ 其中的积极意义,尤其是“大文学”观念的提出以及提出的方法,在本文前面提到的部分书评中有具体的阐述。
㉙ 对此二战后开展的对消费文化现象的研究与批评有丰富阐释;当下发生的变化,使得这一现象发生了不仅是规模上而且可能是属性意义上的变更。
㉚ 维克森(Isabel Wilkerson):《美国持久的种性系统》(America’s Enduring Caste System),纽约时报2020年7月1日。
㉛ 瑞拉·德波里艾(Laurent Dubreuil):《不人云亦云》(Nonconforming),哈珀杂志 ( Harper’s Magazine) 2020年9月刊。
㉜ 颜海平:《跨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和世界始终亟需的能力》,澎湃新闻专访,2020年7月20日。
㉝ 酒井直树及其多语种团队编撰:《TRACES/印迹》,康奈尔大学。
㉞ “诠释学(Hermeneutik) 来源于赫尔默斯(Hermes),希腊神话中一位信使的名字。诠释学是一种语言转换,一种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语言转换,从神的世界到人的世界的语言转换,陌生的语言世界到自己的语言世界的转换”。汉斯·艾斯勒、汉斯·邦格著:《布莱希特、音乐和文化》,黄君梅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第301页。
㉟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是否对二战后欧美学界诸多具有生产力的其他思想脉络展开这样的思考,也许是个可以研讨的命题。
㊱ 《发起》,中英高等教育人文联盟成立暨首届高峰论坛,上海,2016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