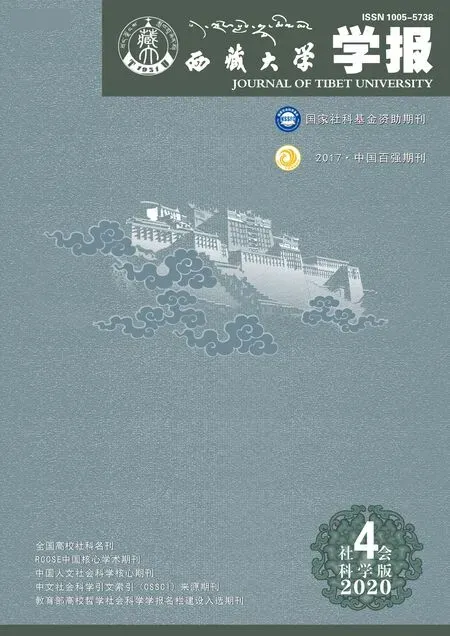《西藏新志》“宗教”资料来源考
吉正芬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成都 610041)
在清代所修的诸多西藏方志中,许光世、蔡晋成所编的《西藏新志》是比较特殊的一部。一是该志面世最晚,其由上海自治编辑社铅印于宣统二年(1911 年)八月或稍后,亦即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前夕。二是该志虽未直接标明,但实际是以章节体进行编纂,这是清代诸多西藏志书中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西藏新志》内容较为丰富,有关西藏的地理、政治、经济、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均有所涉及。新中国成立后,学界对清代西藏方志的研究长期薄弱,对《西藏新志》的关注和研究亦较少。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开始加大对西藏清代方志的关注和研究力度,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赵心愚先生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对清代方志进行系统化研究并出版的《清代西藏方志研究》。[1]但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对象,仍主要集中在清代前期和中期的西藏方志之上,对清代晚期西藏方志,特别是对《西藏新志》的研究,就笔者所见,目前仅有赵心愚先生所著的《宣统<西藏新志>“地理部-驿站”的主要资料来源考》[2]以及杨学东先生所著《山县初男<西藏通览>对近代西藏方志编纂的影响》[3]两文,前者主要就其地理部—驿站史料来源做了较为深入的考订,后者主要是就《西藏新志》与《西藏通览》两书在体例以及内容上做了粗略对比,指出前者全书百分之六七十内容皆参考了后者,仅在文字上略作改动,避免雷同。但杨文主要观点在于介绍《西藏通览》对于近代西藏方志编纂的影响,并未就二者内容上的雷同及史料的源头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考订。此外,其他提及《西藏新志》的文章,均是一些方志著录类著作,仅限于简单或一般性介绍①如,张莉红.西藏地方文献考略[J].中华文化论坛,2005(3),该文中提及《西藏新志》;青龙.西藏地方传统修志初探[J].中国地方志,2009(81),该文对《西藏新志》作了著者、卷数及刊印时间、出版者的简单介绍,并指出了此书为“清末最后一部西藏志书”;何金文.西藏志书述略[M].长春: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5:53-54页。。
因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西藏方志整理与研究”的需要,笔者查阅了多部西藏方志中关于“宗教”方面内容的记述。对《西藏新志》中“宗教”部分细读之后,发现其内容与日本人山县初男所著《西藏通览》一书汉译本中相关内容高度相似,前者应是抄录、改编自后者。而《西藏通览》宗教一章中有关宗喀巴及格鲁派教法史的内容,则可能来源于魏源的《圣武记》。
当然,以后见之明苛责前人文献上的疏漏,并非本文的写作目的。不过,跟随这些文献的演变,能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汉文典籍记载中的西藏史为何会出现一些误解。
一、《西藏新志》中卷“政治部·宗教”内容述略
《西藏新志》全书分三卷,分别为上卷“地理部”、中卷“政治部”及下卷“历史部”。其“宗教”归属于“政治部”,内容分为“(一)沿革”“(二)喇嘛僧”“(三)寺院”及“(四)人民之迷信”四部分。为便于后文分析,有必要先将其大致内容作一简要介绍。
在《西藏新志》“宗教”部分,著者开篇即云:“西藏宗教为喇嘛教(按佛教自印度入藏,周末始称喇嘛,藏语为无上之义),举国信之。其有奉他教者,大率邻国移住之民,且为数无多。”在这之后即按上述四部分内容展开叙述。
在“(一)沿革”部分,著者追溯了喇嘛教的源流与西藏史:“喇嘛教始名红教,其源出自佛教之密教”。周赧王二年,有印度王子乌迪雅纳汗,为邻国所败,自印度逃至藏地,称雅尔隆氏,后其子被众人推为汗,为吐蕃赞普之始,其后历十四世传至多里隆赞汗,东晋义熙三年(407)得百拜忏悔经、多宝经及金塔宝,敬慎供养,是为佛教入藏之始。其后,又传八世至特勒德苏隆赞(即今汉文译为松赞干布),十六岁承袭汗位,二十五岁尚唐文成公主,开创吐蕃王朝,西藏佛教之盛自此始。至公元747 年,巴特玛撒巴斡者(即莲花生大师)入藏,为红教之祖,由于巴师天禀之能力卓越,热心布教,从此红教基础强固,通行全藏。到公元899 年,郎达磨弑兄即位,一改前赞普所为,下令禁止佛教,封闭寺院,烧毁经典。有信佛法者密谋暗杀,事成,其后约百年,西藏佛教又再次兴盛,此后数百年至元初,有高僧八思巴出世,言其“七岁能演其法,论辩纵横,复遍资名宿,勾元索隐,尽通三藏,国人以为圣,呼之为八思巴”,“岁十五闻元世祖之德,驰驿谒之王府,世祖深信之”,并赐与玉印,“任中国之法王,统天下之教”,又受诏制元之文字,即今之蒙古字,升任帝师,红教遂成为元之国教,历代信奉不已。至元顺帝执迷最甚,修习大喜乐法,欲证得“大喜乐之身”,此后导致“淫戏无度,丑闻外泄,实渐促红教改正之时数”。至明永乐十五年,宗喀巴出世,性慧敏,学于后藏之扎什伦布之西萨迦庙,看到红教之流弊,于是易衣帽、改正咒语取代红教而起,同时自其两大弟子达赖与班禅始,开创了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从此“黄教勃兴”。[4]
第二部分题为“喇嘛僧”,介绍了喇嘛等级,谓其最尊者为国师或又称禅师,其下依次为扎萨克大喇嘛、副扎萨克大喇嘛、大喇嘛、副喇嘛等,在服装上以袈袍服色分教派。但又特别指出,也有信黄教(即格鲁派)之僧徒而着红色僧袍,并言黄教内部又分两种颜色,年长者用黄色,而年少者用红色;僧侣中从属于达赖与班禅的人数最多,喇嘛的职责主要为“诵经典修佛事祈冥福”。[5]
第三部分题为“寺院”,这个部分主要介绍了西藏的各大寺庙及其内部的管理结构,并单独介绍了大昭寺、小昭寺、布达拉宫、色拉寺、别蚌寺(即今哲蚌寺)、噶尔丹寺、桑耶寺、萨斯迦寺、热振寺、达隆寺、江巴林寺等。[6]
第四部分为“人民之迷信”,这一部分内容较为简略,主要介绍了藏人如何崇信喇嘛教,以及喇嘛教如何深入藏地人心,并列举了人民见达赖及其他高僧时的情状、达赖及尊贵高僧圆寂时的仪式典礼、六字箴言在藏地的广泛流传以及有关藏民佩戴之念珠。[7]
二、《西藏新志》“宗教”史料来源考
作为清代最后一本西藏方志著作,《西藏新志》大量借鉴前人以及外国人有关西藏的史地著作,对清代西藏地方历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其“宗教”部分对西藏政教源流、宗喀巴宗教改革的叙述也较之前的西藏方志详尽,并被民国以后有关西藏佛教的其他著作所转引。
通过文本的相互对比,笔者发现《西藏新志》“宗教”内容与日本人山县初男所著的《西藏通览》一书第七章“宗教”以及第十四章“寺庙”内容基本一致,甚至《西藏新志》著者对于藏传佛教的个人看法都与《西藏通览》中山县初男的观点完全相同。为便于读者比对,特将《西藏通览》“宗教”及“寺庙”两章节目详列如下:“第七章宗教第一节喇嘛教之沿革,第二节喇嘛之阶级服装职务,第三节人民之信仰”;“第十四章寺庙第一节主要各寺院,第二节寺院之内部及礼拜,第三节喇嘛之训练”。而《西藏新志》在章节的排列上,除了完全引用《西藏通览》第七章内容外,又将其第十四章“寺庙”的内容简化为一节,列入其“宗教”章下。从四节的具体内容上来看,可以发现对具体时间、人物、具体事例的记载,以及对寺庙名称的列举,《西藏新志》与《西藏通览》两书在章节编排上有细微差别,但内容大体相近。考虑到二者的成书时间以及《西藏新志》在其参考文献中也将《西藏通览》罗列在内,大致可以推断,前者内容主要抄录、改编自后者。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能将两书“宗教”内容一一对比,现仅摘录两书中数例相似内容如下,并对其进行简要分析。
例一:
《西藏新志》:“喇嘛教始名红教,其源出自佛教之密教,周赧王二年,岁在戊申,额纳特克(中印度)有乌迪雅纳汗者,为邻国所败,自印度逃至雪山,住雅尔赞塘。遂呼谓雅尔隆氏。其季子生有异表。众人推为汗。(王之意)雅尔隆出兵四方,所向无不利,寻为土伯图国之王,其后历七世有奸臣隆纳木者篡其位,不半载,前汗之子某汗恢复故位,又传七世至多里隆赞汗,得百拜忏悔经、多宝经及金塔宝,敬慎供养,是为佛教入藏之始,时西历四百七年东晋帝义熙丁未三年也。八世特勒德苏隆赞年十六,袭汗位,曾派十六臣至中印度习音学,回国后使译百拜忏悔经与三宝云经,以为治国之助。已娶巴布勒国王之女,二十五岁又尚唐文成公主,当文成公主之至西藏也,携带经卷佛像,于是汗又聘中印度之桑吉刺必满师及巴勒布国之锡拉满祖师鄂斯达师、唐僧之玛哈德斡等,使译经卷,宣布国中。西藏佛教之盛自此始。”[8]
《西藏通览》:“今日藏僧衣冠皆黄色,故称黄教,先本位红教,其源盖自佛教中密教一派出,周赧王二年戊申额纳特克(中印度也)乌迪雅纳汗者为邻国所败,自印度逃至雪山,居于雅尔赞塘遂称曰雅尔隆氏,其季子生有异表,众推之为汗,后雅尔隆氏兵出征四方,无不奏捷,未几遂为图伯特国王,其后传至七世,有奸臣名隆纳木篡据君王,未及半岁,前汗子某恢复汗位,复历七世至多里隆赞汗,得百拜忏悔经、多宝经及金塔宝,敬谨供养,是为佛物输入西藏之始,盖东晋安帝义熙三年,岁在丁未,西历之四百七年事也,八世有特勒德苏隆赞,年十六而登汗位,派遣其臣十六人至中印度学习音学,归国后使之反译百拜忏悔经及三宝云经以为治国之助,娶巴布勒国王女为室,至二十五岁再尚唐之文成公主,公主携带经卷佛像以入西藏,特勒隆苏赞于是更聘中印度之桑吉刺必满师巴布勒国之锡拉满祖师及鄂斯达师及唐僧人玛哈德斡等编译诸经宣布国内,西藏佛教之勃兴实渊源于此。”[9]
通过例一对比,可以看到两书对西藏宗教的源流与吐蕃赞普世系的叙述几乎完全一致。通过考察《西藏通览》汉译本这部分内容可知,山县初男主要参考的文献是正史、《圣武记》以及《蒙古源流》。而后,《西藏新志》的编纂者又透过其汉译本引用有关史料。这一过程,可以以上引吐蕃赞普人名为例加以说明。山县初男叙述吐蕃王室来自印度的世系历史,其实是根据《蒙古源流》的相关记载。然而,《西藏通览》汉译本首先发生几个误抄。一是公元407 年得百拜忏悔经等天降四宝物的是拉托托哩年赞汗,而非书中所记多里隆赞汗,前者在后者四世之后;其次,尼雅特博汗这个人名,在《蒙古源流》汉译本中作“尼雅持博赞汗”。这两个误抄除《西藏新志》外,还被民国时期其他汉文的西藏史地研究著作所承袭,如陈观浔《西藏志》、丁福保《佛教大辞典》等书。其三是特苏隆德灿(按,现汉文译为“赤松德赞”,在藏文典籍中,他是金城公主之子)迎娶金城公主之误,此错误源自《蒙古源流》。[10]但令人意外的是,《西藏新志》虽承袭了前述误植,但在关于金城公主的叙述中,却并未继续《西藏通览》的误抄,而是与藏文典籍中的记载一致,即“隆赞(按:即松赞干布)元孙弃隶缩赞立,复请婚,中宗亦娶以所养雍王女金城公主”。[11]至于其资料来源,此处无法考证下去。但《西藏新志》的作者此处显然在汉文资料之外寻找西藏史料,至少可以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以往所认知的西藏历史有限。
在谈到印度高僧巴特玛撒巴斡(即莲花生大师)入藏及降服幽鬼的传说上,两书所载几乎完全相同。见例二:
《西藏新志》:“西历七百四十七年,巴特玛撒巴斡者被聘至西藏,此人住克什米尔之境,为印度之有名学者,于是巴师以其卓越天禀之能力,热心布教,亲自周行全国,其奇迹甚多,略记如左:
巴师之周行全国也,名为征服幽鬼。一日有鬼顽相抵,欲压氏于山峡,师飞腾得免,又有鬼自雪中掷兵器如雨,自称降魔杵,氏融解积雪为水,鬼遂投水中,师因令水沸腾,鬼骨肉糜烂,又投降魔杵,刺幽鬼之目,鬼始出水,仅存生命;又一日,有妖物大为师苦,化白色牦牛来触,师飘然登天,牦牛忽结其鼻颈与脚而不动,顿变缠白绢之美少年,再三申告,始留其生命,……”[12]
《西藏通览》:“西历七百四十七年,巴特玛撒巴斡被聘自克什米尔境,上至西藏,彼为有名印度学者,天禀才能,真诚热力,卓越众庶,常自行脚四方以宣布教意为事,藏人相传师欲征服幽鬼,旅行某地,忽一幽鬼出现,目前狰恶无比,顽强抵抗,将压杀师于两山峡间,师用高飞之术超越山谷,仅得免于危难,又有一幽鬼用降魔杵之最利武器自雪中向师投掷,纷如雨霰,师乃作法令积雪悉行融解变为湖水,幽鬼无所讬,足以降魔杵弃诸水中,将行逃遁,师更令湖水沸腾,幽鬼骨肉为之糜烂,尚出水欲行,师因用降魔杵击幽鬼眼,使成盲目,幽鬼忽出湖上,仅全其生命,向空走去;又某日有妖灵一欲逼迫巴师,乃化为大牦牛,白而健壮,诱师乘其上,则因以作怪,师知之飘然登天,俯览下界,牦牛忽恍惚有所失,自缚其鼻颈脚三者不能动作,后乃化为美少年,身著白绢布服,向师哀祈生命云,……”[13]
显而易见,《西藏新志》在这里几乎是整段地引用了《西藏通览》的内容,只是在少数地方和个别行文上有所改动。
事实上,除了有关藏王世系等方面的段落外,《西藏新志》“宗教”章通篇的各节内容都可以在《西藏通览》不同地方找到来源,只不过《西藏新志》的编纂者把它们经过加工后拼凑成一个新的整体。如《西藏新志》“宗教”之“寺院”条目下的内容与《西藏通览》第一编第十四章“寺院”内容几乎完全一致,即使用来列举的寺院名称也完全重合。由于其内容篇幅过长,此处就不对照罗列,具体内容可参看两书相关章节。
甚至《西藏新志》编纂者对西藏宗教的个人观感,我们也可以在《西藏通览》中找到相同表述。见例三:
《西藏新志》:“其后约百年,僧侣之数渐增,资产亦富,寺院建设,到处勃兴。于是藏民彪悍气质渐变纯良,然自沾染中国印度奢侈之风,人民寖流于游惰,僧侣道德日替,佛教之衰实基于此。”[14]
《西藏通览》:“此事后再约百年,僧侣之数乃日有增加,佛寺资财亦较前丰富,新立寺院无地不见,空门发达再复旧观,西藏番民旧日所有彪悍气质一易为柔弱卑屈之态,好勇喜战之美风渐销渐尽矣,奢侈风俗复自支那印度二地输入藏中,人民乃流于游惰,社会及僧人道德次第衰落,暨于后世佛教亦渐见颓废。”[15]
上述数例对比,均可见两者内容大致相当,只是个别段落繁简稍异,少数词句表达不同,但意思一致。
总之,通过两书中有关“宗教”内容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虽然除了《西藏通览》,《西藏新志》的两位编纂者在其例言中还明确列举了多部中外西藏史地著作,但他们至少在编纂该志的“宗教”章节内容时主要借鉴、甚至是抄录了《西藏通览》一书中相关内容,仅在极少数的字词或段落方面进行微调或改编,但主要内容不变。
三、《西藏通览》中有关“宗喀巴宗教改革”内容来源分析
在《西藏新志》中,有关藏传佛教的宗喀巴改革记述较为详细,不仅记述了宗喀巴的生平,亦描述了宗喀巴对藏传佛教的改革,以及黄教的勃兴。其两大弟子,即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更是对藏传佛教的发展影响极大。如前节所述,《西藏新志》中宗教部分的内容均来自《西藏通览》,对宗喀巴的记载亦如此,两书中的相关内容极为相似。
《西藏新志》:“(明永乐十五年)宗喀巴(本名罗藏札克卜巴,称五定低之一阿弥陀如来之化身)生于甘肃省之西宁府,性慧敏,年十四学于后藏扎什伦布之西萨迦庙,已涉红教之流弊,忧吞刀吐火之幻术不足为世益,誓洗其风。一日会众,自换黄色衣冠告众曰,教主者,世世呼毕尔罕(转生之义)以救人民,后得道于西藏之噶尔丹寺,此为黄教之始祖。其改正黄教之特点有三:一易衣帽为黄色;二改正咒语;三假定呼毕尔罕之转生以传衣钵,于是黄教勃兴。宗喀巴有二大弟子,一曰达赖喇嘛,一曰班禅喇嘛,此二弟子皆重见度生,斥声闻小乘及幻术下乘……”[16]
《西藏通览》:“永乐十五年宗喀巴(原名罗藏札克卜巴,为五定佛之一世,称为阿弥陀如来化身云)生于甘肃省之西宁府,天性慧明过人,年十四而至后藏扎什伦布西方之萨迦庙学习红教,后知红教流弊日出不已,且吞刀吐火之幻术不足以济渡众庶,誓欲一洗前习,振顿宗风,至某日集众于前,自改著黄色衣服告以西藏教主世世俱为呼毕尔罕转生世间以拯救西藏人民云云,后得道于西藏之噶尔丹寺,是实黄教之始祖也。其改正红教之要点有三;一衣冠不用红色而用黄色;二咒语改良;三假定呼毕尔罕世世转生不以衣钵传授其子,黄教勃兴基础由此日趋坚定。……宗喀巴有弟子二,一曰达赖喇嘛,一曰班禅喇嘛,皆能重见生度生之说,斥声闻小乘及幻术下乘……”[17]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肯定《西藏新志》中关于宗喀巴的相关记载均来自于《西藏通览》。但《西藏通览》一书中关于宗喀巴的内容又来自何处呢?下面对此问题做一简要分析。
《西藏通览》作为清末出版的第一部外国人编著的西藏地方志作品。其日文版最早是1907年由东京丸善社出版,并附有西藏地方地图两幅。清末民初国内出版有两个汉译本,其中较早的是1909年四川西藏研究会编译、成都文伦印书局的石印本,另一个则是1913 年陆军部刊印本。根据1909年的汉译本,此书体例完备,系作者山县初男参阅大量中外有关西藏史地论著的基础上编纂而成,全书共分两编:第一编下设16章,分别介绍了西藏的地理概况、地势、人种、风俗、政体、宗教、语言文字、教育、兵制、贸易、物产、交通、工艺、寺庙、都邑等,叙述详尽。第二编分为6章,主要记述西藏史略、西藏外交现状及原因、欧美探险家在藏的活动和英俄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经过、与西藏有关的几个不平等条约以及西藏与中国内地和英俄等列强的关系。尽管该书在某些地方不够公允,但作为今人了解、认识和研究西藏近代史地而言,《西藏通览》既是一部难得的西藏方志,又是藏学方面的重要典籍。①不管是1909年四川西藏研究会的编译本还是1913年陆军部的翻译本,其目的都是为了让国人更深入了解西藏、认识西藏,以便更好地经营和保卫边陲。正如陆军部在译看《西藏通览》序中所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故经营西藏当以详考藏志为嚆矢,将欲兴其利必先知其弊,将欲革其俗必先得其情”,对西藏“了如指掌而后长驾远驭之策可得而施也”,“以是书为吾国他日缔造西藏之津梁也”。
有关山县初男其人,赵心愚先生在《宣统<西藏通志>“地理部·驿站”的主要资料来源考》一文中已有介绍。[18]笔者在此作一点补充,此人作为日本陆军中的中国通,中华民国成立后,他曾先后出任云南军阀唐继尧和贵州军阀刘显世的军事顾问,从日本陆军退役后,山县进入大冶铁矿担任日本制铁株式会社大冶办事处主任,直到1933年卸任回国,他在中国生活长达40年之久,与鲁迅曾有交往,除了编纂《西藏通览》一书外,还参与主编《最新支那通志》,对中国西南地区的情况极为熟悉。
在《西藏通览》凡例中,山县初男所列引用或参考之书(图)共26种,如《西藏记》《西藏》《西藏旅行记》《四川通志》《清圣武记》《蒙古源流》及各种正史如《明史》等。经笔者查考,《西藏通览》所列参考书目中,《蒙古源流》一书中有关西藏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西藏王统的叙述上,对宗喀巴的宗教改革并未涉及。《明史》中并未有任何关于宗喀巴的记载,也未提及明成祖曾遣使召宗喀巴一事。而早于《圣武记》的官修或私人著述中,有关宗喀巴的记述仍寥寥无几。如乾隆版《西藏志》中就找不到关于宗喀巴及其宗教改革的相关记载。嘉庆二十一年(1816)完成的重修《四川通志》中有关宗喀巴的记述为“罗卜藏札克巴,生于永乐十五年,幼而神异,精通佛法,号曰甲瓦宗喀巴,在大雪山苦意修行穆隆经,其所立也即今之磨罗木,最为番众所敬信,相传其受戒时,染僧帽,诸色不成,惟黄色立成,遂名黄教之宗。头号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皆其弟子,今拉撒大小喇嘛寺皆供奉其像云”。[19]又据民国藏学学者于道泉的研究,直至清代乾隆时期,汉文文献中才首次出现了关于宗喀巴的记载,即修撰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 年)的《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西藏总传》。其内容为:“达赖喇嘛,班禅喇嘛,明宗喀巴二大弟子。宗喀巴兴黄教,弟子数千人。达赖喇嘛居首位,其名曰罗伦嘉穆错”,仅此一句。而历经康、雍、乾、嘉四朝修撰,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最终完成的《大清一统志》里则是以“相传宗喀巴者居喇萨,始兴黄教”[20]这样一笔带过。
《圣武记》是关于清代历史的一部重要专著,清魏源(1794~1857年)撰,成书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共14 卷。前10 卷以纪事本末体记述清王朝建立至道光年间的军事历史,其中包括《开国龙兴记》《康熙戡定三藩记》《国朝绥服蒙古记》《国朝绥服西藏记》等;后4卷用武事余记的方式,论述清朝的兵制兵饷、考证掌故,以及作者对城守、水守、坊苗、军政、军储等问题的见解。在《国朝绥服西藏记》中,记载了关于宗喀巴及其宗教改革的相关内容:
其黄教宗祖则创于宗喀巴,(一名罗卜藏札克巴),以永乐十五年生于西宁卫,得道于西藏之甘丹寺,成化十四年示寂。初明代诸法王皆赐红绮禅衣,本印度袈裟旧式也。其后红教专持密咒,流弊至以吞刀吐火炫俗,无异师巫,尽失戒定慧宗旨。宗喀巴初习红教,既深观时数,当改立教,即会众自黄其衣冠,遗嘱二大弟子,世世以呼毕勒罕转世,演大乘教。呼毕勒罕者,华言化身也。二弟子,一曰达赖剌麻,一曰班禅剌麻。剌麻者,华言无上也。(今俗加口旁曰喇嘛。其班禅又称额尔德尼,相传达赖为观音分体之光,班禅为金刚化身,在印度已转生数十世,其说不可得详云)皆死而不失其通,自知所往生,其弟子辄迎而立之,常在轮回,本性不昧。故达赖、班禅易世互相为师。其教皆重见性度生,斥声闻小乘及幻术小乘。当明中叶,已远出红教上,未尝受封于中国。中国亦莫之知也。达赖一世曰根敦珠巴者,即赞普之裔,世为番王。至是舍位出家,亦名罗伦嘉穆错,嗣宗喀巴法,传衣钵,始以法王兼藏王事。……[21]
魏源的这段记述大致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将宗喀巴的生卒年记为明永乐十七年至成化十四年(1417-1478);其二为宗喀巴创黄教以易服饰、改咒语而取代红教;其三为创活佛转世制度,并自其两大弟子达赖和班禅始,并附带指出一世达赖为藏王后裔,由此开始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以目前学术界对西藏佛教的研究成果来看,魏源的这几点认识全都有误。宗喀巴的准确生卒年应为元至正十七年至明永乐十七年(1357-1417),比魏源所记早整整六十年;以目前学界对藏传佛教的研究而言,一般将其分为宁玛、噶当、萨迦、噶举、格鲁五大派以及其他小派,且格鲁派并未取代萨迦派,直至明中期,藏传佛教教派一直是多元并存发展,而格鲁派的敌人也并非已经衰落的萨迦派,而是当时执掌西藏地方政权的噶玛噶举派;近代以来,通常汉文记载中习惯以颜色来区分为黑、红、白、花、黄教,但严格来讲,以颜色作为教派的区分,并不准确,甚至有时会出现张冠李戴的错误,如以红教来指称除格鲁派外的一切教派或将黑教(苯教)与噶玛噶举派下的黑帽分支混为一谈。
从魏源引松筠《绥服纪略》以及姚莹《康輶纪行》的记录来看,他其实已经注意到黄教源自红教,“宗喀巴初年亦学经于萨迦庙,本出一源,又学成乃自立宗。余巡边见萨迦呼图克图,询其经典,悉同黄教。……乾隆五十四年,驻藏大臣舒濂曾复奏萨迦本同黄教情形。”[22]且松筠还曾就此问题当面询问过达赖与班禅等人,皆同此说。“盖红、黄二教本同,其近日邪术之红教年红教之末失,非萨迦庙之本宗也。”魏源所引姚莹《康輶纪行》中也指出“黄教之先本亦出于红教也”,[23]且其源流载于布达拉经簿,又经乾隆五十七年驻藏大臣和宁在《西藏赋》中引用。但令人不解的是,尽管魏源已从上述两书中留意到红、黄两教的渊源,却仍然将二者截然对立。
事实上,上述三人即和宁、松筠以及姚莹三人关于宗喀巴宗教改革以及达赖、班禅世系的记录并无多大区别,尤其是和宁在《西藏赋》中的相关记载,其自言考自布达拉宫所藏经簿,且曾当面询问过达赖及班禅有关红、黄两教之渊源。姚莹与和宁为同时代人,且《康輶纪行》与《西藏赋》的刊行时间非常接近,姚莹在其书中也直言其有关黄教及宗喀巴的认识来自于和宁《西藏赋》。但考虑到清末以来,魏源的《圣武记》一书影响力大大超过和宁的《西藏赋》,其有关西藏佛教的论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巨大,不断被反复传抄、转引。民国学者于道泉就曾注意到魏源关于宗喀巴的错误记载,被日本人寺本婉雅翻译自藏文的《喇嘛教宗喀巴传》引用。[24]
将上引《圣武记》中有关宗喀巴的记载,与前引《西藏新志》《西藏通览》中有关宗喀巴的记载对比,可发现内容基本相同,区别仅在于用词遣句方面有所差异。考虑到《西藏通览》为汉译本,系翻译自原作日文本而来,如其日文原作相关内容又来源(翻译)于《圣武记》中相关内容,两者之间存在少许差异也在所难免。综合以上分析,至此应可大致推定,《西藏通览》中有关藏传佛教宗喀巴及其宗教改革的内容,应来源于魏源的《圣武记》。
结语
近年来,随着学界对地方志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日益重视,大量方志成为史学研究者发掘、考查、研究的对象。除了学者们的投入,更有为数不少的硕博士研究生纷纷将这些方志选择为毕业论文题目。由此基本形成了一套有序的研究模式,并使得此类论文达到一定学术水准。但其中有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即对志书中的史料考辨不足,尤其是民族地区的地方志在编纂过程中所引用的史料,往往存在翻译、转译、移植、改写、摘译等现象。因此面对这样层层累积的史料,亟需仔细考辨并还原历史语境,显现其本来面目,方能在利用这些方志文献从事具体研究时,不至于被其中一些不实的史料误导自己的判断,进而避免出现对某一历史现象或史实作出过度诠释。这是研究的前提也是研究之初的必要功夫。
本文通过对《西藏新志》所载“宗教”史料来源的分析探讨,可以得出一点认识,即《西藏新志》所载宗教方面的内容材料应全部来源于日本人山县初男编著的《西藏通览》汉译本,而其中有关宗喀巴的记载材料,又至少可再上溯至《圣武记》。众所周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西藏在近代成为边疆危机下突出的议题,清末起,到藏地进行所谓探险、传教及经商的外国人逐渐增加,所写的地理、游记及方志著作也不断出现,如本文所列举的《西藏通览》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在此背景下,汉人关于西藏的史地著作也开始增加。《西藏新志》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编纂而成。与前代汉人有关西藏的史地著作不同,该书在其例言中除了列举本国的参考文献外,还明确列举了大量国外出版物作为其参考和引用资料,这是值得肯定之处。但对比其“宗教”的内容,可发现基本抄录自《西藏通览》,并将其错谬之处不加考辨一并抄录,由此可见,其时国人对格鲁派的认知仍充满空白。本文对相关内容资料来源的分析探讨,并不是要指责前人对文献的失察,而是希望厘清其出现的缘由及流变过程,并梳理出相对可靠的史料,以有助于今后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