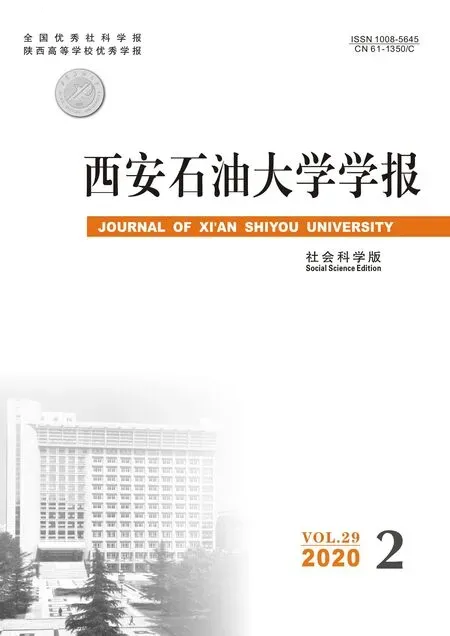日本奈良·平安时代赋得诗的衍生与流变
刘佳琪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0 引 言
赋得诗是产生于中国梁陈时期的一种诗体,通常以“……赋得……”或“……赋……得……”为题。“赋”即“赋咏”之意,“得”即“分得”之意,主要包括分题、分韵两大类,分题大致包括景物、人物、古人诗句。关于中国赋得诗的研究早在明清时期就散见于各类古典诗话中[注]明清时期关于赋得诗的研究,或关注“赋得”二字的意义,如俞樾《茶香室丛钞·四钞》卷十三“古人今韵法”条:“《困学纪闻》曰:‘梁元帝《赋得兰泽多芳草诗》,古诗为题见于此,至今场屋中犹用之。’然所谓‘赋得’之义,多习焉不察,今乃知亦赋予之赋。盖当时以古人诗句分赋众人,使以此为题也。”或致力于追踪赋得诗的渊源,如《四库全书总目·集部·须溪四景诗集提要》曰:“考晋宋以前,无以古人诗句为题者。沈约始有《江蓠生幽渚》诗,以陆机《塘上行》句为题,是齐梁以后例也。”见永瑢等编《四库全书总目》。,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在文体学[注]参考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第五章“诗可以群”及张明华《唐代分韵诗研究》。著作中被广泛论及,且出现了对赋得诗的产生和演变作梳理的专篇论文[1]31-36,[2]86-96,目前已然勾勒出中国赋得诗发展的历史轨迹。相比之下,对作为中国赋得诗域外延伸的日本赋得诗的研究则迟至二十世纪末才有日本学者论及,且研究成果较少。目前问世的学术成果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将中国赋得诗和日本赋得诗看做一个整体,着眼于对“赋得”的含义进行阐释[注]参考斯波六郎《赋得の意味について》,载中国文学报(通号3)。;二是致力于对具体的赋得诗作进行考证[注]参考村田正博《上代の诗苑——长王宅における新罗使飨応の宴》,载《人文研究: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通号36),1984年;井実充史《于长王宅宴新罗客诗の论》,载上代文学(通号73),1994年11月;冈部明日香《王孝廉<在辺亭赋得山花戏寄両个领客使并滋三一首>》,载《アジア游学》(通号72),2005年2月;福田俊昭《长屋王の私邸における诗宴诗(上)》,载《东洋研究》(通号156),2005年9月;福田俊昭《长屋王の私邸における诗宴诗(下)》,载《东洋研究》(通号160),2006年7月。。本文拟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将奈良和平安时代的赋得诗放在东亚世界政治和外交的背景之下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求在宏观上对这一阶段日本赋得诗的衍生和流变进行把握。
关于赋得诗的外延,目前学界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界定方式,狭义的赋得诗仅包括诗题中出现“赋得”或“赋……得……”的诗作,而广义的赋得诗还包括诗题中不含“赋得”但具备多人分题或分韵创作特征的诗作。然而,由于年代久远,部分诗题不含“赋得”的诗作是否能确认为赋得诗,已经难以确考,为避免失实,本文所涉仅指狭义的赋得诗。
1 奈良時代的赋得诗
约在近江朝圣德太子时代(574—622年),中国最早收录赋得诗的《文选》已经传入日本。据江村北海《日本诗史》中的记载,“天智天皇登极。而后鸾凤扬音。圭壁发彩。艺文始足商榷云”,[注]清水茂、揖斐高、大雅谷夫校注《日本诗史·五山堂诗话》,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65卷,1991年。可见在天智天皇(626—672年)御宇时,汉诗文创作已经勃发。《怀风藻·序》中“旋召文学之士,时开置醴之游。当此之际,宸翰垂文,贤臣献颂。雕章丽笔,非唯百篇”描写的便是此间的文学盛况。[注]小岛宪之校注《怀风藻·文华秀丽集·本朝文粹》,日本古典文学大系第69卷,1964年。赋得诗作为一种需要多人分题或分韵赋诗的诗类,本身就与文人宴会紧密相关,因此已经具备了诞生的客观条件。不幸的是,“时经乱离,悉从煨烬”,壬申之乱中,日本汉诗大量失毁,天智天皇时代是否有赋得诗问世已无从考证。直到在公元751年编纂的汉诗集《怀风藻》中,才出现了现存最早的日本赋得诗。
现存奈良时代(710—794年)的赋得诗主要见于《怀风藻》,共八首,均作于神龟三年(726年)为新罗使者萨飡金、造近等人送行的宴会上。[注]据小岛宪之的考证,“于长王宅宴新罗客”诗群的创作时间大概存在三种可能。其一,养老三年五月来朝闰七月新罗贡调使归国,此时长屋王任大纳言;其二,养老七年八月来朝同月归国,长屋王此时任右大臣;其三,神龟三年五月来朝萨飨金造近等七月归国,长屋王此时任左大臣。同时,小岛氏进一步指出,如果从具有宴请新罗使节的资格角度来看,应该是长屋王担任左大臣后的神龟三年最为合适。参见小岛宪之《上代日本文学と中国文学:出典论を中心とする比较文学的考察》(下),1965年。这次宴会在长屋王的宝宅举办,所有存诗皆出自日本文人之手,分别是背奈行文《秋日与长王宅宴新罗客,赋得风字》、刀利宣令《秋日于长王宅宴新罗客,赋得稀字》、毛野虫麻吕《秋日于长王宅宴新罗客,赋得前字》、长屋王《于宝宅宴新罗客,赋得烟字》、安倍广庭《秋日于长王宅宴新罗客,赋得流字》、百济公和麻吕《秋日于长王宅宴新罗客,赋得时字》、吉田连宜《秋日于长王宅宴新罗客,赋得秋字》、藤原总前《秋日于长王宅宴新罗客,赋得难字》。此外,毛野虫麻吕尚有一篇诗序。
“秋日于长王宅宴新罗客”诗群是日本和新罗两国文人相交的产物,因此毋庸置疑具有外交性质。将诗的吟咏作为外交手段的做法,中国在《诗经》时代就已经有了先例,孔子所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即是指此。在唐日交往密切的七、八世纪,“诗赋外交”也是唐王朝“教化四夷”外交策略的重要维度。居于东亚世界核心的唐王朝,对周边国家的思维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而言,对唐王朝先进文学样式的融会贯通水平,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其在东亚世界秩序中的文明开化程度。
就存诗的八位日本文人来看,足以得见日本方面对这次宴会的重视。其一,他们均为身份贵重的官员。除刀利宣令与百济公和麻吕是正六位上的位阶以外,其余六人的位阶都在五位及五位以上,属于贵族官僚。其中,又以长屋王的身份最为显赫,不仅是天武天皇之孙、高市皇子第一子,而且此时已经位居正二位左大臣,是朝廷实际的掌权者。其二,他们均为汉文修养深厚的文人,且经常参加宫廷诗宴。据《续日本纪》记载,背奈行文和毛野虫麻吕还曾因“耀于百僚之内,优游学业,堪为师范”在养老五年(721年)受到元正天皇的嘉奖。[注]参考《续日本纪》,国史大系第2卷,1897年。要之,这八位文人是足以象征日本国家权力和国家文化水准的强大阵容,因此在这样的外交场合,他们诗作的内容和形式都注定是包含政治和外交意识的。
关于此一时期日本对新罗的外交态度,从《续日本纪》中神龟三年新罗使者到日情况的记载可以窥得一二:
夏五月,戊寅朔辛丑,新罗使萨飡金、造近等,来朝。
六月,丁未朔辛亥,天皇临轩。新罗使贡调物。
壬子,飡金、造近等于朝堂。赐禄,有差。
……
秋七月,丙子朔戊子,金、奏勋等,归国。赐玺书曰:敕,伊飡金顺贞:汝卿安抚彼境,忠事我朝。贡调使萨飡-金-奏勋等奏称:顺贞,以去年六月卅日,卒。哀哉。贤臣守国,为朕股肱。今也则亡,歼我吉士。故,赠赙物黄絁一百匹,绵百屯。不遗尔绩,式奖游魂。[注]参考《续日本纪》,国史大系第2卷,1897年。
从“安抚彼境,忠事我朝”“贤臣守国,为朕股肱”中,日本将新罗视为臣属的意识清晰可见,具体到“秋日于长王宅宴新罗客”诗群,这种意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以对初唐诗形式和词句的撷取来表现文化的先进性。初唐诗对奈良时代的赋得诗影响主要有二,其一是分韵作诗的形式。中国赋得诗产生于梁陈时期,绝大多数是分题作诗,分韵作诗则是初唐方才出现的新形式。其二是对唐人诗句的化用。藤原总前《秋日于长王宅宴新罗客。赋得难字》,诗中的“歧路分衿易,琴樽促膝难”和“赠别无言语”句,分别源自骆宾王《秋日别侯四得弹字》中的“歧路分衿易,风云促膝难”和《送吴七游蜀》中的“赠别意无言”。此外,再无明显的影响。与此相对,这八首赋得诗从诗歌规范到审美风格实际上都展现出对六朝诗的效仿,例如五言八句的诗歌体式、压平声的韵部选择,以及典丽的辞藻和对排偶的追求,具体到选词用语上,也不出唐前典籍的范围。以背奈行文的诗为例,诗云:“嘉宾韵小雅。设席嘉大同。鉴流开笔海。攀桂登谈丛。杯酒皆有月。歌声共逐风。何事专对士。幸用李陵弓。”其中,“嘉宾”“小雅”出自《诗经》、“大同”出自《礼记》、“笔海”出自《文选》、“攀桂”出自淮南小山《招隐士》、“谈丛”出自《昭明太子哀册文》、“专对”出自《论语·子路》、“李陵弓”出自《汉书》。总之,在深受六朝诗风诗貌影响这一客观事实面前,对初唐诗的学习只能算是点缀一般的存在。但在关乎国家形象的外交场合中,这种刻意为之的“点缀”是极其重要的。它并不是简单的模仿与借用,而是在众人皆学习六朝诗的时代,通过对初唐诗的“再现”,表达其拥有先进文化的自豪感,目的就是在文明程度上胜新罗一筹。
其次,宾主和谐与压制之意并存。一方面,八首赋得诗描绘出一幅宾主和谐、其乐融融的盛世外交景象,或写宴会的场面,如“杯酒皆有月,歌声共逐风”(背奈行文)、“有爱金兰赏,无疲风月宴”(长屋王),或写对新罗使者的不舍,如“新知未几日,送别何依依”(刀利宣令)、“未尽新知趣,还作乖飞愁”(吉田连宜)。觥筹交错、赋诗咏怀之间,不仅表达出对新罗使者的关怀,更彰显了日本礼仪完备的大国风采。但另一方面,在宾主和谐的同时,也体现出“诗赋外交”的另一面,即通过文化来彰显国力,试图压制对方。毛野虫麻吕所作诗序曰:“文轨通而华夷翕欣戴之心。礼乐备而朝野得欢娱之致。长王以五日休暇。披凤阁而命芳筵。使人以千里羁游。俯雁池而沐恩眄。” 所谓“华夷”,自然是自称“华”而将对方视作“夷”,“沐恩眄”则更流露出日本效仿唐王朝施惠周边的意识。
总之,在生成伊始,日本赋得诗极具公家性格的文体身份就从创作环境、创作主体和创作意图三种角度得以确立。这种与公家意义的密切关系,一方面奠定了它在平安时代前期得以发展的根基,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它在平安中期以后的衰落。
2 平安时代初期赋得诗的新变
平安时代初期的赋得诗主要收录于“敕撰三集”中,其中《凌云集》(814年)收七首,[注]参考塙保己一编《凌云集·经国集·扶桑集·本朝丽藻》,群书类从第8辑,1959—1960年订正3版。《文华秀丽集》(818年)收十一首,《经国集》(827年)收九首。此一时期,曹丕《典论·论文》中的“文章者,经国之大业”成为日本正统的文学观念,汉诗文创作的热情在以皇族为中心的宫廷文人集团中空前高涨。“敕撰三集”的编纂就是在这种经国文学观的指导下完成的,收录在其中的赋得诗则是这种观念的具体实践。总体而言,“敕撰三集”赋得诗在延续奈良时代赋得诗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有了丰富和发展。《怀风藻》中的赋得诗均为五言八句,而在敕撰三集中七言赋得诗已经有十四首之多。在诗歌题材上,出现了咏物、咏史两个新的类别。创作场合大体可以划分为三类,即国家内部的宫廷宴会、国家之间的外交场合及为国家政权选拔人才的取试场合。
2.1 以赋得为题的咏物诗
在平安时代初期的二十七首赋得诗中,咏物诗以十三首的数量占了总数的一半。其中,《凌云集》收六首,分别是嵯峨天皇《九月九日于神泉苑宴群臣,各赋一物得秋菊》和《听诵法华经,各赋一品,得方便品,题中取韵》、淳和天皇《九月九日侍宴神泉苑,各赋一物,得秋露,应制》、良岑安世《九月九日侍宴神泉苑,各赋一物,得秋莲,应制》、小野岑守《九月九日侍宴神泉苑,各赋一物得秋柳,应制》和菅原清宫《九月九日侍宴神泉苑,各赋一物,得秋山》;《文华秀丽集》收五首,分别是王孝廉《在辺亭赋得山花戏寄两个领客使并滋三一首》、嵯峨天皇《冷然院各赋一物,得涧底松一首》、桑原腹赤《冷然院各赋一物,得曝布水,应制一首》、桑原广田《冷然院各赋一物,得水中影,应制一首》和巨势识人《春日侍神泉苑赋得春月应制一首》;《经国集》收两首,分别是惟春道《七言赋得深山寺应太上天皇制一首》和纪长江《七言奉试赋得秋一首》。
据诗题可知,上述咏物赋得诗绝大多数创作于神泉苑和冷然院两处皇家园林里举办的宫廷宴会上。美景美物向来是宫廷宴饮中绝佳的取题,通过对拟定物象的审美化观察和吟咏,使附着其上的平和世象光辉显现,而贵族文人的共同体正是借此来分享和强化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试看菅原清公的《九月九日侍宴神泉苑,各赋一物,得秋山》,诗云:“三山漂眇沧瀛外,五岳嵯峨赤县中。防霞古松千载翠,待风花叶九秋红。落泉曝布悬飞鹄,晴雨收丝闭薄虹。仁者乐之何所寄,国家襟带在西东。”首联写三山五岳,气象恢弘,中间两联则着眼于古松、秋叶、瀑布、飞鹄等细部,描绘出秋山之艳丽多姿。至于末两句,不仅以文入诗,借用出自于《论语·雍也》的“仁者乐山”而浑化无迹,又以“襟带”喻山川之环绕、以“西东”指四方,将吟咏范围进一步延伸,展现出极其开阔的体物视野。而在这种视野的背后,一个意气风发的主人公跃然纸上。再如创作于同一场合的嵯峨天皇《九月九日于神泉苑宴群臣。各赋一物得秋菊》,诗云:“旻商季序重阳节,菊为开花宴千官。蘂耐朝风今日笑,荣沾夕露此时寒。把盈玉手流香远,摘人金杯辨色难。闻道仙人好所服,对之延寿动心看”。“宴千官”所描绘出的宴饮之盛大,“蘂耐朝风今日笑”对宛如笑靥的风中之菊的勾勒,可以说都流露出嵯峨天皇此时超然自逸的心情。而在神泉苑的宴饮中,不论是菅原清宫吟咏秋山所展现出的意气风发、嵯峨天皇吟咏秋菊所呈现的悠然自得,还是其他宴饮之人对秋莲、秋露等的吟咏中显露出的诸如此类的心理状态,实际上都是以特定眼光去观照景物的产物。宴饮的参与者分享这种景物观照的视角,对事物进行审美的再造,并最终在这个共同体中分享和美化对世界的认识。
2.2 以赋得为题的咏史诗
敕撰三集中的咏史类赋得诗共计六首,分别是贺阳丰年《史记竟宴赋得太史自序传》、嵯峨天皇《史记讲竟赋得张子房一首》、良岑安世《赋得季札一首》、仲雄王《赋得汉高祖一首》、菅原清公《赋得司马迁一首》和野未嗣《七言奉试赋得王昭君一首》。
由诗题可知,上述赋得诗全部与《史记》有关。《史记》自七世纪初传入日本后,[3]12在平安时代成为天皇、贵族的必读书目,讲读《史记》成为宫廷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讲读结束后,天皇往往会举办诗宴,组织臣子以讲读内容为题材赋诗。上述赋得诗的吟诵对象均为《史记》中的人物,从身份上大致可以分为圣主与良臣两类。在诗意的构思与展开上,多数都是首联概括中心观点,再以时间先后顺序来平铺直叙人物事迹,诗人的感想并没有过多地见于文字。钟嵘曾以“质木无文”批评班固的《咏史》诗,这一评语同样适用于这六首咏史赋得诗。但是,由于所选取的《史记》人物本身所带有的理想君臣光辉,因此,吟咏达到的实际效果并非仅仅限于平铺人物事迹——其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君臣之间的政治期待。臣子或通过铺陈圣主事迹来夸赞面前的天皇,或通过吟诵良臣的功绩来树立自己的效仿榜样;而君主则借吟咏良臣对臣子施行教导。如嵯峨天皇《史记讲竟赋得张子房一首》,诗云:“受命师汉祖。英风万古传。沙中义初发。山中感弥玄。形容类处女。计画挠强权。封敌反谋散。招翁储贰全。定都是刘说。违宰劝萧贤。追从赤松子。避世独超然。”全诗以时间为顺序叙述张良自辅佐汉高祖以后的事迹,基本上就是以诗的形式将《史记·留侯世家》中张良的故事陈述了出来。但是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看,在嵯峨天皇对张良事迹的铺叙的表层之下,其实更透露出经历了药子之变的天皇对群臣的期待——既竭忠尽智,又至诚高节。又如仲雄王《赋得汉高祖一首》:“汉祖承尧绪。龙颜应晦冥。豁如有大度。生事未曾宫。住在中阳里。微班泗上亭。吕公惊贵相。王媪感奇灵。望气秦皇厌。寻云吕后停。径关创汉统。军旅入咸京。拨乱资三杰。膺天聚五星。乌江穷楚项。轵道降秦婴。命革登乾极。时平戢甲兵。绦候重厚者。刘氏遂安宁。”全诗基本上也是按时间顺序叙述了汉高祖一生的重要事迹,但是从字里行间,还是可以看出诗人在借汉高祖力平战乱来歌颂嵯峨天皇。
2.3 以“赋得”为题的取试诗
以“赋得”为题的取试诗均收录于《经国集》,共七首,分别是纪长江《七言奉试赋得秋一首》[注]纪长江《七言奉试赋得秋一首》上文同样归入“咏物”赋得诗。、丰前王、小野篁、藤原令绪、多治比颖长四人的同题取试诗《五言奉试赋得陇头秋月明一首》、野未嗣《七言奉试赋得王昭君一首》和野春卿《七言奉试赋得照瞻镜一首》。日本以诗赋取试,始于嵯峨天皇弘仁十一年(820年)。[4]51根据古藤真平的考证,野未嗣和野春卿两首诗的具体创作年代难以确考,其他五首的情况分别如下所示:
弘仁十三年(822年)秋九月,丰前王、小野篁、藤原令绪、多治比颖长《五言奉试赋得陇头秋月明一首,题中取韵限六十字》。
弘仁十四年(823年)十一月二十日前,纪长江 《奉试赋得秋,每句用十二律名字》。[注]古藤真平《八、九世纪文章生、文章德业生、秀才·进士受验者一览》,见《国书逸文研究》,1991年。
据此可以看出,“赋得”的形式在日本推行以诗赋取试的制度后不久就已进入这一场合。相较于宫廷宴会中的赋得诗创作,取试场合中的赋得诗的游戏色彩相对弱化,严肃性增加,因此作诗规范更加严格。从《经国集》的七首赋得诗来看,这种规范主要体现在对用韵和句数的限定上。例如,纪长江的《七言奉试赋得秋一首》题下自注:“每句用十二律名字”;丰前王等四人的同题取试诗《五言奉试赋得陇头秋月明一首》题下自注:“题中取韵限六十字”;野未嗣的《七言奉试赋得王昭君》题下自注:“六韵为限”;野春卿的《七言奉试赋得照瞻镜一首》题下自注:“各以名字为韵八韵为限”。限制增多,意味着在遣词造语和谋篇布局上向创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客观上有助于锤炼诗艺。
上述七首赋得诗中,纪长江的《七言奉试赋得秋一首》和野春卿的《七言奉试赋得照瞻镜一首》与普通的咏物赋得诗并无大的区别,野未嗣的《七言奉试赋得王昭君》也与咏史赋得诗相类。从取题方式的演变脉络来看,值得注意的主要是四首以“陇头秋月明”作为诗题的赋得诗。“陇头秋月明”是初唐诗人杨师道《横吹曲辞·陇头水》的首联,杨诗云:“陇头秋月明,陇水带关城。笳添离别曲,风送断肠声。映雪峰犹暗,乘冰马屡惊。雾中寒雁至,沙上转蓬轻。天山传羽檄,汉地急征兵。阵开都护道,剑聚伏波营。于兹觉无渡,方共濯胡缨。”从古人诗作中选取一句作为诗题的做法,客观上需要做到两点,即把握原句意蕴和在此基础上巧妙构思、进行适度的生发。日本这四首以“陇头秋月明”为题的赋得诗,摄取了《陇头水》的吟咏空间——清冷秋月下的陇头夜色,笔触主要集中于对月色的描绘。如丰前王的《五言奉试赋得陇头秋月明一首》,诗云:“桂气三秋晩。萱阴一点轻。傍弓形始望。圆镜晕今倾。漏尽姮娥落。更深顾免惊。薄光波里碎。寒色陇头明。皎洁低胡域。玲珑照汉营。誓将天子釰。奴髪独横行。”全诗除尾联以外,字里行间均是对月色的描绘。相较于杨诗以一半篇幅的叙事将诗境引向现实意义的抒发,丰前王的这首诗更像是在纯粹描绘一个借冷月清辉构建的想象空间,结尾处虽写人事,其意义却只在于给诗境增添一个已然景物化的人物。又如藤原令绪的《五言奉试赋得陇头秋月明一首》,诗云:“箫关天气冷。陇上月轮明。皎皎含冰白。辉辉入镜澄。凌霜弓影静。裛露扇阴清。彩比齐纨洽。光同逍璧生。珠华浮雁塞。练色照龙城。忝预昭君曲。长随晋帝行。”藤原诗依旧是围绕皎洁的月色进行铺陈,尾联中的昭君、晋帝作为点缀存在。至于小野簧与治颖长的诗作,也大体相似。这类以古人诗句为题的诗歌,在中国诗歌发展过程中曾遭到许多批评,如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就认为,“至唐人有五言八韵之试帖,限以格律,而性情愈远。且有‘赋得’等名目,以诗为诗,犹之以水洗水,更无意味。从此,诗之道每况愈下矣。”[5]228但在日本,以古人诗句为题却成为平安后期汉诗创作中的极其流行的取题方式——句题诗。
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赋得”类取试诗是同题共作,因此相较于此前分题或分韵成诗的赋得诗已经有了区别,而这“分题”“分韵”向“同题”的转变,恰恰代表着此后赋得诗的演变方向。
3 平安时代中期赋得诗的转向
平安时代中期的赋得诗主要收录在《菅家文草》、《田氏家集》和《江吏部集》等私家集中。例如,《菅家文草》收七首,分别是菅原道真的《赋得赤虹篇》、《赋得咏青》、《赋得躬桑》、《赋得折杨柳》、《赋得麦秋至》、《赋得春深道士家》和《赋得春之德风》。《田氏家集》收四首,分别是岛田忠臣的《赋得咏三》、《赋得秋织》、《赋得草木黄落》和《省试赋得珠还合浦》;而《江吏部集》收一首,即大江匡衡的《五言奉试赋得教学为先》。总体而言,相较于平安前期,此一时期的赋得诗在数量上大为减少,值得关注的主要是创作场合和取题方式的转向。
奈良时代与平安时代前期的赋得诗,绝大多数是在宫廷宴会和外交场合中产生的。但是进入平安中期以后,“赋得”的诗歌创作形式已经逐渐脱离了原有的宫廷创作环境,而主要以“同题共作”的面貌在取试场合中延续了下来。受私家集的性质影响,上述《菅家文草》等诗文集中,不仅收录了正式的应试诗,还收录了为应付考试在家中写的习作。例如,《菅家文草》的《赋得赤虹篇》诗题下有注云:“七言十韵,自此以下十首,临应进士举,家君每日试之。虽有数十首,采其颇可观,留之”,此后连录《赋得咏青》《赋得躬桑》《赋得折杨柳》三首,就是从数十首习作中选取的“可观”之作。
相较于前述《经国集》中的取试赋得诗,平安中期的这类赋得诗的作诗要求更为严苛,甚至具有了文字游戏的色彩。例如,大江匡衡的《五言奉试赋得教学为先》,作诗要求是“八十字成篇。每句用仲尼弟子名。”诗云:“有时欢受赐。何日忘研精。照卷月清洁。拾萤火灭明。文求无堕地。贤愧不齐名。岂敢非来学。谁应得退耕。”诗题“教学为先”出自于《礼记·学记》,即“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在《艺文类聚·礼部上》《通典·礼十三》等类书中也有收录,强调教育作为治国安民的第一要务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反观《五言奉试赋得教学为先》一诗,虽然满足了“每句用仲尼弟子名”的硬性要求,从首联到尾联依次使用了端木赐、颜何、廉洁、灭明、冉求、宓不齐、秦非和冉耕八位仲尼弟子的名字,诗意的表达也较为流畅,但并没有做到深刻把握“教学为先”的意旨。这说明如果作诗的限制过于严格,那么即使才智超群的诗人也很难在细密的条框之中写出佳作。
除作诗场合外,赋得诗在这一时期的转向还体现在诗题的选取上。《怀风藻》和“敕撰三集”中的诗题,除咏史类和为数不多的几首以古人诗句为题的赋得诗外,大多诗题直接来自于现实生活。而在平安中后期,出于考试的客观需求,诗题多从《文选》《艺文类聚》《淮南子》等中国典籍中选取。这些诗题或是一种情境,如“草木黄落”;或是一种事理,如“教学为先”;又或是一个故事,如“珠还合浦”。不论是哪一类,都需要诗人在充分理解诗题在典籍中的意涵的基础上,再进行巧妙的艺术构思。难度虽然增加了,但也不乏佳作。试看岛田忠臣的《赋得草木黄落》,诗云:秃树飘丛每日催。应似老翁衰发变。不同年少醉颜颓。桑林且尽非蚕食。荻浦初空是雁来。葵藿莫愁逢燥气。太阳有意煦寒栽”。“草木黄落”首次出现是在《礼记·月令》中,“是月也,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在汉武帝《秋风辞》中第一次入诗,即“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并被收入《文选》。在先秦至唐的典籍中,“草木黄落”作为秋天的象征性意象,在《淮南子·时则训》《吕氏春秋·九月纪》《逸周书·时训解》《黄帝内经·六元正纪大论》《艺文类聚·祭祀》《艺文类聚·草》等书中均有收录。岛田忠臣的《赋得草木黄落》一诗,上篇紧紧围绕“草木黄落”这一象征秋之萧瑟、衰飒的意象展开铺陈。下篇在上篇的基础上展开,继续对相关秋景进行描绘,但又一改上篇的衰飒之感,转而以“雁”、“葵”、“藿”与“太阳”四个意象营造出秋天温暖的一面,可谓是相反相成、相得益彰。相比之下,岛田忠臣的另一首赋得诗《省试赋得珠还合浦》就稍见逊色了。诗云:“太守施廉洁。还珠自效珍。光非怀汉女。色似泣鲛人。旧浦还星质。空涯返月轮。行藏犹若契。隐见更如神。感化来无胫。嫌贪去不亲。希哉良史迹。谁踏伯周尘。”“珠还合浦”原出自《后汉书·循吏传·孟尝》:“(合浦)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阯比境……(孟)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此后,这一故事被后世许多诗人吟咏,[注]例如,王维《送邢桂州》、杜甫《广州段功曹到得杨五长史谭书功曹却归聊寄此诗》等。在《艺文类聚》等类书中也有收录。岛田忠臣的《省试赋得珠还合浦》虽然将“珠还合浦”的故事交代得较为清楚,但从整体结构上来看,第一联叙写太守孟尝的廉洁,第二、第三和第四联着眼于描绘明珠的光彩,末两联又继续对太守的廉洁进行描写,稍显杂乱。
奈良时代至平安时代的赋得诗演变轨迹,上文已经作出基本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尚需探讨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个即日本赋得诗在平安中期淡出宴会场合的原因。这里首先需要明确一点,即赋得诗是产生于中国的文体,其包含“皇族的参与”、“宫廷文化的构建”和“国家意识的认同”等内涵在内的文体身份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就已确立。对于日本文人而言,不论是在宫廷宴会中通过赋得诗创作来参与构建宫廷文化,还是在外交场合将赋得诗作为表达国家意识的载体,实际上都是对中国赋得诗创作的模仿。这种模仿的热情直接来自于唐王朝在东亚世界的核心地位,创作赋得诗就等同于对唐王朝先进文化表达方式的积极实践。然而,随着九世纪中叶唐王朝的国立衰减和随之而来的灭亡,其在东亚世界的文化向心力已经逐渐减弱,日本不再对唐亦步亦趋。作为完全中国化的作诗形式,赋得诗淡出日本的文化舞台是必然趋势。此外,平安前期宫廷宴会频繁举办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以及和歌在宫廷宴会中的抬头,都加速了赋得诗退出宫廷宴会的历史进程。至于赋得诗在日本外交场合中的消失,则主要是由于同处于东亚汉文化圈的新罗和渤海两国在十世纪上半叶的相继灭国——日本实际上已经不再有外交场合了。
第二个问题即从本身的文体特征来看,赋得诗的创作场合转向取试场合意味着什么?作为一种起源于以皇族和贵族为中心的文人集团唱酬活动的诗体,赋得诗在吟咏内容上并没有特别的要求,在演变的各个阶段几乎都不出时代的吟咏范围之外。它之所以可以作为一种单独的文体存在,主要是由于其多人分题、分韵作诗的群体交游特质,俞越《茶香室丛钞》概括为“题非一题,人非一人”。[6]1679在淡出宫廷宴会和外交宴会的同时,尽管这一全然中国化的诗歌创作形式依然能在取试场合留存,但是,取试场合的赋得诗却是完全意义上的同题作诗。这些诗题虽然被冠以“赋得”的名目,但是“赋得”在其中已经不再具有“赋诗得某题”的意涵。而一旦缺失了这种指向群体性的意涵,赋得诗就变成了一种可以独自一人创作的诗体,这就与其本来的公家性格背道而驰。也就是说,取试场合的赋得诗,就文体性质而言,已经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赋得诗了。
4 结 语
文体的国际移植及其在异国的生长和演变往往不是单纯的文学事件,而是包含着丰富的政治、外交和文化信息。日本赋得诗在奈良和平安时代的衍生和演变,实则折射出的是日本文人借由赋得诗高贵的文体样貌来构建主流官方话语的历史轨迹。这一来自中国的文体在日本皇族和贵族交游中的流行程度,明显与唐帝国在东亚世界轴心力量的强弱具有逻辑上的对应关系。政治意涵已经植入文体内部,因此对这一文体被日本文人接受、使用和弃用的考察,就成为还原特定历史年代政治和外交风貌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