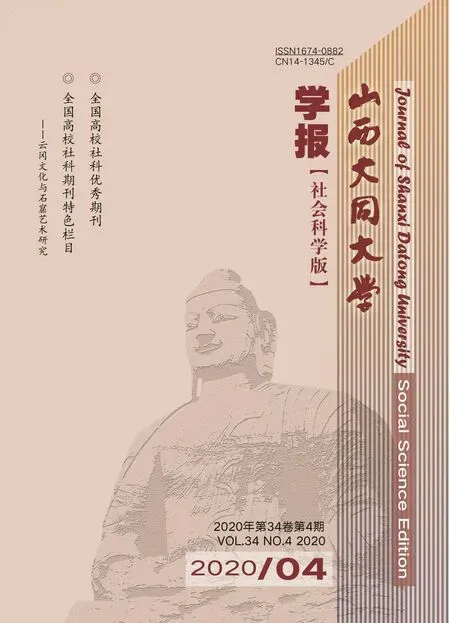试论《魏书·官氏志》的创作意图及价值
王宵宵,胡祥琴
(北方民族大学民族学学院,宁夏 银川750021)
《魏书·官氏志》是《魏书》十志之一,是魏收根据鲜卑拓跋部汉化的实际状况而新创的体例,该志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记载了北魏建国之前的官制情况及建国后改革官僚制度的过程,第二部分主要记述鲜卑拓跋部氏族变化的情况。《官氏志》首次将氏族列于正史,这是其创新之处。氏族是否应该列于正史,后世学者多有争论,刘知几认为“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于《百官》之下。”[1](P68)然而浦起龙在注解中却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并不赞同刘知几这一观点,认为氏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的产物,不应列于正史。后世学者多数认为氏族不应被列于正史,因此《官氏志》是正史中唯一一部用“志”的方式记述氏族的专篇,具有特殊的价值,林传甲先生就认为“魏书文体惟官氏志最重”,[2](P130)针对《官氏志》本身的研究并不多,大部分都是在研究《魏书》的基础上,对《官氏志》进行简单的介绍与评价,如张峰《〈魏书〉的编纂特色与史学价值》[3],王志刚《试论〈魏书〉典志的历史编纂学价值》[4]等。胡鸿《北魏初期的爵本位社会及其历史书写——以〈魏书·官氏志〉为中心》[5]以《官氏志》为中心探讨了北魏初期的爵制及魏收的书写方式。这些著作虽然都涉及到《官氏志》,然而专门研究《官氏志》的论著并不多见,本文试图通过对《官氏志》的撰述意图及内容进行探讨,以期进一步发掘其历史的和史学的价值。
一、魏收及《魏书·官氏志》的创立
魏收(507—572),字伯起,钜鹿下曲阳县(今河北晋州市)人,生于北魏宣武皇帝正始年间,卒于北齐后主武平年间,一生历北魏、东魏、北齐三朝。他追述自己的祖先为汉初的魏无知,①从其曾祖父魏歆开始,家族世代为官。魏收的曾祖父魏歆“博洽经史”。[6](P2321)其父魏子建曾平定氐人叛乱,回到洛阳后,累迁常侍、卫尉卿、右光禄大夫,后又任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品行端正,“正身洁己,不以财利经怀。”[6](P2323)生于官宦家庭的魏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在自序中说自己“年十五,颇已属文。”[6](P2323)魏收年少时已经颇具文采,并且喜欢骑射,后弃武专心于读书,遂以文华显,“与济阴温子昇、河间邢子才齐誉,世号三才。”[6](P2325)北魏节闵帝普泰年间,魏收“迁散骑侍郎,寻敕典起居注,并修国史。”[6](P2324)这是魏收修史的开端。东魏和北齐时,魏收曾任重要的官职,但都兼任史职,北齐文宣皇帝天保二年,奉命编纂魏史,这时他已经有数十年接触魏史的经历,也就为他著述魏史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经验。天保五年三月,撰成纪、传,共110卷,十一月完成十志,创设《释老志》、《官氏志》。
魏收创作《官氏志》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记载官职制度有前例可循。《隋书·经籍志》对汉代以来的官职撰述情况有详细解说:“今《汉书·百官表》列众职之事,记在位之次,盖亦古之制也。汉末,王隆、应劭等以《百官表》不具,乃作《汉官解诂》《汉官仪》等书。是后相因,正史表志,无复百僚在官之名矣。”[7](P969)可见,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已有对于官制的记载,并使官制内容在正史中有了一席之地,不过以“表”来记载官制的时间并不长。汉末时,王隆、应劭等人认为《百官表》不够完备,不足以记录官制情况。在这种背景之下《百官志》应运而生并最终取代了《百官表》。司马彪作《续汉书》,首创《百官志》,其后史家多有效仿,如沈约《宋书·百官志》,萧子显《南齐书·百官志》。魏收遵循已有的惯例,将官制列入《魏书》,并以“志”的形式书写。第二,根据实际情况创设氏志。魏收在《前上十志启》中表述创作《官氏志》的原因,“时移世易。理不刻船,登阁含毫,论叙殊致。《河沟》往时之切,《释老》当今之重,《艺文》前志可寻,《官氏》魏代之急,去彼取此,敢率愚心。”[6](P2331)为什么魏收舍弃了《艺文志》而撰写《官氏志》?秦始皇焚书、项羽火烧秦王宫,使先秦的文化典籍遭到严重的破坏。汉朝建立以来,广收散佚的典籍。汉武帝时还设立了“写书之官”,文献数量不断增加,而且有编次错乱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之下,刘向父子奉命对文献进行了整理和编纂,并撰著《七略》,班固在此基础之上创作了《艺文志》。反观北魏,北魏占有的北方自西晋以来,战争频仍,文献数量不多,远不如汉代浩繁,撰写《艺文志》有所欠缺。官制在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官志书写毋庸置疑。“收以魏初部落之众,最重族姓;其后孝文改代姓从华俗又多纷扰。”[8](P281)北魏有重视族姓的传统,之后孝文帝又进行了姓氏的变革,这是北魏特有的现象,于是魏收将其列入了《魏书》。魏收继承志书的传统,而不固守传统,舍弃了《汉书》中的《沟洫志》、《艺文志》,极有卓识地根据北魏姓氏改换及兴衰存灭的实际情况将‘官’与“氏”合为一志,创立《官氏志》,这符合刘知几所说的“窃以国史所书,宜述当时之事”[1](P52)的作史原则。魏收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重要内容,具有极强的史家自觉意识。
二、《魏书·官氏志》的创作意图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新的政权建立以后,往往会寻求合法性的依据,以期巩固统治。史官作史时往往也会有此倾向,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等,都有为政权服务的色彩。魏收编纂《魏书》也不例外,在书写《官氏志》时有意向中原文化靠拢,以证明北魏是中原先进文化的继承者,进而确立北魏的正统地位。
魏收在《官氏志》开头就说明了自己作官志的意图“书契已外,其事蔑闻,至于羲、轩、昊、顼之间,龙、火、鸟、人之职,颇可知矣。唐虞六十,夏商倍之,周过三百,是为大备。而秦、汉、魏、晋代有加减,罢置盛衰,随时适务。且国异政,家殊俗,设官命职,何常之有。帝王为治,礼乐不相沿;海内作家,物色非一用。其由来尚矣。”[6](P2971)百姓不能自己治理国家,所以需要君主管理事物,君主不能独断,所以需要官员辅佐。官制法令在安定国家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没有书契的记载,无法了解官制的情况。官制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断地变化,官职名称也并非完全相同。如果不把官制记载下来,那么就没办法让后人了解这一时期的状况。同时也可以看出,设官命职由来已久,代代相传,尽管北魏崛起于朔北,不过“及交南夏,颇亦改制”。[6](P2971)北魏对官制的重视程度与中原一致,之后的一系列改革和发展是对中原官制的继承和创新。魏收的这一意图与《后汉书·百官志》有相似之处,“昔周公作《周官》,王室虽微,犹能久存。今其遗书,所以观周室牧民之德既至……所以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学汉官篇》,诸文倜说,较略不究。唯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记汉承秦置官本末,讫于王莽,差有条贯;然皆孝武奢广之事,又职分未悉。世祖节约之制,宜为常宪,故依其官簿,粗注职分,以为《百官志》。”[9](P3005)周公作《周礼》,使周朝拥有礼乐制度,这一制度维持了周朝长盛不衰,有《周礼》遗留下来,所以才能看到当时周朝礼乐制度的情况。司马彪也强调法令制度的重要性,同时也认为官制应该载入史册。也就是说,魏收和司马彪都希望通过载入史书的方式,能当时官制的相关内容保留下来,以供后人查阅借鉴。此外,还可以发现,司马彪也认为官制是承袭并不断变化的,“汉之初兴……法度草创,略依秦制,后嗣因循。至景帝,感吴楚之难,始抑损诸侯王。及至武帝,多所改作……世祖中兴,务从节约,并官省职。”[9](P3555)只不过司马彪仅把官制的继承和发展限定在汉代,不像魏收追述到远古时期。司马彪首创《百官志》,完全是以正统王朝的视角来书写的,魏收创作官志的旨趣与其有相似之处,可以推论魏收赞同这一视角,甚至可以说魏收认为北魏就是正统。
与记载官制的情况类似,记载氏族之前也有一句话追述氏族的由来。“自古天子立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则以家国与谥,官有世功,则有宦族,邑亦如之。”[6](P3005)这句话改编自《左传》,鲁隐公八年,无骇去世,羽父请求鲁隐公为无骇赐姓,他向众仲询问相关情况,众仲回答“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10](P10)如果说,魏收和司马彪作官制的旨趣只是有相似之处,那么这句话就可以看成魏收对《左传》的照搬,只改动了部分的字句,其含义完全相同。《左传》既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儒家经典著作,继承《春秋》大义。魏收直接改用了其中的内容作为《氏族志》的开头,说明魏收对于中原文化的认同。接下来魏收描述北魏的情况,“魏氏本居玄朔……安帝统国,诸部九十九姓。至献帝时,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氏。自后兼并他国,各有本部,部中别族,为内姓焉。”[6](P3005)北魏先祖居住在偏远地区,赐姓氏还没有完整的体系,安帝时已经有了九十九姓,献帝时,根据土地、功绩有了氏、族,这明显符合《左传》中赐姓命氏的记载。北魏先祖很早就认同了中原文化,并改造自己的制度,北魏建立之后,自然也会承袭这一制度,具有浓厚的中原色彩。北魏虽然是鲜卑族建立的,然其在发展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中原的文化。
《官氏志》的一个特点就是大量使用了“比”字,将拓跋官职“比”中原官职,如“蒙养职比光禄大夫”。[6](P2976)魏收以这样的方式书写官制,一是因为拓跋部的官职名称及设置有其自身的特色,用这样的方式便于理解拓跋族官职的具体职能。二是因为有意向中原官制靠拢。魏收用鲜卑官职比中原官职,存在着两种情况,第一,鲜卑官职与中原官职并存,即两者都确实存在。第二种情况,用来比况的中原官职名称是存在的,有学者认为魏收大量使用“比”的手法,有攀附华夏之嫌,“《魏书》以一些不存在的汉晋官名替代那些不雅观的真实官名,代替的结果,造就了拓拔政权从一开始就是华夏式政权的形象。”[5]也就说魏收用了“比”的手法,使北魏的官职制度从起初就具有中原官职制度的样貌,有意引导读者产生一种假象。魏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使拓拔政权更接近与华夏政权,也是在为北魏寻求政权合法性的依据。“魏收强调地域差异和文化高下是判别华夷的主要准则。”[11](P303)北魏占据的地区本来就是正统王朝所在之处,在地域上就具有优势。此外,如果在文化制度方面也继承中原传统,无疑更加有利于确立北魏的正统地位。
三、《魏书·官氏志》的价值
《官氏志》是魏收新创的体裁,不仅丰富了史学的发展形式,而且对后人了解北魏鲜卑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保留了鲜卑的发展状况,同时保存了同时期其它部落的资料。
(一)研究北魏政权官制和氏族发展的重要史料 《魏书·官氏志》最主要的目的在于记载北魏的官制、姓氏,这就使得《官氏志》成为研究北魏官制和氏族必须要参考的史料。《官氏志》中对于官制的记载十分详细,设置的时间、名称、品级均记录在册,不管是对北魏整个官职制度的的研究还是某一官职的研究都大量使用了《官氏志》里的相关内容。《官氏志》中虽然详细列出了官职,但是有些官职见于纪、传,却不见《官氏志》,有些官职名称还有些许的不同,这就为北魏官职的考释提供了资料,随着北魏碑刻的出土,出现了文本与碑刻互相印证的研究,如张庆捷、郭春梅的《北魏文成帝〈南巡碑〉所见拓跋职官初探》。北魏官制的研究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官氏志》中官职的价值,在此不再赘述。
《官氏志》中除了对官职的记载之外,还记载了北魏时期的爵位制度,据统计,直接有“爵”字眼的共有10 处,其中2 处为“光爵”,“光爵”为官职名称,也就是说有8 处与爵位相关,最早的一条为道武帝“天兴元年十一月,诏吏部郎邓渊典官制,立爵品。”[6](P2972)道武帝令邓渊制定官制和爵位制,这就说明北魏建立初期,实行官制与爵位并行的制度。下一条出现于道武帝天赐元年九月,对爵制进行了调整,把原来的五等之爵分为王、公、侯、子四个品级,同时对这四个品级的授予进行了调整,只有皇子和上勋者才有资格被封为王,其余有爵位者依次下调一个等级,王爵之所有等级中最高的一级,这一调整就使得与皇帝有密切关系的人具有显赫的地位,即使是宗室子弟也不能与之平起平坐,这无疑有益于皇权的加强。之后相关的记载也是不断调整爵制的过程,可以看出明显的趋势,爵位的赐封越来越严格,看重实际的能力,孝文帝延兴二年下诏“非功无以受爵……旧制诸镇将、刺史假五等爵,及有所贡献而得假爵者,皆不得世袭。”[6](P2975)没有功劳的人不能授予爵位,假爵也不能世袭,这样就有效地控制了获得爵位的人数。最后一条记录出现于太和十六年“改降五等,始革之,止袭爵而已。”[6](P2976)北魏旧制,以勳赐官爵的人,其子孙可以承袭军号,这一改革之后,“使授予爵位与将军号分离,封授诸王加拜将军号的制度也就同时取消了。”[12]另有其它无“爵”字,但与爵位相关的语句,“十二月,诏始赐王、公、侯、子国臣吏,大郡王二百人,次郡王、上郡公百人,次郡公五十人,侯二十五人,子十二人,借立典师,职比家丞,总统群吏。”[6](P2974)从中可以窥见王、公分为不同的等级,王分为大郡王、次郡王,公分为上郡公、次郡公,而侯、子没有再次分等级。这就为研究北魏的爵位提供了相关的资料。
《官氏志》后半部分为氏族专篇,也是正史中独一无二的姓氏专志,其中记载了118 个姓氏,先写明鲜卑旧姓,每一姓后写明改姓后的汉姓,一一对照,十分便于检索。《官氏志》保留的北魏姓氏不仅为研究北魏汉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且有益于探讨具体姓氏的变化,这方面的价值也早已被学者关注和发现,对姓氏的考释研究较多,最为著名的当属姚薇元先生的《北朝胡姓考》,这本书大量参考了《官氏志》中的相关记载,详细考订了北朝时期的胡姓。为研究氏族提供资料是《官氏志》明显的价值,除此之外还有其它方面的价值。
从《官氏志》中可以看出拓跋族发展的过程。拓跋部原是鲜卑的一支,后来迁往辽西,发展壮大。安帝统国时,诸部共有九十九姓,献帝时“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氏。”[6](P3006)这七族和献帝本族及其叔父的两族,共十族,构成拓跋部的核心族群,也是拓跋部十姓的由来。随着拓跋部力量的增长,实力的增强,不断有新的部族加入,“神元皇帝时,余部诸姓内入者,丘穆陵氏,后改为穆氏……”[6](P3005)神元皇帝力微时期,又有其它部族并入了拓拔族,《官氏志》中记载了76 个新入的氏。另有四方部落的35氏,“四方诸部三十五氏是与拓跋部有同盟关系的氏族,道武帝时终于归属于拓跋部国家,为新加入的氏族。”[13]道武帝时期这四方诸部最终成为编民,由此可以看出拓跋族早期在不断地发展、兼并、扩大,它不仅仅包括拓跋本部,也包含着其它并入的族群,由单一的族群逐渐发展为多元化的族群。
《官氏志》也为研究拓跋族以外的部落提供了资料。姓氏出现的时间非常早,在母系氏族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姓氏,不过早期姓与氏代表着不同的含义。“姓则表其所由生,氏则记族所由出。”[6](P3005)姓代表了个人的血缘关系,氏则代表了宗族关系,三代之后,姓和氏合二为一,具有了双重含义,汉代时普通民众多使用单姓。少数民族多使用复姓、三字姓,“在中国古代,以部落或国名为姓氏的例子极多。”[14]这里的国通常指的是某一个部落,所以《官氏志》当中记载的部分姓氏很有可能代表的是某个部落,而不单单只是姓氏,由拓跋部发展的过程可以推断这些部落也不仅仅是鲜卑部落,还包括其它民族的部落。“破多罗本部落之名,即魏书太祖纪之破多兰部也。”[15](P200)《官氏志》记载破多罗氏后来改为潘氏。破多罗原本是鲜卑的别种,后来被拓跋部打败,纳入到了拓跋部,拓跋与破多罗氏同属于鲜卑,这些记载无疑为研究鲜卑的聚散提供了资料。除此之外,还记述了许多鲜卑以外的部落姓氏,如解枇氏、齐斤氏、独孤氏、须卜氏、宇文氏等,“解枇氏即解批氏,齐斤氏即异奇斤氏,都是加入到拓跋部落联盟中的高车部落。”[16](P64)
这两个姓氏属于高车部落,而须卜氏、宇文氏则属于匈奴部落。《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载:“单于姓虚连题。异性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9](P2944)须卜氏后来改称卜氏。独孤氏出自刘氏,后经几代的变迁,被封为谷蠡王,号独孤部,后来又并入到了鲜卑部落,改称陆。②关于宇文氏,《魏书》当中有相关的记载,“宇文忠之,河南洛阳人也。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世据东部,后入居代郡。”[6](P1795)宇文部原是匈奴的别属,后来入代郡。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虽然《官氏志》只是简单地记载,在哪个皇帝在位期间,有哪些氏族并入,后改为什么汉姓,但也保留了这些氏族部落的相关信息,为研究这些部落提供了佐证。
(二)体现了北魏鲜卑政权汉化的历史进程
汉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封建化和门阀化,“《官氏志》……是反映北魏统治封建化、门阀化的重要文献。”[17](P232)官制的改革最能体现鲜卑族封建化的过程,即从一个具有部落性质的官制逐渐发展成高度集权的官制。《魏书·官氏志》明显地表达出鲜卑逐渐汉化的轨迹,有学者讲到:“《官氏志》的前后两部分,内容上虽各有侧重,但其认同中原传统,表现汉化进程的旨趣却是一致的。”[4]北魏最为人所知的官制改革当属孝文帝时期的改革,由于其影响力巨大,以至于造成一种只有孝文帝进行官制改革的错觉,实际上官制变化很早就出现了,“及交好南夏,颇亦改创。”[6](P2971)《官氏志》传递出这样的历史信息,即北魏原本的政权范围在北方,也有自己的官制,但是和中原接触之后,开始改创官制,《官氏志》记载了这种渐次改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大概经过了三个阶段才完成的。
第一阶段拓跋族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官制,《官氏志》中并没有记载最初设置官制的具体内容,但是从一些语句中可以窥见一二。“初,帝欲法古纯质,每于制定官号,多不依周汉旧名,或取之周身,或取诸物,或以民事,皆拟远古云鸟之义。”[6](P2973)这里的帝指的是道武帝,他最初制定官号的时候,想要按照古法来制定,也就是依照拓拔族的习俗和需要来制定官制,可见拓跋族最初建立官制时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第二阶段保留自身特色,仿照晋制设立官职。这一阶段以部落行政机构为主,并建立具有晋制官名的官职,“这样的官制,其名称虽有一些同于晋制,但并没有封建官制的实质内容。”[18](P294)只是模仿了表面的官职名称还没有改革实质职能。最后一阶段是高度汉化的官制。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孝文帝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鲜卑官制基本被中原官制所代替。孝文帝改革之后,一些具有鲜卑特色的制度被废除,内行官系统③北魏建国时就存在,昭成皇帝时期设置内侍长四人,据严耀中先生的统计,文献可见的担任内行长、内三郎等职位的共有44 人,而汉人担任这些职务的只有3 人,这些职位绝大多数由鲜卑族担任,这显然有排斥汉族的意味。《官氏志》中记载的内行官并不多,但是也记载了“内侍长”、“内署令”、“内部幢将”等官职名称,但是这些官职名称在太和二十三年的官制改革之后,此种名称均不见记载。废除具有民族歧视意味的官职制度,显然更有利于吸收汉人为北魏政权服务,也显示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融合和发展。
南北朝时期的门阀研究,很多集中于南朝而忽略北朝,但是从《官氏志》中也可以窥见门阀之风对北魏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官员的选拔上。昭成皇帝之时设置了近侍的职位,“皆取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仪貌端庄,机辩才干者应选。”[6](P2971)从高门豪族之中选择有才干的子弟担任近侍,不考虑地位较低的人。昭成皇帝是北魏建立者道武帝拓跋珪的祖父,也就是说在北魏正式建立之前,门阀就已经影响到了官职的任命,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北魏始祖神元皇帝时,就派遣其子文皇帝到魏“且观风土”[6](P4)文皇帝回国之后,很有可能将魏实行的制度用于治理国家,到昭成皇帝时,一方面是受到残余的原始宗法氏族的影响,另一方面可能是门阀产生的作用。其次表现在氏族的厘定上。在孝文帝当政之前,汉化就已经开始,也有不少中原人为拓跋政权服务,中原人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往往能够帮助统治者加强管理,这显然会损害到部分鲜卑贵族的利益,统治阶层之中还有其他非鲜卑族的官员,彼此间的冲突显然不利于鲜卑政权的进一步发展。孝文帝迁都之后,脱离了旧势力盘踞的平城,迁到洛阳的贵族也必然面临与汉族高门贵族接触的局面,民族隔阂同样不利于北魏的统治。孝文帝企图消除统治集团内的这种隔阂,将鲜卑贵族门阀化,企图以这样的方式拉近民族间的距离。太和十九年下诏“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热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6](P3014)将太祖以来功勋卓著的鲜卑八姓定为高等,与四姓享有同样的权力,这四姓主要是汉族。除了四姓、八姓之外,其它宗族按照先祖的官职地位分别列入姓和族,五世之外的不在此列。“一般本族人民被排斥在姓族之外,他们和本同一源的贵族分割开了,成为编户与庶姓。”[19]经过氏族的量定,鲜卑内部也存在着高门和寒门,拥有各自的谱状,氏族高下一旦确定,官制地位与婚姻也随之确定,这与南朝的状况别无二致,甚至更严格,南朝并没有以皇帝诏书的方式规定氏族的高低。到世宗朝时,仍有姓族争论发生,又进行了第二次的厘定,以解决纷争,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门阀制度。
无论是官制的改革还是氏族的厘定,都体现了鲜卑拓拔族不断汉化的进程,但并不意味着拓拔族抛弃了所有鲜卑的习俗,也并不意味着鲜卑创造的某些制度是落后的,“前世职次皆无丛品,魏氏始置之,亦一代之别制也。”[6](P3003)北魏将官阶分为正、从,如正一品、从一品,这一制度为北魏创设,且为唐朝所沿用。各民族在接触碰撞之间产生了新的有益于继续发展的因素,“北方少数民族的部落制度与华夏制度的剧烈碰撞,最终在北方地区激发出了新的变迁动力和演进契机,交替‘胡化’和‘汉化’孕育出了强劲的官僚制化运动,他扭转了魏晋以来的帝国颓势,并构成了走出门阀士族统治、通向重振的隋唐大帝国的历史出口。”[20](P131)
综上,《魏书·官氏志》是北魏发展过程中特殊政治文化的产物,是基于时代背景下的史学叙事方式,反映了魏收把握时代特征的自觉意识。从《官氏志》中可以看出魏收对于中原文化的认同,他在书写过程中有意靠近中原文化,并运用了“比”的手法,将鲜卑官职与中原官职挂钩,造就拓跋政权是中原制度和文化继承者的形象,达到为拓跋政权寻求正统地位依据的目的。作为民族史专志,该志不仅保留了拓跋政权的官制和氏族资料,而且体现了其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与其它民族间的交流和碰撞,同时体现了拓跋部逐渐汉化的过程,是研究鲜卑拓跋部汉化及与周边民族发展交融的重要史料。
注释:
①洪迈认为此说法不准确,并借此证明魏收作史不实,参见洪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47页。
②参见欧阳修《新唐书》卷75,《宰相世系表五下》独孤氏条,中华书局,1975年,第3437页。
③北魏前期官制分内、外、地方三个部分,由于内官员的官职名称一般会加上“内”、“内行”等字样,以区别于其它并存的官职,所以称作内行官系统。参见严耀中:《北魏内行官试探》,《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4年。